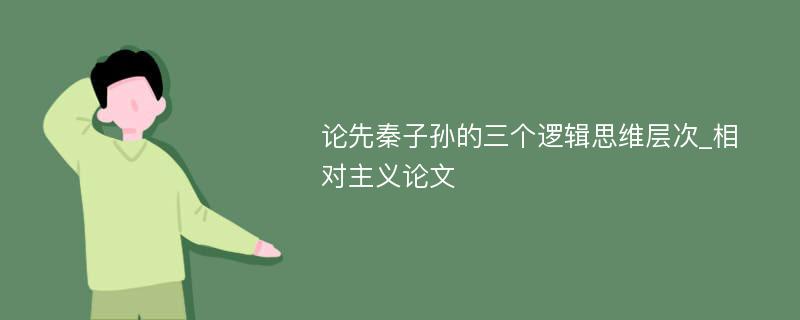
论先秦诸子的三种逻辑思维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先秦论文,三种论文,逻辑思维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674(2000)01—0001—05
先秦诸子中儒、墨、名、法等诸家,都各有辩资,但是在逻辑思维方面影响较大的仍是道、法二家。总括先秦诸子在逻辑思维方面的论述,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是“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形式,第二是“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第三是“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形式。
“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形式以法家韩非为代表,中文“矛盾”一语即出于韩非。“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层次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就是形式逻辑所说的“矛盾律”。
法家又称形(刑)名家。《史记》说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又说申不害“主刑名”。刘向《新序》说“申子之书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司马谈《六家要指》说名家专决于名,“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所说的名家指的就是形名家,不是倪说、惠施、公孙龙等的名家。形名思想在法家学说中踞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法家理论的核心。
韩非十分注重名实关系,有很多逻辑推理方面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如“自相矛盾”、“郑人买履”、“郢书燕说”等,今人往往当作寓言看待,实际上都是严格的逻辑推理,而且目的所指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司马迁所特别慨叹的《说难》篇,其核心实际上也是在名实关系一点上。
《韩非子·难一》(又见《难势》):“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如何?”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注:马叙伦《庄子义证佚文》辑佚《庄子》有“陷大矛”一语,并以楚人卖矛及盾者作注,事无旁证。庄子是否也讲过“矛盾”一事,尚不能肯定。)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争鸣,其争鸣对立之处即在“矛盾不相容”上面。晏子之批评孔子,孟子之抵距杨墨,荀子之非难十二子,韩非之批驳儒墨五蠹,李斯之禁百家语,司马迁所说汉初之儒道互绌,实际上都不离“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层次。
“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以老庄为代表,即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互为成立的条件,同为相对而存在,对此老庄二人都有论述。
《老子·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注:帛书《老子·章》有“有无相生也”,郭店竹简《老子》有“又亡之相生”,与传本基本无异。)
《老子·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此处的有和无,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和没有的意思。老子的原意是说,美与恶,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音与声,前与后,都是相互依存的相对的概念。对立的双方如果各自偏执于自己的一方,就会使双方都不能存在。强调了自己,否定了对方,对方失去了,自己的一方也不复存在。“反者道之动”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和自己对立的一方实际上是支持了自己。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天下大乱,道德不一,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注:《庄子·天下》、《庄子·齐物论》。)。由于诸家各持一说,互相非难,于是就产生了诸如“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注:《庄子·齐物论》。)的问题。为此老庄提出了“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对“矛盾不相容”的逻辑思维形式进行批评,其中尤以庄子的批评最为激烈。
庄子认为,事物的个性和各自的原则,包括各家各派的是非之争,不能作为衡事物存在的根据和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是因为:
第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究竟有没有是非的分别,彼此二者不能互证。
《齐物论》:“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
第二,是非不是绝对的。互相“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此所以是所以非,是由于彼此各有是非的。是非出于彼此各自自身,因此彼此同样都不具有普遍意义。
《寓言》(《齐物论》略同):“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秋水》:“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第三,彼此虽然对立,却又互为存在的条件。
《齐物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方方可。”
《秋水》:“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迄今为止,学术界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老子的上述思想叫做“朴素辩证法”,或把老子和庄子的上述思想叫做“相对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庄子”条目(冯契撰)认为:庄子在认识论方面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庄子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他看到一切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又同书“相对主义”条目(林青山、李景源撰)解释相对主义为:“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本身及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客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相对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它是诡辩论、不可知论、唯心主义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在中国,老子和庄子辩证法思想中也包含了相对主义的因素。”
以上这二处对庄子和庄子“相对主义”的论述并不符合庄子哲学的本意,因而并不能反映庄子哲学的真实内容。因为第一,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在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有其独特的地位和独到的贡献。正如冯契自己所说:“庄子的相对主义起着反对主观主义的作用,是哲学向辩证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先秦诸家在认识论上都有独断论的倾向,而庄子则认为经验和理性都是相对的。从而否定了人们认识上的‘独断的迷梦’。”(注:冯契《对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一点分析》,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9期。 )李震也说:“笔者以为庄子泯是非之说,并不意谓庄子在知识方面的怀疑论,而在于肯定感性和理性认识之限度。庄子所追求的真知是绝对性的,亦即有关‘道’的认识。‘道’不是理智分析的对象,‘道’超越了是非相对的层面。”(注:李震《中外形上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出版。)第二,庄子哲学的核心是他的形而上学抽象思辩的本体论,也就是“道论”,而不是用来建立这“道论”的认识论、方法论。“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注:《庄子·外物》。)即使是专论庄子学说的认识论、方法论,庄子由以建立“道论”的方法论也不是“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而是“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形式。第三,所谓“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它的作用只是用来批驳儒墨,并与“儒墨之是非”一起被共同否定掉了。“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形式才是正面的概念,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则是一个反面的概念,在整个庄子学说中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
“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具有更充分的思辨因素,从哲学的意义上看,较之“矛盾不相容”逻辑思维形式更高一层。但是因为“有无相生”的双方既不能进行肯定判断,也不能进行否定判断,双方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美与恶、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无论其美、善、有、易,或者恶、不善、无、难,都不具有绝对的性质,因此都没有意义。《老子·二十章》又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唯与阿都是叹词,是答应的声音,唯是正常情况下的答应,阿有谄谀的意思。唯与阿,善与恶,同样是偏失,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庄子·盗跖》:“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君子与小人各失其性,同样没有意义。因此,在“有无相生”的逻辑论证中,就存在了一个内在矛盾。实际上,作为道家学者的庄子,其否定儒墨的过程,也是在“以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从逻辑上说,庄子就该和儒墨一样,同样是没有道理和不能确定的。这就产生了庄子认识论中的自我矛盾。所以,这种“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实际上最终为老庄所否定了。事实上,庄子在建立自己形而上学的道论的时候,是在否定“矛盾不相容”的形式逻辑的同时也否定了他的“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老庄“道论”的建立,是通过“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形式而达到的。
“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形式是论证绝对无条件性的逻辑思维形式,仍然以老庄为代表。
《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庄子·齐物论》:“夫在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大象无形,“大”是至大,“无”是无对,也就是绝对。至大的象,涵括了所有的形,所有的象,无所不形,无所不象。因而有形同于无形,有象同于无象,至大而无对,孤立而自存,所以说“大象无形。”
大象无形中的“象”和“形”替换作“辩”和“言”,就成为“大辩不言”。替换作“有”和“无”就成为“大有即无”。同理,大有者无所不有,无所不有则无所谓有,无所谓有则无有,故大有则无有,大有即大无。有即无,无即有,有无合在一起,就是“道”。
所以,在“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层次上,就不再是有无相反相成,而是有无同一了。
《庄子·天下》述惠施“历物”学说,有“大同异”、“小同异”:“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所谓大同异、小同异,是在一个不同的思维层次上而言。在形而下的物的层次上,物与物有同有异,叫小同异。在形而上的道的层次上,万物一体,无同无异,叫大同异。《庄子·天下》称惠施对论辩有特别的兴趣,所以在他有了“大同异、”、“小同异”的理论成就以后,就周游天下,与天下人论辩,以口谈自衿,以胜人为乐,一直到他死去。惠施的论辩,大概主要就是用他“大同异”、“小同异”的理论在形而上,形而下二个不同层次上从事换概念,因此得以应辩无穷,连环可解。同样,在老庄的著作中由于老庄二人既使用“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又使用“大象无形”、“大辩不言”的逻辑思维形式,以至也常常使得后人在这二种逻辑思维形式之间发生错解,致使老庄本义淹没不明。
以下仅略举《老子》首二章及《庄子·胠箧》所说“有无相生”与“玄同”二义做一探讨。
《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紧接着在《老子·二章》(见上引)中,又说到了“有”、“无”。而这两章中所说的“有无”,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属于二个逻辑思维层次的。
就二章所说“有无相生”而言,此外的“相生”意为“有”、“无”相互关联而并存,而不是说“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此章中,难易相成的“成”,长短相形的“形”,高下相倾的“倾”,音声相和的“和”,前后相随的“随”,也都是并存的意思,而非互相派生。在“有”、“无”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时,只能够说“有中有无”、“无中有有”,所谓互为消长,而绝不能有“有生无”或“无生有”出现。犹如“阴阳”这一对概念,只能说阴中有阳、阳有有阴,而不能说阴就是阳、阳就是阴一样。
就一章所说“有无同出而异名”而言,而可以说“有生无”或“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无生于有”)了。但此处的“有生无”与“无生有”,并非认为“无”即是“无”、“有”即是“有”,认为“无”之“无”亦能生“有”,“有”之“有”亦能生“无”。而是认为“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在“无”就是“有”,“有”就是“无”的层次上,才有“有生无”与“无生有”。
《老子·一章》寥寥数语,把道家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概念“道”、“无”、“有”、“同”都提了出来。其中“玄同”一语,义极不显。学术界多将“同谓之玄,玄之又玄”的“同”解为副词,作“共同”、“都”的意思。如许抗生据此将《老子》原文译为:“无名与有名两者同出一处,不同的名称而所称谓的对象则是一个,真是玄妙而又玄妙,是众多奥妙的门户。”(注: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后又修改为:“无名与有名这两者,同一出处而有着不同的名号,都可以说是深远的。深远啊又深远,是一切微妙变化的总根源。”(注:许抗生《再解〈老子〉第一章》,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三联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照此, 《老子》首章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两句,成了虚泛无实意的感叹语句。
其实,“同谓之玄”在句法上本十分简单。“同谓之玄”就是:“同”叫作“玄”。“同”和“玄”都作名词。《老子·一章》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有和无两者同出于道而名称各异;“同”就叫作“玄”;玄之又玄,也就是同之又同,是理解“道”的关键。依照《老子》原文,“玄”字的意思就是“同”,“同”字的意思也就是“玄”,二字的字义本来是互释的关系,而“同”字的字义又很常见,因此“玄”字的字义也就很易于明白,本不需要再求证于别处。“玄”、“同”二字可以连用,如《老子》第五十六章,“塞其兑,才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庄子·胠箧》:“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玄同”连用,作同义复合词,仍表示“同”的意思。“同”的意思为“会合”,《说文》:“同,合会也。”古时亦称诸侯一齐朝见天子为“同”,《周礼·春官·大宗伯》:“殷见曰同。”文字学解释为“会合”之义,实即同于哲学家所常说“合一”之义。
小柳司气太据吴澄《道德经注》和陈景元《道德真经纂微篇》,认为“同谓之玄”的“同”不是“谓”的副词,而是名词。(注:小柳司气太《老庄的思想与道教》。)牟宗三也说:“道德经首章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两者指道之双重性无与有。无与有同属一个根源,发出来以后才有不同的名字,一个是无,一个是有。同出之同就是玄”(注: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牟宗三不仅明确的说“同出之同就是玄”,并且将“同谓之玄”一词在“同”字后面断开,使之不得再生歧义,是非常正确的。
道本无名,不得已而假托为名。所假托的名称很多,比如天地、阴阳等等,其中一个名称就是“大。”《老子·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关于“大”,《庄子·天地》篇解释说:“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不同同之之谓大。”“不同同之”,亦即“玄之又玄”之同之又同,亦即《庄子·大宗师》之“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及《庄子·知北游》之“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亦犹惠施之“大同异。”由此,也可以佐证“同”与“道”的关系。
再以《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论:其中“一生二”的“二”是指阴和阳两个概念,自《淮南子》以下,各家都持这个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阐述的就是物质起源与宇宙生成的过程,阴和阳就是阐述物质生成的两个概念。在这个物质生成的序列中,“二”或“阴阳”就不能取代为“有”和“无”。“道”本无名,无名而强名之,于是有“一”。“道生一”的意思,是“称为道,于是有了一”,不是“道”又生出了“一”,所以“一”就是“道”,“道”就是“一”。“一生二”是“道”分出阴阳。“二生三”是“道”与“阴阳”合而为三。在此之间,唯独没有“有”、“无”的出现,原因就是“道”就是“有”,也就是“无”。“道”与“有”与“无”本是“同之又同”,“道生一”也就是“有生一”,也就是“无生一”。“道”与“有”与“无”本是“同之又同”,“道生一”也就是“有生一”,也就是“无生一”。“道”与“有”与“无”是同一的,所以“一生二”的“二”才只是“阴阳”,而不是“有无”。
由此可见,“玄同”之“同”,与“彼是方生之说”的“方”,“齐物论”的“齐”,以及“天地与我为一”与《庄子·天下》老聃“主之以太一”的“一”,本有相同的意义和内涵。玄之又玄,就是同之又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同之又同,以至于无异。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道既无所不在,又复归于一。“同”就是逻辑上联结抽象绝对的道与具象无限的天地万物的中间环节。《老子》中所说“众妙之门”,当即此意。
由于“有”、“无”这二个概念在“有无相生”和“大象无形”二种逻辑思维形式中的含义不同,所以在形而下的宇宙生成和形而上的抽象思辩中的含义也就不同。在宇宙生成过程中,说“道”之“无”生成了万物之“有”,是合于老庄哲学的内在逻辑的。但在形而上学中,“有”与“无”其实已不再是“无”生“有”的派生关系,而是二者同一的关系了。
魏晋时裴頠提出“崇有”,著《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裴頠从物理学角度上,认为无不能生有,否定“有”和“无”的本体论概念。即便是尊崇庄子的郭象,也认为“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一无有则遂无矣”,“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注:郭象《庄子·庚桑楚注》、《庄子·齐物论注》。)。仍然是用物理学上的“无”来否定形而上学本体论上的“无”。而否定了“无”,也就继而否定了“有”。那么天地万物的根据是什么?郭象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哉?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注:郭象《庄子·知北游注》。)又说:“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注:郭象《庄子·有宥注》、《庄子·齐物论注》。)这就割裂了“有”和“无”的关系,取消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的联系。因为就老庄本义来说,“玄同”就是同,道论就是同论。无就是有,有就是无。从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无则无为,有则自存。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抽象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
杨汝舟认为:“‘无’是宇宙的本体,‘有’是宇宙的生成发展。‘道’之‘无’如何成为万物之‘有’,这就是从‘无’到‘有’必须经过‘道’之‘变’的历程。从‘无’到‘有’的‘变’化程序循环不已,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故老子说‘有无相生’。老子的宇宙哲学体系由此即告完整无缺了。”(注:杨汝舟《道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出版。)杨汝舟先在宇宙生成的概念上解释“无”生“有”,又在形而上学的概念上解释从“有”到“无”,然后用《老子·二章》的“有无相生”互证,对老庄“有无相生”与“大象无形”二种逻辑思维形式间的变换是含混不清的。
唐君毅将“同谓之玄”解释为:“有无相生而同也,谓之玄。”(注: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77年再版。)李震也认为:“《老子》一章告诉我们,道包括无与有,二者同实而异名,因此可见道之玄。”又说:“《老子》以‘有无相生’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注:李震《中外形上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出版。)则是“有无相生”和“玄”二义都没有解对。
[收稿日期]1999—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