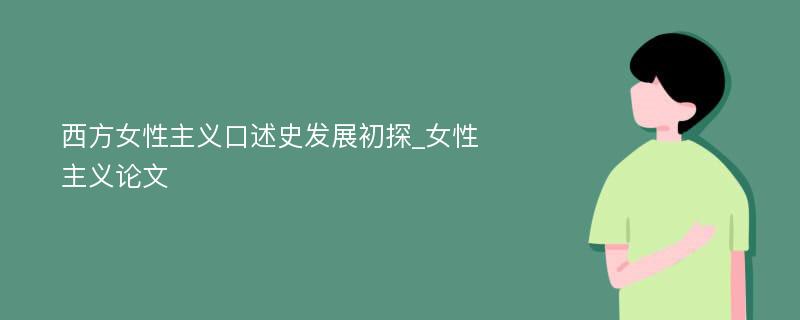
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女性主义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掀起浪潮之际,采录妇女口述即成为美国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妇女史研究,作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就史学而言,口述撰史并非始于妇女史的研究。可以说,它是西方史学研究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如果大卫·亨内格(David Hinge )的研究可以为凭据,那么,西方的历史撰写始于口述。现存最古老的史学著作为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两位史学家(Hero dotus和Thueyd kides)的作品,而这两位史学家就是通过采录不同个人的口述来收集史料的。
口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渐被史学家们所遗弃。这与史学界内部的变迁直接相关。特别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各主要城镇和宗教组织开始聘请专人,为本地和本组织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做历史性的记录。这些文字记载为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定依据。它们的存在不仅使史学家们察觉到口述中的种种历史误差,而且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凡是值得研究的历史内容都可以有史料为凭,而无史料为依据的课题则是不值得研究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对史学进行学科建设,使史学研究专业化、科学化,并高于其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精英价值观念在史学界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以研究有文字记载的主要事件、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名士风流为己任,而把对普通人及其文化的研究,贬为“原始文化”的研究,认为属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范围。由此,档案文献逐渐成了史学研究的唯一途径,而口述则被打入冷宫(注:有意思的是,邦尼·史密斯(Bennie Smith)的研究显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男性文化主导了西方史学界。 详见该学者所著“Gender and the Practice of Scienticic History:The Seminar andArchival Researc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100.4(October 1995):1150-1176.)。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除了少数史学家仍用口述的传统研究历史外,访谈这一形式已基本被史学界所摒弃。四、五十年代,有一小部分史学家力图将口述史重新引回史学研究中,但总成不了气候。口述史在西方史学界重见天日,乃是在近二、三十年的事。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传统史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冲击。一个通过重现平民百姓、下属阶层的生活,来重审历史的社会史学流派,开始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由于现存史料多以名人将相的生活变迁为历史的座标,社会史学家们不得不通过访谈、采录口述的形式填补史料,重审历史。口述撰史也就因此重新成了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至今它仍被西方社会史和文化史学家们广泛使用(注:有关以上两段的内容,请参阅David Henige 所著Oral Historiography(London,1982).)。
综上所述可见,口述既非始于妇女史的研究,亦非妇女史研究的“专利”。那么,为什么它一被引入,就深受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欢迎,而且到今仍被广泛使用?女性主义口述史和一般口述史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对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和认识上,有何发展?本文将对以上问题加以阐述。
(一)妇女口述史中的女性主义:领域的开拓
应该强调的是,口述之所以成为妇女史和女性主义研究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与女性主义的精神及其指导下妇女史研究的目的息息相关的。虽然至今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的定义及其实践看法不一,起码在一些方面是有共识的(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阅Leila J.Rupp
andVerta Taylor 新著“Forging Feminist Identity in anInternationalMovement:A
Collective Identity Approach to Twentieth- Century Feminism"Signs 24.21(1999):364)。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由社会、文化、历史因素所造成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现象,就要改变妇女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妇女史的目的就在于向男权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通过重现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
和社会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以妇女为研究主体的女性主义史学,没有太多的现成史料可作依据。这种现象对于研究劳工或少数族裔等下属阶层妇女尤其如此。采录口述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虽然就过程而言,妇女口述与一般访谈没有多大差别:由三个步骤所组成——准备访谈、访谈和访谈内容的分析,但在目的和具体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和一般访谈不同的是,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就采录口述作为一种学术手段而言,女性主义者认为,访谈不仅要了解客观上发生了什么,访谈对象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如何,感受如何。她们认为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反映出男女价值观的不同,妇女的独特视角,以及传统观念与实际生活的不符之处。即使在访谈中出现了访谈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传统观念影响的现象,她们认为访谈者应善于捕捉访谈对象在“我”和“非我”之间的徘徊,通过对这种“徘徊”的分析,加深对社会性别形成过程的认识。
为体现上述精神,女性主义者认为,在访谈中应打破过去以访谈者和研究者为主体的传统访谈法,在访谈中要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平等互动的关系。不仅要做到由妇女来做研究、做有关妇女的研究和为妇女而研究(to do research by,about and forwomen),而且要与妇女一起研究(with women)。在称呼上, 也把被访谈者(interviewee)改为叙述者(narrator )(注:本文从这里起,也会尽可能地用“叙述者”来代替以上所用的“访谈对象”一词。)。
为了真正体现访谈者和叙述者平等互动的关系,以及实现赋权于妇女的政治目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还应该批判传统访谈要求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们认为,访谈者应该带着感情去倾听叙述者的叙述,要善于理解她们的心声,从她们所处的特定的语境中去认识她们的视角。
为了将以上精神贯穿于访谈的始终,女性主义者认为,访谈者首先要对访谈这一形式中潜在的不平等关系有所认识。 戴安娜·沃尔夫(Dinae·Wolf)后来对此有所总结。她认为访谈中不平等的关系, 主要反映在如下三方面:1、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社会身份的差异, 包括种族、阶级、国家民族、生活际遇、城乡背景等等差异;2、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权力的行使,包括确定其本人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与研究对象不平等的交换、甚至对对方形形色色的剥削等;3、 田野调查后权力的行使, 包括研究者对研究结果的撰写和对访谈内容的“再表现”(representation)。她认为第一种不平等是客观存在、难以避免的,即便是对本族裔的研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仍存在着阶级、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第二、三方面的不平等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态度。研究者首先应该认识到,即便研究对象的社会身份,或在特定文化中辈分比研究者高,研究者仍控制着项目的设计、素材的取舍、分析和研究成果的享用等权力。特别是在研究下属群体时,如何处理好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使得最后呈现的不是研究者而是研究对象自己的心声,这是值得每个女性主义学者注意的问题(注:有关以上内容,请参阅
Diane Wolf"
Situating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in FeministDilemmas in Fieldwork,ed.Diane Wolf(Boulder,Colorrado:Westview,1996).1-55.)。
为了在访谈过程中避免不平等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做了种种尝试。比如,在准备过程中,她们认为不仅要做好充分的调研、项目的设计、对叙述者的了解,而且要向叙述者讲清项目的目的和意义,自己的背景,以及访谈可能给叙述者带来的正反面影响。由叙述者作出是否愿意接受访谈的决定。她们认为,为了在访谈过程中给对方有充分自我发挥的机会,即便出现与项目设计相左的话题,也不要轻易打断对方的思路。要注意观察对方的言行和感情的表露、语言的使用。访谈结束后,应尽可能和叙述者一起分析口述内容,而且研究成果应该双方共享。具体做法是:有些女性主义学者将研究成果带到叙述者所在社区推广,有些则与对方分享经济报酬,或与其同列为作品的合著者等。为了避免对叙述者有任何形式的剥削,除了对其所付出的时间予以一定的经济报酬外,在访谈的整个过程中,应尽可能地对对方或其所在社区提供服务。
总的来说,使用妇女口述这一研究形式早期所反映出来的取舍是将妇女看成一个整体。用谢尔纳·格拉克(Sherna Gluck)的话来说,就是一味地颂扬妇女的经历(to celabrate women's experience)。 虽然此研究法推广不久就有人对个人口述能否反映妇女整体的经历表示怀疑,而女性主义学者也注意做了对不同阶层妇女进行访谈的大型研究项目,但是她们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注意了客观因素对访谈结果的影响,但对访谈者和叙述者主观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认识不足;注意了形式,但对其复杂内涵剖析不足。
(二)近十年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
随着访谈形式的广泛运用,女性主义者对其复杂性的认识也有所加深。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有不少学者对早期种种尝试的实际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比如,在与叙述者一起分析口述内容时,出现了意见分歧怎么办?有人认为,既然要尊重对方,平等相待,就应以对方的意见为准;其它人则认为这不是真正平等互动的关系。因为,如果分歧是由访谈者思想上的问题所导致的,难道仍应以其看法为准吗?以谁为准?以什么观点来判断是非?大家意见不一。于是有人建议,遇到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时,最好把有关内容去掉。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导致最后的分析和总结半途夭折。
除了对具体做法中如何体现女性主义精神的讨论外,还有学者从根本上对访谈这一形式能否体现女性主义精神提出质疑。这里,仅以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 )《可能有女性主义人类文化学(ethnology)吗?》一文为例。文中, 作者基于她本人访谈的体会指出,即使女性主义学者本着女性主义精神与叙述者平等相待,在涉及到个人隐私时,对方也未必和盘托出;即便对方在访谈时肯谈出一些问题,尔后立场也可能改变。再则,尽管访谈者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和感情上的依赖,有问必答,访谈者完成项目后,总需离去,这种结局对对方感情上会造成一定伤害。这种研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叙述者感情上的利用。更有甚者,由于对方的信任,女性主义访谈者取得了比一般访谈者更多的资料,如果对此资料处理不当,就可能对叙述者造成更多的伤害。虽然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否认有女性主义访谈者与叙述者建立持久关系的成功案例,但是,鉴于上述的种种恶果,她告诫大家应该接受访谈只能部分地体现女性主义精神的事实(注:有关以上内容, 见Judith Stacey"Can There Be a
FeministEthnography?"in 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History,ed,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New York andLondon:RouHedge,1991).111-119.)。关于访谈这种形式是否能、以及如何才能体现女性主义这一系列的问题,至今仍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中十分有争议的话题。
女性主义史学家和其它专业的女性主义学者一样,对上述问题十分关注。除此之外,她们还尤为注意叙述者对过去回忆的特点,以及造成这种特点的种种主客观因素。这里让我以1997年《妇女史学刊》中埃米莉·霍尼(Emily Honig)的文章和艾琳·莱德斯玛(Trene Ledesma)的回应为引子,对近年来女史学就口述史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做个简单的介绍。
霍尼是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白人女史学家。她关心劳工生活,对下层群体有深厚感情。此文谈的是她早年访谈的一些体会。作者在文中谈到她于1977—78年间,对曾参加过七十年代初得克萨斯州法拉衣厂大罢工的女工进行过访谈。她发现,虽然女工们在访谈中一再强调罢工如何增强了她们的社区(community)观念, 使她们从原来的胆小怕事、被动变得充满信心、敢想敢干;然而,在具体的内容,谈的则多是她们如何从小就具有反抗精神事例。如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作者列举了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1、 罢工的经历改变了女工的视野,使她们对童年有重新的认识;2、 对方明白访谈者的意思是要了解罢工如何改变女工的观念,因此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做了努力;3、 与此同时,女工们也想通过对童年的回忆,改变主流社会认为墨西哥裔妇女被动的刻板形象。由此,作者的结论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去都会有多种、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妇女口述史是对历史现实的直接反映,不如说它是在种种媒体影响下对过去的复述(retelling)。因此,在分析访谈内容时, 必须对对方访谈的状况可能造成的影响予以充分注意。
莱德斯玛是从小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墨西哥裔女史学家。她的博士论文以该州制衣女工史为题。在与霍尼的对话中,除了肯定前者的观点外,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访谈不仅受叙述者当时状况的影响,也受访谈者当时状况的影响。文中,她以自身的经历为例,谈到由于本身地理文化背景的特点,原以为对所选研究题目应是驾轻就熟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访谈开始,她就遇到种种困难。由于是通过工会的关系访谈,工人不是不愿意接受访谈,就是在正式录音时,把在非正式场合下谈及的敏感度较高的内容——比如,工会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罢工中出现的暴力现象等有意删去;对此,作者深感无奈。检查自己,莱德斯玛认识到自己过去对自己“局内人”的身份过于乐观。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所受的训练,使她重视了社会性别和种族身份的认同,而忽视了自己与叙述者阶级的差异。文化和性别的认同,使她容易看到女工积极的一面,而对她们对工会的种种顾虑认识不足。与此同时,她也指出霍尼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女工们是有斗争传统的,即使没有罢工,若访谈涉及到她们的童年,她们也会讲同类的故事;所不同的只是所用语言不是罢工后学会的新词,而是社区里惯用的俗语罢了。再则,社区里有集体观念的人,未必都参加过罢工。因此,她认为霍尼对社区了解不够,有过于强调罢工对工人影响的倾向。然而,霍尼作为局外人,对工会和罢工影响的敏感度,又远胜于她本人(注:以上内容请参阅Emily Honig,"Striking Lives:Oral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和Irene Ledesma,"Confronting Class:Comment on Honig-"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9.1(Spring 1997):139-163.)。
以上两位女史学家的对话,揭示了近年来女性主义史学界对妇女口述史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下面仅就其中几个问题做个小结:
1、“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问题
女性主义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由于采录口述的形式多用于研究缺乏文字史料的劳工或少数族裔妇女,而访谈者又多为白人知识分子,这就极易出现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叙述者所在社区文化缺乏认识的现象。解决这种现象的办法多为有意识地培养本族裔的研究者,用一位白人女性主义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即使这意味着她本人会因此而失去就业机会, 那也是必需的(注:见Debra J.Blake, "ReadingDynamics of Power Through Mexican - Origin Women's Oral Histories",Frontiers 19.3(1998):35.)。但是,正如上述莱德斯玛的讨论所指出的,培养少数族裔研究者,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原因是:a、人的社会存在是多元、多层面, 而且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个人因此很难代表任何集体。b、 即使所培养的人与所研究的群体在各种社会身份上完全一致,经过了培训后,视角也不可能与原先一样:可能变得更敏锐,但是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主流文化的影响,与社区里的人拉开了距离,从而失去了其局内人的优势。
相反的,不少研究少数族裔的白人女性主义学者的实践证明,虽然她们不具备局内人的许多优势,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她们具有“局内”学者所没有的有利因素。比如,她们发现,对一些个人或文化方面敏感的问题,叙述者往往宁可对外人说,也不愿意对本族裔的研究者披露。同时,她们中一些人对外族人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导致她们在一些问题上对外族人能畅所欲言。这里可以黛博拉·布莱克(Debra Blake )的研究中所举的几位白人学者的经验为例。她们发现,在性和家庭暴力等敏感度高的问题上,她们所访问的少数族裔妇女能对她们畅谈;但是对本族裔的研究者,反而顾虑重重。原因是,对方认为白人文化不忌讳谈论这些问题,也不把这些看成是个人隐私。当然,这些学者也指出,要真正消除少数族裔叙述者与她们的隔阂,她们需要付出比本族裔学者更大的努力(注:见Debra J.Blake,"Reading Dynamics of Power Through Mexican-Origin Women's Oral Histories ",Frontiers 19.3(1998):24-41.)。
以上关于访谈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的讨论,揭示了社会身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如何在不同情况下,有意识地克服自己身份的不利因素,则是每个研究者和访谈者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2、回忆过去的一些特点
专业所致,女性主义史学家对人们回忆过去的特点分外关注。可以说,人们对过去的回忆都是有选择的。往往对自己身体力行或感受最强烈的事情记忆最深。而且正如上霍尼的文章所指出的,对过去的回忆,还会随着个人情况、环境、时间和社会话语的变迁而产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在不同情境对过去的回忆,都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新塑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在叙述者无意识中进行的。
这里可以用玛格丽特·斯特罗贝尔(Margaret Strobel)在1999年第一期的《妇女史学刊》里的文章为例,说明回忆的不稳定性和反复性。文中作者谈到自己的一段经历。事情发生在1994年和1995年间,当她和一位同事合教一门课时,为使学生对六十年代美国青年的生活有感性认识,她把一位暂称鲍勃(Bob )的男友当年发表在一个地下刊物的诗文给学生阅读。鲍勃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与她交过朋友,尔后参战并于越战中阵亡。对于为什么鲍勃决定参战,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鲍勃与后来成为她的男朋友的约翰更为接近。
为了找出鲍勃决定参战的原因,1994年她查阅了自己过去与朋友特别是鲍勃来往的大量信件。她发现,鲍勃曾在信中提到他在大学一年级时,有对自己性倾向不明确的感觉(a sense of sexual ambiguity ),同时也谈到自己与作者及其男友,卷入了一场感情上的三角纠纷。后来从其它朋友处,作者了解到鲍勃在来看望她和约翰时,曾与后者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基于以上种种迹象,作者猜想鲍勃当时不是同性恋,就是双性恋者。对此,她当时并没有察觉。
1995年,她重读鲍勃的信时,发现自己错读了该信。鲍勃在信中谈的不是有不明确自己性倾向的感觉,而是明确自己的性身份(a sense of sexual identity)。这一发现,使她更肯定自己的猜想。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对过去回忆的正确性,她设法找到了原来的男朋友约翰·约翰承认鲍勃当年确实觉得他很有吸引力,想与他发展进一步关系。当他发现约翰与作者相好后,他有了被遗弃感,所以决定参战。就此,作者以为自己在事过三十年后,总算明白了事情的真像。
使作者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她以为找到了事实的真像而重读自己的札记时,又发现1968年她与约翰分手后,在一篇札记里提到鲍勃是双性恋者。这说明她当时对鲍勃的性倾向是清楚的。为什么后来对此全无印象?作者分析了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可能不愿正视自己对鲍勃最后的阵亡有一份责任这一事实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分别在68年、94、95、96年找她访谈,尽管她诚心诚意地想重现历史的真像,所谈的内容恐怕难以相同(注:以上内容,
请参阅MargaretStrobel"Becoming a Historian,Being an
Activist, and
ThinkingArchivally:Documents and Memory as Sources",Journal
ofWomen's History 11-1(Spring,1999):181-192.)。这种无意识地对过去有所选择、不稳定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会有更复杂的表现。
除了上述这种无意识的表现外,个人对过去的叙述还被叙述者有意识的主观因素所左右。上述内容霍尼和莱德斯玛对口述史的评述,都反映出口述内容会受到叙述者与访谈者的关系、对访谈目的的认识以及自我形象的塑造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是,这种种主观因素,不仅导致叙述者对过去的粉饰和修改,而且在发此重复多次后,还会使其本人成为自我塑造的、与事实不相符的历史的俘虏。
桑地·玻利舒克(Sandy Polishuk)最近一篇题为《秘密、谎言和记忆的失误:口述史访谈的危险》的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文中,作者谈到了自己多年来对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工运积极分子进行访谈的体会。作者文中暂称此人为朱莉娅(Julia)。 对她进行访谈的目的是为了给她写传记。据作者介绍,此人希望通过传记为自己塑造一个独立女性的形象。用朱莉娅本人的话来说,则是希望后人通过她的自传,了解工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出于此目的,在访谈中她谈的多是她在公众领域中的政治生涯,而不愿谈个人的私生活。即使在作者鼓励她谈自己的私生活的情况下,她也不是避而不谈,就是把它政治化了。因此在访谈过程中,尤其在私生活方面,出现了许多前后所述不符的问题。朱莉娅健在时,作者为此常与她对证,发现有些不符是她记忆中失误所造成的,有的则是由于她在意识地掩饰或歪曲。对此,有时她也坦白承认了。使作者感到棘手的是,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是在她逝世后才发现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成了文章议论的焦点之一。
文中作者举了许多例子,这里仅以两例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事实是,朱莉娅在1950年曾自杀过。为什么自杀?朱莉娅对此问题的回答总是很模糊,而且变化多端:有时说是因为对现实不满,有时说是因为负债过重而不想活了,有时说是没有成就感,还有时说是因为无法交电话费,进而不能完成正写着的一篇文章等等。朱莉娅逝世后,作者对她的一位朋友进行了访谈。这位朋友自称是她介绍朱莉娅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三任丈夫的男人。据这位朋友说她在朱莉娅自杀末遂后,曾到医院看过她,而朱对她说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爱上了一位男性,但恋爱不成,所以轻生。因此她给她介绍了新的男朋友。作者查阅了朱莉娅的口述,发现朱的说法与朱的这位朋友的说法相左:朱说她在自杀前就认识了她的第三任丈夫,而且对方是在她自杀未遂、身处医院时向她求婚的。当作者把这一内容转告朱的朋友时,对方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据她说,朱在结婚数年后,还为因她的介绍认识了第三任丈夫,而特地向她表示感谢,她说是这位朋友使她明白了什么是爱。
如何对待朱与她的朋友对同一过去不同的记忆?作者分析了种种可能的原因。比如,可能是因为朱在朋友向她介绍男友时,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已认识了他;也可能是因为她的朋友想表示自己在她的第三次婚姻中起了作用,等等,由于有关人士已相继去世,事实的真相已无从考证,但是,从朱本人所写下的自传性文字和她的另一个朋友的回忆,以及她企图自杀的时间(1950年11月5日)与她第三次结婚的时间(1951 年1月3日)来看,作者认为朱对自己与第三任丈夫认识的过程的叙述,可能更接近现实。通过这一例子,作者想说明的是,即便对于同一过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朱莉娅对自己一生的叙述,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个人,确有不同的版本。她的感情生活其实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三次婚姻外,她还有许多罗曼蒂克史。但是对不同的个人,她有不同的说法。对于作者本人,她倾向于将这一切政治化。比如,在谈到第一次婚姻失败时,她曾屡次提到是对方的种族主义导致两人分手的。她还曾绘声绘色的谈到一次在餐厅进餐时,她如何从谈话中察觉对方的这种倾向,当场决定离婚。但是数年之后,在一次访谈中,她终于承认对方殴打了她,是家庭暴力导致婚姻破裂的。
但是,对于自己的朋友,特别是工运中比她年轻的战友,她不仅不会避而不谈自己的私生活,而且有时还会加以渲染。比如,在对一位年轻的战友谈到如何处理个人生活时,她谈到在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前,在芝加哥时就和一位男性相爱,而且怀了孕。作者查阅资料发现,她到芝加哥时已结了婚并且怀了孕。为什么会出现与事实如此不相符的叙述?作者的分析是,朱是想在对方面前塑造一个私生活解放的新女性的形象,因为对方的母亲虽然也是工运的积极分子,但在私生活方面却很保守(注:有关以上内容,详见 Sandy Polishuk,"Secrets,Lies, and
Misremembering: ThePerilsonOralHistory Interviewing"Frontiers,19.3(1998):14-23.")。虽然作者在文章中提及的一些问题,其它学者在不同的研究中多少也谈到,但是通过案例分析,读者对口述史中的种种复杂现象,加深了认识。
正由于上述口述史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已明确表示,妇女口述史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直接依据。有些学者则干脆把它定性为仅仅是妇女主观世界的记录。比如,研究1933年加州桑·茄昆(San Joaquin )墨西哥族裔棉田工人大罢工的女史学家黛博拉·韦伯(Debra Weber)认为,因为口述史中充满了不准确性和自相矛盾, 与其说它反映了妇女的真实经历,倒不如说它只是关于她们主观意识的一种提示。 研究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工人的女史学家路易莎·帕塞里尼(Luisa Passrini)则认为,口述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记录、对集体回忆的反思和讲故事的一种形式罢了(注:
以上内容请参阅 Emily
Honig," Striking Lives:Oral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Memory"和Irene
Ledesma,"Confronting Class:Comment on Honig-"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9.1(Spring 1997):140.)。
如何看待妇女口述史对史学研究的意义?可以说,对妇女口述史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主义的认识,而且反映出她们对传统史学和现存史料的看法。近年来,随着对传统史学的不断批判,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识到,尽管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的撰写则难于谈得上是纯粹客观的,因为它直接受着史学家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注:这里谈史实的客观存在,目的是区别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史学研究是受史料制约的。)。现存史料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每个时期史料的收集、撰写都与当时的社会话语、史学界中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等方面的倾向性有直接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妇女口述史,作为一种新型的史学研究文本,具有受着来自于各种因素影响的种种复杂性,也是不足为奇的,关键在于对这些复杂现象的认识和对口述内容的使用上。和许多口述史学家一样,女性主义史学家认为不应把口述史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现象作为问题来看待,相反地,应将其视为窥探妇女内心活动的重要门窗,要重视妇女的视角和心声,就应按她们的视角重现她们的历史。史学家也是通过分析种种不同的视角来挖掘历史的复杂性的。
应该指出的是,对口述史是否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议论,其实并非始于妇女口述。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口述史在史学界有过沉浮。它的沉浮,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史学界的动向。口述史在西方七十年代的再度兴起,就是史学家们向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中的精英价值观挑战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对史学研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这一方法充满了“危险”,但是想到它的意义,还是值得去冒这些险的(注:有关以上内容, 见 Judith Stacey"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ed,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New York and London:RouHedge,1991).117.)。
当然,为了增强对口述内容主观因素及其影响的警觉,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基于本人的实践,提出了建议。比如,玻利舒克的研究显示,在分析访谈内容时,有必要穿插使用有关文字的记载(注:有关以上内容,详见Sandy Polishuk,"Secrets,Lies,and Misremembering:The Perils on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Frontiers,19.3(1998):14-23.")。斯特罗贝尔则呼吁妇女组织与个人要注意保存本组织和个人重要的文字或实物史料,
以助将来对历史的回忆(注: 以上内容,
请参阅Margaret Strobel"Becoming a Historian,Being an Activist, and
Thinking Archivally:Documents and Memory
as Sources",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1-1(Spring,1999):181-192.)。虽然迄今为止,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对口述史的使用和认识,仍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而且口述这一形式也不是研究任何历史阶段的史学家都能采用的,但是这一形式背后的指导思想,即向传统史学中的精英思想挑战,则是所有史学家所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