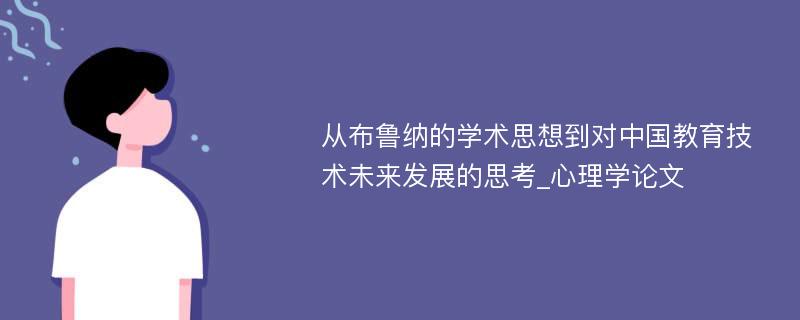
从布鲁纳学术思想两次转向反思中国教育技术学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教育技术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5)06-0030-07 doi10.39696/j.issn.1009-5195.2015.06.004 布鲁纳一生在学术上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第一次转向可以称为“认知转向”,引领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第二次转向可以称为“文化转向”,催生了文化心理学,这两次转向均对当时及后世的教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两次转向分别产生了两本在教育心理研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教育过程》与《教育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以《教育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转向见证了布鲁纳引领的教育心理研究从“因果解释”到“文化诠释”的转变,这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一、从“因果解释”到“文化诠释”:布鲁纳的实践与理论反思 20世纪60年代,基于结构主义的《教育过程》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教育研究者的热烈追捧,曾一度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最终获得了“圣哲罗姆赞美诗”的美誉。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被视为教育改革蓝图的《教育过程》却由于在实践中囿于避讳历史文化的特性,很快失去了早期在理论上的感召力。这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课程与教学改革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发现贫穷”等社会性议题的不断高涨,学校教育文化中立的价值观念持续受到冲击,严重影响了当初这场声势浩大的教改运动的实践效度。布鲁纳本人在其自传《心灵的求索》一书中也曾提到,有些社会公众将造成学生辍学与青少年暴乱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以结构主义为指导所开设的某些不合理的课程,他们否定教改运动的历史效用,重新掀起了“回复基础”(Back to Basics)的教育运动。这迫使布鲁纳不得不重新思考与教育研究相关的文化适切性问题(Bruner,1983)。 就布鲁纳自身所参与的教育实践改革而言,作为一位致力于改善教育的心理学家,布鲁纳参加的各种教育研究项目的不佳效度直接导致了其学术研究的转向。他曾经指导过的博士后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就曾指出:“‘开端方案’(Project Headstart)、‘人类研究课程’(Man:A Course of Study,简称MACOS)及‘非洲儿童认知与田野研究’等都对布鲁纳教育研究思想的转变产生过重大影响。”(Greenfield et al.,2003)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研究课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作为三大设计者之一的布鲁纳以结构主义教学观将课程设置为促进学习者智力发展的结构模式。这一举措过于重视教学过程中的智育发展,严重忽略了影响学习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综合因素。更有甚者,为还原某些学科发展的本真面貌(结构),有些课程内容还触犯了社会伦理道德的边界与底线,这引起一些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与诘责,最终导致国家卫生基金会(NSF)终止了对该项目的资助(徐珊珊,2012)。 纵览布鲁纳教育研究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作为一位热切关注智育发展的心理学家,他自始至终都致力于对智慧生长的探索与观察。在其学术研究生涯早期,布鲁纳首先对心理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转向教育领域,强调有必要在教育学中建立一门“规范性教学理论”,而后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馈并以此来推动心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由此建立一个双向流动的由描述性学习理论、处方性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构成的连续统,以期最终能够打通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双向道”的交互机制。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布鲁纳关注的主要范畴是科学主义背后的因果解释机制,并没有为人文主义的文化诠释留下任何空间。正因如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科学心理学将心灵运行机制还原为因果解释而又无法构建文化实践的情况下,布鲁纳断然摒弃科学主义的研究信念,在对教育实践的考究下又亲手“埋葬”了其早期在教育研究中极力主张的认知结构观,转而借鉴文化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更具人文色彩的研究经验,试图以叙事的思维从文化、语言等更为宽广的人文视野中探索人类智力与教育发展事业,并以此揭示人类特有的教育、心理与文化现象与规律(Harré,1992)。 这种转变映射着整个20世纪教育研究的基本历史景观,是教育研究科学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发展演进的基本逻辑缩影。其大致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阶段:进入20世纪以来,以桑代克和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倾向于以经验论作为学习研究的基本哲学观,将学习者的内部心灵视为“白板”,强调外部环境刺激对学习者行为表现的决定性作用。当教育研究科学化运动进入20世纪中期后,以格式塔学派、皮亚杰、布鲁纳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则偏向于以唯理论作为其学术研究的认识论根源,在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强调“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原则,并在此前提下推演出结构主义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然而,不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经验归纳所抽象出的“刺激—反应”模式,还是基于认知主义逻辑推理而演绎出的“信息加工”模型,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运动仍在以归纳法与演绎法为主要方法论的科学“伊甸园”中徘徊,极少关注文化实践中的人文“尘世”。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学术研究的科学迷信被破除、工具理性遭到排斥、对人之主体地位的关注成为学术争鸣的研究焦点,教育研究科学化运动便从科学主义的“伊甸园”转向了人文主义的“尘世”,教育的因果解释也开始逐渐让位于意义建构的文化诠释。 二、教育文化对教育研究中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叛与颠覆 如果说《教育过程》是一曲立足于认知研究的心灵独奏乐,那么《教育文化》则是一支由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与心理学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教育交响曲。从《教育过程》到《教育文化》的转向,蕴含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人文主义为主导的教育文化研究理念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而这场科学革命最早发端于科学心理学临摹已久的自然物理学领域。20世纪初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推翻了经典物理学中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的概念体系,“在高速微观世界,时间与空间都是相对的,真理的建立应当是一个概率事件,而非必然事件”(H.赖欣巴哈,1966)。相对论的诞生由此浇灭了人们对客观普遍真理的科学幻想,掀起了人们对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学术研究热潮。赫伯特·马尔库赛就曾指出:“科学通过消除中世纪的神话而起步,但直到现在,科学迫于其自身的一致性而意识到,它不过是建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神话而已”(赫伯特·马尔库赛,1988)。随着自然物理学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信念逐渐分崩离析,心理学依据的哲学基础开始不断崩塌,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心理研究之科学体系也随之瓦解。 随着心理学中客观主义研究范式的式微,以物理学为标杆的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因而心理学化的“教育科学研究”也受到了极大的困扰。科学的教育研究究竟该何去何从?是秉承“伊甸园”中科学主义的因果解释机制,继续探求具有客观普遍性的真理?还是重新调整方向,从现实而鲜活的“尘世”出发,在对人的科学研究之中另谋出路?这成为摆在教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要解决这些研究信念的立场、归属等基础问题,还需从教育研究所秉承的基本科学认识论着手,而率先打破这一僵局的便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在特定时期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循的科学理念及立场,科学定理与科学发现只有在特定范式的理论框架中才能成立”(托马斯·库恩,2003)。换言之,在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家总会受到特定历史文化环境所形成的价值观与哲学信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科学范式。 既然像物理学、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都无法完全避开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人文要素的影响,那么作为与人息息相关的教育与心理研究则更不能忽视历史与文化的综合特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历史文化因素才得以正式进入人们的科学研究范畴,并获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而作为一位真诚关注教育实践的心理学家,布鲁纳在见证了实验室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差距之后,便决心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他转变了《教育过程》中将研究视野限定于狭窄的认知探索的做法,而将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教育与心理的文化视域。布鲁纳在借鉴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础上,还吸收了维果斯基的“历史—文化”理论,不断对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文化中立观进行解构。另外,在生物性条件限制的前提下,布鲁纳尝试将历史文化等综合要素引入教育研究中,在文化主义的视域里对教育与心理进行新的探索,由此构建了一个以生物性条件限制、历史文化研究、教学实践为支点的教育、心理与文化研究之三角框架。 三、教育文化推动的教育与心理研究之“文化转向”及方法学创新 “文化”在布鲁纳的教育与心理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Takaya,2013)。在早期的教育研究中,作为心理学家的布鲁纳将文化作为教育的内容来看待,在研究中坚持文化传承的教育逻辑。在布鲁纳看来,教育既然是文化的传承,那么教育研究的首要议题就是要鉴别出那些能够促进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最有价值的文化,而后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把这些作为内容的文化传递给学习者。但到了《教育文化》这一时期,布鲁纳的观点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把文化仅仅视为教育的内容,而是将其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境脉与工具。因为只有在这种文化境脉中,学习者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和所蕴含的意义才能够得到解释;只有借助于文化这一工具,学习者才能够完成意义建构。这样一来,教育研究首先要关注的就不再是剥离了文化属性的文化内容的递送,而是如何帮助学习者经验各种不同的意义建构模式与信息传播模式,如何创造一个社群,让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得以发生。通过对文化理解的转变,布鲁纳告别了过去的那种心理学,即把学习认为是一种“去文化”的心理过程,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取的是价值中立且客观的知识。 在《教育文化》一书中,布鲁纳发展了一种教育的“心理—文化”取向,将学习置于广阔而复杂的文化境脉中进行考察。他指出:“尽管意义是‘存在于头脑之中的’,但其仍然无法摆脱其文化本源,而且这些意义的重要性也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够得到彰显,因为正是文化才创造出了这些意义……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不管主体看起来是多么的依靠自身的努力,如果没有各种文化符号系统的辅助,意义的建构仍然是做不到的。”(Bruner,1996)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不仅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是教育的境脉,那么这就意味着:第一,意义是依赖于文化框架的,文化境脉决定了意义建构的内容;第二,在意义建构中,主体间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脱离了具体的文化境脉,主体间性就会变得非常空洞;第三,立足于文化境脉,学习者在群体框架内进行的人际交互才可能为学习提供丰富的机会;第四,“叙事”是非常关键的,它不仅是教育实践中思维的模式和意义建构的工具,而且是教育研究中对思维与意义建构进行把握的有效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里斯·吕腾(Karis Rutten)和罗纳德·泽特瑞特(Ronald Soetaert)认为,布鲁纳开创的叙事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对于教育研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撼动了建基于心理学之上的教育研究之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石,推动了教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叙事转向(Rutten et al.,2013)。 在《教育过程》向《教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叙事法”是布鲁纳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崛起,一些认知心理学家将计算机隐喻引入教育心理研究领域,由此导致教育与心理研究逐渐脱离早期认知心理学设想的对情感、态度等高级心理机能进行探索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一种狭隘的“计算主义”的偏好(Bruner,1990)。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才更加彰显了布鲁纳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认知心理学家在教育研究上开启“文化转向”的突破性意义。若泽·蒙特亚古多(José Monteagudo)指出:“布鲁纳勇于进行自我批判,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早期所极力推崇的认知心理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与机械还原倾向的弊病,并甘冒挑战权威的风险,将历史、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方法论引入以科学主义为标杆的教育与心理研究领域。”(Monteagudo,2011)从新的认识论立场出发,布鲁纳主张知识的传播不仅存在于以归因论为认识基础的心灵与抽象自然的交互,更以一种故事演讲的文化叙事方式,表现于“人—人化自然—人”之间的互动建构之中。就教育学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知识不是存在于教师与学生的头脑与心灵之中,而是存在于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叙事建构之中。 《教育文化》不但引领了心理学研究从认知到文化的转向,而且同样引领了教育学研究从认知到文化的转向。理查德·宽茨(Richard Quantz)曾经这样评价《教育文化》:“我相信,有些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尽管是在批判的、后现代的、文化的立场上从事研究,但却没有能够真正深刻理解我们本应该理解的心理学。这一新的‘文化心理学’提供的远见卓识可能会帮助我们重拾那些被视而不见的要素,但《教育文化》更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把业已穷途末路、奄奄一息的教育心理学带到文化的新世界。在我的教育心理学同事中,曾经有人这样讲过:‘教育心理学已经死了,在教育研究中,未来最重要的概念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文化学的。’可能我的这位同事的话带有感情色彩,有些言过其实,但我的确相信,布鲁纳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起码在这本书中……这位备受尊崇的纽约大学教授(而不是刚刚从伍兹霍尔会议出来的布鲁纳)把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的人置于书中的核心位置,哪怕这仅仅还只是修辞与理论上的。至少从现在开始,教育心理学可能要把焦点更多地置于我们所有人——学者、教师、学生、家长和政治家们——对教育经验进行意义建构而不可或缺的‘叙事’上,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学习的‘结构’上。”(Quantz,1997) 四、在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历史激荡与融合中开创教育技术学的未来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心理学与教育学是其不可缺少的学科背景与知识境脉,二者的激荡与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作为一个潜在学科的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现实。从布鲁纳学术生涯的两次重大转向尤其是文化转向的艰难探索中,我们能够为教育技术学未来的学科发展找到哪些启示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教育技术学在从领域向学科的挺进中应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匹配 教育技术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要想实现自身研究的规范化,就必须遵从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规律。我国学者唐莹在《元教育学》中指出,在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体系构建规范中,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匹配程度是衡量学科建设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唐莹,2002)。而纵览教育技术发展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对象经由从媒体到过程与资源的变化(郑旭东等,2014),研究方法也从早期的实验研究发展到如今的基于设计的研究。这体现了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借鉴心理学、教育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正因如此,教育技术才打下了多学科交叉的印记,但同时也彰显出其自身缺乏独有研究方法,以及使用这些独有方法来解决学科面对的科学问题的缺陷。 在布鲁纳学术生涯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从心理学的范畴转向了教育学的范畴,并相应带动了研究方法的转换与创新,不但引领了早期教育研究的认知转向,而且还引领了其后教育研究的文化转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鲁纳并不像桑代克那样仅仅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教育学身上,而是首先从教育自身找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开展科学探索,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科学理论,发展研究方法。这对教育技术的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沿着布鲁纳开创的道路,我们可以设想,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也必须根植于教育学的历史境脉中,凸显教育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并以此为基础,从技术干预教育的复杂现实中确立其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并发展能够匹配这一研究对象的独特研究方法。而在使研究方法匹配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找到并抽象出应该研究的科学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认为,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才能够在科学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带动学科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2.以布鲁纳教育思想为参照对教学媒体理论与教学设计理论的批判 对人文主体与历史文化的关注成为布鲁纳从《教育过程》转向《教育文化》的“第一推动力”。《教育过程》凸显的是去情境化的文化中立观,而《教育文化》则更多体现出“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文化价值观。在《教育过程》历经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各种杯葛之后,布鲁纳打破结构主义文化中立的枷锁,不断对文化中立的《教育过程》进行解构,推动教育与心理研究的文化转向,最终完成了《教育文化》。反观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展,长期以来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为自身学科定位与发展带来了极大困扰。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教育与技术定位的争论长期存在,虽然这样的争论在教育技术学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学科界定的难度日益增大,我们几乎很难说出教育技术学到底是什么。而在各种争论的背后,更是暗含着教育技术两大学术流派——教学媒体派与学习派之间的分歧与争论。 实际上,不论是以埃德加·戴尔(Edgar Dale)为代表的媒体派,还是以罗伯特·加涅(Robert Gagné)为代表的学习派,往往都囿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要么仅仅就媒体研究教育,要么仅仅基于对学习的机制进行探索,进而研究如何设计教学,均难以从整合的视野把握教育,从而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教育技术研究的正途。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不论是孤立的媒体观,还是去情境化的学习观,都不利于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教育技术学的未来发展。为实现教育技术学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愿景,我们可以借鉴布鲁纳教育研究思想转变的历史经验,借助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现代科学理性至上的原则,使教育技术摆脱工具理性知识观下对自身作为辅助工具和技术手段的狭隘定位,真正让技术渗透人文关怀,让教育回归经验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具有不同气质的教育技术学理论。 3.何去何从: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构建究竟是重蹈覆辙,还是另辟蹊径 布鲁纳早期的教育研究向世人表明:传统的教育研究继承了心理学家分析还原的思想方法,把真实情境下的教学实践还原为实验室中接受严格变量控制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实际教学情境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事实上,以牺牲教学情境本身的复杂性为代价,不仅影响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也失去了在复杂情境中从更多方面对教与学进行探索以揭示其复杂本质的机会。因此,当教育工作者将心理学家在实验室这一理想情境下得到的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真实情境时,并没有给教学实践带来明显改观,教育研究自身最终也因面对实践的无力而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心理学家打造的教育研究之“伊甸园”中取得的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鲜活而复杂的“尘世”,因而将教育研究的场所转向现实教学情境的呼声不断高涨。布鲁纳通过《教育文化》实现的教育理论建构的文化转向正是对这一时代呼声的回应。 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教育技术学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实践应用有余而理论构建不足的尴尬。为摆脱这种困境,学者们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与其他交叉学科的交流对话中,总能感觉到自身面临的理论构建不足之缺憾。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主体在构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仔细审视《教育过程》到《教育文化》转变的理论财富与思想精华,认真思考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构建究竟是继续沿着布鲁纳早期学术研究的老路,对受教育者进行同质化处理,进而重蹈《教育过程》的覆辙;还是像后期的布鲁纳一样,另辟《教育文化》的蹊径,在文化生成的大背景中重新厘清“教育—技术—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理性层面上重构人与人、人与技术、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构建需要回答的课题。 收稿日期 2015-09-24标签:心理学论文; 布鲁纳论文; 教育技术论文; 教育心理学论文; 教学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教学过程论文; 心理发展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教育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教育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