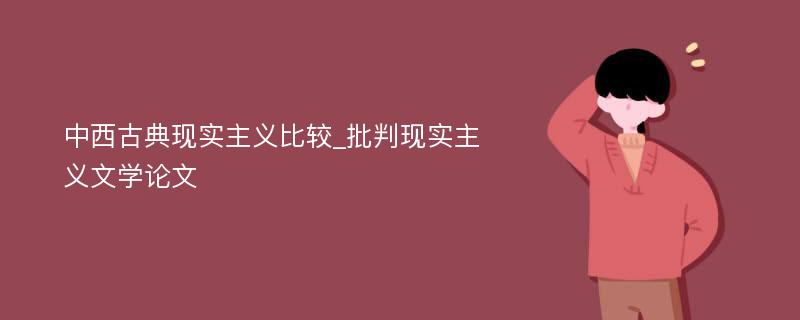
中西古典现实主义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中西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在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中出现了一股摆脱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他们更多地注意并吸收西方印象派、抽象派、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流派的经验;但在西方,不少作家与艺术家,特别是海外的华裔作家,在久久浸润于西方文艺之后,他们又转过来重新寻求现实主义。这种不同的趋势说明,事物总是在相反的两极运动之中前进的,各种文艺思潮,各种创作流派都需要发展。但不管怎么说,古往今来,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文艺潮流,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它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中西文学史上,什么时候才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存在分歧的。大致上有两类看法:一类认为现实主义是古已有之的,一般认为西方始于古希腊,荷马的叙事诗《奥德赛》就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则始于《诗经》。这就是说,无论中西,在奴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已形成了。另一类看法认为,现实主义产生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和文学发展的较高阶段。在这类看法中又有不同,对欧洲的现实主义,有人认为始于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其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是戏剧中的莎士比亚,小说中的塞万提斯等等;有人认为要从更晚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算起。至于中国,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形成是在唐代,它以杜甫、白居易的出现为标志;有人认为应该从南宋时代算起,因为南宋城市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孕育了资本主义因素,而现实主义的产生是同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
我认为无论中西,现实主义都是古已有之的。持第二类看法的人,大致有三条理由,而这三条理由我觉得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条,他们认为只有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才是现实主义的,所以西方要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算起,中国要从杜甫的“三吏三别”或南宋话本小说算起。实际上恩格斯这句话是对某些文艺样式(主要是小说、戏剧以及长篇叙事诗)而言的,并非是对一切文艺样式提出的现实主义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有基本的和严格的两种要求。基本的要求是现实主义真实性,即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严格的要求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较高阶段的某些文学样式的要求。用现实主义较高发展阶段的要求来否定现实主义较低发展阶段的存在,实际上否认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不断发展的,是目趋丰富、逐步成熟的。而且,即使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要求,说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始于杜甫或南宋话本小说,也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古希腊的悲剧,有的就达到了这个要求;在中国,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辞》等也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第二条,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是伴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因素一起产生的。这是用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其他阶段现实主义的不同创作方法,用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否定其他现实主义的存在。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它最早来自人民群众的劳动与审美实践,而且所有的历史上的不同阶级都曾经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文学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了的。第三条,他们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潮,最早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开始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形成和提出于十九世纪,因此现实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这种看法实际上混淆了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理论思潮的区别。这二者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理论、思潮是对创作的总结与推动,总是先有作品和创作方法,然后才有现实主义的思潮和理论。
虽然在西方和中国,现实主义都是古已有之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差异,现实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现实主义在西方古代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古代的现实主义;(二)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三)批判现实主义。西方古典现实主义的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是与西方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相联的,同时又是与其他文艺思潮相交叉而更迭的。比如西方古代现实主义产生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之后经过中世纪的宗教神秘主义与禁欲主义,发展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之后经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发展为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又出现了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等。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不同,没有那么多的各种主义。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并非象西方那样,按照社会性质以及与其他文艺思潮的交叉更迭而区分为不同阶段,而是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我国不同文学体裁中的发展和成熟过程来划分的,即:(一)先秦至魏晋的诗歌、散文中的现实主义;(二)唐宋时期的诗词与传奇中的现实主义;(三)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四)近代谴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我们将在以下与西方的比较中详而论之。
首先我们将西方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与中国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加以比较。中西方的这两个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大致都属于从公元前约五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左右,而其社会制度也都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
人类最初的精神活动是以客观现实为认识对象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于是在哲学思想上产生了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在艺术上则产生了朴素的现实主义,这在原始的绘画和歌谣中就已经存在了。但现实主义的发达,无论在西方或中国,都是在奴隶社会。古希腊时期,现实主义在创作上的代表是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德斯的部分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以及希腊的雕刻艺术;其理论上的代表则是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一开始就面向外部世界,侧重于客体。亚里斯多德所强调的艺术真实性是艺术对于自然客体的摹仿。它不但要求摹仿事物的外形,而且要求体现整体的真实。比如他认为,画鹿而不象鹿,比错画母鹿有角还不可饶恕,虽然他也强调技术上的精确性。他所说的摹仿,还要求人物直接出场而不依赖于诗人的叙述。他说:“史诗诗人应尽量少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否则就不是摹仿者了。其他的史诗诗人一直是亲自出场,很少摹仿,或者偶尔摹仿。荷马却在简短的序诗之后,立即叫一个男人或女人,或其他人物出场,他们各具有‘性格’,没有一个不具有特殊的性格。”(《诗学》第二十四章)西方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一开始就以摹仿论为基础,要求对人物的行为和性格作出刻画。这是因为西方的现实主义一开始便是在叙事诗与戏剧中成熟的。这种摹仿论正是对古希腊的雕刻、史诗、悲剧、喜剧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总结。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在抒情诗中成熟的,它以《诗经》为代表。《诗经》中的现实主义诗歌内容,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反映男女真挚爱情与婚姻问题的作品,如《关睢》、《卷耳》、《行露》、《静女》、《将仲子》等;(二)反映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作品,如《伐檀》、《硕鼠》、《黄鸟》、《板》等;(三)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如《七月》、《载芟》、《良耜》、《丰年》等;(四)歌颂国家和民族英雄人物的史诗,如《文王》、《绵》、《生民》、《公刘》等。其中除第三类中的《七月》和第四类的史诗可以算作叙事诗之外,其余占《诗经》绝大部分篇幅的,皆为抒情诗。在《诗经》阶段,少量的叙事诗都是以记事为中心,而不是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其中的人物,只是活动着的一个轮廓,看不到性格。比如《七月》虽然是《诗经》中有名的长篇叙事诗,但也只是记叙了农民自春至秋的辛勤劳动生活过程。《生民》、《公刘》写的是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后稷与公刘,是写人的,但同样没有性格,而只是记叙了他们为本民族所创的业绩。在中国,现实主义的叙事诗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典型环境,则是东汉以后(《孔雀东南飞》)的事,经过南北朝(如北朝的《木兰辞》)到唐代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以杜甫与白居易为代表)。
抒情诗是《诗经》中数量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在叙事诗中见不到的人物性格,在《诗经》的抒情诗中却可以略有所见。如把《柏舟》、《谷风》、《氓》这三首抒情诗加以比较,同样是遭到男子遗弃的三位女性主人公,表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性格。《柏舟》中的女子虽有怨恨,但很含蓄,很有身份,是上层社会家庭妇女的性格;《谷风》中的女子忠厚善良,丈夫新婚,她可怜自己,又不忍离去,是民间女子的柔弱性格;《氓》则是直率泼辣的劳动妇女性格了。但总的说来,这是一种抒情性格,通过不同的抒情方式和抒情内容,大致显示出某种性格倾向。而大量的抒情诗则是在抒情中带有某些简单的叙述和描写,有形象而无性格。通过抒发真实的感情来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达到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这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国的现实主义是在抒情诗中成熟的,因此在美学思想上,它一开始就面向内部世界,侧重于主体,通过主体的感受来反映客体,强调“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古典美学把审美情感视为艺术反映现实的中介,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所以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它以“言志”论为基础,首先强调情感的真实,所谓“修辞立其诚”(《周易》),“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论衡·超奇篇》)。对外界客体的真实描写,是为表现主体内部的真实情感服务的。外物只是“摇荡性情”的一个条件,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所以“状物”是“寓目写心”的一种手段,“写形”“貌色”是为了“畅神”(宗炳《画山水序》)。
中西方古典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不同还在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始于诗歌。希腊的史诗、悲剧与喜剧都是诗体文学,而且是叙事和戏剧的诗体文学,所以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一开始就重视语言修辞技巧和写作方法。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强调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在《诗学》中,他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中心,论述了刻画性格的各种方法和要求,如性格应当寓一致于不一致之中,“一桩事件随另一桩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情节应当“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等等。
中国的现实主义不仅始于诗歌(抒情诗),而且始于散文(历史散文)。在先秦阶段,散文中的现实主义是以《左传》为代表的。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历史散文,《左传》是第一部带有文学性的历史散文著作。《左传》虽然记载历史事实,但是其中不少章节已经把记事与写人结合起来,并且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了。它常常是在历史事件和政治、军事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刻画出他的特殊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通过郑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兄弟、母子之间矛盾的描叙,刻画出郑庄公沉着多虑、虚伪而又果断的性格;《曹刿论战》用人物对话来刻画曹刿的足智多谋和富于远见;《晋楚城濮之战》用很大的战争场面和错综复杂的矛盾描写,着重刻画了三个人物:楚国统帅子玉的骄傲鲁莽和匹夫之勇,终于因失败而自杀;晋文公的退让沉着和善用人谋;晋国大臣子犯的谨慎多智,用计击败强大的楚军。历史散文中的现实主义,到《史记》的人物列传就完全成熟了,它以刻画人物为中心来连贯历史事件,人物的特殊性格十分鲜明生动,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这类成功的人物描写,在《史记》中是很多的。因此西方古希腊时期对于史诗、悲剧、喜剧等艺术的现实主义要求,在中国却是在历史散文中得到实现的。只是中国历史散文中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又不同于西方的艺术“摹仿”,而是强调真实地记载真人真事的历史真实。这种对于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在历史散文中演化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就是提倡“信”与“真”,“勿虚美,勿隐恶”,“务实诚,疾虚妄”。而“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便成为体现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方法。历史散文中这种文学与史学结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方法,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与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重“美刺”、重“教化”、重文学社会作用的理论传统。
在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之后,中国和西方的现实主义命运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继奴隶社会的艺术繁荣而来的,是更高的社会形态——封建制度的降临,然而艺术却反而衰落了,现实主义遭到了禁锢和扼杀。从公元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将近一千年,西方处于封建专制与宗教独裁之中。高于一切的宗教神权与封建政权合为一体的统治,扼杀了科学和艺术,也就扼杀了现实主义的发展。中国却相反,艺术繁荣的极盛时期,无论就诗歌、绘画、雕塑、戏曲、小说而言,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都是在封建社会。在西方,艺术的再度繁荣,现实主义的高度发展,出现在封建制度动摇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来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中国又恰好相反,封建制度的动摇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并没有带来艺术的繁荣和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却呈现了相对的衰落状态。中西方这种二极背反的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暂不细论。
西方的古代现实主义经历了中世纪长期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之后,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其代表主要有卜迦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达·芬奇的绘画等。在文艺思想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戏剧的目的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塞万提斯在《唐·吉诃德》的序言中说:“描写的时候摹仿真实,摹仿得愈亲切,作者就愈好。”达·芬奇曾把画家的心比作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主张要用事物本身来检验所画是否符合实际事物,这是对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的进一步发展。而亚里斯多德提出的性格论,到文艺复兴时期则发展为个性论。卜迦丘提出诗应“描绘人类性格的不同方面”(《异教诸神谱系》),意大利著名雕刻家阿尔贝蒂要求艺术表现“这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与众不同的特征”(《论雕刻》)。他对于人物个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之上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体都是有差异的,“在成群的人中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声音、鼻子等等,完完全全跟另外一个人的声音、鼻子等等相似。”(同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经过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更迭,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便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阶段。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首先在法、英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西欧文学的主要潮流,它的最大成就是在小说、戏剧与绘画方面。法国第一部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斯丹达尔的《红与黑》,英国是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俄国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之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把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高潮。在绘画方面,法国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为自己的画展取名为“现实主义展览馆”,并在《宣言》中阐发自己的文艺主张。他说:“我认为绘画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艺术,只能描绘现实的和存在着的事物。……象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其《石工》、《葬议》、《画家的工作室》等画作,体现出完全不同于学院派的贴近生活的画风。库尔贝的支持者,文艺理论家夏夫列利把自己的论文集定名为《现实主义者》,公开揭起现实主义的旗帜,此后便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的理论思潮。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论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发展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再现”论。“再现”论的主要口号便是“不美化现实”。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人间喜剧〉前言》)别林斯基说:“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象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露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高尔基则说:“对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亚里斯多德的性格论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论,发展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巴尔扎克提出“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人物揉成典型人物”(《〈人间喜剧〉前言》),别林斯基则认为“典型是一般与特殊这两极端的混合的成果”,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人物、情节、环境的典型化原理,在他们那里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中国的现实主义在经历了第一阶段之后,仍然按照在不同文体中成熟的次序向前发展。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到唐宋不但成熟,而且有了高度的成就。这不但表现在反映社会生活面的广度和深度上大有进展,不但表现为现实主义内部形成了各种创作流派,而且表现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已经由《诗经》阶段的通过抒发真实感情来真实地反映生活、塑造抒情性格的方法,进入到用成熟的叙事诗的形式,以人物本身的行为,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性格的较高阶段了。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新丰折臂翁》等,白居易的《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是这一阶段诗歌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唐宋以后,现实主义的主要成就便让位于戏曲、小说了。但在唐宋,小说艺术也已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鲁迅所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中国小说史略》)因为魏晋的“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仍然没有跳出先秦历史散文的实录性质。所谓“志”,也就是对生活中存在事件的记录。到唐代,小说艺术有了质的变化,它从历史散文中完全独立出来,成为文人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称之为“传奇”。“传奇”表明并非历史实录,而是子虚乌有的离奇故事,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其中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其中塑造各种被侮辱、受损害的女性形象最为成功。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便是元明清的戏曲、小说阶段。与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在唐代完全成熟,达到古典高峰一样,小说、戏曲中的现实主义此时完全成熟,达到了古典的高峰。戏曲中的现实主义以关汉卿、王实甫、孔尚任等为代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以《水浒传》、《红楼梦》等为代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小说、戏剧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少有的。作品不仅反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爱情的题材更为深化,而且社会低层的普通人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和情感追求进入了文学,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村姑、绿林好汉,以至三教九流人物,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并且由于白话小说的繁荣,使现实主义小说更加贴切了生活和人民。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发展的第四阶段,便是近代谴责小说阶段。现实主义发展到近代,负起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的使命,产生了专门暴露封建制度和官场黑暗的批判性小说,自觉地用小说来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但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成熟就与繁荣远不如前。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峰。
从上述中西现实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现实主义最早是从叙事(史诗)与戏剧文体(悲剧、喜剧)中发展起来的。这两种文体要求如实地描绘和表现外界事物,创作主体应当隐藏在对客体的描叙和表现之中,而且愈隐蔽愈好。这就决定了西方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向着强调忠于客体的单线方向发展,产生了前面所述从“摹仿”到“镜子”到“再现”的理论。同时在艺术形象的构成上,重视细节真实和客观真实,力求逼真于生活原貌。如契诃夫所说:“描写首先应当逼真,好让读者看完以后一闭眼就立刻能想象出您所描写的风景。”(《致席尔凯维奇》)法国艺术家安格尔则说:“造型艺术只有当它酷似造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把它当成自然本身了时,才算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地。”(《安格尔论艺术》)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宙克西斯和帕尔哈西奥斯。他俩举行了一次绘画比赛,以决定水平的高低。宙克西斯画的是一个小女孩头上顶着一筐葡萄,葡萄画得非常逼真,以致麻雀都飞来啄食。宙克西斯洋洋自得地走到帕尔哈西奥斯的旁边说:“快把蒙在你画面上的幕布揭下来吧,让大家看看你画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帕尔哈西奥斯却若无所闻,仍然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宙克西斯忍耐不住,便伸手去揭画上的幕布。当他的手指一碰到那块“幕布”时,就猛然叫道:“我输了!”他对大家说:“我的画只不过骗过了麻雀,而帕尔哈西奥斯的画却骗过了我的眼睛!”原来帕尔哈西奥斯画的就是一块幕布。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实主义最早是从抒情(《诗经》)与叙事(历史散文)两种文体中发展起来的,此后现实主义的发展也是按这两条脉络交错推进而各自成熟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两种不同文体的现实主义精神方法又互相影响、渗透而终致融合。所以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呈双线方向交错发展的态势,既重视主体,又重视客体;既抒情、又状物;既强调情真,又强调事真。因此在艺术形象的构成上,要求达到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的统一。中国诗歌美学提出“诗言志”,其实所谓“志”即包含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要求在内。根据闻一多的考证,“志”既有志向、怀抱之义,又有记录、记忆之义(《歌与诗》),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诗言志”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这就是说,一方面思想感情的表达要与艺术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相符合,另一方面对客观事物的记叙描绘要为表达思想感情服务。主客观统一,也就有了中国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性。唐代的张璪说到画家的创作应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达到心与物的统一。陆机《文赋》一开头就提出了正确处理“意”、“物”、“文”三者关系的问题,主张“意”须“称物”,“文”须“逮意”,“文”便是“意”与“物”融合的结果。钟嵘把这个道理概括得更加简洁明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清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情景交融”的要求。所以中国现实主义美学所要求的艺术形象与西方不同,不是纯客观的描写,而是情与物的主客体统一。因而艺术形象所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也不是逼真与酷肖生活,而是“介乎似与不似之间”。“似”是由于它有忠实于生活的因素,“不似”是由于它融入了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对客体有所改造。清代的松年在《颐园论画》中对中西绘画作过如下的比较:“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赋色真与天生无异,……中国作画,专讲笔墨钩勒,全体以气运成,形态既肖,神自满足。”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重视的不是表现现象的真实,而是强调自然与人格的统一。举例而言,中国画喜欢画竹子。从西洋画的观点看,艺术家眼中只有自然之竹,应当把竹子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地画出竹子形状的特征。用这种画法画竹子,画不了几次就没有什么可画的了,可是中国画便不然。中国画不但强调画出竹子自身的特征,而且强调要在笔墨的运用当中,表现作者的精神和人格。所以郑板桥说“眼中之竹非胸中之竹”,因为“胸中之竹”已经融入了艺术家的人品和情感体验。竹子成了某种人格精神的生气灌注,具有无穷的笔墨情趣,永远画不完。徐渭讲到自己画竹时说:“山人写竹略形似,只取叶底萧萧意。譬如影里看丛梢,哪得分明成个字?”他画竹用笔涂抹,不拘泥于叶片的“个”字形状,而求其精神气韵,这便是“介乎似不与似之间”的“不似之似”的艺术形象。
中西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在艺术形象构成方面的另外一个重要差异便是,西方提出了“典型”论,中国提出了“形神”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一)它们都是造型艺术和叙事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二)它们都要求写出人物性格的个别性和特殊性。西方的典型理论自十八世纪以后对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尤为关注,德国的希尔特首先提出:“我认为古代艺术的原则不在客观的美和表情的冲淡,而只在个性方面有意义的或足见出特征的东西。”(《古代造型艺术史》)歌德认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歌德谈话录》)黑格尔要求典型人物应该是完满有生气的“这一个人”,别林斯基则强调典型应当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陌生人”。总之,独特的个性刻画是典型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的艺术形神论最早产生于绘画艺术,自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的原则之后,至明清便逐渐渗透到小说与戏曲理论之中,其目的是为了塑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李贽称赞《水浒传》作者“真是传神写照妙手”(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四回评语),金圣叹指出《水浒传》“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读第五才子书法》)。但是“典型”论与“形神”论在共同重视人物形象个别性的基点上,却朝着不同的方向演化。西方的“典型”论可以说是由性格的个别性向外、向量的方面铺开,而中国的“形神”论则由性格的个别性向内、内质的方面深化。“典型”论强调性格的个别性必须体现普遍性和概括性,也就是共性。这种共性实际上就是人物性格的代表性。在西方,“典型”这个概念的提出,最初指的便是代表性。在古希腊文字中,“典型”的语义本是指铸造的“模子”或“模型”,引申为“楷模”。这与中国汉代《说文解字》对“典型”的解释不谋而合:“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为之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为典型。”因此西方的“典型”论视这种普遍性、概括性、代表性为艺术典型之内核。因为个别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但生活中的个别并不都具有代表性,艺术典型的任务便是使生活中的个别经过艺术概括而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比如贺拉斯就把典型视为某一类人物的代表;孟德斯鸠举例说,“美的眼睛就是大多数眼睛都象它那副模样的眼睛”(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巴尔扎克认为,“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点;典型是人类的样本。”(《〈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别林斯基表示了相似的见解,认为“典型人物是整个一类人物的代表”,以至“即使在描写挑水人的时候,也不要只描写一个挑水人,而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别林斯基论文学》)由于典型的普遍性包含着这种数量上的要求,因而在典型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某种类型化的倾向。比如从古希腊到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典型理论便是以“类型说”为主导的,其代表人物为柏拉图、贺拉斯、布瓦洛,即便是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典型时,也存在着类型化的倾向。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典型理论向强调个性特征的方向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希尔特与歌德。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与别林斯基则建立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统一的典型理论,但在别林斯基的有关论述中,仍然存在着某种类型化的倾向。
其实,典型是否必须是一定数量的某类人的代表呢?中国古典美学并不这样认为。艺术形神论完全撇开了这种数量上的代表性,它在人物个别性的基础上向内、内质的方面深化。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便是要求人物的独特性须经外在的“形”(形状、言谈、行为)向内在的“神”(精神、气质、个性)推进。中国美学家认为,人的形体外貌可以相同或相似,但“神”却是个人所特有的。比如清代的美学思想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所谓“传神”,就是要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与个性特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神”是与“形”相对而言的,“形”是事物的现象,而“神”才是事物的本质,“以形写神”就是要通过对独特的现象的描写来揭示事物独特的本质。所以艺术形神论认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并不在于它的数量上的代表性,而是要紧紧抓住事物的个别性与独特性向内部深处开掘。艺术的生命在于“神”。只要既写出生气灌注、气韵生动的个别性格,又揭示出这种个别性格所蕴含的内在本质意义,它就达到了形与神的统一,它便是高度成功的艺术形象。所以,中国的艺术形神论一开始便避免了西方典型论所出现的类型化倾向,而强调刻画人物的个性性格与特殊性格。李贽最早将“神似”的要求运用到小说创作与评论中来。金圣叹接着用性格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和研究《水浒传》与《西厢》,指出这两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就在于人物个性性格刻画的成功。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西厢记读法》)创造了三个个性独特的人物。又说“《水浒》所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等等(《水浒传序三》)。由此可见,金圣叹所说的“性格”是指人物身上内在的与外在的两方面独特性的统一。内在的是独特的“性情”、“气质”、“胸襟”、“心地”等,外在的是独特的“形状”、“声口”、“装束”等。这两方面的统一,就是人物的独特个性。
中国艺术形神论的美学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笔者已有《论艺术形神论之三派》(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与《中国典型理论与形神论》(载《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1期)二文略加探讨,故而不再细论。这里仅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角度将西方的典型论与中国的形神论作一些粗浅的比较,以期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标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诗经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七月论文; 诗学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