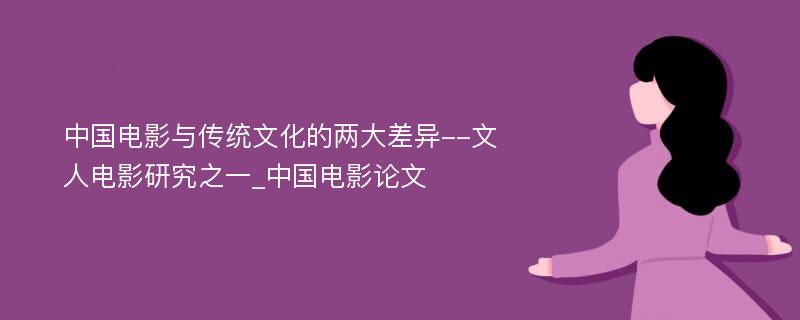
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两大分野——文人电影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两大论文,文人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传统文化一维来探讨中国电影发生、发展的面貌,并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整体影响,这是本论文的基本出发点。本论文试图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梳理起步,在对古典文化中与电影艺术演进有着密切关系的“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两大文化传统细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电影传统的两大分野: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人电影做一个初步的工作。
对古典文化传统的梳理
讨论百年中国电影,也许最不应该忽视的是传统文化对电影这个现代媒体的影响。
190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注:《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作《定军山》的拍摄时间为秋天,有误。依弘石考为春夏之交的一天。见《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二期。),当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第一次欣喜地站在那个当时还称作“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旁,技师刘仲伦第一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摇动起这个机器时,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胶片上感光的却是京剧《定军山》。在这一极容易被看作是一次偶然的行为上,似乎不应该忽视它的必然性。当风景、时事、滑稽短片在中国银幕上大行其道已十年,并越来越遭到观众的厌弃时,与一个深厚的传统文化结缘的京剧走进了电影。史学家提醒人们也许不该忽视的是此举的象征意义:“中国人自己一开始拍摄电影就与本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联姻,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新兴的外来艺术形式,在民族传统艺术中汲取生长的营养和依傍的力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注:《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作《定军山》的拍摄时间为秋天,有误。依弘石考为春夏之交的一天。见《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载《电影艺术》1992年第二期。)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提醒:中国电影的发生与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多少论证的命题。事实上,近百年来传统文化这只无形的手一直潜在地支配着中国电影的面貌和特质。
电影作为一种纯正的舶来品、一种现代媒体,其生成、发展一直与域外的异质文化结缘。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第一部短片《定军山》时,中国观众已看了十年的外国短片。资料显示,1896年到1937年在中国发行的外国影片共有5058部,而到1937年国产影片数量不过1144部,仅占上映影片总量的约18%(注:资料出处:《在华发行的外国影片目录》,载《中国电影研究》第一辑。转引自刘成汉《电影赋比兴集》,(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一版P166。)。而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电影市场中又占有绝对的地位。“中国解放前的电影市场,五光十色的好莱坞作品遮天蔽日,拥有绝对的优势,上海豪华的高级影院,都由美国制片公司踑踞独坐……”(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蔡楚生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6 月第一版。)中国电影的生长、发展与域外电影文化有着相当明晰的关联,也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语境中,任何一种艺术种类或媒介的基本面貌都是由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等三维文化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影响而决定的。但是作为一个与外来文化广泛交流的时代,人们对这一个时代的文艺似乎更关注于外来文化的强劲撞击。不妨先看一下与中国电影同时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学(注:中国电影虽起步于1905年,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合作拍出《难夫难妻》,但形成一个叙事影片的完整概念应该是10年代末与20年代初的一批长故事片的拍摄。而此时中国现代文学胡适、陈独秀扯起的“文学革命”的大旗正猎猎飘扬。中国电影与现代文学具有相似的时间段与文化语境。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为一个时代里并肩长大成人的姊妹。)。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感受一直是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断层”与“决裂”。这样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往往注意中国作家对某些外国文学的形式技艺或思想观念的模仿,而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另一种情况;域外文学只是提供一种与具体表现手法无关的新的文学观念,由此诱发出追求革新的文学运动;在此期间,中国作家无师自通地转化了传统文学形式。”(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 月第一版。)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显然而且也必然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不论什么方向的风吹雨浸,决定这块土地物种面貌的仍然是这方水土。
著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建立起一个被人广泛赞誉的、具有方向性意义的起点,也是他“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题目之一”(注:《序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即五四新文学与古典文化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无论如何都不会摆脱的强大背景。在普实克所有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中,都敏锐地觉察到古典文化在五四新文学上产生的复杂的历史回响。其实标明这种联系并不是特别重要,普实克的意义在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审视中,为我们梳理出的被美国学者李欧梵称之为“准传统”的两个重要的文学系统,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进一步细化的分解:
“传统的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这正是他着力研究的题目)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不断增长的活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所谓的士大夫文化教育——其道德影响、其语言的精确性以及表达上的技巧和复杂性。”(注:《序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
这两个传统,更具体来说就是李欧梵在编辑普实克的论文集中起的那个画龙点晴的名字:《抒情诗与史诗》。在普实克的研究中,“‘史诗(的)’是用来概括一个比诗歌更为广泛的文学体裁范围。它与‘抒情(的)’一词相对立而成为艺术反映现实的另一个主要的手段。如果说郁达夫和鲁迅的小说在抒情性方面使人联想到诗歌,茅盾的小说则以其大规模地、客观地表现生活和社会的艺术构思而具有‘史诗’的气魄。”(注:《序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尽管普实克着眼于“抒情诗与史诗的交汇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角度(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1224。),并以此来展现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交汇影响,但我们感兴趣的仍然是普实克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两大系统的清理,即“高雅精致、注重抒情的文人文学”与“粗俗清新、长于叙事的民间文学两大传统”(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1225。)。“史诗的—民间文学/抒情的—文人文学”这种便捷而清晰的归纳,对于中国电影的研究探明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向标。因为在我们看来,在20世纪初共同发轫的现代文学与中国电影,无不背倚着强大的同一个古典文化的深厚背景,无不处在同一个古典文化高大背影的笼罩之下。
《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宋代话本小说、明清章回小说及说唱文艺和《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歌、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等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它们几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很难想像当抽掉了这些文化典籍后传统面貌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细加辨别,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两个并行的文化序列积淀下来的艺术精神。那就是以史、传或者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文学作品为主要形态的前者,表现出了讲究再现、注重叙事的文化传统,以诗歌或者是以诗歌精神为基因演化出来的文学作品为主要形态的后者,表现出了讲究表现、注重主观情感抒发的文化传统(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钟大丰《艺术个性与审美主潮》等相关论述。其中钟文收《论水华》,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也许这两个传统塑造中国文化面貌的作用太强大了,以至于我们在普实克的观点外,或可以列出一组基于不同的语境而类似的概念:史诗的/抒情的,民间的/文人的,俗的/雅的,热闹的/冷隽的(注:“热闹”与“冷隽”这组概念是弘石在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中,针对以郑正秋、张石川为代表的和但杜宇、洪深为代表的两种银幕美学风格的概括。参见《无声的存在·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大众的/精英的等等。 这些或着眼于艺术形态,或着眼于文化类别,或着眼于美学品格等不同路径的表述,但都能九九归一地感悟到强劲的两大文化传统。或许每一个视角都会带来不必要的岐义,现代文学学者陈平原干脆以其典籍的名字为这两个古典文化传统命名,称之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即“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与《诗经》、《离骚》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骚’”(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472。),也就是“编年史、纪传、 纪事本末等多种历史编纂形式和古风、乐府、律诗、词、曲等多种诗歌体裁”。如果说史传传统重客观、写实,建立并丰富了一套人们详熟的叙事观念与法则,尤其是在明代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其中的许多叙事观念与技术都滋养并繁盛了民间文化,并与市民阶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么诗骚传统则以主观、抒情、表现,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抒情言志的传统,深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表现出文人文化的观念与操作。因此,诗骚传统常与雅的文人相联系,而俗的民间的文化形态又常常在史传传统中吸取。我们不妨说史传传统基本体现出民间文化的特色,而诗骚传统体现出文人文化的特点。
戏人电影传统
由中国古典文化的两大系统的梳理起步,我们也就有理由探讨电影这位纯正的外来品的现代技术宠儿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如何打上中国古典文化的“胎记”,如何与中国古典文化结缘的。
两大文化传统在中国电影百年中荡起的回响应该是很清晰的,这就是流淌百年而不绝如缕的两大电影传统,我们称之为“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是香港电影学者在对3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群体研究时,广泛使用的两个称谓(注:参见焦雄屏:《时代显影》一书,(台湾)远流股份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3月出版。)。 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已经不仅局限于3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它已构成了整个中国电影百年的一种创作现象,同时也成为程度不同地弥漫在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精神。
电影本质上是属于民间文化/市井文化的范畴,民间文化充满着对“故事”的渴望,民间文化的消费者常常从一个一波三折的叙事中带来愉悦、幻想与满足,因而电影很容易与史传传统发生天然的粘合与亲情。城镇是与商品经济紧密相连的,城镇的出现与繁荣必然会出现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必然产生本阶层的文化,这就是市民文化。在市民阶层最终形成的宋代,以瓦子为特点的娱乐场所的出现表现了市井文化的高度成熟(注:参见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明清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与壮大,市井文化蔚为壮观。近代的市民文化为20世纪初电影这个涓涓细流注入了活力,市民文化直接催生并发育了电影。 从电影诞生到30年代,电影一直被称为“影戏”或者“西洋影戏”或“电光影戏” 。而影戏这个最早出现于汉代,兴盛于宋代,千余年来生生不息的市民玩乐方式,不过是林林总总的市井娱乐技艺的小小的一个(注:《武林旧事》卷6曾列举了55种的市井技艺,棋琴说唱, 杂耍游戏等不一而足。转引自参见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P76。),“影戏”这个最具市民化的称谓,反映出人们在对电影最基本的观念:看来电影如影戏一般,不过是个消遣、解闷的方式之一。最能说明个中道理的还有一件颇值得说道的事情。中国电影诞生于北京,却兴盛于上海,弘石注意到这个有趣的现象,“由北京至上海,这种地域的变迁所预示是什么呢?”(注:“热闹”与“冷隽”这组概念是弘石在对20年代中国电影的研究中,针对以郑正秋、张石川为代表的和但杜宇、洪深为代表的两种银幕美学风格的概括。参见《无声的存在·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在弘石看来,正是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近代文化中心的上海”才能为电影提供了经济和“精神气候”的保障,同时也在上海这个“新剧的大本营”找到了“另一种本土文化的依傍”,“为中国叙事电影的最初成长提供了经验和人才”。我们更想进一步说明的是,正是上海这个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沿海商业城市,其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和相当兴盛的市民文化无疑为电影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并成为电影地缘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电影当时的消费场所常常是茶楼、戏院等公共场所。市民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保障。当人们看这个“电光影戏”时,也粗心地把它等同于皮影时,这实在小看了它。至少皮影戏那种手工艺人的小操作、小玩艺的寒酸相已不能同日渐财大气粗的电影同日而语了。电影作为现代光学、化学、机械学的产物,在观众几角钱、几分钱的门票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电影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像是安装一个永动的马达,开始进入了一个无休无止的运动轨道。与任何一种商品形式一样,在“生产者/作者—产品/作品—消费者/读者”的流程上,消费者永远处在高度主动的地位,它支配着产品的生产,左右着生产者的决策和意志。“作者”作为“最善于掌握他与听众共同使用的代码的人”,已不仅是对作品拥有的一个标志,“任何叙事作品都依属于一种‘叙事作品语境’,即叙事作品赖以受到消费者的整套规定。”(注: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作为长期在说唱文学、话本小说、戏曲、 民间故事等通俗文艺形态下滋养起来的市井文化,他们的文化趣味直接规约了电影的发展。电影因对物像的直观录制,本身所具有的新奇、热闹、好玩,就注定了电影起初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藏在深闺对春伤神的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而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大街上放浪形骸的顽童。电影面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必然与长于叙事中获得满足的史传文化传统发生较强的亲和力。
更具体地来说,史传传统究竟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样的遗产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史籍尚表现出文、史、哲一体的混沌面貌,即便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中已出现了讲究情节的曲折、突出人物形象的若干篇章;纪事的编年史书《左传》中多国交战的战争描写,其叙事来龙去脉交待的完整,叙事结构的清晰,颇具戏剧性的情节,无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国策》中鲜明而鲜活的历史人物,同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而被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其实录精神,善于在复杂而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其琳琅满目的人物形象也构成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长廊。《汉书》作为断代史的纪传体史书,主要着眼于那些忠臣、奸臣等类型化的人物,不妨说这些类型化的人物已长久地活在后世的民间故事、戏曲等作品中了。这些特色鲜明的史籍以自己的方式对于此后的叙事文学都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人们往往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感受到叙事魅力,表现出对戏剧化情节的迷醉;喜欢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鲜明的或者说类型化的性格;结构当然有头有尾,条理清晰而完整;伦理化、道德化的意旨自然流布于故事的里面等。史传传统显然启迪了后来的传记文学、传奇文学、话本小说、白话小说(注:参阅《中国传统文化大观》中《章回小说》一章,P145—P16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明清章回小说发源于宋元的“说话”民间样式, 其叙事形态在其四大经典的白话小说名著中已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章回小说特别强调一个完整结构的故事,遵循“入话——正话——煞尾”的封闭式叙事模式;新奇、曲折的情节、故事在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一部小说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有一个让人们感叹不已的“故事”;在情节的演绎中一定有着类型化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由此最终故事的背后自然呈现出劝善惩恶的主旨。口传心授,代代不息,从民间到文人,在叙事的丰富的传统中,人们接受了此类的叙事方式,也不自觉以此类的叙事方式传播于后。当20世纪初的人们看电影这个光怪陆离的黑白影像时,这个积淀于人们血脉之中的叙事法则作为一个无形的手在悄悄地发生着作用。其结果就是“戏人电影”(注:此处的“戏”是戏剧的“戏”而非戏曲的“戏”。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中曾辨别了中国戏曲与外国的戏剧有何不同。他认为,把中国的戏曲译成drama 并不准确,更应该译为opera,因为中国戏剧本质上与英国传统戏剧不同, 歌曲时时出现,比对白更显重要。因而中国人的观念往往是去“听”戏,而不是去“看”戏。歌曲的本质在于“是以色彩、声音、气氛和情绪的组合来造就艺术效果。”“戏剧的表演手段是口头语言,而歌剧却是音乐和歌唱。戏剧的观众希望了解剧情,并为戏剧角色的冲突、出人意料的发展和新奇的表演而感到喜悦;而歌剧的观众之所以去度过剧场之夜,却是为了让音乐、色彩和歌曲来麻木自己的理智,抚慰自己的感官。”林语堂认为,“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中国戏剧作品中诗化的内容所包含的力度和美感远胜于唐诗。我深信,尽管唐诗十分可爱,然而中国某些最伟大的诗篇还得到戏剧和小调中去寻找。”“如果一个人读完了古典诗歌转而而去读剧本里的曲词(如上所述,中国戏剧基本上是诗的集合),那么他的感觉就像先观赏一束精神美的瓶花再去游园一样,感到后者远胜于前者:新鲜、丰富、多样。”)。
在郑正秋、张石川(20/30年代)、蔡楚生(30/40年代)、郑君里(40/50年代)、谢晋(50/80年代)这几组横跨中国电影百年的电影人物及其影片背后,我们直感到这个无形的手的鲜明存在。在他们身上体现相似的特征:要求新奇、热闹的银幕形态,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获得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满足,追求简单、明了的类型化的人物,他们常常是善恶的化身,其主旨自然呈现出伦理教化的主旨等等,显示出史传叙事传统的潜在影响和本世纪初市民趣味的巨大存在。不妨看一下在戏人电影的诸特征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情节。情节在影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越是在电影的早期,这个特征也越是明显。只要讲清一个“故事”,影片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而人物常常是情节发展的一个善善恶恶的标志符号。这样的影片情节的发展最重要。20年代的默片中,以郑正秋、张石川为典型代表的创作者那里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郑正秋看来,在影片的创作中,“先决问题还在有没有好情节,要是想出好情节,不论什么顾虑都是杞人忧天;要是想不出好情节,那就是什么好处都是镜花水月。”(注:郑正秋:《“姊妹花”外“再生花”》,明星半月刊,三卷四期。)曾有人向张石川打探他的影片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张回答:“无他,剧情见胜耳。盖国产电影怒崛至今不过三年而已,观众程度于上海一埠稍见参差外,余皆以明了为先。而吸引观众以动情者,惟有剧情见胜。”(注:引自弘石等:《中国电影史》 P20,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有人在总结以郑、 张二人为代表的20年代的所谓“旧派”创作特点时,就把他们的创作归结为“情节剧”:“对情节剧的追求,和由此产生的旧派剧作情节曲折多变的共同风格,构成了旧派创作的情节剧特征。”(注: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P108。 )从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经1913年的《难夫难妻》,到20年代初包括《海誓》、《红粉骷髅》和《孤儿救祖记》在内的一批长故事片的拍摄,电影由原来的不足七本的短片跃为超过十本以上的长片,电影突出的成长与变革就是有了一个较大容量的“故事”。能否编一个很好看的“故事”成为影片创作的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决定一部影片成功的主要因素常常是编剧而不是导演。这也就是郑正秋为什么在二三十年代如日中天的原因之一。
选择这几组电影最典型的人物,不仅是为了论述上的便捷,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类”的意义。事实上,判评一种事物“类”的意义时,并不要采集全部标本,而只要所选取的标本具有“类”的意义。正如研究一株植物,并不需要把一座山上所有同类的植物都要采集来一样,只需把最典型的此类植物特性充足的样本加以研究即可了。20世纪上半叶,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显然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重要转折点。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才根本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柯灵将其称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而这一分水岭左右的标志一个是郑正秋,一个是蔡楚生:“郑正秋逝世表示结束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着另一幕的开头”(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蔡楚生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但是如果从戏人电影的传统着眼,我们倒是愿意把他们两人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大传统的土壤中、在不同时代里生长出来的两棵大树。郑正秋在1922 年编剧的《孤儿救祖记》、1931年编导的《姊妹花》,蔡楚生1934年编导的《渔光曲》、1945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中国电影前半个世纪的一个个伟大的界标,不仅成为电影本身的巨大收获,而且成为轰动当时的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戏人电影当然会拥有最大量的观众,它们总是与最广泛的观众达成最大程度的认同。《孤儿救祖记》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曾庐影戏院一开始公映就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它给各地观众带来的兴奋超过了任何一部外国影片,“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注:引自弘石等:《中国电影史》P20,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姊妹花》当年在上海新光戏院连映67天(注:香港博益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的《论尽银河》P67。 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台湾)电影图书馆出版部,1986 年9月出版,P18。)。《渔光曲》创下了比《姊妹花》还要多出20 天的营业纪录。而《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注:刘成汉:《电影赋比兴集》,(台湾)远流股份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9月出版,P129。)成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卖座之一”(注 :刘成汉:《电影赋比兴集》,(台湾)远流股份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9月出版,P129。),“首映时曾创下连续放映3个月、观众达70余万人次的空前纪录。”(注:引自弘石等:《中国电影史》P20,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1月出版,P95。 )“似乎本片能使受过八年苦难的人们得到宣泄,普天下同声一哭。”(注:刘成汉:《电影赋比兴集》,(台湾)远流股份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9月出版,P129。 )这该是何等的轰动!
在中国电影95年历史中,这些影片都成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无可争议的代表作。而谢晋在中国电影下半个世纪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余秋雨称,“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那是因为谢晋“成了一个历史的象征”(注:余秋雨:《序言·论谢晋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0月版。)。5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80年代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同样也是该时期的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之一。
面对《孤儿救祖记》(郑正秋/1922年)、《姊妹花》(郑正秋/1931年)、《渔光曲》(蔡楚生/1934年)、《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1945年)、《林则徐》(郑君里/1959年)、《红色娘子军》(谢晋/1960年)、《天云山传奇》(谢晋/1980年)、《芙蓉镇》(谢晋/1986年)这一个纵跨近百年的电影名单,其间电影由默片到声片,由黑白到彩色,由单声道到立体声,由普通银幕到宽银幕,但却反映了戏人电影的一个大致特征:主题的明确而鲜明,矛盾冲突的尖锐、激烈,情节的跌宕起伏,叙事结构的完整而清晰,鲜明的人物性格等等。在戏人电影这个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谢晋成为四棵巍然挺立的大树。而其影片形态与史传传统的接近,还可以通过人们对影片的评价看出来。人们在对影片的赞美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史诗”之类的字眼。“将人物命运的传奇性、价值评判的伦理性,以及传统的编年历史叙述方式,与博大深刻的社会内涵统一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式的银幕史诗树立了杰出的典范。”(注:李少白、陆弘石:《昨夜星光灿烂》,《羊城晚报》,1999年4月25日。)对于《八千里路云和月》, 人们则认为“创作者有着明确的以电影的方式概括和书写历史的‘史传’意识。”(注:引自弘石等:《中国电影史》P20,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P94。)
文人电影传统
正如人们面对茅盾小说很容易想到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深度和广度的“史诗”气魄,而在郁达夫、鲁迅小说中更多感悟的则是他们与中国抒情诗传统的内在关联(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同样我们也会在清理出郑正秋、 蔡楚生、郑君里、谢晋构成的链条后,发现与之并行的另一个链条。这就是经过20年代的但杜宇、史东山、洪深等尚为混沌、但已个性初露的面目后,在30年代的孙瑜、吴永刚、费穆等人的如《大路》、《神女》、《浪淘沙》、《天伦》等形态发育相当成熟的作品,清新、淡雅、别致令影坛为之一震,到40年代费穆的《小城之春》达到一个令后人至今仰慕不已的高峰。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这条并没有消失的河流在当时的气候中又泛出极为珍贵的浪花。这就是50年代的《林家铺子》和60年代的《早春二月》。电影在经过一个封冻的文革十年后,一个如涨潮般的创作现象开始出现,80年代以《城南旧事》、《乡音》、《青春祭》为典型代表,90年代初以《心香》等为代表,我们都能明显地找出一条与诗骚传统相接应的抒情的文人电影的生生不息的潮流。
具体来说,诗骚传统给电影带来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呢?
不论是来自民间的《诗经》,还是文人的唐诗、宋词及至元、明戏曲,都构成了与史传迥然不同的文化艺术形态或者说艺术精神。而在诗、骚、词、曲、赋各类抒情性的体裁中,诗歌又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古代诗人数以万计,流传下来的作品数以百万计(注:《诗歌词曲·中国传统文化大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仅一个唐朝现存诗就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歌大国。闻一多先生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注: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转引自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第一版。)。诗歌在社会中扮演着如此强大的角色,以至于在孔子看来“不学诗,无以言”,诗歌在社会中还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甚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现代人认为,“一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社会性史、心态史。”(注:参阅《中国传统文化大观》中《章回小说》一章,P145—P16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P111。 )与之相伴的是关于诗的理论也就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说诗论几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代表。关于古典文艺美学的最重要的观点都几乎与诗歌有关。诗歌的作用是如此深厚而强大,其审美风格、精神气质如此广泛辐射于中国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林语堂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他甚至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注: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P241。)诗歌的美学特质已融入中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诗歌这一载体所体现的艺术观念甚至在无形塑造着中国文人的人格。而以诗入画就可以看作是绘画的最高境界,此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魅力独具、源远流长的独特画种——文人画就与诗歌的精神结下了不可解的缘份。
诗骚传统是中国文人文化的载体,在其所有的特质中最根本的是它的抒情传统。诗、骚、词、赋、曲是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形态内,展示作者的性灵与才情,抒情言志成为附着在这个传统上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在诗骚传统上绝大多数文本都是抒情性作品,“这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名篇都是抒情诗。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474。)抒情不是一个技巧层面的, 而是体现在文本整体上的一种精神。普实克就把中国文艺中这条“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概括为“抒情诗传统”(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 林语堂在探讨中国绘画的传统时也把它总结为“抒情性的传统”,他提醒读者要从造成绘画特质的诸多因素如诗歌中才能理解绘画的这种抒情传统(注: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12 月第一版,P292。)。
诗骚的传统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能不影响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骚’的抒情特征,否则就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474。 )电影当然也无法逃脱这一传统的滋养,表现在电影文本上,导致情节必然弱化、退隐,取而代之的是抒情性文艺精神在文本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并决定了文人电影颇具特色的镜头语言。不过诗歌与电影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体裁。诗歌是抒情的,电影是叙事的。至少诗歌以抒情为主,叙事为辅;电影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仅靠抒情而存在的影片;电影必然有基本的叙事存在。电影总是植根于深厚的民间土壤中,并在大众乐于掏钱买票入场的支持中获得生存。不妨说民间文化已成为电影的母体,电影成为人们联结民间文化的“脐带”。电影作为一项媒体,在民间土壤中诞生出来的戏人电影也就成为电影史的主流。正是由于诗骚传统与电影的先天性“不和”,在史传传统支配下的戏人电影构成的滔滔不绝的河流中,文人电影却一直若隐若现。人们也只能从繁茂芜杂的电影面貌中,仔细探寻才能发现文人电影的文本。
史传/诗骚两大传统与戏人电影/文人电影绝对不能是一个各顾各、一对一的直系单传。事实上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交互的而非独立的,融合的而非分解的,相互渗透的而非相互排斥的。普实克固然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史诗传统与抒情诗传统各自与古典文化的承传关系,但其是以“抒情与史诗的交汇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这样一个角度(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P1224。)来建立他的学术视野的。同样,我们以一种融合的眼光看待中国电影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不过本论文的重点是对中国电影一脉——“文人电影”的研究。
从电影史整体观之,电影作为一个叙事艺术,其戏人电影表现出天然的强大力量,一直主宰着电影史的方向,并确凿无疑地在电影史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不过,与蛮横的戏人电影相比,娇小可人的诗骚传统也总会从另一个角度不断地撞击着电影史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电影史增加一个独异的面貌。这种撞击不仅表现在即使一个典范的戏人电影也常常会吸取诗骚传统的某些因子,并出现了许多早已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影片个例,而且在合适的条件和气候下,某些典范的文人电影文本就会发育成熟。
不过仍需补充的是,戏人电影与文人电影这一组相对的概念,其本身自有其相对性的一面。概念无非是对某一事物“类”的界定,必然造成对一个完整事物的硬性分解,特别在性质与形态相近的事物上相对性更会明显。本论文中使用的戏人电影、文人电影文本,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有着该属类的文化特征的文本。事实上电影史上相当数量的影片有着混沌的面貌,像一个连体婴儿一样。正如阿诺德·豪泽所说:“精英艺术、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的概念都是理想化的概念;其实它们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的。艺术史上出现的艺术样式几乎都是混杂样式。”(注: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一版,P120。)对戏人电影、文人电影也作如是观。
设定戏人电影/文人电影这样一个框架来讨论中国电影,当然也就有了一个框架的明晰、概括和高度,也同样有了一个粗线条应有的不细致和可能出现的误用。应该警惕非此即彼的决断。同样,我们也绝不能以戏人电影/文人电影对中国电影传统的梳理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对中国电影史的想像的激情,这或许是本论文的价值所在。
电影当然是一项文化工业,面对着电影百年充满着浓厚“制作”色彩的一层层冻土,一个个充满着性灵的“电影作者”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破土而出。这个突围的过程是悲壮的,孤独的,当然也是痛苦的,其间常常需要忍受着不被观众认可,不被投资人认可,甚至不被一个时代认可的郁闷。
这个突围的结果就是“文人电影”的出现。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一江春水向东流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孤儿救祖记论文; 定军山论文; 姊妹花论文; 渔光曲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