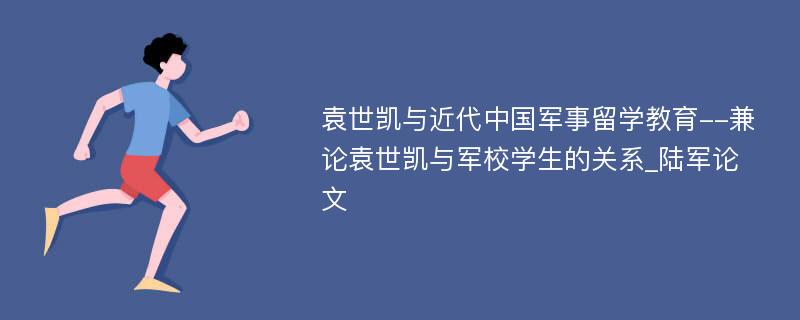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军事留学教育——兼论袁世凯与军事留学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事论文,留学生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关系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4-0012-05
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社会首先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就是军事制度。其时,清帝国的旧式军队已经日趋腐化,在西方列强的坚甲利兵面前,更是不堪一击。因此,朝野人士亟思改革,一方面设立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另一方面,选派军事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
1875年,福建船政学堂派魏瀚等5人赴英法参观学习海军。1876年李鸿章派遣武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这是近代派遣军事留学生之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欧洲的先导。此后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清朝派遣军事留学生始终以赴欧洲学习海军专业为主。与海军留学教育相比,陆军留学生人数少,规格低,处于可有可无的次要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陆军留学生逐渐增多,成为军事留学生的主流,而派遣国则主要集中在日本。陆军留学生的派遣之所以长期不受重视,与清政府抵御外侮的“重海轻陆”政策有关。直到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清廷才将军事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新式陆军建设上来。如同海军建设一样,陆军建设首先需要人才,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就是留学,而且比作为练兵第一要义的设立学堂还要重要。
袁世凯对于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1895年5月7日,他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说:“仍一面广设学堂……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1](P218-219)在同年11月呈报军务处的《练兵要则十三条》中又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2]。于是,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就创设了德文、炮队、马队、步队四个随营武备学堂。从正兵内考选粗通文字者230余人入堂学习,“此学堂学生分三部分:一为留学预备班,五十人,德国军官为总教习,学德文、武备、汉文三种……”[3](P70)。虽然这批留学预备生没有赴德学习军事,但说明袁世凯当时已有派人留学军事的考虑。
1898年,浙江省首次派遣4名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为近代留日陆军生之开始。这年湖北学生吴禄贞、张绍曾等4人也考取官费,由张之洞选送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日士官生。1902年,袁世凯奏派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第三期毕业生55名赴日留学军事。在奏章中他详细分析了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臣观近日各营将弁,其朴诚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尤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求,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现已三届毕业之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干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4](P487)在这里,袁世凯首先强调了派遣军事留学生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抛弃湘淮军制而建立新式的、近代化的军队,要提高军官的气质和素养,要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精髓,必须以大量派遣军事留学生为前提。其次,强调军事留学生的水平高于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学堂学生中质量最好的官佐据说是直隶、湖北和安徽学堂的学生,可是,就是这几所学校的学生在技术上也不及那些在日本留过学的人。”[5](P212)袁世凯承认北洋军事学堂毕业生“虽规模颇有可观,而谙练犹有未至。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再次,强调派遣军事留学生应以派往日本为主。在甲午战争之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朝野上下推崇英法的海军、德国的陆军。经过甲午惨败的教训,以及1897年以后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而导致中德关系急剧恶化等多方面原因,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朝野人士普遍认为选派陆军留学生应以留学日本为主。其后虽偶尔有派往欧美的军事留学生,但与留日的军事留学生数量相比,则相差甚远。近代陆军留学史可说是一部留学日本史。
在地方督抚的推动下,1904年练兵处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选派留日学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6]。据统计,1904年派往日本的军事留学生共计108名;到1906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就学者已达671人;1908年“统计赴日陆军学生数目已不下一千余人。间由振武学校毕业得入联队学生四百九十九人,现在联队者七十五人,在士官学校二百五十五人”。就读于士官学校“现在毕业回国学生已有二百二十九人之数”[7](P342)。中国学生人士官学校始于1900年,至1911年,毕业于士官学校者共计673人[8](P296)。目前,尚难精确统计袁世凯直接派出了多少军事留学生。但是,根据各种迹象分析,袁世凯起初是积极派遣军事留学生的,而后来,态度则趋于冷淡,并且对学成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处处加以提防戒备。从总量上看,袁世凯派出的军事留学生人数在初期比较多,在当时中国派出的留日陆军生中占有较高比例,后来比例则明显下降。袁世凯一方面积极推动军事留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借机扩张培植私人势力。在这之中,同样充满着袁世凯同其他地方实力派及清廷权贵之间的斗争。
为加强对陆军留学生的监督管理控制,1904年,清廷正式颁布《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章程规定:“凡人民志愿游学武备的学生都可由各省督抚咨送练兵处,经甄试后即可膺选。”[6]执掌练兵处大权的袁世凯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进行“甄试”的机会,除了北洋系选拔派出的留学生以外,“要出国留学的他省学生也必得拜于袁的门下方可出得国门,例如蒋介石赴日留学,也是走的袁家之门”[9](P12)。1906年8月陆军部下令将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更名为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开办不久,学堂经陆军部批准,附设了留日学生预备班,在本堂学生中挑选学生入班,经半年多的培训后送日本军事学校留学。1907年,近代著名人物蒋介石、张群、王柏龄、杨杰等65人从该预备班被选送日本。
对于归国士官生,袁世凯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除了由其挑选派出者得以回到北洋任职外,其余各省回国的士官生,在北洋很难有立足之地。如士官一期生毕业回国者39人,“除几个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二、三期也“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10](P111)。尤有甚者,即使是北洋士官生在北洋派内部亦受到排斥,如北洋大将段祺瑞就“颇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军官学生,不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11](P34)。北洋士官生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12](P11),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
从晚清开始派出陆军留学生直到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袁世凯基本上对士官生采取排斥态度。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袁世凯从小站练兵到1905年北洋六镇编成,都是以原北洋武备学堂学生为骨干,形成所谓小站班底,亦称武备系。同时,他还创办一批各种门类的军事学堂,成为北洋系统的军官培训基地。因此,到士官生陆续回国时,北洋军标统以上的中高级管职,皆为武备系所把持;下级军官也都由北洋军事学堂培养。“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士官生)不能插进”[11](P41)。
其二,留日学生在留学期间,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认识到唯有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或成为民主革命的同情者,“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13](P181)。还有的陆军留学生,如陶成章、李书城、陈其美等人,在国内早已具备革命思想,留学军事只是作为革命手段,“陶成章提议革命党人捐官去日本学习陆军,学成后打进清政府军事系统,掌握军政,以谋‘中央革命’”[14](P22)。李书城“深感革命须靠武力”[13](P181),为此再次赴日,冒名顶替进入振武学校。陈其美“因为感到实行革命需要军事知识,便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学”[15](P127)。这样的陆军留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起义的领袖人物,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当时的“日本成了反满活动的中心”,赴日陆军留学生数量在急剧增加,他们归国后或是担任国内军事学堂的教习,或是担任新军中的军官,这样不可避免“要酿成对旧秩序的不满”[5](P143)。“武昌起义后,几乎各省的兵权都由这些留日士官生掌握,据统计,参加云南起义的40名新军将领当中有31人是留日生,而90%毕业日本陆军士军学校。”[16](P193-194)由此反观袁世凯排斥、限制留日陆军生的举措,应该承认袁世凯毕竟是老谋深算,有先见之明的。在武昌起义后,各地新军纷纷群起响应,而北洋军却能基本保持稳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袁世凯不仅对其他省份选派的陆军留学生不予信任重用,而且对于北洋系统选派的陆军留学生也存有戒心。但是,这些学成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却往往成为其他督抚争先延聘礼遇的对象,有的甚至很快升到很高的职务,手握重兵,这在辛亥起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同时,他们也成为清廷反袁派权贵用以同袁世凯争夺兵权的重要工具。
作为反袁派权贵领袖的铁良和良弼,都曾是袁世凯拉拢的对象。1903年,袁世凯曾保荐铁良会办京旗练兵事宜,委任良弼为统带。但由于铁良政治野心膨胀和满洲贵族与汉族官僚集团斗争的加剧,铁良最后却成为袁世凯的死敌,反袁派的领袖。士官生出身的良弼,则积极为铁良出谋划策,并利用自己与留日士官生的关系,极力拉拢士官生,作为争夺军事领导权的工具。而士官生们也希望通过对袁世凯的打击,掌握北洋军的领导权,进而推翻满清政府。这样,在晚清政局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士官生,却与满族亲贵集团结成了反袁同盟。
为了打击、排斥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控制,良弼曾宣称:“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他。”[17](P547)所以练兵处成立后就从各省调集数十名士官生来京,在练兵处担任各种要职。“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11](P41)。陆军部成立以后,铁良将“在练兵处招致士官生,纷纷带到陆军部”[11](P41)。鉴于“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陆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当然“自非旧派所能甘服”[11](P51),双方斗争更趋激烈。为了进一步剥夺袁世凯的实权,反袁派先后将袁明升暗降,北洋派不敢像袁在朝时那样趾高气扬。“同时清廷中的亲贵又利用湖北派陆军留学生,如卢静远、哈汉章等,以挟制北洋派势力。”[17](P489)“那时北京中央军事机关如军咨府、陆军部、练兵处等重要人员是留日士官生回来的居其多数。”[18](P196)其中,“军咨府各厅处长悉为留学日本的士官毕业生……对于用人,行政握有相当的实权”[18](P96)。
在北洋各镇中,北洋派的一统天下也被打开了缺口。士官生开始占据了一部分中高级军官岗位。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这一趋势定将继续下去。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多年经营,北洋势力已根深蒂固,并非轻而易举所能动摇。反袁派士官生虽取得了中央军事机关部分权力和北洋军部队部分指挥权,却未能完全达到其预期目的。故而武昌起义之后,虽有吴禄贞策动的第六镇起义和二十镇部分军官发动的滦州兵变,但都失败了。袁世凯出山之后,仍然能以北洋军为资本,在南方革命力量与清政府之间周旋,最终攫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北洋派势力进一步膨胀。但是,其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裂的征兆,尤其是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膨胀,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在感到老部下不可靠的情况下,袁世凯图谋在小站老班底之外,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军事力量以对冯、段进行制约。另外,经过辛亥革命,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士官生在国内军界中的势力不可低估,乃一改过去的态度,除了大力提拔重用原属于北洋系统的士官生以外,对南方各省的士官生也多方进行笼络,以为己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任用士官生设立模范团,开办讲武堂,扩展军事力量。2.对士官生委以重任,先后负责军事处和统率办事处的实际工作,从而架空段祺瑞掌管的陆军部,黎元洪任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更是形同虚设。3.用金钱收买士官生。
面对袁世凯的利用笼络,士官生的态度如何呢?如前所述,大多数士官生之所以在清末参加反袁活动,是由于受到北洋派的排斥和视袁世凯为反清障碍。随着清廷倾覆,民国建立,加之袁又大力对士官生进行笼络,这两个影响因素均不复存在。除少数坚定的革命党人之外,大多数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标志着革命已成功。近代中国深受政局动荡之苦,今后的任务是巩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时,蔡锷的思想就具有典型性,他认为目前“除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不足以维持国脉”,而只有袁世凯能当此重任,“总统当国家行使中枢,负人民负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意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19](P627)。基于这种想法,蔡锷、蒋百里等人应袁之召,进入其军事班子。当然,不排除其中部分人为高官厚禄所收买,或为保住已有的地位而主动投靠,陈宦、阎锡山等人即属此类。
袁世凯在民国建立之初,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以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自诩。当自认为地位已经巩固之后,他就开始了帝制自为的活动,做起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梦。这显然违背了大多数士官生的初衷,以蔡锷为代表的士官生再度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成为讨袁护国的中坚力量。
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对发展国内军事教育仍一如既往地非常重视,这点学者已多有论述。相比较而言,袁世凯对于发展军事留学教育则不够重视。对于海军留学教育,袁世凯仍然不予重视。只是偶尔零星派出部分海军留学生。这与晚清形成明显差别。清政府派出海军留学生是成批的,主要去向是英法。1904年日俄战争后,又大批派往日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由于军阀混战,经费用于内战,且对海军建设极不重视,根本无力也无心成批派出留学生。但是在萨镇冰等人的努力坚持下,对世界先进军事先进技术,如飞机、潜艇、无线电技术等,仍较为重视,间或派出少数留学生学习追踪世界海军最新发展,以为将来发展中国海军打下基础。但“其成效除在马尾能自制飞机,为国内首创,潜艇则无成就。”[20](P93)
对于陆军留学教育,袁世凯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如对国内军事学堂那样重视。1904年以后,清政府的军事留学生由各省选拔,由中央统一派遣。民国建立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也各自为政。军阀之中不少出自清末留日的陆军学生,因而他们仍然倾向于将自己的部属选送日本,培养自己的人才,加强自己的实力。加之民国以后废除了不许自费留学军事的限制,青年学生竞相出国学习军事,甚至一些师范和工科的学生也半途退学转入军校。其时,日本“士官学校只要录取八九十学生,报考者竟多至四五百人”[21]。有的学生是为谋生而投考军校。也有不少学生抱着强兵救国的理想而从军,他们声称:“我们之所以志愿为军人,在拨乱反正,并不想做军阀,实在为要讨灭不正当的军阀,才投笔从戎的。”[22]然而,这种思想又恰恰是袁世凯所深为恐惧的,万一将来自己实行帝制,这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洗礼的军事留学生,很可能会像当初反清一样将进攻的矛头指向自己。
袁世凯对于选派陆军留学生仍如清末时期,持限制、怀疑、不信任的态度。同时,国内各类军警学堂纷纷建立,并日趋完善,而需求逐渐减少。因此,袁世凯在担任民国大总统期间没有大批量派遣陆军留学生。
总而言之,袁世凯一生对国内的军事教学高度重视。但是,对于派遣军事留学生则主要由于担心留学生所带来的革命影响,以及国内派系斗争的影响,而不够积极主动。对于海军留学教育更是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轻视军事留学生特别是留日陆军生在中国现代政治、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据统计,1900-193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多达1535人。[21]与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生总数相比,军事留学生总数很少。但是,他们在国内军界、政界的地位却绝非无足轻重。1927年,日本教育家松本龟次郎指出:“今日中国军人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曾经留学过我国。”[23](P63-64)舒新城亦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八九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年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中求得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应负重大责任。”[23](P212)袁世凯与此自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2-10-20
标签:陆军论文; 士官学校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袁世凯论文; 日本海军论文; 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海军论文; 北洋集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