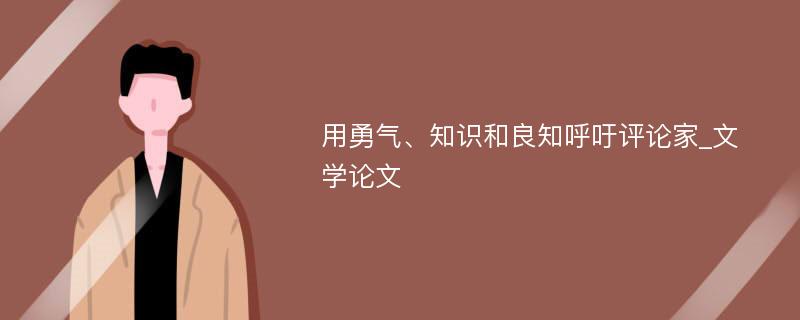
呼唤有胆有识有良知的批评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胆有识论文,批评家论文,有良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把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大块。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当代文学包括文学批评是自然而然的。又因写过一些批评当代一位走红女作家的论著,被称为批评家。不过因有过这样一次闹得沸沸扬扬的批评实践,对当下批评状况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近日读了曹万生先生的《当代学院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一文后,感触颇深。
(一)
批评困境的问题,近几年也有不少圈内人士关注。曹文所谈的问题十分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充分地阐发了当下文学批评的现状危机及出路。对于他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
按人们通常的理解,学院批评(习称学院派批评),是以高校、研究机构中的文学教师、研究人员为批评主体,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等的学理化解读为主要评判对象,以思想和意义的阐释为基本目的,在学术话语的规则中加以运作的批评样式。曹先生之所谓学院批评即人文性批评。虽然他未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关联作必要的说明,但这无关宏旨。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在描述困境之后的提问:
我们要不要人文性批评?如果要,我们的力量在哪里?队伍在哪里?思想在哪里?
这是三个有力的追问,这是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包括学院派批评有很大成绩,在帮助作家校正自己的创作方向和帮助读者鉴赏优秀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令作家和读者不满的一些现象。如随意性太大学理性不够、批评成了表扬、骂派批评一度风行、红包批评成了文坛的潜规则等等。总之,批评的公信力不高,曹文认为批评陷入了困境并非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之论,而是对当下批评现状的敏锐诊断和严肃拷问。
我认为,从文学批评者自身而言,造成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无识无胆,队伍乏人。
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由20世纪50到80年代的宣传喉舌到80至90年代启蒙大使到90年代以来的纯粹职业,其中心角色大大地转换了。有人甚至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死了。只有一个个从事具体的不同的专业的学者专家,作为整体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少文学研究者要么成了西方学说的贩子,要么成了古籍材料的整理者。只要外语好,只要资料多而新,还要什么思想?何况今日的学术研究高度体制化并极度量化,评价文章不论质量只论刊物级别,评价学术著作不论质量只论出版社级别。文学批评因其开创性即时性特征,其学术性学理规范往往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显得扎实而有学问,论著很难得以在高级别刊物出版社发表,从这样一种现实功利出发,专搞批评的人在学院体制内“吃不到香”,因此文学批评的队伍就大大萎缩了。
应该看到,当下有思想冲击力有文坛影响力的批评家大都身处边缘。他们少了某些限制,反能率性而为,自由挥洒,无所顾忌,迭出新见。学院内的批评家很少是专门的批评家,他们往往还有足以支撑其学术地位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成果。他们的文学批评不是出于饭碗的考虑而是出于内心的热爱,出于对当下文坛现象非说不可的冲动。
队伍小了,力量当然也小了。学科体制限制了批评,自己瞧不起自己,有什么力量可言?此其一。其二,文学边缘化,文学批评就更在边缘之边缘,学院批评的声音被媒体批评所淹没,力量就更小了。这是很多人早已看到的事实。其三,是当下的文学批评者自身乏力。前段时间老说批评失语、缺席、误读,是因为面对种种新的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批评家没有了价值支撑,没有了分辨能力,因而也失去了言说勇气或者人云亦云地乱说一气。这是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变成了文学表扬?除了资本和人格的因素外,还因某些批评家缺乏分辨的能力。他心中没有一杆秤,掂不出作品的分量。把学理阐释价值评判变成了商业广告肉麻恭维。自己太弱了就只好说别人强,借以掩盖自己的贫弱。
为什么有人总是颐指气使地指斥文坛,是因为他固守某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学价值,一成不变,他心中只有一杆秤,看不到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价值。看起来豪气冲天,但文学价值观偏狭固执,实际上也是虚弱的。
今日中国价值多元但也多少有些价值混乱。在这个思想文化价值多元文学形态空前丰富多样的时代,一个文学批评家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评判标准问题。我认为,我们既应充分注意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新变化,也应重申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特异功能和普适性价值。前几年有人提出重读经典重新认识经典的价值,近年诗歌界亦有重新回到伟大的标准的提法,其积极意义还未得到充分重视。的确,我们今天有了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文学与影视攀亲的越来越多了,下半身也可以写了,隐私日记也文学了,但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最重要价值非如此不可的价值,足以让她伟大起来经典起来的价值难道不该重新讨论和重新正视吗?
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思想。曹文问当代学院批评的思想在哪里?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审美价值的创造,那么文学批评则是对其价值真伪高低的评判。评判价值者自身应有坚定明确的价值尺度。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某些批评家过不了关。思想的贫弱必然导致批评的乏力,无胆是因为无识。
(二)
回想起最近几年我对有位著名作家的批评和二人之间的论争,我感到,做一个有胆有识的批评家,颇为不易。
我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批评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的。那就是人性的含量和审美含量。我认为她的小说,不能够丰富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不能给读者高层次的审美愉悦。这样的观点,是建立在我对她的全部作品的阅读分析和对已有的100余篇研究她的专论的辨析借鉴基础上的。我的某些表述或有不当,某些分析也还有加强学理之处,但没有对其人格的半句贬损、对其作品的空谈捧杀。
某些被批评者没有正视自身缺陷的勇气和深厚的涵养,想方设法替自己开脱。不是在学理的层面上面对自己的不足和与批评家的分歧,而是不停猜度和有意歪曲批评家的批评动机。我们出于学理和良知的批评受到过不友善的非议。
与之相仿,有的学者是靠对某些作家的一味吹捧和拥有作家的独家隐私发布权立于学界的,你批评某作家的不足,无异于抹杀了“吃x x作家饭”的学者的研究之功,因此他出于对自己的“成果”捍卫,想方设法“找茬儿”,无视他人批评意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自批评界内部的某些对我们的“批评”,就是这样发出来的。
此外,批评“名家”的难度还在于,不少地方是把成名作家当作“政绩”的一部分看待的,你批评某地某个作家,就被潜在地认为有否定其“政绩”的可能。因此本地评论家批评本地作家殊为不易。作为本地学者批评本地作家,有人赞赏我的勇气,有人希望我更“策略”一些。我在写作时从没考虑过什么本地外地,我认为学者只有一个定位:那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地域的限制是可笑的。在当下语境中,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倒是要特别注意的。
一个公开宣扬“文学是俗物”的著名作家,得到了广泛迎合和应和,读者追捧如明星,有一些评论家也不停地为她唱着廉价的赞歌。仗着一些评论家的赞扬和众多读者的喜爱,这位著名作家对我的批评颇不以为然,视之为“酷评”。并斥责我未与她交流就写书,还在好几个场合继续宣扬她的“文学是俗物”论、记者和评论家都是“瞎扯淡”论。我想质问这个因俗闻名以俗为荣的所谓作家,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文学是俗物,还有什么是不俗的?如果文学不能给人以心灵的美化和精神的提升,还要文学作什么?
在这位女作家关于创作的表述中,多次谈到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好看”。她为畅销书的价值大唱赞歌。不少读者和某些评论家也常常以畅销这个市场法则而非审美法则评价作品高低。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畅销的优秀作品非常多,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乔伊斯,都不怎么畅销,跟这位女作家的作品销量简直没法比。如果我们仅以好看畅销作为标准,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师就只有两个。前半叶是张恨水,后半叶是金庸。他们作品的读者远远超过了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如果仅以畅销作为标准,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了。只要一台电脑,把作家的著作销售数量和阅读量进行排列,就万事大吉了。鲁迅、郭沫若的读者大大少于张恨水、金庸是很正常的事。名家不等于大家,流行不等于经典。
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事件,我深深认识到,一个作家受欢迎的程度不是由评论家决定的,也不是由“精英读者”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国度的国民的平均文化水准决定的。在中国读者大众目前这种阅读水准阅读趣味面前,反媚俗是批评家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有的作品津津有味地描绘文化名人玩弄异性恩宠女人(如《废都》),有的作品肆无忌惮地鉴赏中国野蛮地杀人刑法(如《檀香刑》),有的作家毫无现代感地鼓吹反法制反社会的侠义精神(如金庸),有的作家把粗鄙当潇洒把流氓当英雄把杀人当浪漫(如池莉),电视屏幕上成天充斥着有德有才风流儒雅的好皇帝形象,在这样的作品和欣赏者面前,严肃的有良知有胆识的批评家,应该站起来,应该发言。
尽管一些作家多次表白,不在乎他人的批评。但我认为,批评任何一个当代作家既是一个学者独立的工作,也是一个读者应有的权利。作品一经诞生,一经问世,就是社会化了的精神产品,就是任人品评的对象。读者的喜爱是作家的荣耀,读者的批评是对作家的爱护,也是对自己作为审美主体权益的保护。只要不是诽谤、谩骂,只要不侵犯名誉权,批评就应该得到尊重。
文学批评家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批评家不应沉默,沉默就是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