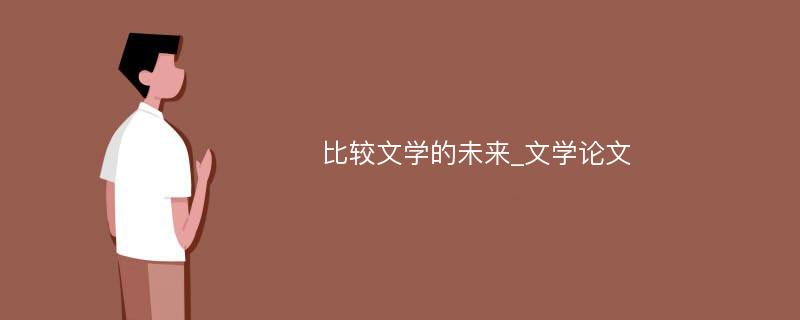
比较文学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文学研究方法自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大陆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步履艰难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早已有人预言,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世纪”,如果这话果真被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实践所验证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一个“批评的世纪”,一向与理论批评格格不入或相互抵牾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已经或者将要面临何种局面或挑战?在以多学科整合研究和超学科考察为特征的当代文化研究大潮中,比较文学将如何得以生存?确实,对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已经有人作出了颇有远见卓识的预测(参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中“导论”及有关论文,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公司1989年版),而且其中的不少洞见已被实践所证明。而对于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年月里将如何发展演变,则未见到令人信服的著述,甚至有人倒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持一种悲观或消解的态度。我认为,不管对之乐观或悲观,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毕竟已经存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学术土壤中了,而且始终在纷纭变幻的文化学术气候下健康地发展着;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则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本文正是本着推进和发展这一学科之目的,从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交汇、沟通对话以及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这门学科的未来景观作一预测和描述。
比较文学自身的挑战和历史演变
任何熟悉比较文学发展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比较文学在本世纪至少受到了本学科内部两次以上的挑战: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中叶,当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比较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和研究机构后,首先在法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特征是致力于探讨事实存在的文学的接受与影响,但这种模式却一度被法国学派推向了一个不恰当的极端,其实证主义的刻板的“科学性”使得比较文学所应当具有的文学性和审美愉悦性黯然失色。毫无疑问,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草创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必然会以失去其审美特征的分析和文学形式技巧的探讨为代价,从而模糊文学和科学的界限。因为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尽管文学研究需要从科学的方法论中接受启迪,但文学的对象首先是人,它的鲜明的人文特征是任何科学研究都难以替代的,因此当雷内·韦勒克于50年代后期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届年会上发出“比较文学的危机”之警告时便得到大批学者的响应,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参见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中译文见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价值和质量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审美性和愉悦性。作为文学学术研究一分支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第一次挑战取得的成果显然是积极的,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的研究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以平行研究和文学文本的美学形式分析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的崛起,为后来的“三足鼎立”之格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共同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美国学派的崛起也为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这并未能根本改变后来更为霸道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价值取向。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成立自然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化和机构化,使得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有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乃至对话的场所和论坛。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协会成立的头二十几年内,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所研究的课题并未涉及广大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问题,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协会主持编写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才由熟悉中文的佛克马教授率先在其主编的《后现代主义》分卷中突破了这种思维模式。现在,这一工程浩大的研究项目终于吸收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方和第三世界的代表,研究的范围也越过了西方的疆界。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东方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早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页,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因而东方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东方本身,而取决于它所展现在西方人眼中是何种形象,也即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永远只能是一个“他者”(other),而他者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退居边缘。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文学遗产的中国文学的成就视而不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封闭和与世隔绝,另一方面显然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冷战”策略和殖民主义的“东方主义”视野所致。东方国家的日益强大,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得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逐步从边缘步入中心,对业已形成的“西方中心”之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结果,比较文学研究的机构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可以说,现在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能反映全世界范围的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机构。比较文学研究内部经历的第二次挑战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中心东移的过程,但是这种东移并非那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单向度运行,而是一种“播散形”的,即由原来单一的“西方中心”为主导(在这方面,所谓“苏联学派”不过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的影响并未超出东欧)过渡到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新的“三足鼎立”之格局:以法国为中心的重视经验研究以及重视接受与影响考察的欧洲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强调美学形式分析和平行理论阐释的北美学派和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中心的致力于跨东西方文化传统研究和学术理论对话的东方学派(参阅拙作《走向比较文学的新格局》[Toward a New Framework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mdian Res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21卷第4期,1994年)。至此,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研究格局内部机制的调整。
在新理论的冲击之后
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文学以外的理论思潮有力地冲击着文学理论自身,致使本世纪的西方理论批评界出现了四个取向: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和一部分后结构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种语言学—科学批评取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原型理论以及拉康的一部分批评理论构成了一种心理学—人本批评取向;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读者反应批评则形成一种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取向;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带有政论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形成了一种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参阅拙著《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第125-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毫无疑问,这种复杂局面的出现使得当今的文学理论与语言学以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一些西方学者干脆用“理论”(theory)或“文本理论”(texual theory)等术语来描绘日益庞杂的文学理论(参见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序言”,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不可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另一事实,即“在一定程度上由比较文学中产生出的另一些力量也改变了北美的文学理论批评状况”(见克莱顿·克尔伯等编著《文学的比较研究视角》[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第9页,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因而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之间实际上呈一种互动的关系:谁也无法离开谁,而且谁也吞并不了谁。在众多当代理论流派中,真正对比较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理论当推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当接受美学于70年代后期发生分化时,其中的重要一支应用于文学研究则形成了文学的经验研究,对刷新欧洲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直接的结果便是导致了行将衰落的法国学派重新焕发了生机,并使得专事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学者把视角转向对文学接受的考察研究和从比较的视角来重新撰写文学史。在平行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则体现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论阐释和文学意义的重构上:一方面,从某个现成的理论视角入手,对文学文本进行理论阐释,其目的在于验证这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行之有效,又在多大程度上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则从现成的文学文本以及读者自身的(带有能动的建构意识的)阅读出发,对某种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理论进行追问、质疑乃至重新建构。这种双向的理论阐发若用于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其效果就更为可观,因为对事实上存在的影响的追踪总可以穷尽,而对理论的阐释和建构则是不可穷尽的。对第三世界的学者来说,借用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某个现成的概念是不足为奇的,但这并非其根本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旨在通过这种对外来理论的借用和将其与本土现实和经验的糅合而产生出某种新的居于原体的相似和不似之间的变体,最终对西方的理论话语进行消解和重构(参阅霍米·巴巴《关于模拟和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Of Mimicry and Man: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十月》[October]第28卷126页,1984年)。近十多年来在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争鸣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对西方话语的消解过程中也推进了本民族的“非殖民化”进程,并且将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推到了前台,从而实现了多元共存的目标。
从比较文学研究自身的机制更新着眼,我认为,新理论的冲击还产生了另一方面的效果,即使得比较文学研究从原先的“两根支柱”(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逐步过渡到现在普遍存在的“三根支柱”(接受与影响研究、平行与理论阐释和超学科比较研究)鼎立的局面。所谓超学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是指除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外,还应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次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及艺术表现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次回归到文学本体,这样便求得了一个外延了的本体。另一极则是平等对待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和表现领域的关系,揭示文学与它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最后,在两极效应的总合中求取“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参阅拙著《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第1-17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提倡使我们得以将一切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置于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多视角的语境之下来进行透视性的考察研究,从而找出文学之所以得以生存的独特审美价值和表现特征。同时,超学科研究也使得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沟通和借鉴,对未来的文学理论之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外,通过比较文学的超学科研究,也促使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使得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面对文化研究的挑战
如果说前两节仅仅是对一些已经成为或刚刚成为历史的现象和事件作了一番回顾的话,那么本节便要直接正视比较文学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即文化研究的挑战。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西方学术界江河日下时,文化研究逐步登上前台,并迅速渗入到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把原先的一些处于边缘地带和冷落状态的研究课题统统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诸如殖民地话语和文学,女性文学,性别差异,少数族话语,第三世界批评,消费文学,大众传播媒介,影视文化,音乐电视,广告文化,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等等,真是无所不包。这无疑对相对纯净的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挑战,以致一些学者惊呼,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比较文学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比较文学究竟应当占何等地位?尽管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但就其当代意义而言,却包含着新的内容。“与其他研究所不一样的是,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学科,它既不拥有一种定义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供研究者切入进行探究的界限明晰的领域。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说,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但当今西方的文化研究对象并非高雅的精英文化,而是通俗的大众文化(参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选读》[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导论”第1-2页,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对一向被认为是属于知识分子精英之领地的文学研究(自然也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已经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一些大学,比较文学系科不是被其他系科兼并就是改名为文化研究系科,原先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地大大地缩小了,比较文学又面临着新的学科危机。
确实,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把许多作用让与研究能力的启蒙力量之后,文化研究必定还是保留了作为一种范畴的艺术,而正是在这一框架之内,男人和女人才不仅可以讲述关于现状的真实情况,而且还可争相表达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参见弗里德·英格利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论点概要”第11页,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3年版)。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一个长处在于它可以把文学从高雅的圣殿中解脱出来,使其直接面向大众,同时也使得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人为界限模糊甚至消解;其次,作为一种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的全球化也打破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等级序列和对立状态,使之相互沟通,互动互补,使一向处于边缘的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向中心运动,近几年来的对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关注也许就是一个明证;再者,文化研究渗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则打破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话语和非文学话语的界限,文学文体和亚文学文体的界限,文学和大众传媒的界限。总之,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也包括文学)都被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围,至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则为其重新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文学批评从“文本中心”的死胡同里解脱了出来。但是这样一来,文化研究的明显的局限性便暴露了出来:它没有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甚至连最起码的理论建构愿望都不存在,也没有一个大体相似的研究方法论和理论视野,因此它的多元取向和权宜性就是在所难免的。它的兴旺只是暂时的,当它的高潮过去之后,文学研究却依然存在。文化研究不会吞没文学研究,更不会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反而会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学科更加开放,更有生气,更能在纷纭变幻的情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暂时的结论
针对比较文学在未来的发展及前景,美国学者勃洛克曾预言,“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20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说,他这番话仅能为近三十年前比较文学在西方学术界的景观所证实的话,那么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便可成为其在东方的一个例证。综观当今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现状,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断言,这是一门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学科,它早已通过内部机制的自我调节而克服了自身所曾面临的种种危机,率先从边缘步入中心,登上国际论坛,一方面和西方主流学术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为把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起到了其他学科难以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试图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学,这一点已为世人所瞩目。因此,任何悲观的论点和无所作为的态度都与这一现实相抵牾,任何持“比较文学消亡论”者都无法改变这一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