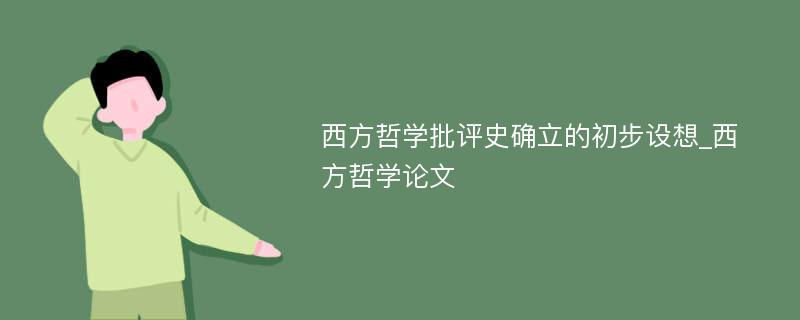
关于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初步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4)03-0064-02
此处所谓“西方哲学批评史”,主要是指中国人自己应具之“西方哲学批评史”。这样的“西方哲学批评史”,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方人对西方哲学之批评,考察其成败得失;二是中国人对西方哲学之批评,亦考察其成败得失。两方面的内容可以分开写,也可以结合起来写。著者以为结合起来写或许更有深意,更能体现中国人所创“西方哲学批评史”之特色。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与创建“中国哲学批评史”,可以有相同的理由,也可以有不同的理由。之所以不同,就因为“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是不相同的。“中国哲学”领域至少已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两门学科之创建、两门课程之讲授,而这在“西方哲学”领域是没有的。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中国之“西方哲学”的研究,显然是落后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不仅“西方哲学批评史”需要创建,就连“西方哲学史史料学”、“西方哲学史方法论”之类基础学科,也需要从零开始进行建设。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之理由
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理由可以有很多,著者以为有三项少不了:一是学科建设方面的理由,二是材料方面的理由,三是内涵方面的理由。
第一,学科建设方面迫切需要“西方哲学批评史”。查“西方文学”,其中“西方文论”或“西方文学批评史”学科,总是要占很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它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对研究“西方文学”的西方人是如此,就是对研究“西方文学”的中国人,同样是如此。中西研究者或许会有所偏重,如西方人详而中国人略,但中国之“西方文学”的研究者,不管他如何“略”,总不能把“西方文论”或“西方文学批评史”都“略”掉,各大学中文学或文学系,总不能把这门课“略”而不提。
为什么哲学系就可以对“西方哲学批评史”根本不提呢?是因为外国没有这门学科,所以中国就不提吗?外国有没有,著者目前不太清楚。但著者可断言的是:外国有,我们可有;外国没有,我们亦应当有。因为这是“西方哲学”领域以及学科方面的一个“基本建设”。“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外国早就有了,中国人要想在这个方面超越西方人,是很难的。若“西方哲学批评史”外国没有,不正给中国人留下一片“施展拳脚”的天地。这是就学科建设方面,谈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理由。这个理由几乎无需多论,因为这是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必备步骤。除非我们不想深化“西方哲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或者现实生活不需要深化这个领域的研究,否则“西方哲学批评史”就是绝对必需的。
第二,材料方面,“西方哲学”中“批评史”的材料,几乎是现成的。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各哲学家之间的辩论,就是“西方哲学批评史”很好的素材。“西方哲学史”看重结果,不太讲辩论的过程;“西方哲学批评史”则专门研究其过程,探讨辩论各方所采用的批评“格式”。这样的研究与探讨,对于我们明了“西方哲学”的本质,会帮助很大。
再如“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也可成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重要素材。经院哲学是以理性形式,以抽象、烦琐之方法,论证基督教教义与神学之“真理性”。简言之,是以哲学论证神学。这样的一门学问在“西方哲学史”中,或许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故许多“西方哲学史”对此写得极为简略,甚至略而不提。但对“西方哲学批评史”而言,这却是一座宝藏,一个值得重点而详细研究的阶段。为什么?就因为“西方哲学批评史”只重“形式”而不重“实质”,换言之,只重它“如何”以哲学证神学,而不重它“是否”能够以哲学证神学。再换言之,“西方哲学批评史”只重点研究“经院哲学”之方法与“格式”,总结其经验教训。至于其有没有“真理性”,在哲学上能不能成立,“西方哲学批评史”可以暂时不管,甚至根本不管。早期“经院哲学”重视对《圣经》及其它宗教典籍的“注释”,这个“注释”,“西方哲学批评史”就可重点研究之。10世纪以后“经院哲学”内部出现长达几个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或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西方哲学批评史”就可重点研究之;“后期经院哲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注重自然法理论,从上帝之全善“推论”出人之理性与意志,及其在自然秩序中之地位,这个“推论”,“西方哲学批评史”就可重点研究之。19世纪中叶以后又出现所谓“新经院哲学”,试图以经院哲学“解释”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哲学,这个“解释”,“西方哲学批评史”亦可重点研究之。这样一来,“西方哲学史”中的“弱项”,就可一跃而成“西方哲学批评史”中的“强项”。
再如“解释学”(Hermeneutics),几乎就可直接拿来作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材料。古希腊文“解释”一词,原指对于神谕的“解说”,涉及“原意”与“解说者”、“解释”等方面,这个“解说”,就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至中世纪,出现一批专门以“解释”或“注释”《圣经》及其它宗教典籍为职业的人,“解释”或“诠释”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这个“解释”或“注释”,就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着力于“意义”之“寻求”,或通过分析语言、语句、逻辑关系等“寻求”各种命题、陈述、句子之意义(如科学主义诸派),或通过分析异化、沉沦、死亡等“寻求”人之存在的意义(如人本主义诸派),这个“寻求”(其方法、格式、得失等),就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哲学解释学”肯定“前结构”或“偏见”在理解或解释活动中的不可避免与不可或缺,这个“前结构”或“偏见”,就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还有所谓“解释学循环”,亦应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解释学”可有与“西方哲学批评史”重迭的地方,但却不可能相互替代。
类似“对话集”、“经院哲学”、“解释学”的材料,在“西方哲学”中还有很多。可知在“西方哲学”领域,并不缺乏“西方哲学批评史”的材料,只是没有详加整理而已。若是详加整理,就可写成一部“西方哲学批评史”。这是就材料方面,论证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必要性。
第三,内涵方面,有很多“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地方,必以“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之。如“经院哲学”与中国“经学”之比较,就是“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这个区域正好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的用武之地。中国哲学中有所谓“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解释学”的探讨,其与“经院哲学”之训诂、诠释、考据等,正可“相互发明”。这个“相互发明”只有在“西方哲学批评史”中,才能得到完整而准确的论述;若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讲,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可能既讲不通,也讲不透。
再如哲学史的分期问题,黑格尔曾把到他本人为止的全部“西方哲学”分为“希腊哲学”(从泰勒斯至新柏拉图派哲学,公元前600年至公元5世纪左右,时约1000年)、“中古哲学”(以经院派为主,时1000余年)、“近代哲学”(从培根、笛卡尔等人开始)三个时期,[1]这种分法可能就跟中国人的分期法有些不同。再如“现代西方哲学”的上限,中国学者有定为“19世纪40年代”者,有定为“19世纪末”者,有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者,亦有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者,等等。这些分法也可能跟西方人的相应分期法有些不同。这些“不同”,“西方哲学史”不会着力去研究,但却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假如中西学者有“相同”的分期法,“西方哲学批评史”要研究何以“相同”及其所致之后果;假如中西学者有“不同”的分期法,“西方哲学批评史”要研究何以“不同”及其所致之后果。这几乎是“西方哲学批评史”之专门任务,“西方哲学史”完全可以不管的。
总之,在内涵方面,“西方哲学史”有许多“被遗忘的角落”,不交给“西方哲学批评史”,根本无法处理。这亦是创建“西方哲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理由。
“西方哲学批评史”之位置安排
目前,“西方哲学史史料学”、“西方哲学史方法论”等学科还没有建立,所以用不着探讨“西方哲学批评史”与这些学科的关系,及其位置安排。
唯一要探讨的是“西方哲学批评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可能存在一种诘难,就是以为有一个“(扩大的)西方哲学史”就够了,用不着另行创建一门“西方哲学批评史”。此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一个“(扩大的)西方哲学史”,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就算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它能覆盖以上所说的那些内容吗?它能涵盖“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与罗素《西方哲学史》之批评格式的对比”这样一个主题吗?如果它能涵盖,则这部“(扩大的)西方哲学史”也无非就是“西方哲学史”与“西方哲学批评史”的一个混合。
众多已有的“哲学史”著述,是一部“西方哲学史”无法涵盖的。换言之,“西方哲学史”乃是“西方哲学批评史”的对象之一,这是不能以“西方哲学史”(不管它是“扩大的”,还是“微缩的”)取“西方哲学批评史”而代之的根本理由。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人的西方哲学观”,也是“西方哲学史”覆盖不到的。中国人“解读”西方哲学,从明末算起,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其中经验教训颇多,没有“西方哲学批评史”,根本无从做全面的总结。中国人对“进化论”与“进化哲学”的“解读”,有很多“断章取义”、“六经注我”的地方,有哪部“西方哲学史”曾有时间光顾?对“康德哲学”的“解读”,歧义纷纭,王国维有解读,陈昕有解读,张东荪有解读,牟宗三有解读,等等,这些“解读”之间的利弊得失,有哪部“西方哲学史”曾有篇幅去总结?还有关于“实在论”之“解读”,关于“唯物辩证法”之“解读”,关于“实用主义”之“解读”,关于“维也纳学派”之“解读”等等,均是“版本”众多,一部“西方哲学史”说什么也无法涵盖。这些内容只能纳入“西方哲学批评史”,纳入“中国哲学批评史”,总之无法只呆在“西方哲学史”中。
若用一句话来表达“西方哲学批评史”在“西方哲学”领域中的位置安排,则可曰:“西方哲学批评史”在“西方哲学”中之地位,等同于“西方文论”或“西方文学批评史”在“西方文学”中之地位。这就是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