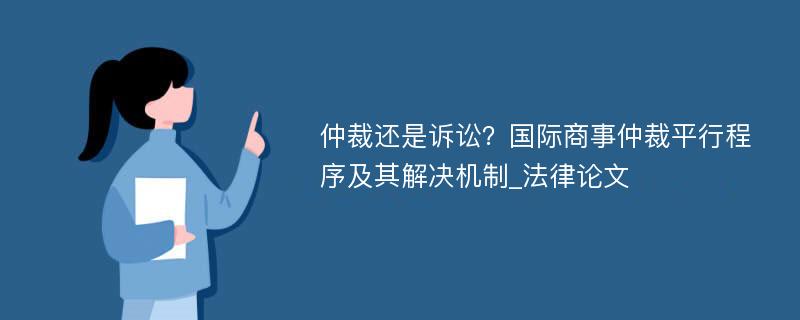
仲裁抑或诉讼?——国际商事仲裁平行程序及其解决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事论文,机制论文,程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1)05-0084-09
一、平行程序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平行诉讼(parallel proceedings)被描述为一种相同当事人基于同一诉由同时在不同国家进行诉讼的现象。平行诉讼是与各国对案件的平行管辖联系在一起的。通常,各国只对涉及国家和社会重大利益的案件进行专属管辖,而对于那些与内国不存在任何属地、属人联系的案件拒绝管辖。这两种管辖之外的更为广泛的案件都属于平行管辖的范围。在有一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民商事争议主张管辖时,就出现了平行诉讼或诉讼竞合的现象。而当事人因不同的诉讼动机启动不同的诉讼程序是导致平行诉讼发生的直接诱因。
由于商事纠纷数量的增加,仲裁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优越性,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很多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成为基本原则或已经解决的问题在涉及仲裁时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仲裁与诉讼间的平行程序问题正属于此类问题。与国际民商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不同,仲裁庭与法院间并不存在平行的管辖权。根据“或裁或诉”原则,一份有效且可执行的仲裁协议排除了任何其他公共机构的管辖权。此时仲裁权和诉权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但这首先需要存在一种划分法院与仲裁庭管辖权的规则,而当这一规则缺失或规定不明时,当事人便有了通过启动不同的程序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救济的可能,仲裁与诉讼间平行程序问题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平行程序的产生固然使得当事人增加了胜诉的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平行程序所造成的诉讼资源的浪费以及不公正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正因为如此,各国一方面通过国内立法或缔结国际公约的方式来尽量避免平行程序给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带来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发生平行程序问题时,不断寻求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案。
二、跨国平行程序及其解决
(一)国际仲裁及管辖权公约
1.《纽约公约》
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为重要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吸取了1923年《关于仲裁条款的日内瓦议定书》以及1927年《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日内瓦公约》的经验,在第5条第1款a项中规定,仲裁裁决的效力依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在没有选择时依据仲裁地法。但这仅适用于执行程序。在协调法院与仲裁庭管辖权方面,第2条第3款规定,如果缔约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当事人已经就此达成仲裁协议,法院应当依一方当事人请求将争议提交仲裁,除非法院查明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未生效的或不可能实行的。这意味着,法院将对仲裁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仲裁庭在管辖权问题上没有绝对的优先权。
另外,由于《纽约公约》第2条在最后一刻被订入公约正文,其订立者们未就第2条中仲裁协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规定。在实践中一些法院倾向于适用法院地法。例如,比利时法院曾依据1961年比利时独家经销契约法(Statute on Exclusive Distributors)认定经销契约中的仲裁条款无效。虽然合同的准据法并非比利时法并且仲裁地位于外国,法院仍对因终止经销关系产生的争议主张管辖,并给予了经销者一系列赔偿。德国法院在适用公约第2条时,也曾认为涉及未来投资及期权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因依据德国法此种合同属于“赌博合同”[1]。
当各国法院适用不同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效力时,极易产生诉讼与仲裁间的平行程序问题。如A国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而主张管辖,B国法院却认为仲裁协议有效而将争议提交仲裁。必须指出的是,某些法院为主张自己的管辖权而利用法院地法来判断仲裁协议效力,或无视仲裁协议的存在而强行主张管辖的狭隘作法应当被抛弃。根据学者们的主流观点,一份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当无论在公约第2条的向法院提出实质性申诉的程序中还是在执行裁决程序中适用同一法律。如果法院在不同诉讼阶段以及法院与仲裁庭在认定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上能够适用相同的准据法,那么无论谁先享有判断这一问题的优先权,都将较大程度上避免平行程序的产生。不过,即便如此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因仲裁员与法官还可能在适用同一标准的情况下,因对同一问题认识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实际上,仲裁协议效力以及仲裁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常涉及众多复杂的因素,即使十分有经验的律师和法官也容易产生分歧[2]。总之,在《纽约公约》框架之下,平行程序往往无法避免。
2.《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
对此问题,《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下称《欧洲公约》)的规定与《纽约公约》有所不同。公约第6条第3款规定:“如仲裁协议一方当事人在向法院起诉之前,已经提交仲裁,缔约国法院在以后审理该当事人间的同一事项,或审理该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或无效,或已失效等问题时,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前,应停止对仲裁员的管辖权作出裁决,有正当而真实的理由反对者除外。”反之,在法院程序已经提起后,仲裁庭也应中止仲裁程序,等待法院的管辖权决定[2]。《欧洲公约》的这一规定使平行程序问题得到了协调解决,相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国际公约中尚未见到。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依照“法院地法”该争议不能通过仲裁解决时,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仲裁协议。这似乎又为法院干预仲裁打开了缺口,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第6条所规定的处理规则的和谐。《欧洲公约》甚至鼓励诉讼与仲裁间平行程序的发生[1]。
3.欧盟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相关公约
1968年由欧共体国家在布鲁塞尔签订的《关于民商事裁判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下称《布鲁塞尔公约》)及随后在卢加诺签订的《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构成了布鲁塞尔/卢加诺体系,创设了缔约国之间关于民商事诉讼管辖及法院判决执行事项统一的制度和规则。2000年12月22日,欧盟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公约》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第44/2001号条例》(下称《布鲁塞尔条例》),条例在调整范围上和内容上与《布鲁塞尔公约》基本保持一致,但删除了其不合时宜的规定。
这三个公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欧盟内部诉讼的便利,建立清晰明确的管辖权规则,简化和加速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因此,在适用范围中均明确规定,仲裁不在公约调整范围之内。在处理未决诉讼的问题上,三个公约均采取了先诉优先的原则。根据《布鲁塞尔条例》第27条的规定,如果具有同一诉由相同当事人的诉讼在不同的成员国法院提起,任何后受案的法院应自动中止诉讼,直至先受案法院确立管辖权。而根据条例第34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如果外国法院判决与被请求国法院就同一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所作判决或与其他成员国或第三国就同一当事人之间具有同一请求所作的判决不相容时,执行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此处,“在先判决”很清楚是指法院判决而非仲裁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第34条第1款规定了判决与承认国公共政策相抵触将被拒绝承认的情形。似乎可以认为,如果外国法院在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强行管辖案件,违背了该国作为《纽约公约》缔约国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从而违反了承认国的公共政策。但实际上,欧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在Renault一案①中表明,应当对公共政策做非常严格的适用。这意味着,虽然已经存在仲裁程序,但外国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而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在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有效而该外国法院没有管辖权,也不能够以此拒绝承认判决。另外,条例第35条第3款规定,执行法院不对外国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审查。这实际上也阻止了执行法院审查外国法院对仲裁协议相关问题的判断。
因此,无论是否已经存在一项仲裁协议还是一项仲裁裁决,法院判决的执行都不会受到影响。欧盟有关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的公约无法为解决仲裁与诉讼间的平行程序提供有力的途径。
(二)两大法系的解决机制
基于诉讼经济、防止滥诉及避免出现相互冲突的法院判决的理念,各国均通过立法和实践活动对平行诉讼现象加以限制。以英美为主的普通法国家依据“不方便法院”原则自由裁量是否中止本国的诉讼程序;而存在外国法院的平行程序仅是法院作出中止诉讼决定的若干考虑之一。此外,英美法院在实践中还可以通过“未决诉讼”、“滥用程序”和“禁诉令”等方式避免国际间平行诉讼的发生。大陆法系国家则遵循“先诉优先”原则,这在一些早期的欧洲国家间缔结的双边条约②以及晚近的欧盟立法中都有所体现③。根据德国、瑞士的实践,如果外国法院受理在先,且存在该法院判决能够被内国承认与执行的可能,则内国法院应中止对同一案件的审理。这一原则可以更确切地表述为“先诉优先及可预期执行”原则。实践表明,国际民商事诉讼中规制平行诉讼的方法仍是解决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平行程序问题的重要借鉴,但仲裁不同于国际民商事诉讼,应有其特有的解决机制。
1.瑞士及其司法实践
瑞士无疑是世界上最支持仲裁的国家之一,在规制仲裁与诉讼平行程序的问题上,瑞士司法实践的演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瑞士传统的仲裁理论并不认可法国法中管辖权/管辖权原则的消极效力④。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7条规定,如果当事人已就一项可仲裁的争议订立了仲裁协议,法院应拒绝管辖,除非法院查明该仲裁协议失效、无效或不能实行。这与《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如出一辙,瑞士法院将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全面审查。随后,瑞士联邦法院在一项重要案例中认为,当仲裁地位于瑞士时,联邦法院应当对仲裁协议效力仅作表面审查(prima facie)。这一判定等同于承认法国法中所适用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的消极效力[3]。
当外国法院与仲裁地在瑞士的仲裁庭之间发生平行程序问题时,瑞士法院的传统做法是适用《联邦国际私法典》第9条的规定。据此,如果外国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或不可执行,瑞士仲裁庭并不必然受其约束,而是首先对外国法院判决在瑞士的可执行性进行预测。如果仲裁庭作出正面判断,它将中止仲裁程序,直至外国法院肯定其自身管辖权;否则,仲裁庭应继续仲裁。著名的Minera Condesa[4]一案正是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该案争议源于一个秘鲁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第一优先购买权没有被满足。依据章程仅有一部分当事人受仲裁条款的约束。首先,原告在秘鲁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所有行使第一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已经满足。被告援引仲裁条款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法院驳回了被告的异议,因根据秘鲁法律仅在所有程序参加人均是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时,仲裁协议才有效。之后,被告依据仲裁条款在瑞士提起仲裁。原告对仲裁庭管辖权提出异议,并提出仲裁程序与秘鲁法院的平行程序问题。仲裁庭在临时裁决中确认厂自己的管辖权。仲裁庭认为即使在当事人及诉因相同的情况下,法院与仲裁庭之间的管辖权并不平等,不存在平行程序的问题。仲裁员就管辖权作出的决定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仲裁庭在确定仲裁条款效力时具有优先权,这也是管辖权/管辖权原则消极作用的体现。原告进而在瑞士法院提起撤销仲裁庭临时裁决的申请,被瑞士法院驳回。法院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仲裁庭应当依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9条关于处理未决诉讼的规定中止仲裁程序。而是依据《联邦国际私法典》第25条审查是否秘鲁法院的判决能够在瑞士得到承认。法院认为秘鲁法院违背了《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的规定。秘鲁法院所认为的仅有一部分程序参加人是仲裁条款当事人并不能作为认为仲裁条款无效的有效理由。因此,法院认为秘鲁法院并不具备《联邦国际私法典》第25条中所要求的国际范围内的适格管辖权。
Minera Condesa案为解决国际仲裁中的平行程序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但从瑞士相关法律规定来看,瑞士法院将解决法院未决诉讼的“先诉优先及可预期执行”原则适用于仲裁,却不尽合理。《联邦国际私法典》第26条规定,如果一项外国判决是在违背了有效的法院选择条款情况下做出的,判决将不能够得到承认。但是,第26条并未明确,仲裁协议是否等同于法院选择条款。另外,《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仅适用于国际仲裁裁决的执行,并不涉及执行外国法院程序中判断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而且,在Minera Condesa案中瑞士法院对秘鲁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的理由进行审查,无异于在执行时对外国法院就案件实质问题的判决进行审查,这违背了瑞士法律在外国判决的审查上仅进行形式审查的原则。
瑞士法院随后处理的Fomento v.Colon(Fomento)案[5]更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并最终导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86条的改革。该案案情大致如下:依据一项建设合同Colon Container Terminal S.A.(Colon)委托Fomento de Construcionesy Contratas S.A.(Fomento)在巴拿马建设港口航运站。该合同含有仲裁条款。争议产生后,Fomento于1998年3月12日在巴拿马法院起诉,Colon依仲裁协议提出抗辩。一审法院认为Colon的管辖权抗辩逾期并继续审理案件,对此决定Colon提出上诉。在巴拿马法院已于1998年6月26日作出决定的情况下,Colon于1998年9月30日在日内瓦依据国际商会1998年仲裁规则提起仲裁程序。Fomento对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其通过在巴拿马法院起诉已经放弃了仲裁协议,而Colon未在法院程序中及时提出抗辩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法院管辖权。Fomento因此认为,巴拿马法院享有管辖权,双方仲裁协议已被取消。随后,巴拿马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决定并认为Colon的抗辩已经及时提出。Fomento对上诉法院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上诉。2000年11月30日,瑞士仲裁庭在明确援引巴拿马上诉法院决定的情况下,确定了自己的管辖权。此后,巴拿马最高法院在2001年1月22日再次认为Colon提出的抗辩逾期,并指令法院继续程序。但案件并未就此结束,最终Fomento在瑞士最高法院提出撤销仲裁庭管辖决定的申请,认为仲裁庭错误地认定了自身管辖权,特别是误用了平行程序原则。
瑞士最高法院首先认为避免相互冲突的决定涉及公共秩序问题。仲裁与诉讼间平行程序问题可以与法院间的平行诉讼问题一样适用未决诉讼原则,并遵循先诉优先的原则。法院认为,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9条关于未决诉讼的规定应类推适用。另外,法院考虑了下述问题,即是否仲裁庭在决定自身管辖权时应当具有优先于任何法院的地位从而限制了法院审查仲裁裁决的权利。法院对此予以了否定,并认为法院与仲裁庭对于认定仲裁庭管辖权方面具有同等的资格。任何冲突均应依据平行诉讼原则予以解决,给予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或仲裁庭以优先权。
有学者认为,Fomento案将并未在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国际仲裁)中规定的未决诉讼原则适用于国际仲裁,制造了这样的假设,即适用于法院的规则也适用于在瑞士进行仲裁的仲裁庭,而这种假设恰恰是《联邦国际私法典》所摒弃的。Fomento案同样为当事人采取规避策略,通过先一步在外国提起法院程序从而阻挠在瑞士进行仲裁铺平了道路。法院将撤销那些因仲裁庭不中止仲裁程序而作出的裁决,这一风险将足够抑制瑞士作为国际仲裁地的地位[6]。
基于类似考虑并希望能够巩固瑞士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地位,瑞士对《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86条进行了修改。于2007年3月1日生效的新18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应就其自身管辖权作出决定。其决定自身管辖权,不受在一个法院或在另一仲裁庭已经进行的基于相同当事人之间相同争议的诉讼的影响,除非值得重视的理由要求中止程序。”由此,瑞士法律承认了仲裁庭管辖权/管辖权原则的全面效力。仲裁庭可以决定自身的管辖权,瑞士法院将依据《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90条的规定在仲裁程序结束之后对裁决进行全面审查。未决诉讼规则不适用于仲裁领域。
2.英国及其司法实践
普通法国家发展出了禁诉令这一独特的方式来执行仲裁协议。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的主要依据是1981年的《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 1981)第37条及《1996年仲裁法》第44条。正如Hobhouse大法官在Turner v.Grovit(2001)一案中强调的,禁诉令不在于向国外扩张管辖权,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法院对受限的一方当事人具有对人的管辖权(the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签发禁诉令的权力是以一方当事人存在可以被限制的过错行为为基础,而且申请人对该行为有权起诉并具有预防受损的合法利益(例如,根据伦敦仲裁条款,不在外国法院受诉的合同权利)。自英国上诉法院在Anglic Grace案⑤中作出裁决以来,英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常使用禁诉令阻止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在欧盟的另一国家进行诉讼。但在欧盟法院最近的两个判决中,英国法院在欧盟内部使用禁诉令的权利已经受到了极大约束。在Gasser v.MISAT案“中,欧盟法院认为,《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的效力超越第17条的效力。即使后诉法院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exclusive jurisdiction),先取得管辖权的法院也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后诉法院必须中止法院程序并等待前诉法院的决定。在稍后的Turner v.Grovita案⑦中,英国法院为先受诉的法院,被告在原告在英国胜诉之后在西班牙再次提起诉讼。欧盟法院在对英国上议院的答复中认为,公约不允许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由某缔约国法院禁止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向其他缔约国法院提起诉讼或禁止其继续进行诉讼。即使该当事人为挫败对方的诉讼进行恶诉也一样。
如果仲裁协议同样可以被视为一项关于管辖权的排他性条款,那么类推上面两个案件的结论,英国法院在仲裁领域也不能够签发禁诉令。但《布鲁塞尔条例》第1条第2款d项却明确将仲裁排除在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arbitration exception),这引发了关于英国法院能否在仲裁领域签发禁诉令的争论。而这一问题随着欧盟法院West Tankers案尘埃落定⑧。
该案主要涉及船东West Tankers将其Front Comor轮出租给意大利承租人Erg Petroli,租约适用英国法,伦敦仲裁。船舶在意大利卸港Syracuse卸货时发生碰撞,把承租人的泊位破坏。承租人曾针对损失购买保险,但投保金额不足以清偿全部损失。承租人在意大利保险公司Allianz赔付之后,在伦敦提起仲裁向船东索取不足的金额,而保险人Allianz在赔付之后根据代位求偿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向意大利当地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向船东索赔保险金。船东希望在伦敦进行仲裁,因根据合并在租约中的《海牙规则》,航行疏忽可以免责。因此,他向英国高院商事庭(High Court of Justice of England and Wales,Queens Bench Division(Commercial Court))申请一项宣示判决,判决所有争议在伦敦进行仲裁。另同时申请法院签发禁诉令,以禁止保险人进行仲裁之外的程序。法院支持了船东的请求并签发了禁诉令。保险人则上诉到了英国贵族院。贵族院在法律地位不明的情况下向欧盟法院提出请示,“成员国法院以违反仲裁协议为由,裁定阻止当事人在其他法院开始诉讼或继续进行其他法院诉讼的做法是否符合欧盟第2001/44号指令。”
欧盟法院在分析中肯定了先受案法院有权决定其管辖权,后诉法院应当基于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司法主权的尊重而中止其诉讼,除非先诉法院裁定拒绝管辖。法院还认为,《布鲁塞尔条例》的目的在于促进各成员国司法体系的相互尊重,而禁诉令与该目的不符。针对《布鲁塞尔条例》不适用仲裁的问题,法院认为,规则制定“仲裁排除条款”的目的在于不影响《纽约公约》的适用。而且,依据《纽约公约》,并不只有仲裁庭及仲裁地法院有权对仲裁协议进行审查(其他国家法院也可,例如本案意大利法院)。意大利法院所进行的涉及仲裁条款的诉讼属于该法院排他性管辖的范围。最终,欧盟法院认为,为保护仲裁而做出禁诉令从而限制当事人在另一缔约国开始或进行诉讼与《布鲁塞尔条例》相抵触。
在不考虑欧盟相关公约的情况下,普通法中的禁诉令是一件非常有力的武器,也是英国作为仲裁地的一项重要优势之一。欧盟法院的判决对英国仲裁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将鼓励投机性的诉讼,使当事人可以恶意违反仲裁协议向法院起诉。在未来,仲裁与诉讼平行程序的经常发生几乎是可以预见的。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禁诉令的替代性方式,如对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请求损害赔偿,不承认违法的判决,信赖其他欧共体国法院并中止程序等⑨。
三、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完善
我国对于仲裁中的平行程序问题也有一定规定。从仲裁与诉讼的关系上看,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情况,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其分别进行了规定。
在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后,对仲裁庭管辖权有异议一方可以申请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据此,似乎仲裁委员会需等待法院的决定,而不能自行先就其管辖权作出决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⑩(下称批复)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该批复第3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13条也与批复的精神相一致,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另外,《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这一规定明确了诉讼中仲裁协议的放弃问题,与《示范法》第8条第1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一些采纳了《示范法》的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再者,我国《仲裁法》和仲裁法司法解释没有提及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上述批复第4条对此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作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另外,即使原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应撤案而继续仲裁,法院也可以在撤销或执行程序中对仲裁裁决效力予以否定。
值得一提的是,仲裁法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这一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仲裁机构间平行仲裁的发生。但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出发,似有侵犯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之嫌,并且在双方不能协调一致时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也不利于仲裁业的发展[7]。实际上,无论约定唯一的还是两个以上仲裁机构来解决争议,均体现了双方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时的合意。在争议发生后允许启动程序的一方选择其一进行仲裁并不违背双方当事人的原意,也有利于争议通过仲裁方式尽快得以解决。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启动另一仲裁程序,则后一仲裁庭应当终止程序。例如,德国最高法院(BGH)(11)在一项判决中认为,一项仲裁协议约定了不止一个仲裁庭,或者同时约定了申请仲裁和向法院起诉的,一般而言,申请人应享有选择权。
上述相关规定仅涉及国内发生的仲裁平行程序问题。在我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如何处理与外国仲裁机构和法院的平行程序方面,我国的规定和实践都极为缺乏。在未来制定相关规则时应当注意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性,在解决时不能照搬解决平行诉讼的方式。如果无法避免平行程序的发生,可以通过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执行程序避免相冲突的结果。目前,《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及其执行裁决的机制是我国处理相关问题的最为重要的依据。
四、解决平行程序问题的困境、建议与展望
各国司法实践揭示了诉讼与仲裁间平行程序问题的复杂性。各国在处理内国平行程序问题上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则。如何协调二者在国际范围内的管辖权冲突始终是一个难点。如果各国均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不承认仲裁在争议解决方面的地位和正当性,法院可以无视仲裁协议的存在而主张管辖,二者间就不会存在平行程序问题。但这显然不符合目前国际仲裁的法律与实践。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种规制仲裁与诉讼平行程序问题的统一法则。多数有关仲裁及诉讼的国际公约忽视了仲裁庭与法院在管辖仪问题上的交叉和矛盾,即使是对此有所规定的《纽约公约》、《欧洲公约》也未能起到约束平行程序发生的作用。最为理想的结果,是通过统一各国仲裁法或制定同时适用于仲裁和诉讼的国际公约,避免法院和仲裁庭的管辖权冲突。
通过对两大法系的考察,我们看到,不同法系国家在处理平行程序问题上分歧较大,各自都面临一些障碍。
以瑞士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先诉优先及可预期执行”原则,也影响了一些欧洲仲裁员的观念。例如,在一起捷克斯洛伐克的仲裁程序中(12),申请人因买卖合同纠纷提起仲裁之后,又基于一张担保对方在买卖合同项下义务的汇票在布鲁塞尔向法院起诉。被申请人对仲裁庭提出存在平行程序的抗辩。仲裁庭依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不能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执行而驳回了被申请人的抗辩。类似地,在比利时商会处理的一起案件中(13),申请人首先提起了仲裁程序,就一批卖给一法国公司的货物寻求赔偿。当被申请人在法国被宣告破产后,申请人又在法国破产法院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被申请人要求仲裁庭终结仲裁程序。仲裁庭认为,破产法院的判决没有域外效力,不能据此剥夺仲裁庭的管辖权,因而拒绝了被申请人的请求。上文对瑞士法院实践的分析已经揭示了适用这一原则的弊端,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186条的修改也体现了瑞士法律对“先诉优先及可预期执行”原则的摒弃。另外,仲裁庭将先诉法院判决能否在仲裁地国得到执行作为处理平行程序时的考虑之一,也不甚合理。实际上,当事人选择在某地仲裁往往基于多种考虑,例如仲裁地对于双方而言是较为中立的地点,或者双方较信赖仲裁地的法律制度等。无论仲裁庭还是当事人都不一定能够预测在当地是否会发生执行程序。
而在普通法下生长出来的禁诉令对支持英国仲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和法官来说,禁诉令与其法律传统相去甚远,引起了一定争议。例如,签发禁诉令被认为是干预了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仲裁的权利。一些欧洲国家法院认为,英国法院的做法是司法霸权的表现(14)。另外,由于各国法律以及理解上的偏差,英国对于仲裁协议范围的理解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通过签发禁诉令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法院或当事人,显然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从这一意义上讲,禁诉令并不是一个解决平行诉讼问题的良方[8]。另外,禁诉令受到了欧盟规则的限制,West Tankers案甚至预示了英国禁诉令在欧盟范围内的终结。今后,英国不得不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以继续保持英国仲裁的优势。
从仲裁庭角度来看,各国法律缺乏对仲裁员处理相关问题的指导。仅有个别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排除平行程序问题有所规定。例如,1998年《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3.4条规定:“当事人协议同意依照本规则进行仲裁应视为当事人已经同意不向任何国家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就仲裁庭的管辖权或权限之事申请救济,但全体仲裁当事人书面约定的、仲裁庭事先授权的或在仲裁庭已经作出裁决对其管辖权或权限的异议作出裁定之后提出的除外。”国际法协会(ILA)在《平行程序及仲裁的最终报告》中从仲裁庭的角度提出了如下建议[2]:1.肯定管辖权原则的积极效力,这一原则特别是在诉讼程序不在仲裁地国进行的情况下适用;2.考虑到仲裁的效率,避免相冲突的结果、昂贵的重复(costly duplication)以及采取不公正手段(oppressive tactics),建议仲裁庭在适当的场合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中止仲裁程序;3.仲裁庭应当尊重仲裁地的实践,尤其因为该国法院能够撤销裁决,并且往往不能容忍就管辖权问题不一致决定的存在。如果仲裁地法律规定仲裁庭应当遵从法院就管辖权问题的判决,仲裁庭就应当遵从;4.强烈建议仲裁庭在类似Fomento案的案件中,对自身管辖权作出裁决;5.平行程序并非公共秩序的一部分,仲裁庭不必主动提出,但当事人应当尽快提出与平行程序有关的任何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各国对于管辖制度的构建都具有合法的利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在制定国际公约相互融合时将遇到许多困难。如果各国希望通过国际协议的方式避免诉讼与仲裁的冲突,就需要协商和妥协,因为任何公约的形成都是各缔约方相互碰撞和妥协的结果。同时,各国法院之间、法院与仲裁庭之间、当事人对法院和仲裁庭,均应当建立信任。特别是要信赖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这种信任与促进国际统一规则的发展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的浪费是密不可分的。
收稿日期:2010-12-24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1年4月1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注释:
①See ECJ,Renault v.Maxlcar,May 11,2000,case C -38/98,para 31(not yet published).
②E.g.French-Italian Convention of June 3,1930 Art.19; Italian-Swiss Convention of January 3,1933,Art.8; Swedish-Swiss Convention of January 15,1936,Art.7; German-Italian Convention of March 9,1936 Art. l l; Belgian-German Convention of June 30,1958,Art. 15; Belgian-Swiss Convention of April 29,1959 Art. 10; Austrian-Swiss Convention of December 16,1960,Art.8; German-Greek Convention of November 4,1961 Art.3.
③如欧共体1968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及判决执行公约》及《卢加诺公约》第2l条,继这两个公约之后的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与判决承认及执行的规则》第21条,以及1999年《海牙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第27条都采纳了“先诉优先”的原则。
④依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58条,在仲裁庭依据仲裁协议受理案件后,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争议应宣告无管辖权;即使仲裁庭尚未受理案件,除仲裁协议明显无效之外,法院亦应当宣告无管辖权。这一规定同时适用于国内和国际仲裁。虽然与其他国家实践类似,法院可以在裁决作出之后对仲裁协议进行监督,但依法国法的规定,在仲裁程序中法院让与了仲裁庭对于实体争议的优先审判权。
⑤The Angelic Grace,(1995) 1 Lloyd's Rep.87.
⑥Case C-116-02 (2004) 1 Lloyd's Rep.222.
⑦Case C-159/02 (2004) 2 Lloyd's Rep.169.
⑧Lloyd's Rep.391,有关欧共体法院在该案前后的态度参见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仲裁法——从开庭审理到裁决书的作出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258页。
⑨同注释⑧,第258,266页。
⑩法释[1998]27号。
(11)BGH,30.1.2003-III ZB 6/02.
(12)Case No.RSB57/78,6Y.B.Com.Arb.127 (1981).
(13)See 4 Y.B.COM.ARB.191(1979).
(14)同注释⑧,第251,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