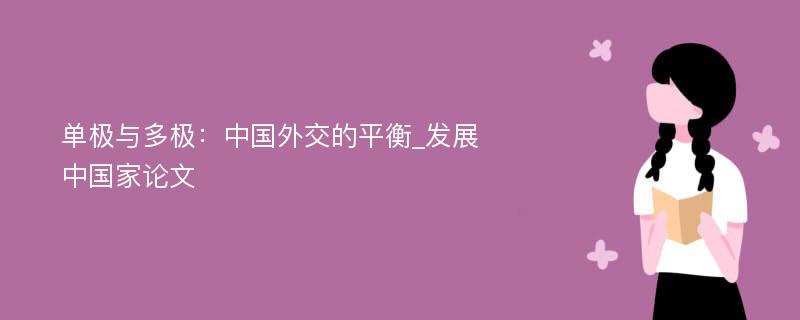
在单极与多极之间:中国外交的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多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儒家经典《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①中的“礼”指的就是“秩序”,它与“和谐”、“和平”、“致中和”等合和思想的辩证统一,成为今天中国人看世界的主要方法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和平与发展为旗帜,为一个人类永久和平与和谐的世界秩序②而孜孜以求,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为中国外交战略取得成功提供了坚定的理论支持。国外学者就指出,“新世界秩序问题几乎是和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古代学者就常常提出和探讨这一课题,包括古希腊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而“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来解释”世界秩序,就是实现“大同世界”。③如何建立一个对世界和中国的和谐发展更加有利的世界秩序?中国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谋求世界“单极”主宰世界地位的美国与中国、欧洲、整个阿拉伯世界、东盟④、整个非洲、整个拉丁美洲构成的多极世界之间,中国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度?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进行探讨的。因“世界秩序”本身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也应该作一些相应的调整,甚至在某些关键的领域,可能要作根本的改变。中国外交提出“一超多强”界定今天的世界格局是科学的。今天的世界,美国的单极霸权欲望甚嚣尘上,但是单极世界——美国治下的和平——不可能真正实现⑤,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世界上的某种主导地位(这里不用“领导地位”的提法,因为美国既无此资格,也无此种能力)则是客观的,估计在本世纪是可以继续保持的,世界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如欧盟)也在致力于多极世界的构建,但是,多极世界在本世纪无法实现,而且一个致力于多极化的世界一方面存在有利于世界和平格局和平倾向(或者说结构)的产生,就如《易经》中所说的,“见群龙无首”大吉一样,“群龙”形成了相互制约和相互平衡的格局,但同时也会出现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混乱情形,比如,今天日本和欧盟的崛起,很难说是和平力量的崛起,因为其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他们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侵略和扩张,他们的再次崛起,会不会旧病复发,这是很难说的,再说,日本长期以来也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什么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它实际上更愿意自己是美国的附庸国(当然,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出现动摇,在崛起的中国、和正在成为世界一极的俄罗斯、一体化加速发展的欧洲等多极化倾向日益明朗的世界中,日本也在考虑是否继续充当美国追随者)⑥。早在1990年代初,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中国学者就指出,“多极之中的不少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实际上相当紧张”⑦,这正好反映了多极中“恶”的一面。另一方面,美国的单极世界目标,总体上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不利,美国今天采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仍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还不够充分,美国某些时候和具体的政策,也可能对暂时的和平努力和世界稳定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我们不可忽视强大的美国民意对美国政府强权政策的一定程度的遏制和牵制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今天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中国在坚持自己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基本理念不动摇的前提下,总的方针应该是采取一个介于多极化与单极化之间的中庸哲学式的“混合极”理念,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战略才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国际关系才会向一个和谐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世界也有可能会建立起自己受人尊重的地位。《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⑧所以我们在多极世界和单极世界之间,应该把握好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⑨这样一个度。我们无论倒向多极世界或者单极世界的哪一边,在今天看来都是“过度”的形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界定“过度”的形式是“恶行的特征”,是一种“失败的形式”。⑩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关系中的“多极”和“单极”都是一种极端的形式,都是国际关系中的“恶”,中国只有在“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之间去努力寻求平衡,才会发现其中的“善”,那么这个“善”用什么样的措词来表达呢?恐怕最好的表达就是中国今天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了,这就如“勇敢”处于“鲁莽”与“怯懦”两恶之间,“自尊”处于“傲慢”与“自卑”两恶之间,“慷慨”处于“挥霍”与“吝啬”两恶之间,“谦恭”处于“无耻”与“怕羞”两恶之间一样,在现实生活是拥有“勇敢”、“自尊”、“谦恭”、“慷慨”等美德的人,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世达到了“中和”的境界,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成功也是一样,只有在若干两恶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才会取得坚定的成功。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似乎已经发展到向“中和”阶段(或者也可以说向和谐的中国外交的阶段)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今天中国及时地提出“和谐世界”的新外交理念,可以说是真正地超越了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极”的观念,正在向“合和”的观念发展。从“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争斗演变为“和谐世界”——表现为如何使世界和谐发展和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样两层含义,这是中国传统合和思想的回归,也符合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认为的“和谐产生于对立面的差异”,“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11)的哲学思想。中国推动“和谐世界”观在外交手段上最大的技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把握好外交平衡术。而特别有意义的是,“和谐世界”观,实际上我们从中国人几千年前的国际政治观中能找到她们的线索,比如五帝时代就有这样的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2),“百姓昭明,合和万国”,(13)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4),野无遗贤,万邦咸宁(15),庶政惟和,万国咸宁(16),唐朝有“遇大道行而两仪泰,喜元良会而万国贞”(17)。古代中国的帝王和政治家懂得,治理天下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合和”思想,以“合和”的思想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二、中国外交平衡的背景与措施
中国外交如何取得平衡,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中国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在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提出实事求是的、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中国外交平衡的背景
外交平衡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头戏,也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对于日美同盟,西方学者就认为,它的存在,“提供给了其他亚洲国家的第三方予放心(据说因为这样可以平衡中国的威胁),一个确切的例子是,有关作为军事大国德国在冷战期间的行为,北约把放心感给了第三方的苏联(third-party reassarance)”(18),这就是一种外交平衡术的研究,如果这些分析是客观的,至少我们不能指望日美同盟马上消失掉,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市场,它可能对中国周边国家平衡大国关系的心态发挥一定的作用。西方世界的旧安全观仍然有广泛的市场,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就不把它从2007-2012年的东亚外交战略的重点放在如何加强它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同盟的安全合作上了。(19)不仅如此,日本在美国的鼓励下,似乎和澳大利亚也在抓紧建立军事同盟关系(20),《远东经济评论》认为,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安全条约“核心就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别的”(21)。《经济学家》也直截了当表明,“日澳安全协定主要的催化剂最明显的证据是,中国的崛起!”(22)。所有这些都是从平衡的角度对付中国的。中国没有理由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地缘政治地位所具备的条件。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中国处在协调东西方关系的位置,过去中国强调意识形态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不搞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一政策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目前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还相当突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日本对伊斯兰国家,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对抗突出,中国由于走和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道路,西方国家一般认为中国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资本主义化”)。
第二让我们来了解一个中国“有容”政治文化的软实力基础。《道德经》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23)旷世教诲,林则徐堂联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自勉。中国几千年“有容”文化的培养,容得下世界上任何文明的存在,中国把“国际关系民化”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作为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和核心价值理念,对平衡世界的各种矛盾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可以乐观地预测到的。
第三让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意识形态新姿态的发展。“实事求是”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当代中国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都是主张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观,既是主张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世界观,又是主张合作与协调的世界观,即主张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协调,也主张和发展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即反对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也主张以“积极和平”——即不以战争和其他硬性冲突的方式处理简单地对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努力通过强调经济发展,加深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通过功能主义等方式,努力推动遏制霸权主义横行天下的机制,以达到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之目的。
最后再来考察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仍然落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仍比较低,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仍需要完善,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上述这些问题,没有上百年时间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根据这些基本国情,中国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仍然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为解决上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矛盾而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一方面要坚决地遏制各种干扰中国发展和前进的因素,另一方面更要努力地构建和谐的地区环境与和谐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目光如果只是放在中国如何参与到“多极世界”中对抗美国的“单极世界”,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就仍然找不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国根据自身国情称自己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外,中国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一般表述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关系中,相对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称自己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反映在对外政策导向上,中国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但是西方国家不顾中国的国情,看中国却有另外一种眼光和方式,称中国为“次超级大国”有之,或者干脆就称中国为“超级大国”、“世界仅存的老帝国”、“独裁国家”,……所以,在世界上,“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西方世界扭曲地认识中国的原因很多,核心是恐惧中国的崛起,当然我们政策上有时候过度强调世界“多极化”的主张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中国外交的平衡措施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注意到平衡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列子》就说“均,天下之至理也”,谁要是掌握了“均”的原理,“则天下可运于一握”(24)。解决好在多极世界和单极世界之间的外交平衡,最主要的是要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1.在多极与单极之间寻求平衡
(1)中国反对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但是中国承认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某种客观的主导地位,对美国有利于世界和中国的和平、繁荣、安全的行为,中国要以行动支持和配合,但决不意味着中国倒向美国或者承认美国为既定的单极霸权,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美国单极霸权的地位已经取得(25)。不要说美国并非真正的单极霸权,即使是完全意义的单极世界,中国也决不会丧失自己的立场,正如儒家经典《中庸》所说的“君子和而不流”(26)。有学者就指出:“虽然美国确实具有其他国家短期内无法超越的强大实力,但是要构筑一个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其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2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秩序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高度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同时贯穿安全、生产与交换、金融及意识形态四个领域,建构这个结构的主要行动者就是美国。”(28)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承认美国单极世界的地位,对美国力量的认知绝对化。从客观情况来看,美国最多只能算是处于“准一元化”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承认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某种客观存在的主导权。当然如果从中国的民族感情和美国长期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们确实不愿意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一地位,但是感情的东西毕竟不能简单地取代国家利益和客观现实,也不能产生理性的精神。
(2)中国尊重世界多极化的客观发展趋势,但是中国对新霸权主义和新强权政治的抬头必须以高超战略和策略的动作加以遏制,此举并不意味着中国否定多极世界目标的道德价值。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但邓小平同时又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29)如果说用一百年时间都未必能够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种看法可能并不算过分;而且如果真的会形成个多极世界,是否就一定能保障比今天的和平质量还要高也未必如此。至少我们今天看到的多极化的进程是相当不稳定的。
2.重视区域机制协调平衡与全球机制之间的平衡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性政治与安全机制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国在全球性经济机制中的作用也在开始加强(比如中国在世行和IMF中的投票权),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性机制中众多的领域中中国的存在。中国在区域机制中的存在也是很充分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上合)、东盟10+3机制等,总体而言,中国总体上很好地协调了全球性机制与区域性机制的关系,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为全球性机制的联合国的作用停滞不前,即使现在能听到一点关于它的声音,其背后也能常常有美国和欧洲大国的影子,比如美国和欧洲近年来总是威胁要用安理会机制制裁伊朗和朝鲜两个以和平为目的的开发核能的国家,好在安理会中有中国和俄罗斯的坚决抵制,才使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安理会制裁这两个国家的图谋未能产生什么效果。当然联合国还能在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它总体上是被动的,所能发挥的政治和安全作用越来越小。早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就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国际组织是一定的世界秩序的产物,又是为维护这种秩序而存在的。联合国是以雅尔塔协议体系为基础并以维护这一体系为目标,在安理会中赋予5大国以否决权,实行‘大国一致’方针,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合国因两极格局的制约,作为是很有限的”(30),“联合国前50年的历史,如果同其创建者在旧金山开会时提出的目标相对照,总体上很令人失望。任何人试图说明联合国那令人冷静思考的头50年的历史,都必须首先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使世界、也使联合国陷于分裂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31)目前,中国正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区域组织倒是发展得不错,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目前正处于平稳的发展时期,它以从容的姿态向印度和伊朗等国开放,它将极大地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弱小国家的恣意妄为。观点十分右倾的日本《世界日报》社论无不恐慌地说:“上合在2005年事实上要求美国撤走其在中亚的军事基地,特别是中俄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和上合准成员国印度达成演习的协定等等,上合正在逐渐地显示‘非美军事同盟’的特点。如果伊朗成为上合正式成员,它有了上合这一后盾,国际社会正在讨论之中的对伊朗的包围网就会泡汤,与此同时,所谓军事制裁这一最后的杀手锏最终将派不上用场。”(32)显而易见,“上合”正在日益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区域多边组织和全球性组织之间关系如何?换言之,上海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因为联合国作用有限才回头注意发展区域组织?还是充分考虑到了它和联合国之间战略上的互补的,或者说有某种重要的协调性(或者说联合国对它有指导或者领导作用)?会不会出现“20世纪末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所显示的地区主义在形成世界秩序方面潜在的和现实的缺陷,即像北约那样绕过联合国对某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干预,显示出明显介入性的组织”(33)?上合不是脱离联合国框架之外发展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开放透明,这是它不同于北约之处,也是它的希望所在。关键是要看它将能否把自身发展和联合国作用的加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非常重要。
3.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寻求平衡
先秦时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非常重视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平衡,他指出:“大国好比江河的下游,天下的牝雌。天下雌雄交合,雌性常以安静战胜雄性。因此雌性安静无争,所以宜居于下位。所以大国屈己尊重小国,就得到小国的归顺。小国屈己尊重大国,就被大国所容纳。因此,有的谦下而有所得,有的谦下而归附他人。所以,大国谦下不过是想兼并蓄养小国,小国谦下不过是想要侍奉大国。(如果要使)双方都满足他们的愿望,那么,大国宜居于卑下的地位。”(34)当然老子所讲的大国和小国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含义上有区别,即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那个时代名义上还是把“周天子”作为他们的正宗和权威的中央政府看待,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形式上列国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之间的争斗,尤其是大国和小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有效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最后导致相互摧毁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老子以巨人般的气魄和卓越的智慧,站在哲学的高度,给出了使当时的“世界”能够和谐相处的药方,尽管老子所想达到的目的并非是今天中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但是他所强调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今天应用于实践之中去。中国作为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对待小国,首先要谦恭,这也是深入到当代中国外交骨髓之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美国软实力近年来处于急剧下降之趋势,其实就正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杰弗瑞·威兹曼(Geoffrey Wiseman)撰文指出的,美国严重地忽视了“武力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透明度、持续的对话、多边主义、谦恭”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外交文化(35)。
我们不但要重视大国外交,也要高度重视小国外交,这既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外交科学和准确把握国际关系脉动的需要。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撰文认为,“现在是一个小国时代”(36),如果从人均财富和人的安全和幸福指数排名等指标来看来,一些发达的小国确实占有明显的优势。世界确实出现了老子所希望的“小国寡民”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国和若烹小鲜般那样小心仍然困难重重的大国并存竞争的时代。当然,拉赫曼只说对了一半,绝大多数小国仍然在今天的世界面临深刻的生存与安全危机。而这个绝大多数的小国,均是中国外交的天然的立足点,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所在。目前学术界比较重视大国协调的研究,而大国和小国之间如何协调的研究比较薄弱。小国研究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排挤和欺负中小发展中国家,在今天的世界随处可见。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目前除了联合国成员国之间好像大小国家之间通过联大尚有一定程度的协调机制。最极端的情况是八国集团,他们完全是富国俱乐部、大国俱乐部,当然,他们现在也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参与,但是坦率地说,中国和印度也是大国,大国聚在一起如果没有小国平等的参与,这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表现。而且只是由大国聚在一起所作出的决定,肯定是片面的。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没有无产阶级的行动,民主的和平也好,裁军也好,都根本无从谈起”(37)一样,世界事务如果没有在世界处于绝大多数的目前仍然贫穷落后的小国的参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就无从谈起。
鉴于这样的认识,中国要发起建立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协调与沟通机制,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任何形式的,真正体现大小国家平等的战略性和日常性的协商和对话机制。
4.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平衡
发达国家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主要由单极世界的美国和欧洲、日本组成,他们与实力弱小的极——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和大国集团构成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属于发展中的成员,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主要的是遏制和防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欺压政策,但同时也不会寻求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发达国家的正常国际行为。努力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实际上就发挥了此种作用。中国既不是华盛顿的现实主义者看作的别无选择的、只能为美国所领导的“杠杆盟友”(the leveraged allies),更不是华盛顿理想主义者所喜欢的、和美国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繁荣民主的“天然盟友”(natural allies)(38),这就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外交可以最大限度地执行一个如果美国的政策是符合和平与发展要求的,中国就可以和它“合而同之”,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违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则采取加强和美国沟通和对话但对其行为敬而远之的“合而不同”的政策。
发达国家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力为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但由于他们的发达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剥削穷国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中国必须通过引导他们积极地、建设性地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改变发达国家单边的国家利益趋向,通过协调南北对话,实现南北共同发展。中国总体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也具备了发达国家所具备的相当程度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地位决定中国客观上处于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关系协调者的地位。
5.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国际环境的好坏,往往决定一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好坏,列宁曾经在他的最后的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生动地描述到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是如何地影响着新生的政权发展的艰巨性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他说:“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39)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是在“战争”与“和平”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争取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充分抓住“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在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旗帜,对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谋求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显示了勃勃生机。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中国内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在初级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盛行等问题比较突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党和政府的核心关注。对外方面,由于沟通不够,特别是西方国家固有的偏见及对不可逆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嫉妒,“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客观上对世界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比如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使世界享受实惠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和中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深的国家的经济和相关产业受到冲击,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盈余过大,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或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对市场和资源的激烈的竞争,中国的一些公司在进口别国产品时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忽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国内需扩大与进出口不平衡等等问题,这些矛盾也为“中国威胁”提供了一些佐证和口实,有国外媒体就认为,“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引起不满,它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土壤”(40)。当然,中国现在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以解决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以中美经济关系为例,为缩小对美贸易顺差,中国一直在作积极努力。就在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访美前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代表团与美方签署了总价值约162亿美元的107份采购合同,涉及飞机、软件、移动通讯、机电等产品。联想集团还表示将在12个月内向微软采购价值12亿美元的产品。2006年4月18日到22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访问,他在和布什举行会谈时,除了对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之外,胡主席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布什总统谈扩大内需、人民币升值、转变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export-driven growth),强调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刺激国内消费、改善卫生、教育和退休等国内经济和社会及民生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主要依赖内需促进经济增长(41)。很明显,胡锦涛主席和美国总统的正式会谈中如此重点地谈中国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经济贸易不平衡问题,其中一个明显意图,就是努力地消除在美国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为中国现代化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双边环境。中国的经济面临转型,这不但是中美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人民自身能否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当然也是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日本媒体对此评价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对外政策,走上了一条“内政与外交相协调的路子,中国正在从经济增长一边倒的政策向重视如何可持续的增长的政策转变”(42)。这里面所暗含之意,就是自身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关注点。
6.在官方外交与非官方外交之间寻求平衡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是官方外交,随着时代的发展,超越传统的外交迅速地发展起来。一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如果只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显然已变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官方和非官方的多轨的外交对一国有效达成外交目标非常重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针对中国最近在低级政治领域所遇到的一系列麻烦问题而使外交处于某种尴尬局面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官员习惯于通过传统的方式和其海外的外交同行打交道,但是西方社会中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他们活动范围可以从气候变化到达尔富尔问题等广泛领域,其影响可以左右国际进程和影响公众舆论,中国官员还尚不知如何和这些针对单一问题的倡导团体(the single-issue advocacy groups)打交道。”(43)我们剔除该报对中国外交官明显的偏见成分之后似乎也应该承认,我们对中国外交中的许多新的变量缺乏了解和应对之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外交应该努力使官方外交和非官方外交平衡发展。欧美国家当代外交一般都非常重视在非官方的层次发挥其影响力,比如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就强调“通过自由欧洲模式的电台项目,对其劳工联盟加紧攻关和加强学生交流”(44),当然我们在剔除其干涉别国内政的成分的基础上,把“公民社会”纳入外交的视野,建立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的非官方外交的新机制和新平台,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国际关系学学术界应该重视公民社会条件下的非官方外交的研究。我国国际关系学著名学者王逸舟的《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从市民社会成长及其作用的角度,透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的若干进步及其动因(45),应该说开了一个好头。
7.在总体外交各个方面寻求平衡
中国外交之所以显示其勃勃生机,关键就是总体外交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协调和平衡的发展,在中国总体外交之下,有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军事外交等功能性的外交。不同的阶段中国总体外交下的各项功能性外交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所不同,比如,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不但巩固和发展了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外交和科技外交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对我的遏制,政治外交和科技外交、包括经济外交、环境外交的难题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外交瓶颈,在努力保持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势头的同时,中国重点地抓了文化外交、军事外交和环境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军事外交方面,中美、中日之间军事交流的风景线,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议程之中的新举动,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所有这些,都增大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互信,提高了世界对中国以谋求世界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外交文化(外交文化是指根深蒂固存在于国家层次的有特色的外交机制、价值和规则)的认识度。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外交还有什么需要更加优化的地方的话,最主要的恐怕是要从外交的内涵上平衡中国的外交行动和调动中国和世界的外交资源,比如,怎样使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硬实力外交和提高国际形象为主要目的的软实力外交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在改革和开放时代主要进行的是硬实力外交,软实力外交相对滞后,这就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过来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中国政府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等举措,就是使软实力外交与硬实力外交取得平衡的努力。为了巩固和扩大中国软实力外交的空间,中国还应该在充实自身的外交机制、提升中国外交的价值和适应世界外交的规则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在单极世界企图和多极世界目标的较量过程中,中国外交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使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和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中国外交应该采取各种外交变量的平衡之策,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和谐世界观的核心内涵,从而为世界和平作出中国自己的特殊贡献。
注释:
①《论语学而第一》。
②世界秩序有两层含义:从客观方面看,它表明国际关系体系中,各个行为体之间分化组合的状况、位置排列的次序、相互作用的方式。从主观方面看,它是由各国公认的、用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具体包括国际惯例、国际道义、国际法原则、国际关系准则、国际条约制度,以及负责这些法规得以遵守的或制裁违法者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是世界秩序的关键组成,它力图在没有中央权威的多国家体系之中,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参见韩朝东:《世界秩序简论》,《国际政治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2页。
③(阿根廷)C.达贡《新世界秩序纲要》,《国外社会科学》,1983第6期,第41页。
④Joseph Y S Cheng."China's ASEAN policy in the 1990s:Pushing for regional multipolar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Aug 1999.Vol.21,Iss.2; p.176.
⑤过去,国家之间的秩序大都是优势和屈服:“罗马治下的和平”就是一个帝国对世界的统治:“欧洲的协调一致”就是少数几个相互之间保持平衡的强国的共同统治;这些就是历史给秩序规定的公式。
⑥《米大統領選[变化]の行方を見定めたい》2008年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
⑦Nicholas D.Kristof,China Gains in Mideast Crisis But Loses Cold War Benefits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New York Times.(Late Edition (East Coast)).New York,N.Y.:Nov 11,1990.p.A.1.
⑧《中庸》第一章。
⑨此句意思是,“你无法与它亲近,也无法与它疏离”,《道德经》五十六章。
⑩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1页。
(11)王敏,吴晓蓉:《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的哲学看古希腊的和谐教育》,《当代教育论坛》2007年第11期。
(12)《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13)《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14)《尚书》虞书·尧典。
(15)《尚书》虞书·大禹谟。
(16)《尚书》周书·周官。
(17)《贞观政要》规谏太子第十二。
(18)Paul Midford,China views the revised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popping the cork?,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Feb 2004; 4,i; p144.
(19)U.S.Department of State,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07-2012U.S.,p46.
(20)"Japan,Australia Eye Regular Talks of Foreign,Defense Ministers",Jiji Press English News Service.Tokyo:Feb 20,2007.pg.1
(21)Robyn Lim,Japan and Australia:A Bridge Too Far?.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Hong Kong:Apr 2007.Vol.170,Iss.3; p.33,
(22)Asia:We're just good friends,honest; Security in Asia,The Economist.London:Mar 17,2007.Vol.382,Iss.8520; p.73
(23)《道德经》十六章。
(24)《列子》汤问第五。
(25)"An American Empire?," The Wilson Quarterly(Summer 2002),pp35-82.Willian,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 Security,24-1(Summer 1999),pp.51-41,esp.7-9.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June 2002).pp.1-19.Charles Krauthan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Spring 1991 ),p.23 ff.Bruce Cumings," Still the American Centu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Special Issues)(Dec.1999),pp.271-99.转引自“日本平和学会編:《世界政府の展望》《平和研究》,第28号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第59页。当然,最近对美国单极霸权进行反思的西方研究成果也逐渐出笼,如Robert Jevis,"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 The washington Quaterly SUMMER 2006.
(26)《中庸》第十章。
(27)李鑫炜:《大国冲突与世界秩序政治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28)朱云汉:《中国人与21世纪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54页。
(29)《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
(30)陈鲁直:《国际组织与世界秩序》,《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第4期,第1页。
(31)唐纳德·J·普哈拉:《世界图景,世界秩序和冷战:神话制作的历史与联合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第31页。
(32)“上海协力機構/ィラン包囲綱に水を差すな”,2006年6月1日日本《世界日报》。
(33)阿米塔夫·阿齐亚:《地区主义和即将出现的世界秩序:主权、自治权、地区特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3页。
(34)《道德经》六十一章。
(35)Geoffrey Wiseman,Pax Americana:Bumping into Diplomatic Cultur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Volume 6,Number 4,November 2005,pp.409-430(22)。
(36)英国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全球进入小国时代?》,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7日。
(37)《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1页。
(38)Edward A Lynch.Uganda and U.S.Foreign Policy,Orbis.Greenwich:Winter 2006.Vol.50,Iss.1; pg.103
(39)《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第341页。
(40)“米中首腦会談利害共有者の責任ガ試される”,2006年4月22日日本《每日新聞》。
(41)Joseph Kahn,Bush and Hu Vow New Cooperation,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2006.
(42)“米中首腦会談利害共有者の責任か試される”,每日新聞2006年4月22日。
(43)Peter Ford ,"Beyond food and toys,China struggles with its global reputation:From climate change to Darfur,public opinion polls reveal a global unease with the growing superpower" .the September 12,2007,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44)Howard La Franchi," A new US bid to contain Iran" ,the June 01,2006,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45)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