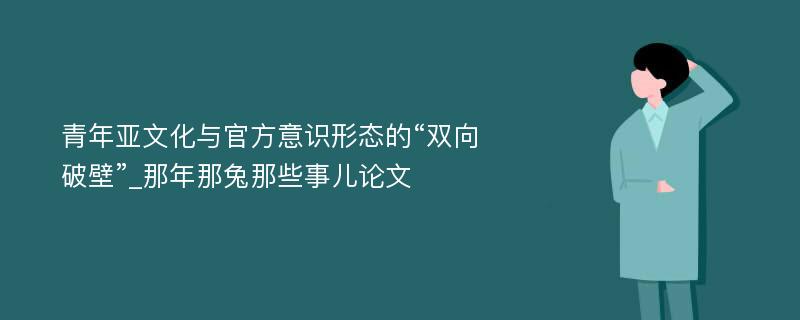
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双向论文,文化与论文,青年论文,官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与数码转型的推进,民族主义正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演变出多种新的形态,近年来在中国网络空间兴起的“二次元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当代民族主义的这副新面孔展开追溯与考察。 二次元的双重面向:ACG文化与趣缘社交网络 在进入对于“二次元民族主义”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先就“二次元”这个关键词做一番基本的描述和界定。 “二次元”(にじげん;nijigen)这个词源自日本,它在日文中的原意是“二维空间”、“二维世界”,本是一个几何学领域的术语,后来被日本的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爱好者用来指称这三种文化形式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幻象空间。这三种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互渗和产业互动,因而在日本也被合称为MAG,即Manga、Anime、Game的英文首字母缩写(Manga特指日式漫画,Anime特指日式动画);而在华语地区,这三者则通常合称为ACG,即Animation、Comic、Game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在不同的语境中,ACG既可以特指产自日本的动漫游戏,也可以泛指各个国家的动漫游戏)。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后冷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ACG产品通过种种正规或非正规的流通渠道,大规模地流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的新生代文化消费者的接受习惯和审美趣味产生了相当深广的影响。随着ACG文化的跨国传播,在日本被用于指称ACG爱好者的“御宅族”(おたく;otaku)一词,也一道传入了华语世界。在从日语到汉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中,由“御宅族”这个日源词又逐渐衍生出“阿宅”、“死宅”、“宅男/宅女”等称呼。由于互联网络的传播效应,“宅男/宅女”这组较之“御宅族”而言更为本土化的词语,逐渐为越来越多并不爱好ACG的人所使用,而在指代对象上,也由ACG爱好者置换为“长时间待在住宅里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宅男/宅女”被大众舆论注入了不少贬义的色彩,甚至在一些主流媒体那里遭到污名化和妖魔化。为了避免“御宅族”这个词所容易带来的误解,近年来,中国的很多ACG爱好者倾向于使用“二次元”这个词来作为自指称谓和身份标识。这个意义上的“二次元”,不但可以用来指称作为个体的ACG爱好者,而且更多的是用来指称ACG爱好者基于趣缘认同而形成的亚文化社群。 这种“二次元”文化社群是在数码媒介环境中形成的趣缘社交网络。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大多都是熟练使用数码媒介的“数码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数码媒介的理念更新与技术演进,使得新媒体的使用者不仅是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和媒介信息的接收者而存在,而且能够通过人机交互的用户界面,借助种种具备可读可写性、允许用户生成内容、支持群体协作任务的互联网应用,成为文化产品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和媒介信息的双向交互者。作为这样一种新媒体用户,二次元爱好者不仅能够从既有的文化产品中创造出与自身情境相关的意义与快感,进而通过互联网的评论机制,将各自的意义与快感转化为种种声明,甚至通过“弹幕”①这样的技术手段,即时地将自己生产的声明直接添加到正在消费的文本对象之上。而且,二次元爱好者还能够将那些文本对象当作“为我所用”的素材,借助各种媒体工具创作出各式各样的“同人”②文本,进而利用各种互联网应用提供的发布平台与传播渠道,公开地发行这些自创的文本,能动地参与到“二次元文化”的扩大再生产之中。 这些行为会使得原本在现实空间互不相识的二次元爱好者,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发生频繁的人际互动,并由此生成崭新的情感联结。在这里,对于ACG文化的兴趣爱好扮演了“因缘之纽带”的角色,牵引着弱联结向强联结转化,进而凝聚成社交关系相对紧密的“趣缘社群”。这些社群的集体认同,并不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而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社群成员会基于这种趣缘认同而集聚在与共同爱好相关的目标之下,受共同目标的引导开展各尽其能、各显其才的团队合作,以网络协同作业的方式从事文化生产;社群成员还会在现实空间中开辟出想象性的飞地,将其临时改造为“同好面基”(共同爱好者面对面交流)的聚会场所,凭借移动智能终端支持的即时通讯,组织起丰富多样的集体活动。这些同好之间的同人活动与趣缘社交,是“二次元”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对ACG产品的消费。因而,作为当代流行文化场域中的新兴词语,“二次元”不仅意指ACG文化,而且意指ACG爱好者所形成的趣缘社交网络。 二次元/三次元的壁垒:趣缘认同与国族认同的矛盾 虽然二次元爱好者的趣缘社交融合了线上交流和线下交往的方式,消解了赛博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但在话语层面和心理层面,中国的很多二次元爱好者却又格外凸显某种将二次元世界与别的世界区隔开来的壁垒,他们将这种壁垒称作“次元之壁”。 在ACG文化的面向上,“二次元”这个概念强调的是ACG的媒介特性,在三维动画技术成熟之前,这三者在视觉上都是由二维的图像所构成的(即便是在三维动画技术已然相对成熟的当下,日本的ACG产品也依然相当普遍地延续着二维时代建立起的美学风格),这个意义上的“二次元”,既与“一次元”——以文字而非图像作为基本媒介的文艺形式——相区别,又与“三次元”——由真人、真实事物作为拍摄对象的营造三维幻觉的电影、电视剧——相区分;与此同时,“二次元”这个概念还强调ACG创造的世界所具有的“虚拟”、“幻象”等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二次元”主要是与“三次元”相区隔,这里的“三次元”指的则是真人置身其间的三维现实世界。而联系着这个面向的“二次元”概念,“次元之壁”既是指区别二次元与一次元、三次元的媒介规定性,也是指阻挡ACG爱好者“真正地”进入二次元世界的物理和生理限定。 在趣缘社交网络的面向上,“次元之壁”则经常被二次元爱好者用来形容二次元与三次元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这里的“三次元”指的是那些无法共享ACG文化经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对二次元抱有偏见而又占据着强势话语权的人群。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心理感受,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虽然市场细分的创意生产和源流多样的类型嬗变,早已使得日本的ACG产品覆盖了其国内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但迄今为止,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依然是以青少年、在校生为绝对的主力人群③,因而,二次元文化在中国仍是一种相对小众的青少年亚文化,二次元爱好者与掌握强势话语权的成年长辈之间,存在着代际的鸿沟和文化经验的隔阂。二次元爱好者所喜爱的动漫游戏,常常会被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视作“无益于学习”的不良爱好,而日本的“全年龄向”ACG产品乃至“成人向”ACG产品所或多或少包含的色情、暴力元素,更是常被以“监护者”自居的成年人视为动漫游戏“毒害未成年人”的“罪证”,成为老师、家长仰仗他们的制度性权力和习俗性权威来干涉青少年文化生活的依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正如“二次元”的词源所提示的,中国现有的二次元爱好者,大多是由国外的动漫游戏——主要是日本的ACG文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培育而成的,而同一时期的国产动画、漫画、游戏的质量和口碑却普遍欠佳,在国内市场的实际占有率也相当有限。④因而,中国二次元爱好者的趣缘认同,主要建基于他们对日本ACG文化的兴趣爱好,这种状况使得这些二次元爱好者常常要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强势话语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是来自国家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从2006年起,广电总局、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多次出台了针对国外动漫产品的禁令,对于那些熟练使用互联网新媒介来获取资讯和资源的二次元爱好者来说,政府机构的这些举措虽不能实质性地威胁到他们的“二次元”文化生活,却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的兴趣爱好遭受了来自“三次元”强权的粗暴打压。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于同代际或稍微年长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所谓的“反日愤青”。毋庸赘述,中国与日本之间不仅横亘着至今仍然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而且存在着不时便会引发争端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现实利益纠葛。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仇日情绪成为了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普遍具有的一种敌对情绪,而向日本(即便只是并不与现实政治直接相关的日本商品或者日本文化)表示好感的行为,则容易招致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诸如“汉奸”、“卖国贼”等骂名。在民族主义盛行的舆论环境下,二次元爱好者对日本ACG文化的狂热喜爱,难免会遭到“反日愤青”的抨击和打压,他们的趣缘认同甚至会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放置在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族认同的对立面,因此面临着某种“合法性的困境”。 面对师长的权威、政府的权力和民族主义者的强势话语,中国的很多二次元爱好者并没有选择积极地申辩或者主动地回击,而是采取“次元之壁”这样的隐喻性修辞,进一步强化了不同人群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心理暗示,并通过与此相关的话语实践,展开某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通过建构一道想象性的壁垒,这些二次元爱好者尝试划分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壁垒之内的世界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亚文化圈子,二次元爱好者经由线上交流和线下交往结成“圈内好友”,借助网络社区和面基聚会建设趣缘共同体,由此获得“抱团取暖”式的情感支持和“有爱的大家庭”一般的集体归属感,共同抵御来自“三次元”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交活动又遵循着某些特定的默契或者“网络礼仪”,从而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等“三次元”的话题一如现实政治事件、民族主义思潮、中日外交冲突,等等——统统隔离在壁垒之外,打造出一片非社会化、非政治化的想象性飞地。通过这样一种话语策略,二次元爱好者回避了对其“合法性困境”——尤其是趣缘认同与国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正面应对,而是以消抹问题的方式予以了想象性的化解。 次元之壁的双向破解:ACG文化与民族主义的接合 虽然很多二次元爱好者对“次元之壁”进行了心理层面的想象性建构和话语层面的象征化表达,但这种试图将二次元的趣缘社交网络圈定为某种非政治化的自治空间的“次元之壁”,从来都是裂隙重重、岌岌可危的。近年来,在多方势力的合力之下,这堵“次元之壁”更是从内外两个方向遭到双向的破解,并由此生发出多种崭新的文化现象,“二次元民族主义”就是由此兴起的文化潮流之一。 造成“二次元民族主义”兴起的内部动力,是源自“二次元文化”这种青少年亚文化所发生的主流化趋势。“次元之壁”的话语策略,在帮助二次元爱好者暂时消解二次元文化与三次元文化的矛盾冲突时,也意味着将“二次元”的趣缘社群与“三次元”的主流人群对立起来;随着“80后”乃至“90后”日益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因年龄增大和社会地位提升而部分地获得主流话语权的不少二次元爱好者来说,“次元之壁”这样一种自我边缘化的对策终究不是解决矛盾的长久之道。对于这些追求主流化的二次元爱好者来说,寻找一条与社会主流话语的有效对接路径,完成ACG爱好的自我合法性论证,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话语,正是相对而言最为近便的选项之一。以2008年4月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为一个标志性的契机,越来越多的二次元爱好者“破壁”而出,积极主动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且通过ACG同人创作这样的二次元文化形式抒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 事实上,这些二次元爱好者大多都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真切地置身于转型期社会的价值真空之中;而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日本ACG作品尤其是不少“燃系动漫”⑤的世界观设定,虽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大都堪称宏大,它们正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为填补二次元爱好者在文化价值上的匮乏,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代偿。因而,虽然中国的许多二次元爱好者在“三次元世界”从应试教育到职场就业的残酷竞争环境中,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利己主义者的姿态、一种个人主义的生存策略;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会从“二次元世界”中汲取一种替代性的世界感和临时性的宏大叙事。这些二次元爱好者对于ACG宏大叙事的这种接受,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间依然保持着某种具有亲缘性的接口,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会与中国崛起背景下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官方机构所着力宣扬的“中国梦”话语发生非必然的接合。 另一方面,官方的意识形态部门在宣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也在尝试突破旧有的已然僵化的宣传模式,尝试借重为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以期实现更为良好的宣传效果。就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宣传需求而言,备受新生代喜爱的ACG文化无疑是一种可资借重的重要文化资源;而官方意识形态部门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就构成了破解“次元之壁”的一股外部力量。青少年亚文化的主流化诉求与官方宣传的大众化需求的接合,形塑了一个富有潜力的市场空间,敏感的文化产业从业者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商机,随即将积蓄多年的同人创作潮流转变为商业化发行的文化创意产品。 例如,成立于2014年的民营公司翼下之风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在2015年出品的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简称《那兔》),就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创意产品。《那兔》改编自网友“逆光飞行”自发创作并在网络发表平台连载的同名漫画,其主创人员大多都是投身动漫行业的二次元爱好者,对于ACG的媒介技法和文化语法可谓谙熟于心。这部动漫作品颇为有效地运用了ACG文化的“拟人化”手法——先是将各个国家比拟为各种动物,再对这些动物进行拟人化的处理——为并非“化身为龙”而是“化身为兔”的中国塑造了一副颇为讨喜的“萌化”形象,使得在正统叙事中显得严肃沉重的历史讲述变得活泼而轻盈。在《那兔》中,同一形象的兔子在不同的段落扮演了两个层面的角色:在展现国际关系的段落中,兔子是人格化的中国,他与鹰酱(美国)、脚盆鸡(日本)、毛熊(俄罗斯)等国家—动物的拟人化形象进行着国与国之间的角力;而在涉及具体事务的段落,兔子又是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的一个又一个中国人,从国家领袖到高级军官、学科带头人再到最普通的士兵或科技工作者,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外表,彼此之间以“亲”互称,共同守护和建设着“种花家”(“中华家”的谐音,在这里是对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的昵称)。通过这种双重的拟人化手法,作为个人主体的“我”与作为国家主体的“我兔”,经由直观的视觉形象建立了直接的身份同一性。而这两个层面的“兔子”角色,又对应着《那兔》的另外两重情感编码:以个人主体的牺牲达成“虐”的效果,进而以国家主体的逆袭达成“燃”的效果。通过“萌—虐—燃”三种动情方式的交替运作,《那兔》顺畅地讲述了众多个体兔子纵情燃烧自己的生命,让国体兔子发展成为“蓝星”(地球)最强者之一的故事,而这种主角通过努力奋斗由弱变强的故事,正是“燃系动漫”最经典的情节套路。虽然在此变强的真正主角,只是作为国家主体的那只兔子;但正如那句无数次出现在弹幕上的重要台词——“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所昭示的,在《那兔》的上下文语境中,个体兔子的梦想也就是国体兔子的梦想,第一人称“我”在此同时重叠了作为个体的兔子和作为国体的兔子。 《那兔》不但有效地运用了ACG文化的特定手法,而且极为自觉地打破了“次元之壁”。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那兔》每一集的片尾都并非动画,而是滚动播放若干张历史照片,这些有意挑选的“三次元”照片会与各集动画以“二次元萌化”的方式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形成呼应,配合片尾字幕对照片内容的介绍说明和资深“兔粉”利用弹幕所做的“历史科普”,似乎是在强调《那兔》的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进而强调“兔子—中国”的对应关系的“一致性”。为了达成特定的意识形态效果,《那兔》自觉地将其历史视野局限在军事战绩和军工成就的领域,其历史叙事看似包含了许多“虐点”,实则规避了数不胜数的创伤性事件和灾难性事故,它试图将充满断裂和冲突的中国当代史,整合成一个朝着某种预定目标进步的发展过程。而既然个体兔子与国体兔子的“镜像复制”,已然将身份认同的向度限定在民族—国家的维度,屏蔽了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地域冲突等其他维度的矛盾,想象性地抹除了国族内部的对抗性张力,那么,《那兔》的这番“我兔逆袭”的“燃向”叙事,也就可以相对顺畅地在文本外部获得“中国崛起”这种历史—政治逻辑的支撑。凭借多平台的网络播放和跨媒介的品牌运营(《那兔》已开发出一条从漫画到动画到电子游戏到相关周边的产业链条),《那兔》这部“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动画”,为多个活跃而又相对封闭的亚文化圈子提供了一个趣缘扭结点,成功地将相当一部分二次元爱好者与网络民族主义者(“自干五”、“四月青年”、“爱国小粉红”等)连接在一起,整合成一个数目可观、声势浩大的“兔粉”群体。通过视频网站用户仪式化的弹幕评论,以及包括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账号在内的网络节点在社交媒体上的转发互动,围绕《那兔》形成的粉丝文化又与官方意识形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共谋关系。 虽然中国现有的二次元爱好者主要是由日本的ACG文化培育而成的,但近年来,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时代语境之下,中国本土的动画、漫画、电子游戏也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基础(动画年产量甚至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正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涌入这个潜力巨大的“二次元产业”——ACG产业及相关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链条,通常被文化产业从业者与资讯提供商概称为“二次元产业”。 政府有关部门也已多次出台文件,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中国梦”的国产动漫提供政策扶持。在资本力量与行政力量的作用下,二次元文化的主流化已是大势所趋。从这个角度观察,“二次元民族主义”可谓方兴未艾。更加多元的“双向破壁”,或许同样前景可期。 注释: ①“弹幕”是指在提供即时评论功能的视频网站上,那些横向飘过视频画框或悬停在视频画面之上的文字评论。参见林品、高寒凝:《“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二次元·宅文化》,《天涯》2016年第1期,第185-187页。 ②“同人”在日文中的原意是“有相同志向、爱好的人”,后演变为泛指二次元爱好者以正式发行的流行文化产品作为源文本,随性挪用其世界观、角色设定、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由此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其形态有同人文、同人画、同人视频、同人音乐、同人游戏、同人周边,等等。参见林品《“有爱”的经济学——御宅族的趣缘社交与社群生产力》,《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11期,第7-12页。 ③根据艾瑞咨询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二次元用户的年龄分布为:00后占15.8%,95后占57.6%,90后(1990-1995年出生的人群)占20.9%,85后(1985-1990年出生的人群)占4.6%,80后(1980-1985年出生的人群)占0.9%,其他占0.2%。中国二次元用户的职业分布则为:“学生党”占80.8%,上班族占14.3%,自由职业者占3.1%,个体经营者占0.6%,其他占1.2%。参见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二次元用户报告》,第13页。 ④据统计,中国二次元用户的“入坑作品”(使其从此成为ACG爱好者的作品)中,日本动画占76%,日本漫画占14.8%,日本游戏占2.8%,国产漫画占1.9%,国产动画占1.2%,国产游戏占1.2%。就“经常看的作品”这个多选问题,82.2%的中国二次元用户选择了日本动画,66.1%选择日本漫画,27.1%选择日本游戏,19.7%选择国产漫画,13.7%选择国产动画,16.5%选择国产游戏。表示“非常喜欢”日本动漫的中国二次元用户占比达77.3%,而表示“非常喜欢”国产动漫的则只有6.5%。参见艾瑞咨询:《2015年中国二次元用户报告》,第24、39页。 ⑤对于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来说,“燃”强调的是一种热血沸腾的情感状态,多与战斗竞技的场面、激情澎湃的音乐、角色努力奋斗的情节、富有崇高感和正义感的行动逻辑相联系。参见林品、高寒凝:《“网络部落词典”专栏:二次元·宅文化》,《天涯》2016年第1期,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