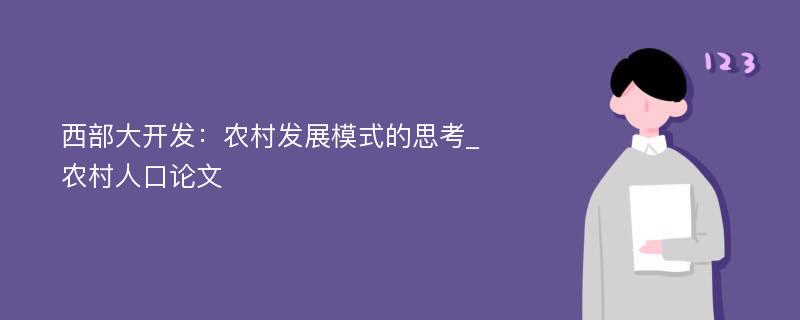
西部大开发:农村发展模式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部之所以成为全国欠发达地区,且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加大,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西部存在一个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恶化,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实施以缩小东西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将西部农村的开发列为重点。反过来讲,西部大开发成功的基础在于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地区。笔者认为,从西部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的现状出发,解决西部大开发中农村发展滞后的关键是处理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这两大问题,故人力资源开发主导型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应是未来西部农村开发的目标。
一、可持续发展模式:西部农村的必然选择
(一)西部农村发展模式选择
当前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中,农村发展应当选择怎样的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加快西部农村的发展,最终缩小乃至弥合两个地区间的差距呢?发展问题上,有两种可供西部农村选择的模式:一种是“突进发展”或突进的经济增长方式,其主要特点是以经济增长为社会奋斗的唯一目标,以牺牲环境质量,延期环境消费(即资源的过量消耗),轻视环境保护为代价来达到强制的,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突进发展或增长往往以很高代价(经济要素资源投入)换取“立竿见影”的(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顾这种增长对自然、人和社会是否带来实际的好处,故生态环境的破坏,区域资源的浪费和枯竭是其必然的结果;经济大起之后势必大落,形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更有甚者,突进发展对系统平衡破坏的代价不仅由当代人偿付,而且延及子孙后代。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屡受“突进发展”之害,50年代末期的工业“大跃进”,以及稍后实行的“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便是突进发展的典型例子。简言之,突进发展或增长就是“竭泽而渔”,“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另一种供西部农村选择的模式是可持续发展。以现代系统科学原理为指导的可持续发展是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大生态系统(以下简称大系统)及各子系统平衡、协调的良性循环中寻求区域全面发展的模式。可持续发展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续性与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密切相联”(注:宋健:《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光明日报·绿色周刊》,1996年第19期。)的关系,为此,它主张在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经济持续、快速(但无大起大落)、健康的增长,达到人人受益,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归根到底,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既符合局部利益又符合全球人口利益的发展。”(注:杨开忠:《一般可持续发展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4年第1期。)
(二)西部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中包含了需求、限制和平等三项原理:首先,发展的目标就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其次,人口、资源和环境对满足人类现实和未来的需求构成限制;最后(自然)资源须在同代人和代际之间平等分配。如果说需求和平等原理是从消费和分配两方面对发展本身提出普遍性要求的话,那么限制原理则因时空条件的差异呈现出特殊的针对性。换言之,不同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对区域发展会形成互有差异的限制。因此,在需求和平等原理对所有地区均具普适性的前提下,探索西部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充分考虑该地区内各种限制性因素。以笔者之见,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有:
1.资源和环境限制
西部地区除个别小区域外生态环境恶劣而脆弱。从西北5省区看,虽有广阔的草原(约1亿公顷),尚待开发的土地潜力较大,气候资源中光、热条件充足。但由于该地区处于内陆腹地,气候干燥,降水量少(其产水模数仅及全国平均量的1/4),故水资源极为匮乏,加之水、土资源空间匹配差,造成西北地区植被(特别是森林)稀少(据调查,西北森林覆盖率仅1%,为全国平均覆盖的1/13),且再生能力差;该地区不适于人居的沙漠、荒漠、戈壁地带面积大,已经被沙漠吞蚀的土地约16万平方公里,潜在的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多年来,由于对山坡、草场、林地的过垦、过牧、滥砍滥伐等人为破坏,西北地区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干旱及季节性的洪涝、冰雹、霜冻、风沙、干热风、沙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其中,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尤为严重: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流失为5000-10000吨,少数流失严重区域高达20000-30000吨,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吨之多。仅陕西一省水土流失面积就达13.75万平方公里,每年输入黄河泥沙达8亿吨。西南4省区1市,虽然地形气候条件不同于西北地区,但生态环境问题同样严重:西南地区地形、气候复杂多样,水资源虽然丰厚(产水模数相当于全国平均量的1.9倍),但其地理分布极不均匀,大部分地区水、土、光、热在空间上不匹配。部分省区(如青藏高原的西藏、川西高原地区、云南迪庆州)地貌切割强烈,土地开发难度大。约占西南地区面积一半的青藏高原(145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高度3000-5000米,酷寒、缺氧、大风致使植被稀少乃至无法存在,其区域生态环境恶劣而脆弱。云南、贵州两省所处的云贵高原虽然生态环境较好,但多山多石少土,土质瘠薄,坡度大,可供开发利用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近年来,由于对森林、林地、草坡滥施垦伐,其生态环境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热带雨林大面积减少,部分地段沙化、荒漠化,贵州省部分地区出现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均与云贵高原的生态失衡有关;四川省和重庆市所处四川盆地为西部重要的农业区,水、土、光、热等条件较佳,多年积蓄起来的人口膨胀压力使人们对土地、森林、林地、草坡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原有植被资源荡然无存。加上川西高原林区因过度砍伐,森林面积大面积减少(已由50年代30%的森林覆盖率降为目前的13.6%),致使整个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气候恶变,雨量偏集,干旱、洪涝及大面积水土流失时有发生;四川盆地除少数地段(如成都平原)外,近年已屡屡出现水资源缺短的“水荒”。此外,西部也是我国工业性污染日趋严重的地区之一。西部工矿业结构大都以高能耗、高物耗,排污重为主,故大量的三废排放所造成的水、大气污染,不仅使工矿区居民生存环境恶化,更对其周边农村居民和农业生产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西南工业重镇重庆市大规模的工矿三废排放形成酸雨和水污染;重庆市郊县农村和农业生产深受其害的事件则不断见于新闻报道。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农村正在兴起的乡镇工业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西部乡镇工业的发展基本沿袭了东部乡镇工业的发展模式,故布局分散、劳动力密集,大量挤占农用耕地,规模小,排污量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不可忽视。
由于农业自身的特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其所产生的限制往往带有根本的性质。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含农林牧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仍然是对大自然(自然资源、气候资源、生态环境)依赖性最强的一类弱质产业。此外,整个西部地形复杂,地势高峻、交通运输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等地理条件更强化了资源—环境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限制。
2.人力资本限制
西部9省区1市,总人口为2.73亿人(1994年),其中,农村人口约占80%,农村劳动力总数达1.4亿之多。从数量上讲,西部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庞大且有富余。有学者估计,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5828.3万,劳动力剩余率(剩余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率)为51.1%(全国农村平均为35.9%,东部农村为36.2%)(注:参见陈栋生等著:《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表5-4。)。但是,比较而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质量或素质却十分低下。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西部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4.31年,东部为6.71年。另据近期的统计,西部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1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比例为36%,东部为48.7%;成人文盲率西部为28.7%,东部为19.4%。这些数据仅仅反映西部城乡人口总体的平均文化素质。而事实上,西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比平均水平更低。以四川省为例,1990年,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为8.35年,而农村仅5.36年,相差约3年之多。同期,四川农村劳动力的文盲率高达20%。除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低之外,西部农村人口中残疾人口比例(1990年)为5.17%,也比东部(4.62%)高。正因为如此,按人口的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综合计算的我国三大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西部仅为0.541,远低于东部的0.757和中部0.602,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人口教育指数西部与东部差距十分明显(详见表1)。
表1
1995年中国东、中、西部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人类发展指数
人口预期寿命指数 教育指数 国内生产总值数
(HDI)
西部(9省、市、区)
0.750.640.284 0.541
中部(8省、区) 0.730.740.337 0.602
东部(13省、市、区)
0.78 0.790.709 0.757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199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09页表2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人类发展指数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笔者认为,西部农村人口多,劳动力素质低对区域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限制主要表现在:(1)人口数量大且不断膨胀对西部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在农村人均和劳动力平均耕地日趋减少而农业生产技术无显著改进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以掠夺的方式对有限的森林、林地、草场、草坡、滩涂滥施开发,以取得生活资料(如粮食、燃料等),从而导致当地生态失衡、资源耗尽,可再生资源绝种绝迹。其后果则是区域内气候恶变,灾害频繁,农牧业边际生产率下降,农业和农村发展无持续性,农村居民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形成了“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反过来,农村发展的滞后和贫困又加速了人口数量的膨胀(即“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形成人口(数量大的)压力→滥用自然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滞后与贫困→人口膨胀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恶性循环圈。事实上,人们看到,这种恶性运动方式广泛存在于西部很多农牧区内。其中,西北的贫困地区(如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陇西组成的三西地区)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云、贵两省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上述情况尤为典型。(2)从农村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源与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的配置角度上看,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西部农牧区内,很难做到农牧业和农村经济运行中人力资源与其他物化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高投入低产出,农牧业经济效益差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广泛存在于西部农村;(3)西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文化科学知识的欠缺的特点,使农牧民难于通过教育宣传树立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更谈不上具备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故个人和群体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浪费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乃是其必然的结果。
3.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限制
迄今为止,西部农村仍维持单一型的传统产业结构,即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农业又以单一的种植业或(牧区)单一的畜牧业为主体。事实上,这种传统的产业结构,既不利于西部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来实施农林牧渔业多种经营,农工贸一体化的综合发展,也不利于充分开发西部农村存量丰富的人力资源,实现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与东部相比,西部农业内部经营方式落后。目前西部农村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如四川成都平原、陕西关中、汉中平原等)之外,农牧业仍然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其主要特征是:(1)大部分地区依然维持一家一户的半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营方式,即处于三低状态(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低,市场化水平低,农牧产品的商品率低);(2)农牧业经营中对要素资源,特别是耕地和草场等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很差。据统计,西部农用耕地总面积中有3/4为中低产田,边远山区粮食平均亩产不足400斤。在西部牧区人工改良的草场和围栏草场仅分别占草场总面积的1.8%和1.2%。青藏高原面积广大的牧场因多年虫害、鼠害、沙化、过牧而严重退化,如(西藏草原目前平均每16.8亩草场方能放养1只标准绵羊);(3)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低。据1990代中期的统计,西部(广义)农业劳动力(不包含乡镇企业劳动力)人均产值2875.7元/人,而东部为6434.7元/人,即西部农村劳动生产率不及东部的一半;(4)除土地、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投入很低。1994年,西部每一农业劳动力拥有的农机总动力为0.56千瓦/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西部农村每亩地施用化肥量为17.76公斤/亩,仅及全国平均施用量的3/4;(5)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科技贡献率已达60%以上,而西部则不到50%。有的省(如甘肃省)则只有40%。上述特征表明,西部农业和农村经济仍停留在“靠天吃饭,凭经验干活”的阶段。
我们认为,在上述诸因素的限制下,农牧业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资源的枯竭,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无持续性,乃是当前西部面临的严重问题和挑战,因此,要通过西部开发使农村真正发展起来,可持续发展模式应是西部农村的唯一选择。
二、西部农村可持续发展中的两项重要对策
1.以产业生态化政策指导西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所谓产业政策一般是指政府从宏观上确定产业(和产业内部的行业)发展重点以及相应发展层次来进行第一、二、三次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的西部农村产业政策,则是通过宏观结构调整、重组,达到区域总资源(含人力、自然、技术、信息、文化等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促成大系统和各子系统相互协调良性运行的政策,即产业生态化政策。当前,西部农村地区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至少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内容:(1)选择本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即找准最具区域资源优势,同时又能获取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最佳综合效益的产业或产业中的某些行业作为开发重点;(2)以开发重点为基准排定产业发展的层次及其相应的资源利用层次和资源开发的规模阀、匹配阀;(3)以上述两项内容为中心确定产业调整转移导向;(4)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投资力度、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对西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所作的倾斜措施。应当强调指出,西部农村以实施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结构调整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这就是说,西部各地农村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如资源优势,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特别是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等)选择产业调整的重点并作出相应的层次安排和转移导向。
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宏观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这一大生态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的良性化运行中实现各种要素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以求得生态、经济、社会最佳综合效益的过程。事实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设想的有效性、合理性已在某种程度上被小区域的试验所证明。陕西榆林、延安两地农村多年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为主体的治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生态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农村面貌为之一新,最近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与表彰。这正是因地制宜地实施产业生态化政策的成功范例。
2.以人力资源开发主导西部农村可持续发展
鉴于人在促进大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具有能动作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西部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高低。5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含普通教育,专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以物化形式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即劳动者的素质;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胜于物化资本(K)和劳动力数量(L)的增加。而教育和培训则是人力资本(H)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有知识技能和环境保护意识的高素质人口和劳动力,增大区域人力资本的存量是实现我国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关键环节。发展西部农村教育必须首先转变以往的教育观念,将教育作为一种“超级产业”来进行规划、发展。所谓“超级产业”,就是置于农村其他产业之上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特殊产业。教育之所以应当列为“超级产业”,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源只有经过教育这种特殊产业才能转化为发展中所需的人力资本,故教育的投入往往决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近期的经济理论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加大,经济系统的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科技素质已成为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的内生变量,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经济越是高级化,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的分量和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人们应当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将教育经费列为消费性乃至社会福利性投入的旧观念;另一方面,教育又不是一般性的产业,而是培养造就能够对大生态系统及各子系统良性化运行起决定作用的人,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中的农村发展只能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主导型的可持续发展。
但遗憾的是,西部,特别是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在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部分的教育方面都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不足且有停滞下降之势。据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资料计算,西部1996、1997年两年预算内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83.2元/人和90.7元/人,同期东部分别为126.8元/人和143.0元/人,前者仅分别为后者的65.6%和63.4%;同时统计资料还显示,西部地区1997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20.71%降到20.08%,降低了0.63个百分点,其降幅大于全国和东部地区;(2)西部教育资源相对于东部不仅短缺而且利用结构也不合理。以1997年大专院校、中专和普中、职中三类学校的生师比为例。全国平均分别为1∶7.8,1∶16.8和1∶15.9,而西部地区则分别为1∶7.4,1∶14.5和1∶14.0;(3)西部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投入与东部和中部相比也相对滞后。(4)西部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稍高的劳动力在强烈的比较经济利益驱动下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孔雀东南飞”使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以教育、培训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应予高度重视。为此,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中央和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了西部农村发展的长远利益甚至可以考虑缓建一部分经济建设项目,将资金转用于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西部教育的预算内投资,应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较快增加到与东部地区同样的水平(人均教育经费),西部各级政府应当考虑将财政补贴和扶贫资金的一部分转为当地农村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之用,即变单纯的经济支援和扶贫为教育支援与教育扶贫。同时,我们建议中央对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实施特殊的教育投入政策,如对这些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实行专项资金划拨,专款专用,即重新审查和修改自8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95%用于高等教育,不足1%的预算用于小学和普通中学的规定(注:详见《人民日报》1997年9月3日第1-2版。另据陈栋生等学者的研究,这一举措给经济社会滞后收入单一的西部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教育造成不利影响:中央和省两级财政对基础教育投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导致一些财政困难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有的甚至出现大规模拖欠教育工资,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现象。……据统计,在“老、少、边、穷”地区每年大约200万初中和小学生失学。(参见陈栋生等著:《西部经济崛起之路》,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一位县教育局长提出“设立教育银行,把教育经费与地方财政分开,最起码从省上单列下来”的意见(注:见《中国教育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不失为切实有效加大西部教育投入,促进这些地区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好建议。
第二,改革西部农村地区现有的教育模式,建立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模式。针对西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普遍低下,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和受过教育、培训的技术能手奇缺的状况,西部农村教育结构必须作相应的调整:根据为本地区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的实际需要,选择教育发展的重点并作出相应的层次安排;在办学方法、形式、学制及农村专业技术人员、操作能手的培养方面走与我国东、中部省区不同的、切合当地特点的新路。应当指出,西部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村当前迫切需要的是能扎根本地,受过初、中等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及其后备队伍,而不是以脱离农村,远走高飞为目的大学生(据调查,农村地区考上大学的毕业生返乡率极低)。因此,西部农村应坚决摈弃以追求大学升学率为目标的“应试教育”模式。由于西部农村教育投入十分有限,审慎确定教育投资的重点,优化其投资结构,改变人力资本不合理的“过度耗费”的现象,尽量提高教育投入的利用效益也相当重要。对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而言,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不一定要求越高越好,但是,具有6年初等文化教育或初中文化水平并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则是最起码的要求。为此,首先,对西部农村第一、二、三次产业中16-45岁这一最有生产潜力的劳动力人口群体进行扫盲和职业技术培训,使之达到初级文化和专业技术水平。其次,当前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放在6-15岁组人口的9年义务教育普及上,因为这一人口群体作为劳动力后备资源,对西部农业和农村未来几十年的可持续发展有决定影响。最后,要根据农村地区自身特点,特别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环境、气候、交通、当地师资、教学设备等项条件采用特殊办法,改善办学环境,以提高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总之,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一要加大投入力度,二要结构合理,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
第三,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对农村人口实施素质—技能教育和培育。其内容包括:(1)在农村适龄人口(6-15岁)当中全面普及6-9年基础教育,使这支劳动力后备队伍达到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具备接受一般科技知识的能力,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今后通过继续教育,(即职业技术培训)成为农村劳动能手,或少部分人继续深造成专业技术人员打下基础。(2)改善现有农村基础教育(如扫除文盲和提高文化水平)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西部某些贫困地区的经验表明,举办短期扫盲与农牧业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分层次培训班,对农牧民有较强的吸引力,易于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宁夏西海固地区西吉县耀洲村举办的扫盲加农技培训班就是一例;(3)在素质—技能教育和培养中增设生态课程,培养受教育者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应是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环境教育或培训使西部农村的所有人,特别是新一代劳动力懂得,本地区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只有保护自己和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才能利国、利民、利于子孙后代。
标签:农村人口论文; 西部大开发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生态产业论文; 三农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