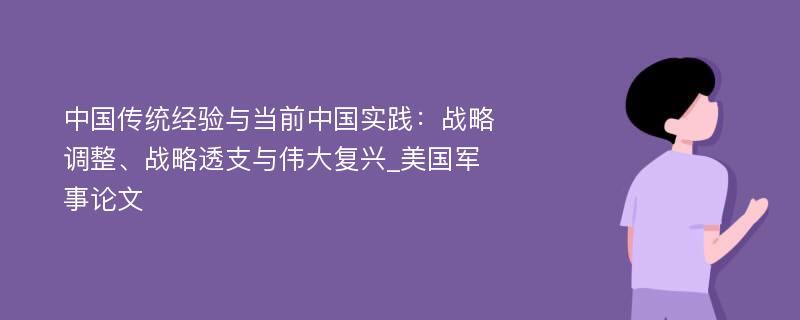
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中国论文,伟大复兴论文,当今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喻”为“晓喻”的意义上,以古喻今应当永远是一种殊为有益和非常重要的认识方式、论辩方式和话语方式。尽管历史事态在其绝对个性即独特性的意义上从来是创造,因而古今相异,但它们在其相对共性和深层机理的意义上又从来是某种类同,因而古今相通。 就战略原理来说大概尤其如此:无论古今中外,“战略广而言之,实际上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不过这里的‘事’指的是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或目的(特别是政治任务或目的),连同旨在实现它们的内在连贯和系统的实践。”① 在传统中国殊为悠久和非常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思想史册中,以古喻今一向被频繁和显赫地使用,甚至在思想理念来源的意义上更是其根本之一。它不仅可见于下面援引的某些“传统中国经验”例解中间,而且有时构成一个核心成分,用以形成一个伟大的传统中国王朝的时代性国策大方向。后者的最好最重要的例子,大概就是在经“君主教育者”陆贾振聋发聩的教育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民、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君主刘邦所发出的一项重大指令,那实际上开始确定了初汉“休息无为”的国家方向。② 在上述意义上,“太阳底下无新事”,古今何等相似乃尔!在此,我们试图深切地借鉴传统中国经验,来考察和谈论当今中国四大互相密切联系的实践问题:(1)从对外战略方面的“战略军事”为主转变为“战略经济”为主;(2)“战略经济”或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的内在平衡;(3)“战略透支”问题,或曰国家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大致平衡的绝对必需;(4)作为传统的和当代的一大主题的“伟大复兴”,连同其传统的和当代的根本路径。 一、“屈伸异变”:传统经验和当今实践 东汉伟大史家班固曾以他的一则非常深刻的长篇政治评论去结束《汉书·匈奴传》,以基于比他古老得多的中国政治经验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历史教益,论说对付“蛮夷”的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它大概是班固曾做过的最精彩的政治/战略论说,而在其丰富和深切的基本思想当中,有一项是强调这个大方针应当是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内含合适的种种“硬”、“软”成分。用他的话说,“久矣,夷狄之为患也!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整个汉初约七十年漫长的历史经验必然是复杂能动和情势性的,“旷世历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屈)伸异变,强弱相反。”③ 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的合成实践。无论是习近平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的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他于2014年5月在上海“亚信峰会”上作出的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主导的显要言谈,或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有中国政府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甚至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项目。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加速突进的中国战略军力建设、中国对美国的强劲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显著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与日本以及美国加剧冲突的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从去年秋天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也契合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但顽固下行的严峻形势下输出过剩产能的紧迫需要。考虑到去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如果注意上述所有重要事态显著的逻辑关联和内在整合,甚至可以说一套中国对外大战略——过多对外政策的自相矛盾和波动而使中国在前些年间所缺乏的东西——正在浮现。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关乎全局的重大优化。 然而,在做了关于当今“战略经济”为主的所有上述谈论之后,应当牢记“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习近平主席的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性军力经久急剧的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此外,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的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迄今在南沙群岛多个岛礁所进行的大规模扩建活动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也在迅速取得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鉴于从“战略军事”为主到“战略经济”为主的转变,中国在战略性外交方面颇大的一部分任务,是要在广泛强劲而又细致审慎地推进“战略经济”的同时,进一步从强度和频度两方面适当地缓解周边政策中的某些强硬甚而超强硬的方面,争取有分寸地减抑中国某些邻国的疑惧甚或惊惧,从而大大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争取不让美国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某种战略“统一战线”。更广泛和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周边关系中的全局性问题,即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之间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争取到适当的时候“理顺”中国对周边的总体战略和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战略实践。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对此,需要再次强调,“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国对外态势仍有其相关的显著复杂性。在“战略军事”的若干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是中国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上必须严肃应对的问题。 二、战略内在平衡:传统经验和当今必需 美国主导达成十二国TPP基本协议是一项重大事态,可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长期的经济及战略格局有重大影响,对世界未来的新贸易构造及新贸易规则体系的逐步形成有重大作用,并可产生相应的地缘政治效应。同样主要从中长期预计,一旦TPP基本协议获得各主要成员国即发达成员国国会的批准,就会开始对中国形成非同小可的压力。中国需要化压力为动力,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有效的运作,真正加速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由此在获得其他重大裨益之外,较快地缩小乃至渐次基本消除下述两者间的巨大差距:(1)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模式和惯例;(2)TPP在几乎全系列的多领域多方面的很高的贸易标准。否则,中国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过久地置身于新贸易构造和新贸易规则体系的创设、构建和制订之外,从而处于相对孤立、被迫跟随和被迫从命的处境,跟不上世界贸易高端、技术高端和操作管理高端的发展潮头。这对中国中长期的国运和国势而言殊为不利。 从中长期来说,压力还在于我们这里谈论的“战略经济”。TPP基本协议的达成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战略经济”基本方向的显现大致同时发生,如上所述,后者是指去年秋季以来的一系列事态,主要是“一带一路”创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经贸突进,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这是一种中长期后果可能很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主要是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输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输出过剩生产能力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的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北美及日本得到。TPP基本协议的达成,加上导致美国对华当前主要经济不满的那部分中国政策原因,告诫我们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而其中最大最深远的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促进中国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战略经济”(或更准确地说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 广而言之,在此谈论的内在平衡需要属于对外战略诸方向的彼此平衡问题。就此,可以略举一二中国传统经验。曾经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④且“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⑤然而同时,他还有另一个对外战略方向,与“卻匈奴”方向一起构成了某种战略平衡,那就是目标不同、情势不同因而战略方式也不尽相同的南越方向:“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⑥还有一个较小的例子:东汉初年,光武帝一方面着力安抚和规制经他努力适才成为帝国附庸、且提供重要战略服务的南匈奴,但另一方面又不顾后者对不欲归附的北匈奴的仇视,不顾这附庸为此对帝国北方政策的干扰和捣乱,决定“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连同“服顺者褒赏,畔(叛)逆者诛罚”的警告。⑦如此,帝国北方战略达到了一种重要的内在平衡。 三、“战略透支”问题:传统教训和经验 在可以有的战略或大战略错误中间,有一种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错误可以称为“战略透支”。战略因其估算本性(特别是对目的、手段、效益、代价这四者间复杂和辩证的全局性关系的估算),可以说——借用一位美国当代战略学家的话——“在其最佳形态上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学”。⑧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即财政金融学的意义上,透支是指银行存户超过存款余额支用款项,或财政部门在财政存款支用完毕以后继续签发支票。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入不敷出,乃至在最糟情况下资源耗竭,能力耗竭。“战略透支”的含义,在于战略或大战略有一根本隐患或明祸:战略目的和追求目标的努力漠视或轻视若干原则或机理,以致在愈益增大、最终可能是灾祸性的程度上损害乃至杜绝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大致平衡,从而减损乃至抵消最终成功的可能性。 在此,可以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的某些部分的有关记载和评论为经典范例,谈论传统中国的历史上“战略透支”的教训和防止“战略透支”的国策。 汉武帝极严重的“战略透支”是中国史上特别显赫的战略教训之一。尽管击破匈奴帝国殊为必要,但无论如何,和平、“消极”和节约的初汉方针被他彻底抛弃。在武帝的再三重启、经久不息的大规模征战和四面扩张中,初汉积累起来的巨量财政资源迅速耗竭,社会则开始重演初汉以前的凋敝过程。巨额的耗费导致国库耗尽,帝国中央财政破产,于是乎才有孤注一掷的财政“改革”。这位皇帝为了自己反复不已的攻伐征战,加上其晚年几乎无以复加的宫廷奢侈,在几十年里多番以多种措施,剥夺民间商人,使他们在古代传统意识形态下背负“商为末”甚而“无商不奸”的恶名。⑨从此往后直至武帝去世的漫长后续主要是:采取将匈奴人推挤至越来越远处的多个战略措施;为摧毁他们而反复进行要么失败要么虽胜犹败的远程征伐。这两者代价巨大,大到令帝国破产的地步,但却不是必需的或紧迫的。⑩不仅如此,武帝还大致同时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武力扩张和征服,成效各异,但成本一概巨大。(11) 载于《汉书》的“徐乐上武帝书”是一番伟大的论说。它基于反复强调的暴秦的教训,告诫正处在武力征服和扩张高峰时期的武帝。它属于中国历史性政治经验中的一类最佳产物,提醒“战略透支”的无谓和危险。(12)更精彩的是,班固在结束《汉书·匈奴传》的长篇评论中强调,对付北部和西北部边疆以外的“蛮夷”的合适的战略方针应当是一种混合的和情势性的,从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基本的差异——族裔/文化/地理差异——的牢固而坚定的理解出发,加上由此而来的一种清醒的意识,即像被应用于“我们”的那样,去对他们施以同化或直接治理是不可能或不大可能的,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由此,必须有一种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大方针,内含合适的种种“硬”、“软”成分,去将他们当作不同的人民对待和对付,在坚决和有效地捍卫边疆安全的同时,不梦想对它们的治理一般高效可行,近乎对两汉华夏人自己的治理那样。(13) 范晔《后汉书》有一项就“战略透支”问题而言特别有价值的战略记载。(14)伟大的光武帝——历时195年的东汉帝国的创建者——经过20余年的革命战争和统一战争后,面对社会亟待恢复、人民亟待休养的根本局势,深知“天下思乐息肩”,决意经久和平,压倒性地优先追求国内的安宁和繁荣。在两位重要将领提出一项统一后好战提议(必将导致“战略透支”的提议)之后,他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立意和平、节俭、社会恢复和民众繁荣的历史性宣告,作为其帝国的坚定的大方向。其中,他阐发了反对扩张主义和反对好战的深刻哲理,或曰防止对外政策“战略透支”的哲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他接着说,“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这里的远近是就空间/距离而非时间而言,亦即广义的地缘政治“成本效益估算”)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社会状态之间的本质关联)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他最后直指时下百废待兴的全国态势,那是决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前提:“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15)……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这一宣告有其大效应:“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很长一个历史时段内东汉“战略透支”的大风险得以杜绝。 四、防止“战略透支”:当代保障与和平发展 人口多达13亿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颇大部分渊源。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包括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关于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在成本效益方面极为合算(不“烦汗马之劳”)。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有利于中国的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关于对外政策的审慎的战略文化。 诚然,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强国影响力相对衰减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天然吸引力,并非全无可能结合起来,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然而,也许我们和世界都可以期望,基于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经久的国内任务的艰巨性,特别是多达13亿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限度内。 当前,有一个可谓基本的战略问题与能否坚持有益的“战略保守主义”传统、能否坚持应当经久的和平发展国家方向紧密相关,那就是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之间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定的战略轻重缓急意识,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战略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16)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给打上恰当的折扣。 然而可以说,中国在最近三年这么短的时间里,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打个比方,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 我们面临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国内的保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内任务真正紧迫,而中国在国外的战略发力、权势扩展和光荣获取总的来说却远非如此。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具有决定意义。更广泛地说,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 五、伟大复兴:传统的一大主题 复兴是传统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政治/社会甚或民族主题。所以常有,恰恰是因为衰落甚或衰毁——王朝、国家、社会甚或民族的衰落或衰毁——构成了传统中国几乎周期性的最大事态类型之一,犹如“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在哲理上显示的那样,另外也是因为传统中国贯穿千年而恒久不息的伟大“复原力”(resilience)。无疑,最大尺度上的衰落和复兴,是华夏或中华民族的衰落和复兴。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历史上(甚而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复兴乃是2000余年前的初汉,因为此前中华国度经历了约600年大乱,即从西周崩溃到楚汉战争为止连续不断的普遍分裂、频繁征战、暴烈血拼、外族侵掠、帝国暴政和激烈内战,以致社会凋敝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7) 从高祖吕后,经文景两帝,到击破匈奴帝国为止的武帝,初汉诸君主是传统中国所曾有的头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者。这个复兴之起始的根本认识和根本理念,是如前述高祖从善如流所接受的儒生陆贾的告诫“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到文帝时期的贾谊笔下,被凝练为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政论文《过秦论》中仅五个字的最关键论断“攻守之势异也”(“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据此,西汉根本的战略方向被定为、且坚定地保持为“离战国之苦”,“休息乎无为”,以便“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8)与此相应,对内坚持惠农惠民,加上在文帝那里达到极致的宫廷节俭,对外坚持忍辱负重,仅以坚决不容匈奴帝国向南长驱侵掠为限。这坚韧的努力到头来造就了惊人的伟大结果,即“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19)以此为资源基础,武帝得以发动数次巨大规模的远征,决战决胜,击破构成致命威胁的匈奴帝国。 另一场伟大复兴,是由光武帝刘秀及其儿子明帝和孙子章帝造就的,这在刘氏王朝恢复的意义上史称“中兴”。在王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20)以致社会严重凋敝、帝国边乱烽烟四起之后,先有“自然状态”似的暴烈的革命战争,继之以经久和艰辛卓绝的统一战争,其间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以致食人惨剧比比皆是。光武帝在统一后的根本意向非常明确和集中,用《后汉书》的概语来说,即是“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未尝复言军旅”。(21)如前所述,特别是针对两位重要将领在统一后的好战提议,他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立意和平、节俭、社会恢复和民众繁荣的历史性宣告,以此作为东汉帝国的坚定的大方向。他“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22)严格规制和教育东汉首代贵戚,使他们大都深知“天道恶满而好谦”,(23)并且以“方平诸夏,未遑外事”、“羁縻之义,礼无不答”(24)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总方针。在他和明帝、章帝治下,逐渐复兴的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内部条件,使得明帝能够征匈奴、通西域、击叛羌,章帝能够“叵平诸国”(25)、恢复西域。然而无论如何,“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依然是他们的坚定原则。(26) 六、伟大复兴:当代的一大主题 仅就复兴的一大关键——“文治”与“武功”的恰当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中华复兴”努力与传统中国史上的辉煌范例何等相似乃尔!邓小平在他执掌最高领导权的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的伟大国务家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础优先。 “军队要忍耐”原本就意在一时,如邓小平所说,“(将来)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27)两大急剧的事态变化大概多少使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提前强劲发力,那就是:(1)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极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给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军界造成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继而,“台独”威胁随李登辉1995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并急速加重,从而带来了进一步的强烈刺激。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发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代化,一言以蔽之,其目标就是使中国与其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到如今,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掌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三年来,中国战略性军力的大增强和战略性活动的大扩展已经是世界上最显著、最重大、最深远的战略性事态之一,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趋势的头等表现和头等动能之一。 然而,除非在最不平常的最紧急情况下,“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依然必须是中国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不仅如此,中国未来在军事上无论可能变得多么强大,都须谨记中国传统战略哲理中头等重要的一条:“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即如中国史上“战略保守主义”的一篇杰作、武帝时代初期的《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援引老子“师之所处,荆棘生之”一言,强调“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28)不仅如此,像刘安告诫的那样,也是克劳塞维茨式“战争迷雾”的最大类型之一,在于不要事先持有过分的必胜速胜信心:“《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因而“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29)或者用《孙子兵法》中意义更宽宏、风格更凝重的第一句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0) 就此,可以援引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国庆节时的宣告: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爱好和平,历来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31)这样的宣告既出自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也出自当代中国基本经验。 ①时殷弘编:《战略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编者序”,第1页。 ②《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③《汉书·匈奴传下》。 ④《史记·匈奴列传》。 ⑤《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抄录贾谊《过秦论》。 ⑥《史记·南越列传》。 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⑧Sherle R.Schwenninger,“Revamp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World Policy Journal,Vol.20,No.3,Fall 2003. ⑨这些尤见于《史记·平准书》的集中记载。 ⑩《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大宛列传》。 (11)《史记·南越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朝鲜列传》。 (12)载于《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13)《汉书·匈奴传下》。 (14)《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 (15)颛臾,鲁附庸之国。鲁卿季氏贪其土地,欲伐而兼并之。时,孔子弟子冉有仕于季氏,孔子指责之。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为子孙之忧。”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见《论语·季氏》。 (16)《后汉书·郑孔荀列传》。 (17)《史记·平准书》。 (18)《史记·吕太后本纪》。 (19)《史记·平准书》。 (20)《汉书·王莽传下》。 (21)《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2)同上。 (23)《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 (2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25)《后汉书·班梁列传》。 (26)《后汉书·西域传》。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129页。 (28)《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 (29)同上。 (30)《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31)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0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