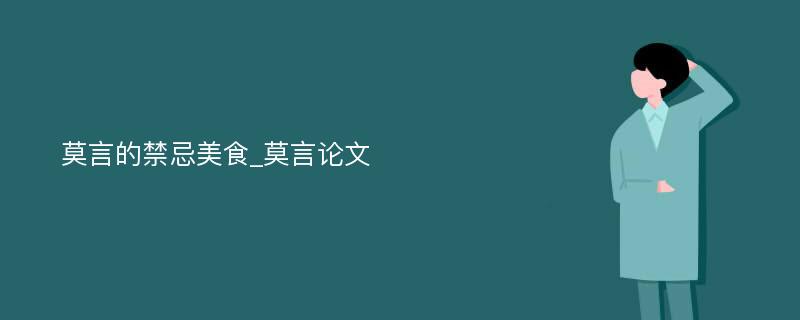
莫言的禁忌佳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佳肴论文,禁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可能,不妨设想这幅情景:农舍内农夫看着报纸,农舍之外的谷仓中,五只牛围在桌旁,其中一只注视着农舍的方向,另三只站着旁边,眼巴巴地瞅着第五只,它正稳坐桌前,脸颊肉鼓鼓的,颈系围嘴,手握刀叉,大快朵颐盘中多汁的牛排,画面的标题上写着:“嗯嗯,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吃起来有点像鸡肉。”①你定能认出这是美国玩世不恭的漫画家盖瑞·拉尔森《远方》漫画系列表现的另类幽默。
对于多数人而言,吃人肉一事,不管怎么说都是会令人反感的,甚至构成犯罪和亵神。嗜食同类(cannibalism或吃人)乃世俗禁忌,因为从任何极端意义上来讲,吃人为的是复仇、求生抑或是好奇、快感(如拉尔森漫画中所画),既有罪孽(sin),亦是谋杀(crime of murder),践踏神圣的遗体,无视文明行为的规范。主要的宗教经文,从圣经和可兰经,再到印度教、神道、或佛教典籍(除开涉及素食规定的部分外),没有一部特别提及这一问题——相比经文中其它明令禁止的行为,吃人会引发更多的惊骇与谴责。然而正如他人所展示出的,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国家实际发生过的吃人行为皆有一段悠长、复杂、记述丰富的历史,并且每一次吃人行为的发生都会伴有不同的目的、手段与步骤付诸实施。大多数社会团体对此持批判谴责之态,相反个人之见却较少挞伐之意②。本文沿着有关为何吃人③、怎样吃人的评论与观察记录略做勾勒,再将研究的中心转向小说家们的写作缘何涉及吃人问题,最后以中国作家莫言如何处理吃人主题的探讨终结本文。
怪诞的饕餮(Grotesque Gourmandise)
依照郑麟来(Key Ray Chong)的分类,吃人行为大可分为两类。两类在世界文学中都有所体现并对发生吃人现象的文明有所揭示。第一类是“求生性吃人”,大体而言,饥荒可能导致吃人行为发生较频繁,另外,天灾人祸也偶尔会迫使人们不得已而为之。1847年的当纳一家人以及亲友(the Donner Party)于迁徙至加州途中遭遇大风雪被困且粮食殆尽而食人肉,是无数吃人记载中最为轰动的一例。郑麟来断言“甚至那些依靠吃人幸存下来的人也会谴责吃人”④,所言甚为正确,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他后来所叙,1972年安第斯山飞机坠毁事故的幸存者,正是他们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允诺他们食用空难同伴尸体以求生存之机,并把这种事儿当做一种“团契(kind of communion)”来赞美⑤。在诸多写到吃人的作家中,中国作家郑义(Zheng Yi),在其书中列出不少吃人的事例,发生在中国现代史上两段时期(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这两个时期都曾引起人们对人肉的食欲,甚或培养出此一野蛮残忍的嗜好⑥。
第二类是“习得性吃人(learned cannibalism)”。习得性吃人往往获得公开或文化上的认可,导致习得性吃人行为的原因有多种,诸如“憎恨、热爱、尽孝、尽忠、品尝人肉佳肴的欲望、惩罚、战争、相信人肉具有医疗功效、盈利、精神错乱、强迫、宗教、迷信”如此等等⑦。这张清单并不完整,至少无法涵盖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刻画的吃人行为。
西方文学中吃人之例不胜枚举,且描写吃人主题的文学传统持续千年。从萨杜恩(Saturn)食子的神话(戈雅在自家餐室的墙壁上绘出这恐怖之景)到佩特洛尼乌斯的《萨蒂利孔》(Satyricon),再到塞内加戏剧,再到奥维德的《变形记》。延续几个世纪以来⑧,吃人,虽然常与野蛮的文化(savage cultures)相提并论,但作家加以利用,以激起丰富的寓言性、劝诫性、耸闻性和讽刺性⑨。乔纳森·斯威夫特1729年创作的讽刺随笔《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无疑是吃人主题中最负盛名的文章。文中建议以爱尔兰儿童代替屠夫刀俎之肉,这不仅可以拯救饱受饥饿威胁的大众,也能满足富庶之家刁蛮的胃口。斯威夫特笔下“虚构的吃人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寓言:以童肉交易为主的假想的人肉经济模式,隐喻了英国宗主体制对爱尔兰人的压迫,并指控宗教仇恨和对其他族群的轻贱如何迫使人们吞食他者。”⑩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吃人还另有一个领圣餐(Eucharist)的意涵,即“礼拜者借此与基督融为一体”(11)。
这种交融之举在新近出版的两部欧洲小说得到再现。徐四金(Patrick Suskind,大陆译为帕特里克·聚斯金德。译者注)1985年出版的小说《香水》(Perfume)里,那个恶魔,一个活着就得汲取年轻处女香的异食癖和谋杀犯,被追捕后被人杀死,最后成为镇民的口中之食:
后来,他们中最后的障碍被冲垮了,圈子不复存在……霎那间,天使被分成三十块。这一伙人每人抢到一块,他们在贪婪的欲望驱使下退了回来,把肉啃光。半小时后,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已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一根头发也没留下…他们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已经参与了一次凶杀或另一种别的卑鄙的犯罪行为,但是把一个人吃掉?他们以为他们绝不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他们感到惊奇,他们竟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奇怪自己尽管非常难堪,却没有发觉有过一点坏心眼。(12)
小说血淋淋的尾声中浮现了几个值得深思的片段。“最后的障碍”轰然塌陷,部分是源自于群兽心态(pack mentality)(13),同时也是除掉这个世界恶魔的唯一方式:那些参与狂筵的人必得共食恶魔,一人一口吃掉他的肉;但恶魔在他们的身体里消化之后,他的“种子”依旧留在他们体内,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们能够活多久,他也可以再活多久。
在克罗地亚作家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c)的小说《人的味道》(The Taste of a Man)里,爱、摄食(ingestion)、滞食(retention)得到更鲜明的体现。这是一本令人颤栗的小说,书中色情意义的吃人与宗教意义的吃人两相结合,竟使不可思议之事成为极致的善行。叙述者“她”追忆自己信仰天主教教义的少女时期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转而迷恋上她男朋友所调查的1972年安第斯山飞机坠毁事件。她知道只有情人的死亡才是“我们两人永远在一起的唯一机会”(14),之后,她杀死了情人得到了“绝对的结合”。当她剃掉已逝情人的指尖之后:
我往舌头上放了一小块儿肉,尝到了血的咸味。我的舌头噙住它好一会儿,这样我就可以尽情地感受每一丝它带来的快感,好像在等着它在舌苔上融化。我完全能够意识到这一时刻的庄严性,我在打破一个禁忌,但却毫不费力的吞咽下那块儿肉。事实上,它给我带来愉快的颤栗。是的,在那一刻,我陶醉在自己的力量感之中。我想完完全全占有Jose,现在,我做到了。(183)
由此我们可以认可巴特耶(Bataille)的看法,即吃人的人虽然觉得他们的行为令自己以及社会感到极端噁心,但他们仍旧触犯这个“宗教禁忌”。吃人变成圣餐仪式。人肉是灵魂之食。
中国文学中的吃人(Chinese to Go)
[Chinese的意思是中菜,to go指的是外卖。作者注]
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中,吃人的描写,尽管数量不算庞大,但有些例子相当著名,时常被人讨论。传统以及近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明清戏剧、民间传说和历史小说屡屡写到吃人,复仇、惩罚、孝悌、饥馑的诱因最为常见(15),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人嗜好”(16),除易牙杀子满足齐桓公这个食客“怪癖的胃口”之外,中国还有不计其数的文献记录国人尝试人肉的异常食癖,尤其是对婴孩肉与女人肉的食癖。
几乎每一个文学作品中提到的吃人例子,都活灵活现地描述可怖的吃人主题,但小说所描写的只是表面上为读者所排斥和谴责的行为,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吴承恩宗教寓言《西游记》(英译Joumey to the West),唐僧肉被传富有神力,众妖竞相追逐。书中唐僧虽并未被吃,但小说并不否认吃唐僧肉会长寿的观念。当然除此之外,小说本身的讽刺和幻想特性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反讽:“小说的宗教信仰——禁止肉食,遑论人肉——却是透过这样一个食人肉的寓言来宣扬的。”(17)《西游记》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有吃孩童可长生不老(1111个孩童的心脏做药引子会增寿)。如我们所见,孩童作为珍馐美味——其所激起的文学灵感由来已久,从古代,到斯威夫特,再到20世纪。
民国之时,鲁迅在其作品中两次大胆涉足吃人(18)(即,他头三个现代短篇小说的两篇)。若论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了解,无人能出鲁迅其右。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和迷信人血的疗救功效的愚昧在小说中纤毫毕现(19)。鲁迅名篇《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嘲讽了中国四千年来的吃人文化,五四口号“礼教吃人”——礼教成规、道德教义戕食国民——深层隐喻了全体国民‘禁锢在同类相残的恶性循环中’——欲食他人又惊恐自身被食——直到所有的人完全被消灭”(20)。小说提到一些历史上的真实例子,并未直接描述吃人的情况,但狂人却确信自己的家庭也有吃人一事:
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making us eat it unwittingly)。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21)
读者千万不要被上述引文中的“unwittingly”(未必不)一词误导,因为鲁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吃人”的见地是明确的(虽然只是在象征寓意的层面),即,礼教吃人。
鲁迅为其讽刺短篇《药》(英译:Medicine)中的人血馒头掺进迷信元素,描摹享用被砍头的牺牲者的鲜血的古老传统。“人血馒头”素有提升性欲的美名,在小说里变身成救治店主患有肺结核的儿子的药(a cure),这一比喻在《狂人日记》已经出现过。药并未起效,吃药的孩子和革命者遭遇同样的命运。读者还可以这样解读这个复杂故事的寓意:“彰显了革命的失败——中国年轻一代复兴民族的希望破败。”(22)小说中的吃人是一种自我消泯,因为康大叔的承诺——“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无法实现。很显然,如果中国人无法全然绝弃吃人的过去,将会危及中国人的未来。对于鲁迅而言,“吃人”的描述渗透了他对中华民族的失望甚至绝望。在《狂人日记》最终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之前,鲁迅只是以微弱的声音发出他残存的希望:“或许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如我们所亲眼目睹的,这个问题最终会变成:“或许还有没吃过孩子的人?”
救救/留下孩子——以后再吃
Save the Children(for Later)
[此处save是留下的意思,双关语,把孩子留下,以后再吃。作者注]
如前所示,60年代初期及“文革”期间有无数吃人的实例,有部分是因饿吃人,也有部分是习得性吃人,但吃人并未成为文学通用的隐喻,我们可以理解其原因,因为这一隐喻极具诱惑却也充满了危险。
新时期小说中充斥怪诞的暴力与对身体的戮残相当值得研究,但本文重点在于小说如何将摄食式的食人融入小说里。世界各地的作品不乏残酷不仁的描述,但据我的了解,中国只有三位作家——余华、韩少功、莫言——比其他作家的书写更加耸人听闻,他们大胆描写屠戮和馋食人肉。其中,余华与莫言的吃人的故事以大饥荒或乡村野蛮为背景。
余华早期因其作品的暴力而享有盛名,但只有一部作品涉及吃人主题。小说“《古典爱情》(英译:“Classical Love”)模仿传统小说的题材和叙述手法,是他该时期最令人惊怵的作品,其中描述了读者所熟知的像鬼魂显灵、死而复生、废墟,甚至吃人的主题。”(23)《古典爱情》中有关“吃人”的场景发生在饥荒年景的屠夫茅棚内,一个妇人及其女儿被当做肉来卖,但是正如下选文所示,买卖人肉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棚外数人此刻都围了上前去,与店主交涉起来。听他们的话语,似乎都看中了那个幼女,他们嫌妇人的肉老了一些。店主有些不耐烦,问道:“是自己吃?还是卖与他人?”有二人道是自己吃,其余都说卖与他人。
店主又说:“若卖与他人,还是肉块大一些好。”(24)
这时,故事转向描述屠宰妇人与幼女的残忍情况(25)。安道(Andrew Jones)认为这个部分是属于“拼凑”的书写方式,即,余华在此加入一幕源出唐代传说中宰杀妇人的情节;安道并指出余华略过传统思想中的孝悌——自身被杀与被吃的前提,“使故事既在道德层面上站住脚又具有真实发生的可能性”的观念(26)。既然故事里少了这个传统的被杀与被吃的原因,很显然我们必须关注余华小说中的吃人者和徐四金小说《香水》中的众人有何等相似之处,在参与禁忌之举,却没有“一点点的良知”的谴责。
在处理吃人主题方面,莫言可以说是最富有想象力而且也最常触及这一题材的小说家。除了《十三步》中吃胎盘的描写,他至少还有两个短篇涉及吃人主题。《弃婴》(英译“Abandoned Child”)讲述了一名军人返家途中偶遇被弃女婴,徘徊不决后出于怜悯将其抱回家。小说接下来批判了当下社会残留的传统思想与官僚行为。对于他抱回弃婴并将其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的提议,家人,尤其是妻子,都强烈反对。军人不得不去当地政府部门求助,为弃婴寻得一户领养人家,军人遭受了当官儿的冷漠与傲慢的白眼,而这又是莫言批判社会的靶子,一直到故事结束,军人都无法妥善处理弃婴的事。在小说结尾,作者置入了一段看似无关的插曲:
我想起在一个城市里,发生过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美丽温柔的少妇,杀食年轻男子。股肉红烧,臀肉清蒸,肝和心用白醋生蒜拌之。这个女子吃了许多条男子,吃得红颜永驻。我想起在故乡的遥远的历史里,有一个叫易牙的厨师,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据说易牙的儿子肉味鲜美,胜过肥羊羔,我更加明白了。(27)
这段插曲与传统的“红颜祸人”故事相呼应,毒蝎心肠的少妇伪装狐仙引诱杀(或吃)青年男子(28)。“美丽温柔的少妇”的故事与易牙蒸子的历史记载都强调了食人的社会现象。这些受害者往往是社会的“多余之人”,沦于被他人蒸煮烹调的命运。
稍后创作的短篇《灵药》(出自“灵药”)叙述了两个前后关联的故事:当权者耀武扬威,以意识形态为由,任意逮捕无辜,以完成上头规定的处死名额,因此,四位村民——村长和老婆、地主和其老婆——被枪杀了。同时,叙述者“我”和父亲躲在行刑地近旁的桥洞中,静静地等待四具死尸。几声枪响之后,四人的尸体坠落于干涸的河床,父亲等待的目的终于揭晓:
爹从嘴里吐出刀子,攥在手里,在马魁三胸脯上比划着,寻找下刀的地方。我看到他用刀子在马魁三胸脯上戳了一下,就好像戳在充足了气的马车轮胎上一样被反弹回来,又戳了一刀,又弹回来……
爹一咬牙,一瞪眼,一狠心,一抖腕,“噗嗤”一声,就把刀子戳进了马魁三的胸膛。刀子吃到了柄,爹把刀往外一提,一股黑血绵绵地渗出来。爹旋转着刀子,但总被肋条阻隔着……
我听到“咕嘟”一声响,先看到道口两侧的白脂油翻出来,又看到那些白里透着鸭蛋青的场子滋溜溜地窜出来,像一群蛇,像一堆鳝,散发着热哄哄的腥气……
爹捅破了马魁三的隔膜,揪出了一颗拳头大的红心,又揪出了几页肝。终于在肝页的背面,发现了那颗小鸡蛋般大小的胆囊。爹小心翼翼地用刀尖把胆囊从肝脏上剥离下来。举着,端详了一会儿,我看到那玩意儿润泽光华映日,宛若一块紫色的美玉。(29)
之后父亲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了第二具男尸,取出苦胆,而这些鲜血淋淋的“战利品”又有何用呢?
奶奶目生云翳,请神医罗大善人看。罗大善人说,这是三焦烈火上升所致,非大寒大苦的药物不能治了。然后挟着包要走,爹苦苦哀求,希望罗神医开个方子。罗神医说:用个偏方吧……你去弄些猪苦胆,挤出胆汁来让你娘喝,兴许能退出半个瞳仁来。爹问:羊胆行不行?罗神医说:羊胆、熊胆都行——要是能弄到人胆——他哈哈笑着说——你娘定能重见光明。(181)
人体内脏器官诚然是传统中国民间偏方,但莫言描写了毫无人性的野蛮的杀戮和父亲令人颈背发凉、头皮发麻的收取人胆的细节,对照神医罗大善人开药方时轻率的态度给残杀与毁尸的画面平添的诙谐色彩,前后两种不同的叙述,将杀人与吃人的行为呈现得更加鲜明生动。最终奶奶并没食用苦胆恢复光明,相反,当其得知她苦苦等来的神药是人胆之后便一命呜呼了。人胆入药是否真有疗救功效,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探讨吃人暴行及其背后的残忍的人性本质。莫言笔下被父亲摘取的苦胆亦如鲁迅笔下被吞食的人血馒头,皆取自受刑的“敌人”之躯,因而两者行为都被认为有勇之为。但在莫言的小说里,革命者所遭受的暴行与其鲜血制成的“灵药”(鲁迅的“药”)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被庸医愚弄的父亲为了尽孝心收割的人胆(30)。
目前为止,我们所读到的吃人之举和吃人概念都显得残酷不仁,间或有情色的描述,但绝大部分都是警世寓言、恐怖至极的煽情描写和绝望呼喊。看起来,斯威夫特或伏尔泰嘲讽的写作风格已不再(对他们而言,透着讽刺之光的“冷眼”是描绘吃人老饕的最好工具)。但这么说并不全面,先不表莫言高密东北乡作品对故乡的叙述充满热情与关怀,他的长篇小说《酒国》(英译“The Republic of Wine”)叙述方式复杂精妙,兼有讽刺家卓绝超然之态和寓言家寓言创作之技巧,可以说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作品里的上上之作。一如前辈作家鲁迅,莫言探究吃人禁忌,但与鲁迅《狂人日记》不同的是,《酒国》并不呼吁拯救孩子,也不是很明显的说教:我们甚至戏仿了鲁迅早期作品。
《酒国》包含多重虚构,描述中国国民性的一些缺失——暴食成性,贪杯纵酒、谈性色变,另外也涉及怪诞的人际关系。作为中国文学吃人主题创作的新近力作,它有力审视了滥性背景下的暴食暴饮。
《酒国》大致情节是讲述一位名叫丁钩儿的高级人民检察院特级侦查员的酒国之行(根据故事的发展,这场旅行亦可被当作食物的消化系统之旅)。酒国市位于酒国中心,丁钩儿此行的目的是调查酒国市被举报的市民养肉孩儿以满足当地官员口腹之欲一事。莫言塑造的丁钩儿读来更像是一个丑角而非神探。在求得罪证的过程,他被卷入各种情欲、美食、犯罪和搞笑的狼狈活动。故事情节主线之外,另加一个也名为莫言的作家与酒国市民、酿造大学博士研究生兼业余作家的李一斗的数封通信。小说也穿插九篇李一斗创作的短篇,希望作家莫言能帮其发表。最后,虚构的“莫言”“变成”丁钩儿,透过乔伊斯般的意识流手法,重复叙述特级侦查员的心路历程,并影射一连串影响中国数十年的政治事件。作家/主人公在酒国这个吃人社会的食道中游历一圈又到酒国弯弯曲曲的肠胃系统行走了一番后,最终却跌进一个户外大茅坑的粥状秽物中,同时,从上游缓缓驶来的画舫上正举行吃人盛宴,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31)。
《酒国》通篇沉浸于人欲、性欲、口腹之欲中,充满了无度的挥霍与纵情食色,最过度放纵的当数吃入场景及因吃人引发的相关事件。小说违反了传统叙述手法,在这里,“吃人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无物可食而是食物过剩。既非发生于饥荒年代更非出于食敌人之肉的冲动,单单是为了味蕾的享受与刺激。”(32)小说开篇部分即描写味觉享受的过程——侦查员在堆满美食与美酒的三层圆形大桌旁接受款待,渐渐喝得酩酊大醉:
在他们豪饮的过程中,一道道热气腾腾、色彩鲜艳的大菜车轮一般端上来,三位红色服务小姐,像三团燃烧的火苗,像三个球状闪电忽喇喇滚来滚去。他恍惚记得吃过巴掌大的红螃蟹,挂着红油、像擀面杖那般粗的大对虾,浮在绿色芹叶汤里的青盖大鳖像身披伪装的新型坦克,遍体金黄、眯缝着眼睛的黄炯鸡,周身油响、嘴巴翕动的红鲤鱼,垒成一座玲珑宝塔形状的清蒸鲜贝,还有一盘栩栩如生、像刚从菜畦里拔出来的红皮小萝卜……(33)
之后,“一位红色服务小姐搬走了餐桌上那盘仙人掌。两位红色小姐端来一只镀金的大圆盘,盘里端坐着一个金黄色的遍体流油、异香扑鼻的男孩。”(61/52)
这到底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孩?还是一个精心制作的惟妙惟肖的烹饪仿真品?很显然这一次是后者,尽管侦查员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肉孩儿。
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侦察员丢魂落魄般望着男孩,吞咽着翻卷而上的胃中液体。男孩水灵灵的眼睛回望着他,鼻孔里喷出热气,嘴唇翕动,好像要开口说话。(91/75)(34)
宴席的东道主一再声称这道菜并不是以真正的肉孩儿为原料,然而这并不表示吃人的情况就不存在了。随着小说的发展,读者得知养育、挑选、准备肥墩墩肉孩儿(当然可能也包括取食肉孩)的整个流程是如何惨无人道却又永无尽头(35)。比如,李一斗的短篇《肉孩》描述农民元宝将孩子小宝儿送往烹饪学院卖掉之前如何细心洗净男孩儿。
“他也不是纸扎的,那么容易就擦破了?!你不知道那些验级员是多么刁钻,连孩子屁眼都要扒开检查,有点灰泥就要压你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就是十几块钱。”
终于洗完了。元宝提着小宝,女人用一条干净毛巾搭着小宝身上的水。在灯光里,孩子红彤彤的,散发出香喷喷的肉味。女人拿出一套新衣服给小宝穿上,顺手把小宝从男人手里接过来。小宝又噘着嘴寻找乳房,女人把乳房给了他。(78/64-65)
李一斗稍后的短篇《神童》讲述了婴孩儿被圈围起来养肥的过程,以及天真的小孩们反抗被蚕食失败的举动。读者因而得知为何酒国的小孩儿那么珍贵:
他们为什么要吃小孩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吃腻了牛、羊、猪、狗、骡子、兔子、鸡、鸭、鸽子、驴、骆驼、马驹、刺猬、麻雀、燕子、雁、鹅、猫、老鼠、黄鼬、猞猁,所以他们要吃小孩,因为我们的肉比牛肉嫩,比羊肉鲜,比猪肉香,比狗肉肥,比骡子肉软,比兔子肉硬,比鸡肉滑,比鸭肉滋,比鸽子肉正派,比驴肉生动,比骆驼肉娇贵,比马驹肉有弹性,比刺猬肉善良,比麻雀肉端庄,比燕子肉白净,比雁肉少青苗气,比鹅肉少糟糠味,比猫肉严肃,比老鼠肉有营养,比黄鼬肉少鬼气,比猞猁肉通俗。我们的肉是人间第一美味。(121-22/100)
当然以上的描述出自与“莫言”通信的李一斗之手,但几个情节发展路线逐渐汇聚成一条时,吃人事件不但属实,侦查员其实也是共犯。丁钩儿受不起诱惑,而且又饥肠辘辘,当然就免不了会加入吃人行列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丁钩儿眼中幼儿园孩童的肖像和他在酒国遇到的官员模样:
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正在他左前方横穿马路,阳光照着他们的脸,好像朵朵葵花。他不由自主地沿着马路的边缘向那群孩子们靠拢,自行车贴着他的身体滑行,宛若一条条鳗鱼。骑车人的脸在强光照耀下变成一些模模糊糊的白影子。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白白胖胖的脸,笑眯眯的眼睛。他们仿佛被拴在一根粗大的红绳子上,好像一串鱼,好像一根枝条上缀着的肥硕果实。汽车的烟雾喷到他们身上。光焰白亮如炭,孩子们宛若一大串烤熟的小鸟,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调料,香气扑鼻。(15/13)
这二位干部都是五十岁左右,脸庞圆乎乎,好像小面包;脸色红扑扑,好像红皮蛋;略有将军肚。(24/20)
接下来是李一斗一篇名为《烹饪课》的小说,其中详尽描写了可怖的烹调肉孩的方法。下面这段引文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
肉孩在笼中,身体被禁锢着,只有一只又白又胖的小脚,从笼架下伸出来,显得格外可爱。我岳母说,第一步,是放血。有必要说明,在一段时期内,个别同志认为不放血会使肉孩的肉味更加鲜美、营养价值更高,他们的主要理论根据是高丽人烹食狗时从不动刀放血。经过反复的试验、比较,我们觉得,放血后的肉孩,比不放血的肉孩,味道要鲜美的多。这一步的目的很简单:放出肉孩体内的血,放得越干净、肉的色泽愈好。放血不彻底的肉孩,制成成品后,色泽晦暗,腥味较重。所以大家不要轻视这一步……选择切口的位置,是为了保持肉孩的完整性,一般采用从脚底切口,暴露出动脉血管,然后切断引流。她说着,手里便出现一柄银光闪闪的柳叶刀,对着肉孩的小脚……刀口已切开,一线宝石一样艳丽的红血,美丽异常地悬挂下来,与他脚下的那只玻璃缸联系在一起……大概一个半小时后,肉孩的血被控干,第二步,要尽可能完整地取出内脏;第三步,用70℃的水,屠戮掉他的毛发……(271-72/225-26)(36)
一如一位学者所道:“讽刺小说里常有的骇人的描述令读者看不下去,因此而得到其讽刺的目的。吃人的题材反复推倒我们尊严之墙、瓦解我们的冷漠、使我们所谓的高度严肃得到应有的嘲笑与戏谑。讽刺的手法要成功就必须沦入兽性野蛮的层面,正像瑟茜(Circe)把人变为猪。”(37)莫言《酒国》的讽刺写法符合这个要求,是毫无争议的;但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又如何?
作者讽刺对象也许包括了作者自己,但更贴切的诠释应该是吃人很明显是一个比喻以描述权势阶级如何迫害老百姓,描绘他们豪奢生活方式,特别是花着纳税人的钱大肆铺张浪费。盘腿端坐于镀金大圆盘中的肉孩儿来自乡村,这一点强烈提醒读者:中国历史上城市压迫乡村,剥夺农民的传统由来已久;然而,在莫言的世界,农民乐于为当官的共犯,因此小说把野蛮兽行描写得极端残忍,进而使人质疑整个社会的人性何在。
莫言《酒国》的语调有别于其它小说,比如《红高粱》那种富于热情奔放的描写,这种语调上的突破为莫言带来了国际声誉。大量的修饰性形容词、作者介入的评论、自传性元素,这些能增强读者认同中国近代悲剧或哀歌的东西在《酒国》里都不见了踪影。《酒国》的作者变为态度超然的讽刺家,透过诙谐风趣的叙述、平面的人物和模棱两可的事件,冷静地剖析当下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约翰·霍克斯小说《吃人》(The Cannibal)或布瑞姆·斯多克的小说《德库拉》(Dracula)巨细无遗展示了吃人细节(描写了吸血引发被“吃”之人的死亡以及吸血的情色层面),《酒国》迥异于上述两部小说,除却吃人行为本身之外,一切都得到精确的描写,这可能会让读者以为莫言本人无法确定是否真有吃人事件——金副部长,传说中的吃婴孩阴谋集团的主谋,就说丁钩儿想象力之丰富可以与小说家比美。但笔者并不认为如此。首先,任何有关馋食香飘四溢肉孩儿的描述都会侵扰小说寓言色彩、破坏小说完整的结构(38)。
其次,我也不同意莫言不描写吃人是因为他怕恐怖的场景会吓坏读者(若属实,那么《红高粱》就不会有罗汉大爷被剥皮的描述,《酒国》里也不会有一只倒霉的驴子遭到蹄子被割去炮制全蹄餐)。我认为原因与小说中心主题有关:吃人行为离不开牺牲者与杀食牺牲者的人。戕食同类的描写自然而然会引起对前者的怜悯,读者不可避免或是潜意识会由人及己,反而减轻了对后者的咒骂。换句话说,被吃者缺位时,我们会更公开声讨吃人之人,这也是讽刺家之笔所极力鞭笞的,吃人隐喻因而显得更有力。
最后,既然我们承认莫言创作的目的是戏仿五四时期鲁迅所抨击的中国这个吃人社会,那么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过后的75年里中国这片大地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下面所引的这段《酒国》中鲜有的感情丰富的描写便是莫言给出的答案:
你们是领导干部,杀百姓的儿子喂自己的肚子。天理难容!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番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哭啊哭,令人不忍卒听的啼哭声,从苹果里、鸭梨里、葡萄里、桃里杏里核桃里发出。水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蔬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屠宰场里是婴孩的哭声。酒国的盛宴上回响着一个个被害男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哭声。我不对你们开枪对谁开枪?
但是,这个“狗熊”主人翁所谓的愤怒只是短暂的,因为在人类普遍堕落的情况下,丁钩儿潜意识中或许认为吃人胜过被吃。最终他的枪并没射向吃人的魔王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魔王群的一员。莫言想告诉我们,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丁钩儿。
原刊编辑致谢:在校译、审稿的过程中,葛浩文教授数度电邮编辑,讨论如何理解原作中的关键概念、引文和双关语,挑出错漏,修正误译,调谐行文。原作有大量莫言、余华等人作品的引文,出自葛浩文和安道等人的英译,本篇论文的译者很自然地将其“复原”到大陆出版社中文出品状态,如,《酒国》引文出自《酒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版,《古典爱情》引文出自《鲜血梅花》,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版等。经由他的提醒,我们注意到中文原文与英语译文之间的差异并由此感知到译者的雕龙文心。例如,《酒国》中有一句:“……孩子们宛若一大串烤熟的小鸟,撒了一层红红绿绿的调料,香气扑鼻”,葛浩文教授译为:“…the children were just likea skewer of roast lamb,basted and seasoned.(孩子宛如一肉叉的烤羊羔,涂满了卤汁,撒满了调料)。
限于篇幅,此处不能一一列举那些富有意义的差异,但期望有心人循着这一线索对读原文和译文,考察葛浩文的翻译艺术,尝试回答本雅明之问:忠实对意义的复制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①盖瑞·拉尔森:《远方的画廊》第223页,安德鲁&麦克米伦出版社1995年版。
②一如乔治·巴塔耶所记:“人从不会被视为到刀俎之肉,但却无法逃脱经常被残忍吞食的命运。吃人之人明明知道吃人是禁行,知道这种禁忌是带有原始蛮荒色彩的,又虔诚地违背它。”(《色欲主义:死亡与淫欲》,第71页,城市之光出版社1986年版。)
③似乎诱惑之大使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去避免脑中的意念,正如我们从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的喜剧小说《吃人是错误的》书名所示(学术出版社1986年版)。其他人则有不同看法,以史密斯飞船《吃掉富人》歌词为证:“吃掉富人:他们只擅长一事;吃掉富人:现在咬一口;回头再咬更多;吃掉富人:我要说说心里话;吃掉富人:现在咬一口,吐出剩下的。”
④⑦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1、2页,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⑤玛吉·克尔郭:《从沟通到吃人:联合隐喻的剖析》第149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郑义:《红色纪念碑》,西方视点出版公司1996年版;在虹影1998年出版的自传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可读到如下的话:“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儿的肉剁烂做的馅儿,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英译版本《饥饿的女儿》第68页,葛浩文译,丛树出版社1999年版。郑义在其书中P110、P111讲述到吃人的另一种方式即是人肉可做成食物。
⑧但丁《神曲·第一卷》中,被囚禁的乌戈利诺伯爵的儿子邀请他尽情享受自己的肉身以求得生存,他接受邀请并开始享用。
⑨在德国格林兄弟原汁原味的童话里,馋食幼童屡禁不止,具体见《奇幻森林历险记》和《桧树》。
⑩弗朗克·莱斯特兰冈:《吃人肉者》第182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西奥多·瑞克:《神话与罪行:人类的犯罪与惩罚》,引自爱德华·A·布鲁姆和丽莲·D·布鲁姆:《劝讽之声》第89页,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克郭尔在书中第三章描述了关于基督被吸收消化的象征性场景(“主的形成”)。
(12)聚斯金德:《香水:一个杀人犯的故事》第308、309页,约翰·E·伍兹(译),华盛顿广场出版社1991年版。
(13)“狩猎集团全力奔向它要杀死的活生生的目标,然后把它吃掉……一旦达到目标,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非常清楚,集团也明显且突然地发生了变化。在杀死猎物之际,狂热的情绪骤然冷却下来。所有的人都围着牺牲品,突然安静下来。在场的人围成一个圆圈,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一部分战利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第97—98页,卡尔·斯图沃特(译),Farrar 1984年版。
(14)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人的味道》第171页,克里斯蒂娜·普瑞布切维奇·佐里奇(译),企鹅出版社1997年版。
(15)见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五章,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16)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137页,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17)乐钢:“饥饿,吃人,与吃人政治:汉语视野下中美文学饮食对话”,《博士论文》第71页,俄勒冈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137页列举两例发生于共和国时代的晦涩事件,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19)胎盘、上肢、内脏器官,人肉以各种形式存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大量医药论文、民间偏方等都经常提及人肉。
(20)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第53—54、56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1)鲁迅:《鲁迅选集》(第二版卷一)第51页,杨宪益、戴乃迭合译,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
(2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第66页,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3)安德鲁·F·琼斯:《文本中的暴力:读余华与施蛰存》第582页,见《位置》2∶3。
(24)余华:《古典爱情》,《世事如烟》第250—251页,源流出版社1991年版;英译本译者安德鲁·F·琼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5)描述会勾起对约翰·霍克斯小说《吃人者》有关残忍杀害、剁碎孩子只为给孩子姑母煮汤情节的回忆。
(26)安德鲁·F·琼斯:《文本中的暴力:读余华与施蛰存》第582页。
(27)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第58页,洪范书店出版1993年版。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吃人事件细节为:“在齐桓公当政期间(公元前685-前643年),桓公的忠实支持者易牙为了主人的快活,把自己的长子杀死并蒸成食物。桓公以专好食异肴著称,除了人肉什么都尝过。因此当易牙献上用自己儿子肉做成的食物时,桓公完全明白,但他还是吃了”。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53页,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28)在“女性情欲之威胁”的研究中包含吃人之例,见布鲁姆·迪克斯特拉:《邪恶姐妹花》,猎头出版社1996年版。
(29)《灵药》,葛浩文(译),出自《莫要嘲笑毛主席》第180—181页,丛树出版社1995年版。
(30)毕竟,为人子女者需履行出于孝顺之由的可怖要求,砍下人臂治愈患病双亲。但是一些声音认为因复仇、腐败、甚至饥饿导致的吃人与用自己的肉身喂食亲族的自残式孝行有根本的区别。然而,不管儒教社会多么肯定推崇后者,依旧无法更改摄食他人肉身的事实,更何况被吃之人并未真正丧命,后者当是鲁迅视为国耻的吃人传统的代表。
(31)承蒙米歇尔·桑斯指出有关“莫言首要讽刺对象——作者的不明信息”之旅的三大阶段的细节。未出版的论文。
(32)杨晓宾:《酒国:奢华的衰退》第18页,见《位置》6∶1。
(33)莫言:《酒国》第51—52页,洪范书店出版1992年版。文中《酒国》引文页码分属于中文版本与英译本,英译本《酒国》,葛浩文(译),拱廊出版社2000年版。
(34)这节描述与稍后的描述让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族长的没落》一书中的片段:“……大门上的帘子掀开了,于是大家看见了卓越的活动家、师团将军洛德里奇·德·阿吉拉尔全身直挺挺地放在银质托盘中,整个周围围着花椰菜做的沙拉、调味用的肉桂叶和其他香料,在烤炉里烤的绯红……嘴里衔着一小枝香芹菜,托盘搁在宴会桌上……而当每人的盘子都盛好了有核桃仁和香菜做馅儿的国防部长的这分量相当丰富的菜时,下令宴会开始:‘祝大家好胃口,先生们!’”克拉克大学出版社出版。
(35)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11页,“南美某部族喜爱人肉之至,他们让女俘虏生育小孩儿,以保障族人的正常人肉供应。”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36)郑麟来:《中国古代的吃人》第24—30、128—137页,“世界烹饪人肉方法大全与中国烹饪人肉之法”,朗伍德学术出版社1990年版。
(37)克拉克,第133页。
(38)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读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鲜有吃人情节发生,除了鲁迅《药》中面上沾满人的鲜血的馒头,已是老生常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