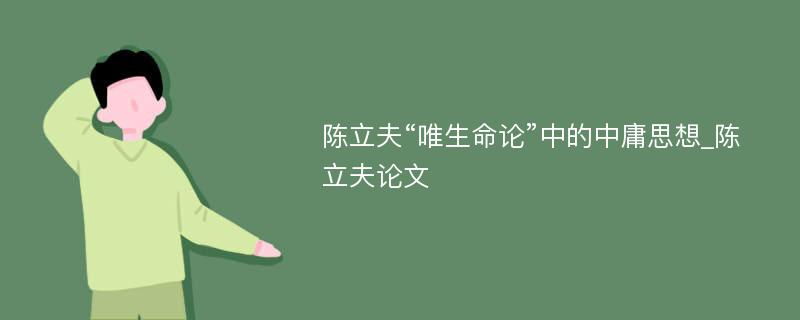
陈立夫唯生论中的中庸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思想论文,陈立夫论文,唯生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主要人士陈立夫提出了一个“唯生论”思想体系,其基本思想包含在他于1944年发表的成熟作《生之原理》一书中,这一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色彩。其中,陈立夫论及中庸思想很多,先后提出并阐述了“中之原理”、“中庸之道”、“五伦之教”等有关内容。这些内容,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陈立夫对先儒中庸思想的体认和发挥。
“中之原理”
“中之原理”是陈立夫在其唯生论的“本体论”中提出来的。
在陈立夫看来,宇宙的本体是“生元”。“生元”含有精神、物质两种性质和作用。精神是生元的动势,向外发散能力;物质是生元的静势,吸收并藏摄能力。生元这两种性能,不断地同时发挥作用,不断地生化出现象即存在;各存在之间又相互感应、相互补足和相互创新,从而就构成了宇宙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生命大流。
在宇宙生命大流中,任何现象即存在,都是一个生命过程;每一生命过程,都是由无秩序均衡结构的状态,到秩序均衡结构状态的完成与解散,而重新建设新均衡结构之过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1〕,“总要求继续存在,总不愿意死,……以表现生元之本体的好生之德久生大生的功能。绝对的久是不可能,它总希望比较久一些;绝对的大是不可能,它总希望比较大一些。”〔2〕
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宇宙生命大流中,每一生命过程之所以能有一个自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而存在,就在于它具备了适于它存在的“中正”之位、“中和”之体和“中庸”之用。“中正”之位,是指相对周围其他存在,存在者处于适于生存的位置,即周围其他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交汇、统一的中心,而不是它们相互冲突、斗争的场所;“中和”之体,指存在者自身各机能的配合呈和谐之状。即内部所含精神与物质的比重适当,适于外部环境;“中庸”之用,指存在者对外所发出的作用恰到好处,即发挥作用于周围各相反力量的两端之间,不偏不倚地贯注于当中。这三者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合起来就是“中之原理”。宇宙中一切存在,都是一生命过程,都要依据着中正、中和、中庸,然后才能维持它们的生命,发展它们的生命,使它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意义”。因此,“中之原理”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普遍原理”〔3〕。
陈立夫的“中之原理”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他充分运用了传统中庸思想的有关词汇或概念,如“中正”、“中和”和“中庸”。这三者合起来总的意思,也就是传统中庸思想所强调的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或无“过”无“不及”。他把这些视为一切存在之能以存在的根据,而其“能存在”的“存在”,并不是哲学唯物论中所指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既然一存在即一生命过程,这一生命过程无论如何长、久,终归是要死的、要结束的,因此所谓的“存在”,就是一现象或一事物相对保持一定的质、自产生到突变所持续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事物相对同一、和谐的发展状态或过程。这样看来,陈立夫是把传统的中庸思想同客观世界事物的和谐发展现象联系了起来,“中庸”的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或无“过”无“不及”,既是事物和谐发展的条件,也是事物相对和谐发展的状态。因此,陈立夫的“中之原理”,也就是中庸思想的原理。
那么,“中庸”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何以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呢?陈立夫还有一大段解释,他说:“因为凡两端都是相对,只有中才是相对中之绝对。凡两端之相对都是互相转移,都是无常;只有中之绝对才是常。存在要求继续存在,是要求常;所以必须得中。凡两端的相对都是互相转变。……太刚者折,太高易落,进锐者退速,过盛者衰,满则溢,盈则虚;凡是偏于一面,往而不返,过激而不知中,则无不失败。因为相对的两面,本来任何一面都是由于相对另一面而始有。假使执定一面为绝对,而以相对者为绝对,当然是必归于失败了。然而中则居相对者之中,它握住相对者之权衡,它不偏于一面;所以中为相对中之绝对,成为变中之常,成为一切相对者之主宰,成为一切能存在者达到胜利必由之正道”〔4〕。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和同一,都有它存在的质在量上的规定。“中”之所以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在于它在量上对应了事物得以存在的质的规定,是事物的同一性。
此外,陈立夫还解释说:“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中”是相对中的绝对,而相对者是多变的。所以,“中”无定位,无所不在,“所谓得中是随时得中,求中是随时求中;中无定在,惟时所适”。“一切存在之所以能存在,必须随时求此无所不在之中以实现之,而后能存在。这才是一切存在所根据的最普遍的宇宙,没有绝对同一的东西。绝对是对相对而言的,“常”是对“变”而言的,任何同一都是包含着差异的具体的同一。因此,“中”做为对立中的同一,相对中的绝对,变中的常,也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只有随事物的发展而时时为“中”,才是中之原理所谓的“中”,才是一事物所以存在的根据。
以上就是陈立夫在其唯生论的本体论中,所讲“中之原理”的全部内容。不难看出,陈立夫认为宇宙本体不是物质,而是含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性能的“生元”;并认为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导”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生论思想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但是,就其中所论有关中庸思想的“中之原理”来说,有些内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传统的中庸思想的内容,一般只笼统地称之为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执两用中或无“过”无“不及”,其他有关概念如“中正”、“中和”等,不曾被联系、集中起来。陈立夫把它们联系、概括起来谈,就使中庸思想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规定。
其二,传统的中庸思想的产生,应该说也基于先哲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和谐发展现象和对立同一性的发现。但是,先儒并没有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仅只是简单、笼统地称“中庸”为“天下之大本”〔6〕或“天下之定理”〔7〕陈立夫则把“中庸”与事物的相对同一、和谐现象相结合,又以事物的对立同一性给于说明,在此基础上命之曰“中之原理”,这就弥补了先儒的不足,使被视为“大本”、“定理”的“中庸”有了具体内容,从而实际上传统的中庸思想有了鲜明客观依据。
其三,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强调“权”的重要,如所谓“中无定体,惟达权然后能执之”〔8〕。“中之所贵者权”〔9〕等等。但是,正因为他们没能把“中庸”与事物的对立同一性相结合,所以何以要“权”?也没有明确解释。陈立夫以事物的对立同一性为根据,指出“中是相对中之绝对”、“变中的常”〔10〕,就具体正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庸之道”
继“中之原理”之后,陈立夫又在其唯生论的“人生观”部分,阐释了“中庸之道”。
在陈立夫看来,由于人是社会上的人,欲为己必须为人”〔11〕;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天生有向善的本性,即人心中有宇宙本体“生元”之生生不息之机的表露〔12〕,因此,为社会服务、求人类的共生共存,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最高道德和目的;在此过程中,人才能光大自身生命的意义,以完成人格,“使人与宇宙合一”〔13〕。
为实现这一人生最高道德和目的,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培养智、仁、勇“三达德”。
但是,“要具备这三达德,以完成我们之人格,就必须有一根本的生命原动力”〔14〕。何为“生命原动力”?即“诚”。“诚是指生元所发之精神能力比较的纯一与继续不已”〔15〕,“是一领导生命、集中其散漫的精神能力而使之统一的根本原动力”〔16〕,一切生元之精神能力都是依着诚之纯一与继续不已的原理去求发展”〔17〕。人是宇宙进化的顶点,人能自觉诚之原理,因此当宇宙进化至人出现后,“宇宙之诚之全体,都可谓表现于人之心中”〔18〕,“贯通在人类知、表、意三种机能之中”〔19〕。同时,人要真正具备“诚”,“能为宇宙之诚之所寄,参赞宇宙之诚”,也“只有向善,只有按照智、仁、勇三德而行”〔20〕。
此外,还应注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阶段或步聚。前四个为修身的功夫,是成己,是使自己具备智仁勇三德,以完成自己的人格;后四个是修身的应用,“是从修身上发出的功能”,〔21〕是成物,是在完成人格的同时,也完成他人之人格,即互相促进,共同进化。因此,“人生的目的,即在求人类之共生、共存、共进化”〔22〕。
然而,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毕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道德和目的,是“由共进化而使人人都到完成其至高人格的地步”,“可是人的工作却只能从当下作起”〔23〕。那么,当下应如何去做,才能促进这一最高目的的实现呢?陈立夫说:“这便必须认识我所处的空间时间的地位,而以我为我生命原动力发出之中心点,看如何使我之生命原动力自此中心点发出后,能发生最大最好之效果,即最大的功用,此即所谓中庸之道”〔24〕。
陈立夫对“中庸之道”的阐述,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内容中开始的。他所讲的“人生观”,基本上揉合了中国先儒的人生理想、人性论和道德论。
其中,他脱离社会物质生产和人的阶级性,来谈论人生道德、理想和目的,把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这一最高人生目的置于人性本善的基础上,视其为宇宙本体“生元”之好生之德,宇宙之“诚”在人身上的体现,就再一次表现了陈立夫整个思想体系的唯心主义特色。他在专门论述过宇宙本体“生元”之后,又拉出个“诚”来,把“诚”视之为可以和“生元”相提并论的东西,也表现了其思想体系在逻辑概念上的冲突和混乱。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陈立夫是明确地把“中庸”作为最好的道德实践方法来看待的。即其所谓由此“生命原动力”“能发生最大最好之效果”、“最大的功用”,即“中庸”是实现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最好方法。这比起先儒笼统地称其为“至德”〔25〕,就真正靠近了人生、社会,去掉了几分朦胧不可捉握的玄秘色彩。
“中庸”何以是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最好方法呢?陈立夫解释说:“因为世间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同时存在,而且相对的互相转变。一切偏于一面的过激行为常会转到另一方面,所以人必须看清楚社会上各种相对、相反的力量之互相夺争、互相转移;不要陷于一偏,随时择取最妥善的方向、两端同时顾及的方向,去安排行为,使其所发生的生命原动,能通过各种矛盾的力量而向前进。最后便自然会使两方面的矛盾的力量,在此中心的力量下统一起来,犹如物之重心将物之各方面下坠力统一一般”〔26〕。显然,陈立夫这里运用的是他先前讲过的有关“中之原理”的内容,是把“中之原理”即“中庸”的思想原理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方法论。其意是说:“中庸”之所以是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最好方法,在于社会是各种矛盾的对立同一事物的集合体,对立是社会力量的分散,是社会的不和谐,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则是兼顾各方的社会力量的聚合点,是社会的和谐,是合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要求的。
“过”与“不及”,即相互对立的两方,或落后于或超越了事物的质在量上的规定,都不符合事物和谐发展的要求,只有兼顾两端、在量上对应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中”,才是事物和谐发展的条件要求。这是传统中庸思想所含方法论的价值所在。它自动控制人们:无论思考或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背离事物的客观要求走极端。陈立夫的解释有些迂回,缺乏针对性,但大意不错。
此外,陈立夫还强调说:“中是相对的”、“善是绝对的”。所谓“中是相对的”,是说“中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全靠人之随时不断的权衡于其所认识的两端之间,然后才能随时用中”〔27〕。所谓“善是绝对的”,是说“中”是手段,善是目的,无论“中”点如何改变,求善、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目的是恒一的。“中”只有在离合、多少、大小、刚柔、缓急等各种相对对立的关系之间求,而不能在善恶、是非、真伪、美丑等各种绝对对立的关系之间求〔28〕。这两点可以说是陈立夫所谈“中庸之道”的两个原则,前一个是对先儒“时中”的进一步解释;后一个是陈立夫的发挥,旨在说明先儒的中庸观念,并非简单、无原则地折衷、调和。所有这些,就是陈立夫关于“中庸之道”的基本内容。
1939年,毛泽东在谈及“中庸”时,曾这样说:“‘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的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拆异己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29〕。
毛泽东对中庸思想所含方法论的挖掘和表述,其精当是陈立夫的“中庸之道”所不能比拟的。这不仅在于陈立夫整个思想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一些重要概念上的混乱、冲突等严重思想缺陷,具体差距在于他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在传统的道德领域进行的。传统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代表天意的“圣人”、“君子”的境界,是治国平天下,也即陈立夫说的求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既然如此,“中庸”作为最高道德的实践方法,上升到理论,树立、维护中心势力就必然是思论问题的出发点和该论理的特色。陈立夫在关于“中庸之道”的解释里,所谓“以我为我生命原动力发出之中心点”,“使两方面的矛盾的力量,在此中心的力量下统一起来”等等,就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看,陈立夫的“中庸之道”,也像毛泽东所评孔子的中庸观念那样,“乃是排拆异己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
但是,陈立夫毕竟也发现了“中庸”所含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它是最好的方法,而不像先儒,笼统地称之为“至德”;其论述虽然是在道德领域,虽然不很精确,但也触摸到了“中庸”“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方法论实质。从这些方面看,陈立夫的“中庸之道”,又有其可肯定之处。
“五伦之教”
“五伦之教”是陈立夫所讲的,关于中庸思想的基本实践内容和方法。
五伦之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关系准则。陈立夫认为它们“是真正的以我自己为中心,而对四方之人表现我的生命活动,亦即使我们前所谓内心之诚,通达于四方……,而与四方之人构成和谐的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关系。此之谓‘和’之达道”〔30〕。这就是说:五伦之教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之所以如此,在于它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和”。以下是陈立夫对五伦之教及其为“中庸之道”的具体解释。
陈立夫说:“最先应讲求的对人之道,便是处分父子、兄弟、夫妇之道”,因为“每个人出生以后,便不能不构成这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是最切近的人与人之关系。人之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关系,最初即于此三种关系中显现”〔31〕。父子之间:“父母之责任在养育子女”,因此父母应以严、慈之道,“养其心身,培其意志,以至于成人”;子女对父母应奉孝道,即“甘旨以养之,衣物以奉之,求父母之生存”,并承父母之意志“继往开来”,“事父母几谏,父母有过必求其改”。兄弟之间:兄居长,弟当对之以恭;弟居幼,兄当对之以友,行而进之。彼此“急难则相助”,“有过亦相规”〔32〕。夫妻之间:和顺敬爱,互勉其德,共养其家。“人处此三种关系之中,则必先由此三种关系以表现其求与他人共生、共存、共进化之精神”。因此,我们“如果要有最伟大的对人类之热情,便须自我对家人父子之间的情感培养起”〔33〕。
关于朋友之间和君臣即长官与部属之间的关系,是“由家庭中的关系,扩大到国家社会中的人与人之关系”〔34〕。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信”即彼此相信其人格和守信约。君臣也即长官与部属之间,“各以尽忠于其职守为目标”〔35〕,彼此以礼敬相待,共同对国家社会尽忠负责。〔36〕
最后,陈立夫总结说:“人谁无父母、兄弟、妻子、朋友及君臣关系?人以其自己之地位为中心,上而父,下而子,横而兄弟、妻子,外而朋友、君臣,而即处此五伦关系之中。人随时随地便接触此五伦关系之人,而须行此五伦之道。行此五伦之道,亦为人人所易于实行,但顺其自然,四方通达起去,即所以促进国家天下人类社会之进步。这正是用人身自己的生命原动力中心的‘诚’,向四方表现以求贯彻其‘诚’,由致中而致和之最简易直捷的道路”〔37〕。
传统的五伦之教,是精华与糟粕俱在的人伦道德思想。所谓其精华,因为它概括了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准则,规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应该享有的基本生存权力,和应该付出的基本责任、义务。从人类自身的生产是永恒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繁荣进步需要人际关系的和谐等角度看,它不乏有永恒的价值,是一份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所谓其糟粕,因为它是纯粹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是绝对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并且,传统的五伦之教,自汉朝以来常常是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连在一起的。在政治、伦理相互渗透的中国,“三纲”已经取代“五伦之教”的原始意义,成了极度残害个性自由、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柱。近代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皆把斗争的矛头首先对准这些伦理纲常,其症结就在这里。而陈立夫仍然把五伦之教置于具体社会、阶级之上来谈论,并认为人人如此行,就可以达到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理想社会,其思想的保守、落后乃至道德主义的空想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另一方面,陈立夫在阐述五伦之教时,没有突出“三纲”之意,而重在它的原始意义,即人的社会基本权力和义务,并强调人对社会的热情应从家庭培养起,这是应该肯定的。
陈立夫把“五伦之教”看作是“中庸”的基本实践内容,也是对先儒有关思想的认同。陈立夫毕竟抓住了“中庸”在形式上的“中”与在目的上的“和”,这就分别对应了“五伦之教”所规定的每个所必然要处的位置“中”,和兼顾各方所达成的“和”;加上他所强调的家庭是培养社会热情的摇篮,就使得“五伦之教”之所以是“中庸”的基本实践内容和方法,有了具体的解答和逻辑根据,从而也就弥补了先儒在这方面的思想缺陷。
三、四十年代,在国共之间反革命势力与革命势力剧烈斗争的年代,陈立夫与中国共产党的“唯物论”相对,抛出“唯生论”,从思想上打击共产党的政治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他如此关注和称道传统的中庸思想,也并非发思古之幽情。1989年,陈立夫在谈及“唯生论”时说道:“为辟唯物论之不合理,依据吾国‘经中之经’之《易经》(生生之谓易)之宇宙万有生存原理及国父生元有机论及民生史观,著《唯生论》以打击共党,盖宇宙间一切生命为物质与精神两者配合而成,即阴与阳之配合,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其理易明,则‘唯物’保能生存耶?‘唯心’亦然?依此而知‘唯生’始能得其中而合乎生存原理,唯心唯物俱只偏于一面,而不能得生命之全体大用”〔38〕。
由此可知,陈立夫之所以在其唯生论的著述中,连篇累牍地论及“中庸”,就在于它是其唯生论的一个隐含的、不可或缺的注脚:既然一切存在皆依据不偏不倚、兼顾对立的两端而得以存在,宇宙本体就不能不是既含物质又含精神的“生元”,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就不能不是既要求物质又要求精神的人类的“求生意识”等等。然而,陈立夫似乎疏忽了他所论述的“存在”,并非对客观世界的抽象概括,而是指各个体的事物从生到死的“存在”。个体的存在原理既然是维持一定质不发生根本变化的、相对和谐发展状态的原理,如何能等同于客观世界绝对的冲突与相对的和谐、不断从旧到新、生生不已的发展原理呢?且不论唯生论的其他方面,仅此一点已足以说明其思想体系的荒谬、虚弱和无力,从而其政治用意的失算,也就在所必然了。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陈立夫:《生之原理》,第76、75、79、80、80、80、118、129、132、146、150、151、153、154、 156、169、171、172、172、173、173、175、181、183、183、183、 184、186、185、186、187—188页。
〔6〕〔7〕〔8〕《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第17页;第357页;第28页。
〔9〕《二程粹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25〕《论语·雍也第六》;“中庸之为德也,共至矣乎!”《四书章句集注》,第91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147页。
〔38〕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台北东大图书馆1989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