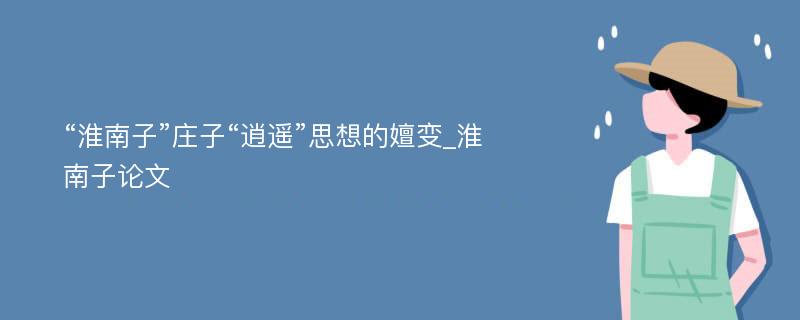
《淮南子》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改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子论文,庄子论文,逍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069-07
在庄学史上,征引《庄子》最为频繁者当推《淮南子》。王叔岷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该书思想“尤与庄子为近”,故引其文特多。①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可总括为其书首篇之题“逍遥游”,此三字既代表庄子的卓然超拔之生命志趣,同时也是一种流传久远、影响复杂的精神传统。若从“逍遥游”的诠释史来看,《淮南子》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书中大量出现了近于庄子“逍遥游”思想的文本。鉴于书中此类文本出现甚多,且篇幅较长,故兹略引一例:
所谓真人者也,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机械之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毁山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淮南子·精神训》,下文引《淮南子》处,仅标注篇名)②
《淮南子》中的类似文本在语辞、文风和思想内容上都带有庄子哲学的显著影痕,其中“真人”、“至人”、圣人等理想人物所具有的与道相合、超越生死和人间事务、畅游无极、神通天地、不为灾祸所伤等特点,则与庄子的“逍遥游”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问题是如何理解《淮南子》中这些文本的思想实质呢?
主角及主题的转换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刘安等人曾著书“言神仙黄白之术”。胡适由此提出,《淮南子》描画的逍遥“真人”,表现的是渴望不死不生的神仙家之出世哲学,甚至其书总旨亦在于此。③近乎此,丁原明先生认为,《淮南子》张扬的逍遥秘境既反映出汉初士群“营造精神家园的离世倾向”,同时又“充满着出世成仙的冀求”。④如果仅着眼于相关文本的字面意思,似可说《淮南子》提倡出世或离世的人生哲学。但是,此类看法却忽视了该书思想的内在复杂性或矛盾性,例如《泰族训》的一段话就直接否定了上述观点:“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可谓养性矣,而未可谓孝子也。”这里虽对养生而求长生者亦不乏肯定,但其总体倾向却是基于入世的儒家立场批评他们出世、离世而不尽人伦。据此,那种笼统认为《淮南子》提倡出世成仙之哲学的看法是片面的。
迥异于上述观点,徐复观先生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政治的压迫和中央对地方王权的削弱,淮南宾客向往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特为迫切”,而在先秦诸子中,惟有庄子“逍遥游”包含渴望“精神解放而获得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便使淮南宾客感到“特别亲切”,“觉得《庄子》是他们的代言人”,故其书中就大量袭取庄子“逍遥游”的思想观念,以寄托他们“在压迫和危机感下对精神自由的向往”。⑤与此略异,陈静先生认为,《淮南子》之“逍遥游”主要蕴含着刘安本人对自由的向往:首先,在王权不断被中央削弱的困境下,作为受制于朝廷的封王,刘安向往自由⑥;其次,除了是国主,刘安作为“人”,同样渴望不受现实对象性关系制约的“人之本然”的自由⑦。在笔者看来,陈氏所说的后一种自由或可视为本真的人性自由,而刘安作为封王所向往的自由不过是政治上的王国独立、王权专断,实际上很难称得上自由。另据《汉书》其本传,刘安在书成后献之于武帝,“上爱秘之”。由此可推,《淮南子》之“逍遥游”的蕴义应非自由,否则刘安怎会将其献给武帝,而武帝也不可能“爱秘之”。
且不论未加分辨地用现代性的自由去诠释刘安君臣之心态是否贴切,也不论把其书描述的神异之境解读为离世的人生哲学是否确当,仅就研究方法而言,上述诸说的缺陷有三。第一,过于信任有关文本的字面意思,而没有考虑该书的独特文风。我们看到,前引“逍遥游”文本可谓极尽排比、铺陈、夸饰之能事。之所以采取此种表述方式,《要略》解释说,这是因为“今学者无圣人之才”且“道论至深”、“万物至众”,故作者不得不多辞以抒情、博说以通意,以致其文辞显得“坛卷连漫,绞纷远缓”。另一方面,在先秦子书中,《庄子》最具美富之文辞和瑰奇之意象,而这恰好暗合并可满足《淮南子》的多辞博说之需。换言之,《淮南子》的文风极有可能受到《庄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无论如何《要略》的这段“夫子自道”都提醒我们,在探讨其“逍遥游”文本之蕴义时,不应拘泥于其文辞之“迹”,而应透过表面以揭明其内里的“所以迹”。
事实上,在前述引文中,某些近乎繁琐、失于枝蔓的文句和意象只是修辞性的粗糙堆砌,有的甚至是对《庄子》的直接抄袭和简单照搬,它们不仅并无实质性的内涵指涉,而且对于上下文之间思想逻辑的推进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胡适从中解读出神仙家的出世哲学,徐、陈认为内中蕴有刘安君臣渴望自由之秘旨,其观点虽异,但显然都把《淮南子》对“逍遥游”的“虚张声势”之叙说过于当真了。
第二,未能认清《淮南子》“逍遥游”话语中的理想人物之实际所指。在庄子,“至人”等理想人物皆为普通个体或士人精神品格之完美化身,而在《淮南子》中却并非如此。以《精神训》中的“至人”为例:“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委万物而不利,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登太皇,冯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在这段话之前,作者首先批评了压制欲望以致使人“不得其和”的儒家主张;之后又批评了那些因为放纵欲望以致亡国丧家的君主;最后作者提出,若能“适情辞余,以己为度”,即可免遭社稷败落之厄运。据此语境分析可知,这段话的中心是批评禁欲和纵欲之两端,强调君主应节制欲望,而“量腹而食……”的“至人”则是作者期待的能够节制欲望之典范。所以,此中“至人”虽然也像在庄子笔下那样“游无极之野”,但其实质内涵却是指节欲适情、无为无不为的理想君主。概言之,虽然具体语境不同,《淮南子》所推崇的“至人”、“真人”及圣人等亦不出此类,故作者时或称其为“圣主”、“明主”、“圣王”、“明王”、“有道之主”。
第三,仅仅局限于书中那些袭自庄子“逍遥游”的思想文本并用现代理念加以审度,而未能将其放到全书整体结构中去分析,更未将其与《淮南子》自身的总体旨趣结合起来考察,故所得结论便难免爽失。学界一般将《淮南子》归为黄老道家。冯友兰先生更具体指出,该书旨趣有二:其一是使精神翔于“虚无之轸”(《淮南子·要略》)⑧,此为“黄老之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其二,迥异于先秦道家之避谈世务而只求超乎尘表,该书“不但不逃避社会,而还企图解决其中的问题”,⑨所谓“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⑩冯氏此论即为黄老思想的两大主题:治身与治国。具言之,治国根于治身,身治则国治,而治身之本则在于治神(心),如《泰族训》说:“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依此本旨,《淮南子》的“逍遥游”文本首先应被纳入人主治身的主题内考察,而其中那些与道合一、超越尘垢及生死的逍遥之境则应从人主治神的角度来理解。
基于不同的主题和主角,《淮南子》改铸了庄子的“逍遥游”思想。在庄子,个体应远离庙堂,专注于自我生命的自在和超越;《淮南子》则认为,君主个人的身心生活应与治国理政相结合,后者以前者为本。由此,作为个体生命理想的庄子“逍遥游”就被转化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如前述引文对“至人”、“真人”之逍遥自得一面的描述,“逍遥游”可谓君主个人生活的理想样式;其二,依黄老之旨,君主个人生活的逍遥又应与其治国理政相结合。综之,《淮南子》之“逍遥游”的主旨是:君主如何能既无为而治其国,又同时可保有逍遥的个人生活?这两个方面的理想结合,借《诠言训》的话说就是:“闲居而乐,无为而治”。进一步,若把君主的逍遥归拢于其个人形神的修治,而治身又是治国之本,那么由此产生的另一问题便是:君主个人的逍遥如何外化、落实到其外在的政治活动中?
“逍遥游”的养生化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汉书》其本传则说他“辩博善为文辞”,曾作《离骚传》、《德颂》等文,《艺文志》存有题为“淮南”的《琴颂》篇名。又,《文选》卷三十三收有其《招隐士》一文,《古文苑》还有题为刘安所写的《屏风赋》,大意是抒发怀才不遇之怨。从这些资料看,刘安虽贵为帝后封王,但却颇富风雅高逸的个人情趣。或正因此,他才与追求生命之自在自得的庄子“逍遥游”发生了共鸣。
一方面,结合刘安的个性特征,《淮南子》描述的那些逍遥之境可被视为其理想中的圣主所拥有的内在生活之极至。《要略》把作者著书之目的概括为内外两方面:“外与物接而不眩”、“宰匠万物之形”,“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逍遥一世之间”;这两个方面皆属“帝王之道”。进而书中直言,通过“处神养气”而有的逍遥优游之乐,惟圣人(实指圣主)方可获得,“齐民”却无从享有,如《原道训》说:“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黑,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将圣人与“齐民”截然二分,且认定只有前者才能内通“天机”,不被声色和困顿扰乱心志,而总能保持精神的超然自乐,类似表述在庄子处从未出现。这无疑是刘安的封王身份使然。这也就提醒我们,无论书中那些逍遥之境如何神异浪漫,以现代自由观念加以诠释并不确当。
另一方面,正如冯友兰所言,黄老学的旨趣之一是养治精神而使其翔于“虚无之轸”。《淮南子》阐发的“逍遥游”恰有与此相合之处。例如,《精神训》:“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要略》:“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原道训》:“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达而不荣,……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势而尊,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在这几段话中,一方面,“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以及“不以物易己”、“穷而不慑,达而不荣”,这种类于庄子的放达超脱之意趣,连同“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与化翱翔”,皆属“逍遥游”之思想内涵(11);另一方面,“神无累”、“心不惑”、“志不慑”以及“抚静其魂魄”、“坚守虚无之宅”、“平虚下流”则是指精神的虚静状态。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内容被密切结合到了一起:逍遥超脱成了精神虚静的前提或表征,甚或二者本为二而一的关系。而在末段引文中,“尊”、“富”、“强”又隐隐透出虚静和逍遥背后的帝王心态。因此不妨认为,前述引文中的神异浪漫之“逍遥游”,实质上是对圣主之精神虚静状态的夸饰性叙说。
以“游心于虚”为目的(《淮南子·俶真训》),《淮南子》提出的养心或养神之术,要之有三。其一是“偃其智故”(《淮南子·原道训》),“不为谋府”、“不为智主”,以“保于虚无”而“游无朕”(《淮南子·诠言训》)。其二,排除情欲对心神的干扰,以使精神“坚守虚无之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淮南子·原道训》)在这方面,《淮南子》一转其希求超越生死祸福的精神向度而表现出悉心养护自我生命的显著特征,这也与庄子的“逍遥游”逐渐拉开了距离。其三,由于“精神劳则越”(《主术训》),“用而不已则竭”,因此必须做到“精神之不可使外淫”或“神气不荡于外”(《淮南子·俶真训》),从而使之持守“恬愉虚静”之“根”(《淮南子·精神训》)。
我们知道,庄子虽亦讲不得已情形下的安命自适,但他最看重的却是自我精神的卓然超拔,《淮南子》以“恬愉虚静”为究竟的养心术显然与此不同,因为其精神向度不仅不是为了卓然超拔于尘垢之外,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参与世间生活。《俶真训》云:“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祸福弗能挠滑,非誉弗能尘垢”。以“静漠恬澹”、“和愉虚无”为要诀,该段主题是养生,其中既有精神层面的性德之养,又有形体层面的血脉五藏之养,而圣主养生之目的则在于“经世”、“终年”。
如果说《淮南子》在养神问题上已与庄子逐渐拉开距离,那么二者在对待形体的问题上的思想距离则愈加拉大甚至分道扬镳了。
上节已及,有鉴于纵欲和禁欲之弊,《淮南子》提倡的养形之道是节制欲望,使之保持适度状态,所谓“适情辞馀”(《淮南子·泛论训》)、“适情知足”(《淮南子·缪称训》)。另外,如同反对精神的过度使用一样,《淮南子》同样反对过劳形体。书中反问:“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作者认为,如同神之用必有所节一样,形之劳也应保持适度。这不仅是因为“形劳而不休则蹶”(《淮南子·精神训》),而且形体过劳也会相应造成心神不宁,亦即“形劳而神乱”(《淮南子·说山训》)。
比较而言,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虽则亦有保全自我肉体生命之义,但在多数情况下,他更为强调遗形于大化,全然不以其存亡全损为虑,而为确保神之逍遥,形之寿夭甚至可以弃置不顾。而《淮南子》虽有时也主张超越形之存灭,但其所指不过是一种虚静恬淡而非超拔卓然的心神状态。事实上,对待肉体生命,通过养护而获得适逸终年之乐才是其真正期求。
《淮南子》希求的圣主治身之最终目标是形神各得其宜、各得其养,“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训》),或谓“心常无欲,可谓恬矣;形常无事,可谓佚矣。游心于恬,舍形于佚,以俟天命”(《淮南子·诠言训》)。在这种和谐的身心状态中,圣主即可拥有自得之乐。《原道训》强调,此“乐”是指“得于心”而“以内乐外”,绝非声色犬马的自我放纵,具体来说亦即“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慷慨遗物,而与道同出”。该篇又把自得解释为“全其身”,作者认为,能如此,则“不待万物之推移”、“非以一时之变化”,“性命之情处其所安”,“以随天地之所为”。要之,圣主的自得之乐兼包神之逍遥和形之全佚,这种乐既受用于己身,同时又合通于道或天地。
《原道训》反复强调“尊天而保真”、“贱物而贵身”。冯友兰认为,这正是《淮南子》自我设定的思想“出发点”(12)。由此方面看,对待己身,《淮南子》所持的无疑是兼括形神的养生主义的立场,而它追求的则是一种恪守节制原则的快乐主义的生命理想,其中既包括心神的虚静恬愉之乐,又有形体的安逸尽年之乐。这与庄子“逍遥游”大为不同,因为庄子面对的迫急问题是怎样在险恶的环境中保全自身,养生而当下安乐对于他来说乃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其终极理想则是超越现实的存亡祸福,寄身于大化流行,精神与天地相往来。再者,由于外在环境的逼迫,庄子“逍遥游”内中隐含着无比沉痛的生命体验基调,而《淮南子》全书则在一定程度上洋溢着快乐主义的人生意趣。
毫无疑问,造成这些差异的根由是庄子和刘安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构成的不同生命境遇。同样因此,基于饱受苦难的个体立场,庄子激烈批判扼压士人生命的政治现实,他坚持在庙堂之外开展自在独立的身心生活。然而这种基于个体生命立场的社会批判意识在《淮南子》中却并不存在。退一步看,如果说《淮南子》也有基于生命立场的类似批判,那也只是某些从圣主治身角度展开的近乎自我警戒的批评,例如对君主纵欲亡国的批评、对君主不知避祸就福的批评,等等。一方面,这些批评内蕴着的是理想圣主的视角和立场,另一方面,《淮南子》提出这些批评之目的仍是为了倡导君王的贵身养生之道。
“逍遥游”的政治化
依黄老之旨,《淮南子》不惟不会像庄子那样基于个体生命的立场批判现实,相反它力图把己身逍遥与现实治理结合起来。《缪称训》云:“主者,国之心。”意思是正如心之於身,君主在政治秩序中乃是最高宰制者,而其治身状况则直接关乎国家的治乱存亡,故《原道训》说:“天下之要,……在于我身,身得则万物备矣!”何谓“身得”?《齐俗训》云:“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此谓“视则明”云云,既是圣主之形神皆宜、各尽妙用的自得状态,又是他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的高超举措艺术,这两方面皆归因于“道之得”。进而,以道为枢纽,圣主的治身之术亦可相应转化为治国之方,借《吕氏春秋》的话说:“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淮南子·审分览》)《淮南子》希望圣主既因得道而使其身逍遥自得,又因得道而治平天下,所谓“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淮南子·原道训》)。
如同在治身方面一样,在政治实践中,圣主之心神同样是至为关键的因素,所谓“凡将举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淮南子·齐俗训》),“以中制外,百事不废”(《淮南子·原道训》)。《人间训》更详曰:“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此段化自《庄子·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在庄子,“外化而内不化”是说个体在随外物迁变时,内心仍然持守高远独立之境。也就是说,在“外化”和“内不化”之间,庄子看重的是后者。而《淮南子》所说的“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不仅异于庄子原意,并且它所看重的实质上是基于“内不化”的“外化”,即圣主若内守“一定”,那么他在外在政治实践中必能“与物推移”、任由所欲。可见,依托道的贯通,圣主的高明政术最终被归根为其心神的理想状态,而庄子之谓“内不化”的精神境界也俨然变成圣主政治实践智慧的内在支撑点或生发点。
为使心神得以虚静逍遥,《淮南子》主张祛除智巧。而在治国活动中,该主张则被转化成无为而治的施政纲领。《诠言训》云:“圣人无思虑,无设储,来者弗迎,去者弗将。人虽东西南北,独立中央,故处众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独不离其坛域。故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故圣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见誉。法修自然,己无所与。”“无思虑,无设储”等数语袭自《庄子》,(13)指祛除智虑而达到的虚静逍遥之心境。此处提出,面对各种意见和力量的交错纷杂,君主务必消泯显智求名之心而遵循自然无为之天则,做到“不专己”或“己无所与”。这种似乎超然于复杂政治现实之外的姿态,与圣主虚静的心态恰成内外对应。进而,《淮南子》又将祛智而虚与君主无为、臣子有为联系起来。《诠言训》说:“故得道以御者,身虽无能,必使能者为己用。……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孰能訾之!”“人能虚己以游于世”出自《庄子·山木》,本是市南子用以批评鲁侯对势位的贪恋,在《淮南子》这里却被扭转为君主以“无能”之身驾用有能之臣的统治术,而君主的“虚己”恰恰通过其大智若愚的“无能”、无为表现出来。市南子之谓“虚己”意在劝鲁侯捐国弃位以避害免忧,而《淮南子》之“虚己”则是一种借以巩固君位的政术。
圣主养神及养形的另一关键是不过劳形神于外。《淮南子》也把该原则与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联系起来。《主术训》提出,如果君王耗神劳形、事必躬亲,“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正确的为政之道是主逸臣劳,这恰对应于人主形神不劳的治身原则。《泰族训》说:“宰、祝虽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引文首句化自《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圣主之逸既包括形神的不过劳,又兼涉其不夺臣民之事的无为政术,而舜即为能践行主逸臣劳之道的典范。《淮南子》希望圣主凭依此道,既能在繁杂的政治活动中保有适逸闲静之乐,同时又不劳形神而实现平治天下之伟功。《主术训》便说,“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归本而言,只有有道之主才能既得享其身之逸,又治国而有功,所谓“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淮南子·原道训》)。
必须指出,在从心神之虚静到无为之政术的转换中,老子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原道训》云:“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感而应之”;“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不为先唱,感而应之”化自《庄子·德充符》,哀骀它的“和而不唱”,而“柔弱者,道之要”、“志弱而事强”、“清静者,德之至”等则取自老子。在庄子,“不为先唱”是个体于危世中的避祸之术,“恬然无虑”、“虚无恬愉”则是其安命自适的当下心境。《淮南子》参照老子虚无为用、以静制动的思想,不仅把这些原本属于微贱个体之生命哲学的范畴施以政治化的改造而使之成为人主的微暗心态,并且进而将其转换成人主驾驭臣子、治国应事的政术。就此而言,原本作为个体精神境界的庄子“逍遥游”经由被老子化而最终被政治化了。
与圣主形神各得其宜的和谐身体状态相对应的,则是《淮南子》所欲构建的和谐有序的政治图景。《泰族训》说:“今夫道者,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岂节拊而毛修之哉!圣主在上,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隐士,无轶民,无劳役,无冤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此段前半部分是说圣主治身所达到的形神各处其位、各尽其养的自得状态,后半部分则是说圣主治国所实现的上下各居其守、各安其职的政治局面。其中,与心神“得其位”、“静漠恬淡”相应的是“圣主在上”及其治国理政的“廓然无形,寂然无声”,与形体之“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相对的则是其治下诸阶层的“各得其所宁”。总之,圣主个人的形神自得与政治秩序的和谐安定已完全统一。
据《要略》,作者著书之目的是为了使人主“知举错取舍之宜适”,以“应待万方,鉴耦百变”,同时又“有以处神养气”,“内治五藏,瀸瀒肌肤”,从而最终“逍遥一世之间”,“自乐所受乎天地”。由此可见,《淮南子》的最高理想是通过内养形神、外理国政,以获得至极的逍遥之乐。而圣主恰恰拥有此种至乐:“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淮南子·齐俗训》)在庄子,“轻天下,……下与造化为人”的主角是普通个体的理想化身,而在《淮南子》这里则是“五帝三王”。作为家国天下的主宰者,不能想象帝王之至乐仅仅来自其个人私秘的身心生活。《原道训》云:“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在专制社会中,与天下无间者惟有帝王。故此谓天下之“得我”,实指由于帝王之形神得治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的安稳太平。由此,“吾与天下相得”作为《淮南子》追求的目标也就涵纳了两方面的内容:帝王本人之形神的和谐自得以及社会政治的安宁有序。考虑到帝王独具的身国一体性,可以认为,与“吾与天下相得”形成对应的帝王的逍遥至乐,实质上既来自于其私秘身心生活的安适优游,同时又建立在其治平天下之伟功的基础上。换言之,卓有成效的政治实践以及由此实现的政治成就也是帝王逍遥至乐的源泉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通过强调圣主身心生活的逍遥自得与现实政治实践的一体化,《淮南子》彻底消解了庄子“逍遥游”思想的超越性、批判性和非政治性。
注释:
①王叔岷:《〈淮南子〉引〈庄〉举隅》,《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
②本文所引《淮南子》文本,均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1989年)。
③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4-168页。
④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
⑤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121页。
⑥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⑦同上,第169页。此外,孙纪文认为,《淮南子》的精神范畴“是庄子之学的产物”,“它的内涵保持了道家追求精神自由的学术理念”。(孙著《淮南子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⑧高诱认为,《淮南子》之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转引自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06页)
⑨⑩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三松堂全集》(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132页。
(11)[南宋]高似孙:《子略》云:“《淮南》之放,得于《庄》、《列》。”(转引自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89页)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三松堂全集》(第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13)《庄子·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刻意》:“圣人之生也天行,……去知与故,循天之理。……不思虑,不豫谋。……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惔,乃合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