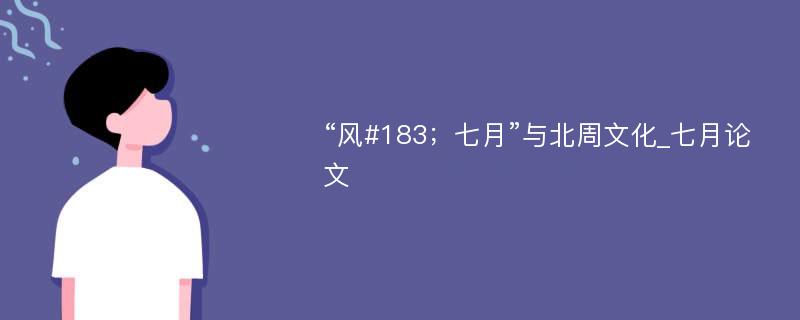
《豳风#183;七月》与北豳先周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豳风论文,周文论文,北豳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最出色的一首农事诗。它生动而真实地记述了周先祖在其发祥地古北豳(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之庆阳县、宁县、正宁县一带)率民稼穑,艰苦创业的农事活动。但是,长期以来,传统说诗者或由于对“豳”之地域概念认识的偏差,或由于对周先祖在北豳的活动估计不足,或由于对地方史志和民间文化资料的忽视,因而导致对周族发展历史的阐述乖离常出,也导致对《七月》诗中所描述的一些农事现象的解说和章句的注释错讹时见,不中肯綮。本文拟从北豳先周文化遗存的角度考察周先祖在古北豳的农事活动及其在《豳风·七月》一诗中的反映,以求理清周族发展史的源流,确解《七月》之章句。
一
《豳风·七月》是古豳地的民歌。那么,豳地究竟在何处呢?这有必要从周室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加以考察。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室自后稷至武王以前共传15世。这15世以其活动地域和创业成就而言,有五个特别突出的领袖人物代表了五个最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古公亶父居歧”,“文王姬昌居丰”,“武王姬发居镐而有天下”。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而且从《诗经》本身中就能找到极其可靠的证据:(1 )《大雅·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即有邰家室。”邰,地名,一般认为在今陕西武功西南。(2)《大雅·公刘》:“笃公刘,……豳居允荒。 ”又:“笃公刘,于豳斯馆。”此豳,亦地名,即“豳风”之“豳”。(3 )《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歧,地名,一般认为即今陕西歧山县。(4 )《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丰,地名,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水以西。(5 )《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镐京,西周国都,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水东岸。很明显,这五个发展阶段中,“公刘居豳”之“豳”,就是《诗经》中的“豳风”之“豳”,也正是《七月》涉及的地域。可惜,对“豳”的涵盖意义,历来认识却存在着偏差。
传统说诗者均认为此“豳”只是指今陕西省旬邑县、邠县一带。如东汉郑玄《毛诗笺》注诗豳说:“豳者,公刘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按:郑玄所说本质有误,自邰而出徙戎狄之地的并非公刘,而是公刘的祖父不窋。对此史多记载,本文后面亦有辨)唐颜师古依此错论注《前汉书地理志》进而说:“旬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南宋朱熹《诗集传》亦言:“豳,在今邠州三水县。”三水县乃旬邑县之古名。今人高亨《诗经今注》更明确而又肯定地说:“豳国疆土在今陕西旬邑县、邠县一带。周王祖先公刘始迁于豳,都城在今陕西旬邑县西邠县北。”实际上,这个说法只是片面地顾及到公刘后半生在今旬邑、邠县之“豳”(或称“南豳”)的活动,并用此涵盖了“豳风”之“豳”的全部内容,是既不完善,也欠准确的。因为从历史事实来看,公允地说,“豳风”或“诗豳”之“豳”,就其地域及周族活动的史实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周先祖不窋、鞠陶以及公刘前半生的创业之地——北豳,即今甘肃省庆阳县、宁县及正宁县一带地区。
何以如此说呢?我们通过对正史、地方史志以及民间文化资料的综合考察,就可以得到证据确凿的清晰回答。
首先,从正史的记载看,《史记·周本纪》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奔戎狄之间。”又云:“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其德。”从这两条记述可以看出,周先祖不窋早期袭后稷之职,曾在夏政权中担任负责农业的官员。后来夏政权衰微,年老的不窋被免去农官之职,因而出走,奔避到了“戎狄之间”。以后,他的儿子鞠陶和孙子公刘也一直继续在这“戎狄之间”从事耕种的创业活动,从而为周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道之兴自此始”。那么,不窋、鞠陶、公刘祖孙三辈所居的这“戎狄之间”,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宁、原、庆三州,是指今甘肃省庆阳、平凉部分及其以北的宁夏、陕北小部分地区,并非传统说诗者所说的旬邑、邠县一带。《括地志》又具体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弘化县,即今甘肃庆阳县。可见《周本纪》所说不窋“奔戎狄之间”,以及公刘“在戎狄之间”,就是来到了今庆阳县一带,并筑城而居,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主要包括庆阳地区的庆阳县、宁县、正宁县,及合水县、华池县、镇原县的部分地域。因当时这一带属义渠戎所辖,故言“戎狄之间”。而这“戎狄之间”的属地,先周时则称其为“北豳”。关于这一点,地方史志的记载有着很好的补证。
其次,从地方史志的记述看,甘肃省《通志》及有关县志即明确记载,从陕西旬邑县、邠县以北的甘肃庆阳地区之宁县、正宁、庆阳,乃至合水、华池都称为“北豳”。具体如《庆阳府志》记载:“庆阳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又云:“不窋,后稷之后,值厦德衰乱,窜居北豳,即今庆阳也。子鞠陶,孙公刘,俱历世为兹人。”《宁县志》记:“宁州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谓之北豳,有公刘邑。”又云:“公刘旧邑,在州西一里,周之先公刘居此,号北豳。《诗》云:‘乃积乃仓’,即此地也。”《正宁县志》记:“正宁县禹贡雍州之域,周为北豳地,公刘旧邑。”又云:“正宁为北豳旧地,公刘属邑。”所有这些史志的记载无不证明,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在“北豳”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一带的创业活动当是无疑的。
再次,从庆阳的先周文化遗存看,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在北豳即今庆阳的创业活动,不但史志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而且其活动的许多遗址至今犹留存于庆阳一带,又为史志的记载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据庆阳地区博物馆编辑的《庆阳地区文物概况》所载,经普查确认庆阳地区地下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多达三十几处,遍及先周时称为“北豳”的今庆阳、宁县、正宁、合水、华池、镇原及西峰市各地。之外,庆阳地区地表留存的关于周先祖不窋、鞠陶、公刘的文物遗迹和民间流传的关于他们的遗事尚有不少,今就其要者略列于兹:(1)不窋城,在庆阳县城北关,民间称为“皇城”。(2)不窋坟,在庆阳县城东山之顶,有残碑可证,民间称为“周老王墓”,今已僻为“周祖陵森林公园”。(3)庆城东10里有地名曰“花坡”, 传为“不窋遗园”。(4)庆城内有“鹅池洞”,保存尚完好, 传为不窋子鞠陶养鹅之所。(5)庆城东70里有“天子沟”,两侧深谷, 中央平坦,树木葱茏,传为鞠陶牧羊造林处。(6)庆城北30 里有“腴田数亩,号天子掌,人莫敢垦”,或称“公刘庄”,传为鞠陶子公刘出生之所。( 7)庆城西南3里有地名曰“西姬峪”,传为公刘族人之聚居地。(8)西峰市温泉乡有“公刘村”, 宁县焦村乡亦有“公刘村”, 传为公刘后裔聚居之地,至今仍有姬姓民户。(9 )宁县城西庙嘴坪有“公刘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传为公刘南迁中,从庆阳到宁州的留居中心。(10)今西峰市温泉乡有“公刘庙”,民间亦俗称“老公殿”,解放初陕西旬邑、邠县一带乡民每年于农历三月十八日(传为公刘生日)还专程赶到此处,与当地居民一起举行纪念公刘的“献牲”、“禋祭”、“赛社”活动。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公刘南迁至陕西旬邑、邠县一带之“豳”地或称“南豳”以前,确实在甘肃庆阳、宁县一带之古“北豳”渡过了长达3代人的一段艰苦创业的历程。
二
周族之先祖在北豳即今庆阳地区一带的创业活动,不但有大量的史志记载和文化遗迹作为证明,而且在《诗经·豳风·七月》诗中还得到了写真性的反映。只要我们把《豳风·七月》的内容与庆阳先周文化的遗风加以对照,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七月》诗中有些语句所表达的意义,是非用北豳一带的生产生活习俗加以解释而不能贴切的。试例说如下:
(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这是《七月》第一章中的句子,其中“无衣无褐”的“褐”,《郑笺》云:“毛布也。”基本意义是对的,但尚有欠确切处。其实,“褐”是庆阳地区一带最富传统的代表性御寒衣物。它的原料是羊毛或麻,用一种叫做“拨条”或“线杆”的工具捻成粗线,这种线不但线条粗,而且不很光滑,一些毛纤维外露,用它织成的布质地特别厚,叫褐布,有很好的御寒性能。褐,宁县土语读“huò”,至今宁县人还把类似的质地粗厚的纸叫“褐纸”。捻褐线的“拨条”或“线杆”,其形如倒“J”字,至今庆阳地区民间尚有实物,山区一些村民还偶为使用。 据此,“褐”的确切解释似应为:用毛或麻捻成粗线织成的质地较厚的粗布。“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就是说:“没有衣服也没有粗布,怎样才能度过这一冬呢?”
(二)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这是《七月》第三章中的句子。传统的解释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释“蚕月条桑”之“条”为“挑”的借字,义为挑选;“猗彼女桑”之“猗”为“掎”的借字,义为摘取。譬如高亨《诗经今注》言:“桑枝长得又高又大,用手摘不到桑叶,所以拿斧子砍下枝条摘取。”这种解释无异于“毁树采叶”,实为农夫所不取。尤其是地处西北的古北豳即今庆阳地区一带农民,最忌为采叶采果而毁坏树枝,可以说明这种解释是不妥的。另一种是把“条”释作“条理”之“条”,即修剪、修理;“猗”如上仍为“掎”的借字,义则释为牵引、拉着。于是认为前三句写男人修剪桑树,后一句写妇女拉着桑枝采桑叶。古今学者,多持此说。但据事理而言,凡剪枝修树总在初春树叶尚未生出之时,未见桑叶长大到已能摘才修树剪枝的,这是极普通的生产常识,故此说似亦难通。
细审文义并兼及农事常识和古豳地之风俗,我认为这四句诗只是写修剪桑树一件事。前三句意思是说:春天,养蚕的季节来临了,农夫们先要忙着修理桑树。怎样修理呢?拿圆孔的斧和方孔的戕,把那伸得又高又远的老枝荒条砍去。末句“猗彼女桑”,补充说明为什么砍掉荒枝:是要使那嫩桑枝茂盛地生长。稍有修树经验的人都明白,去老扶新,抑强扬弱,正是修剪树木的基本原理。因为老枝上的叶子老而小,新枝上的叶子则嫩而大,所以要去掉老枝,使新枝茂盛生长。《古谣谚》卷四十二《斧桑谚》即云:“远出强枝,当用阔刃锋利扁斧斫之,叶必复茂。谚曰:斧头自有一倍叶。”古北豳庆阳地区一带也有类似农谚云:“杈头生火,锄头生雨,斧头生叶”都可以作为拙说的力证。至于“猗彼女桑”之“猗”释作“茂”、“盛”,也是有词义根据的。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朱熹注云:“猗猗,美盛也。”又《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有实其猗。”《毛传》云:“实,满。猗,长盛也。”是说山上草木丛生,繁密茂盛。所以,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戴震语释“猗彼女桑”就说:“戴震读如有实其猗之猗,谓盛貌也。”准确地说应是“使之盛”。故“猗彼女桑”当译为:使那嫩桑枝茂盛地生长。
(三)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这是《七月》第五章中的句子。其中“穹窒熏鼠”,高亨《诗经今注》解释说:“穹,借为烘。窒,当作室,形近而误。此句是说用火烘干屋子,同时烟气把老鼠熏走。”其实这里似不存在“穹借为烘”和“窒当作室”的问题,而用的正是本字本义。“穹窒熏鼠”是古北豳民间采用的一种较原始的杀鼠方法。穹,即窟窿,就是鼠洞;窒,即窒息而死。冬季老鼠大都躲进了洞里,把柴草点着让烟进入鼠洞,使老鼠窒息而死,然后再用泥堵上洞口。这种杀鼠方法,在庆阳地区一带的山区村民中至今还有运用。至于“塞向墐户”,就更是庆阳一带人最常用的越冬措施。方法是用谷草、麦杆或将其织成帘子,塞挡窗户;又将谷草、麦杆摁成棒状,堵挡门缝;或用泥、破布条等涂抹门缝,以求室内保暖。这种御寒方法不但农村常见,解放后50年代,就连机关、学校也普遍运用。这也可以看作是古北豳先周生活遗俗的表现。
(四)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这是《七月》第六章中的句子。庆阳地区一带习惯上一直将阴历七月称为“瓜月”,八月称为“果月”,这与“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的描写正好互为印证。“八月断壶”的“壶”,借为瓠,即葫芦。《大雅·公刘》篇又有“酌之用匏”一句,《说文》:“匏,瓠也。”均为葫芦之类。葫芦在庆阳地区一带民间使用十分普遍。葫芦一破为二可以做成瓢,用之舀水;将葫芦颈处切断开口,可以做成罐状容器,用以盛装菜籽、杂物等;小葫芦做的容器,可以盛针线,叫“针葫芦”,等等。这也是古北豳先周生活遗俗与《七月》之描写相吻合的又一表现。
(五)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这也是《七月》第六章中的句子。“薪樗”一般都解释为拿臭椿树当柴烧,说是表现了农夫生活的困苦。如王力《古代汉语》:“薪樗,拿樗当柴。薪,用如动词。樗,臭椿。”其实,臭椿树本是一种上好的烧柴。据《辞海》载:“其高达20米,不裂,本质粗硬,种子可榨油。”因其含有油胶,干湿皆可着火,发木又快,故今之庆阳地区古北豳一带民间即称之为“柴王”。可见,说这里的“薪樗”是拿臭椿树当柴烧以表现农夫生活的困苦,似乎言不及意,不能说明问题。而且更欠妥的是,把“薪樗”解为拿臭椿树当柴烧,同下句的“食我农夫”显然搭配不当。“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是连文,“采荼”“食我农夫”是通顺的;但“薪樗”“食我农夫”,若按上面的解释,在语法、语义上就无论如何也讲不通了。
所以结合古北豳一带的生活习俗,我认为,“采荼薪樗”中的“荼”、“薪”、“樗”皆为“采”的宾语,都是拿来“食我农夫”的食物。
荼,苦菜,可食。薪,《说文》解为:“荛也。”荛,即指可烧之柴,也指可食之菜。《方言》第三曰:“荛,菜名,即芜菁。”芜菁庆阳地区一带俗称“蔓菁”,似萝卜,有甜味,根和叶常作饲料,亦可食用。这里的“薪”正是指此。《孟子·公孙丑下》:“有采薪之忧。”是说生活贫困,有挖野菜吃的忧愁。此处“采薪”搭配组词,正与《七月》句相同。樗,臭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椿树,前冠一“臭”字者,是为了同叶可作香菜的香椿树相区别。香椿树的嫩叶,是庆阳地区一带经常食用的很普通的蔬菜,至今市场上仍常有出售。而椿树叶始生的嫩芽可以养蚕,称作“樗蚕”,《辞海》即有此词条;灾年亦充作救荒植物,供人食用。《诗·小雅·我行其野》第一章:“我行其野,敝芾其樗。”第二章:“我行其野,言采其蓫。”第三章:“我行其野,言采其葍。”蓫,又名羊蹄菜,可煮食。葍,野菜名,可蒸食。此诗中将“樗”、“蓫”、“葍”对举,可证樗之嫩叶亦为当时农夫采食之物。并且孔颖达疏《毛诗》也说:“言我行适于野,采可食之菜,唯得敝芾然樗之恶叶。”又说:“《正义》曰樗是木也。言敝芾始生,谓叶在枝条始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可见,我们所引《小雅·我行其野》三章的句义是:在灾荒之年,诗作者来到野外本想采一些如“蓫”、“葍”之类好一点的野菜,结果却很难找到,只能采一些始生于嫩枝的椿树叶充饥。这与《七月》诗“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的情况完全相同。通常香椿叶可吃,椿树叶本不能吃,现在却采来同苦菜、芜菁一起“食我农夫”,这才真正地显出其食物的粗劣不堪。这样解释,不但本句连贯,词义有据,语法通顺,而且有《七月》之产地庆阳地区即古北豳一带的民俗为依据,又同这章诗前三句“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等反复叙述食物的内容取得了一致,整个诗意也就讲通了。
(六)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这是《七月》第七章中的句子,具体表述当时粮食作物种类的多样。其中“黍稷”与“禾麻菽麦”义甚明确,唯“重穋”指何种作物,历来未得确解。高亨《诗经今注》言:“重,穋,都是谷名。重,大概是秫,今称高梁;穋,大概是旱稻,今称粳子。”从高亨先生这里用“大概”一词猜度看,其不确定性是明显的。而且,本诗第六章即有“十月获稻”句,故说“穋”是“稻”,似不可能。 郑玄《毛诗笺》引郑司农词则说:“后种先熟谓之穋。”根据庆阳地区一带的作物特点和称谓习俗,结合郑司农的解释,我认为这里的“重穋”应是指复种的小糜子、小谷子。庆阳地区一带种糜谷有正茬和回茬之分。正茬糜子和谷子生长期长,均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但在古历五月收获冬小麦后,在腾空的小麦地里还可复种生长期较短的小谷子、小糜子,俗称回茬,又称复种。复与重义同;而这种糜、谷,生长60天即可成熟,故也叫“60日糜子”、“60日谷”,是以秋补夏的好品种,而且正符合郑司农所谓“后种先熟”的生长特点。因此,我认为《七月》中的“黍稷重穋”一句,“黍稷”分别指正茬糜子、正茬谷;“重穋”,则指复种的回茬糜子、回茬谷。所以说,这两句诗既见当时作物种类的丰富,又见其种植形式的多样。
其他如《七月》篇采用的按月令顺序歌咏事物的民歌形式;“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反映的直到阴历十月才打碾庄稼的“碾冻场”的习俗;“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所表现的送饭到田间地头的习俗等等,都可以在庆阳地区一带生产、生活的民风民俗中得到印证。
三
综上,《诗经·豳风》的涵盖地域,应该包括今陕西省旬邑县、邠县一带之古豳地(或称南豳)和今甘肃省庆阳县、宁县、正宁县一带之古北豳的广大区域,而《豳风·七月》则是对包括古北豳在内的豳地生产生活状况的一种风俗写真,这从庆阳地区一带至今留存的先周文化的遗迹遗俗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这同时对于我们进一步从历史、民俗、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有机结合上去研究《诗经》,无疑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