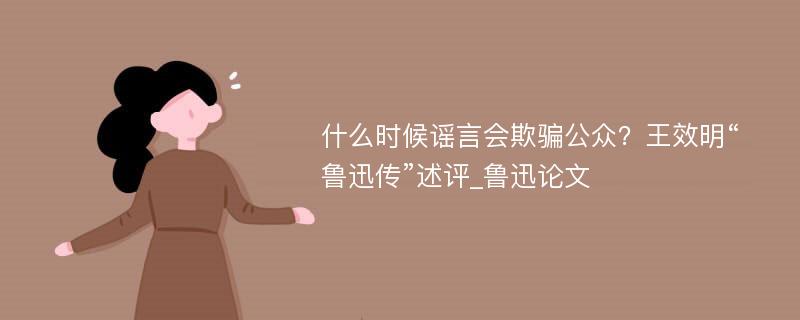
谣言惑众几时休——评王晓明《鲁迅传》的一条注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谣言惑众论文,鲁迅论文,注释论文,几时休论文,王晓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众多的鲁迅传记中,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无疑是极为出色的一本。这部别开生面、重在凸现鲁迅“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对传主的心理分析和作者的人生感悟融为一体,愤激和悲哀的情调贯穿全书,流畅的文笔传达出深邃的思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无怪乎在知识界尤其是青年读者中颇受欢迎。但是,正如张梦阳所指出的,“王著有很突出的优点,也有很明显的偏颇”。他甚至强调,“对这本鲁迅传的偏颇之处进行纠正和批评,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了”。(注: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宏观反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4页。)其实张梦阳的批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是否得当还可以讨论,我也并不完全赞同。然而,王著有一处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地方,张梦阳却没有注意到,我倒以为比他所说的偏颇更应该及时纠正,这就是第八章《小成功和大绝望》的注释第13条,即对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信的注释,全文如下:
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75、73页。)
千家驹是在造谣,想用谣言这“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来损害鲁迅,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谣言本应止于智者,但是非常遗憾,王晓明却很不明智地充当了谣言的传播者。对于周作人和鲁迅决裂一事,当事人虽没有直接说过什么,但知情人并非像王著说的“都回避谈论”,许寿裳、郁达夫、俞芳、许广平、周建人等都在回忆文章里(还有章川岛在与人谈话里)具体谈论了此事并且明确表示了态度。这些材料,陈漱渝的文章《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作了详尽的叙述和考证,已成为学界共识。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无法推翻他所使用和依据的史料。例如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的一段话,是最具权威性的,连周作人在晚年与友人通信中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为事实: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史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注: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8页。)
然而,奇怪的是,王著对所有这些知情者言之凿凿的回忆材料不但只字不提,还要十分肯定地写道:“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75、73页。)不对,应该说,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王著的论述方式向读者“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这方向与所有知情者在回忆材料中表明的基本一致的态度恰恰相反。于是,千家驹所造的谣言就成了王著提供给读者用来解释兄弟失和原因的唯一材料,以“暗示”方式对读者造成明显的误导。虽然只是一条注释,似乎是无关紧要,但谣言借王著广泛传播,淆乱历史,迷惑读者,对传主和作传者双方形象的损害却不可低估。古人云:《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我不忍看到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竟使用谣言作材料,更不能容忍这种手段拙劣品质卑劣的谣言因此而继续传播贻误青年,所以不得不写这篇并非多余的辟谣文章。
二
造谣者文章的首段开宗明义,反对中共神化鲁迅:
在《明报月刊》十一月号上拜读李欧梵、刘再复两位在东京大学“鲁迅和异文化接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深有同感。中共把鲁迅作为一个“神”来膜拜,完全是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是别有用心的。老实说,鲁迅如果在解放后还活着的话,在一九五七年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右派”,或者有如五十年代批胡适一样,要掀起一个大批鲁迅思想的运动。好在他死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他就可以与雷锋一样,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并用来作为“整人”的武器了。鲁迅九泉有知,也一定要提出抗议的。(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这段话的偏颇和武断自不待言,但反对“神化”鲁迅,不把鲁迅当成“神”而把他作为人来描写来研究,都是对的。然而有一条基本的学术原则必须遵守,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造谣,否则,“鲁迅九泉有知,也一定要提出抗议的”。可是,这篇“也谈鲁迅研究”的文章,却是以造谣言作为主要论据,来解释鲁迅在处理与周作人夫妇的关系中“难言之隐衷”,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鲁迅,真实的鲁迅”。(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鲁迅生前说过:“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注:鲁迅:《准风月谈·归厚》。)鲁迅绝对不会料到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竟有人造出他和羽太信子是夫妇关系的谣言,而且造谣者和传谣者还都是极有才能的文人学者。论证这谣言之伪,固然需要多花些笔墨,但这项工作是不能不做的。
王著作为注释引用那段谣言时有删节,为便于分析,我先恢复它的原貌,再与读者奇文共赏,看看造谣者的手段:
我后来才间接听到与鲁迅兄弟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讲,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这在日记中屡有记载。例如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记:“上午收羽太家信,十七日东京发”。九月三日记:“上午至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氏信并银二十圆。”十一月二十一日记:“午后赴保商银行易日本币,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日银五十圆。”如此日记,不一而足。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第一,从全文叙述的时间判断,这里的“后来”指的是1976年以后。与鲁迅兄弟相熟悉又了解日本留学时情况的莫过于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蒋抑卮数人,而他们从来没造过鲁迅的谣,且都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去世。九十年代的造谣者说“间接听到”“一位老朋友”讲,却不说出这位老朋友的姓名,用故意含混的模糊语言掩饰自己的造谣。其实说鲁迅与日本女人同居的谣言早在鲁迅留学时就已有人造过,鲁迅的母亲就是听到了这种谣言,于是声称有病催鲁迅回家,令其与朱安成婚的。这一点,多种鲁迅传记和史料考据文章都有叙述,文字详略不一,情节基本相同。例如,1945年,林辰在《鲁迅的婚姻生活》一文里就考证过谣言的内容,说:“这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不知怎地,他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并已生了孩子,有人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注:林辰:《鲁迅事迹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新1版,第92页。)90年代,几乎与造谣者的文章同时,林贤治在《人间鲁迅》文学传记里这样描述谣言的起因:“从仙台返回不久,有一次,周树人同许寿裳一起去逛公园,途中碰到一个日本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背着一个小孩,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孩,拖泥带水地走着。周树人马上跑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的小孩抱了过来。也许被哪一位同乡的留学生看见了,事情便演变成了这样一种流言:周树人同日本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他常常携带儿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呢。”(注:林贤治:《人间鲁迅》上册,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1、199页。)林著含有想象成分,但是合情合理,与林辰的考据论文是一致的。只是当年口耳相传的流言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造谣的人也无从查考,而新造的谣言却堂而皇之地载入了颇有影响的期刊和著作,真不知道这究竟是进步呢还是倒退。
第二,造谣者说“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7月与朱安结婚后,即与周作人同赴日本,几经搬迁,于1909年初同时认识羽太信子,很快周作人与信子恋爱,1909年夏结婚。根据鲁迅的文章书信,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以及王士菁、朱正、林贤治、陈漱渝等人所作的传记,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居住地点及房舍可以依次排列如下:
1902年4月初,从上海到达横滨,住麴町区平河町四丁目“三桥旅馆”。4月中,进东京弘文学院,在牛入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住学生寝室,曾住公寓“东樱馆”。
1904年9月,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寓居当地包办伙食住宿的小客店,先住片平町五十二番地佐藤屋,后迁土樋町一百五十四番地宫川方。
1906年3月,从仙台退学返东京,住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公寓,学籍挂在一所德语学校。7月,回国结婚后,与周作人同赴东京,再住伏见馆。
1907年春,与周作人移居本乡区东竹町“中越馆”。
1908年4月,应许寿裳之招,周氏兄弟迁往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一所豪宅,同居者还有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因署名“伍舍”。
1909年初,钱朱二人提议散伙,退出伍舍,为减轻负担,鲁迅与周作人、许寿裳迁居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公寓。是年春,许寿裳回国。8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鲁迅回国。
所有的史料都没有鲁迅曾与日本女人婚恋的记载,而在最后迁居丙字十九号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何许人也?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对她不作任何说明,还说周作人也“没有留下一个字”,因此“只能暂付阙如”。(注: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林贤治在《人间鲁迅》里只说她是“公寓里的姑娘”。(注:林贤治:《人间鲁迅》上册,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1、199页。)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里是这样写的:
周作人和鲁迅、许寿裳一起,于1908年冬(应为1909年初——引者注)住进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有一位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为住客们办理伙食。她叫羽太信子。过去有些记载说她是房东的女儿。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指出:这种说法不对。羽太信子是作为“供应饭食的人”也住进丙字十九号的。用中国通行说法来说,她是小厨娘一类的角色吧。她对于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有好感,慢慢地他们就亲近起来。
羽太信子的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没有正式的职业。她的弟弟重久、妹妹芳子、福子,都还在少年、童年时代。这是一个贫困、勤劳、人口众多的家庭。(注: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8页。)
马蹄疾在《鲁迅生活中的女性》一书中有一节《“天威莫测”的羽太信子》,介绍的情况与倪著大致相同,说羽太信子“幼年曾受过义务小学教育”,是丙字十九号住宅的房东雇用的一名“侍女”,为鲁迅等三名房客做饭的。(注: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我很难理解有些人为什么竟然会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上述历史事实,公然无所顾忌地制造和传播鲁迅与羽太信子是夫妇关系这样离奇荒诞的谣言。
第三,造谣者把“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作为鲁迅与羽太是夫妇关系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是的,鲁迅在1909年8月返国,就是“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注:许寿裳:《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8页。)从此直至1919年12月全家搬进八道湾交由羽太信子当家,他不仅负担羽太信子的生活费用(但从来没有单独给羽太信子寄过钱),而且在1911年7月由于他的催促信子随周作人回中国绍兴的婆家后,还按月给日本东京的羽太家寄钱帮助信子的娘家人。鲁迅日记对此有详细记载,造谣者文章中所引的几则日记并不错,怪就怪在把“寄羽太家信”即“给羽太家寄信”曲意解释成“称羽太为‘家信’”,实在用心良苦,连语法常识都不顾了。在鲁迅日记中,“寄羽太家信”有时也写“寄东京羽太家信”或“寄羽太氏信”、“寄羽太宅信”,句式和意思都一样,一般寄钱同时寄信,多写“寄羽太家信并银××元”,也经常;只寄钱不寄信,一般写“寄羽太家××元”,或“寄羽太家泉××元”,有时还写“寄羽太家月用钱××元”,“银”与“泉”、“钱”通用,“元”字常常省略,只寄信不寄钱的情况极少。鲁迅和羽太家并无感情,他自己忍受着无爱婚姻的痛苦,希望弟弟们(1914年2月周建人也和羽太芳子在绍兴结婚)爱情美满生活幸福,他对兹的友爱和资助真正达到了无私的地步。当然这也体现了他在父亲死后作为长史对家庭的责任感,他牺牲自己的利益,尽力维持和供养母亲与三兄弟及眷属的大家庭,对羽太信子的自私、乖戾、挥霍,也尽量宽容忍让,做到仁至义尽。正如他说柔石的,“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注: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他在厦门与许广平通信中就谈到自己竭力帮助亲戚本家结果反而遭致怨恨的痛苦教训,晚年在与友人通信中感叹:“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注:鲁迅:《致台静农320605》,《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89页。)鲁迅把弟媳妇娘家的生活也要“背起来”,未免管得太宽,自讨苦吃,终于不堪重负,大家庭于是破裂,自己被周作人夫妇赶出八道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所背负的传统道德的沉重和性格与行为的软弱,但不能像造谣者那样,据此推断“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不同寻常”。(注: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香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三
鲁迅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伟人不是庸人。他的思想性格和为人处世上都有弱点,表现于家庭问题尤其突出,他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自食其果。我们应该正视事实,学理性地研究,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抓住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关系散布流言,不过是暴露出他们的灵魂深处即意识的深层仍然存在着禁欲主义的反人性的传统文化心理,即“万恶淫为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从这种传统心理和观念出发,要败坏一个人的名声,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在与性有关的私生活上做文章,找出对方“生活作风”即“道德品质”的污点,或用比较“现代”的说法曰“人性的弱点”,加以渲染,重者可使之臭不可闻,轻者也使其形象受损。近些年海内外书刊上贬损鲁迅的言论,有不少就是围绕鲁迅与异性的关系,明明暗暗地指认他有问题。“暗示”的这里且不说,公开造谣的也不止前述的一例。
1989年,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系沈卫威在河南开封出版的《心理学探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分析比较三人的异同,就制造了鲁迅和羽太信子曾是情人关系的谣言。这更是一段奇文,编织故事的手段还要高明一些:
他的第一爱是发生在母亲的制约力量难以完全控制的日本,这位情人恰恰又是他后来的弟媳妇(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阴差阳错——正当他和日本女郎羽太信子热恋时,母亲召他回家乡与朱安结婚,尔后他带弟弟周作人去日本,于是羽太信子在失去鲁迅的情况下,和周作人结为夫妻。周作人开始并不知道此事,但这却使鲁迅的内心不能平静——痛苦的折磨。1925年,周作人知道了此事,于是,兄弟的手足之情就此一刀两断。鲁迅原来同母亲、朱安、周作人夫妇共住一处,但此事由羽太信子泄露后,兄弟彼此难堪,加上“女师大风潮”后北洋军阀的通缉,他便逃出北平,最后在上海定居。这一所谓的阴差阳错,又导致鲁迅的心境更坏:阴冷、多疑、尖酸、刻薄。同时,由爱着一个漂亮的东洋知识女性坠落到与一个不识字的瘦小的小脚村姑结婚,便使他产生“心理阳萎”,在无法克服的“儿子与情人”这一情结上又加上了带有道德伦理与情爱冲突、人的正常的价值和应有的爱欲失落的心理重负。所以说鲁迅一生是最痛苦的。(注:沈卫威:《“儿子与情人”——鲁迅、胡适、茅盾婚恋心态与情结阐释》,原载开封《心理学探新》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
全部推理是以造谣为前提,其中叙事的错讹显而易见,无须一一指出。这种把谣言和真话混杂在一起的文章,使人读后,糊涂人把谣言也当成真话接受,明白人则对其整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用鲁迅的话说,“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注:见王福湘:《关于周作人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如此“权威”迷信不得》,《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4期。)我在几年前曾对此文提出批评,(22)可是没有引起反应。而造谣者的文章则被有影响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造谣者也将荣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如果说沈卫威谣言的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千家驹的谣言则随着王晓明的《鲁迅传》一版再版,多次印刷,传遍全国并且翻译到国外,至今已延续十年之久,还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造谣的手段、内容和结论一脉相承,成前后呼应之势,可见并非偶然,也不是孤立的。这种严重背离学术规范的现象,说明我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的思想混乱风气堕落到了何等程度,实质上,这也是一种学术腐败。
在鲁迅研究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不同的见解是正常的。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有一种声音,表面上没有不同见解,思想高度统一,而实际上是不同见解遭到压制不能发表不敢发表,那才是不正常的。学术上应该有百家争鸣的自由,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在争鸣中才能发展和进步。现在,压制不同意见的问题不能说已经彻底解决,但是,滥用话语权力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也应引起重视。学术研究只能从事实出发,学术见解只能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说真话不说假话,讲事实不准造谣,应该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即人人必须遵守的底线。如果连这一条底线都没有,说起话来真真假假,那就无法展开正常的学术争鸣,连对话都难以进行。这不是学术见解问题,而是学术品质问题,不是水平高低问题,而是态度真伪问题。然而,从本文所举证的事实来看,这条底线已被践踏得不复存在。造谣者和传谣者乃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博士、导师,以及享有盛誉的刊物和出版社,而且谣言一经造出,即畅通无阻,在读者中颇有市场。归根到底,这种混乱和堕落,也是一种源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文化现象。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说过:“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这一类事实,古来很多,鬼崇著作却都消灭了。不肖子孙没有悟,还是层出不穷的做。不知他们做了以后,自己可也觉得无价值么。如果觉得,实在劣得可怜。如果不觉,又实在昏得可怕。”(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我不能不为这些不肖子孙感到悲哀。
近些年造谣行为之所以在学术界一再发生,跟学术界缺乏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有关。学术界似乎划分成不同的阶层和大大小小的圈子,在同一阶层和圈子内,学者文人们自说自话,互不争论,一团和气,互不得罪,相互之间多有你好我好的庸俗吹捧,少有指名道姓的严肃批评。像鲁迅那样严厉地解剖自己,发现错误即公开纠正,这种风范在当今的学界名流身上更是很难见到了。现在许多人热衷于阐扬胡适的自由主义,却不注意继承他在学术上的大家风范。当年与鲁迅政治和学术见解相左的胡适,在与鲁迅的学术关系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很值得今人效法。鲁迅逝世后,苏雪林致信胡适,利用胡适与鲁迅的矛盾,极力颂胡而骂鲁,想让胡适支持她发表“反鲁文字”。但胡适不但没有支持她,而且责备她对鲁迅的漫骂“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他甚至为鲁迅辩诬,希望十年前曾造谣诬蔑鲁迅的陈西滢(通伯)此时写文章公开认错。胡适说: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之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注: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通信)》,《围剿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159页。)
胡适这段文字,真可以垂范后世,令不肖子孙应该知道惭愧。所谓“gentleman的臭架子”,就是要讲究堂堂正正的学术规范,光明磊落的学理精神。有此规范和精神才能造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我这篇反对造谣的文章也能如造谣文章一样不受阻碍地问世,如果沈卫威能够悔其少作承认当年造谣的荒唐,如果王晓明在他的《鲁迅传》再次印刷时能够删掉那段谣言并声明改正错注,同时换上许寿裳或郁达夫等人的解释,如果今后学界中人能够见谣言则群起而攻之,迫使造谣者销声匿迹,……我不敢再奢望了,但愿这些“如果”都能成为事实,不肖子孙就算是有悟了。
标签:鲁迅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传论文; 王晓明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人间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许寿裳论文; 羽太信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