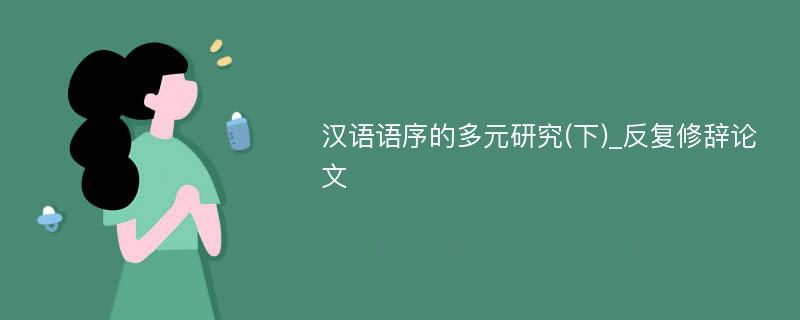
汉语语序的多面考察(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序论文,汉语论文,多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语序的逻辑考察
3.1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思维依附语言进行, 因而对语序(不论是句内语序还是句际语序)的考察都不能缺少逻辑的考察。可以这样认为,汉语语序不仅仅是汉人的认知模式的一种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汉人思维模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汉语语序是客观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汉人对这些逻辑关系的主观认识在汉语中的反映。
3.2 一方面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另一方面是事多端而言之多方,因而语言单位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逻辑关系,在语序中都相应地有反映。比如说,“a太阳出来了,b黑夜过去了。 ”(话剧《日出》)a与b是平行关系;“a自然科学的皇冠是数学,b数学的皇冠是数论,c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北京晚报》1996.3.22)abc是递进关系;“a 刘胡兰用忿怒和鄙视的眼光对着敌人。b 接着,她昂然走向刑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a与b是接续关系;“a 老李是保定人,b 老王是邢台人,c 老张是石家庄人,d 他们三位都是河北人。”a b c与d是先分后总的总分关系;“a 因为昨天下大雨,b 我没出门。”a与b是因果关系。所有这些语序,都反映出一定的逻辑理据。
3.3 语序不可先后倒换, 往往是受原语序所体现的逻辑关系决定的。那些已明确表明语序排列先后的逻辑关系的不能换序,如按音序排列的不能换序。问话在前,答话在后,本体在前,注释在后,整体在前,从整体中特别提出的部分在后(如“a 全世界人民b 首先是中国人民”),以及如实反映说话人表达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变化的语序是原想法在前,改变的想法在后(如“a 他已经病了三天了,b 不,c 应该说他已经三天没去上班了”),都是不可变换语序的,其理据也在逻辑中。
当然,有的语序是可以变换的,“a 太阳出来了,b 黑夜过去了。”就可以换成b c语序, 那是因为“太阳出来了”意味着“黑夜过去了”,同样,“黑夜过去了”也意味着“太阳出来了”,变换了语序并不改变平行关系。总分关系的语序作先分后总或先总后分也都是可以的。这都具有逻辑理据。
如果以修辞格为考察对象,则可以看到有的修辞格其内部语序是不可变换的。以起兴而言,语序是起兴在前,本体在后,如“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起了共产党。”(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睢》)起兴是借用与所咏本事或题旨相关的其他事物来发端的一种修辞格,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26〕“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27〕可见起兴在前,本体在后的语序是必然的逻辑顺序。以顶真格而言,语序是本体在前,接体在后。如“小城有a河,b河边有c柳,d柳外有人家”,“有山就a有水,b有水就c 有脉,d有脉就e有苗”(杨朔《香山红叶》)。a对b来说是本体,在前, b是接体,在后,b对c来说是本体,在前,c是接体,在后, 依次蝉联而下。“顶真格的逻辑思路是:逻辑上的接续关系,要求用蝉联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前项与后项之间又存在由A及B,再由B及C,再由C及D的关系,即接续关系〔28〕。”它表述了事物的状态或性质的理。这种语序不可变换,是理所当然的。以连贯喻而言,语序是本体在前,继体在后。如“a重庆的台阶特别多,它们好像是数不尽的钢琴键。b勤劳的山城居民,祖祖辈辈踏着这琴键,演奏着生活的交响乐”(陈汉元《从宜宾到重庆》)。连贯喻“从语言形式上说,是几个比喻的连贯运用,而从逻辑思路上说,则是在对前一个思维对象的思考上引发出对一个新的思维对象的思考来。所以后一个比喻衔接前一个比喻,是完全合乎思维活动的规律的”。〔29〕这也就是说,如果变换语序为前一个比喻衔接后一个比喻,就完全不合乎思维活动的规律了。所以连贯喻的语序也是不能变换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客观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有自己的主观认识,客观事物本身,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因而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也就有了不同的语序。从这个角度观察和表述,其语序是合乎逻辑顺序的,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表述,其语序也同样是合乎逻辑顺序的。比如表述时间,其语序既可以适应由小数到大数的逻辑顺序, 如12 3 4 5 6 7 8 9 10,也可以适应由大数到小数的逻辑顺序即所谓倒计时,如10 9 8 7 6 5 4 3 2 1;其语序既可以适应先过去后现在的逻辑顺序,如“a 饮马早闻临渭北,b 射雕今欲过山东”(吴融诗),也可以适应先现在后过去的逻辑顺序,如“a 今日六军同驻马,b 当时七夕笑牵牛”(李商隐诗)。再如表述空间,语序既可以由此处及彼处如“即从a 巴峡穿b 巫峡”,也可以由彼处及此处如“即从b 巫峡穿a 巴峡”,如果是溯长江而上,这种语序也是合乎逻辑顺序的。以事理的表述而言,语序同样是可以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的,如“由a弱变b强”“由b强变a弱”之类。
3.4 语序的变换,有的还涉及逻辑推理和论证。 推理和论证依存于两个以上的语句,涉及两个语句的组合和语序问题,因而语序的变换,有可能导致逻辑关系的改变。比如因果关系的主从句,如果表因的从句在前,表果的主句在后,是一个由因推果的亦即以因为论据推出结论的推理,如果表果的主句在前,表因的从句在后,就变为一个由果溯因的亦即以果为论题以因为论据的论证了。所以“因为昨天下大雨,他没出门。磌他没出门,因为昨天下大雨”。其语序的变换,实际上是反映了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关系的改变的。从逻辑上说,直言判断的换位,就是把直言判断的主项换成谓项,把谓项换成主项,但不改变主项、谓项的联系,也不扩大主项、谓项的外延,从而形成一个新判断的推理。比如“有些文艺评论家是作家(SlP)”, 可以换位作“有些作家是文艺评论家(PlS)”,而这样的换位,从语序来说,便是语序变换了。
如果联系到修辞格来考察,则回环格就是以判断换位构成一个直接推理为其逻辑基础的。如“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互喻格则是以对称关系推理为逻辑基础构成的,如“去岁荆南a 梅似雪,今年蓟北b 雪如梅”(张说诗)。
当然,由于语言和逻辑到底分属不同的范畴,所以语序的改变未必和逻辑相吻合,某些因受语言习惯的影响和语言内部规律的制约而不合乎逻辑的语序也是有的,比如人们只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这是违反季节顺序的逻辑的),而不说“春困夏打盹秋乏”(这是合乎季节顺序的逻辑的)之类。
4.语序的语用考察
4.1 作为抽象系统的语言本身和语言的运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交际中运用的语言固然是以抽象系统的语言作基础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抽象系统的语言本身。从语用学来说,它首先关心的是语言的运用,而不是语言本身,是语言的功能而不是语言的结构,是语境意义而不是抽象系统的语句本身所负载的意义。因为语言的结构随着语用有不同的分析,甚至产生新的功能,同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有所不同。这些都是话语的语用特点,对语序的语用特点的考察,就是语序的语用考察。
4.2.1 语言运用中,信息焦点直接影响到语言单位的排列次序。 从语用学看来,话语在交际过程中,并不是任何一个语言单位都具有信息性,只有那些为共同的背景知识增添的信息的语言单位才具有信息性。比如弟弟对母亲说:“姐姐考上北京大学了。”“姐姐”这个语言单位传递的就是“弟弟”和“母亲”共有的背景知识,只是一种已知信息,没有信息性,因为“姐姐”是何许人也,“弟弟”和“母亲”都是早就心里明白了的,对他们来说,“考上北京大学了”才是新的信息。
人们说话,总是为了传递新的信息,人们听话总是希望接收到新的信息。已知信息一般不能成为交际的兴趣中心,新的信息或者说意义内容中心才是交际兴趣的中心。“弟弟”和“母亲”的兴趣中心不在“姐姐”其人,而在她“考上北京大学了”是显而易见的。而所谓焦点信息,也就是话语中的新的信息或者说语义内容中心。
按照通常说法,汉语话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倾向于由旧到新,因而焦点信息通常排在句末或句的后半部,可以称之为句末焦点信息或常规焦点。
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则如下话语的语言单位的序列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①“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有一次,斯大林同志去剧院看演出,扮演斯大林的演员同志演得十分出色,斯大林同志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您演得真好,我真像您啊!’”(转引自潘晓东《1+2≠2+1》,《修辞学习》1984年第2 期)原引用者解释说:“斯大林不说‘您真像我’,表示谦逊。”我们说,从表达效果说,这看法是不错的,但没有说出采用这样的语序之所以能够表示谦逊的原因。其实,关键之处是信息焦点发生了变化:“你真像我”,“我”是句末信息焦点,是语义内容中心,可以理解为以我为准;“我真像您”则“您”是句末焦点信息,是语义内容中心,可以理解为以您为准。不以我为准而以您为准的表达,自然也就含有谦逊之意了。
②“食在广州”。这是广州酒楼饭店常用的广告语言,目的在夸耀广州是吃的好地方以招徕顾客。焦点信息在“在广州”,要突出的信息是“在广州”,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如果变换语序作“在广州食”,则句末焦点信息不再是“在广州”,也就收不到用美食著名的广州来招徕顾客的广告效应了。他如“满意在北京”、“我们相会在龙年”(龙年来到前夕用语)、“我们相识在前线”等同此,可类推。
③“平儿笑道:‘a 他是谁?b 谁是他?’晴雯听了,把脸飞红了。”(《红楼梦》63回)“a 他是谁”的句末焦点信息是“谁”。问话人的兴趣中心是“谁”,要求回答这个“谁”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b 谁是他?”的句末焦点信息是“他”,问话人的兴趣中心是“他”,要求回答他是在一定范围内许多人中的哪一个?〔30〕平儿用a b 两种语序表达不同的焦点信息,左右夹攻,所以问得晴雯把脸飞红了。
④“闻诸先辈云:平江李次青元度本书生,不知兵。曾国藩令其将兵作战,屡战屡败。国藩大怒,拟奏文劾之,有‘屡战屡败’语。曾幕中有为李缓颊者,倒为‘屡败屡战’,意便大异。”(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38页)杨先生指出“意便大异”是对的,但没有说出意所以能大异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语序变换使句末焦点信息不同了。“屡战屡败”,句末焦点信息在“屡败”,表明以“屡败”告终,因而如要加上后续句可以用“十分悲惨”一类语句;“屡败屡战”,句末焦点信息在“屡战”,表明以“屡战”告终,因而如要加上后续句可以用“十分顽强”一类语句。他如“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和“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因此,可类推。
⑤若干年前,电视台播出上海某个代表团的团长答外国记者问实况。记者问:“上海肝炎患者29万,卫生检疫太差,上海政府负什么责任?”团长回答说:“上海市长作了努力。a 上海肝炎疫情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我们正在吸取教训。b 上海肝炎疫情在这么短时间内控制住,没有引起严重第二次感染,是很不容易的。”如果a b 两个复句调换语序,这段话就由采取了有效措施告终变为吸取教训告终了。这是焦点信息在句际语序上的反映。
⑥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杨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钱钟书《谈艺录》324页)这也是“一篇全在句末”之意。〔31 〕如果从焦点信息原则加以解释,这也是焦点信息在句际语序上的反映。
4.2.2 按汉语寄信写地址姓名惯例,是以国名、省市、街道、 单位、单位内某一部门、收信人姓名为序的。英语书写顺序与此恰恰相反。就汉语来说,这种写法正是贯彻了汉语句末焦点信息原则的。这原则运用到收信人是十分恰当的,因为放在最后的姓名,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中心,他最需要知道的是这封信是不是寄给他的,至于国名、省市、街道、单位等等,他无需关心,而且全是已知信息。而对邮递员来说,把信送到单位就完成任务,因而他最感兴趣的中心,不是作为焦点信息的人名,也不是单位内的某一部门,而是单位名称。对收信单位的收发室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把来信分发给单位内的各个部门,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中心,也不是国名、省市、街道、单位这些已知信息,也不是作为句末焦点信息的收信人的姓名,而是单位内的各个部门的名称。这说明,所谓焦点信息在句末,是以一般情况而言的。在不同的语用环境中,焦点信息在原语序不变换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转移的。信息接收者在接收信息时,对信息的理解是可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的。
4.3 从语序上说, 汉语焦点信息在句末和汉语的“话题——述题”结构有一致性,因为作为“话题”的语言单位表示已知信息,作为“述题”的语言单位表示新的信息,二者都是由旧信息到新信息的排列顺序。比如“我知道这件事”,从焦点信息在句末的原则看,“这件事”是焦点信息;从“话题——述题”结构看,“这件事”是“述题”。不过,如果变换语序作“这件事我知道”,则从焦点信息在句末的原则看,“这件事”不再是焦点信息,变成已知信息了;从“话题——述题”结构看,“这件事”不再是“述题”,而成了“话题”了。二者的语序在由旧信息到新信息的排列顺序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
从语用上说,“我知道这件事”和“这件事我知道”,二者由于语序不同,各有用场。前者是把“这件事”作为句末焦点信息即常规信息来处理的,后者是把“这件事”作为话题,作为凸显语序来处理。凸显语序是依据说话人的兴趣、态度、目的而采取的打破常规语序的语序。表达常规信息的常规语序一旦改变为凸显语序,就立即突出表明了语序所负载的信息中心的转移、说话人兴趣中心的所在和他所希企达到的交际目的。比如说,汉语主从复句的常规语序是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但是为了凸显主句,可以采取主句在前,从句在后的凸显语序。一则售房广告使用了这种凸显语序:“北京力鸿花园64640216 a请不要拨通这部电话——b 如果您有更好的选择。”(《北京晚报》1996.11.8)这则广告明明告知了电话号码,却紧接着叫人不要打电话来,颇有点语不惊人誓不罢休的味道。目的是采取以退为进的说法,招徕买主。如果改用ba的常规语序,就不能凸显a,减少了出语惊人,以退为进的语用效果了。
5.语序的修辞考察
5.1 修辞,广义地说,也属语用范畴。 修辞学与语用学交叉之处,在于二者都以信息语用特征为研究对象,都关心信息的传递和接收准确无误。不过,语用更侧重于话语信息的有效传递的必要条件,修辞,尤其是积极修辞则更侧重于话语信息传递的充足条件,要求在交际中收到最好的表达效果。因而语序的语用的考察不能完全代替语序的修辞的考察。
修辞的语序考察着重考察语序的修辞结构形式和语序的表达功能及其表达效果。语序修辞是句法修辞的一部分,它有时涉及词汇修辞(参看0.5.2)和语音修辞(参看0.5.3),同篇章修辞有密切关系,也是语体特征和风格特征借以体现的一种修辞手段。
语序修辞是以常规语序即自然语序为基础的,但同样用得着凸显语序即特异语序。对常规语序和凸显语序的运用是语序修辞的主要内容,而其运用方式大致包括选用和创新两种。所谓选用,是从现有的语序(包括常规语序和凸显语序)中选用,如从“状语中心语”和“中心语状语”的语序中选用一种。所谓创新,是临时创造出一种为现有语序所没有的语序,目的是适应修辞的特殊需要。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按现有语序表达,本应作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的,这是杜甫在语序上的创新。为的是适应修辞的特殊需要。这特殊需要,周振甫说得很清楚:“原来杜甫这诗是写回忆长安景物,他要强调京里景物的美好,说那里的香稻不是一般的稻,是鹦鹉啄余的稻;那里的碧梧不是一般的梧桐,是凤凰栖老的梧桐,所以这样造句。就是‘香稻——鹦鹉啄余粒,碧梧——凤凰栖老枝’,采用描写句,把重点放在香稻和碧梧上,是侧重的写法。要是改成“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成为叙述句,叙述鹦鹉凤凰的动作,重点完全不同了。”〔32〕而创新之处,在于整个打乱了汉语语序的本有结构。按语法常规,我们只能这样析句:“香稻”本来是“粒”的定语,现在作了主语了,“鹦鹉”本来是主语,现在作了“粒”的定语了;“碧梧”本来是“枝”的定语,现在作了主语了,“凤凰”本来是主语,现在作了“枝”的定语了。从语法的角度说,这种语序的创新,是语法的任意主观化,应该说是不允许的,而从修辞的角度说,只要表达得更好,这种创新又是容许的,而且人们本着善意解释的原则,可以从不正常的语序中推出正常的信息〔33〕
5.2 有的语句,语序不同意义就不同,从中选用一种, 是非同义形式的选用。如对“斗争后的胜利”和“胜利后的斗争”的选用。有的语句,语序不同而意义基本相同,从中选用一种,是同义形式的选用。如对“你们出来吧!”和“出来吧,你们!”的选用。
相对地说,语序的同义形式的选用,在修辞上更为重要。这种选用,通常在常规语序和凸显语序构成的同义形式中进行。比如对“主语谓语”和“谓语主语”,对“定语中心语”和“中心语定语”的选用。当然,常规语序,也有同义形式的选用问题。比如说,在句际中,主语通常可以有多种语序,主语语序不同,可以构成语序的多种同义形式。这就有一个选用问题。“看看醉猫似的爸爸,看看自己,看看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只剩了哭”(老舍《骆驼祥子》),主语“小福子”的语序也可以提到句首而句意基本不变。现在这样选用,可以使主语“小福子”和句末焦点信息“只剩了哭”紧挨着,从而加强了句意。再如同位语,其本位和同位,也有前后不同的两种语序,也有一个选用的问题。“信笺上是这样几个字:‘屠维岳君从本月份起,加薪五十元正。此致莫干翁君照。荪十九日’”(茅盾《子夜》)。也可以把“这样几个字”放到全句末尾。作者选用了前者,是因为本位太长,放在末尾,句子就不便于阅读,更不便于上口。
从修辞格内部构造来观察,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语序的同义形式的选用。比如倒喻”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诗)可以是从“面如芙蓉眉如柳”的比较中优选来的。其优势在便于和上文“太液芙蓉未央柳”中作为话题的“芙蓉”和“柳”相衔接,在句际中显出其语序的优势来。再如对比喻相似点的表述文字,其语序可以在句末,也可以在句中。“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眼,味儿终究有点寡淡”(杨朔《泰山极顶》)也可以作“登泰山而看不到日出,味儿终究有点寡淡,就像一出大戏没有戏眼”。作者选用前者,最后才说出比喻的相似点,是为了适应同先说出谜而再揭开谜底相类似的修辞需要。
5.3 从修辞格来考察, 有的修辞格是连续使用两种语序不同的同义形式构成的,这样的修辞格其结构形式相当精巧别致,语序的修辞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回环(“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比如反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诗),比如“梅似雪,雪似梅”。连续使用两种语序不同的非同义形式构成的修辞格也是有的,如序换格。比如:“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水浒传》第21回)这两个语句字面不变、语序不同而含义迥异,换序换出了阎婆惜抓住把柄倒打一耙的嚣张气焰。
5.4 语序的安排离不开篇章的考虑。 因为语言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一个语言单位往往受到其他语言单位的制约。比如孤立地看“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和“似梦如情漓江的水!”两种语序都是可以选用的,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它们所在的更大的语言单位中来看,比如联系上文“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来看,“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自然是更好的选择对象,因为它和上文衔接紧凑自然。修辞讲究衔接、照应,语序是衔接,照应的重要手段之一。语序不当,可以造成衔接脱节、有失照应,言之无序,行文粗疏;语序恰当,可以取得接榫精巧,前后照应,言之有序、思路周密的表达效果。
应该看到,有的语序在篇章中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言语活动中,有时多种表达形式都能适应同一的思想内容的表述,而又各有修辞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语序的安排,具有灵活性。比如“a做梦,是自由的, b说梦,就不自由。c做梦,是做真梦的,d说梦, 就难免说谎”(鲁迅《听说梦》)。这是一种语序安排:a b为一个层次,c d为另一个层次;先以a b摆出论题,再以c d申说证明。如果改用a c b d的语序, 就是把a c作为一个层次,b d作为另一个层次,然后将这两个层次对比。而a和c的关系,b和d的关系又都是论题和申说证明的关系。选用前一种语序和后一种语序都能适应对做梦、说梦的评议,但选用前者,有行文错综的美趣——隔句承接,c隔b而承接a,d隔c而承接b,此即前人所谓丫叉法。〔34〕选用后者,有行文整齐单一的快感。
有的语序,在篇章中,却有较强的规定性。这规定性,除来自语法规则之外(参1.4)还来自表达的必需,即非用这种语序无法达意。 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除非……。’她咬住了嘴唇,没有说下去。‘除非什么?’我不安地诘问道。‘除非你不革命。’她严肃地说”(《小说月报》1980年第8期29页)。 “除非……”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有前置、后置两种语序,如“除非你去,他不会去”,“他不会去,除非你去”。但在这里,“除非……”只能后置,如果前置,作“除非……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就简直是语无伦次了。
5.5 不同的语体和风格,对语序的要求不尽相同。 这一方面表现为语序在某些语体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另外一些语体中具有较强的规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有的语序在某些语体中出现频率较高,在另外一些语体中出现频率较低。以语体的两大类别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而言,前者语序较为灵活,如“真不像话,这也算一次活动了吗?难道。”(口语实录)“吃了饭了吧?该。”(口语实录)又如虽然以书面形式出现但实为模仿口语的文字:“怎么回事,这是?”(张天翼《清明时节》)“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鲁迅《范爱农》)其中的“难道”“该”“这是”“王金发他们”都是说话人急不择言以至语序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后者有较强的规定性,亦即合乎常规语序的规范,即如以上说法,在纯正的书面语体中是不会出现的,只能用“难道这也算一次活动吗?”等规范语序来表达。以文艺语体和公文语体而言,前者凸显语序出现频率高,后者凸显语序出现频率低。因为前者往往有突出兴趣、态度、情绪、增加美学信息的任务,用得着凸显语序,而后者是直接指示语体,感情处于中立状态,不用传递美学信息,按常规语序直白陈述就可以了。这就不难理解,文艺语体比如诗歌,为了押韵,为了调协平仄,为了强调某种情绪,为了突出某个中心意思,常常用得着诸如“谓语主语”“主句从句”之类的凸显语序。古代诗句中常有时空状语放在句末的,如“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白居易诗),“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阑干欲暮时”(吕居仁诗),“芳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长卿诗),“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杨孟载诗)。这种语序在公文语体中也是罕见的。像京剧唱词“舍不得太爷恩情有”、“二弟张翼德性情有”的语序在公文语体中就更找不到了。
不同作家的不同语言风格,也往往可以由语序的不同选择显现出来。语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作家的语言风格特征的。比如“我告诉他们,我晓得一些孔孟庄老和佛与耶稣的道,我喜欢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拒绝了我。他们的道才是道,世界上并没有孔孟庄老与佛耶,仿佛是”(老舍《四世同堂》下)。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作者是谁,这种语序,我们还不好说一定是出于老舍的笔下,表现了老舍的语言风格特征,但是,我们说这不是赵树理的语言,恐怕还是有几分把握的,因为这与赵树理的朴实无华、有话直说的语言风格不相类。
5.6 在语序变换造成的各种修辞效果中, 别具一格的修辞效果是滑稽、幽默。所谓滑稽,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是“滑稽的事情是某种不引起痛苦或伤害的错误或丑陋〔35〕”。用列普斯的话来说,是“滑稽手法常把二分之一相似转化为全部相等”。〔36〕语序变换造成滑稽、幽默,其具体方式是通过语序的变换,使语言单位本身未变而语序不同,致使意义内容相去甚远甚至刚刚相反。这是把完全相同转化为完全相反造成的滑稽、幽默。这和列普斯的说法,是相反相成的。比如“‘生了,生了!’他语不连贯,显然在向亲人通报他当爸爸的喜讯。‘我儿子给我生了一个老婆!’”(《小说月报》1984年第11期41页),“年轻时,我很喜爱体育活动,……打过篮球,垒球、尽管常常名列第一——倒数,但兴趣却是广泛的”(《光明日报》1990.9.234版)之类。
5.7 如果把语法认知、逻辑、语用、 修辞放在一起来作一个综合考察,可以看到它们往往是一致的。从大处着眼,我们首先看到,认知、逻辑是语序形成的深层基础,语用、修辞是语序运用的表现形式,语序是语法形式,大致是表里一致的。而从认知、逻辑来说,正如上文所说的,如果汉语语序以感知为基础,是基于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临摹的产物,而客观现实本身又是具有事有本末,物有终始的逻辑特征的,则认知与逻辑必有相通之处。而从修辞、语用来说,二者都和语言的运用相联系,因而相通之处也很多。再以“屡败屡战”为例。这种语序即反映了先败后战的逻辑事理顺序以及人们认知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又反映了“话题——述题”和焦点信息在句末的语用特征,还适应了表述斗志顽强的题旨的修辞需要。
当然,语法、认知、逻辑、语用、修辞并不完全相等。对语序考察时,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一般地说,常规语序,其认知、逻辑的深层基础与语用、修辞的表层形式比较一致,而凸显语序则二者有相当距离。但凸显语序却更多地成为语用,特别是修辞的表达形式。
从语序的运用,务求收到最好的表达效果说,在语法认知、逻辑、修辞、语用四者之中,修辞是最活跃的因素,处于制约的地位。修辞可以顺乎认知、逻辑、语用的常规,也可以越出认知、逻辑、语用的常规,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超常语序,达到无理而妙的境界。为此,我们不采用“倒序”的说法,但却承认超常语序的存在。比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舜尧”,按常规语序应作“尧舜”,这里使用超常语序作“舜尧”,是适应调协平仄、押韵的修辞需要。而这样的修辞需要,又未必合乎语法认知、逻辑规律。修辞要求语序在上下文中有照应,也要求符合音律。“有照应”,涉及语言单位的意义内容,自然容易同认知、逻辑、语用相一致,而“音律”是语言单位的语音形式,却不一定同语法认知、逻辑、语用相吻合。遇到这种情况,修辞往往舍有照应而取合音律,于是造成与语法认知、逻辑语用不一致的超常语序。比如“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鲁迅《电的利弊》)。上文先用“外国”后用“中国”,下文本应合乎逻辑地用“外中”来照应,但这里却为了适应并列构词成分平声字在前仄声字在后的音律原则用了“中外”。
不少凸显语序,是“五四”以后新兴的语序,来自对西方语言的语法的吸收,如状语、定语放在中心语之后,从句放在主句之后,等等。汉语之所以要这样吸收,固然和逻辑思维的发展有关,但根源还在于修辞的需要。这些新兴的语序,大都是能给汉语增补修辞资源的。
5.8 我国语序的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 《春秋经·僖公十六年》云:“陨石于宋五。”《公羊传》曰:“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春秋繁露·观德第三十三》曰:“‘陨石于宋五’,‘六鸽退飞’,耳闻而记,目见而书,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这样的语序的考察,可谓开认知的、修辞的语序考察的先河。其后刘勰《文心雕龙》《文则》以及历代诗话对语序也多有考察。他们一方面赞赏收到良好修辞效果的凸显语序(例散见上文),一方面又批评偏离规范的语序,比如刘勰说:“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乎顺序。”〔37〕胡仔说:“《和东坡金山寺》云:‘云峰一隔变炎凉,犹喜重来饭积香。’《维摩经》云:‘维摩诘往上方,有国号香积,以众香钵盛满香饭,悉饱众会。’故今僧舍厨名香积,二字不可颠倒也。太虚乃迁就押韵,殊不成语。”〔38〕他们对汉语语序的考察是实事求是的。近人杨树达对汉语语序给了较多的关注。他在他的《汉文文言修辞学》一书中对语序作了较为广泛的考察,第十六章错综,考察了名词与其状词的倒置、错综,主辞与述辞的倒置、错综,动词与宾语的倒置、错综,介词与其宾辞的倒置、错综,等等语序问题。第十七章颠倒,考察了词的颠倒、句的颠倒、趁韵颠倒与非趁韵颠倒、主语与述语颠倒、因句与果句颠倒,等等语序问题。自然,现代尤其是近年对汉语语序的考察较之过去是深入得多了,而对汉语语序的考察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将有更多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
(续完)
注释:
〔26〕朱熹《诗集传》。
〔27〕《朱子语类》。
〔28〕〔29〕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384、390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0〕参看方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中国语文》,1995(4)。
〔31〕姜夔《诗说》。
〔32〕周振甫《诗词例话》,29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33〕参看张炼强《修辞与汉语规范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2)。
〔34〕参看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858~860页,中华书局, 1979。
〔35〕亚里斯多德《修辞学》,55页,三联书店,1991。
〔36〕转引自钱钟书《旧文四篇》,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7〕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3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