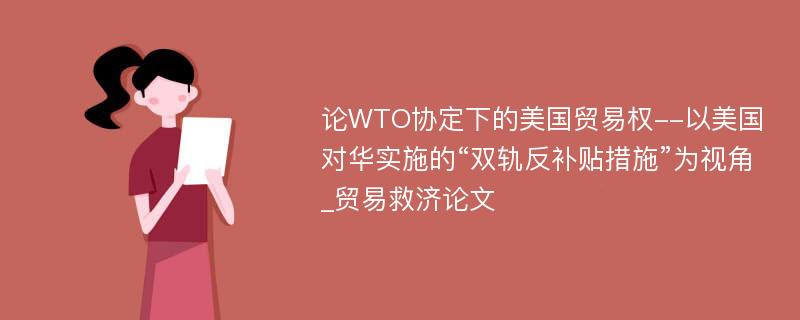
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论——以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双轨制论文,协定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14(2008)02-0156-(07)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极为不平常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美国使用新型贸易政策工具,一改23年来对“非市场经济”(Non Market Economy,以下简称NME)国家不适用反补贴税法的立场,对中国出口铜版纸提起反补贴调查,这也是美国自1991年对中国出口摇头和装饰电风扇进行反补贴调查之后的首起案件。[1]7美国克林顿政府于2000年批准了授予中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Act,以下简称PNTRA,编号为106-286),从而使中国部分脱离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The Jackson-Vanik Amendment)的制约要求①,但美国商务部根据该修正案的授权,按照《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确立的NME国家定义与六条标准在对中国适用贸易救济法中仍将中国视为NME国家,[2]116据此,中国的NME国家地位与美国反补贴税法之适用成为中美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从1987年第100届国会开始至今主张将反补贴税法适用于NME国家的议案从未中断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7月27日由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H.R.3283-United States Trade Rights Enforcement Act),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授权商务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NME国家适用反补贴税法。尽管该法案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但国会两院一系列贸易救济立法行动足以表明美国国内“进口竞争性产业”(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试图通过其利益代表人(国会两院议员),推动国会向商务部立法授权,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补贴调查,从而缓解由于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在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之法律依据尚未确定的前提之下,商务部对铜版纸反补贴案件做出肯定性终裁及相继对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等出口产品提起十几起“二反合并”(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之事实,充分说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正在从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层面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积极行使WTO协定下美国的贸易权利②。2007年2月以来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先后就禁止性补贴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音像制品与出版物市场准入等问题向中国发起质难,其背后的法律逻辑表明美国正在积极主动行使WTO协定下的国家贸易救济权利。美国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在WTO体制中将贸易与政治或意识形态脱钩③,监督中国履行《入世议定书》下对美国的贸易义务④,通过积极行使WTO协定下美国的贸易权利,缓解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过快给美国国内要求贸易保护的相关产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这种以行使贸易权利为助推的新型的对华贸易政策将成为后过渡期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尝试站在后过渡期中美贸易关系所处的新阶段,从中美贸易争端之实践出发,以WTO协定下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理论与实践为视角⑤,将中美贸易关系之法律研究范式定位在以美国贸易权利为导向,通过对美国宪政体制下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之制定与执行机制、国家经济主权让渡与强化机制及自由贸易协定缔结与执行机制三者关系的一般梳理,总结并归纳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之性质与分类,同时指出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实质,最后提出中国之对策与启示并展望中美贸易关系之发展趋势。
二、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论
无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一直是围绕美方作为发起者而中方作为应对者这一格局展开的。2001年中国入世使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的场所与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入世之前,美国主要由国会制定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来定位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单边评价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与立法实践,并且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入世之后美国以贸易权利为导向,一方面由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及国会专门机构定期出台有关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报告,监督中国执行《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书》的立法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打压我国在WTO体制下的法律与政策空间,入世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倾向于通过充分行使美国在WTO协定下的国家贸易权利来制衡中国。2006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与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数次控告中国涉嫌违反WTO协定的政策与制度之做法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开始监督中国履行复杂承诺的最好例证。据此在就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进行分析并作出回应之前,必须对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分析。
(一)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之性质
对于国际条约法作为WTO协定的法理支撑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WTO协定下成员方之国际条约权利与义务的行使与执行却遵循着一套独特的规则:“《WTO协定》是一个国际条约,其实质相当于一个国际合同。达成这些协定条款本身表明WTO成员是在行使国家主权,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协定。为获得作为一个WTO成员可以获得的利益,作为交换,各成员同意根据《WTO协定》的承诺来行使国家主权。”[3]27美国作为成员国积极倡导并推动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与发展,通过国家经济主权让渡为自身创设国际条约权利与义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基于国际条约协定在美国宪政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二元制的划分⑥,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国际法之双重视角审视美国在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下贸易权利之性质应当是非常重要与客观的。
1.国家经济主权行使中的WTO自由贸易协定
追溯美国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之历史可以发现,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RTAA1934)确立的“1934年贸易政策制定体制”(以下简称“1934体制”)开启了美国贸易自由化的征程。[4]6RTAA1934经过11次延长至1962年,美国坚持以互惠理念为本位,以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机制,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制度,通过国际经济主权让渡与强化⑦,达成了一系列双边性质的互惠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性质的GATT1947,主导了二战前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自GATT1947至1994《马拉碦什协定》,美国依托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在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充分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让渡之方式行使国家经济主权,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国会在以总统为首的贸易行政机构参与双边、区域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维护甚至强化美国的经济主权。1948年哈瓦那宪章无法生效;1955年当有关国家要求修改GATT1947的有关条款,成立贸易合作组织,国会以多边贸易体制侵犯国家主权为由不予批准;东京回合(1973年—1979年)谈判中在涉及“祖父条款”之问题时,国会坚决反对等事实足以表明,国会对自身享有的宪法性对外贸易管制权的捍卫与警惕⑧。1994年美国签署《乌拉圭回合协定》时,国会中的主权大辩论是主权危害论者对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强有力的抵制。[5]149-151纵观从“1934年体制”的确立至1994年WTO的成立这60年,美国贸易政策从高关税保护主义向贸易自由主义转变,最后转向公平或战略贸易政策,[6]27但始终没有脱离自由贸易的轨道。从美国国家经济主权让渡与强化之双重视角及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关系之变迁角度审视,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美国如何利用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为自身创设贸易权利:
第一,美国联邦宪法明确授予国会关税制定、征收权与对外贸易管制权,没有明确授予总统管制对外贸易的宪法性权力,这个授权机制促使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争夺在1934年达到了顶峰,而国会向总统立法授权的“1934年体制”使美国真正开始行使国家经济主权,服务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在美国让渡与强化国家经济主权的进程之中,国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以总统为首的贸易行政机构倡导并推崇的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是实现美国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法律形式。
第三,无论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如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还是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均是美国行使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它们为美国创设了一系列的条约权利与义务,而这些贸易权利与贸易义务主要是互惠性质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除外)或者说本质上主要是双边的。[7]80-90
第四,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导向,而三个层次的互惠自由贸易协定,特别美国参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是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这方面可以在国会强化与捍卫国家经济主权之实践与美国不时地革新“二反一保”进口贸易救济措施与创造出口贸易救济措施(如《1974年贸易法》中建立的“301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中得到最好的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在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是美国行使国际经济主权的结果,这是站在国际法的角度,就美国如何依托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对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的法理剖析并得出的结论,但是在贸易权利被创设之后,还需要在成员国国内执行,这主要取决于美国宪政体制及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国内法关系之理论与实践。
2.WTO自由贸易协定在美国国内法中之执行
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之“至上条款”(the Supremacy Clause),条约无论是否是“自动执行”(self-executing)都应是“美国的最高法律”(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8]90-98尽管从国际法角度条约与行政协定在美国都被视为国际协定,但在美国宪法下两者是严格区分的,而且根据杰克逊的分类,美国的“条约”权利与义务可以通过三种不同方式确立,[9]222-223因此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之缔结与执行程序也可以分成几种不同的方式。WTO自由贸易协定事实上主要指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协定》,该协定是在“快车道”程序下签订的⑨,属于美国的“非自动执行”(nonself-executing)的自由贸易协定⑩,美国国会于1994年通过《乌拉圭回合协定法》,转化适用或执行《乌拉圭回合协定》,因此从理论上讲,《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书》在美国也应当如此执行。
综上分析,美国在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之执行应当从以下两个角度审视:第一,美国作为WTO协定的缔约方可以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直接行使该协定下的国家贸易权利;第二,作为国内法中的WTO协定,美国国内私人(主要指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但不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NGOs)可以通过适当的诉讼或行政程序要求司法或行政机关间接行使已经立法转化的贸易权利。但必须指出的是,此处的贸易权利并非WTO协定为成员方私人创设的权利,也非受美国宪法保障的关于参与国际贸易的私人固有的“贸易权利”,实际上在美国关税与上诉法院于1975年所作的一份判决——“United States v.Yoshida International Inc.”中该项权利早已被否定;在该案中,法院裁定:“没有人拥有一种与外国进行贸易的既得权利。”[10]206-207因此该贸易权利从本质上讲仍是美国作为成员方的条约权利,但在美国国内法中该权利的行使主体最终却是私人。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国际法之双重视角理解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之性质后,有必要对贸易权利作一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美国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之实质。
(二)WTO协定下美国贸易权利之分类
成员方在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是基于国家经济主权让渡后的条约权利,WTO在新千年面临的体制性挑战之一就是成员方之主权让渡与WTO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11]47-61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WTO确立了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为核心的反歧视模式,通过互惠性关税减让,实现了货物贸易的充分市场准入;以最惠国待遇原则为前提,初步实现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但是随着劳工、环保、卫生和安全等本应由主权国家监管的问题进入WTO的管辖视野,成员方之国家主权与WTO可能形成的监管模式之间产生冲突并且与业已成形且运行良好的反歧视模式展开竞争。[12]66-72但无论如何,现行的反歧视模式所确立的成员方之间的市场准入权利以及对该权利提供救济的贸易救济权利应当是WTO协定下最重要的两大类权利。
1.作为实体性贸易权利的市场准入权利
从GATT1947到1994《马拉碦什协定》,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成员方之间的关税壁垒(TBs)与非关税壁垒(NTBs)的挑战,特别是东京回合以来,为了实现货物、服务与技术在成员方相互之间的市场准入权利(Market Access Rights,MARs),GATT1994制定了包括一系列对技术标准、卫生与植物检疫等“管制性壁垒”(regulatory barriers)进行法律规制的协定。[13]359-362这种市场准入权利从法理角度看应当是由不同国际条约创设的实体性贸易权利,而且是专门为各成员方(包括主权国家与单独关税区),如美国创设的,美国国内私人不是直接的权利主体(11)。从权利行使角度看,此种实体性贸易权利是以程序性贸易权利为依托的,而这种程序性贸易权利在WTO协定下主要指美国的贸易救济权利。
2.作为程序性贸易权利的贸易救济权利
一般认为WTO协定中的贸易救济法主要指“二反一保”救济措施,这主要基于GATT1994中《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保障措施协定》三个国际条约分别对成员方的反倾销、补贴与反补贴与保障措施贸易救济授权。事实上美国在WTO协定下拥有以下两大类程序性贸易救济权利:第一、从缔约成员国角度看,美国享有上述三个“二反一保”协定下的“进口贸易救济权利”之外,美国根据《马拉碦什协定》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享有将其他成员方国内的涉嫌违反WTO协定的措施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救济权利,即“DSU下的贸易救济权利”(12);从国内私人角度看,美国私人寻求贸易救济的权利是经国会立法转化的相关WTO协定(主要指关于“二反一保”的三个协定、《入世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条款下的美国贸易救济权利,即“国内法上的进口贸易救济权利”。当然国内私人可以利用国内行政程序性制度,即《1974年贸易法》之“301条款”或“301贸易壁垒调查制度”,[14]75-76要求美国政府进行贸易外交保护,从而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DSM)。该条款本质上授予私人“国内法上的出口贸易救济权利”,使国内私人有权间接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与美国政府“共同行使”WTO协定下的贸易权利,但它绝不是WTO协定授予成员方的贸易救济权利,因为“301条款”不是美国经济主权让渡的结果,而是美国宪政体制下GATT/WTO协定执行方式的创新;第二,除了上述《马拉碦什协定》下的“一般意义”上的“二反一保”救济权利之外,美国在《入世议定书》下享有对中国“特别意义”的“二反一保”救济权利,主要指《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下15年的反倾销救济权利与反补贴救济权利、第16条下12年的特别保障措施救济权利与《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下的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救济权利。同样这些“特别意义”的“二反一保”救济权利的权利主体是作为WTO成员方的美国,若国内私人要行使这些救济权利,则必须经过美国国会之“转化立法”(act of transformation),成为“国内法上的出口贸易救济权利”后方可执行。
通过对实体性与程序性贸易救济权利之分析,我们认为贸易救济权利是直接服务于市场准入权利之实现的,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救济权利与国内私人享有的、“301条款”创设的出口贸易救济权利就是两个典型,而“一般意义”与“特别意义”上的“二反一保”救济权利须经国会立法转化才能被国内私人行使,故从根本上讲它们是间接服务于公平贸易理念下的市场准入权利的。从2006年10月美国开始对中国出口铜版纸提起反补贴调查与2007年2月将中国禁止性补贴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之理论与实践观之,美国正从可诉性补贴与禁止性补贴两个角度,采取“双轨制反补贴诉讼机制”(DSB诉讼机制与国内诉讼机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与补贴措施发起进攻,[15]139这种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对华贸易政策正在对中国形成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同时也为我们探究并解读此种贸易政策之法律路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三、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之实质探析
美国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在2007年3月27日向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中国问题”(US Trade Policy:The China Question)的证词中指出,当今美国贸易政策中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中国问题”;其二是美国面临的“出口保护主义”(export protectionism)(13)。商务部在缺乏明确国会授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一系列的“二反合并”调查与美国政府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禁止性补贴措施、音像制品与出版物市场准入等问题提出涉嫌违反WTO协定的指控正是从贸易权利角度对中美贸易关系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做出的法律回应。
(一)国会试图转化SCMA与《入世议定书》下反补贴救济权利指控中国可诉性补贴措施
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是要求国会授权商务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NME国家适用美国反补贴税法,至此两院议员推动国会立法转化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SCMA)与《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下反补贴救济权利之努力达到了顶峰。尽管该法案最终仍未获批准,但它主张通过对《1930年关税法》中反补贴税法规则的修改使其直接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NME国家并主张将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同样适用于反补贴税法等做法使我们必须首先思考其法律依据问题。SCMA并没有明确授权成员方对NME国家适用反补贴法,但它也没有明确禁止成员方如此行为。《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下美国是否被授权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及在补贴计算中是否被授权使用“替代国制度”似乎也非具体而明确。[16]96但是美国商务部对铜版纸案做出终裁及中国政府正式就美国对华铜版纸反补贴调查案提起了WTO争端解决项下的磋商请求之实践,足以表明中国政府在WTO体制中开始用“贸易救济权利对抗贸易救济权利”,至于美国在两个协定之下是否拥有对中国行使以及拥有什么样的反补贴救济权利最终应由WTO专家组作出裁决。
(二)美国行使DSU下反补贴救济权利控告中国禁止性补贴措施
2007年2月2日,美国正式就中国贸易补贴措施在WTO提出磋商请求,主要指控中国贸易税收政策与制度违反SCMA第3条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入世议定书》第10条及《工作组报告书》第167与168段的要求。[17]该案至今尚未走完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争端解决程序,但不管结果如何,在中美贸易关系进入第三阶段时美国行使“DSU下的贸易救济权利”,监督中国履行《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书》下的补贴义务之实践充分证明美国正在实施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的新型的对华贸易政策,这将考验中国政府履行复杂入世承诺的能力,特别是处理补贴问题的智慧。
据上所述,无论美国对中国自铜版纸反补贴案之后发起的一连串“二反合并”案件还是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控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出版物与音像制品市场准入等案件均说明美国真正开始与中国在“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发展中展开较量。而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对中国的可诉性补贴与禁止性补贴左右开弓恰恰正是在这场较量中,美国刻意选择的突破口,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作出积极的应对。
四、代结语——启示与对策
随着中国WTO后过渡期的来临,美国在WTO协定下对中国行使贸易权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打破不对NME国家适用反补贴税法的羁绊及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监督中国履行《入世议定书》下对美国的补贴义务是美国在反补贴救济权利领域中迈出的第一步,仅这一步对正在构建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应对日益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中国而言,其涵义是深远的,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启示,同时提供了中肯的应对策略与思路:
首先,美国在WTO协定下以贸易权利为导向,特别以贸易救济权利为主要手段对中国实施“高压态势”的贸易政策,严格监督中国在后过渡期执行对美国复杂承诺之实践证明美国正在践行WTO作为“成员驱动型”(member-driven)、“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及“规则导向型”(rule-oriented)的多边贸易组织之“权利本位”理念。[18]80-84在当前美欧学者正从多重视角探讨WTO贸易宪政背景下,[19]32-38中国应当转换入世前后“国家贸易义务”为主导的传统观念,牢固树立“国家贸易权利”的本位意识,善于并敢于通过行使WTO协定下的贸易救济权利来应对美国的挑战,同时保护在进一步履行入世承诺过程中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
其次,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四个“歧视性”贸易救济条款是美国在WTO协定下依据国内法将中国视为NME国家的具体表现,并且国会已经分别将特别保障措施与纺织品特别保障措施条款下的贸易救济权利转化成国内法上的救济权利,为私人行使权利服务;国会也试图转化《入世议定书》第15条下的反补贴救济权利。尽管美国在《入世议定书》拥有对中国“特别”的贸易救济权利,但从四个具体条款之文本含义与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救济之实践审视,中国除了原则上积极利用两个商务外交磋商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与中美经贸混委会机制)与美国保持对话与沟通之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必须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澄清并界定美国在四个条款下具体的贸易救济权利,因为WTO体制下源于经济的贸易摩擦,其首要的解决途径应当是法律;其最重要的依据仍然是法律。[20]11
再次,从美国对中国实施“双轨制反补贴措施”,打压中国国内可诉性补贴与禁止性补贴之实践看,我们有必要真正反思并检讨自身在SCMA与《入世议定书》下对美国应当履行的补贴义务,而主要方式是将涉及外汇、银行利率及税收等政策与制度与我们的补贴义务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考虑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有关补贴措施之执行或实施机制,将加快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上来,特别要研究在WTO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进行适度干预的思路与方式。
最后,基于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再加上美国贸易政策不仅有关经济,也有关政治,不仅有关国际政治,也有关国内政治,不仅有关政治运作,也有关意识形态之基本事实,[21]190我们必须关注美国以中国在WTO协定下对其应当履行的贸易条约义务为切入点,从外部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之意图,这对试图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中国而言有着深刻的意蕴。
注释:
①《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就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02条款,该修正案是对前苏联于1972年出台的限制公民移民政策的政治回应,建立了美国自由移民政策并且将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特别对共产主义国家违反美国确立的具体自由移民标准拒绝给予某些经济利益包括享有美国非歧视贸易待遇;同时该法案还授权美国商务部认定市场经济国家的权力并通过豁免与不违反两套程序对NME国家进行监督。美国给予中国PNTR待遇是中国接受《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双边协定》之四个歧视性贸易救济条款为代价的,同时美国仍根据该法案将中国视为NME国家。参见William H.Cooper,The Jackson-Vanik Amendment and Candidate Countries for WTO Accession: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eceived through the CRS Web,Order Code RS22398,March 14,2006,资料来源:http//www.us-asean.org/vietnam/CRS-JacksonVanik.pdf.pp2-6.访问日期为2007年11月22日。
②WTO协定除了1994年《马拉碦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马拉碦什协定》或《WTO协定》)之外,当然包括2001年《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以下简称《入世议定书》与《工作组报告书》)。
③自中国2001年入世以来,美国在贸易领域与中国的较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由中国入世前通过国内单边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向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来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之立法与实践转变,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关系从根本上无法摆脱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但2000年PNTRA开创了中美贸易关系“脱政治化”的趋势,这对双边贸易关系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参见孙哲、成帅华著:《美国国会与后PNTR时代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
④2006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关系加入一个更大责任与执行的新阶段》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中美贸易关系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年至2001年,美国推动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在开放市场和改革贸易体制方面作出全面承诺;第二阶段,从2001年至2005年,监督中国实施WTO承诺;第三阶段,从2006年开始,中国履行WTO承诺的过渡期基本结束,简单的承诺大多已经履行,而复杂的承诺面临更多的困难。报告指出美国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监督中国加强对这些复杂承诺的实施,另一方面是要求中国对全球不平衡问题承担起责任。参见USTR:《U.S.-China Trade Relations: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Top -to-Bottom Review》,Feb,2006,资料来源: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Library/Reports-Publications/2006/assets-upload-file921-89。
⑤本文所称的“双轨制反补贴措施“指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适用反补贴税法,另一方面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对中国国内补贴措施提起反补贴诉讼。
⑥美国将国际条约协定分成“条约”(在美国宪法意义上,这是必须提交参议院批准的协定)与“行政协定”(无需提交参议院的协定),根据美国宪法之实践,行政协定获得批准的方式共有四种。从国际法角度看,所有这些手段都是条约,但是从美国宪法角度看,两种不同术语的区别非常重要。参见[美]约翰·H·杰克逊:《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与政策》,张乃根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90-91。
⑦无论在美国国际法学术研究或者对外关系范畴中,学者或政府官员一般都使用“主权”或“国家主权”,很少使用“国家经济主权”这一概念,即使在美国与WTO关系这一领域也是如此。之所以在此使用“国家经济主权”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特别参与GATT多边贸易体制与贸易政策规制权紧密联系,当然1994年乌拉圭回合之后,WTO的管辖范围从学理上似乎在超越贸易本身,与劳工、环境等非贸易问题挂钩,但至少到目前为止,《WTO协定》的涵盖范围仍没有超出成员方经济主权的范畴。为了论证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本文使用“国家经济主权”概念,关于这一概念与美国贸易政策规制权之关系,详见徐泉著:《国家经济主权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187页。
⑧《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一项与第三项分别明确授权国会制定与征收关税及管理州际、对外及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而宪法没有明确授予总统管制贸易的任何权力,因此美国通过互惠自由贸易协定机制,行使国家经济主权过程中,国会与总统就贸易政策与贸易法律之制定与实施方面的权力争夺贯穿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始终。关于国会要求保护国家主权,对多边贸易体制保持适当警惕的论述,参见白明韶著:《WTO下的美国国家主权保护机制及其启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
⑨“快车道”(Fast-track)程序是由美国《1974年贸易法》确立的,它是美国国会-行政协定(th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agreement)的一种批准程序,2002年布什以“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TPA)之名义取代了“快车道”程序,现在统一采用“贸易促进授权”这一称谓,关于TPA之具体内容,详见徐泉、陈功著:《美国外贸法中“快车道”模式探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2卷)。
⑩所谓“自动执行”的协定是指协定经一国接受后,无须再用国内立法予以补充规定,即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那类协定;“非自动执行”的协定是指协定经一国接受后,尚须用国内立法予以补充规定才能由国内司法或行政机关予以适用的那类协定,这类协定是美国法上的特有概念并且是严格区分的。详见韩立余著:《美国外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2页。
(11)国外有学者认为在《装运前检验协定》下出口商可以以进口国政府(即装运前检验机构)违反该协定为诉因将其告上WTO“法庭”,换言之,个人被授权通过WTO的独立机构来执行国际贸易法,但至今为止,此项独特的条款尚未接受检验。参见[美]斯蒂夫.查诺维兹著:《WTO与个人权利》,张若思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12)DSU确立的适用于成员方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本质上仍属于WTO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美国将其他成员方告上WTO“法庭”是行使美国作为缔约国应有的贸易救济权利。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贸易救济体系之组成的论述,详见翁国民:《贸易救济体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7页。
(13)“中国问题”主要指日益攀升的中美贸易顺差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与压力,而“出口保护主义”是指美国在《WTO协定》下向其他成员方开放市场,而其他成员方如中国通过国内劳工与环保标准实施贸易壁垒,对美国出口产品或服务之市场准入设立障碍,简言之,其他成员方没有向美国对等开放市场。详见Jagdish Bhagwati,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标签:贸易救济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wto论文; 反补贴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贸易协定论文; 法律论文; wto争端解决机制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