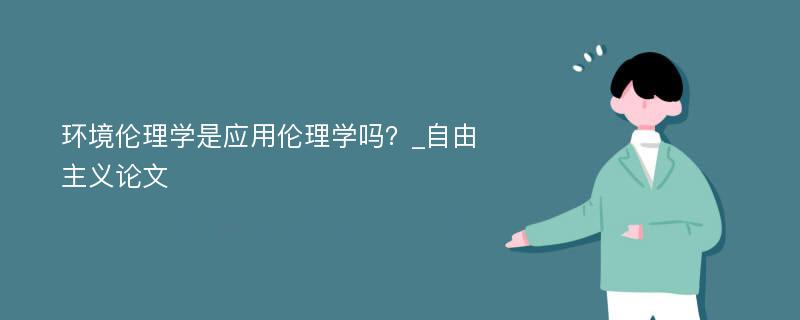
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用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学科,它的基本价值倾向一般被概括为是以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它强调程序共识和尊重个人的自我决定,其实质在于确立尊重人权的原则。那么,这样一种概括是否准确呢?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它虽然可以反映生命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本质,但是却不能正确地反映环境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倾向。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反,它所挑战的是自由主义[1]。
一、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对立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和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如果说21世纪是“环境”和“健康”的世纪的话,那么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就共同承担着建构21世纪人类活动伦理原则的崇高使命。按理说,二者在价值倾向上具有一致性,但遗憾的是,它们却是对立的。这种对立集中反映在对人的伦理地位以及个人自由(自我决定)的理解上。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道德共同体的成员局限于人类的范围之内,只有人类个体享有生存权。这一理解主要来自康德的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康德曾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权利享有者作过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只有“人格”才是“目的”,才是一个在道德上受尊重的对象,而其他一切则是“物件”,只能被视为“手段”[2](P46-47)。“社会契约论”也有类似的规定。按照“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权利和义务具有“相互性(reciprocity,又译互惠性)”,一个权利享有者必须能够尽义务,而能够自觉尽义务的最典型的存在莫过于有良心的成年人。因此,权利的享有者必须具备自我意识、语言、反省和自我选择等高度的理性能力,理性能力是一个存在物拥有权利的前提,我们可称之为权利的“理性标准”。这一标准在历史上曾对启蒙运动和人权运动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今天,“理性标准”却成了扩展道德共同体、开展伟大的动物解放运动的最大障碍。因为,非人自然物,即便是具有一定意识能力的高等动物,也无法满足这一标准。因此,对于动物权利论者来说,要把动物也纳入进道德共同体,恐怕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这一标准降低到动物也能适应的水平上。关于这一问题最典型的证明是由美国的哲学家范伯格(Joel Feinberg)作出的。
范伯格从分析现代社会法律权利所需的条件入手,提出拥有法律权利的必备条件是“要求(claiming)”,即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能够申诉、抗议。这显然需要足够的理性能力,用范伯格的话说是“对应能力(competence)”。但问题是,像胎儿、婴儿、痴呆人、植物人等“准人类”虽然不具备“对应能力”,却不是享有了同正常人一样的权利了吗?范伯格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否定了“理性标准”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典型的“极限案例”的论证方式,即如果你把理性和自律能力作为某物拥有道德权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你就必须把“准人类”(sub-human)也排除到道德共同体之外;如果你不想否定“准人类”的道德权利,那么你就必须把权利标准降低到“准人类”也能适应的水平。那么,这一水平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准人类”和正常人一样,也拥有趋乐避苦和满足食、性等欲望的利益。只要有利益就可以找到代表,就可以通过代理人的方式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像石头那样的非生物由于没有利益,无法找到代表)。因此,权利拥有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权利拥有者必须有代表。毫无利益的存在物不可能有代表;(2)权利拥有者必须是受益者。没有利益的存在物既谈不上受益也谈不上受损。”[3]两个条件可以简化为一条原则,即只要有利益就拥有权利的“利益原理(interest principie)”。
如果“利益原理”能够取代“理性标准”成为权利标准的话,那么动物就应该拥有权利,因为,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具有趋乐避苦、食欲、性欲等利益。既然伦理的本质在于消除特权、贯彻公平原则,那么你在承认“准人类”生存权的同时,也就必须承认动物的权利,否则就是“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这样,功利主义的动物权利论者就完成了有关动物拥有权利的证明。
“利益标准”和“极限案例”虽然成功地把动物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但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在逻辑上为降低人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铺平了道路。因为,以利益为权利标准,物种之间的界线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人和动物就被置于同一个道德平台上,成了可以进行生命比较的存在。而且,是利益就有大小,是“感受性”就有高低,以人和动物的这种共性为权利标准,会不会否定那些感知能力较低的残疾人、胎儿和婴儿的生存权呢?尽管这在开始时只是人们对环境伦理的一种担心,然而不幸的是,动物解放论者辛格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辛格在《实践伦理学》一书中提出,应按意识的发达程度即“生命的质(quality of life)”来划分所有生命,并以此来判定该生命的价值。由于胎儿和婴儿的生命价值和猪、狗的差不多,既然我们为了品尝美味可以屠杀动物的话,那么人工流产和杀婴就不应受到什么谴责。而且,由于大猩猩要比残疾婴儿的意识能力高,“因此可以说同杀死那些天生智障、非人格且不可能成为人格的人相比,杀死大猩猩更恶”[4](P117)。至此,辛格得出了可以对残疾婴儿实施安乐死的结论[5]。
这样,辛格在要求给动物权利的同时,却缩小了享有生存权的人的范围,在提升动物的道德地位的同时,却取消了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动物权利论所出现的这一状况就好比形式逻辑中内涵和外延的反比关系,当外延扩大时,内涵却相对缩小。这一反比关系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其他流派,诸如“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之中。它们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向时,都普遍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在要求“给自然物以平等的道德尊重”的口号下,正逐渐颠覆着“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信念。
同环境伦理学相反,生命伦理学则表现出高扬人的尊严、严格界定人格范围的倾向。这一倾向可以从生命伦理学的“人格”概念中得到证明。
“人格(person)”在生命伦理学中是一个能够决定人生死的关键概念。现代的生命伦理学为了使堕胎、对智障儿童实施安乐死以及停止对脑死患者的治疗等合法化,存在着用人格范畴对人类个体进行再分类、取消一部分人生存权的倾向。
这种人格论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由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其理论原型是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洛克和康德的人格概念。在西方近代哲学中,人格是自我意识和记忆的主体,也是权利(特别是所有权)和义务的主体。洛克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人格是“具有理性和反省能力,总是能够把自己看作是自己的思考的存在”。康德和洛克略有不同,他没有把人格单纯还原为自我意识,而是从道德的角度把人格看作是“理性自律的行为者”、具有“归责(Zurechnung)”能力的人。但是,“自律”和“归责”毕竟是以理性能力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和洛克一样,也把理性能力的有无当作评判一物是不是人格的标准。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康德讨论人格概念的初衷却是为了尊重所有的人,正像他把人格规定为“目的”,反对把人格当作“手段”那样,其目的是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人权。但是,现在的人格论和康德的初衷相反,它要把一部分人从道德和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中剔除出去。最早明确提出这一主张的是图利(M.Tooley),而后是辛格、恩格尔哈特(H.T.Engelhart)等人。图利认为,患有严重智障的婴儿因不具有自我意识而没有了生存权。辛格也沿着这一思路,把人区分为人格和人种的成员,最后得出了和图利同样的结论。恩格尔哈特为了避免图利和辛格等人的极端结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做法,即区分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格(person in a strict sense)”,另一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格(person in virtue of social)”。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识、理性、道德感觉和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这也就是康德的人格概念。所谓“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并承担着某种社会角色的人,比如婴儿、残疾人、植物人等“准人类”[6](P143-161)。“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无条件地拥有生存的权利;而“社会意义上的人格”,虽然享有生存权,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后者被赋予生存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人格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理或者道德共同体有影响,如果他们不能满足这一条件,那么其生存权就只能是相对的[7]。因此,“社会角色上的人格”虽然不同于非人格、物件,但是也不能同“严格意义上的人格”等值。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承认了可以从“手段”的意义上对“社会意义上的人格”进行利用。总之,在康德那里,人格还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概念,因为它让人感到了人的荣誉、尊严;而在生命伦理学那里,人格却成了冷酷无情的标尺,成为实验室里的标本、可以任意摘除的器官。
综上所述,在权利标准的问题上,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生命伦理学维持着近代以来的康德理性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传统,以高度的意识能力作为权利的基础,甚至还存在着自我意识主义的倾向;而环境伦理学则反对以自我意识、理性能力为权利的根据,试图把权利标准降低到感受痛苦的能力(感觉主义)或是否有生命(生命中心主义)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道德关怀的范围上,二者的理解也是截然相反的。环境伦理学为了确立自然物的道德地位,试图把动物、植物甚至大自然都纳入道德共同体的范围;而生命伦理学则试图把权利享有者的范围缩小,动植物自不必说,甚至还要把“准人类”也排除到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
环境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的对立还反映在对个人自由的理解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倾向是整体主义,主张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而生命伦理学则是一种把个人主义推向极致的理论,它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
我们知道,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资源有限和可污染空间有限)和“公共性”(大气、水和草地的公共性质)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凸显了在资源分配和环境责任上公平的分量,而且还要求对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其中主要是生殖和经济自由进行严格的限制,把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在自然界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关于环境问题的这一特点,笔者曾在《自由主义和地球的有限性》[8]一文中有所阐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环境伦理具有整体主义的色彩,它把地球人类整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体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这种重整体轻个体的价值倾向可能会导致对个人自由进行干涉。比如,为限制人口增长,国家实行强制性节育和鼓励人工堕胎的政策;为控制地球温室效应,严格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和加大对个人汽车消费的限制等。
日本的哲学家加藤尚武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的代表,他曾提出了“地球全体主义”的设想。所谓“地球全体主义”,是指个人和国家的自由应该服从地球整体的利益,从保护地球环境这一整体利益出发,世界各国必须对欲望和自由的总量进行限制。具体做法是,在环境问题上国家和个人不再有自我决定权,一切权力属于地球,代表地球整体利益的权力机关可以对国家、组织甚至个人进行干预。
但是,这种整体主义不仅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成立过程背道而驰,而且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直接冲突。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个体的价值要优先于整体,不能因为整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而且,人的生殖欲望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应该是最自由的两个领域,也是近代自由主义所要保障的基本权利,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是不能被限制的,限制它们就等于违背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原理。
与此相反,生命伦理学则充分尊重了自由主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的核心概念“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中得到证明。
“自我决定”也可称为“尊重自主性原则(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它是公认的生命伦理学的四大原则(自主性、不伤害、行善和公正原则)之一,是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的概念。
所谓“自我决定”,是指人对自己的行为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生死等拥有支配和决定的权利。它根源于近代自由主义的道德与政治传统,反映的是对个人的理性能力、自律、自我支配和选择、自由等理念的尊重。首先,它肯定了“自我决定”的能力基础,即前面所述的“对应能力”。在安乐死、人工流产等这类有争议的实践领域,当事者“对应能力”的有无还构成了决定人生死的最终的伦理依据。这与近代自由主义把人的意识能力看作是人区别他物的指标、看作是人获得尊严、权利以及享受道德关怀的依据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它强调人对包含自己生命在内的所有物拥有支配权。这一点,源于洛克等人建立的“所有权”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财产以及自己的身体拥有处置权。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身体的主人,如果把精子、卵子、胎儿以及身体器官都看作是他或她的所有物,那么现在备受质疑的借腹生子、人体改造、基因操作、器官买卖和移植等都无可厚非。再次,它贯彻的是“只要不危害他人就不能干涉”的原则。譬如,成年人出于宗教的理由拒绝输血,尽管这明显对该人不利,可是人们也必须尊重该人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拒绝权”、“自杀权”问题。这与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提出的“危害他人原则(harm to others principle)”是一致的。密尔曾写道:“对文明社会的成员,与该人的意志相反,正当地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对他人的危害。”[9](P224)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能够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该人的行为危害到了他人的利益。
“自我决定”在医疗层面上具体表现为“知情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知情的同意”这一用语最早出现在《赫尔辛基宣言》(1964年)之中,意思是在医疗实践中,患者或充当实验对象的当事者有获得相关信息、自主作出同意或拒绝决定的权利。这一概念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是前提要素,即患者或被实验者具有“理解和决定的能力”和“决定的自主性”,也即自律性(autonomy);第二是说明要素,即医生和实验者必须要向患者及被实验者公开实质性信息,对实验方法和治疗方法予以说明并提出建议;第三是同意要素,即患者或充当实验对象的当事者必须对治疗方案和试验方法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知情的同意”原则,其实就是“自我决定”概念的具体应用。如果没有充当实验对象的当事者或者患者的同意,实验者或医生对当事者进行实验或者对患者实验治疗就是违法的,即使这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从上述分析来看,生命伦理学可以说是对自由主义的全面拥护和继承,“自我决定”以及与其相关的“对应能力”、“所有权”、“不危害他人原则”和“知情的同意”等基本概念都体现着自由主义的精神。环境伦理则相反,它认为环境破坏恰恰是由于行使“自我决定”权所引起的,因此必须对个人的“自我决定”权进行限制。
通过对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比较、考察,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环境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人的伦理地位和个人自由的理解上是针锋相对的,它们的对立是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由于生命伦理的本质是自由主义,因此,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其实也是自由主义。第二,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本质是自由主义,那么,生命伦理学无疑是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应用到生命、医学领域的典范;相反,环境伦理学则显然是一个例外,它很难纳入到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中去。
注释:
①吴新文认为:“应用伦理学涵盖了理论伦理学,理论伦理学的存在意义在于其融入应用伦理学中并对把握、理解和解决应用伦理问题有贡献。在宽泛的意义上,当代道德哲学就是应用伦理学。”(参见吴新文《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性质与“学科”定位》,《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4期)赵敦华也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参见赵敦华《道德哲学的应用伦理学转向》,《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