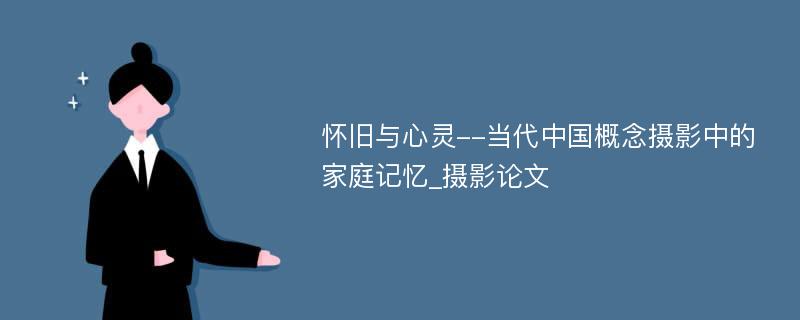
怀旧与招魂——当代中国观念摄影中的家庭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观念论文,记忆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当代观念摄影发展状况
中国当代观念摄影①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日益蓬勃的观念摄影艺术。摄影和观念艺术起初是一种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但这种关系被一些艺术家颠倒过来,成为一种专门以摄影形态为表现形式的先锋艺术创作,这就是观念摄影。观念摄影是一种以摄影为媒介的观念艺术创作,其实质是观念艺术在媒介上的一种延伸和演变。它是从观念艺术中抽离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创作手段和形式。相对于纪实摄影等其他摄影门类,观念摄影更注重图像观念在照片上的运用和把握,注重观念艺术的“挪用”概念(主要是以现成图像的挪用为主),以及试图“探究和探索摄影表现的本质”②。
1989年北京的“现代艺术大展”是当代美术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以“关注当下”为口号的中国“新潮”美术呈现多元化发展,艺术家们开始创作录像、装置、行为、摄影等方面的艺术作品,打破了美术为主的单一创作格局③。对当代摄影的众多研究都认为,在90年代中期,中国摄影的主流开始由纪实转向观念,观念摄影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④。中国当代摄影领域最早出现“观念艺术”这一概念,是在1998年4月28日的《摄影报》上⑤;此后中国摄影学界对“观念摄影”这一称谓及内涵都颇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对艺术家来说,摄影只是观念艺术的一种形式,是挪用的手段,其重点在于借由摄影传达艺术观念,它可以与其他艺术媒介任意组合。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观念摄影艺术家层出不穷,刘铮、荣荣、王劲松、洪磊、邱志杰、徐一晖、安红、杨福东、吴小军、庄辉、郑国谷、罗永进、刘树勇、莫毅、徐晓煜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频繁地在国内外参加展览,其艺术作品散见于各种观念艺术展。第一次明确使用“观念摄影”一词并举办的公开展览,是1997年由诗人兼艺评人岛子等人策划、于北京亚运村剧院举办的“新影像——观念摄影艺术展”。随后艺评人朱其也于1998年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了“影像志异——中国新观念摄影艺术展”。这两个展览带动了观念摄影展的热潮⑥。在期刊方面,1996年,前卫艺术刊物《新摄影》首次出现。由刘铮和荣荣创刊并编辑的这一期刊,是继停刊的《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后较为重要的艺术刊物。“星期六摄影沙龙”⑦等一些艺术活动也促进了观念摄影在学术理论方面的发展⑧。
在这些观念摄影作品中,艺术家再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或反映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巨变,例如传统景观的消逝(尹秀珍《诱惑》、王劲松《百拆图》),生活方式的改变(罗永进《新居民楼》、张大力《对话》)等;或关注日益多样化和分化的人群,例如都市中的底层市民(刘铮《国人》、赵半狄《下岗》)或“雅皮”的琐碎生活(杨福东《别急,我会越来越好》、郑国谷《阳江青年的生活与梦想》)等;或表现身体的认同变异与权力的身体书写,例如行走的身体语言与空间的关系(宋东《哈气》、马六明《芬·马六明在长城上行走》),身体展示和行为表演(邱志杰《纹身》、荣荣《苍鑫:踩脸》)等;或传达中国集体和个人记忆,建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例如政治事件的再回首(如宋东《哈气》、邢丹文《与“文革”同生》),对往日时光的怀旧与招魂(海波《三姐妹》、宋永平《我的父母》)等;或再现当代消费生活的重复与无奈,例如无处不在的商品符号(王庆松《我能跟您合作吗》、赵勤和刘建《我爱麦当劳》),对现代日常生活状况的反思(王岩《我想飞》、翁奋《骑墙》)等;或借由超现实主义表达对现实的批判,例如营造远古或超时空实现逃逸(马良《草船借箭》、洪浩《我的东西》),借由“3D”或“photoshop”技术实现艺术家的幻想世界(缪晓春《文化碰撞》、李小镜《夜生活》)等;或借由重复、戏拟等手法表现后现代主义风格,例如戏拟和解构经典名作(周俊辉《雅典学院》、王庆松《老栗夜宴图》),营造类似波普艺术的重复与类象(苍鑫《亲吻多样物品》、崔岫闻《洗手间》)等。
其中一些观念摄影作品探讨了“家庭”这一主题。从北京艺术家冯梦波创作的互动式装置艺术《私人照相簿》开始,家庭老照片从简单的记录功能转变为艺术创作的材料、手段和灵感来源。荣荣《1996》、王劲松《双亲》、尹秀珍《尹秀珍》、郑连杰《家族岁月》、海波《三姐妹》、宋永平《我的父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们往往不单纯是平面摄影作品,也将摄影和装置、行为等艺术类型相结合。其中最多的是摄影装置艺术,即将摄影作为装置艺术的材料之一⑨。本文不过多考虑装置的作用,仅分析平面的摄影作品,尤其是艺术家对家庭老照片的采用。艺术家们借家庭老照片表达对过去时光的回忆,通过“定格”的历史和现状的对比,思考时代发展和变迁的脉络。
这些作品中的家庭老照片构成了当代艺术中个人化的微观家庭史,并通过艺术处理呈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本文将细读以上作品,分析艺术家们以家庭照片再现记忆的两种方式:怀旧与招魂。借由20世纪90年代的老照片热潮,探究这些艺术作品中的家庭老照片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思考不同时代中国式家庭的影像特征。
一、“老照片热”与家庭摄影
上文提到的观念摄影文本,也属于家庭摄影的范畴,只不过是较为特殊的家庭摄影:以家庭照片为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摄影形式。家庭在摄影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尔迪厄曾在《论摄影》中指出,摄影这一技术最传统的价值就是家庭摄影;家庭摄影从功能上令摄影快速普及,也作为一种“家庭崇拜的仪式”被保留,实现了摄影“社会功能的内在化”⑩。从概念上说,只要照片内容同家庭相关都可成为家庭摄影,其中人像拍摄构成了主要部分。照相机虽在19世纪中叶便传入中国,但大规模进入中国家庭还是近三十年的事(1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众摄影活动变得更加司空见惯。家庭摄影强调纪实性和纪事性,并不强调个人观念的表达;换句话说,一般的家庭摄影同艺术或观念摄影是很远的。只有在艺术家将家庭照片作为材料进行艺术创作、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时,这些以家庭为主题的摄影作品才成为观念摄影。这些作品中包含了家庭摄影的纪实性和观念摄影的观念性,这两种特性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
作为记录家庭生活状态的一种影像形式,家庭摄影保存了家庭在某个时间点上的人物样貌、神态、动作和衣着;数年之后,这些家庭摄影便成为发黄变旧的老照片。90年代有关家庭摄影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就是“老照片热”(12)。它波及的范围很广,从时尚餐厅墙壁到古董市场的私藏照片册,家庭老照片成为人们用来怀旧的流行热潮。这一文化现象是理解90年代家庭摄影的重要背景,也是观念摄影采用家庭老照片作为灵感和材料的重要推动力。
1996年末,山东画报出版社发行了《老照片》丛书。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期共售出一百二十万册。它之所以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保持了底层化和平民化的特色”,在“数百万的普通读者中唤起了一种亲切之感”(13)。这引起了大量的效仿者,很多出版社都以“老照片”为题发行了很多书籍刊物,如内蒙古出版社的《老相册》和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百年老照片》。后来一些出版物越来越针对某一特定题材,例如城市与建筑、生活方式和服饰装束、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著名学府及机构、早期摄影师作品以及特定人群和时代(14)等,带动了文化上的怀旧之风。这股热潮到21世纪初逐渐衰退,从印刷形式转入了网络。
这些老照片大都来自私人照相簿,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们和宏观历史叙述不同,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而是讲述平民百姓的零碎经历,可以说构成了个人化的微观历史(15)。尤其经历了“文革”等政治事件,遗留下来的个人和家庭影像更具有私人历史的记录价值。《百年老照片》丛书的卷首语说:“一张张老照片,直面历史的丑恶与美善……一个个瞬间,构筑了波澜起伏的历史。让历史还给历史,让历史馈赠今天。”(16)在同年出版的《私人照相簿》中,刘心武在《影子大叔》一文中肯定了这些照片的价值意义:
我觉得尽管经过“文革”的浩劫,中国大地上的旧照片总量有惨痛的锐减,但被侥幸保存下来的,肯定也还是一个客观的数目。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个人都还有自己的私人照相簿或照相匣,里面仍旧珍藏着无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原版”。当然,很多人是不肯将它们公诸于社会的。这种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但也会有为数不少的人乐于或经过说服应允将一部分私人照相簿上的“原版”提供给社会,加入当今的“信息大爆炸”,以丰富和增进世人的情感和思想。(17)
这些传达了个人生活回忆的私人照相簿大多是家庭摄影,是家庭成员的个人照或合照,很多是全家福。在2007年《新天地》杂志的“影像珍藏”栏目回顾了“中国人20世纪全家福”,它选取了20年代、40年代、50年代、80年代等不同时期的全家福,显现出不同时代的家庭特征,例如1919年裹小脚的家庭妇女,60年代每个人都别着毛主席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80年代“富裕起来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在新居前合影,等等(18)。这些照片似乎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家庭老照片表达记忆的力量,也深为编辑者所知。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丛书第一辑中,编者以“一种美好的情感”为题,叙述了家庭记忆的作用:“回忆是人类独有的权力。它不仅是情感的投入,而且是一种理智的收集,收集掉落的一切,进行崭新的排列,于是生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结果……那瞬间形象的定格,常常含有难于估量的信息和意蕴,似乎说也说不完。”(19)
而这些说不完的意蕴,在当代观念摄影中继续讲述。受“老照片热”的影响(20),中国先锋艺术家也纷纷以老照片为文本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属于观念摄影的范畴,和上述老照片印刷品不同(21)。1995年,时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于北京召开之际,中央美术学院的隋建国、展望和于凡策划了一场题为“女人·现场”的非官方装置艺术,第一次使用家庭照片来叙述个人历史。此后很多先锋艺术家开始探索老照片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怀旧:灵光消失的年代
在这些讨论家庭的观念摄影作品中,怀旧是最重要的主题。常见的表现方式是将家庭老照片与当下拍摄的家庭新照片进行对照,构成过去和现在影像的对话。
1995年冯梦波创作的《私人照相簿》装置艺术使用了若干组老照片,每一组都将不同时代的照片利用电脑技术合成一张,记录不同岁月的家庭人、事、物。它们再现了某一年代的风貌,展示了艺术家的祖父母、父母和他自己三代人的生活和社会背景。当这些照片合成一体时,欣赏者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似乎前世、今生、来世在同一个时空中展演。
同样是将过去和现在的家庭照片互文对照,郑连杰2000年的《家族岁月》并未采用电脑技术,而是以摄影的叠加进行表现。他翻出自己家庭1957年的一张全家福(其背景为天安门广场),同儿子一起手执放大的老照片在天安门广场拍摄了另一张照片。老照片中的全家福人数众多,大人们都穿着清一色的服装,显示了浓厚的时代特色。新照片定格的地点和四十三年前并无二致,但仔细观察能发现老照片中的背景应该只是布景。这也反映了不同时代家庭摄影在技术、布景和构图上的显著差异。老照片居于画面中央,并由父子二人托举,从而获得了一种被强调的地位,同时被强调的还有它所隶属的过去时态。作品以一种后设叙述(22)的方式,强调了新旧两张照片的关系,将摄影的主题指向过去和现在的对比。
以上两个作品虽然手段不同,但都实现了在一个文本中将历时的照片共时展现,在一张照片内部进行时间的对话。同样是记录时间的流逝,海波1999年的作品《她们》(以及《他们》)系列使用了一种近乎直白的手法,将两张不同时代的照片并置。前一张是一群年轻女子于1973年的集体照,年轻的脸上闪耀着坚定的信念,后一张则是二十七年后拍摄的,仍带着灿烂的微笑,但岁月还是在脸上留下了痕迹。相对于1973年完全相同的衣服,1999年的装扮变得多元,很多人还佩戴了饰品。
这几幅作品所传达的艺术家意图是明显而统一的,即对时间流逝的记录以及对过去时代的记忆。这些记忆是集体生的,其运作方式是由叙述时间所激发的。在这些作品中,叙述时间的最大特点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但与现在的影像相比,老照片都因其过去时而被强调,观者也自然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对老照片的部分投注更多的感情——或留心过去家庭的人员构成,或在意旧时代的衣服和物品摆设。因为对现在的观者而言,现在的影像是熟悉的,过去的影像是有距离感的。对这些老照片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怀旧也是艺术家利用这些老照片进行创作的主动意识。海波曾说他的作品“并不仅仅是要表现出人与社会的变迁,时光的流逝,更重要的是我企图再现往日的时光,哪怕是在快门按动的瞬间”(23)。怀旧对过去的记忆不仅来自老照片在时间上的过去,也来自于老照片的光晕。
根据本雅明的解释,在摄影史上,胶印法的发明,修饰、润色技术的发展都使照明度提高,照片上的黑暗则被排斥,这种做法似乎是努力模仿光晕,却反而消灭了图像中的光晕。真正的光晕是原始照片中的“自然黑暗”,而不是人为的后期制作(24)。比较70年代和90年代的照片(如《家族岁月》和《她们》),会发现在曝光和画面质感上有明显的不同:旧照片的曝光度低,照片以黑色调为主,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90年代的照片则较为轻快明亮。因此,老照片的历史感不仅来自对象本身,也来自摄影技术。虽然我们无法断言光晕在当代照片中的消失,但从摄影技术本身来看,新照片缺少老照片的沧桑感和沉重感。
怀旧所表达的情绪也不仅是对过去的向往,同时也来源于某种痛苦和焦虑感。在病理学上,按照茨威格曼的说法,怀旧作为一种思乡恋旧的情感再现,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对剧烈和变动的现实生活的不满,继而转为一种寻求自我同一与连续性的弥补,弥补过去和现在的断裂”(25)。当被问及为何不断以摄影碰触记忆时,海波也有类似的解释:
这纯属是我的一种精神疾病。一个人的童年对他的一生影响是巨大的,60-70年代的中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至今我仍感觉我自己的一部分还生活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的内心活动与外在环境产生了断裂,有时候你会因为生活在“过去”而感到痛苦,但这没办法。一把刀可以切割任何东西,但永远削不到自己的手把儿。好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创作和表现这种“疾病”就是治疗它的惟一方法。(26)
所以,海波的怀旧更多是治疗创伤的需要,是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断裂,寻求“连续性”和“自我同一”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老照片也能激发观者对那个时代的回忆:那个时代的服装、李铁梅式的发型、革命“样板戏”、天安门、红小兵电影院等等。这些带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是艺术家有意传达的,令观者怀旧的方式是“冲击”;而观者个体则可能会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某个时刻,对照片的某个细节产生联想和感受,这种方式是“刺点”(27)。
在海波《她们》系列之六有一个副题:面向未来。等到未来某一天,现在的照片也会发黄变旧,成为老照片,成为怀旧的对象;现在的“她们”会成为未来的记忆。怀旧在时间的流逝中也具有了相对性。整个构图其实缺失一张未来的照片,而再过二十七年,或许她们已经不在了。因此,这张照片真正的“刺点”或许不是来自人物或图像,而是这个副题——它预示着死亡的来临。从怀旧到死亡,文字和照片之间的张力赋予这幅作品多重诠释空间。这有如麦茨对摄影的论述:被拍摄的永远是过去,因此照片中人“被看见的部分已经死了”(28)。更加反讽的是,1973年时“面向未来”其实是一句朝气蓬勃的宣言或祝语:大家一起为了未来而努力。从这个层面上看,海波的这一作品再现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方向: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死亡。
三、死亡叙述
在1999年的观念摄影作品《三姐妹》中,海波同样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思考和对过去时光的怀旧,却以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触探了死亡主题。同样是将新旧两张照片并排,我们赫然发现,旧照片中的三姐妹只剩两位。健在的两位姐妹虽然脸上都浮现慈祥安逸的神情,但岁月的沧桑在她们的身上留下了痕迹。由于两张照片的构图完全一致,因此新照片中缺席的位置直接展示了死亡。
另外一位艺术家不仅展示死亡,而且记录死亡。宋永平作品《我的父母》系列是他从1998年到2000年拍摄的父母从生病到去世过程的照片,直接呈现了这对老年夫妻的病中生活。其中一幅是将一张1999年的照片和上世纪50年代的照片并排在一起,呈现出生死之间的对比。后一张照片里,青春洋溢的母亲和英气勃勃的父亲笔直地站立着,透露出那个时代意气风发的浪漫情怀。在后一张照片中,两位老人手牵手站着,上身衣物褪去,露出皮肤上深深的旧伤疤,表情空洞,干枯的双眼盯着前方。
这幅作品其实传达了很多信息,政治的反讽、疾病的隐喻都是可以察觉的“冲击”。但我所关注的是它对死亡的叙述,或者说预知死亡的叙述。正是这种迫近死亡的危机,促使宋永平开始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他本来“无意成为一个摄影家”,但当1997年父母相继病重并送入医院后,他拍了些照片,本想留做素材以备绘画之用。但当他将胶卷在路边小店扩洗出来时,他“完全被那些有如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惊呆了”,并且“有了一种房屋将要倒塌的感觉”。他曾想逃避这种被死亡威胁的心理,但“最终被这种感觉牢牢抓住”(29)。
和海波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她们》不同,这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逝去的绝望和等待死亡的悲观,而且作为拍摄者的儿子是记录这场死亡过程的作者。父母的无力感和儿子的无力感叠加起来,强调了生命的无常。这里的一个悖论是:摄影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死亡的艺术,如何能够抵抗死亡?
几乎所有摄影理论大师都同意摄影的死亡特性。罗兰·巴特在照片中看到了死亡,“死亡就是照片的外貌”(30)。麦茨认为“静止”和“无声”作为摄影的独特语汇,本身就表达了与死亡的直接关系——它们不仅是死亡的两个客观方面,而且是死亡的主要象征(31)。杜博斯将照片喻为镜子,而且“比现实的镜子更可信,在那里,我们见证着自己的成长,见证着我们的每一年”,实际的镜子伴我们穿越时间,但在照片中,我们“显不出任何变化”(32)。
这些仅仅是摄影本身的死亡性质,当用来保存那些已经死亡(如《三姐妹》)或逼近死亡(《我的父母》)的家庭成员时,照片就具有了双重死亡的性质:一方面照片本身再现了死亡,另一方面照片的内容叙述了死亡。像宋永平一样的拍摄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招魂者的作用:为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亲人招魂。宋永平意欲挽留生命的方式,使被摄者的灵魂进入另一个空间和时间——影像世界。一旦快门按下,照片中的世界时间完全静止,即将逝去的生命也随时间的静止而得以保全。正如麦茨所说:“摄影诱骗客体逃离一个世界而进入另一种时间。照片的拍摄是当下和确定的,就像死亡和在无意识中物恋的构成一样,是对孩童时光匆匆的一瞥的固定,此后将不再改变且永远生动……对于每一幅照片,那微小的时间片段会残酷地永远逃避一般的命运,由此抵御自己的缺失。”(33)
不只如此,宋永平将拍摄的照片与几十年前的老照片并排,成为一种时间或死亡的叙述,这可谓以影像的方式书写死亡。有学者提出“书写即招魂”(34),叙述的过程其实就是招魂的过程。所招之魂何去何从?“鬼之为言归也”(35),死亡亦即回到人所来之处。于是,招魂是对抗时间的线性流逝、沿着时间逆流而上的实践。
宋永平这一系列的作品发表之后,很多人对艺术家产生了道德方面的质疑和批评,焦点问题是艺术家所拍摄的父母亲松弛的裸体——在东方家庭语境中,父母的身体是一个禁忌。宋永平后来也发表文章坦诚自己的“不孝”,但仍认为他的作品“把这些情同家丑的悲凉情景昭示于天下”的原因,是“想通过对平常百姓卑微而真实生活的关注表达他的爱慕之心,也为了纪念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36)。
从家庭的角度看,这种拍摄实践记录的其实不仅是个体或身体的死亡,也是一个东方传统家庭的解体。在1998年父母住院之后,宋永平因为工作赶赴美国,但“心里觉得特别难受”,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艺术创作而全心全意照顾垂危的父母(37)。因此,在谈到《我的父母》时,宋永平认为它展示了中国当下的现状,即越来越多的父母到老年时缺少子女的照顾,这个问题亟待解决(38)。
对于父母的照顾和赡养问题,也有一些观念摄影有所表现,例如王劲松的《双亲》。王劲松在1998年以“采样”(39)的方式拍摄了很多张老年夫妻的合影,并将其中一些整齐排列在一起,以拼贴的手法组成摄影装置。每一张照片的构图几乎完全一样,都采用摆拍的方式,端坐正对照相机镜头。同样是双亲题材,相对于《我的父母》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双亲》中更多地弥漫着祥和平静的氛围。这种氛围不仅来自被拍者面对镜头安逸的微笑,而且来自彩色照片恰当的曝光度。其摄影语言取自中国普通百姓的留影方式,即“稍加修饰的着装和环境,正经端庄的姿势,以及典型的中国普通家庭的布置——温馨、喜气但艳俗”(40)。作品中人物平和端正与知足常乐的姿态也是中国百姓传统的精神状态。
《双亲》直面老年人生在社会变革中的位置,对于不同身份、阶层、阅历和环境的老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给予直白的再现。面对这样的作品,观者不禁要问:经历风雨的父母双亲已年迈,赡养他们的子女是否能够尽到照顾的责任?作为家庭摄影或全家福,这些照片中的子女都是缺席的。20世纪末的中国家庭,多数子女不与父母合住,能够相濡以沫度过晚年的只有父母彼此。因此,照片安详平和的表面下,暗藏了孤独、寂寞、无奈的情绪。从这个角度来看,《双亲》和《我的父母》有同样的社会关怀。
余论:“血缘线”与集体记忆
从《私人照相簿》到《三姐妹》,从《家族岁月》到《我的父母》,这些作品都利用家庭老照片进行观念创作,以怀旧或招魂的方式再现家庭记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以家庭记忆言说时代变迁,力图以老照片为材料,将家庭的图像史转换为共同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传达出中国人在特定时期独特的生存体验。
家庭摄影保存了社会集体的记忆。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家庭摄影表现了社会记忆的核心”。因为摄影的年代顺序,也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时间顺序,所以人们在观看旧时代的家庭摄影时唤起过去的时代记忆,而“过去的记忆令现在的整一性更加巩固”。这不仅是一种怀旧,也是一种招魂;因为“家庭摄影通过对过去时间的定格,找回了对逝者(或人的过去)的记忆,记起他们的过往,并且在生者(或人的现在)身上延续”。以这种方式,家庭摄影“证明并实现了家庭和社会记忆的连续性”(41)。
沟通两个时代的方式有很多种,家庭摄影提供了血缘线的连接方式。例如《家族岁月》,父亲和儿子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家里长辈;或者《私人照相簿》,将父亲和祖父的老照片同自己的照片相互叠加和比照,令人体会到血脉相连的家族历史。不同时代的记忆以血缘线的方式相连,不同之处除了服装、发型、动作等面貌之外,还有家庭成员的构成:上一代的全家福成员远远多于下一代,或者说从大家庭变为小家庭。所以很多人不断拿起从前的全家福,缅怀和回顾大家庭的时光。张晓刚曾创作了著名的油画作品《血缘:大家庭》系列,作品充满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和思考,探讨了家庭血缘线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大家庭》系列虽然是美术作品,但取材于摄影。镜头中的家人或坐或站,集体目视前方,表情庄严而神圣,衣冠整齐而矫情。这种纪念照是当时家族摄影的写实,我们在《她们》或《家族岁月》中都能看到相似的构图、衣着和表情。和观念摄影家一样,张晓刚的创作灵感也来自老照片。他说:“1993年我刚开始画《大家庭》时,是基于旧照片的触动,我无法说清楚那些经过精心修饰后的旧照片,究竟触动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哪一根神经……家庭照这一类本应属于私密化的符号,却同时被标准化、意识形态化了。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42)
他还说:“《大家庭》对我而言,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43)他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血缘牢不可破”。在该系列的每一张画中,都有一条细长的红色血缘线,连结着画面中每一个家庭成员,也连结着每一个在画面中出现的中国人。因此,血脉相连不仅在家族内部,也在整个国家民族之中。牢不可破的血缘连结了个人、家庭、集体、国家,沟通了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因为血缘线而互相连结,并在不同时代传承。这正如张爱玲在《对照记》中看到祖父母老照片的感受:“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44)那些在家庭相簿中静静躺着的老照片,也在观念摄影展览中进入公众的视线,成为文化生产的一环。而现在的照片,有一天也会成为私人相簿中的老照片,再现属于这一时代的独特记忆。
注释:
①在中国艺术界,“观念摄影”有很多提法,如先锋摄影、新摄影、前卫摄影、实验摄影、概念摄影等。它可以包括较通俗的说法“艺术摄影”和较正规的分类说法如“表现主义摄影”、“抽象主义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等等。在语义层面,它与写实摄影或纪实摄影等语汇相对应存在。从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状况来看,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是较为重要的两种摄影形式,但这并非惟一的划分方法。而且,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一直分属摄影和美术两个领域。
②美国纽约摄影国际中心编《美国ICP摄影百科全书》,王景堂等译,中国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
③中国当代摄影的文化定位一直是以新闻现实主义为主潮的。1976年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四五运动摄影纪实”和1979年北京“四月影会”开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个人纪实摄影,可看作摄影开始偏离主流的标志。而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张海儿、韩磊、袁东平、吕楠、赵铁林等人开始将摄影镜头对准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试图呈现一种“对象的存在本质”。他们的作品都是中国纪实摄影的重要代表作。而从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开始到90年代中期,很多艺术家开始从事观念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的创作,观念摄影达到一个实验高峰期(参见朱其《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载《中国艺术》2004年第2期)。
④例如舒阳《从观念摄影到新摄影》,载《中国摄影家》2003年第5期;凯伦·史密斯《从零到无限——90年代中国当代摄影之发展》,巫鸿主编《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澳门出版社2002年版。
⑤当时的提法是“观念主义”,出自王虎、王友身、陈淑霞、刘庆和《我们的作品等待社会的检验》,载《摄影报》1988年4月28日。
⑥具体可参见岛子《新影像:当代摄影艺术的观念化》,载《现代摄影报》1998年第1期。
⑦“星期六摄影沙龙”是中国观念摄影家组织的第一个讨论小组,于1997年9月成立。他们不仅举办展览,而且发表观念摄影研究评论文章。
⑧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念摄影的发展历程,可参见巫鸿《过去与未来之间:中国当代摄影简史》,《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60页。
⑨关于摄影装置艺术的概念及类型,可参见邱志杰《拼贴在环境中:摄影装置》,《摄影之后的摄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74页。
⑩(32)(41)吴琼、杜予编《上帝的眼睛——摄影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第43页,第38-39页。
(11)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照相业有了长足进步,到1985年国产相机的社会保有量有800万架,为中国家庭摄影的蓬勃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见《家庭摄影大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2)(13)(15)巫鸿:《“老照片热”与当代艺术:精英与流行文化的协商》,《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第161-185页,第163页,第169页。
(14)例如《老城市》丛刊,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2000年版;《老新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北大老照片》,中国对外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等。
(16)杨熙越、石仁主编《百年老照片》,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7)刘心武:《影子大叔》,《私人照相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18)山鹰:《中国人20世纪全家福回放》,载《新天地》2007年第11期。
(19)《书末感言》,冯克力编《老照片》第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
(20)或者说,观念摄影对老照片的采用和大众文化“老照片热”是并行发展的,都在90年代中期起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按照巫鸿的观点,90年代“老照片艺术品和大众读物经历了平行的变化”(巫鸿:《“老照片热”与当代艺术:精英与流行文化的协商》,《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第181页)。
(21)巫鸿总结过当代艺术中的老照片图像和大众文化的老照片的“五点不同”(详见巫鸿《“老照片热”与当代艺术:精英与流行文化的协商》,《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第170-171页)。
(22)“后设叙述”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小说,戴维·洛奇(David Lodge)将后设小说(或元小说)定义为“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叙述方式也可以用以解读图像。例如在《家族岁月》中,照片之中又含有照片。不仅如此,艺术家暴露了自己创作照片的过程,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关于图像(老照片)的图像(新照片)。
(23)转引自栗宪庭《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摄影——代序〈与我有关〉实验艺术图片展》,见http://wwwionly.comcn/nbo/zhanlan/zhanlan_2169.html。
(24)Walter Benjamin,"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in 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Technological Reproductbility,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86-287.
(25)Charles Zwingmann,"The Nostalgic Phenomenon and Its Exploitation",in Charles Zwingmann and Maria Pfister-Ammende(eds.),Uprooting and After,New York:Springer-Verlag,1973,p.29.
(26)《海波的摄影作品》,载《中国摄影家》2002年第10期。
(27)“刺点”和“冲击”两个概念来自罗兰·巴特,详见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5页。
(28)(31)(33)Christian Mets,"Photography and Fetish",in Carol Squiers(ed.),The Critical Image:Essays on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Seattle:Bay Press,1990,p.158,p.157,p.158.
(29)(37)(38)刘淳:《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在乎自己能做什么——宋永平访谈录》,载《北方美术》2002年第1期。
(30)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第9页。
(34)王德威:《魂兮归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35)就字源而言,“鬼”和“归”互训,故“鬼之为言归也”,见《尔雅·释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61页;或“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见《礼记·祭义》,(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757页。
(36)转引自舒阳《从观念摄影到新摄影》,见http://art china cn/xinmeiti/2008-05/07/content_2209218.htm。
(39)“采样”摄影是指根据类型学的原则,“将同一主题,甚至造型本身也极为相近的对象进行拍摄,然后拼贴成为棋盘的格局”(详见邱志杰《采样时代:数量的意义》,《摄影之后的摄影》,第119-125页)。
(40)栗宪庭:《1996-2006王劲松观念摄影10年》,载《中外文化交流》2006年第8期。
(42)欧阳江河:《大家庭:与张晓刚对话》,载《东方艺术》2007年第6期。
(43)《张晓刚:挖掘生存记忆》,载《华人世界》2009年第2期。
(44)张爱玲:《对照记》,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