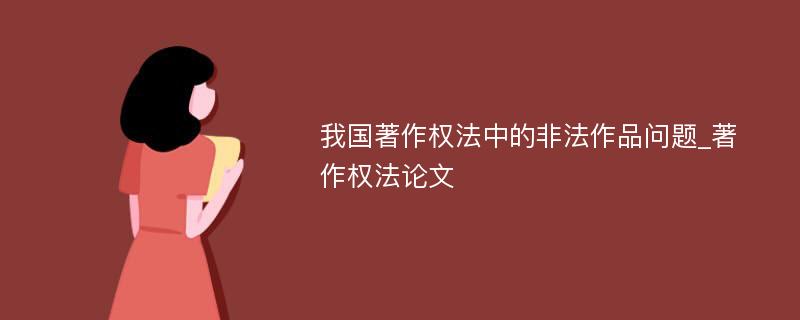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违法作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权法论文,我国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著作权法》对违法作品的否定态度十分坚决,其第4条第1款规定:“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在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之初,学界就存在着对该条规定的批评。理由是该规定违背了版权自动保护的国际原则,抹杀了我国《著作权法》的民事权利法的性质,不恰当地用调整不平等主体的纵向关系的行政法律手段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等等。① 然而,当时的立法者并未接受这些意见,郑成思先生就此曾说明:“当年列这一条的初衷正是要想指出禁止出版的作品根本不享有版权,只是表述为‘不受保护’更易被人接受。”②
在我国《著作权法》通过之后,对于违法作品问题的讨论仍然有其必要性,因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悬而未决:“违法作品”究竟是指内容违法还是指程序违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应当如何使这一规定既发挥其保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又确保其不与国际著作权公约相冲突?2007年4月,美国向WTO提起两项针对中国的争端解决磋商请求,即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及执行的措施案和中国影响特定出版物及音视频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及发行服务的措施案。在“美国诉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及执行的措施案”(DS362)中,就包括一项专门针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诉求。立法的模糊性加上后续研究的缺位,令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国的谈判代表直言承认,美国的主张“涉及中国法律中复杂难解的领域……在实践中缺乏或者说没有以资借鉴的经验。”③ 这直接导致WTO争端解决机构就“美国诉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及执行的措施案”所成立的专家组对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及相关制度进行独立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著作权法》第4条不符合中国所承担的WTO条约义务,违反了《伯尔尼公约》第5条第1款(该条由TRIPS协定第9(1)条纳入到WTO义务中)和TRIPS协定第41(1)条的规定。④
有鉴于此,本文就违法作品问题进行独立的、实证法学上的研究,希望弥补此前的缺憾,为今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违法作品是指内容违法还是程序违法
(一)实证法上的规则
有学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应当仅仅指内容违法的作品”,⑤ 有的司法判决也采用了这种“内容违法说”。⑥ 在上述WTO纠纷中,中美双方所争论的也只是“内容违法的作品不受著作权保护”是否违反中国的WTO义务。笔者认为,尽管将违法作品问题限制在“内容违法”范畴,无论是从国际谈判的角度还是从某种价值关怀的立场出发,都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如果我们秉持严谨的实证分析法学研究路径,就会发现: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严格区分甚至可以说是未意识到要区分“内容违法”和“程序违法”。
首先,对于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表述,从文义上无法获得“仅仅指内容违法”的理解。该法条中“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属于典型的援引性规范,任何其它法律法规中只要存在对作品出版、传播的强行性规范,都可能直接导致不符合这些规则的作品成为“依法禁止”的作品。而程序性规则往往都是强行性规范,一旦不能满足这些规范所设立的前置程序,作品的出版、传播便也存在合法性上的疑问。因此,从单纯的文义解释是不能推出“内容违法说”的。
其次,在我国各种立法文件中,存在着许多关于作品不满足程序要求即不能出版、传播的规定。有支持上述“内容违法说”的论著援引了2002年2月1日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中所谓“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就是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所列举的10类内容的作品。⑦ 但这种判断并不完全正确,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禁止出版发行的并不只是这10类内容上违法的作品。例如,与《出版管理条例》同属行政法规,并且同时实施的《电影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不得进口、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片。”也就是说,“获得许可证”是摄制、发行、放映、进口、出口电影作品的行为合法的前提性条件,如果没有获得许可证,则这些作品当然都属于“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又如,同样与上述两个法规同时实施、效力等级相同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重大选题音像制品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不得出版。”换言之,如果没有履行报备案程序,涉及“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是不得出版的,这当然也属于“依法禁止出版”的范畴。再如,2002年文化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音像制品进口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复制、批发、零售、出租、营业性放映和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未经文化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据此,“未获得批准进口”的国外音像制品在中国的出版、复制及其它传播行为,也是“依法禁止”的。如果将其它效力等级相对更低的规范性文件纳入研究范围,类似的立法还有很多,而这些法规中所涉及的都是程序性违法。由此可以推断,在有权机关作出专门解释前,至少在实证法意义上不可以认为“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仅指“内容违法”的作品。
最后,我们可以从个案角度来进行分析。以2007年的著名香港影片《色戒》为例,为了符合审查尺度,进口到中国内地的《色戒》版本和在中国香港地区发行的版本在内容上是不同的。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如果进口到中国内地的版本中的删剪是由著作权人而非行政机关完成的话,那么它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作品。⑧ 中国内地版本的《色戒》获得了进口许可证,属于“合法作品”,自应获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至于中国香港地区发行的《色戒》版本,由于其在内容上不符合中国内地的电影发行要求,也不可能通过相关的电影审查制度,所以属于“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进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规定“不受本法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一部电影中并不含有审查当局难以容忍的内容,只要这部电影(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没有提交相关行政部门审查,就都不能获得发行和放映的许可,根据上述《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都不能予以出版和传播,仍然属于“违法作品”。其法律后果是:如果某人将未取得许可证的香港版《色戒》DVD予以盗版复制,然后在中国内地进行发行,或者将香港版《色戒》的数字文档放置在互联网上供他人下载,由于这个作品在程序和内容上都不是“合法”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规定“不受保护”,所以尽管发布人可能会因为“传播淫秽作品”一类原因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检控,《色戒》的著作权人却无法获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因而不具备向该发布人提出侵权主张的资格。
(二)“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导致作品属性不确定
若对违法作品问题作出更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所谓程序与内容之间,并不能够真正被区分。一方面,程序上的不合法,将直接导致一件作品被归入违法的范畴,而这件作品中的内容,则很可能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另一方面,内容上不合法的作品,如果暂时没有被审查者所发现,其仍然可能被予以发行和传播,而当审查者发现的时候,作品传播过程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甚至完成了。因此,在有权机关修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之前,作品的属性是不确定的。举例而言,假如某甲写了一本包括性爱内容的小说,这本小说出版后很受欢迎,某乙盗版复制了五千本并准备销售,某甲因此起诉某乙,主张著作权侵权责任,而此时国家出版管理机关将这本小说认定为淫秽作品,禁止出版、传播。那么,某乙完全可以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规定,主张这本小说的著作权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在刑法上,某乙也不能被判处侵犯著作权罪,而只能被判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罪。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程序决定了内容,同时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又概括性地排除了“违法作品”的著作权,所以“没有经过审查程序”(而非“已经经过审查程序被确定为内容违法”)的作品究竟是否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三、违法作品是否仍受著作权法保护
(一)国内著作权法视角:否定的答案
德国著作权法理论认为:“那些含有不道德内容的作品,只要刑法禁止它们使用,在这些作品上就不产生各种积极权利,而只产生消极的著作权权利……针对第三人的权利(比如针对剽窃行为有权请求法律保护)却仍然存在。”⑨ 1979年美国发生的Mitchell v.Cinema Adult案,也是采取这种思路作出的判决。⑩ 在该案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的关键性理由在于:版权法中没有一个地方表明国会打算排除对淫秽内容的保护,因此对淫秽作品的作者而言,其仍然有权获得侵权救济。(11)
但是,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说,上述观点之成立需要一个前提:法律中承认(至少不否认)违法作品的著作权。和美国版权法一样,中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基础决定了著作权属于一种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在这一性质的决定性作用下,授予哪些作品著作权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选择。我国《著作权法》可以在第5条中排除对官方作品和时事新闻的著作权,当然也可以在第4条直接排除了一切“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的著作权。因此,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内容违法”还是“程序违法”,只要是“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就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同时,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即声明其立法目的是“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在国内法层面,并不存在法教义学上的合法性问题。
(二)国际著作权法视角:“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缺乏正当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国际公约。下文首先对“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作出分析,然后再对内容违法进行研究。
中国所加入的著作权国际公约以“作品自创作完成时自动产生版权”为原则,《伯尔尼公约》第3条规定:“作者为本同盟任何成员国的国民者,其作品无论是否已经出版,都受到保护。”而我国著作权法上有关“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的规定,显然与该原则相冲突。但是,仍有学者认为:“《伯尔尼公约》和一些国家也有对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给予法律保护的规定……因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符合国际惯例。”(12) 其所说的公约规定,应是指《伯尔尼公约》第17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各国“基于公共秩序、道德、健康或环境原因”,(13) 对包括权利人在内的任何人对特定作品的使用,都可以予以禁止。而笔者认为必须澄清的是,《伯尔尼公约》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要求各缔约国赋予作者“排他性”的著作权,也即公约只要求各缔约国保护权利人“授权或禁止他人从事行为”的权利,(14) 至于权利人“自己从事”复制、发行等行为是否会触犯各国的国内法,则不是公约所涉及的范围。换句话说,强行法对作品传播的禁止与公约无关,但强行法禁止传播的作品,如果仍然被他人传播了,著作权人仍得依其消极权利向行为人主张版权。WIPO秘书处在解释其它问题时,也提及这一观点。(15)
四、运用“三步测试法”检视“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的规定
上文已论证“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与国际著作权公约相冲突。那么,“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是否也与国际著作权公约存在冲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运用国际知识产权纠纷中著名的“三步测试法”予以解析。
(一)“三步测试法”的适用性问题
“三步测试法”是指在判断各国国内法是否违反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时候,以三个标准来作出评价,即国内法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和例外规定应局限于:(1)特定的特殊情形。(2)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3)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正当利益。这三个标准首见《伯尔尼公约》第9条,但仅涉及复制权;TRIPS协定第13条(16) 将其扩展至所有版权专有权,包括出租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第10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第16条再次采用了此标准。由于TRIPS协定对上述判断标准的引入,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度又远远大于其它国际条约,因而其成为一项重要的判断规则。
就通常情况而言,“三步测试法”的目的在于防止各国对既存版权的不适当的法定许可,也就是说,是对各国法律中“鼓励自由利用作品”的规定的限制。例如WTO首例版权争端裁决所涉及的美国版权法“商业例外”条款一案(DS160)。(17) 而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情况恰恰相反,其不是直接地“鼓励自由利用作品”,而是出于禁止对作品的传播的目的,不给予当事人著作权保护。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三步测试法”能否应用于评判中国著作权法对内容违法作品的限制?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TRIPS协定第13条有关“专有权的限制和例外”中的“专有权”究竟是指国内法中规定的“专有权”,还是指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中规定的“专有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其是指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中的规定。有学者指出:“对于这个条文的解释,必须与TRIPS协定第2(2)条和第9(1)条相结合。”(18) 而TRIPS协定第2(2)条规定:“本协议第一至四部分之所有规定,均不得有损于成员之间依照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及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已经承担的现有义务。”TRIPS协定第9(1)条规定:“全体成员均应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第1至21条及公约附录。但对于伯尔尼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之权利或对于从该条约引申的权利,成员应依本协议而免除权利或义务。”因此TRIPS协定第13条中的“专有权”指的当然不是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专有权,而是国际公约中所确定的专有权。
其次,既然“三步测试法”所针对的是各国国内法对国际公约中所确定的专有权的“限制与例外”,那么即使一国国内法中没有对某些作品赋予专有权,也仍然不能免除“三步测试法”的适用性。相反,不管国内法是以法定许可、强制许可、合理使用还是其他立法方式对国际著作权公约中的专有权予以限制,都应该以TRIPS协定第13条的规定作为检测这些立法是否违反WTO义务的标准。当然,如果我们将“对专有权的限制与例外”理解为逻辑上首先要有专有权,然后是对这些权利的限制性规定,也不无道理。但是即使如此,由于这里的“专有权”是指公约中要求各国赋予的专有权,而非各国自身内国法中的专有权,所以TRIPS协定第13条仍可以作为对“违法作品无著作权”的国内法规则是否符合TRIPS协定的评判标准。(19)
(二)用“三步测试法”评价“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
解决了TRIPS协定第13条的适用性问题,我们即可用上述三个标准来检视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中“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的规则是否与国际著作权条约相冲突。
第一个标准是对作品的限制应局限于“特定的特殊情形”。所谓特定的特殊情形,在WTO首例版权争端裁决所涉及的美国版权法“商业例外”条款一案(DS160)的专家组报告中已作出过解释,即成员国应清楚地将对知识产权作出的限制和例外规定限定在狭窄范围内,在统计学上和性质上两个方面来说,被限制了知识产权的客体都不应具有普遍性。(20)
纵观我国对作品内容管制的法律法规,大多列出以下10类内容并禁止其传播:(1)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5)宣扬邪教、迷信的。(6)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7)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9)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10)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21)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规定中有许多模糊不清和不确定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是援引性规范,这使我国的版权制度在强行法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只要任何立法主体新颁布的强行法中包含了对“违法内容”的描述,都可能使“违法作品”的范围发生变化,所以笔者认为,以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的表述来看,是很难达到“特定的特殊情形”的要求的。
第二个标准是“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如上所述,“三步测试法”主要针对的是一国法律中不恰当地“鼓励作品非经作者的许可传播”的情形,这个标准也是依据此目的而设立的。而在内容违法作品的问题上,由于《伯尔尼公约》第17条的存在,允许一国通过强行法禁止特定作品的传播,那么对作品也就不存在所谓“正常的利用”的情形,因此我国《著作权法》通过这一标准应无难度。
第三个标准是“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正当利益”。WTO首例版权争端裁决所涉及的美国版权法“商业例外”条款一案(DS160)的专家组报告认为,在“依据专有权所蕴涵的保护目标,足够合理的利益应予保护”的语境中,TRIPS协定第13条中的所谓“正当”不仅与“法律实证主义视角上的合法性有关,而且还含有规范主义视角上的正当性的意思。”(22)
所谓法律实证主义视角,前文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在国内法中的合法性问题的实证法上的回答,以及对“程序违法即无著作权”直接与《伯尔尼公约》相冲突的问题而作出的实证分析即属此类。依此视角,根据《伯尔尼公约》第17条,缔约国国内法有权限制和禁止内容违法的作品的传播,而在有作品内容审查制度的国家,无论是权利人自己还是其他人传播这些作品都属于非法行为,不存在合法的利益,所以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将这些作品上的消极权利一并克减,也不存在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的问题。
所谓规范主义视角,则是对“实证分析的结果作出诊断和评论,这种诊断和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认识和价值观。”(23) 在不同文化中,对特定内容是否合法,自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现在的分析中,要点不是对特定的作品内容,而是对“内容违法的作品是否应该受到消极保护”这种制度本身作出价值判断。笔者认为,考虑到TRIPS协定所涉及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这一根本性因素,因此其所保障的权利,当然是为了促进知识产权贸易,既然内容违法的作品本就不能被予以流通,不可能存在合法的贸易,那么即使赋予了权利人消极的排他性权利,其救济中也不应包括相关贸易所产生的利益。换句话说,贸易的客体本身需要满足合法性的要素,否则非法商人进口的鸦片被收缴后,也可藉“消极权利”的理由,要求予以归还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结论显而易见:内容非法的作品上的排他性专有权,并不属于TRIPS协定第13条中的“正当利益”,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是可以通过第三个标准的测试的。
综上,“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的规定应可通过“三步测试法”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检测,问题主要出在第一步的检测即对“特定的特殊情形”的要求上。就我国著作权法来说,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短期内无法彻底废除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的规定的话,那么至少需要对“内容违法的作品”的范围予以明确。相应的方案,将在下文中予以探讨。
五、“超国民待遇”的出现及解决方案
(一)“超国民待遇”的出现
国际著作权公约不是国内法,也不像国际人权法一样有对人民的直接赋权效力,而只是对各缔约国履行国家义务的要求。其所关心的主要是缔约国作品进口到另一缔约国后,能否在这个国家获得不低于公约水平的保护的问题。《伯尔尼公约》要求各国为同盟国其它国家的作者提供国民待遇,但并没有要求各国对其本国国民的作品也适用与公约一致的保护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1988年《伯尔尼公约实施法》将作品分成两类:一类是来自公约成员国的作品,享有版权和提起侵权诉讼不以注册等形式要件为前提;另一类则是来自美国及非公约成员国的作品,仍然以注册等要件为提起侵权诉讼的前提条件。(24) 这在实际上就是对国外作品,在形式要件方面提供了超国民待遇。
同样地,虽然中国著作权法中“作品违法即无著作权”的含糊规定有违国际著作权公约,但如果中国按照美国式的解决方法调整现行制度,则其后果也只能是:其它《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作品在中国不受该规则的限制,来自中国的违法作品则并不因此而自动获得著作权的保护;而且从实证法上看,中国当前的立法其实已经可以被解释为“超国民待遇”。对此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如下。
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国际条约与中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有不同规定的,国际条约可以直接适用。这貌似解决了超国民待遇的问题:一旦违法作品在国际著作权公约中仍然能得到保护,似乎国内作品也可以适用公约的规定而获得著作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前提是“国际条约与中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有不同规定”,换言之,如果中国民事法律中对相关法律冲突作出了规定,便不再存在“有不同规定”的问题。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作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法保护。”这显然已经将外国作品“根据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和中国作品根据中国《著作权法》本身所享有的著作权进行了区分。同时,尽管其大部分内容已经为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修正案》所吸收,但1992年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并未被废除,因此在实定法上,中国对国外作品和国内作品事实上仍然给予不同待遇。所以,尽管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所导致的“作品违法即无著作权”与国际著作权法相冲突,也只能得出“联盟其它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作品不应因为这个条款而被剥夺其排他性的消极权利”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境内作者的作品在程序违法的时候,仍然可以获得哪怕仅仅是消极方面的著作权保护。
(二)我国著作权法修改的方案
如果仅仅通过应然性的价值考量去评价现行法律,那么这种批评即使合理也会显得无力。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我们需要探讨更为实际的解决方案。上文通过“三步测试法”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不能在立法中限制某些内容违法的作品的著作权,而是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明确内容违法的范围,使其符合TRIPS协定第13条中“特定的特殊情形”的要求。相应的修改方案也可依此思路展开。
首先,明确程序违法的作品自创作完成时即产生有消极的著作权。即在任何作品被判定为内容违法之前,无论是否满足行政机关有关出版发行的程序性规则,著作权人都有权禁止他人复制、发行或通过其它方式传播作品。著作权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消极权利,其主要作用在于对著作权人以外的人的复制、发行等行为予以限制。因此,这样的规定已经可以满足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这种制度并不会造成对相关管理体制的冲击。其原因在于,即使相关作品最终因为内容上的违法性而被判定禁止传播,著作权人在此种判定之前所作出的禁止性意思表示,也只会缩小作品的传播范围。
其次,当程序违法的作品因为侵权行为而受到著作权人追诉的时候,侵权人可选择直接赔偿或立即向法院指定的机构提存赔偿金,但如果选择后者,其赔偿金中必须包括额外的法定孳息。如果经过审查程序后确定内容合法,或者在经过一定期间后(此期间不应过长,否则仍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虞)未被判定为违法,此孳息由著作权人一并领取。
第三,对作品内容管制制度进行改革,改变简单禁止的粗糙立法,采用分级制度,划定不同类别作品的传播范围,将大部分作品从模糊的标准中解放出来。同时,应该以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代替事前的行政审查制度,将内容的合法与否与著作权的行政保护相分离,避免作品因无法确定其合法与否而处于权利不确定状态。
第四,我国著作权法“鼓励有益作品传播”的立法目的固然使“违法作品即无著作权”的规则有了国内法上的合法性,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即使赋予所有内容违法的作品以消极的著作权保护,也并不违背这个立法目的。相反,如果赋予违法作品著作权,则其传播者将会受到双重的限制:一是公法上的禁止和惩罚;二是私法上著作权人的权利主张,增加了遏制违法内容作品传播的力量。
最后,如果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的确暂时无法被取消,也应将其开放式的援引性表述修改为封闭式的确定性陈述,以符合TRIPS协定中“特定的特殊情形”的要求。例如,可以规定只有当一件作品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即已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内容违法,其著作权才不受本法的保护。同时明确规定,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司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确定作品内容违法之后,作者仍有权主张除取得报酬的权利之外的其它著作权,侵权者不能以作品含有违法内容作为免除责任的抗辩理由。
综上所述,上述修改方案的综合运用,既能让我国不至于因为违反WTO的规则而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陷于被动地位,又能防止因我们被迫实施超国民待遇而影响国内产业发展,还能使国内的出版物管制制度更加明确和理性,防止选择性执法和权力寻租的可能,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法治化进程。其中的具体制度设计也许还需予以进一步研究,但笔者认为,这应当是现行法律体制下解决违法作品著作权问题的合理思路。
注释:
① 参见刘剑文、王清:《关于版权客体分类方法与类型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郑成思:《试论我国版权法修订的必要性》,《著作权》1994年第3期。
③ See China-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Report of the Panel,WTO Document WT/DS362/R.Footnote 31.
④ Ibid,para.8.1.
⑤ 王迁:《著作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⑥ 参见“《大学生》杂志社诉京讯公司、李翔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0)二中初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法院尽管维持相关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裁决,理由却是基于时事实的重新认定上:认为相关作品在内容上和程序上都是合法的(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知终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制度的模糊性给司法裁决带来的任意性。
⑦ 参见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⑧ 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并不必然形成新的作品,但如果被删改的内容在作品中构成实质部分的话,则修改会形成新的作品。笔者认为,对电影《色戒》来说,基于其主题,被删剪的部分显然构成实质性内容,因此删剪后的中国内地版本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同名新作品。
⑨ [德]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⑩ See Mitchell Brothers Film Group v.Cinema Adult Theater,604 F.2d 852(5th Cir.1979).
(11) 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12) 吴汉东、刘剑文:《知识产权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13) See Hoe Lim,Trade and Human Rights:What's at Issue?,U.N.Doc.E/C.12/2001/WP.2.
(14) 《伯尔尼公约》第8条、第9条、第11条、第11条之二、第11条之三、第12条、第14条是对著作权人的种种实体性专有权利的规定,这些规定中,除了第8条中对翻译权的规定表述为“(原作者)享有翻译和授权翻译其作品的专有权利”之外,其余全都仅仅表述为“享有授权(他人做某事)的专有权利”。
(15) See WTO Secretariat,Preliminary Systematic Analysis of National Experiences with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Expressions of Folklore,WIPO/GRTKF/IC/4/3,para.68.
(16) TRIPS协定第13条规定:“全体成员均应将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局限于特定的特殊情形中,该特殊情形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应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17) See United States-Section 110(5) of the US Copyright Act-Report of the Panel,WT/DS160/R.
(18) See Daniel Gervais,The TRIPS Agreement:Drafting History and Analysis,2nd ed.,London:Sweet & Maxwell,2003,p.144.
(19) 遗憾的是,在美国对中国的WTO知识产权争端中,由于我国著作权法理论的准备不足,无法对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1款给出令人信服的、确定的法律解释,令专家组有理由直接从文义上判定“内容违法即无著作权”违反了WTO条约义务,而并没有采用“三步测试法”对其进行评价。笔者认为,与专家组的进路相比,“三步测试法”的进路应更具有说服力。
(20) See United States-Section 110(5)of the US Copyright Act-Report of the Panel,WT/DS160/R,paras.6.112,6.113.需要说明的是,根据WTO争端解决规则,在先的争端裁决并不具有羁束效力,但正如WTO争端上诉机构所言,生效裁决中的观点“会在WTO成员中产生关于其行为合法性的期待”,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II,WT/DS8/AB/R,WT/DS10/AB/R,WT/DS11/AB/R,p.14.
(21) 参见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3条、《电影管理条例》第21条等。
(22) 原文为“…the term relates to lawfulness from a legal positivist perspective,but it has also the connotation of legitimacy from a more normative perspective…”(See United States-Section 110(5)of the US Copyright Act-Report of the Panel,WT/DS160/R,para.6.224.)有学者将此句后半部分理解为“还应该从法律规范主义的角度来衡量”(参见朱理:《后TRIPS时代版权限制和例外的国际标准——WTO专家组首例版权争端裁决之下的三步测试法及其未来》,《知识产权》2006年第1期)。但实际上这里并不是指“法律规范主义”,而是指国际贸易学上的规范主义。
(23) 海闻、[美]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4) 同前注(11),李明德书,第179页。
标签:著作权法论文; 法律论文; 伯尔尼公约论文; 知识产权法院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知识产权管理论文; 出版管理条例论文; 色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