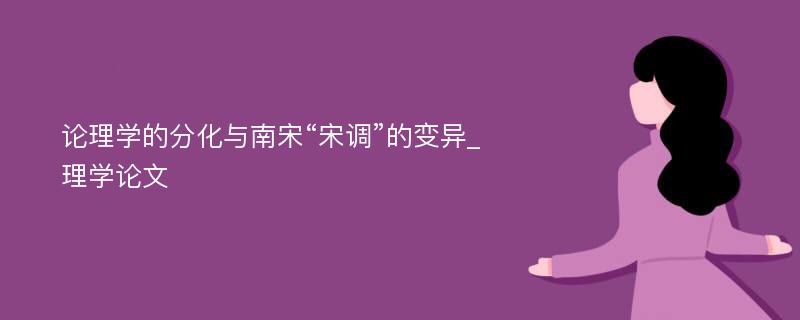
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理学论文,化与论文,宋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6198(2000)06—0130—07
一
纵观宋学的发展全程,如果说北宋时期表现为众派争流、多向发展的态势,那么到南宋时期则显然已形成定于一尊、单向发展的局面。就理学而言,宋学的进程实即理学从民间之学逐渐发展为主导之学的过程。至南宋中期,无论是在学术地位、学者成就还是在客观影响方面,理学都无可置疑地以自身的集大成状态统治着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甚至延及元、明,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直高踞着统治哲学的地位。然而,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其发展峰巅也即其衰落的肇始,从理学本身来看,甚至在其发展到极盛阶段的南宋时期,即已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衰落因素。最突出的表现,是理学内部所出现的分化。就在朱熹、张栻将程系理学推向极盛的同时,理学内部已经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是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正统派,另一则是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派。当然,即使在理学正统派之间,朱、陆亦有相当的分歧,并因之而最终导致理学的解体,而事功派与正统派之间的分歧,显然尤为严重。
就当时的影响而言,事功派自不能与正统派同日而语,但就其阵容而言,事功派却并不太弱。其构成主要有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由于这些代表人物都出生于南宋的浙东路,因而亦统称为浙东学派。在思想上,事功派内部亦有分歧,但就总体而言,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因此与朱、陆正统理学家相比,思想观点与认识上的分歧显然明朗得多。
首先,由于对实际、实效的注重与讲求,事功派学者对朱、陆等人空谈心性极为不满,并屡加抨击,其中以陈亮持论最为深刻而激烈,他的《送吴先成序》充分揭露出空谈心性对社会实际而言的无用性与虚伪性。当然,浙东事功派的务实精神仅仅局限于思想上,并未能将自己的主张运用到政治实践之中。但在这方面的大量论述无疑甚为精彩,如薛季宣在回答薛象先的信中说:“务为深醇盛大,以求经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注:薛季宣.答象先生侄书〔Z〕.)足见其治学态度的务实性, 在给杨简的信中进而称那些“矫之情过者”、“语道乃不及事”等于无知,而自己则对“清淡脱俗之论”,“未能无恶焉”(注:薛季宣.抵杨敬仲简〔Z〕.)。 正是因此,薛季宣甚至把“言道而不及物”的空谈家视为“今之异端”(注:薛季宣.抵沈叔晦〔Z〕.), 其指斥对象显然正是那些所谓的正统理学家。对此,浙东事功派中与朱、陆最为接近的吕祖谦曾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称薛季宣“向来喜事功之意颇锐”,“于事务二三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注:吕祖谦.与朱侍讲〔Z〕.),在肯定薛季宣的同时,显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其次,就学术思想渊源而言,浙东事功派出乎经而入乎史,注重史学的研究并有所成就。而朱、陆等人则纯乎以经学为本,甚而有意识地排斥史学。如朱熹尝言“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抬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注:朱熹.朱子语类:卷122〔M〕.),对吕氏宗史极力诋諆。除此之外,朱熹进而批评陈亮“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注:朱熹.朱子语类:卷123〔M〕.),要害亦在“看史”。可以说,朱、陆理学正是由于一味宗经并抽空了史的实在的内涵而日益走上空疏之路,其与现实的日益脱节,既背离了宋学的初衷,又成为自身走向分化乃至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浙东事功派则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探索,吸取史学的方法与精华,既形成解决现实问题的见解,又充实了自身重实际的理论与学说。
再者,在理学的一些根本性理论问题上,浙东事功派与朱、陆亦有相当的分歧。如在义利观上,从二程到朱熹皆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继承孔、孟、董仲舒到司马光等儒家正统派观念,主张重义轻利;浙东事功派则继承了李觏、王安石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义利统一论。又如在理欲观上,程、朱一系的理学家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其极端的“灭欲论”对人的基本欲望加以彻底否定;浙东事功派则承认人生存的基本欲望,陈亮就提出“节欲论”以与“灭欲论”抗衡。更有甚者,对程、朱一系理学家所构筑的庞大的儒家道统,浙东事功派亦提出怀疑乃至否定。在这一点上,浙东事功派正是发挥了史学之长,在辨明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疑问,对程、朱一系赖以确立其崇高地位的道统学说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
除事功派与朱、陆的分歧之外,南宋正统理学本身亦已产生了分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朱、陆之争。固然,朱、陆同为祖述二程,皆属程系理学传人之代表,治学方法上的不同,并不妨碍二人在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故朱、陆皆属宋明理学主流派中的正统派。但是,在朱、陆所祖述的二程那里,实已蕴含了分离的契机,朱熹主要承程伊川而建道学,陆九渊则主要承程明道而建心学,于是,二程学说隐含的某些差异在朱、陆分庭抗礼之时便暴露出明显的分歧。
如果说,朱、陆之争在宋代尚属理学正统派内部的分歧,那么,到元、明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学术的演进,朱、陆之异实已形成水火不容的两大对立学派。元代一统南北,理学北传,其时学者沿南宋朱陆异同之辩,或宗朱兼取陆,或宗陆兼取朱,大多“往来其间”,并主张“和会朱陆”。然而由于统治者恢复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取士,朱子之学便逐渐成为踞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陆子之学遭冷落。至明代,朱棣敕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皆主朱子学,一时宋濂、方孝孺、薛瑄等著名学者都以朱学为矩,于是朱学成为学术正统,其他学说包括陆学皆被视作异端。如此一来,朱学一方面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亦因作为科场教条长期运用,明显渐次僵化。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也更加明晰地暴露出来,由此便引发了人们对朱学的不满与反思,出现于明中叶的王守仁就是其中突出代表。在朱学踞统治地位之时,为避免作为异端的巨大压力,王守仁抬出同属宋代理学正统派的陆九渊为旗帜,构筑起陆、王“心学”体系以与程、朱“道学”体系相对抗。
宏观整个理学行程,其真正解体固在明代中后期,但追溯其矛盾蕴蓄之基始却早在极盛的南宋时期,而导致其最终解体的最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当时作为非主流派的浙东事功派与理学正统派之间的矛盾,而恰恰在于被视为同是正统派的朱、陆之间的分歧。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在南宋时期理学发展到集大成之际,亦即其自身趋变并走上衰微乃至解体之路之始。
二
与理学与南宋中期发展到集大成境地一样,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期诗坛,于江西诗派式微之际以其旺盛的创作活力与全新的艺术视角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使宋诗史在停滞后的猛然前行中出现中兴繁荣的局面。从宋代诗史全程的宏观角度看,南宋中期的突出成就几已超迈于北宋中叶以欧、梅等人为代表的宋诗歌革新运动之上,成为仅次于北宋后期以王、苏、黄、陈等人为代表的宋诗艺术高峰的又一座高峰。这种以对江西诗派末流僵化模式的超脱为契机而表现出的强烈趋变性,固然与前此宋诗逐渐形成的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也正因此而显示了特立于唐诗之外自成面目的宋诗的总体构成的丰富性,成为典范的宋诗的又一重要标志。具体地看,诗风构成的丰富性,也是处于艺术高峰期的宋诗的共同特点,如果说,北宋后期的宋诗极盛,主要由于创作个性的极度发挥,形成多向的表现与发展,那么,北南之际的江西诗派由作为宋诗最本质特征的典型表现而逐渐走入穷途,则主要是由于创作模式的规范与凝定,形成单向的表现与发展,而南宋中期的宋诗中兴,恰恰体现了对凝定模式的打破,对单一方向的改变,这就与北宋后期宋诗艺术高峰的特征具有了相当的可比性。
然而,南宋诗歌与北宋相比,在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共同特征的深层,又确实存在着重要的变异,特别到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由主体高扬转为主客平衡,由内在感受转为外在体验,由人文意象转为自然意象,这些变异,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宋诗本质性格的超越,显露出向唐诗审美范式回复的趋向。而这又恰恰与南宋理学的变异一样,其趋变机因正包含在南宋中期兴盛的诗坛之中。不过,这些变异在陆、范、杨诗歌创作中尚表现为局限性与渐进性,总体上仍然体现为宋诗总体特征内部的发展与丰富,如陆、范、杨都是由江西诗风孕育而出,宋诗的理性精神也在其创作中烙印始终。只是到杨万里所倡晚唐诗的一面经姜夔而叶适终于再次形成单向发展态势时,才导引出永嘉四灵及江湖派,在晚唐诗风的完全回复的过程中,所谓的“宋调”也就褪尽了其独具的风貌与色彩。
就对“宋调”隐含的变异及其程度而言,在南宋中期的大诗人中,无疑以杨万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而深刻。杨万里针对江西诗派而变革诗风的过程,显示了其主观上摆脱一切束缚与成式的努力,但由于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以及宋人典范意识的强固性,杨万里对成式束缚的摆脱实际上仍伴随着对前代典范的转换过程。其《致徐达书》云:“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专乎我,斯之谓赋。至于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在这段话中,杨万里概括了诗歌创作中的三种不同境界,但这些境界并非一个过程的各个阶段,而是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三个不同的过程,因此他认为,作为真正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达到一个过程的终点,而是应当由低层次过渡到高层次,也就是达到“兴”的境界与水平。从其将“兴”具体解释为“触先焉,感随焉”,并联系其《荆溪集序》中“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的感受和体会看,杨万里强调的正是自然的感发,而这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以缘情论为标志的审美诗学观的体现。这种诗学观作为对言志论的反拨,经六朝诗人的实践至唐代而臻于完善,形成以大量自然意象构成的情景交融的审美范型,而宋诗总体上以人文意象取代自然意象,以主观世界排斥客观世界,正是对唐诗情景交融、主客平衡的审美范式的打破与改变。因此,杨万里的诗学观,在宋诗主潮中表现出不和谐状,而在整个诗史上却表现出向唐诗典范的复归。不过,杨万里毕竟由江西派超脱而出,其超脱江西的同时仍深受江西风习的浸染,因而在杨万里之时,诗坛实具江西体与晚唐体并存的两重性。
这种情形,到叶适时则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叶适全然从杨万里诗中晚唐风韵之一端承袭发展而出,同时几乎消尽了江西一面的影子,一味地宗唐斥宋。其于《徐斯远文集序》中云:“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于《习学纪言序目》中又云“杜甫强作近体”、“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后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可见其由排斥江西而及于江西远祖杜甫,甚至鄙视欧、梅以来所形成的独具面目的宋诗而钟情于庆历、嘉祐之前以林逋、潘阆、魏野等人为代表的宋初晚唐体诗。因此,叶适的诗风也主要表现为清凉精巧,着意于在狭小的境界中做精巧的构思与炼句,虽然艺术的生成仍然依循着自然的感发,但其狭小的境界本身却已与杨万里诗显然不同,而是将杨万里着眼尚较广泛的晚唐诗定向到贾岛、姚合二家,其后四灵中的赵师秀选编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即承此而来。叶适作为南宋一位大儒,诗歌艺术成就与其学术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就构成其艺术源流的角度来比较,叶适诗也远不及其前宋初晚唐体之精致与其后永嘉四灵诗之灵秀。但是,一方面,叶适由杨万里诗中晚唐一面出发并加以定向,另一方面,永嘉四灵皆师事叶适,叶适诗实际上直接开启了其后四灵诗乃至江湖派之先河。因此,从宋诗史的发展阶段看,叶适诗已具有了既受杨万里诗风影响又与四灵诗沟融的两面性,成为南宋中期与南宋后期两个阶段的诗风嬗递的一个重要转接。
当然,南宋后期诗风的变异显非个别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时代性思潮与趋势。其实,早在江西诗派僵化模式形成之际,派中重要成员如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人已努力追求一种清新圆活、轻快自然的风格,显示了江西派内部的趋变要求。其后,以陆、范、杨为代表的中兴大家正是推扩了这一趋势,而杨万里作为当时诗坛宗主,其对创作方向的倡导乃至实践自有尤为重要的影响,使这一趋势得到加速发展。如杨万里在《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诗中称赏张镃与姜夔“新拜南湖为上将,更牵白石作先锋”,预言二人将主盟诗坛,而这两人则已具更多的晚唐诗风,张镃诗被评为“绝似晚唐人”(注:杨万里.诚斋诗话〔M〕.),姜夔诗亦被评为“甚似陆天随”(注: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M〕.)。其时与姜夔等人酬唱交游的周文璞, 亦以所作“辘轳体”诗“野人无事时,常诵极玄诗,写遍千山寺,吟行九曲溪”逼肖晚唐贾、姚诗而自得,潘柽则被叶适“快称其诗,竟谓永嘉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注:方回.瀛奎律髓:卷3〔M〕.),更被视为四灵诗的直接先导。由此已可概见,四灵诗的出现,初始在于对江西诗风的趋变与超越,其间经过吕本中、曾几、杨万里、张、姜夔、周文璞、潘柽、叶适等人的转接承传,逐渐集中定向,终于成为与江西诗风完全对立的反题。比如,江西诗派宗法杜甫,诋諆晚唐,四灵则抛弃杜甫,崇尚贾岛、姚合;江西诗派主张“资书以为诗”,四灵则主张“捐书以为诗”;江西诗派要求做诗“无一字无来处”,四灵则要求“诗句多于马上成”;江西诗派着意生硬拗折,四灵则讲究浮声切响。
江西诗派是北宋诗发展到极至后而定型的产物,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宋诗的最典型形态,因此,对江西诗风彻底反拨的四灵诗,尽管其创作规模及艺术成就在宋诗史上都远非上流,但这一反拨本身实已显示了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中云:“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立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者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清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在这里,全祖望将四灵与欧梅、苏黄、尤杨范陆一起并列为宋诗变化阶段的代表,已充分注意到四灵诗作为宋诗之“变”的影响与地位。王绰《薛瓜庐墓志铭》进而指出:“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四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继诸家之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徒,风流相沿,用意益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明确以四灵为晚宋“唐诗”之首作,同时描画出由其肇端的“相沿”盛况,足见四灵诗风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文人集团的意义,而成为“唐音”复现、“宋调”式微的标志。
南宋后期,永嘉地区因永嘉学派的关系,于师承中凝聚着众多趣味相同的文人墨客,成为复兴晚唐诗风的一个重要基地,且其影响远未局限于永嘉一地。如宁海薛泳“从赵天乐游,得姚贾法”(注:台州经籍志:卷25〔M〕.),河阳张弋“专意于诗,以贾岛、 姚合为法”(注:张弋.秋江烟草:卷首〔M〕.),长乐林尚仁“为诗专以姚合、 贾岛为法”(注:林尚仁.端隐吟稿:卷首〔M〕.), 黄岩葛绍体“其诗颇近四灵”(注:台州经籍志:卷25〔M〕.),等等, 皆见明确的指向与同一的趋归。而以此为标志,占据整个宋末诗坛的阵容庞大的江湖诗派实已形成。全祖望《宋诗纪事序》认为“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赵希意《适安藏拙余稿跋》亦云“四灵诗,江湖杰作也”,可见江湖派盛行实由四灵发其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即指出:“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固然,宋末以江湖派为主体的诗坛,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具体的审美情趣亦因人而异,但从总体上看,一方面,江湖诗人与四灵一样,自标“苦吟不脱晚唐诗”,在艺术追求上显示出向北宋初年以林逋、潘阆、魏野等人为代表的晚唐诗风的完全的回复;另一方面,江湖诗人比四灵更为平民化,所谓“幼孤失学,胸中无千百字书”(注:赵汝腾.石屏诗集序〔Z〕.)的经历自易滋长与平民相沟通的意识,形成有意为“俗”的意趣,戴复古《自嘲》诗云“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正是这两点的生动写照。如果说,诗倡晚唐尚可见出对初宋的回复,那么,大量平民诗人创作中表露出的平民意识,则已与宋代政治文学一体化进程相背离,从而在与元明诗风及其特质的接近之中,使“宋调”之根本特性被彻底抽离。
三
由上所述,在南宋中后期,哲学史上表现出的理学趋变与文学史上表现出的“宋调”式微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分观两者的发展进程与演变趋势,亦皆各有自己的逻辑与规律。然而,比较两者的发生时序、走向特征及其内在性质,则不难发现其间惊人的相似,从这两大领域中主要成员的师承交游角度着眼,尤可明见两者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渗透与推促关系。
先看促使“宋调”式微、唐风复盛的关键人物在南宋理学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当然,南宋后期诗风由“宋”向“唐”彻底转变的标志是四灵及江湖派,但四灵及江湖派诗风是由叶适直接开启的,而叶适诗风主调则是从杨万里尚较繁富的诗风中所包含的晚唐风韵一面出发并加以定向的结果。再向前溯,杨万里作为出自江西门第的诗人,其诗风的变异实际上又是对江西派后期重要人物吕本中、曾几首倡的以清新活泼诗风改造江西末流生硬僵化模式的努力的直接推扩与发展。由此看来,南宋中后期诗风的变革实已形成了一条轨迹明显、联系紧密的索链,其间的关键人物依次是吕本中、曾几、杨万里、叶适,而这四人却恰恰皆是南宋时期在理学上颇有造诣的理学家,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已表明了南宋中后期诗风变异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整个宋代理学发展体系的角度看,吕本中、曾几固然对程系理学在南宋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杨万里亦与朱熹等人交往甚密,但毕竟未入程朱之正统体系,至于叶适,则是更明显地属于与朱学相对峙的理学中的事功派代表人物。因此,这四人既是颇有造诣的理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属于南宋理学发展中的非主流派,这就进一步表明了促使南宋诗风变异的主要力量存在于理学的非主流派之中,实际上也就说明了在那一特定时期诗风变异与理学趋变之间的微妙关系。
再试将南宋理学主流派之间观点分歧的实质与南宋诗风变异的主要特征加以比较。南宋理学正统派之间的分歧以朱、陆之争为标志,其实质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道学”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体系的各自形成并分道扬镳。而从发展的眼光看,则显见由程、朱“道学”向陆、王“心学”演变的趋势。陆学对朱学的改变,根本在于将朱熹截分两端的“道”与“器”、“心”与“理”合一,主张“道器合一”、“心即理”,一切外在的“天理”、“道心”都转化为内在的“本心”的感性欲求即“人心”、“人欲”,于是那束神圣的理性神光变成了世俗的感性物欲,理学便俗化了。就治学方法而言,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陆氏指斥朱氏治学为“支离事业”,极倡“易简工夫”,由此便导引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极端化思想,于是,圣人即等同于凡人,学术也就平民化了。
南宋后期以四灵及江湖派为最突出标志的诗风变异,恰恰体现了强烈的俗化意趣与普遍的平民化特点。四灵及江湖诗人固然“苦吟不脱晚唐诗”,在艺术上表现为向北宋初年的晚唐体诗风的回复,但细较两者的内在情怀却显然有别,试看宋初晚唐体代表诗人潘阆《叙吟》诗:“高吟见太平,不耻老无成,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再看宋末四灵之一赵师秀《赠陈宗之》诗:“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绿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两诗都是对狭小范围内个人生活的描写,但前诗为寻觅精巧清新妙句而至于“沧海竭”、“鬼神惊”,并置“人间万事”于不顾,表现出力求脱俗的孤高的审美情趣,后诗由闲坐街中书肆而“留饮”、“索吟”,并以书“时借检寻”为乐,表现出力求合俗的开放的审美情趣。江湖诗人较之四灵,俗气普遍更重,即使其中少数诗人曾经做过官,但诗中仍多浓厚的平民意识。这样的艺术表现的普遍化,也就与宋诗一贯保持的高层的知识水平、理性的创作精神、“以俗为雅”的审美祈向形成明显的不同,而作为艺术渊源与典范模式,江湖派诗人自然在更大的范围里走入平易浅俗的晚唐诗风之中。
从另一角度看,陆九渊的“心学”其实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颇深,发展到明代王学之后,由“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之说出,使儒家圣人形象被彻底破坏,尤与呵祖骂佛的佛教狂禅风习相似,整个学派至王畿之时即“竟入于禅”(注:黄宗曦.明儒学案:卷11〔M〕.)了。 由此看来,南宋理学趋变实际上包含着由儒向禅的演化因素。
无独有偶,南宋后期以四灵及江湖派为标志的诗风变异也突出地表现出这样的内质特征。在南宋诗风趋变的进程中,早期的杨万里已明确倡导“晚唐异味”,但其所谓的“晚唐”范围尚较广泛,到叶适时,则表现为向宋初“晚唐体”诗风回复,迨四灵及江湖派,更直接以宋初“晚唐体”的典范为典范,将“晚唐”乃至“唐诗”概念完全定向为贾岛、姚合诗风。四灵学晚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晚唐禅化诗风的受容与复现,他们不仅与僧人来往密切,与诗僧如居简、永颐、葛天民等交游唱和,而且还曾以僧为师。作为四灵诗的理想范型,晚唐诗的意义就不仅在于“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的艺术特色,而且更在于“背箧笥,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林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颂”(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8〔M〕.)这样一种禅化诗风。宋末对晚唐禅化诗风的崇尚,固有两者因时代社会环境相似而发为同样的衰世之音的因素,但对照理学的禅化趋向,在文化的整体进程中,深受理学浸染的诗人同时接受其禅化的导引,也就显然不言而自明的了。
由此可见,站在理学与诗学关系的这一特定角度,无论是宏观南宋理学主流本身的发展,还是具体地分析理学正统派之间的朱陆之争抑或正统派与事功派之间的分歧实质,其对诗学的作用及衍射,都恰恰使之导向同一的归宿,从而使由理学自身充当深层内质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宋调”又因理学自身的趋变而式微。
〔收稿日期〕2000—04—28
标签:理学论文; 宋朝论文; 杨万里论文; 江西诗派论文; 江湖派论文; 南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唐诗论文; 朱熹论文; 叶适论文; 晚唐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