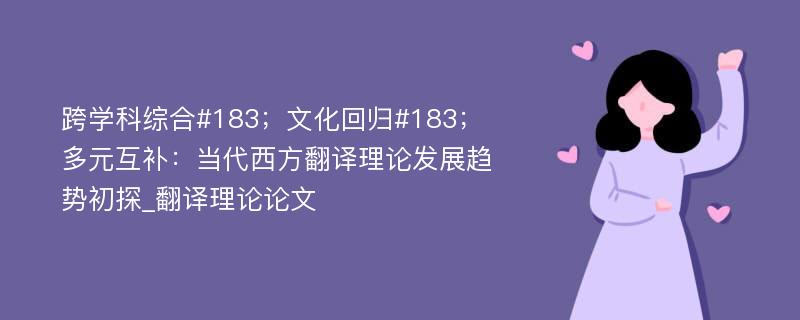
跨学科综合#183;文化回归#183;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茨勒(Gentzler)1993年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断言,90年代“将以翻译理论的繁荣为特征”(Gentzler:183)。当世界走向21世纪的时候,世界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已经印证了根茨勒预言的正确性。翻译理论专著和论文的数量日益增多,翻译研究园地日益扩大,翻译国际会议日益频繁,翻译研究探讨的问题日益广泛,随之引起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研究角度、翻译思想的迅速变化和创新,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和时代。翻译理论家从个案描写、文本内微观的语言层次的精细分析到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论证,从哲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学、信息论到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甚至大众传媒、计算机识别和机器翻译等跨学科领域所作的深入细致的探讨似乎证明,以一种主导理论号令世界翻译界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冲突、对抗、互补和多元的翻译研究格局。
纵观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源流与发展,西方译论的流变与文学、语言,特别是哲学思潮的演变不无关系。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已日渐力不从心。许多翻译理论家已经认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上来分析翻译的研究方法已“过于狭隘”。奈达认为“翻译远远超出了语言的异同”,
语言反映了文化, 并在“许多方面构成文化的类型”(Schaffner:1)。可以预测,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利用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研究翻译与翻译教学仍将是一个广阔的领域。马隆(J.L.Malone)在其著作《翻译艺术中的语言学科学》中虽承认翻译是一门艺术,但深信语言科学仍能为翻译研究提供锐利的武器。奈达先生在其新著《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论述说,语言的社会学与心理学作用对理解语言的功能至关重要(Nida,1996:30),在翻译家心目中语言不再是一套复杂枯燥的教条,而是
奇妙的、富于创造性的交际工具。类似的思想可以用不计其数的形式来表达:演讲、说教、随笔、小说、短篇小说、历史、传记、日记、信函、诗歌(史诗、说教诗、抒情诗)、法律、规章、行政命令、通知告示、系谱图、清单、寓言、谜语、笑话、预言、启示和祈祷。而每一种话语类型都有习惯形成的模式或一套规则(Nida,1996:107)。
诺伊贝特(A.Neubert)以文本为出发点, 不仅考察翻译中文本与词语、句子以及文本与翻译方法的关系,而且考察翻译过程与结果,视野已大大超出文本语言学研究领域。他认为,“文本与文本生成的情境决定了翻译过程”,文本是情境、 过程和结果的三合一关系(Neubertand Shreve:5—7)。 他提出,研究翻译既然是研究文本的形成过程(textualisation),就必须考察以下因素:
1)相关语言的一对一机制;
2)原语与译语的文本特征;
3)译语的情境、意图、目的和需求;
4)文化、社会与交流习惯的差异;
5)知识结构的文化差异;
6)共同知识的范围与构成;
7)读者对文本的期望;
8)原语的信息内容;
9)译语文本可接受的限度(Neubert and Shreve:7—8)。
换言之,翻译必须倚重语言分析,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了解社会和行为模式,甚至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对翻译的影响。随着语言学自身研究领域的拓展,特别是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深入,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也开始研究一些不那么客观的翻译因素。例如“感觉更好”“读起来更顺口”这些似乎无法定量分析、难以琢磨和把握的个人体验也成为译文评定的标准(Gentzler:182)。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还体现在翻译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的交融结合上。德国学者着手研究美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加拿大,特别是蒙特利尔、渥太华和魁北克的一些翻译研究者将加拿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例如加拿大人的身份、殖民主义、双语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等均联系起来,重新评价主导的翻译思想与标准。加拿大女权主义者戈达德(Barbara Godard)将魁北克的殖民化地位(colonized position)与妇女语言上的异化相提并论, 提出女性语言是“批判性地转换文本”(criticaltransformation),是劝服或改造(persuade and transform)男性主导语言。妇女语言是双向的,既反映自身,也反映别人(男性),带有从口语到书面语的流动性质和流言蜚语的特征。女性话语对语言进行反政府主义的处理, 颠覆正统意义, 并在分裂中形成多极(Bassnettand Lefevere:88)。 翻译理论之所以“与女性文本理论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妇女文本理论表现了认知过程中差异这一关键因素,而当代翻译理论也强调译文中存在多种声音,突出了译者/作者语言的自反(sel-freflexive)(Bassnett and Lefevere:93)。
自C.S.皮尔斯和索绪尔创立符号学之后,符号学方法已广泛应用于语言、文学的研究。60年代以来到列维—斯特劳斯将符号学应于用文化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神话和仪式等等。M.福科和巴特进一步将符号学应用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高于语言这一级符号系统的第二级符号系统。奈达先生多次指出,用社会符号学研究翻译是最有成就的方法之一。兰伯特(J.Lambert )应用符号学研究翻译时声称,每一文本、每一话语均含有“翻译的成分”,翻译不过是永无止尽的符号链中的一环!这种翻译思想消解了原文,使其成为无数的原文、无数的代码和无数的语言。这样,翻译不仅是在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而是在任何互相竞争或互有差异的言语中进行(Gentzler:186)。帕兹(Octavio Paz)断言:
翻译即是翻译的翻译的翻译……每一文本既是独一无二的,又是另一文本的翻译……每一文本,到某一点为止,都是创新,正因为如此它就形成一个独特的文本(Bassnett & Lefevere:92)。
符号学的引入使翻译的定义与观念均发生了质的改变,使其成为文化这一大系统中的代码转换。翻译研究的重心即从作者到文本,再从文本转移到读者和行为阐释(act of enunciation)。
信息论和传播学的最新成果对推动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奈达很早就尝试过用信息论中的传输负载、编码、解码、噪声、信息冗余来研究翻译,并试图精确地量化传输负载,以求得冗余平衡。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是否能完全应用于翻译现颇有争议,但其基本原理已得到许多翻译理论家的认可。随着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长足发展,特别是信息论与跨文化交际、符号学的结合,这一研究领域将为翻译提供新的启示。
大众传媒对翻译的影响也日渐显著。由于“美国电视、广播、音乐和国际广告对讨论世界范围的翻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些翻译理论家开始从影视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德拉巴斯蒂塔(D.Delabastita)认为,历史上影视翻译被简单地等同于配音与字幕翻译,如今影视翻译被看成是一定社会价值观念、标准、程式和态度的反映和改造:
在配音和字幕中俚语和方言通常消失了……社会批评的调子降低了,色情镜头被删剪了……其他文化成为奚落对象……影视翻译不再是语言转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接受文化需求的制约(Bassnettand Lefevere:98—99)。
研究影视翻译除了必须研究接受文化的选择策略(引进哪些、排斥哪些、引进多少)和翻译直接程度(directness of translation )之外,还必须:
1)研究影视传播通常依赖的视觉和听觉两个传播渠道;
2)研究构成影视的多种符码:语言码、叙述码、服饰码、 道德码、电影码;
3)研究大众传媒、影片放映、剪接处理上的技术限制。
德拉巴斯蒂塔认为,要使译制片真正影响观众的行为,还应解决有关原文化和目标文化的数十个问题。既然影视翻译是典型的跨学科活动,成功的影视翻译离不开电影电视专业人员、心理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电视符号学家和翻译家的协作配合和共同努力。
此外,不少新兴学科也已应用于与翻译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研究上。模糊集合(fuzzy set theory)、熵(entropy)、 配价理论(valency theory)均已在语义分析、定位、转换和搭配研究中得到应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控制论(cybernetics)、接受美学、 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又对翻译信息的传输、反馈、控制以及如何防止信息丢失和失真产生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哲学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更引起翻译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变革与创新。解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均为翻译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再现与创新的关系和作者、译者、读者的关系以及文本意义的确定因素、时代因素与历史条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回归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使译论家们认识到,当代译论不可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必须有一个多学科综合、跨学科领域相互渗透、不同思潮互补的基础。翻译已从单一的翻译科学论走向了翻译文化论。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Lefevere and Bassnett )甚至认为翻译单位也已开始“从词到文本,从文本到文化迁移”。21世纪的译论必然会如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所说“向文化回归”(cultural retum)。
诺德(C.Nord)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理论”研究的范畴,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内容:
人类交际受情境的制约。情境绝非千篇一律,而是植根于文化习惯;而文化习惯又反过来制约情境。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言语交际因此受文化情境条件的制约(Nord:1)。
例如,文本功能在不同文化中往往会发生迁移。一般来讲,信息性功能的文本在译入文化中基本能维持不变,但呼唤性功能和表达性功能却因文化而异。政治家的竞选演说即是一例。竞选演说在原语中是呼唤性文本,是要直接调动选民参加选举,赢得他们的支持和选票;一旦翻译成其他语言,演说便转变成信息性功能的文本,译文的读者通常只是客观冷静地阅读演说的内容,介入感(involvement)已大大降低。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必然导致一系列翻译思想的转变:
1)传统的思维方式(形式/意义、直译/意译、原语/译语、 作者/译者等两分法)必须让位于整体的、格式塔式随具体情况而变异的思维方式;翻译的多维性,似是而非和矛盾冲突是翻译研究的基础;
2)译文文本不再是原文文本字当句对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 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
3)文本不再是语言静止不变的标本, 而是读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2)。
从翻译的文化功能考虑,许多翻译理论家已提出翻译就是介入,就是对文本的操纵处理。N.弗莱(N.Frye)详细地论述了在交际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中立并非一种介入,用阐释学的行话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人只能是一个不懂语言、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自己准则的人,这种假设的人当然不可能参与文化对话。这样的人将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而在阐释学的意义上则是一个非人(王宁、徐燕红:24)。
列费维尔在其《翻译、重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一书的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
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出某种观念和诗学,并以此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Lefevere,1992:vii)。
根据列费维尔的观点,翻译和具有阐释功能的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选集、读者指南一样,都属于重写范畴,都是对某个文本或某种符号的阐释和操纵,不论我们承认与否,都是人们观念和理念的产物。阿尔瓦雷斯(R.Alvarez)和维达尔(M.Vidal)更尖锐地指出:
翻译从来也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是带有思想并受制于‘权力游戏’(game of power);翻译因而制约了某个社会对某件作品、 某位作家、某个文学或某种文化方式的接受(Alvarez and Vidal:封底)。
实际上翻译意味着操纵处理文本,保存或复制话语,以使其能“在一个封闭的社区内按严格的规定流传”(Gentzler:190)。而现行的翻译理论,包括五种模式和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强化和维护了某些文化价值,排斥和贬低了另一些文化价值。每种翻译理论都支持和赞赏符合某些标准的译作,无视或贬低不符合理想标准的译作。在《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列费维尔和巴斯奈特认为,作品依靠“重写”而生存。离开了重写“原著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重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make or breaka writer)(Lefevere and Bassnett:10)。在《翻译的文化功能》(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沙夫纳(C.Schaffner)认为,翻译是“文化超验过程”(culture transcending process),是“构筑文化特征和文化定位的重要方式”(Schaffner and Kelly-Holmes:2),并反映目的文化的文化与政治价值, 决定目的文化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国际广告翻译和影视翻译甚至促进了“国际文化”或超国家文化的形成。
翻译一方面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译入文化。译入文化是如何选择、规范、强化、排斥、贬低、甚至禁止某一类作者或作品的译介和流行,社会对译作产生过程的制约机制如何即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正如巴斯奈特所说,“今天研究翻译意味着必须考察在某一特定时期文化形成的过程(process)。 这一进程包括文学以外的因素:经济、政治、 社会及形而上的思考”(Gentzler:191)。
列费维尔在《翻译、重写、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文化是如何选择和影响翻译、历史撰写以及选集、文评和编撰活动的。他提出一个时代对原著,特别是经典作品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一个文化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特定文化中文艺理论、社会伦理道德和流行的文学体裁与标准又决定了翻译的原则和手法。他以荷马史诗的翻译为例说明,达希尔(Anne Dacier )在翻译中虽努力不要淡化荷马史诗的特征,
但力求“使那些特征更接近我们所处的时代”。
巴宾(Claude Barbin )声称他“使用一般性的概念”来代替那些今天看来过于猥琐的细节。新古典主义翻译家德拉马特(De Lal Motte)也称他使用当时读者感到愉悦的观念来代替荷马时代感到愉悦的观念。再者,19世纪外译英诗歌几乎总是韵体诗,甚至希腊、罗马无韵诗翻译成英语也必须押韵。显然,社会、文化、历史在暗中左右着译者的抉择。翻译家潜意识的选择绝非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受制于社会文化的深层动因。
在研究文化价值和信仰对翻译自由度的关系时,森古普塔(M.Sengupta)指出,翻译既然是满足文化的需求, 如果原文“接近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中心文本”(central text)体现某一文化的根本信仰(如《圣经》、《古兰经》),文化即要求“最大限度的直译”(Bassnett and Lefevere:7)。反之, 如果文本与根本信仰或经济利益无关,译者便享有大得多的自由。
为了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一些翻译理论家开始系统地研究翻译的文化选择策略,不再将等值看成绝对的标准,不再将译文中出现的“迁移”(shift)视为“谬误”或“差错”, 而是比较“迁移”和“差错”,分析其性质和其中的关系,找出产生迁移的原因。这就对翻译标准的永恒性、“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事实上,不同时代总会产生不同的译文以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这并不表明后来的译作一定优于过去的译作,“并不反映译文……背离了某种绝对的标准,而恰恰证明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加拿大翻译理论家戈达德认为“等值观不是翻译的先决条件,甚至也不是翻译追求的目标”, 翻译应是“变革”(Transformation)。 翻译理论家分析文本演进的历史不是要“发现原文永恒的真实,而是找出历史掩饰原文意义的机制,认清接受文化强加于译文的种种限制”,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Gentzler:196—197)。
另一方面,人类行为理论也阐明,翻译必须是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弗米尔提出,决定翻译目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话语的接受者,即“译者心目中有自己特定文化世界知识、希求和交际需要的文本的接受者或听众”。弗米尔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skopostheorie”, 并将翻译定义为“在目标环境中为目标目的和目标读者而生产的目标情境中的文本”(produce a text in a target setting for a target purpose and target addressees in target circumstances)(Nord:12)。很显然,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在努力协调翻译的文化功能和译入文化对译文的制约机制。目标和目的是译者期望译文对其读者产生的效果,而译文最终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必须考虑目标环境和目标情境,即文化的选择策略。这是一个互动的矛盾体;译文在受译入文化修正的同时也修正译入文化。翻译活动的目的又可进一步划分为:1 )译者的基本目的,2)目标文本的交际目的,3)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法要达到的目的。除skopos(目的)之外弗米尔还系统阐述了目标(aim ):行为要达到的最终结果;目的(purpose):达到目标过程中阶段性结果; 功能(function):即接受者心目中文本传达的意义;意图(intention ):带有目标的行为计划, 即行为的功能在翻译目的论中的重要意义(Nord:27—28)。
同时,目的论还提出了不同的翻译评估标准。赖斯(K.Reiss )认为等值是静止的、重结果的衡量标准,可以指词、短语、句子或文本等不同层次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
而目的论的标准应是“ 充分 ”(adequate)而不是等值。充分是指目标文本完成原语文本同样的交际功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忠实,或互文连贯(fidelity,or intertextualcoherence)(Nord:36)。要达到互文连贯,译者必须根据文本的类型,即信息性、表现性和执行性( informative ,
expressive
andoperative)三大功能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以求原文与译文在不同文化中最大限度上达到交际功能一致。
三、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已开始超越自己封闭的研究体系,形成互补的发展趋势,并从东方翻译理论、拉美翻译理论中吸取营养。翻译理论家已逐渐意识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流派都是对翻译本质和翻译技巧不同侧面或对同一翻译问题不同侧重点的描述。奈达就说过,卡特福德是语言学,特别是系统功能语法翻译理论的代表,奈达自己是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探讨翻译,斯坦纳则主要希望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作出科学概括。根茨勒概括的美国翻译培训班、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说到译论未来的发展时他提出,“未来的译论家应加强合作、消除对立观点之间的误解,进一步为新的、选择性的理论方法敞开大门……使我们更加开放地接受其他观点……欢迎真正的文化内部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Gentzler:199)。
翻译研究派的兴起与发展已预示着以英美法德俄为统治的翻译核心的淡化。低地国家、北欧、以色列、加拿大翻译理论家的崛起使原有的翻译理论派别更呈现出姹紫嫣红、百家争鸣的繁荣形势。与此同时,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等东方译论也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和敏感加入了世界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最令人瞩目的是南美,特别是巴西坎波斯兄弟(de Campos brothers)应用德里达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翻译思想与方法。坎波斯兄弟认为原文在翻译中不应是至高无上、译者只能亦步亦趋仰视和膜拜的权威。翻译应是一种侵越形式(transgression), 与食人主义观点(cannibalism)类似。 所谓的食人主义不是一般西方人理解的含义,“不是捕获、肢解、宰割和吞食”,而是食人者出于对被食者的“崇敬与热爱”,象征性地接受和“吸取被食者的美德”。翻译者必须吞食、消化原文,但又必须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翻译因而被视为原作增强力量、吸取营养、获得生命活力而流传于世的活动。这样译者便不再会因意义丢失而感到无能为力或沮丧,而会领略到“积极参与和肯定的愉悦”(Gentzler:192—193)。
食人主义的理论一方面体现了跨文化翻译思想的融合,另一方面,同一文化中亚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女权主义者和妇女文学彻底批判和解构了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太阳/月亮、文化/自然、日/夜、父/母、男/女等二元项都是不平等的。父权制意味着“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而女性等同于被动者和死亡”(张京媛:3)。 女权主义者将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类比为传统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男性(原文)是主导,是主动,是统治;女性(译文)是从属,是被动,是奴仆。她们认为,翻译中的主从关系与社会性别歧视一样,是人为的,是社会偏见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使然,必须加以矫正。与此同时,译文也如女性文本和文学一样,无时无刻不在“颠覆”或“解构”原文(男性文学)。有的翻译理论家将翻译比作文学中的戏仿(parody)。戏仿是对传统文学规则和惯例的“运用和滥用”,是一种解构手段,解构普遍真理或“正统地位的文化”(哈切恩: 149)。同样,译文是对原文的戏仿,译文一方面要忠实地模仿原文,另一方面又蓄意背离原文,颠覆或解构原文。可以看出,亚文化倾向最大的特点是对“普遍观念”和“权威”的质疑,肯定翻译中的“差异、异质和独创”(哈切恩:146)。 南非的翻译家提出翻译理论不应是一套僵硬的有关“忠实”或文本类型的定义,而是可以灵活运用于任何可能出现的翻译任务的“参照类型”(Nord:136)。
此外,同性恋、黑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等也都为在社会文化历史大环境中研究翻译提供了机会、讲坛和新的思路。翻译曾一度被认为是比较文学或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支”(
smallcorner),如今却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形成力量,任何比较文学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研究”。根茨勒因此认为,我们应重新思考我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将比较文学定义为翻译研究的分支而不是相反”(Gentzler:12)。
综上所述,跨学科综合研究、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和融合的趋势表明未来的译学在深入进行个案研究和描述的同时,必将会打破自身的局限,冲破自己设定的樊篱,营造不同见解和思潮交流、竞争、互补的氛围,使译论得以健康发展。本杰明曾经预言,翻译也许既不倚重原文,也不倚重读者,而是在追求自己的法规,有自身演进的规律(Gentzler:194)。翻译一方面受制于原语和译语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又可能改变这些符号系统。未来的译论必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更深入地探索这些“创造世界文化”的翻译活动的机制。
标签:翻译理论论文; 文化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符号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