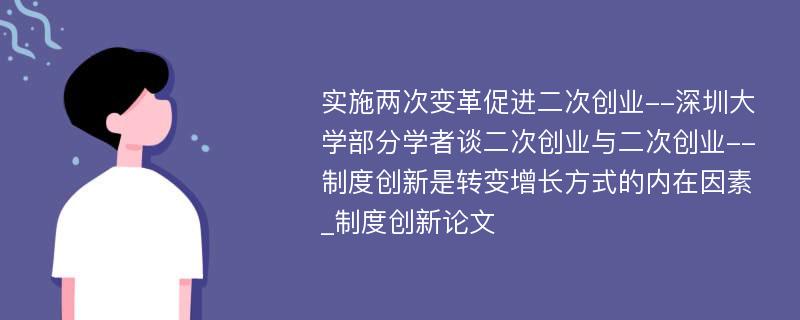
实行两个转变 推进二次创业——深圳大学部分学者谈两个转变与二次创业——制度创新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转变论文,二次创业论文,增长方式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深圳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部署转变增长方式的工作中,一些决策部门与实业界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它可以归结为一个科技进步的问题。因此,面临的任务也就统统概括到“科技兴市”、“科技兴省”里去了。我觉得,这种认识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也过于简单化了。因为中央之所以郑重地提出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入集约型,绝对不是两条不搭界的平行线,甚至也不能被看成是两个问题,而只应被判断为一个问题的两面。
可以说,经济体制的转变不仅必须作为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和外在制度保证,而且还直接构成了它的内在形成因素。这个命题既能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找到根据,又能在当代制度学里得到支持,还可以被新社会进化论所证实,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改变进程它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整体转变只能依赖于制度创新。
正是为了结束从1958年到1978年的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状态,使中国人民在整体上从贫困中真正摆脱出来,邓小平同志才发动了这场波澜壮阔的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运动。改革就是制度创新,其直接目标是,改革掉不适应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其集中表现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寻找出大体适应并积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其集中表现形式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进程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指标和统负盈亏的经济结果,由于既没有市场对需求的外在压力,又缺乏责、权、利相统一的内在动力,其经济增长自然要导致只讲大规模投入,不计较经济效益的粗放型方式。可见,寻找“体制”的“某种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发展”的“特定内容”的,舍此,前者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也有人经常列举我国“一五”时期(1953年—1957年)经济发展的史实来论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或者来说明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进程。对此,我们不仅要客观地分析出在建立独立的工业化体系的基础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宏观直接布局的必要性;而且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对资源的需求的极端有限性;更应当勇敢地承认,旧体制所获得的这些成就与人们所付出的物质上(职工的低工资和工农产品剪刀差)与精神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性代价又是多么不成比例、不相对称啊!这些事实说明,体制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
第二、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强调,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不一般都是科技性因素,而大都还是制度性因素。
那种认为凭借市场价格波动就可以完全自动调节好供求关系、从而使资源优化配置,达到经济增长预定目标的“帕累托最优”,实际上具有两个极为苛刻的前提假设;其一是资源的无限性,没有资源约束;其二是只有“生产成本”,没有“交易成本”,存在一个“零交易成本假设”。
近年来,这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命题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产权经济学的严重挑战,完全能够证伪这两个假设:因为无资源性的约束就等于否定了经济学即资源配置优化学本身,而交易费用为零又等于宣告了社会性分工的消亡,所以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冲动。
试问,在国家最终承担无限责任,对国有企业实行亏损补贴、在国有企业破产几乎就等于国家银行破产状态下(意味着否认有资源性约束),企业如何以市场价格配置资源,又怎能走向预算硬约束的自负盈亏?在既不具有真实的出资人身份,也不存在经理市场,却占经营主导地位的董事长总经理们,在履行“委托——代理”关系时,(意味着否定社会分工)又怎么能不发生“内部人控制”、不出现把“监督机制”演变成“合谋机制”,从而尽可能地将利润转化为工资,去吞食国有资产呢?而这两种行为并存,又怎么能扼止住企业与地方政府去争项目、争货款,怎么能不导致数量冲动的粗放型经营呢?
可见这种制度安排(无限责任扩大了交易成本,“内部人控制”蚕蚀了国有资产)决定的思维定势与利益趋动,最好的结果才能导致经济粗放型增长,一般只会引发经济衰退。所以这里的结论只能是:制度性因素、体制性条件已不应再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般前提与外在环境因素,而是直接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制度的交易成本高低只能呈负相关,成反比。当然,作用都是相互的,集约型增长本身又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巩固,因为提高效益既是集约型增长的直接结果,又是市场经济存在的第一要素。
第三、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飞跃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优胜劣汰自然竞争过程,我们必须寻找到实现这种过渡的“路径依赖”,否则就会被“锁定”在“双轨制”的胶着状态中。
显然,新社会进化论启示着人们: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并不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这里,关键性问题并不在于有一个奔向市场经济的“目标”,而在于架起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彼岸的“桥梁”。
比如即使实现了观念上的飞跃(确认两个转变),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增长的要素(资金积累、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市场开拓)也还有一个完全具备的过程,其运行也还有个组织、实施过程,更何况这一转变根本就不可能不顾地区之间差别,不顾不同发展阶段,不顾行业与产品特点都来一个“一刀切”。
可见在一个相伴着“自然过程”(主要指技术进步)的“人为过程”(主要指体制改革)中要尽量预防与减少“锁定现象”的反复出现,就应如同当年寻找到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在沿海城市实行开放两大政策一样的“路径依赖”。这就是说制度创新也仅仅为增长方式转变打下个良好基础,而并不标志着它的必然实现,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寻找到防止被“锁定”的新的“路径依赖”。
第四、特区的发展应“以‘作用’创‘功能’,以‘功能’定‘政策’”。
作为经济特区,与内地相比,无论是旧体制的束缚,还是传统增长方式的羁绊都相对薄弱些。所以,它能够在一开始就超越几个技术等级,引人适用或先进技术,在短短15年内奇迹般完成了“第一次创业”。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特区正是特殊政策的产物,没有特殊政策就不会有特区本身,而赋予特殊政策正是制度创新的具体表现。问题的实质不可能是有没有特殊政策,而在于有什么样的特殊政策。这样首先要确定在中国办特区的特定作用是什么,接着就研究如何去创造与培养特区能够发挥特定作用所具有的特别功能,最后再制定出为了形成特区的特别功能所需要的各项特殊政策。于是便形成了“政策——功能——作用”的经济关系。
当“优惠的财政政策”在提供了15年之后逐渐削弱,就必须强化它的“特殊的权力政策”,在这里,“权力”也是“政策”、“权力”也是“优惠”。比如,如果让它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它就必须有充分的“体制改革试验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带动”作用,它就必须有一个能够“先富”起来的政策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对港澳回归的“衔接”作用,它就必须具有更大开放度的权力;如果让它发挥精神文明的“前列”作用,它就必须有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但是深圳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而决不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独立王国。离开了全国的大环境根本谈不上体制转变,因为体制只能以“国家”为本位。单项突破并不等于整体推进,基本框架也不等于体系健全。所以,有些事情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去做(如建立地方政府行为的新秩序);有些事情却只能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力度(如作为基本制度的供给者——中央政府去调整地方与中央的财税关系、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等);有些事情则又必须等待全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如内地市场的真实开放度)。这表明许多事不是不想做,而是力不从心,这也就是深圳在两个转变中的客观局限性。从个意义上讲,只能存在“先走几步说”不会出现“一城胜利说”。
如果说深圳在“第一次创业”时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区的话,那么“第二次创业”的主要目标除了这种一般性的“体制目标”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发展目标”,即形成某些类似自由贸易加工区、自由港的更加开放的态势;如果说深圳“第一次创业”在体制改革方面向全国展示的主要“公共品”是“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话,那么,“第二次创业”向全国提供的主要“公共品”就可能是“政府行为的新秩序”。我曾多次说过深圳已经是一个“太累的孩子”和不会永远作“经验批发商”来形容她的处境与实力。但是今天看起来,也大都出于历史的无奈。完全可以说,只要基本政策能够下达,深圳就必须发挥而且也一定能够发挥好“示范”、“辐射”、“带动”、“衔接”、“前列”五大作用,谁让她的名字叫“深圳经济特区”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