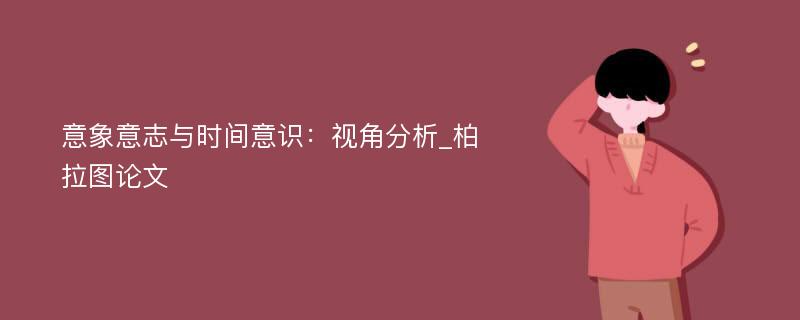
图像意志与时间意识:对看的方式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志论文,图像论文,意识论文,方式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1)06-0037-07
活在看中的驱动或在视觉中的完全沉迷构成了人类的存在方式。
——亚里士多德
一、作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之“象”
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时间所带来的万物流变无常的普遍焦虑一直支配着一系列思考的主题。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变与不变相互关系的困惑,便有了巴门尼德那样一个不动的一,以及芝诺关于阿基里斯永远赶不上乌龟的悖论。当思维进展到超越纷纭变化的表象以及巫术思维那样一种不确定性去试图把握某种更稳定、更普遍的东西时,这种东西必须包含着克服时间的承诺,但同时又必须对流变不居的现象世界进行阐释。在这一点上,柏拉图进行了意义非凡的理论尝试。
在柏拉图哲学中,通过引入一种光学的、几何学的隐喻机制,流变的现象世界的现实性被否定掉了,它被看成是一个充满种种偶然与不确定因素的影子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一个没有时间的“形式”(或“理念”)世界的映照。在这样一个影子世界中,灵魂囚禁于肉体之中,欲望追逐各种虚幻的影像而乐不知返,这样不但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也无从认识真实的自我。只有在另一个形式的世界,在一个消灭了时间流变的天国才能与永恒实在合一。尽管如此,柏拉图并未完全否认现象世界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现象本身,它虽然是虚幻的,但对其的感知却能提醒、启发我们对那样一个更完美的形式世界的回忆(anamnesls)。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警醒,就能透过影像来把握影像背后的实体,或者说光源本身,就能够在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中发现积极的意义。“他主张感性事物之所以能够启发我们认识‘形式’,是因为我们先就已经知道‘形式’的存在。”[1](P25)
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柏拉图的“影子”或“幻象”本身,与那最高的真实本体——“形式”(ei-dos)——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距离?流变不居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把握(即使是作为影像被把握),总是通过一种视觉的格式塔机制,总是包含着某种抽象,总是构成一种可理解的“形式”。无论这种影像是阳光下的阴影还是镜花水月,抑或是我们对现实事物的直接目击,但所得皆已为“象”。
柏拉图所谓的影子或幻象事实上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将现实事物抽象化的过程,使之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或“象”。这种幻“象”与那最高的本体之“象”之间虽然在柏拉图那里被认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象”本身却意味着真实是不存在的,直接性是不存在的,人在意识到一个“象”的瞬间,就已经从那整体世界中分裂开来。人不是直接与现实事物打交道,在人与真实“之间”,总是被“象”所中介,正是通过“象”来与周遭事物打交道。“象”表明,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直接的,而具有一种反思性。因此,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感性确定性分析”中所设定的那样一种“这一个”的感性确定性事实上也只能是一种带有反思的后设。一旦意识到直接性,直接性本身就已经不存在了。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从黑格尔的直接性中读出了间接性:
作为中介者的我们向之屈尊迁就的这个非中介之物,从一开始就在中介和扬弃的统辖之下。而后者只有当屈尊下降(herablassen)到尚未-被中介之物(Unvermittelten)、从而中介之的时候,才能够成其所是。非-中介之物(Un-mittelbare)已经是中介的非-中介之物(Unmittelbare des vermittelns)。[2](P90)
因而,所谓的直接性事实上已经是经过中介的直接性,黑格尔亦清楚地认识到“直接知识甚至于就是间接知识的产物和结果”[3](P141)。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意识”直接性时,直接性已经成为“意识”中介之直接性。没有这种中介,图像(eidos)是不可能的。“是理念使图像成为可视的。因此,人们能够说,只有作为再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图像才是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因为,正是再认识,激发了对于符合图像的理念的追忆。它以这种方式证实了,可感之物并未被开除出可知之物:可感知物,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混合,实在与非实在的混合,并通过对理念的模仿使我们忆起理智之物。”[4](P58)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柏拉图所批判人的动物式欲望也表现出与动物的欲望本身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人的欲望始终与欲望对象的表象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而动物的欲望则直接指向欲望对象的实体。海德格尔分析希腊人的这种“观念”(idee)或“表象”(vorstellen)及其与欲望(appetitus)或欲求(inclinatio)之关系时指出:“在动物那里,这种欲望本身并没有明确地看到它所欲求的东西,并没有把食物表象为食物,并没有把食物当作食物来追求。这种欲求并不知道它所意愿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并不意愿;而且,其实它针对的是被欲求者,而决不针对这个被欲求者之为(als)这样一个被欲求者。但作为欲求的意志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drang)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表象为这样一个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收入眼帘,一道被觉知。”[5](P58)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一书中指出,人的欲望是表象化的欲望,正因为欲望总是指向某个表象,因此才引起了人的行动,即实践。他指出:“这两者,即欲望和深思熟虑的理智,完全有理由显现为运动者;因为在欲望中被欲求者之所以运动,还有,理智、表象之所以运动,只是由于它表象着在欲望中被欲求者。”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将人的行动理解为欲望与表象(图像)的统一的观念支配了整个西方哲学与美学及艺术理论。对此,莱布尼兹就认为:“agere,即行为,是perceptio[知觉]与[欲望]的统一;perceptio就是ιδεα[相],即表象。在康德那里,意志乃是那种欲望的能力,它根据概念发挥作用,也就是这样:在其中被意愿者本身作为一个一般地被表象者对行为来说是决定性的。”[5](P60)可以说,人的欲望因为某种图像意志而具有了区别于动物欲望的本质性特点。
从上述可知,很显然,在柏拉图的图像理论那里,并没有包含着这样一种与人的欲望及行动相互关联的学说,他的图像理论与其说是行动的,不如说是静观的,一切只需要通过一种明心见性的回忆即可达到与永恒本体的至福同一。在柏拉图的图像(形式)理论看来,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总表现为某种“形式”、“形象”。人总是以“象”的方式来与世界建立某种联系。
二、超越时间之“象”
但是,“象”一旦从时间之流中被孤立出来,变为某种形而上的存在,那么就有用这形式来取代更具流变的差异世界本身的危险。一旦将芸芸万象抽象为独一之大象——变为某种纯形式来理解的话,就可能无视于感性生命本身的流涌,同时这种理论也无法有效地阐释时间现象与变化现象。柏拉图的前期图像—形式理论割裂了形式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
柏拉图的迷误就在于,他用另一个影像(eidos)来取代现实的影像,并将那另一个影像当作真实本身。因此,柏拉图无论如何通过一种辩证的方式来追寻那个绝对的知识的世界,这个世界却不过是被预先虚构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柏拉图与他所批评的诗人以及那“制造幻象的魔法师”——智者——事实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对于柏拉图来说,这种与“象”的同一,虽然表现为一个时间的过程,但其目的却在于最终消灭时间,一切最终只是对一个预先存在的形象的确证,一种同一性。也就是说,时间被祛除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没有差异、没有自由意志的过程。
柏拉图的图像或“形式”理论带有很强的巴门尼德的静止、同一的色彩。它从根本上将差异、流变与时间排除出其封闭的体系之外。不过,对早期柏拉图与晚期柏拉图加以区分仍然是必要的。在晚期柏拉图那里,特别是在其《巴曼尼德斯篇》中,柏拉图借巴曼尼德斯之口对其早期理念论进行了批判,将理念—形式从一个超越的世界重新拉回事物的内部,将“形式”内在化。于是,“形式”不再是与现实无关的另一个超验世界的存在,而是事物追求的目的,是事物的普遍本性与内在的“型”。陈康先生指出:“《费都篇》以‘相’为目的解释实际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乃因为个别事物追求‘相’。这个追求者的发动不在追求者这一方面,乃在追求的目的那一方面;后者有一种吸引力,以促动前者。”[6](P377)很显然,柏拉图后期的“相论”将古希腊固有的目的论机制引入事物内部,事物的生成变化与形式的关系乃得以获得理解,万物芸芸变动不息,其背后都受那终极的“相”(或“象”)所驱动。
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将形式看成事物之本质与目的,质料的世界是混沌之流,也是一个无法被把握的世界,只有赋予质料以形式,世界才获得其秩序与结构,整个宇宙洪荒的生成涌动最终都被那超越一切具体事物的形式的“纯形式”所驱动。这种宇宙论超越了古希腊早期那种从physis角度理解自然的倾向,而具有一种强烈的神学目的论色彩。正是将自然界的变化理解为一种对形式的追求的过程,宇宙与人的存在及其在时间之中的变化获得了某种意义。虽然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认为“技艺(arts)模仿自然”[7](P48),但是,在这里,艺术(或“技艺”)并非简单对自然进行一种镜像游戏,而是积极地将事物本身潜在的可能性实现出来,完成其目的、理念(或“形式”),以臻圆满(entelechy)。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颠倒柏拉图的看法,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在古希腊仅仅被理解为发生过的事件,这些事件如果没有被赋予形式就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质料,正是诗歌将质料(一系列发生过的偶然的事件)提炼、整顿为有头有尾、体现了一种时间历程、结构匀称的“形式”。这种形式才是经过反思的自然,才是被人的意识所中介过的历史,才获得其内在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形式与目的的概念既可以用来阐释自然的生成变化,也可以用来阐释人的技艺活动,因此,人的目的性活动与自然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是未加严格区别的,人的技艺性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包含着“形式因”的活动,自然的发展也被设想为是有“目的”的,包含着“形式因”的。历史与自然在此仍然具有一种统一性,人类活动并未独独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加以研究。
因此,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形式与时间的概念更多地用来解释自然世界的生成变化,从根本上说,他们似乎仍然无法区分自然与历史。而且,他们在论述中,虽然引入了时间机制,但时间仍然仍然受制于某种空间化的“形式”,形式才是起真正支配作用的。
三、图像意志与历史意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对自然与历史的变化过程不加区分的看法,直到近代以来才受到根本的质疑。“历史”只有到黑格尔那里,才真正成为一个专属于人类、打上了人性之烙印的概念。历史代表了从一种自觉与反思的态度来理解人的自我实现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必定是哲学的。正如海德格尔指出:“黑格尔以某种方式来规定历史本身,认为历史在其基本特征上必定是哲学的。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乃是精神达到本身的在自身中统一的、因而必然的进步过程。”[8](P503)历史因而体现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线索,历史区别于无意识的自然的地方在于:历史必定是逻辑的。在黑格尔这里,精神或逻各斯与柏拉图、巴门尼德那种自身同一的静态“图像”或“存在”不一样,展现为一种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人性就体现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之上,只有自然是永远同一的、没有发展的,历史却展现为一个时间变化的历程。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因而表现为一个精神的、理念的自我认识、反思或中介化的进程,只有建立在对自然的直接性的否定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有人的历史。因而,也可以说,自然是没有理念、精神或图像可言的,只有历史才展现为一幅时间的画廊,而哲学史则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着的英雄的展览”[9](P7)。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过程也是精神外化、中介化为他者,并在更高的层面上与之同一而层层展开的过程。这种“自我—他者—同一”的过程构成了一种新的镜像游戏。对此,黑格尔说:“一般讲来,这样的对于一个他物、一个对象的意识无疑地本身必然地是自我意识、是意识返回到自身。是在它的对方中意识到它自身。这种从前一种意识的形态的必然进展(前一种意识形态以自身以外的一个事物、一个他物为它的真实内容),正表明了不仅对于事物的意识只有对于一个自我意识才是可能的,而且表明了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前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理。”[10](P113)于是,从意识、自我意识再到精神、宗教,最后抵达绝对知识的历程,只不过是精神在不断地追逐自我的镜像过程中不断前进,最终达到那样一个历史终点的完美图像的历程。而且,在历史展开之初始,那样一种历史终结点的完美图像就已经在逻辑上被预先设置了,也就是说,历史尚未展开就已经结束了。柯小刚先生指出:“在这个思辨的意义上,历史的完成,说的不是历史‘在时间中’的完成,而恰恰说的是,历史‘在时间外’的完成: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地方,在《逻辑学》里,历史就已经完成了。”[11](P67)
尽管更强调客观的物质生产的层面,但黑格尔的观念论及其对于历史与人性之理解仍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在论及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作的区别与差异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区别于最灵巧的蜜蜂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完全观念地存在着。
在这里,人的劳动之独独成为人的劳动,就在于这种劳动同时也是一种“表象”、“观念”的活动,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通过图像来与世界打交道,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图像意志所支配。米歇尔·艾尔德雷德认为:“人首先想像要生产(bring forth)的东西;人已然‘观念地’看见要生产的东西,比如它的‘相’(sight)。”“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从本质上明确区分他们自己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关于生产所说的东西:人看见观念(ideas);人暴露并展示于存在者的存在,当进行生产时,他们的techne(技艺)有目的地—逻辑地指向被生产之物的想像的存在。”[12](P49-50)
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将自我形象投射到一个客体的过程,自然、他者、世界都不过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这种影像与认同的游戏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是一脉相承的。讲到这里,有必要提到拉康那篇经典论文——《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拉康这篇论文从精神分析经验的角度对人从动物状态成长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这一关键阶段进行了揭示,与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相通的地方在于,在他看来,图像、格式塔(形式)在标识人之为人这一点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意象注定会在这个阶段发生作用,就像在分析理论中使用的古代术语——‘意象’(imago)一词所证实的那样。”“一个尚处婴儿阶段的小孩——举步趔趄、仰仗母怀——将镜中意象兴奋地假设为自我,表明了一种典型情境的象征模式。在此模式中,自我突进为一种首要形式。”[13](P76)也就是说,在拉康看来,意象构成了一条分界线,在意象之前的阶段是自然,而在意象之后的阶段则形成了人的历史。正是通过对一个比自身更完美的格式塔形式的认同,人进入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之中,人从那种原初的直接性中分裂开来,进入与他者的关系之中,“镜子阶段”是人社会化的开始。
四、原始之“看”及其时间维度
拉康的“镜子阶段”所表明的象征模式还表明了人所具有的时间结构的开始。动物是没有时间的,只有人在一种图像意志中,在通过其身体的完整形式(the total form of his body)来对将来更成熟自我的预期(anticipate)中,人才获得其时间结构:“镜子阶段是决定性时刻:不但自我由此诞生,‘破碎’的身体亦从此产生。此一时刻既是往后事件之根源,亦是先前事件之根源。通过预期它产生将来;通过回溯它产生过去。”[14](P80)这种在当下对于将来的先行把握以及对于过去的回溯的时间结构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所分析的时间三维具有强烈的相似性。据说拉康通过科耶夫对海德格尔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翻译过海德格尔的文章。但在这里,与其比较两者的相似性[15](P65-69),我们倒更想指出两者的差异所在。
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并不体现于拉康意义上的那种对镜中自我形象的静观上,拉康式的镜像结构无疑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那种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结构的变体。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并不是一种表象的关系,而是一种“在世界中”,与世间事物打交道、操劳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充满意义的因缘联结关系。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上手关系,还是那样一种更本真的听从良知的召唤向死而生都不是一种“观照”的模式。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寻视”(umsicht)、“顾视”(rucksicht)、“透视”(durchsichtigkeit)来取代传统的“直观”以揭示人与世界的生存论关系:
就其筹划性质而言,领会在生存论上构成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视的东西。操劳活动的寻视(umsicht)、操持的顾视(rucksicht)以及对存在本身——此在一向为这个存在如其所是地存在——的视(sicht),这些都已被标明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同样源始地依照这些基本方式,此在乃是在生存论上随着此在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那个首要地和整体地关涉到生存的视,我们称之为透视(durchsichtigkeit)。我们选择这个术语来标明领会得恰当的“自我认识”,以此指明:自我认识所说的并不是通过感知观察和静观的一个自我点,而是贯透在世的所有本质环节来领会掌握在世的整个展开状态。[16](P170-171)
很显然,在海德格尔这里,“环视”、“顾视”与“透视”表明一种人与世界的诠释学性质,人总是在一种“现身情态”中对周围世界有所领会,而“视”则植根于这种现身与领会,“此在以有情绪的方式‘视’它由之而在的可能性”[16](P171)。这种朝向此在的可能性的“视”或者展开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意味着一种“自我认识”,也就是说,此在对世界之“视”同时也是一种“‘自’视”[16](P172)。
此中“视”与“自视”之结构与拉康的镜像隐喻有着一种表面上的相似性,但差异却是根本的。在拉康那里,镜中影像虽然也反映了“他的身体、及他者乃至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但镜子作为“外部可见世界的视阈”,所把握的视像却基本是与周遭现实世界剥离开来并固化下来的某种格式塔。正因为如此,婴儿才能够将镜中形象在心中固化下来(fix it in his mind),并在后来不再面对镜子时也能不断将其重新记起(bring back)。与拉康不一样,海德格尔的“自我认识”却不是以这样一种格式塔机制或表象结构得到把握的,在他那里,“视”并不导向一种对于将某种图像固化下来的冲动,或者说,“视”并不导向将某物孤立出来使之成为某种几何学化的形式的冲动;相反,“视”总是将我们带入事物与事物的因缘关联的整体网络:“这个视的看却一向有所领会,有所解释。这个看包含着指引关联‘为了作什么’的明确性。指引关联属于因缘整体,而单纯照面的东西是从这个因缘整体方面被领会的。以‘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为解释线索解释存在者,并以这种接近存在者的方式把领会的东西分环勾连,这件事情本身先于对有关这件事情的专门命题。”[16](P174)也就是说,那样一种将世界对象化的做法相对于与事物打交道的上手状态乃是一种退化的形式,它将那种原初的现身与领会固化为概念与命题。“在操劳寻视中‘起初’没有诸如此类的命题。然而操劳寻视确有它自己的解释方式。”[16](P184)对象化以其抽象化、形式化的方式将事物剥离出其具体的、感性的、语境化的“因缘整体性”,最终变为一种与流变的现实生活世界无大关系的普遍性的概念、判断、命题、知识。海德格尔说:“例如锤子,首先上手作为工具。如果要把它作为一个命题的‘对象’,那么,命题一旦提出,在先行具有中就已经发生了一种转变。……‘作为’本来分环勾连着指引的联络;现在这个进行分环勾连的‘作为’从意蕴上割断下来,而正是意蕴把周围世界规定为周围世界的。这个‘作为’被迫退回到仅仅现成的东西的一般齐的平面上。寻视解释的原始‘作为’被敉平为规定现成性的‘作为’;而这一敉平活动正是命题的特点。”[16](P184-185)正是这种表象化的活动,或者说对象化的冲动将世界变为一个逻辑学的、几何学的客体,事物与事物之间那种与具体因缘整体关联的差异性被敉平了,在命题语言或数学语言中,世界在任何点上都没有本质的差异,一切都是均质化的,都是巴门尼德式的绝对的同一。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后来的文章中一再提到的神的消隐与世界的图像化。海德格尔试图以现象学的方法揭示出那种更本源的人生在世的存在状态。因为在他看来,对象化的凝视,或“在纯粹凝视之际,‘仅仅在眼前有某种东西’这种情况是作为不再有所领会发生的。这个没有‘作为’结构的把握是朴素地领会着的看的一种褫夺,它并不比素朴的看更原始,倒是从素朴的看派生出来的”[16](P175)。很显然,更原始的看并不是一种图像化的行为,它并不将目光从一种因缘联络中抽象化为某种时间之外的空间形式。
在此,“看”总是与时间境域水乳交融,与人在世界中的操心、决断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那种更原始的看与其说是对象化的,不如说一切对象化的看都只不过是那种上下打量,有所领会的寻视的退化与变质之表现。看的可能性、对象的可能性并非绝然与时间无关;相反,如果缺少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更本源的时间维度,那么,一切看都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之前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的“先验演绎”部分的创造性分析,指出,在感性直观与知性统觉之间有一种更本源的结构性力量,这就是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这种想像力不同于心理学中那样一种无需对象在场的表象能力,而是与直观的“把握的综合”以及概念的“认知的综合”相并列的“再生的综合”。海德格尔更关注更重视康德对于想像力的“先验的综合”的阐述,这种先验的综合是所有经验可能性的基础。它比康德后来所谓的“统觉的本源综合”更为原初,自身具有生产性(produktiv)。这种生产性构成了对象被给予有限存在者的一种先验条件,是一种接受式的纯发生。在这种接受与发生“之间”已先行有一撑开的地平域(horizont)或“回旋余地”(spielraum),这种使得对象成为可能的域或空间乃是原本的时间,“这种域性的时间是被先验想像力构造而成的‘纯象’。……经验想像力产生形象或心象,先验的纯想像力则构成(bilden)地平域这样的‘纯象’(rein bild)或‘几象’(schema-bild)。”[17](P79)通过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再阐释,人与世界的对象化关系发生的可能性乃先验地建基于一时间域之中,这种时间不仅是认识论的先决条件,更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与时间”之时间。这种先于内外、主客之分的时间乃是一种纯构象[17](P88)。可以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更本源的看,那种人在世的操心、牵挂不可分割的“寻视”都与康德所揭榘的时间维度不可分割。
与海德格尔相反,拉康的“镜子阶段”虽然隐喻性地标识着人从自然向历史转变的一种典型情境,标识着人从一种动物式的昏昏默默到能够预期与回溯,并最终意识到人的必死性,但是这种镜中意象本身却是非时间性的,图像总是在时间之外,它意味着时间总是被空间所主宰,赫拉克利特总是不得不向巴门尼德屈服。拉康无疑意识到这种建立于图像意志基础上的人类自我确证的虚幻性及人类知识的妄想狂(paranoiac)性质,但他却悲观地认为人类无法抗拒和逃脱这种命运。因此,他指出:“这个形式(gestalt)通过其显现出来的两个方面,象征了自我的精神的恒久性并预示了其必然异化的命运。此形式(gestalt)也将自我与其树立的雕像,与支配人的幻象幽灵,与自我制造的在多义联系中行将实现自动机制联系起来。”[13](P76-77)他还指出,这种“形式的凝滞”(formal stagnation)“类似于人类知识的普遍结构,此结构使自我及对象具有了恒久性、同一性与实体性”[13](P90)。总之,镜子阶段所体现的那样一种对于确定形式的执迷“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13](P76)。
在拉康这里,感性生命被坚硬的形式所篡夺构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命运,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还有可能通过回到古希腊之前,回到一种更本源的主客体经验之前来对这种“本体论结构”进行抵制。如果说整个西方文化一直贯穿着追求永恒不变的“一”,追求确定抽象的“形式”的冲动,或者说具有拉康所谓的那种“妄想狂知识”(paranoiac knowledge)的性质,那么,在那种以“气韵”而非“形式”为生命与艺术的内在追求的中国文化中,又具有一种怎样的“看的方式”呢?在这种文化中时间与图像具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拉康那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的说法是否过于绝对呢?
标签:柏拉图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