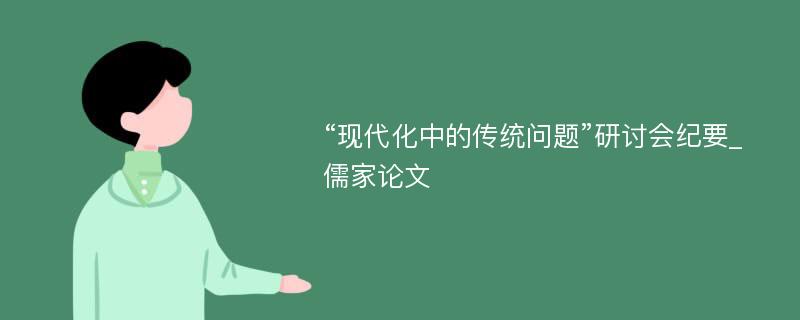
“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纪要论文,传统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1999)03-0005-06
一向为儒家现代价值“不懈陈辞”的杜维明先生从1998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于“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的探讨,除1998年6 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75周年报庆活动中作了《全球化和本土化冲击之下的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之外,1998年下半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见本刊1998年11期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地以“现代性中的传统”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均引起了热烈反应。
随着国际范围内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和国内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特别是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对于儒家精神和东亚现代化互动的论点遭受东亚金融危机的考验,使得这个问题更受学界的关注。因此,1999年1月21 日由国际儒家联合会和孔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吸引了包括美国、新加坡和我国北京、山东等地的知识界人士的关注。
会议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先由杜维明先生提出他的论点,他认为:儒家传统源自农业经济和以宗法社会、家长政治为特色的中国,在东亚社会已经成了工商社会、民间与政体的核心价值,不仅获得了精英分子的自我认同,也是广大人民心灵学习的精神养分。不过以启蒙心态为特色的西方强势文明也在东亚知识分子的心灵中扎根,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作用。
他认为必须打破传统和现代的绝然二分,而应将它们融合在一起考虑问题。他不应将传统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以为现代化必须消除根源化性的想法是危险的。
他强调儒家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效的“知识谱系”的内容,因为人类共存的两大基本原则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相契合。即“推己及人”以人道对待所有的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应充分吸收儒家的人文精神。他说如果想对儒家人文精神有一个整全的理解,我们至少应考虑到四个向度: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然后是自然和天道。他以《中庸》中“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引申出个人与群体要进行健康互动,持一个持久与和谐的关系。
围绕杜维明论点大家发表了评论,李德顺认为中国学术界习惯于在对事实本身有深入了解之前就发表价值判断。比方说传统是什么?它何以就能成为现代化的发端?传统是书本上的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杜先生所指的健康的人文精神,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生的?例如嘴上说的仁爱而实际是专制,那么儒家和专制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儒家理念是否根本就没有力量指导实践?对于启蒙思潮的反思到底应反思什么,我们现在正是在受到工具理性之苦还是仍受不尊重科学理性之苦?这都需要深入的分析。
陈来认为对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的背景的回顾一直是在韦伯理论的影响之下,因而太切近于经济发展,所以反思的范围应该扩大。在西方,现代性是多种多样的,不过现代性主要还是指工业化以来现代社会之所以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即市场、政治民主和个人价值。中国这个问题的出现的背景是殖民主义的压迫的结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之所以能战胜中国的东西十分重视,并将之视为现代性的标志,看待传统文化也以此为基点。与这些因素相合的就是应该肯定的,不相合的便是应该抛弃的。其实西方的现代性是否是仅凭启蒙的内容即可达成,这是一个问题。基督教在西方现代性中的作用应加以充分的关注。
李存山着重探讨了儒学创新和其他文化创新的关系,特别是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问题。他说,杜维明曾谈过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所以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既仰慕西方又拒斥西方的心理相符,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性是被动的,儒家文化有向现代性转化的因素,但以何种方式转化及其结果是不可测的。当然接受西方也有主动的一面,对现代性是什么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贯彻的是救亡图存的意图。应认识到儒家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有契合之处。
郑家栋指出:“五四”以后新传统主义营垒中关于传统与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有三种论说方式:第一种以梁漱溟为代表。在梁先生那里实际上并不存在今天人们所讲的政治儒学或所谓精英儒学与世俗儒学的区分,在他看来儒家的精神资源不是来自学者而是来自民众的生活,儒家传统也只能够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得以保存和延续。所以他要去从事“乡村建设”,并主张“以伦理代替法律”;第二种方式以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牟明确区分了超越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认为儒家超越层面的心性义理具有恒久的价值,而在社会历史层面则必须全然肯定和吸收民主和科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虽然时间上首出于西方,但并不为西方文化所特有,毋宁说是具有普世性的“共法”;第三种以杜维明等人为代表。表现为对于与启蒙精神关联在一起的现代性提出质疑。主张现代性本身也是多元的,而把西方有关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规定视为普世的乃是西方文化的强势所致。晚近流行的“儒家式的民主”或“东方式的民主”一类的提法与上面这种论说方式有关,而这一类提法中蕴涵了很大的危险性。杜维明在回答中说明他承认民主自由等价值的普世性,只是认为停留于此是不够的,但也不赞同“儒家式的民主”一类提法。
郭沂对现代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从旧的文化范式向新的文化范式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促动、相互适应,共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因此,那些新的因素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整个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二是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三是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即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四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世界现代化过程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所以它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一致的。目前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其方针是“中体西用”。“体”、“用”这对范畴的内涵是相对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中国传统价值的根本特征即人文精神是体,不能变;其他都是用,都是可变的,都是可以吸收西方现代化成果加以改造的。
姜广辉认为对传统进行转化是十分必要的。他说最近出土的郭店的楚简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儒家传统有很大的意义。要分析早期儒家和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儒家是否一致,要充分继承传统中的优秀成果使之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干春松认为:需要反思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是一个中国(东亚)问题还是世界性问题。如果是世界性问题,那么西方人眼里和中国人眼里的传统和现代问题是否是一样的,由此中国能否顺利地以自己的知识普系作为现代性的谱系?
对于传统和民族性问题,即文化传统是否和具体的民族不可分开。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认为族性和文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此说来,中国人坚持中国文化的依据何在需要加以反思。
对于创造性转化和吸收文化传统遗产问题干春松认为,文化的创新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兼收世界之美而摈弃一切不良文化。因为任何的创新都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人往往不可能始终作出正确的判断。本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表明我们一直试图兼收世界之美,但事实上全盘西化和扫除封建流毒正是在“去粗取精”的口号下进行的。因此对于文化选择的讨论宜进一步深化而不应泛泛而谈。
杜维明先生对于有些问题作了自己的解释,大家认为如果能使更多的不同学科的人参与,就会形成良性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