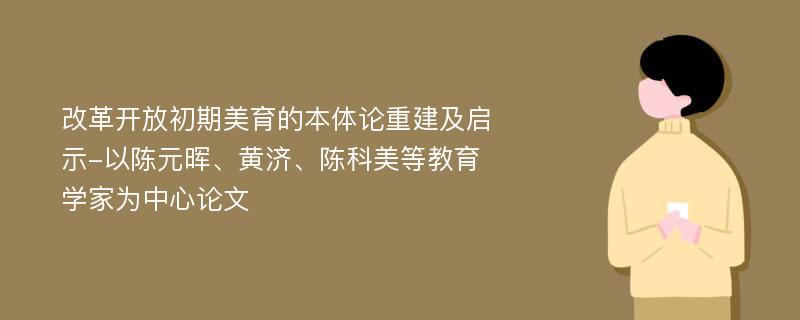
改革开放初期美育的本体论重建及启示
——以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教育学家为中心
杨 朔 镔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美育是教育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初期,以教育学家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为代表的一代学人,通过聚焦学科本质的理论重建、推动学科规训的制度重建、瞄准“全人教育”的路径重建,在教育哲学视域下辨识美育、在教育知识划界中厘定美育、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融入美育。应建构特色化的美育理论体系、学科化的美育知识体系及生活化的美育实践体系,这是美育本体论重建对当下美育实施和教育变革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改革开放初期;美育;本体论;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懈推动下,我国美育事业不仅由恢复逐步走向繁荣,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有力支撑,并上升为国之大计、教之良策。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15年)等国家重大政策,先后对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进行了密集部署。特别是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并明确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美育对建设教育强国、造就时代新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回溯1978年至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制度,面临转型或重建的又一个特殊时代境况之下。美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样态,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思想文化激荡中面临多重使命。既要在经历近20年沉寂后接续“五四”的教育启蒙传统,又要担负新时期重构社会审美共同体的崇高使命;既要摆脱前苏联模式根深蒂固的影响,又要在追赶西方的进程中加快学科发展;既要在新的政策环境下重新探寻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在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人才培养的现实功用。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仍未摆脱新中国成立后“全盘学苏”的思潮,特别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教育模式依旧大行其道,致使美育处于德育和智育的遮蔽之下,对其作为一个实体的学科内涵和功能定位缺少明确认识。以陈元晖(1913—1995)、黄济(1921—2015)、陈科美(1898—1997)等为代表的教育学家,积极从教育学视域推动美育的价值重估与学科重建,“从而在理论上为‘学科合法性’提供论证”[1]1-20,为美育在新世纪的“复归”与“振兴”奠定了基础。值此改革开放40年之际,立足教育学术史视角,回溯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学界对美育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的本体论重建历程,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无疑为当代美育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一、聚焦学科本质的理论重建:在教育哲学视域下辨识美育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新人才观的确立和高考制度改革的推进,对新中国教育学发展道路的质疑和反思也随之展开,教育学研究者亟需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更为深刻地揭示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演化机制,助力国家构建与德智体美劳全面人才培养相应的教育体系。教育学界首先围绕教育的本质属性掀起了一场哲学意义上的大讨论。《哲学大辞典》认为,本体论“研究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探讨大致可分为实体本体论与存在本体论。今天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教育本质大讨论,在实质上是教育学科在历经“文革”否定后对自身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的反思。虽然这场讨论对于向来重视理论构建的美育来说“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2]72,但还是触动了教育学家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对美育存在的实体地位展开新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从把美学和美育视为一种教育学支撑性内容的存在开始的。陈元晖首先指出:“教育学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境地,就是由于它忽视哲学”。因此,在教育恢复重建的背景下,应把美学思想作为能够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一朵彩云”[3]3。黄济、瞿葆奎、潘懋元、陈科美、王逢贤等教育学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视角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美学和美育思想进行系统考辨,对中国传统美学与美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主要范畴、基本特点、形式内容等进行系统探讨和阐发,“为构建‘真正的教育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4]68-73。
陈元晖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研究中国教育学发展史绕不开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5]151-173,他对美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先后有《王国维的美学思想》(1980年)、《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孔子的美育思想》(1987年)等相关著述。黄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哲学学科重建和发展的开拓者和引领者”[6]31-35,在改革开放初期先后有《教育哲学初稿》(1982年)、《教育哲学》(1985年)、《中国的美育传统与时代要求》(1989年)等相关著述。陈科美作为“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之一[7]5-6,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全面发展的教育需要包括美育》(1979年)、《论美育的基本原理》(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1985年)、《论美育心理的要素及其运用范围》(1986年)、《论美育和德育的关系》(1987年)、《谈谈幼儿美育》(1982年)、《再谈幼儿美育》(1989年)等论文发表。以上论著在立足传统文化根脉,对“五四”以后的美育进行系统性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多向汲取西方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成果,在美学的基础理论、美育与教育的学科定位、美育的实践指向等方面形成独特认识。
“中与西”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美育理论引进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教育学家以开放的视野,遵循“洋为中用”的原则,注重辩证地引进西方美育经典文献和前沿成果。基于康德对人类心意机能“知、情、意”的三分说,教育学家们对“真、善、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普遍认同“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真”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现或符合客观规律,属于价值性层面;“善”是能够满足个体或社会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属于目的性层面;而“美”主要表现出人的能动的创造力量,属于创造性层面。作为国内较早从事康德研究的专家,陈元晖抓住康德美学重视心理分析的特点,对康德的“三大批判”中通过审美促进人达到真和善的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康德的“游戏说”弥合了人的天性中存在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实现了感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是其美育思想的精华。黄济进一步指出:“在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上,既要反对否定美与真和善相联系的机械论观点,又要反对把美与真和善等同起来的简单化倾向”[8]241。道德实践和艺术实践都要以“真”(客观规律)为基础,只有以客观规律为基础,人们才能在按照客观规律进行活动时实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实现自由,达到美的境界。席勒关于社会分工和现代教育弊端的认识,也成为教育学家们关注的美育理论资源。陈元晖认为席勒的美育思想主要来自康德游戏说的影响和发展,实质上同样把美作为游戏冲动的对象,经由美从而实现了人性的自由。然而,美先于自由而存在,这一观点在实践中恐怕很难付诸实施。他认为对马克思现实主义美育观的吸收,能够改变席勒颠倒社会政治经济与精神文化艺术的关系。同时,教育学家们普遍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衡量尺度,对康德、席勒等人的美育理论进行价值重估,倡导将“真、善、美”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之中。陈科美更是鲜明地指出,我国美育存在理论与实际、政治与美育相统一的两大民族性特质,应据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育体系[9]94-100。
在美学与美育理论研究“古”与“今”的问题上,陈元晖与黄济都身体力行地倡导本土美学思想的批判性发掘。陈元晖对孔子的美育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孔子的美育思想在本质上与康德相似,都是从情感上与人产生共鸣从而达到美育的目的。正是孔子最先将“诗教”“乐教”作为教育中的美育部分,才形成了德、智、体、美四育的完整结构[3]392。黄济也认为“诗”与“乐”集中体现了孔子的美育思想[10]26-32,但他同时对荀子、墨子、庄子、老子等思想家的美育思想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梳理。尤为重要的是,黄济立足中国美学和美育思想“儒道互补”的特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文与质、形与神、刚与柔、动与静”等儒家美学及美育范畴进行了考证,并敏锐地认识到这些范畴既对“美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美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原则”[11]33-39。陈元晖、黄济、陈科美也对王国维、蔡元培、鲁迅、陈鹤琴等近现代美学和美育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认同“王国维是我国近代传播西方美学的首倡者,也是近代美育思想的倡导者”。陈元晖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体系归纳为“古雅说”“游戏说”“天才说”“境界说”。认为其“古雅说”自叔本华哲学思想演变而来,把美看作是脱离现实、超越现实的东西,具有与现实和通俗隔离的特征,实质上是把映象、形式与本质、内容颠倒过来的美学观。反而正是“境界说”体现了王国维注重自然的美学观。这一美学观强调写“真景”“真情”,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客观反映,从而使其美学思想中渗入现实主义精神[3]357-367。“游戏说”经过叔本华哲学的改造后,带上了悲观主义色彩。“天才说”否定了人的后天努力和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作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陈元晖对王国维美学“四说”的高下评判,反映出他对美育“求真”这一价值指向的认可。黄济与陈元晖一样,认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因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有不少唯心主义的成份”[11]33-39。对于蔡元培,陈元晖和黄济在肯定其美学思想发时代之先声、将美育作为指导方针纳入教育以及促进民族思想启蒙作用的前提下,对其沿袭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唯理论倾向进行了批判。黄济肯定了鲁迅“艺术为人生”的主张,认为这一论断体现了美与真的结合,使美学和美育获得了自身独立的地位,符合新时期美学和美育定位。与此同时,教育学者们还对梁启超、陶行知、陈鹤琴、孟宪承等近现代教育家的美学和美育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尝试构建新的美育理论体系。
作为我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黄济在教育哲学学科的建设和教育哲学的教材编写中,自觉将美育作为重要内容纳入。197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各师范大学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课程,以“摒弃苏联认为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哲学、没必要单独开设教育哲学的思路”[20]32-35。也是在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委托华东师范大学编写《教育学》教材,陈科美受邀参加,并撰写了其中的美育部分,围绕德、智、体、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点,陈科美对中外教育史中的美育史实进行了系统梳理,初步建立了教育学教材中的美育体系[21]79。1980年,黄济受教育部委托编写教育哲学教材,供全国教育哲学课程使用。1982年,由其编著的《教育哲学初稿》出版,该书被公认为我国解放后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其中,“美和美育”单独成章,对中西方关于美育本质的讨论、美育的意义和任务、“真、善、美”三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22]156-173。1985年,该书以《教育哲学》为名再版,“美和美育”章节名称修改为“美学和美育”,“分别从美的本质、美的形态和美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美学同美育的意义、任务、内容以及实施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关系”[23]2。与《教育哲学初稿》的体例相比较,后者明显进一步强调了美育实践的重要性。并且这一编排体例延续到了1998年修订出版的《教育哲学通论》之中,在全国教育界引起了重要反响。
二、推动学科规训的制度重建:在教育知识划界中厘定美育
“学科规训”这一概念最初由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识社会学研究中首先发掘并使用,其基本内涵是指对知识领域进行分门划界,有“规范化训练”之意,后来经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发展为设立首席讲座、开设相关课程、创办专业期刊、建立各种学会、建立分类图书收藏体制等基本路径[12]31。“在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学科史的研究看来,边界不仅仅意味着区隔与差异,它亦是内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界面,事关知识生产、学科认同、学科规训等所需要的一系列资源”[13]301-325。因此,惟有划清美育与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边界,强化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等其他教育相关知识社会空间的互动,才能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社会认可、物质资源和学术声望,从而使“美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获生机和活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美育热潮中,教育学界总体上延续了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育学科建设传统,通过学术会议的召开、学会组织的创建、专业期刊的创办、图书收藏及教材建设等方式,从教育学视角对新时期美育进行了学科制度创设。
致谢 本文参考了大量文献,在此对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感谢高二年级数学小组同学在课堂上的投入表现.
早在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倡议创办新时期国内第一本美育杂志,并拟定名称为《美育》。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美育编辑部主编的《美育》杂志出版发行(68) 《美育》停刊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在1989年10月出版了《真善美》,学界一般看作是《美育》的继承。 。至1988年终刊,该杂志“共出版46期,是中国20世纪出版期数最多的美育专刊”[16]22-32。与此同时,美育类的图书出版量也急剧增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美育类图书从1982年至1989年每年以10种的频率递增。由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历时10年主编的26卷本《教育学文集》,“开创了建国以来选编大型、成套、专题分卷教育学资料丛书的先例”[17]93。《教育学文集》中,《美育》单独成册,对建国后“讨论美的本质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评论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美学思想论文”进行了系统搜集编选[18]11。作为著名教育史专家,陈元晖在书写中国教育史时,主动将美育作为教育史的参照系。他意识到中国近现代美育史与教育史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一贯性。因此,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中,陈元晖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1919—1989)划分为唯理论、经验论、唯物论三个阶段。认为“五四”以前的中国教育史倾向于唯理论阶段,美育占据了显性地位。“五四”以后的教育学急转弯,从倾向唯理论转向到经验论一边倒的新形势。
贺兰山东麓植被稀疏,森林覆盖率低,降低风速,防治沙尘和水土流失功能较弱。对本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改造,减少沙尘源,为降低本区沙尘暴的强度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对本区营造生态经济林,提高地表植被覆盖度,才能有效扼制沙尘暴天气,改善生态环境。
198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不仅将美育列为“四大议题”之一,还围绕提倡美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美育所包含的形式和内容、美育和智育德育的关系、美育实施的路径与举措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为进一步推进美育工作,会议将“提倡审美教育”确定为学会的宗旨之一,写入《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简章》。部分与会学者还共同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14]。1981年春,陈元晖在福州主持召开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以“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强调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是进行“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而美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重新辩证地看待美育与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在美学界和教育界人士的多方呼吁下,第一次全国美育座谈会举办。黄济、陈科美、滕纯等教育学家以及全国大中小学一线的教学科研人员的出席,第一次改变了美学会议参加者主要为美学界、艺术界及哲学界学者的情况。会议对美育的重要性进一步达成共识,对“文革”后初步开展美育的经验进行了总结[15]13-28。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次明确以美育研究为会议宗旨,改变了以往美学兼美育的会议模式。1986年10月,教育学界又在扬州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美育座谈会,与会学者对美育的性质、意义、任务和方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以上会议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中国高校美育研究会等一批美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中国教育学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学会等半官方的学术团体都相继成立了美育或艺术教育的专业分会,几乎所有的高校和一些中小学校都设立了美育研究中心或艺术研究中心,为全国性美育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对美育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的探讨,接续了中国现代美学与美育重视实践的传统,使中国“美育”由重“美”的唯理论倾向开始向重“育”的实践论倾向转变,美育在教育中的实践价值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落实。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对教育实用价值的诱发愈演愈烈,美育在教育实践中的现实功用也在无形中被盲目放大,重实用理性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吻合了教育对美育的实际需要。由此将美育置于尴尬处境,一方面教育学家试图将其从智育和德育的遮蔽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却又陷入应试教育的窠臼之中难以自拔。美育因此被定格为浅表的理论内涵、模糊的知识边界与短缺的路径设想,始终在人们的质疑中左右摇摆、左冲右突,既有浪费资源的嫌疑,又滋生出公众对政策落实的无力感。在种种问题面前,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教育学家将美育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的实体化重建就显得弥足珍贵,对当下的美育推进也具备了更多的借鉴价值。
其次,国土资源财税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相关财税人员的业务培训。比如,定期组织专业的业务培训,聘请专业讲师指导财税人员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财税知识季度考核,这样可以督促财税工作人员不断进行财税知识的更新,为日后的财税预算管理工作做好准备。
三、瞄准“全人教育”的路径重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融入美育
曾任陈元晖助手的王逢贤于1981年“在国内率先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完整内涵”[29]171-189。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除了人们之前公认的体力和智力等劳动能力外,还包括才能与志趣、道德与审美以及改造自然与社会能力的发展,引起了重要的社会反响。陈元晖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他积极尝试和倡导借鉴贝塔朗菲等人提出的“一般系统论”理论,在整体性视域下整合“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建构“大系统”的教育学[30]33-41。他认为,美育得以成立的重要知识依据是源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人关于“真、善、美”或“知、情、意”的三分模式,这一模式对中国教育体系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和精神(或心理)两个方面的发展。就人的精神方面的发展而言,应该包括道德、智力、情感三个维度,与之相对应的,是德育、智育和美育。此三者“是教育的重要支撑,是构成教育之鼎的精神或心理层面的三只脚”[31]89。由此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实践体系中,智育是培养人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目的主要在于教会学生鉴别真伪;德育是为了使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做出符合一定道德规范的行为,目的主要在于教会学生分辨善恶;美育属于感情陶冶的工作,目的主要在于教会学生判断美丑,是德育和智育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具体点说,就是第一使学生能够鉴别真伪;第二要使学生能够分辨善恶;第三要使学生能够判断美丑”[19]90。因此,要实施“真、善、美三种教育,不能缺少三种中的任何一种”[3]547。陈科美在建国后进一步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概念,认为“美育的性质就在通过教育来体现美的性质,美育的作用就在通过教育来发挥美的作用”,美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在美育过程中应紧紧围绕美的价值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等特质,培养教育对象审美的观点、爱美的兴趣和识美的能力。他还通过对审美感知、审美感情和审美意识等美育心理的研究,提出将美育的教育教学过程建立在人的心理规律之上,以提高教育教学效果[32]157-159。
富有前瞻性的是,黄济等教育学家专门就美育师资和幼儿美育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黄济提出“用审美来塑造新教师”的设想,即一方面通过设立专门学校来强化对音乐、美术等学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其他学科教师审美素养的培养。使他们不仅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知识的“杂家”,还成为具有文艺知识和技能的“艺术家”。师范院校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广泛开展美育类的活动”。作为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和克伯屈的学生,陈科美深受二人美育观的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关注国外生活美育,注意借鉴国外幼儿美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学家。立足幼儿美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重要性,陈科美指出应根据幼儿年龄阶段和身心发展特征,采取多种方式的美育路径,“打好全面教育的始基”[34]36-37。他通过对美国艺术教育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艺术教育报告的译介整理,强调因美国的“艺术未能与教育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造成艺术教育踏步不前”[21]92,呼吁应从美国的得失中吸取教训,将艺术教育作为中小学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其他教育教学都围绕艺术教育来开展。
美在实践中产生,美育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开展,开展美育的现实路径问题一直是关乎美育能否真正实现的基础性问题。在20世纪中国美育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中,“美育经过了审美、情感陶冶功能到政治工具,再到德育、素质教育功能转化”[24]92-98。特别是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滥觞之际,美育与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联。与西方美育兴起于哲学中的美学研究不同的是,我国美育自滥觞之际,无论从倡导者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还是从实践向度来看,皆与教育实践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演进史,就是一部美育不断楔入和助推教育实践的学术史。特别是自“五四”以来,尽管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第一代、第二代美学学人的美学思想特征迥异,但他们在美学和美育观念的阐发和传播中,都有意无意地呈现出“教育启蒙”的叙事特征。以致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美育始终因教育启蒙的实践需要被纳入教育体制。其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蔡元培所开创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启蒙价值论思想范式的深远影响,可能更在于“其所涉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张力”符合了社会对教育的诉求[25]11-14。
在美育实践中,对“美育”与“艺术教育”的纠葛,一直是美育史的“显性”问题。“鲍姆加登之后的美学史上,将艺术与美不加区别或混用的情况并不鲜见”[33]80-83。陈元晖也较早地洞察到,正是由于中外教育史“往往把美育限制在艺术教育的范围内陈述”,造成“美育”与“艺术教育”等同或混用,甚至导致“艺术教育绑架美育”的问题。因此应从感受美入手,扩大美育的范畴和路径。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在持续,对美育的实施形成了一定的阻碍。陈元晖在对孔子、蔡元培、凯洛夫等人的美育思想进行探赜索隐时,也重点关注他们提出的美育路径。在艺术教育之外,他还提出学《诗经》或韵文、欣赏悲剧、观赏自然美等广泛的社会美育途径,与今天关注的语言美育、社会美育、环境美育等提法不谋而合。黄济还明确提出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认识和情感、理论与实践、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美育基本原则。指出“中小学教师不仅要很好地利用语文、音乐、美术、劳作等学科的教学及有关课外、校外活动”来开展美育,“地理和生物等学科的自然美、政治和历史等学科的社会美、体育学科和劳动活动的体形美、行为美”等因素,都是美育的内容[8]228-235。陈科美提出了美育应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情绪体验与逻辑思维、艺术内容与表现方法、教育与实践、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实施阶段与学生年龄特点相结合”等六个结合,通过艺术手段、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等三个路径,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表达美的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美育目的[9]94-100。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美育在现代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以及美育对现代社会中人文精神的补缺等方面的现代性建设”[26]156-173成为了新的课题。而美育注重想象创造、倡导个性自由自觉与多样化的价值理念,与现代教育尊重个性、注重个体自主学习、更为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等新质与特色相吻合,契合了改革开放后对新教育、新人才的需要。在此背景下,通过进一步彰显美育的教育特性并使其纳入国家制度轨道,在教育现代化发展中寻求“全人教育”的路径突破就成为必然趋势。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相对沉寂之后,教育学界的专家学者又集中开展了美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大讨论。黄济、瞿葆奎、王逢贤等教育学家较早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了探讨,倡导发挥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将审美需要、审美情趣以及和谐人格等概念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既合乎规律性(真),又合乎目的性(善),并能自由创造(美)的教育”[27]210。自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国之强弱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观点后,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指针。对于素质教育是否全部包含或者部分包含“德、智、体、美、劳”的问题,素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教育学界开始了长达8年的自由讨论[28]。
四、教育学视域下美育本体论重建的当下启示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巨变,毫无疑问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面临“古与今、中与西”的“冲突与张力”。思想禁锢的放宽为重视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的美育提供了精神的“厚壤”,大量西方美育经典及前沿成果的译介与引进,为美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视野。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的逐步复苏为人们关注相对超脱的美学与美育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历史语境下,审美价值的功能性运用和现代美育体系的重要性自然被重新认识,并在20世纪末以教育形态的方式得以重新演绎。“这使我们有理由断言,教育现代化的实现必将伴随着一个教育美育化的过程”[35]108-115。如果遑论实际效果,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学界对美育的重建至少有两方面成效:一方面接续了滥觞自蔡元培和王国维的美育传统,另一方面成功推动国家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有效保障了美育的实施。
德国基尔市电厂投资2.9亿欧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建成一座低能耗和低排放的热电厂,并于今年秋季投入运营。该厂使用天然气的新系统可改善热电联产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和一次能源的利用率,并由此减少70%以上的CO2排放。该厂一个60m高的锅炉中,可容纳3万m3的热水,为7万多用户提供8h的供热。新系统可在5min内达到190MW满负荷运转,而之前发电厂至少需要4h才能达到,将成为德国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新样板。
教材体系是开展美育的重要体系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元晖曾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以及高校文科教材建设教育组组长,负责全国高校教育学科教材建设。改革开放初期,他对“文革”十年间教育学教科书编写中存在的“重智轻德”倾向表示忧虑。他认为有的教育学教科书对美育取消不谈的做法,相当于将教育学的功能窄化为“教学论的专著”,使“教育”等同于“智育”,从而导致“美育”与“德育”难以成为教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他对西方教育学忽视美育的源流进行了追溯,批判了洛克的《教育漫话》、斯宾塞的《教育论》只包括智、德、体“三育”而不包括美育的做法,认为这是教育学体系构建的一种严重缺失。而从1948年至1989年的40年时间里,前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我国教育界奉为圭臬,对中国教育发展史产生的“影响之深和时间之久,没有一本其他教育学专著可以与它相比拟”[3]83。该书的1948年和1956年两个版本都对美育进行了专章讲述,推动美育思想重新走到了中国教育学的前台。在肯定凯洛夫《教育学》重视美育的同时,他批判其把美育看作对情绪的培养,并与“智育”和“德育”对立起来,割裂了“美育”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联系,造成“四育”的分离。而当时的一些教育学者在编写各自的教科书时,多受凯洛夫的影响。为此,陈元晖着重强调要注意消弭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逐步扭转美育与智育、德育间“畸轻畸重”的不平等倾向,使美育和德育、智育、体育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综合和统一”中充分发挥美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9]29。
一是要重视中外教育学领域美育思想的发掘,建构特色化的美育理论体系。从广义来说,美育是与人类的教育历史同在同行的,也是教育这一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色的、鲜活的美育思想蕴藏在世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学科知识领域之中。由此造成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美育思想的研究往往仅局限在美学领域,对中外哲学、教育和艺术等知识领域的美育思想却缺少应有的发掘。特别是从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管理、教育心理学等视角出发,对教育领域的美学理论、美育史以及现代教育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再阐释、再创生关注不够。以高校美育理论研究为例,“一般性的研究成果多,标志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少见”[36]11-113。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教育学家们,立足新时期教育发展变革的时代需要,以中西教育融合的宏阔视野,借鉴和传承教育学思想中的美育思想,创新特色化的美育理论体系,为推进新时期的教育实践提供了指导。在教育现代化向纵深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更应充分吸纳本土文化艺术资源,注重对世界各国先进美育经验的引进与学习,从而尝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理论,开展具有中国传统、中国精神、中国气度的美育实践。
综上所述,式(3)、式(9)和式(10)为根据改进后Druck-Prager屈服函数求出岩石蠕变本构方程。为了验证其正确性,采用最广泛的蠕变参数求解方法为最小二乘法,即通过Origin9.0软件对蠕变曲线进行拟合[18-20],求得σ3=5 MPa、pw=0时的蠕变参数结果见表4。
作为在教研工作中有着丰富经验的教师,王文娟不仅主动将山西的优秀经验引入到团场学校的教研工作中去,同时还十分注重传帮带工作。在教研工作期间,她引入小组合作教学、探究式教学模式在学校进行推广,还把山西长治市清华中学实施的“数学周周练、英语周周清”教学活动和初中的老师进行交流和传授,加强教学过程中的效果检查和落实,在教学成果上取得不错成绩。除了重点科目课程教研工作,王文娟老师还引入山西学校较为重视的新生入学教育、七年级转折教育、中考前的心理疏导教育课程,自己首先示范,并逐步带出一支由班主任组成的心理疏导队伍。
二是在教育学视域下确立美育的实体地位,建构学科化的美育知识体系。反思今天对美育在教育中的内涵定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相对明晰。然而在具体实施中,美学与美育、美育与德育、智育和体育等学科之间依然存在“联裹交融”的问题,美育目标与效果的错位、资源的浪费等问题仍然导致美育踟蹰不前。美育时而作为一种教育的价值导向,时而作为教育学科所包含的一个分支学科,时而又作为“美学”研究在教育实践维度上的延伸。对于“美育”到底属于教育的下设学科,抑或独立的知识领域,仍缺少明确的辨识。更为严重的是,将美育等同于美学,导致美育的内涵缩小为对审美的理论研究;将美育等同于教育美学,导致美育成为教育手段的审美化探索;将美育等同于音、体、美等学校艺术课程的教育,而在现实的教育实践和学科设置中,美术和音乐课程又偏重于技术层面的教学,忽略了情感和审美教育,导致美育的全面育人功能得不到应有发挥。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学家们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其美育学术史中鲜明地体现出学科划界的意识,尤其重视对美育与其他概念范畴的辨识。这给予我们今天试图再次繁荣美育的启示是,应借鉴美学的学科化建设经验,推动美育尽快进入国家学科目录,具体可作为教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进一步推进美育作为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实体化建设进程。
三是要将美育作为理念深植教育教学,建构生活化的美育实践体系。回顾改革开放后的教育发展,尽管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深处,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37],美育也概莫能外。这其中,凯洛夫版《教育学》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迄今为止,美育作为德育之一部分的体系框架也尚未完全突破。而从理论形态的本质上看,凯洛夫版《教育学》根源于德国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适用于制度化的教育安排,自然排斥建基在“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上的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和陈鹤琴“活教育论”[38],致使美育长期与日常生活脱节,欠缺生动性、趣味性。当前,尽管国家对美育的实践体系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距离弘扬中华传统美育精神、倡导美育的人本主义内涵、实现美育与社会深度融合还有较大空间。特别是学校美育的师资队伍、课程教材、经费资源以及评价管理机制等方面仍缺乏有力保障,美育仍然是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虽然都是在教育学理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实践,批判唯理论的美学及美育思想。强调美育与日常的教育教学、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将美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真正融入到教育的实践过程之中,以美育变革促成教育变革发展的新境界。
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个人工作变动、教育体制变迁等种种原因,陈元晖、黄济、陈科美等教育学家对美育的重建不乏有“急就章”之嫌。致使教育学界对美育的本体论重建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热潮之后,逐渐冷却下来,也未能与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管理科学实现更为深度的融合创新。否则,诸位教育学家的美育思想将更加体系化,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将更为重大。
[参 考 文 献]
[1] 徐岱.道之为道:美育学本体论[J].美育学刊,2012(5).
[2] 刘彦顺.走向现代形态美育学的建构[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
[3] 陈元晖.陈元晖文集:上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4] 于伟.陈元晖先生的教育学家之路[J].教育研究,2014(1).
[5] 张聪,于伟.陈元晖先生与我国当代教育学研究[J].中国教育科学,2013(4).
[6] 石中英.黄济先生对中国教育学术的贡献[J].中国教育科学,2013(3).
[7] 顾明远.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祝贺黄济教授90华诞[J].中国教师,2010(7).
[8] 黄济.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9] 陈科美.中国社会主义美育的探讨[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2).
[10] 黄济.中国的美学传统与时代要求[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89(6).
[11] 黄济.中国近代美学与美育思想概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4(4).
[12]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 Steven Fuller.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Social Science[J].Poetics Today,1991(2).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简章[Z].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简报,1980-06-11(6).
[15] 陈望衡.我与《美育》杂志[J].美育学刊,2014(2).
[16] 谭好哲.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J].山东社会科学,2007(1).
[17] 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18] 王佩雄,黄河清.《美育》卷选编说明[M]//瞿葆奎.教育学文集(8)·美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9] 陈元晖.美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20] 李樱.黄济:虚怀若谷八十六载[J].三月风,2007(11).
[21] 陈科美.论美育的基本原则[M]//陈科美,马林.美育研究论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22] 黄济.教育哲学初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23] 黄济.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4] 杨和平,陈海燕.20世纪中国美育转型的多维向度[J].音乐探索,2015(3).
[25] 潘黎勇.中国现代美学的美育化叙事——以蔡元培美学为中心[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26] 曾繁仁.美学之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27] 石中英,于超.黄济教育思想论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28] 柳斌.新时代,把素质教育进行到底[N].中国教育报,2018-09-19(5).
[29] 柳海民,周霖.王逢贤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治学品格[J].中国教育科学,2015(6).
[30] 陈元晖.“一般系统论”与教育学[J].教育研究,1990(3).
[31] 陈元晖.论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32] 陈科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需要包括美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
[33] 王确.勿以艺术教育绑架审美教育[J].当代文坛,2017(8).
[34] 陈科美.再谈幼儿教育[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35] 吴云生.美育与教育现代化[J].南昌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2).
[36] 胡智锋,邓文卿.站在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角度重新审视高校美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7(7).
[37] 邬大光.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N].光明日报,2018-06-19(13).
[38] 凯洛夫《教育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本[N].中国教育报,2009-09-22(4).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Ontolog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entered at Educationists such as Chen Yuanhui,Huang Ji and Chen Kemei
YANG Shuo-bin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e prop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scholars represented by educationists such as Chen Yuanhui,Huang Ji,and Chen Kemei focu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concentrated on the path reconstruction of humanist education.The aesthetic education was identified on the view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was re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knowledge categories,and was integrated into social practice.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implement and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hat we should buil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distinguished features,a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and a life-related practical system.
Key words: Early Day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Aesthetic Education;Ontology;Enlightenment
[收稿日期] 2018-1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CIA160224)。
[作者简介] 杨朔镔,男,东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教育学部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 G41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164/j.cnki.22-1062/c.2019.05.023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9)05-0169-08
[责任编辑:哲 文]
标签:改革开放初期论文; 美育论文; 本体论论文; 启示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