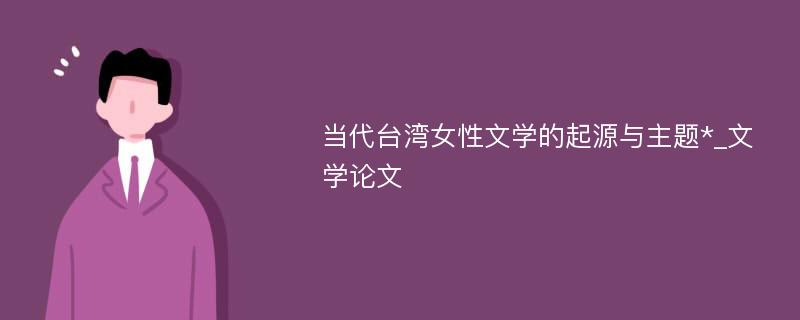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发轫及其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当代论文,女性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稿日期:1996年11月18日。
提要 本文结合战后至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发轫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论述了当代台湾女性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时代机遇,论述了以“乡愁散文”和婚恋小说为代表的女性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 台湾女性文学 怀乡文学 婚恋小说
历史机遇: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和澎湖列岛随即回到祖国的怀抱。光复之初,即有一批30年代享誉文坛的资深作家,如许寿裳、台静农、李何林、黎烈文、李霁野等肩负重建和振兴台湾的文化、文学的使命而相继去台。40年代末期,更有不少或战前生活在祖国大陆、战后返台的省藉作家,如张我军、钟理和、林海音等;或随国民政府去台的大陆作家,如梁实秋、杜衡、谢冰莹、胡秋原,陈纪滢等。这三类先后抵台的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把祖国大陆自‘五四’以来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带入台湾,使得在日本割据下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一步地与大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汇合起来”[1]。
但是,光复后的台湾,决非作家们的乐土:鲁迅的挚友、台大国文系主任许寿裳的遇害;李何林、李霁野被迫离台返回大陆;台静农、黎烈文等人不得不躲进大学校园执掌教鞭,回避抛头露面;台湾省藉著名作家杨达夫妇于“二二八”事变中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因发表“和平宣言”而被判12年徒刑……使人不难想象光复后至50年代台湾社会环境之恶劣与严峻。
然而,就是在这样恶劣与严峻的社会背景之下,50年代的台湾文坛正当官方大力扶植的“战斗文艺”、“反共文学”甚嚣尘上之际,却涌现出一群极少介入政治宣传的女性作家,如林海音、孟瑶、张秀亚、琦君、钟梅音、徐钟佩、郭良蕙、潘人木[2]、徐薏蓝、华严等等,加上20—30年代即已蜚声文坛的苏雪林、谢冰莹、沉樱等人,她们很快以实力不凡的作品,显示了50年代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并成为当代台湾女性文学首度繁荣的标志。与其说这是当代台湾史上的一大奇观和缪斯的格外垂怜,不如说是独特的台湾社会环境为这些女作家成群结队登上文坛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而她们,恰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首先,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文学本身对“政治化”庸俗倾向的拒斥和反拨。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在政治上推行“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方针,继颁布“勘乱动员时期临时戒严令”全岛实行长达37年之久的军事管制之后,又公布对“戒严时期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台湾的出版和言论进行全面控制,禁止印行和阅读“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中的大量进步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因此,自20年代以来在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形成的以反帝爱国、反抗现实为主题的台湾新文学传统被拦腰截断。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通过各种途径加紧反共宣传,在官方扶持下掀起“战斗文艺”运动。“战斗文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歪曲现实生活、颠倒历史是非的“主题先行”的政治产物,思想内容的概念化、艺术表现的公式化,不能不是这种“反共文学”的基本特征。正如50年代后期有人在报上所批评的那样,“只在字面上充满‘战斗热’,在实质上缺乏‘文艺美’,只因只战斗不文艺,官方用‘推销主义’推行,战斗文艺令人失望”[3]。这种被戏称为“反共八股”的战斗文艺作品,随着“反共复国”的政治神话的破灭,逐渐遭到人们的冷遇当是意料中的事。这样,就为在台湾文坛上首先抒发或浓或淡的绵绵乡愁、幽幽离情,基本上不触及现实政治的女作家们,腾挪出现实空间和“用文”之地。
其次,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赴台女作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异族统治下,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制度,尤其是推行“皇民化运动”之后,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习俗、语言文字都受到明令禁止。许多在日据时期以日文创作的台湾省藉作家,包括在台湾文坛已颇有声望的杨达、张文环、吴浊流等人,光复后都面临着重新学习、掌握国语汉字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一蹴而就的语言障碍。著名省藉作家杨达曾在一篇题为《我的小先生》的文章中,追述了他在光复后如何向7岁的女儿学习国语的情景。除此之外,困扰省藉作家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前所未有的生活环境和新的文学主题一下子难以适应。面临着不断遭到退稿、写书无处出版(如钟理和的《笠山农场》等作品)的窘境,有不少人也就知难而退了。而5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台湾女作家,基本上都是40年代末由大陆赴台的,她们在大陆用母语上学念书,自幼即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熏染,有的还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凭,如孟瑶、张秀亚、琦君、潘人木等;她们中有些人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写作投稿,发表作品。赴台后,便立即显示出她们在语言艺术、文字修养方面的明显优势与特长。
再者,台湾女性文学的首度繁荣,表明了赴台女作家把握住了文坛青黄不接的契机与脉搏。光复后,孤悬海上的台湾欣喜若狂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然而,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吴浊流小说中所描写的“范汉智”们以“接收大员”之名抵达台湾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战后的台湾爆发出许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土地荒芜,司法混乱,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等等,造成了台湾历史上空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到40年代末,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上至军政机构的达官贵人,下至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大约200万人从大陆流落到台湾,对于本来就处于各种危机之中的台湾而言,不啻更是严重的大灾难。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为了生存,大多数原来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男作家,不得不手执教鞭,或是从事经商、当公务员等谋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创作数量骤减;而一些为人妻、母,生活条件相对而言稍稍安定一点的女作家,便在这台湾文坛青黄不接之时开始了辛勤的播种和耕耘。
这是历史提供的机遇。这样一种机遇并不是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想成为作家的人都能遇到。对于台湾女性文学的整体而言,这种机遇,除50年代和80—90年代,在整个20世纪似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笔者认为,台湾女性文学发轫期的成绩及其对当代台湾文学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乡愁散文”为特色的“怀乡文学”的开拓与建树,张秀亚、琦君等的作品堪称代表。
二是以描写女性的婚姻、爱情和家庭悲剧为主体的婚恋小说的滥觞与影响,林海音、孟瑶、郭良蕙等的作品可作典型。
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恰好涵盖台湾女性文学发轫期及其以后的两大基本主题。
绵绵乡愁:台湾女性文学的主题之一
毫无疑问,50年代成名的那一群女作家,如林海音、孟瑶、张秀亚、琦君、钟梅音、徐钟佩、郭良蕙、潘人木、繁露、徐薏蓝、华严等等,加上20—30年代已蜚声文坛的苏雪林、谢冰莹、沉樱等人,几乎清一色皆是40年代末赴台的“外省人”,她们的“根”本不在台湾,而在大陆的故乡(唯一的例外是林海音,她的原藉是台湾苗栗,但她出生于日本,并在北京长大、读书、就业、结婚、生子,整整住了25年才返台,因而她也早已在心目中将北京视为她的实际故乡了)。与70年代以后成名的台湾女作家相比,她们这一代人,承担了过于沉重的时代和战争的苦难。她们几乎都生于中国近代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岁月,经历过逃难、别离和迁徙的痛苦,甚至有过流离失所、飘泊无着的生活磨难。然而,时代的苦难、生活的磨难,并未使她们对美好事物、童年印象的心灵触须变得迟钝,相反变得格外敏感。因此,当她们在台湾海峡的那一端拿起笔来,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而又丰富的心灵感受,以往日大陆的生活经历作为主要素材,痴痴地抒发对大陆故乡、亲朋故旧的怀恋之情,从而成为台湾文坛上最早描写乡愁离情的作家群体,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这一来,竟然开了日后40年绵延不绝的“乡愁文学”之先河,恐怕是5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所始料未及的。当初她们抛离大陆故土,飘过台湾海峡,流落到提襟见肘的台湾岛上,她们首先体味到的便是“家乡”的亲切可贵,因为50年代嘈杂拥挤甚至不无丑陋的台湾,并不是她们心目中的真正“家园”,于是,她们翻开记忆的珍藏,细细寻觅那昔日大陆的美丽故乡和金色童年的种种印象,并将其一一描绘出来,记录下来。故土的山景物貌、民风旧俗;家乡的星月风光、花鸟虫鱼;亲人师友的悲欢离合、音容笑貌;童年时代的梦想憧憬、娇嗔憨傻……总之,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万般情怀,使台湾女作家的“乡愁散文”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当时充斥文坛的“反共八股”所截然不同的艺术境界。在她们的笔下,月是故乡明,思如长流水;往昔犹如梦,故乡宛似歌。虽然,这梦往往并不圆满,歌中亦充满忧伤,但台湾女作家执着地以细致而深情的女性笔致,娓娓地抒发着对昔日家园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委婉地表达着对亲善、友爱的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较早表现这一思旧怀乡主题的张秀亚、琦君等人的“乡愁散文”,堪称代表之作。
平心而论,50年代涉猎“怀乡文学”的台湾女作家大有人在,但象50年代初即以散文集《三色堇》出名、而后又出版了十多部散文集的张秀亚这样以大部分篇幅抒写对大陆昔日生活之回忆的人却并不多见。在她的笔下,家乡的花叫“地丁花”(《油灯碗与花》);家乡的草叫“寻梦草”(《星的故事》);家乡的月是“杏黄月”(《杏黄月》);家乡的雨是“六月雨”(《你去问雨吧》),真可谓一花一草,撩人情思;点点滴滴,情意缠绵。作为“乡愁散文”的始作俑者之一,张秀亚的散文濡纸蘸墨抒写乡恋乡情,而落笔之处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寂寞无凭的愁绪。如《星的故事》中写一对情侣在长安街洒泪离别的情景,可谓台湾女作家“乡愁散文”的寂寞无凭的典型氛围。尤其是将“滴雨的梧桐”比作“正在点点滴滴的流着涩苦的清泪”,更令人联想起女词人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写愁名句,这不能不说是属于女性独具的细腻感受与情绪的外现。“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似乎极少会把下雨与流泪连缀在一起,更难以将不见星星的雨夜想象为“星星跌落下来,化成离别前夕的眼泪”。这也正是台湾女作家的“乡愁散文”至今读来仍能撩人情思、让人感动之原因。
另一位较早以“乡愁散文”出名的女作家琦君,其散文亦多取材于亲人师友、故乡童年,因而思旧回忆之作是她写得最多也最出色的,这些题材许多人写过,但琦君写来却与众不同。琦君为文从不呼天抢地或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而永远带着一种轻轻的悲天悯人的态度,一派温情脉脉的笔墨去描述那渐行渐远的场景[4]。于是,琦君的散文常常呈现出一个与纷纷攘攘的现实世界有所隔绝的澄净天地,例如,对于人们抱怨、憎厌的久雨天气,她也会别出心裁地发现它的妙处,她竟说,“下雨天,真好!”她告诉读者:“好象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会到了亲人和朋友,游遍了魂牵梦萦的好地方。优游,自在。……[5]”无疑,这些最早在台湾文坛上抒写“怀乡文学”的台湾女作家,在当时既声嘶力竭又空洞无物的“战斗文艺”的隙缝里,在既混乱紧张又荒凉困窘的现实中,以山水之美、亲友之爱、乡恋之情、童真之笔,为台湾数以百万计的思乡病(home sick)者,悬挂了一道隔离现实、重温旧梦的帷幕,把他们“带到另一个处所,离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很远很远”,从而回避了赤裸裸的政治介入,而保持了文学本身的优美动人之特性,这也正是“乡愁散文”能在台湾文坛上绵延不绝、至今读来仍有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其实,怀乡也好,思旧也罢,除了“乡愁情结”外,也或多或少表现了台湾女作家对现实中真、善、美的人性匮乏的某种不满与反感,甚至是微弱而隐秘的抗议。但由于作者常常是以回忆往事而非客观写实的方式来叙事抒情,因而与现实之间便有了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一方面可以营造出某种含蓄蕴藉的古典式的朦胧美感;另一方面,也常使作者有意无意地“过滤”掉现实中某些假、丑、恶的东西,而又保留了某种借题发挥的自由度。例如张秀亚的散文名篇《遗珠》,写的是作者当年在北京某女子高等学府内亲手捉贼的一件逸事。本来,窃贼当然是人人痛恨的对象,尤其当作者亲眼目睹这位女贼从“那黑皮包里拿出我这月仅余的五十元”,便本能地“一下便捏住那只手,那只手正捏着的是我那五十元的一张票子!”然而,这样一个惊心动魄、人赃俱获的极富戏剧性的情景,却以作者轻描淡写之下“化干戈为泪珠”而收场。最后,“我”不仅“握住一双贼的‘友谊’的手”,还恐怕“别人难为”她而把女贼一路送出校园,并且在这件事过去许多年之后作者还借题发挥:“尽管我们的身世不同,但在造物的眼中,我们的灵魂,同是晶莹的两颗珍珠,只是我被幸运凑巧安置于玉盘之内,益形光泽,而她被厄运的大手,投掷于幽潭,沾染泥垢。盘中的珠颗,又有什么理由来蔑视、来轻贱幽潭深处那珠颗呢?……”[6]这里,贼与人之间的沟壑已完全填平与消弥,剩下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宽恕与谅解。笔者无意于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和是非判断,而只想强调的是:这个发生在作者母校的过去的往事,若干年后作者在台湾把它写出来并加上了一段冗长的议论,多少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剑拔弩张、与人为敌的人际关系的厌恶与嫌弃,以及对真诚、善良、宽容、慈悲的人性的呼唤与企盼。而这种呼唤与企盼是以充份女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并形成了台湾女性文学的传统之一。我们后来在张晓风、三毛、席幕蓉等散文名家的作品中,都明显地看到了这种对真、善、美的人性的呼唤。
女性悲剧:台湾女性文学的主题之二
如果说,以抒发思旧怀乡的情愫和意绪为主的“怀乡文学”,作为50年代台湾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的产物,虽是台湾女作家最早涉及的题材与主题,然而,终究并非女性作家的专利产品,梁实秋、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等50年代台湾知名男性作家,也先后创作了不少“怀乡文学”的佳作,以其深厚而沉重的笔致,“凝固成为具象化的乡愁”[7]。而后,思旧怀乡,作为当代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母题而绵延不绝。不过,当50年代初期孟瑶的《心园》(1952)、郭良蕙的《银梦》(1953)以及紧随其后的徐薏蓝的《绿园梦痕》(1958)、《辰星》(1959)、华严的《智慧的灯》(1961)等爱情小说的发表,加上林海音的长篇小说《晓云》(1959)和短篇系列小说《城南旧事》(1960)、《婚姻的故事》(1963)等作品的出版,无疑为当代台湾文学提供了一种以描写婚姻爱情出发来反映、观照女性外在与自身两重悲剧的新的视角和主题。这些以着重描写男女恋情、婚姻成败的经历、两性关系的际遇为主要内容的爱情小说,更是为后来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在台湾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样式与范例。
描写男女爱情与婚姻关系,早已是古今中外文学中司空见惯的重要主题之一: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日本的《生死恋》,美国的《爱情的故事》,至今读来、观后仍令人感动。然而,50年代至60年代初,台湾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重重困扰之中。一方面,是壁垒森严、如临大敌般的军事统辖与管制,迫使人们远离现实与政治;而另一方面,备受战争离乱而归期遥不可及的民众心理,却格外需要感情的慰藉与补偿。无论是蓬头垢面的灰姑娘,还是冰清玉洁的白雪公主,她们共同的愿望与理想,都在于遇上一位英俊潇洒、可寄托终身的白马王子。这样一种“爱情童话”的模式虽不无肤浅,尤其是60年代后在以琼瑶为代表的台湾言情小说中不断改头换面地重复出现,并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不能不是这种既不触及现实政治,又使不完美的人生有所感情寄托的社会心理的反映,这也正是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的言情小说,在台湾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50年代以后传统的婚姻爱情观念不断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击,因而也给婚姻爱情这一古老的文学主题,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多重色彩。在这方面,应该说,台湾的女作家,从50年代的林海音、孟瑶、郭良蕙、徐薏蓝、华严等,到60年代的琼瑶,到70~80年代的廖辉英、杨小云、玄小佛、苏伟贞、李昂、萧飒等人,这些多产、畅销的小说作者,无不发挥了自身的优势。然而,从反映女性在男欢女爱的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和结局来看,5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显然比较注重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性与悲剧性的描述和揭示。以孟瑶的《心园》和郭良蕙的《春尽》等小说为例。
孟瑶的《心园》,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较复杂的多角爱情故事,其主要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置,都令人想起20年代女作家白薇的一出名剧《打出幽灵塔》,但《心园》却没有《打》剧那打倒土豪劣绅的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时代背景。台湾女作家的爱情小说从一开始就极少让其男女主人公与纷纷攘攘的红尘发生瓜葛,而大都将其置于与喧嚣和动荡的现实相隔绝的山野田园之中。《心园》即是个典型例子,作者不仅将其男主人公命名为“田耕野”,并将其寓所置于“南山”下(这多少使人联想起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名句),而且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在优美宁静、依山傍湖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恢复或是宣泄爱的本能。与一般多角恋爱的庸俗故事不同的是,《心园》中虽也写了一男三女的感情纠葛,但其着眼点却始终在于男女在爱情天平上的不平等。如女主人公之一的胡日涓。这是一位面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童年时因出天花而损毁了容貌,并且左眼失明。但她在父母的关爱、鼓励下终于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特别护士。父母去世后,她来到南山的中学校长田耕野家,专门护理久病的田太太。田太太去世后,她对田耕野产生了难以遏制的爱慕之情。她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可是男主人公始终只是把她当作一名有经验的特别护士,他压根儿也不会象《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爱上家庭教师那样去爱这位面丑心善的女人。因而她只能强抑心中的爱情之花。她的最后结局,只不过成为抚养田家骨肉的保姆而已。女主人公之二的丁亚玫,原是田家的养女,在田耕野夫妇的宠爱与湖光山色的陶冶下长大。她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养父,为了强迫自己斩断情丝,也为了终身不离开田家,她违心地嫁给养父的胞弟,但很快婚姻面临危机。虽然孩子的降生给她带来片刻的欢乐,但她始终无法排遣“恋父”情结,并对养父续娶的一位英文女教师耿耿于怀,妯娌间常起冲突,终于导致田耕野夫妇离婚。而她又因此感到愧疚,竟在深夜吞食大量安眠药而自杀。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50年代初的台湾爱情小说并无后来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俗套,而多为伤感、凄美的男女爱情悲剧。这种爱情悲剧表明,在男女婚恋及其两性关系中,主动权与决定权都不在女性手里,而掌握在男子手中。尽管在小说中,男主人公被赋予“田耕野”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但这位被描述为“象春天的阳光,使接触到的人感到无言的舒适与温暖”的男性,与无法恋爱的胡日涓和所嫁非人的丁亚玫的痛苦恰好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意味,这两位女性的爱情悲剧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她们根本不该去爱那个她们不该爱的男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与女人从来就不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来说,这其实是女人的爱的天性和本能受到压抑与束缚的悲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欢女爱。正因为这样,50年代台湾爱情小说中,大都以女主人公的自杀而结束,如孟瑶的《屋顶下》中的莹莹,如郭良蕙的《春尽》中的沈白英等等,都可看作是女主人公对追求真正爱情的一种悲壮的献祭和牺牲,以及对女性自身的本体价值和理想主义的困惑和盲目。
对婚姻恋爱中的女性悲剧的关注,以及对理想的爱情与人性的呼唤,在稍后些时出现的林海音的长篇小说《晓云》(1959)和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1960)、《婚姻的故事》(1963)中,得到了更为系统、有力的描述。这几部作品,前者写的是50年代大陆去台的“新潮”女性的一桩“畸恋”悲剧;后者则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清末民初至今的形形色色的女子的婚姻悲剧。林海音的小说,几乎全都以历史的或现实的婚姻爱情悲剧作为题材,她的作品整合起来,恰恰构成了一部20世纪中国女子大半个世纪的婚恋悲剧史。尤其是她所描述的那一个个令人颤栗的“生为女人的悲剧”,更是在台湾女性文学的原野上,树起了第一块里程碑。
林海音的短篇系列《城南旧事》,常常被归入“怀乡文学”的典型之作,或是被当作“自传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这都是误解。表面看来,《城南旧事》是根据作者的自身经历与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怀乡”之作。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部笼罩着浓浓乡愁与乡恋的作品中,令人触目惊心的仍然是对二、三十年代生活于大小胡同内的中下层女子不幸遭遇与命运悲剧的揭示,今天读来仍使人心颤。如《惠安馆传奇》中的秀贞,这个追求自由恋爱和人生幸福的活泼泼的姑娘,不仅与青年学生思康的美好姻缘被活活拆散,呱呱坠地的亲生骨肉被活活丢弃,还被视为疯子,在旁人的白眼与鄙视中度日。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么?正如小英子所说:“我只觉得秀贞那么可爱,那么可怜,她只是要找她的思康跟妞儿——不,跟小桂子”。这种出于女性和母性本能的天伦之爱,都不能见容于周围的人们,包括她的父母,毫无怜悯地将刚落地的亲外孙女丢弃在城墙根底下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秀贞的母亲!然而,这位为维护女儿的“贞洁”而狠心丢弃亲外孙女的母亲,不仅造成女儿因骨肉分离而精神失常,而且最终导致失去理智的女儿雨夜带着刚刚相认的孩子去找丈夫而被火车双双轧死的惨祸,落得老来骨肉皆亡的悲剧下场!这篇可称为“女性命运”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突破了当时台湾一般爱情小说的滥情模式,而透过秀贞一家三代女人的遭遇将人们引向对女性悲剧的根源的思考,揭示了女人不仅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而且也是血缘悲剧的制造者这样一个深刻命题。这在此之前甚至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中都是罕见的(直到80年代廖辉英的《盲点》的出现,才又隐含了“对红尘中一切受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悲悯”[8]的命题)。
正是这种基于人道主义的“悲悯”精神,使得《城南旧事》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几乎无一是亲情的幸运者,如《驴打滚儿》中的女佣宋妈的悲剧,不仅在于她终于知道了失去亲生儿女的真相,更在于面对那个嗜赌如命、连亲骨肉都卖的丈夫“黄板儿牙”既恨之入骨又别无选择。这位勤劳能干、善良可亲的老妈子,最后还是坐在毛驴上,跟着“黄板儿牙”回家了。正是在这里,作者通过宋妈从“出来”到“回去”,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遭遇,揭示了传统妇女只能扮演妻、母角色的永恒悲剧命运。
与秀贞、宋妈的悲剧性结局相比,那位曾操贱业、倍受损害的兰姨娘,其结局却颇具喜剧色彩:经聪慧机灵的小英子牵线搭桥,她竟与从事革命活动的北大学生德成叔一见钟情,双双携手同去。兰姨娘的喜剧性结局,在《城南旧事》系列小说中,犹如在一出悲剧交响曲中,突然跳出的一串略带顽皮的浪漫音符。然而,细细思量却不难发现;兰姨娘的“喜”恰恰正是为了衬托英子母亲的“悲”。从表面看来,英子有一个温饱不愁、和睦温馨的幸福家庭,父亲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他正直豪爽、乐善好施,同情革命者,痛恨侵略军,在学生和儿女面前,他不失为一个好教授、好父亲。然而,对于英子的母亲,他却绝不是一个忠实的好丈夫。在他面前,英子母亲只不过是一架供他传宗接代的机器而已。她除了不断挺着大肚子为他生儿育女之外,还不得不忍受丈夫与娇滴滴的兰姨娘眉来眼去的调情,小说虽未明写她的婚姻悲剧,但对于这位贤妻良母的同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这位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别无一技之长的家庭主妇而言,婚姻只是给了她一张繁殖儿女的许可证,并没有成为丈夫对她忠实的保证书。假如丈夫拈花惹草,她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她缺乏谋生的本领和经济的来源。她和宋妈同样别无选择。
可见,即便是在以旧北京特有的风土人情与淳厚“京味”著称的《城南旧事》中,林海音所着力反映的也是旧时代妇女的不幸命运、痛苦遭遇与屈辱地位。与50年代其他一些台湾女作家所描写的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不幸际遇不同(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马兰自传》等),她常常并非将其人物置于社会大动乱的时代背景下,以人物命运来反衬时代灾难或社会祸因,而是执着地将笔触伸入一个个家庭闺阁,从反映少奶奶、姨太太们的不幸婚姻和畸型的两性关系入手,以此来展现上一代中国妇女的性格弱点和命运悲剧,以及长期处于这种妻妾成群的环境中被扭曲的个性和异化的人性。这在她60年代初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婚姻的故事》中显得格外集中而引人注目。在这部小说集中,对于封建的制度、礼教、习俗和家庭,以及对于封建时代天经地义的“一夫多妻”制的腐朽与罪恶,作者都有所揭露。《殉》写的是一个发生在“讲认命的时代”的一位终身守活寡的女子的婚姻悲剧。少女朱淑芸(方大奶奶)被父亲许配方家长子,由于未婚夫患有严重的肺疾而受命“冲喜”完婚。过门才一月,新郎就死了。从此,这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便开始了漫漫长夜无尽期的寡居生活。作者以极其细腻、精致的笔触,刻划出了这位方大奶奶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痛苦心态:“她虽然没有以死相殉,但是这样生活着,也和死殉差不多吧”。
是的,在封建时代,女人始终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物,乃至殉葬品,她们根本没有择偶的自由和权利,也毫无独立的人格与地位。明媒正娶的方大奶奶的遭遇如此,那些使女收房的姨太太的命运,也就可悲可叹了。《金鲤鱼的百褶裙》写的是一位由使女而收房的小妾,她为许家生下唯一的儿子却至死得不到应有的名份和尊重。她生前唯一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在亲生儿子的婚礼上,穿一穿“与老奶奶、少奶奶、姑奶奶所穿的一样”的大红百褶裙而已,却至死未能如愿,而阻挡她这一愿望实现的,恰恰正是那个当初亲手将她送给老爷做妾的许大太太!然而,许大太太也并非凶神恶煞的母夜叉,她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只因生了五个女儿而未得儿子,就面临着“老太太要给丈夫娶姨太太”的威胁,虽略施小技将贴身使女金鲤鱼做了老爷的小妾而解除了外来的侵犯,却从此让老爷“归了金鲤鱼”,自己只剩下一个许大太太的空名而已。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女人不仅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而且还是命运悲剧的制造者的深刻命题。
封建家庭内天经地义的“一夫多妻”制,不仅使生了五个女儿的许大太太忙不迭地亲自为丈夫挑选小妾奉送,而且还造成了打入“冷宫”的大奶奶既戕害自己又折磨别人的变态心理。被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先生称为“题材可怕”而“技巧完美”的《烛》,写的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大奶奶,虽生了4个儿子,但才30岁丈夫就纳了妾。她表面上装得雍容大度,心里却日夜忍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和对小妾的怨恨的煎熬。于是,她就躺在床上装瘫,并不时发出哀嚎,想以此来惩罚丈夫和小妾。谁知她长期卧床造成大小腿肌肉萎缩,由装瘫变成了真瘫。在描述这类封建家庭内妻妾成群的内幕时,林海音基本上不去展示她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宠吃醋,而是全力刻划她们那种无可奈何而又自作自受的悲剧命运。《烛》通过这位可笑、可悲复可怜的大奶奶的悲剧一生,揭示了妻妾成群制度对于妇女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戕害。
除了描写上一代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及其婚姻悲剧外,林海音也从女性生理与心理两方面触及了同时代妇女的非正常的婚外恋情。如《婚姻的故事》中的少妇芳。因姐姐去世而成为姐夫的续弦。表面上看,她的婚姻、家庭都很美满:婆婆疼爱,丈夫厚待,儿女齐全。然而,她却因文弱的丈夫缺乏生活情趣而与同事沈先生“偷情”,招致议论纷纷。丈夫病殁后,她料理完丧事,并未如释重负,公开投向沈先生的怀抱,反而与之斩断了情丝。作者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她是个年青的女子,也需要异性的爱抚。她的丈夫给她的,只是宽恕和谅解,这样反而更引起了她的反感、嫌恶和叛逆的心情”。丈夫死了,反抗对象消失了,她的“偷情”也结束了。因此,芳与沈先生之间的婚外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她对自己丈夫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这种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关系的反抗。
对于孱弱无力的丈夫的鄙视,在《蓝色画像》中成了对性无能的丈夫的莫大嘲弄。丰腴而成熟的丽清,嫁了个“小腿上细细落落的汗毛,那软弱无力的小腿肚子”都使她憎厌的丈夫。结婚数年,膝下犹虚,“当然,根据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传统习惯是该派女人承担下这不育的责任”,但丽清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丈夫得知医生叫他去作检查后却“坚决,强横,而不屑地”一口否决:“我没病!”连丽清也看出来,要丈夫去检查“是如何伤害了男人的优越感”。直到他怀抱着妻子与另一个男人所生的女儿,还耿耿于怀地认为当初医生要他去检查“那简直是侮辱”。明明是丈夫性无能而讳医忌药,却要处处显示“男人的优越感”;而丽清呢,明明怀着另一个男人的骨肉,却又不得不跟令她厌恶的丈夫厮守相处,这里便预埋着多年以后《杀夫》(李昂著)的两性战争的导火索,也提出了《贞节牌坊》(吕秀莲著)究竟为谁而树的大问号。从50年代的林海音到80年代的李昂、吕秀莲,台湾女性文学的主题既有很大区别,又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台湾女性文学发轫期的重要作家,林海音以及孟瑶、郭良蕙等人所塑造的不幸的女性群像,已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画廊中不可或缺的珍稀标本。
(作者系本校中文系博士;责任编辑 胡范铸)
[*]关于“女性文学”的界定,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不外乎广义的、半广义的与狭义的三种划分法。广义的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自然亦包括男性作家所创作的此类作品),如张抗抗的《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等文。半广义的指具有妇女意识的女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如钱荫榆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妇女文学”散论》(《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等文。狭义的专指女作家创作的以描写男女不平等、表达女权观点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朱虹的《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等文。笔者基本上同意后一种意见,对本文所论及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范畴作如下界定:即50年代以来台湾女作家创作的以反映妇女命运及其处境,表现女性意识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笔者注。
注释:
[1]《台湾文学史》下卷,刘登翰等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页。
[2]在50年代成名的台湾女作家中,潘人木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既写过《如梦记》、《马兰自传》、《莲漪表妹》等反共小说,成为当时“风头最健”的女作家,但也写过非政治化的纯文学作品。如反映知识分子家庭悲欢的《哀乐小天地》、《闹蛇之夜》等,“写悲剧是一路巧笑倩兮的含泪而来而去,缠绵委曲,哀而不伤,这是正宗的中国悲剧。”(见《台湾作家小说选集》第2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64页。
[3]《岁首说真话》,载1958年1月5日台湾《联合报》。
[4]徐学:《以爱心洞照忧患人生——浅淡琦君散文》,载《台湾文学选刊》1988年第4期。
[5]琦君:《下雨天,真好》,载《台湾文学选刊》1988年第4期。
[6]张秀亚:《遗珠》,载《台港文学选刊》1988年第2期。
[7]齐邦媛:《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转引自《现代台湾文学史》,第269页。
[8]廖辉英:《我为什么写〈盲点〉》,见《盲点》,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标签:文学论文; 优美散文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台湾生活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城南旧事论文; 林海音论文; 乡愁论文; 张秀亚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