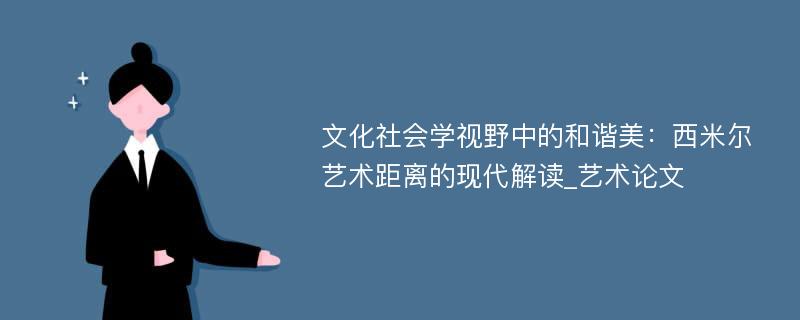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和谐美——齐美尔“艺术距离”的现代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谐美论文,视域论文,现代性论文,社会学论文,距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美尔是德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和美学家。他从现代性体验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对现代都市生活风格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现代文化作了诊断。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深入和大量的碎片化景观对个体的冲击,导致个体在躁动的现代生存中的无聊、无助以及极度空虚;而且,随着现代生活的货币化,现代文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齐美尔提出“距离”概念,认为个体只有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才能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与救赎。在齐美尔那里,作为一个表征现代性的概念,距离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学和美学视域中,同时它也体现在艺术视域中。如果我们把“距离”看作是一个家族体系,而“社会距离”、“时空距离”和“审美距离”是其中的一个家族成员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艺术距离”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成员。在《桥与门》中齐美尔写道:“艺术家以他艺术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并形成他的世界观。”① 也就是说,艺术家总是以他独特的艺术家的眼光和艺术方式对他所面临着的现代世界作出反应。对艺术家而言,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他独特的艺术表现来反映这个世界及其自我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齐美尔的距离思想,“距离”在艺术的层面上便呈现为一个艺术家及其艺术品与他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而艺术对称则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范例,它是对艺术与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平衡,实际上也是希望艺术在社会中保持一种和谐的审美张力。
一、艺术与现实:艺术距离的命意解读
在齐美尔看来,艺术不同于现实,艺术家对现实的把握建构了种种艺术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宗教对于我们现实的双重性,艺术同样具备,艺术是生活的另一种东西,它是生活的解脱,通过生活的对立面,生活得到了解脱。在这一对立面中,事物的纯形式为事物主观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均无所谓,它拒绝被我们现实所触动。但是,当艺术内容和幻想进入到远距离的时候,艺术形式反而离我们近了,比它在现实形式中离我们的距离更近。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生活的手段和材料,而艺术作品则保留着它的独特性。一切现实对于我们来说,最终保留着一种很强的陌生感,人们对于索取和给予的追求,在我们的灵魂和其他灵魂之间,绝对不能相通,毫无逾越希望,浇铸到艺术形式之中的恰恰是我们的灵魂。由于艺术作品更加独特,它就比所有的一切更加向着我们。②
“艺术是生活的解脱”表明艺术与生活不一样,进入艺术乃是一种解脱,就如同宗教一样。这种解脱恰恰是一种距离的体现。艺术是一个与现实不一样的虚幻世界,它是与现实有着差距的想象的生活存在。在讨论舞台艺术的时候齐美尔指出:“演员使剧本形象化,但不能把戏变成现实。因此按其概念,演员的动作只可能是艺术,而绝不可能是现实。”③ 在这里,齐美尔再次强调艺术与现实的不同,在舞台艺术中,演员不是将戏剧艺术作品转变成真实性,而是相反,要把作品指出的现实性变成表演艺术品。因此,舞台上上演的一切都是艺术的“现实”,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不仅舞台艺术,一切艺术均如此。也正是由于艺术与现实的差异,才有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齐美尔那里实际上是以距离为参照系来加以分析的。
在《货币哲学》中,齐美尔曾对“距离”进行这样的界定:“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距离”的实质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主客关系,距离是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关系。“一个经常用以描述生活内容之构成的形象,是把它们围成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心是真正的自我。有一种关联的模式存在于这个自我同事物、他人、观念、兴趣之间,我们只能称之为这两方面的距离。无论我们的客体是什么,它能够在内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靠近我们视野圈和兴趣圈的中心或者外围。但是这不会使我们与该客体的内在关系产生任何变化,相反,我们只能藉着对两者的距离的一种确定的或变化的直观的象征,来描述自我与其内容间特定的关系。”④ 在齐美尔眼里,距离的内在本质是自我同事物、他人、观念、兴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人与种种事物的内在关联的多样性则被理解为二者之间远近亲疏的距离的多样化。个体不得不在客体与自身之间建立一段距离,以此获得关于对象的客观印象。然而,当我们以不同的距离角度去观察一个客体时,所得到的图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每一个距离所得到的图像都是正确的,而且只有在这个距离的基础才可以说是正确的。也正是如此,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理解,如从另一个距离角度来看,又都可以说是错误的。⑤ 正如戴维斯所言:从距离的角度出发,齐美尔不仅分析了客体之间的相互隔离和内在关系,而且也分析了它们与观看者的分离。观看者对客体的不同距离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观看方式,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观看者得以体验到这些客体。不仅仅在美学的和社会学的体验方式中观看者与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距离,而且在那些实践的、科学的、历史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体验方式中也是如此。⑥ 所以,齐美尔认为,应该承认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合法性,它们构成了我们与外在事物关系的多重性。对于艺术而言,更是如此:
一方面艺术使我们离现实更近,艺术使现实独特的最深层的含义与我们发生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艺术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外部世界冰冷的陌生性背后的存在之灵魂性,通过这种灵魂性存在使存在与人相关,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此之外,一切艺术还产生了疏远事物的直接性;艺术使刺激的具体性消退,在我们与艺术刺激之间拉起了一层纱,仿佛笼罩在远山上淡蓝色的细细薄雾。艺术拉近和疏远人与现实的距离的两种效果有同样强烈的吸引力;它们二者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多种多样的对艺术品的要求中的分配,赋予每一种艺术风格具体的特色。⑦
艺术不同于现实,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距离,它可以是拉近,也可以是疏远:艺术不仅具有疏远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功能,而且也能拉近人与现实的关系。“拉近”并不仅仅意味着人与现实的关系的靠近,它的深层内蕴在于:艺术通过特定的表现形式使现实的深层意蕴彰显出来。这种深意原本隐藏于纷乱的生活背后,通过艺术,人们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反观现实,达到对现实的更高层次、更深刻的理解与熟悉。如果说拉近揭示了隐藏于现实背后的深意,那么,疏远则使现实事物直接消退,将艺术自身的独特审美特性凸显出来,使艺术更具魅力。值得注意的是,齐美尔在这里强调了两点:第一,无论是接近还是疏远,两种方式均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对艺术来说,靠近现实与远离现实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它们只不过是艺术与现实的两种关系,或者是两种距离。第二,齐美尔指出,接近与疏远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正是张力的这种多样性构成了艺术的不同风格形态和千变万化的魅力。当然,在接近与疏远之间,齐美尔更注重个体对生活的疏远,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齐美尔距离观念的核心所在:“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⑧。对齐美尔而言,一方面,个体对生活的疏远是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现代主义艺术强调自主性,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变形,其实质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偏离和疏远;另一方面,个体对生活的疏远也是现代性发展的历史必然。现代性的发展使得货币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日益膨胀,物质文化的财富也日益见长,对此,现代个体已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体要想保全自我的完整性,也必须与外在强大的物质文化拉开距离。这正如约莫斯蒂迪特对齐美尔“距离”的分析:一方面,个体通过“距离”而感知外在事物,另一方面,“距离”也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⑨ 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个体努力疏远物化生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带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
因此,通过创造距离,艺术家在这种对生活的疏远中实现对现实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但不论是“拉近”还是“疏远”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上都创造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距离。为了获得对事物的更深刻和更真实的认识,我们只能承认这种距离,甚至我们还应努力地主动创造出这种距离。只有在对距离的体认与创造中,个体才能从外在物化的客观文化中抽身出来,摆脱与外在事物间各种伪俗的、功利性的亲密接触,重返个体内心。顺着齐美尔的分析,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发挥。现代艺术感强调的是距离,而距离能使艺术产生特殊的魅力。艺术距离所散发出的魅力,我们可以理解为艺术的含蓄手法所导致的一种艺术效果。也就是说,从含蓄的艺术风格中寻求理解对象已成为现代艺术的事物的主要特征。艺术品的朦胧和捉摸不定,满足和刺激了主体欣赏的多方面需要。齐美尔指出了现代艺术的含蓄风格的魅力,而艺术品的不完全性、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含蓄性等,均可以看作是现代艺术距离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距离也是一种艺术的内在形态或风格,现代主义艺术明显的原始性、直接性、未完成性、草图性、强烈表现性等等,这些艺术风格从比较的意义上说,都可以视为一种现代艺术规范与古典艺术规范之间的距离,它们导致了现代主义艺术全然不同于古典艺术的精致、完美、完成性和规范性。
此外,现代人审美兴趣的丰富与挑剔拉长了事物成为艺术时所产生的距离,而通过这种距离,则可以超越艺术与我们自我以及世界关系的直接性:
艺术的纯粹性要求一种距离的存在,一种情绪的释放。艺术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于艺术家以及对于艺术的欣赏者,艺术使我们超越了艺术与我们自己的关系的直接性、以及艺术与世界关系的直接性。艺术的价值依赖于我们对此种直接性的克服,以至于艺术就仿佛根本不存在着直接性一样地发挥着作用。如果能够肯定的说,艺术品的魅力毕竟是依赖于与原始情绪的共鸣,正是这种原始情绪从根本上激动了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得承认,艺术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情绪的美学形式和直接性,而在于当直接性退隐之后艺术品所获得的新面目。⑩
以齐美尔的论述为前提,我们发现,现代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变形与遮盖,意味着艺术对自动化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中断和对日常生活意识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若我们进一步地加以分析的话,它实际上是对现行的日常生活秩序的一种抵制或反叛。因此,否定也就暗示着现代艺术对日常生活刻板模式的不满,并希冀对蔓延的工具理性暴力形成的对人性的统治与压迫进行反抗,使现代个体在资本主义异化文明中找到归家的感觉。齐美尔说,现代个体不但“只有在距离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的特征。”(11) 外在的物理距离日益被征服,现代个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却越来越大,因而个体对从物化现实中脱身出来的自由灵性也就愈发珍惜。“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其实就是现代个体面对都市社会心理距离的无限拉大而产生的一种对理想家园的渴望情怀,一种渴望“归家”的怀旧情结。对此弗里斯比写道:“受害者对异化中的客观文化的反应,是对人和价值的不断增加的冷漠,对世界的日趋严重的腻烦态度,以及一种向内心领域的退缩。冷漠和腻烦态度,能被致力强调个人和世界之间距离的更广泛的现实审美化轻易融合……对某些社会阶层,特别是世纪之交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来说,向内心的退隐容易和对生活的主观美化结合在一起。”(12) 可见,个体的内撤,以及渴望在内在世界中寻找“归家”的情绪,实际上也是齐美尔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主观美化。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中断,就是要打破自动化和常识化的习惯生活方式和生活无意识,要否定陈旧的生活模式,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提供一种鲜活的审美经验。
进一步地分析也表明,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是现代文化与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文化中,生活已日趋外化,生活的技术方面压倒了其内在的方面,即生活中的个人价值。在现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这种保持距离的倾向。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外化是趋势,而精神生活的内化则是一种必然反应,这也正是现代艺术距离必要性和合法化的表现。主观性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普遍特征。可以说,对自我的过分强调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现代主义的这种主观性,用齐美尔的话来说,就是疏远物化现实。齐美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兴盛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齐美尔所提出的距离思想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物化文明的一种拒绝,而且也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强调自主性、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冷漠或否定的一个天才预见。如果我们将齐美尔的艺术距离思想与现代西方艺术相对照来看,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无论是现代艺术的自主性,还是奥尔特加的“非人化”,抑或是阿多诺的“艺术否定社会”,都强调了艺术与外在现实的一种距离,而这,实际上是对齐美尔艺术距离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呼应。
二、艺术对称:张力中的和谐美
艺术距离强调艺术与现实的一种关系,而艺术对称则是艺术距离的一个典型范例。对称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审美原则,一方面是对现代生活的非均衡性所导致的距离现象的一种调和;另一方面,对称也创造着一种距离,它意味着日常生活的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就是要在对立的双方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距离。
首先,对称是一切美学的最原初动机,对称的审美性来自于事物原初的实用性。“一切美学的动机最初都是对称”(13),对称是所有美学的最初动机,它源于事务管理中的实用性。齐美尔举了一个例子:在古代文化中,如军事、税务、刑警以及许多其它组织都是由十人组成一个单位,然后再由十个这样的单位又组成一个更高一级的百人单位。这样的组织原则最初目的是使组织机构一目了然、容易标识和便于管理。因此,这些社会组织形态最初往往都是单纯实用性的产物。然而,这些所谓的十人单位和百人单位,其实往往只是徒具虚名,那些百人团体有时多于一百人,有时却不到一百人。如中世纪巴塞罗那的元老院号称百人机构,但实际上人数却超过了两百。因此,源于组织原则的最初的实用性就成为一种虚构,而这说明“单纯的实用性已经转变成了在社会事务中带有建筑学倾向的审美性,变成了对称的魅力”(14)。这样,对称就由事物原初的实用性原则转变成了审美性原则。
其次,对称是审美对象各要素间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一种平衡。“对称的本质在于,一个整体的每一个要素只有顾及到其他要素、顾及到一个普遍的中心才能各守其位,各遵其道,各存其意。倘若各个要素反其道而行之,只听从一己之愿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体的形态就会随意地左冲右突,必定毫无匀称可言。就其美学映象来看,两种形式的这种冲突是一切活动过程的基本主题,它在一个社会整体——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经济的、社交的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及其个体成员之间反映出来。”(15) 在齐美尔看来,对称使整体中的各个要素各安其分,形成了审美的“理性主义”效果,而由对称所导致的理性主义审美状态能够使纯自然形态的偶然性和杂乱无章状态最明显、最直接、最简单地展现在个体面前。“美学中的对称意味着某个要素与它跟所有其它要素交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同时也意味着以这种制约关系为特征的范围的局限性。”(16) 为了使事物具有理念、意识和和谐的特征,为了使事物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显现出审美意味,就必须使它们对称,使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互相平衡,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匀称地排列。
对称原则所导致的这种社会平衡最为明显地体现在货币文化对个体以及现代生活的影响上。对于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文化后果,齐美尔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分析:“货币在自由与结合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联。但同样,货币也在它造成的整合的迫切性和不可避免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这产生了特殊的后果,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感打开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活动空间。”(17) 货币一方面制造了一种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无个性化,另一方面又强化和提高了现代个体的独立性。因此,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现代文化的两极分化,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使之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凸显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为个性保留着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性化和自由成为可能。就前一种倾向而言,货币铸造了现代社会中风格平均化和量化的价值取向,“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18)。货币作为一切价值的绝对表现手段,俨然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唯一法官,它带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平均化和量化。从这个方面来说,货币创造了现代生活中的距离,货币功能的扩大使我们远离事物本身,我们与事物本身之间的亲切性被切断,仅仅依靠一种中介(货币)来体验他们,而这种中介却不将事物的全面性和直接性展示在我们面前。就后一种倾向而言,货币的存在,极大地扩大了现代个体行动的范围。货币可以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使前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事物在现代社会中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来说,货币导致了现代生活中距离的消失。作为一种纯粹的交换手段,货币的使用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可以适用于任何的目的和意图,它使彼此最背离、相距最遥远的事物找到了共同的因素和基点。不难看出,货币所带来的“平均化”及“个性化”其实就是货币经济影响下的一种文化“对称”,它是对货币文化所带来的个体社会反应的一种平衡。
再次,对称原则在齐美尔那里意味着美学欣赏中的“省力”原则。齐美尔写道:“如果我们把美的吸引力作了这样的理解,即认为对美的想象意味着思考上的省力,意味着以最小的努力,展开最丰富的想象,那么,像社会主义者所致力的那种对称的、没有对立的群体的建立,就完全满足了这种要求。”(19) 齐美尔是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美与个人主义的美时提出“省力”原则的。对齐美尔来说,“个人主义的社会利益是不均等的,意向是势不两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它只是由少数人所支持的。这样一种社会使精神显得不安宁、不坦然,要绞尽脑汁才能觉察它,要竭尽努力才能理解它”(20)。因此,个人主义的美具有“不平衡性”,它意味着审美欣赏中的“费力”原则,需要个体用尽心思才能理解。而社会主义的美则与此相反。从表面上来看,社会主义根据和谐和对称的原则来展示自己的合理性,从而使社会生活风格化,似乎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总是按照对称的原则来加以设计的,如居民点或建筑物的布局不是圆形的就是正方形的。但从深层次的原因来分析,社会主义对和谐与对称的偏好主要是为了实现审美的省力,即以最小的努力、最简单的思考展开最丰富的想象。
这种“省力”原则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实用性。如齐美尔所言,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成了一件艺术品,其中的每个部分由于其对整体的贡献都具有一种明显的意义;由一个统一的方针有目的地决定一切生产,而不是自由诗般的偶然性来决定(现在是个人的作用偶然地对总体带来利益或损害);生产要绝对协调,不要搞浪费精力的竞争和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21)。齐美尔认为,社会主义对这种平衡的对称美津津乐道,就在于在这种对称所导致的平衡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按对称原则来运转的。“社会主义的平衡的社会则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在布局上是对称的,在共同的中心里,它的活动的相互接触能够使人不费什么脑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感觉到它所遵循的思想,作出社会形象的概括,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美学意义比抽象的形式所显示的美学意义可能更会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心理状态。”(22)
此外,齐美尔还认为,对称仅仅只是审美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对不规则的非对称的渴望。审美的第一步是跨越了对事物的无意识的一味容忍而达到对称的,审美的第二步则在新的不规则和新的非对称上得以产生。对齐美尔而言,不对称也会产生强烈的审美诱惑,审美就存在于对称与非对称的动态张力中:“只要整个生活是本能的、直觉的、非理性的,美学就永远会以如此理性的形式从生活中获得解脱。倘若生活中充满着理解、对比、平衡,那么,审美的需要又要遁入自己的对立面,又要去寻觅非理性及其外部形式即非对称了”(23)。虽然如此,齐美尔还是强调,目前个体所感受到的美几乎还只具有个人主义的性质,美实质上是个人的感觉,不管个人感觉跟大家的特点和生活条件相反也罢,截然对立也罢。在齐美尔那里,个人不仅是一个整体的一分子,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如我们将社会主义的对称美视为审美的一种普遍主义,而将个体主义对自由的追求视为一种审美的个性主义的话,那么,齐美尔其实是想保持审美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的一种距离的动态平衡,现代生活的审美就存在于这种动态的距离张力中。在齐美尔那里,艺术对称主要强调的是艺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平衡功能,其实质是希望艺术在社会中保持一种和谐的审美张力。
注释:
①②③(13)(14)(16)(18)(19)(20)(21)(22)(23) 齐美尔著,涯鸿等译:《桥与门》,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7页、第141—142页、第197页、第217页、第219页、第223页、第265页、第223页、第223页、第221页、第223页、第217—218页。
④⑦⑧(10)(11)(15) 齐美尔著,陈戎女等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第384页、第363—364页、第87页、第389页、404页。
⑤ K.H.Wolff,ed.,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0)7.
⑥ Murray S.Davis,Georg Simmel and the Aesthetics of Social Reality,Social Force 51.3(March 1973):326—327.
⑨ Otthein Rammstedt,“On Simmel's Aesthetics:Argumentation in Journal Jugend,1897—1906”,Theory,Culture & Society 8(1991):133.
(12) 弗里斯比著,卢晖临等译:《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8页。
(17) 齐美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标签:艺术论文; 齐美尔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现代性论文; 关系疏远论文; 现代艺术论文; 美学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