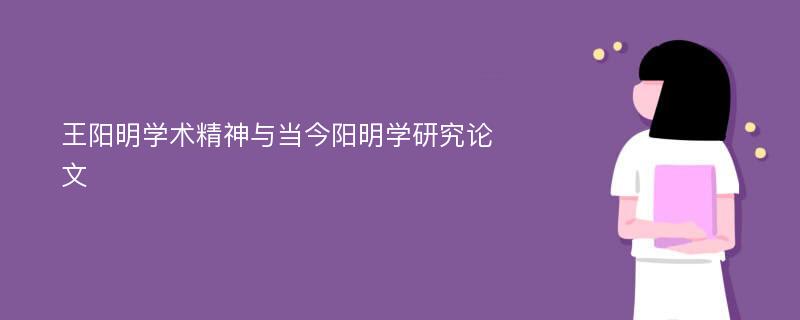
·学人论语·
王阳明学术精神与当今阳明学研究 〔*〕
李承贵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阳明心学之所以成为儒学史上独具魅力且振聋发聩的学说,乃是其固有的学术精神使然。阳明学术精神集中表现为客观精神、怀疑精神、包容精神、关怀精神、创新精神五种,此五种精神内在地规定了阳明心学的品质。然而,此五种精神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甚为欠缺。因此,无论是作为阳明心学的传承,还是作为阳明学的开新,当今阳明学研究都应责无旁贷地拥有并贯彻此五种精神。对正处于热火朝天中的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阳明学术精神似乎也显得颇为适宜。
〔关键词〕 王阳明;学术精神;当今阳明学研究
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是某些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天下之公器,是天下人共享的公理。“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1〕阳明所谓“公言”,就是为天下人主持公正,说公道话。那么,“学术”怎样才能为天下人说公道话呢?答案就在阳明的学术精神中。
一、客观精神
阳明虽然钟情对经书的新解,虽然期待对先贤的超越,虽然致力对争鸣的突破,但对学术的客观性仍然怀有虔诚的敬畏。在阳明看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在没有进入思考、研究之前,都应该是完整无缺的存在,都应该是毫无雕饰的存在,而不应该有随意的删改、主观的损益。顾惟贤曾咨询阳明编撰杨简文集的事,并将“欲摘其尤粹者再图翻刻”的想法告知阳明,但此想法遭到了阳明的否定。阳明说:“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观。来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图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论,自各有见,语脉牵连,互有发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删节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尽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别。”〔2〕阳明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为了后人能够完整地了解、研究杨简的思想,编撰杨简著作最理想的做法是尽力保持原貌,不能根据编者的喜好进行删改、损益。而当下阳明学研究中,对文献随意删改、增减现象仍然司空见惯。有学者为了研究的方便,随意删除自己认为无价值的文献,使阳明思想不能完整地呈现,从而导致研究的结论陷于片面;也有学者为了使自己的“创新观点”不被证伪,故意将不利的文献删去,或者视而不见。学术研究一般的叙述逻辑是,在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才进行总结并给出结论。然而有的研究与此相反,在进入正式研究之前,就对尚未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予以定性,阳明称之为“先有个意见”。阳明说:“大凡看人言语,若先有个意见,便有过当处。”〔3〕在阳明看来,若是在分析、研究某个问题之前就有了“意见”,接下来的研究只是为了这个“意见”寻找依据,只是为了论证这个“意见”的正确性,只是照葫芦画瓢,那么这种研究不仅无法深入下去,甚至无法展开,至于研究的客观性更是一种奢望,当然只能是“过当”。遗憾的是,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我们也时常遭遇“先有个意见”现象。比如,将王阳明心学贴上“神秘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主义”“天下第一学问”等标签后,再煞有介事地论证这些“意见”的合理性。“朱陆异同”仍然是阳明时代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那么阳明是怎样的态度呢?有王舆庵者是象山而非朱熹,有徐成之者是朱熹而非象山,具体情形是肯定象山的王舆庵批评朱熹无“尊德性”、肯定朱熹的徐成之批评象山无“道问学”。但阳明认为二人皆不切实际而各有所偏。因为根据阳明的考证,重“尊德性”的象山并不排斥“道问学”,重“道问学”的朱熹并不排斥“尊德性”,所以王、徐二人皆局于一隅。那么,王舆庵与徐成之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呢?因为二人都是从私心出发,都是出于个人的喜好,都是意气用事,都未能全面地、事实地认识和理解象山或朱熹的思想,从而有失公正。阳明说:“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4〕因此,阳明特别强调全面了解、真实把握、公正评判对于学术争鸣的意义。阳明说:“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5〕但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人们对于学术争鸣或者不置可否,一团和气;或者偏于私情,于亲近者不顾事实地赞美,于疏远者不顾事实地批判;或者囿于好胜之心,意气用事,固执而孤傲,无人能入其法眼。综合言之,阳明关于完整保存杨简文集而不使遗漏的建议,关于研究问题不应先有个“意见”的主张,关于学术争鸣必须尊重基本事实的要求,集中体现了依照事物本身认识、理解和评价事物的精神,此即阳明的学术客观精神。作为以传承、弘扬阳明学为使命的当代阳明学研究,自然应该传承与弘扬阳明的客观精神。而这种传承与弘扬的最有效体现,就是在阳明学研究实践中贯彻其客观精神,使“意必固我”远离阳明学研究。
二、怀疑精神
阳明虽然礼敬先贤,虽然尊重经典,但从不为先贤、经典所束缚,而是提倡独立思考、不断追问,认为学术研究有疑问才会有开新、有思考才会有进步。王阳明礼敬先贤但绝不是无原则非理性的崇拜。在王阳明时代,学术思想界有两大权威,一个是至圣孔子,一个是先贤朱子,天下人为学求道,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无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但阳明认为,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能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同和称许,不是他有多高的地位,也不是他有多大的学问,而是他的学问中有没有“良知”,有没有“本心”。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6〕就是说,孔子的言论固然可敬,朱子的言论固然可亲,但若是与“良知”相悖,不管是孔子还是朱子,都将失去阳明的信任,都将被列为怀疑的对象。然而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于王阳明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歌颂、赞美,将王阳明奉为完美无缺之人。王阳明虽然敬畏经典但绝不沉迷经典。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经典当然不能被轻慢,需要认真学习、切身体悟、虚心消化,但也绝不能膜拜而丧失自我。阳明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7〕对阳明而言,经书只是澄明“本心”的工具或方式,经书所诉说、所追求、所传播的是“良知”。若是相反,经书并不以论述“良知”、传播“良知”为目的,反而要求对之顶礼膜拜,经书赞成的不许反对,经书反对的不许赞成,从而蜕变成禁锢思想的牢笼,怎么还值得信赖呢?然而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于阳明学经书文献大多是极力圆融其抵牾、高扬其价值,少有理性分析和怀疑。王阳明对先贤的学说同样是既尊重又怀疑。朱熹主张“格天下之物”,而且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阳明对朱熹“格物”说提出质疑:“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8〕尽管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标准答案,但王阳明仍然挑战其权威、质疑其合法性,并由此提出新的学问方向:“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9〕阳明因此提出“心即理”命题,推动儒学朝心学方向转移。然而在当下的阳明学研究中,于阳明心学、阳明后学多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赞其为最完美的思想体系,颂其为最有价值的学说,而对其缺陷、不足只字不提。概言之,阳明对以学术权威为是非标准的否定,对以经书为金科玉律的质疑,对为天下人已习惯接受的学术观点的挑战,无不体现了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观点都不盲从、不迷信、不人云亦云而予以理性思考、全面检讨的怀疑精神,此即阳明的学术怀疑精神。而在当今的阳明学研究中,不仅怀疑精神稀缺,而且看不到具有批评意义的逆向研究,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鼓掌、清一色的赞美,诸如“20世纪是阳明心学的世纪”“阳明心学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阳明学可以拯救人类”等论调。因此,当下的阳明学研究应该自觉地引入阳明的怀疑精神,展开逆向研究,使阳明学研究回归理性。
三、包容精神
阳明虽然批评朱子,虽然批判佛老,虽然与湛甘泉有学问上的缝隙,但阳明从未全盘否定朱子,也从未将佛老说得一无是处,对甘泉更是肯定和欣赏。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因而“心”含宇宙万物,容纳万有,故包容精神是阳明心学本有之义。我们都知道王阳明对朱子学不感冒,批评朱子“格物穷理”,批评朱子学沉迷经书、嗜于词章、考索名物,但并没有全面否定朱子学。阳明说:“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10〕即谓他批评朱子绝不是出于私意,而是“道”之使然。因此,他异于朱子者、同于朱子者概不隐瞒:“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11〕可见,阳明对朱子的态度并非极端的否定,而是理性的包容。阳明虽然批评佛教为大偏之学,指责佛教有体无用、有内无外,有上达无下学,有明明德无亲民,所谓“彼释氏之外人伦,遗物理,而堕于空寂者,固不得谓之明其心矣”。〔12〕但阳明并没有完全否定佛教的作用与价值,反而肯定佛教也是“道”。阳明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其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13〕对阳明而言,佛教与儒学、老庄一样,都可以为己所用,这是“大道”;佛老虽然是“小道”,但也在“大道”之中,因而也是有益于我的“道”。阳明说:“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器数、技能之学,非不能超脱世情,直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得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着,移之以治天下国家,便不能通了。故君子不用。”〔14〕这样,阳明以“大道”胸怀容纳了佛教这样的“小道”。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旨趣上存在分歧,特别是不能认同“随处体认天理”说。阳明说:“致知格物,甘泉之说与仆尚微有异,然不害其为大同。”〔15〕虽有异,但不妨碍大同,足见阳明对学术异见者的大度。不仅如此,他还热情地肯定、欣赏甘泉。阳明说:“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多言又乌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与甘泉之不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16〕由这段文字看出,阳明不仅感恩甘泉在学问上对自己的帮助,不仅驳斥视甘泉之学为禅的论调,肯定甘泉学问的圣人之学性质,而且以甘泉为圣学同道而自豪,甚至愿为弘扬圣人之道一同殉身。无疑,阳明对朱子、佛教、湛甘泉都是其所是、美其所美,对合“道”的部分一律予以肯定和欣赏,所表现的是包容缺点、瑕疵、过错以及不同意见的包容精神,此即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包容精神在当今的阳明学研究中也成了稀缺之物。在阳明学研究组织上,各自为政、自立山头者有之;在阳明学研究心态上,嫉妒他人、排斥异己者有之;在阳明学研究成就上,唯我独尊、轻视新人者有之。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能容忍对阳明心学缺陷的揭露,不能容忍对阳明后学缺点的批评,同样是学术上狭隘的行为。如此种种,都是与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背道而驰的,都是无助于阳明学研究开展和进步的。因此,以传承、弘扬阳明心学为使命的当代阳明学研究,怎么能置阳明的学术包容精神于不顾呢?宜当以之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也矣!
四、关怀精神
虽然阳明学术旨趣是反身向内、求诸于心,但“心外无物”之“心”是宇宙的心,是民众的心,是关怀的心。因而在阳明这里,“道”是天下之公理,“学”是天下之公学,此“道”此“学”必须为天下人做主,为天下人说公道话。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17〕所谓“公言”,就是为天下人言,就是为天下人主持公道,就是为天下人的生命、生计、生活发声陈情。那么,怎样发声陈情呢?当然不是空喊漂亮口号,而是对天下生命的真切关怀。阳明说:“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18〕就是说,“明明德”不是美德的自我表演,也不是文字上的宣讲、阐发,而是将此“德”体现于实际事务中,体现于对天下人的关怀上。这种关怀就是揭露现实社会的丑陋。阳明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胜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19〕天下何以不能得到满意的治理?因为人们务虚名、轻实事,人人争相己见,个个沽名钓誉。阳明何以要揭露社会的阴暗呢?因为他忧心社会的沉沦,因为他期待社会的昌盛。这种关怀就是关心人民的生计。阳明说:“臣惟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20〕既然散财于民才能聚民心,所以必须将财富分发给百姓,这样国家才能巩固,社会才能安宁。因而阳明将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中、以百姓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当了解到吉安等县“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发生,尽行枯死,夏税秋粮,无从办纳,人民愁叹,将及流离”。阳明毫无半点迟疑,旋即为吉安等县向朝廷申请免税和赈济:“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诉告喧腾,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久而未获,反有追征之令。……今朝廷亦尝有宽恤之令矣,亦尝有赈济之典矣!”〔21〕百姓遭受灾害,要求政府免去税收,要求国家开仓济民,这就是阳明的关怀精神。这种关怀就是让天下人逃离苦痛。阳明说:“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22〕阳明指出,“致良知”就是以生民之困苦荼毒为己之困苦荼毒,就是视人之饥溺如己之饥溺,就是帮助穷困老弱病残者脱离苦海。可见,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百姓生命的体贴,对民众苦痛的关切,所体现的正是承认人是价值生命的存在、文化生命的存在、主体生命的存在、权利生命的存在和社会发展核心的存在之关怀精神,此即阳明的学术关怀精神。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今阳明学研究中,虽然论文满天飞舞、著作纷至沓来、课题花样百出,但另一面却是阳明学研究者的无病呻吟、逃避现实、袖手旁观,甚至粉饰太平,不能将阳明学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不能正视现实问题,更不能揭露社会的阴暗,这与阳明的关怀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必须重塑阳明的关怀精神,将阳明学研究与当今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揭露社会阴暗、关心民生疾苦、鞭挞社会不公,探讨阳明学对当今社会问题解决的贡献,使阳明的学术关怀精神充分体现于当今阳明学研究中。
五、创新精神
阳明虽然重视圣贤之学的传承,虽然重视对前人思想的保护,但更重视学术的创新。阳明并不满足于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而停滞不前,并不愿意将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当作炫耀的资本,更不认为先贤留下的思想资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应对社会课题,因而他必须创新。阳明心学之所以成为独特的学说,迥异于朱子,超越于孟子,就在于它的创新精神。诚如阳明所说:“但论议须谦虚简明为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而有损。”〔23〕在阳明看来,若为学只是重复叙述,毫无创新,则非但无益,反而受损。可以说,阳明心学从头到尾、从内到外都洋溢着创新精神。“良知”说虽然是孟子的发明,但只有王阳明将其推向了新境界。阳明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24〕由此看来,“良知”的觉悟完全得益于阳明的生命体验。那么,阳明之于“良知”说究竟贡献了什么呢?阳明将“良知”的圆满性、明澈性、直觉性、准则性、能动性等进行了全面、深入阐释和发明,使“良知”作为人本有之善能明晰起来;阳明还将孟子“求放心”发展为“致良知”,强调将“善体”诉诸于生活,依良知纠正恶行,依良知推动善行,而且时时如此、处处如此。可见,阳明的确为孟子的“良知”说注入了新内容,使之成为儒家“良知”说的新标杆。“诚意”是《大学》“八条目”成员之一,本无特殊地位,但经由阳明别开生面的解释,“诚意”成为“八条目”的核心。何以见得?“格物致知”不过是“诚意”的功夫,阳明说:“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25〕“修身”也不过是“诚意”的功夫,而“诚意”中使“心”廓然大公,便是“正心”。阳明说:“修身工夫只是诚意。就诚意中体当自己心体,常令廓然大公,便是正心。”〔26〕这样,格物、致知、修身、正心被确定为以“诚意”为核心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功夫整体”,而且规定了这个整体的精神方向,即“诚纯意念,反身向内”,所以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27〕阳明的学术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学说理论上,也表现在对概念、命题的独特诠释上。比如,有学者请教阳明孔子所说“远虑”何意?阳明的解答是:“‘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28〕通常情况下,“远虑”被解释为长远谋划、周详考虑,但阳明认为,如果“远虑”中没有“天理”,终究还是茫茫荡荡去“远虑”,这种“远虑”将会被毁誉、得丧、人欲所俘虏,因而孔子所言“远虑”必须“存天理”,这就是道德对知识的渗透与护航。这种解释不仅表现出义理的厚度,而且体现了“心学”特质。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释“格物”之“格”为“至”的时候,阳明却破天荒地释“格”为“正”,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29〕这种大胆的解释不能不说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孔子的“上智与下愚不移”命题,人们习惯于“上等人(聪明人)与下等人(愚笨人)关系固定不变”的解释,并顺合了孔子的等级观念。但阳明又贡献了神奇一语:“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30〕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颠覆性解释,不仅显示了王阳明朴素的平民意识,而且提升了人们成为圣贤的自信。概言之,阳明对前贤学说的发展与丰富,对经书中义理的新诠与调整,对哲学概念或命题的发微与增新,对先贤语录的大胆阐发和修改等,充分体现了突破常规思维、超越常人思路、想前人之未想、发前人之未发的创新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大多沉迷于文献的点校与整理,醉心于重复性叙述,热衷于鸡汤式解读,述而不作,抱残守缺,孤芳自赏,鲜有令人振奋的创新性成果。因此,当今的阳明学研究应该毫无迟疑地引入阳明的学术创新精神,不仅要传承阳明学、传播阳明学,更应该创新阳明学、发展阳明学,从而真正做到“创新性发展”。
〔15〕《答方叔贤》,《王阳明全集》(上),第206页。
2.1 教师要透彻理解统计思想 统计学的本质是方法背后的统计思想[3]。统计思想是为解决某一问题而提出来的思维方式,而此方法经理论化、模型化以后可以解决一大类问题。可以说,统计思想实际上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概念化(Generalize)。统计思想是统计方法的灵魂,如果抽掉统计思想这一内核,统计学只剩下公式的推演和证明,那么统计学就与数学没有多大区别。
〔6〕〔10〕〔17〕《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第76、88、88页。
〔13〕《补录·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下),第1301页。
〔1〕〔5〕《答徐成之二》,《王阳明全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下同,不再注明),第892、889页。
〔2〕《与顾惟贤》,《王阳明全集》(中),第1100-1101页。
〔8〕〔9〕〔28〕《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第135、136、124-125页。
〔3〕〔19〕〔29〕〔30〕《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第40、9、28、36页。
〔20〕《计处地方疏》,《王阳明全集》(上),第476页。
注释:
水利工程一般建在高山、峡谷和荒滩、湿地等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为与外界联系,还需要修筑公路、建设相应的办公和生活区等,工程现场的准备时间较长。
〔7〕《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上),第238页。
某建筑工程是某市的地标建筑之一,建筑面积约为5.8万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7万m2,地下建筑面积2.1万m2。建筑主楼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裙房和地下室采用框架结构。在本建筑施工项目建设之前,为了确保整个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性,本工程成立施工项目管理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整个项目的安全风险进行控制管理,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
〔11〕《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上),第233页。
〔12〕《与夏敦夫》,《王阳明全集》(上),第200页。
目前rGERD的治疗尚无肯定的长期疗效,而导致rGERD治疗失败的原因是多因素的,如患者依从性差、PPI快代谢、抑制胃酸不足、不正确的用药时间、解剖异常、精神心理异常[10,11],为此各国研究者努力探索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少的治疗方法,在药物、内镜和外科手术等方面制定了多种治疗策略,目前各种疗法尚缺乏长期有效有证据。
在无反相机刚刚诞生的时代,由于图像处理器的疲软和反差对焦方式的天生缺陷,其羸弱的对焦性能始终在单反相机面前抬不起头。不过随着技术进步,传感器集成相位对焦点以及更先进处理器的出现,无反相机的对焦性能直线提升,富士X-H1这种级别的机型已经可以与D500直面抗衡。富士X-H1拥有99个传感器相位对焦点,是目前富士最先进的系统。
〔14〕《续传习录》,《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30页。
总之,如果说客观精神、怀疑精神、包容精神、关怀精神、创新精神是阳明学术思想的核心品质,是阳明心学之所以为阳明心学的精神根据,那么,当代阳明学研究不仅有义务传承这种精神,而且有义务弘扬这种精神,将此精神贯注于阳明学研究中,以使阳明学研究得以积极展开,并成为真正的“天下之公言”。进而言之,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又何尝不需要阳明学术精神呢?
〔16〕《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上),第257-258页。
微波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棓丙酯氯化钠注射液中8种金属元素的含量 …………………… 钟振华等(12):1612
〔18〕《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上),第251-252页。
〔4〕《答徐成之一》,《王阳明全集》(中),第888页。
〔21〕《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弭灾变疏》,《王阳明全集》(上),第474-475页。
〔22〕《答聂文蔚》,《王阳明全集》(上),第89-90页。
〔23〕《与黄宗贤书》,《王阳明全集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7页。
〔24〕《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下),第1290页。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一个拗口的洋名字虽然“正规”,却不如一个俗称更容易流传。在香港,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认知障碍症”,台湾地区则将其命名为“老人失智症”。根据从各大网络平台上汇总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10日,央视征名活动的总投票数接近90万,其中得票数最高的是“脑退化症”。
〔25〕《答王天宇二》,《王阳明全集》(上),第138页。
生长育肥猪饲料:对于生长育肥猪的饲料而言,宜采用调质器(85~90 ℃,20~30 s)+保持器(45~60 s)+制粒的一次制粒工艺。
〔26〕《〈大学〉古本傍释》,《王阳明全集》(下),第1318页。
〔27〕《〈大学〉古本原序》,《王阳明全集》(下),第1320页。
作者简介: 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性论义理结构与形态研究”(15AZD031)阶段性成果、贵州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王阳明心态思想研究”(18GZGX04)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4.010
〔责任编辑:马立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