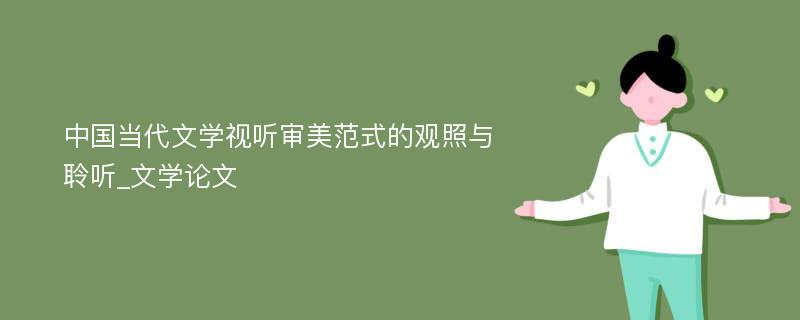
凝视与倾听——试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视听审美范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试论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视听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3)01-0082-06
在H·M·麦克卢汉看来,用眼睛代替耳朵去处理和把握世界的开始,是人类告别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此找到了完善自身感官的可靠形式,事实情况却是恰恰相反。人类之于视觉的运用,更多的只是出于文明技术层次上的实践,视觉在此承担的也仅仅是服务于这种技术力量的被动角色。在崇尚文明的狂热激情之中,人类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日益沦落为科学技术的奴隶,让科学技术变成统治一切的无上权力。故此,眼睛对于耳朵的取代,非但没能充分调动其本身的积极因素,反而还严重遏抑了后者的本能及其生长。故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开创对于人类的感官本能,不是丰富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
况且,就人类的感官能力而言,视觉也明显不如听觉更能激发主体的感受活力。H·M·麦克卢汉曾言:“偏重文字的受众有一个基本的特点,他们面对书籍或电影时,扮演一个非常被动的消费者角色。”[1](P203)他认为,“如与口头和听觉文化的高度敏锐的感知力比较,大多数文明人的感知力是粗糙而麻木的。其原因是,眼睛不具备耳朵那种灵敏度”。[1](P185)他相信之所以“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雅,更富有敏锐的感知力”,其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是“偏重耳朵的人”[1](P185)。D·M·列文针对视觉与听觉的关系问题,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引述梅斯特·艾克哈特的话说:“听可给人带来更多的东西,而看则使人失去更多的东西,哪怕就是处于看这一具体行为之中时。因此在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从听的能力而非看的能力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赐福。因为听这个永恒世界的能力是内在于我的,看的能力却是外在于我的;这是由于在听时我是恬静的,而在看时我则是活跃的。”[2](P32)他还进一步阐明道:“对于我们来说,闭上眼睛要比捂住耳朵容易得多。对于我们,面对所看到的依然保持距离和不动,要比面对所听到的时容易得多;我们所看到的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而我们所听到的却渗入了我们的全身。声音不会在由自我中心的身体设置的界限前停步;但视觉的自我主体通常却能够更容易地保持住它的界限(内与外、此与彼、我与他)。听是亲近性的、参与性的、交流性的;我们总是被我们倾听到的所感染。相比之下,视觉却是间距性的,疏离性的,在空间上同呈现于眼前的东西相隔离。”[2](P32)由此可见,听要比看更接近于文学艺术的期待。也就是说,只有身处在听的状态中,我们才能更容易投入同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交流过程当中。因为相对看来说,听所在乎的正是与对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建设,它比看更能使人同对象结成亲密的联盟。
“当我倾听他人时我也能听到自己:即在他人身上或者他人的立场上,我能够听到我自己。反之亦一样真实。当我倾听自己时我也能听到他人;在我自己身上,我能够听到他人或者他人的立场。在我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着回声与共鸣:当它们变得能够听见时,那些携带着足够能量的极其深沉的反响将会解构由我们的自我逻辑主体性所铸成的界限和盔甲:这些反响将混合、搀杂,甚至颠倒我们的角色身份。”[2](P182)——的确,正是听觉令主体及其对象间的冰冷距离被融化了,从而为两者创造出双向交流的契机。无论如何,听是没法像距离性的看那样,与对象保持着旁观式的关系。“我们的倾听不仅仅就是一种认知能力;它同时也总是一种情感能力和激发能力。”[2](P43)它的行为同心灵密切相连。故而,它不可能像看那样让自身冷静地面对对方。在很大程度上,一旦倾听开始,便意味着倾听的主体已经投身到了对象的世界。此刻,它压根无力制止自己关怀对方的冲动。
倾听的激情状态,令倾听这一行为本身也拥有了某些艺术性况味。为此我们有理由说,倾听较观看更能逼进文学艺术的深处,于其中搭设起尽可能广阔的共鸣空间。再则,后者又因囿于具体形象的在场,所以始终无法如前者一样,在感受对象时可以随意超越对象的制约,尽量用自己的想象去丰富甚或创造它的存在。老子云:“大象无形。”因此,对于“大象”来说,视觉是派不上用场的,惟有凭借听觉的捕捉。“大象”乃不受时空所限的真理性在场,它不但是无形的,亦是沉默的。因为无形,则拒绝了视觉的抵达;因为沉默,却为听觉提供了可能。须知,沉默并不是真正的无声,它是心灵回声的一种特殊表达,正需要主体的倾心聆听。所以,沉默的时刻根本就不是声音缺席的时刻,而恰恰是等待倾听的时刻。愈是沉默,便标示愈是要求倾听者的全身心付出。在此情状下,倾听者从来都只能坚守自己宁静而耐心的内在世界;远远不像观看者那样,常常为满足于视觉的迫切欲望显得焦躁不安。诚若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在所有的感官中,视觉是以最明显的方式听命于急切性的。”[3](P67)鉴于看的这种急切性,它往往不如听能走得更加遥远。并且,由于看的明确欲望目的,它也难以收获到除此之外更多的东西。在这方面,“凝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最为深刻的视觉形式:“它是一种意在重新获得并保存之的动作……注视的动作并非当场终结:它包含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冲动和非再拿回来不可的劲头儿,似乎它受到一种希望的激励,这种希望就是扩大它的发现或者重新获得正从它手中溜掉的东西。凝视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它不满足于已经给予它的东西,它等待着运动中的形式的静止,朝着休息中的面容的最轻微的颤动冲上去,它要求贴近面具后面的面孔,或者试图重新经受深度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蛊惑,以便重新捕捉水面上光影的变幻。”[3](P66)然而,这种攫取般的执着冲动不可能使主体意识到,在痴迷于发现表象背后的秘密时,它早已被自己的贪婪出卖了。凝视者在越发偏离表象的同时,也越发偏离了自我,即其最基本的外在感官能力被逐渐冷落直至荒废了。
虽然,视觉的极端化是招致主体异化的罪魁祸首。但是,自古希腊伊始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着重是以视觉欲望的满足为归属的。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感觉之于知识的始源作用时,说过:“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为多。”[4](P1)而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者,特别是启蒙运动所打开的理性天窗,更是为视觉确定了寻找假想黑夜中理性光芒的神圣历史使命。视觉于形而上学包括文学艺术中的地位,从此便越发被合法化了。由视觉而非听觉出发,就此成为一切意识形态的起点和指向。正像D·M·列文所指出的那样:“正如我们所知,在感官之国中,视觉是最高统治者,这个全景凝视的极权主义帝国——我们感官能力最大程度物化与整体化的结果,继续扩张着其形而上学的霸权:它的本体论、它的知识和真理范式、整体可见性以及绝对清晰性的清一色领域。这种统治特权几乎完全遮蔽了视觉同听觉之间历史斗争的所有迹象,产生了一系列恭奉于视觉范式的哲学文本。”[2](P30)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的历史实质上一直就是听觉遭罹压制的历史。为了结束听觉所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我们不得不进行对于视觉形而上学的彻底清算,重新唤醒听觉的记忆。而这一艰巨任务,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显现得尤其紧迫。
我们必须认识到,“眼睛是智性的器官,而耳朵则是较为原始的”[5](P91)。正是由于受视觉形而上学的牵制,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判断才一直倾向于朝视觉范式的理性认知靠扰,其固有的独特审美品性始终未能成为被格外鼓励的追求导向。唯美主义抑或形式主义的斥责之下,遮掩的其实正是对人类主体感官的无视。这也就促使文学艺术的生产,因而日益走向不重感受只重剖析的畸形模式。在对理性缺少历史反思的情况下,人们偏执地相信:视觉高于听觉,所以前者应比后者更能令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获至尽可能完善的理解。殊不知,在这一问题上,听觉总是能让视觉感到羞愧,而视觉却又总是叫听觉失望。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是,在我们听完一部电影之后再去看它,结果往往不如听时那么令我们满意。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会生出翅膀,它带领着我们尽情向一切未知的领域穷尽;但在观看的时候,这双翅膀却突然折断了,使得我们只能滞留于眼前狭小的时空中间。我想,也恰是源于这一情境的顾虑,德里达在试图理解保罗·德曼之时,这样强调说:“而最起码的尊重或忠实应是:首先倾听并力图听懂德曼……”[6](P237)在德里达这里,我们不难见出其给予听觉而不是视觉的信任。而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则是与好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而自由空闲的好奇操劳于看,却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事的存在,而仅止为了看。它贪新鹜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这种看之操心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世界。”[7](P200)(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显然,在海德格尔眼里,看并不能够真正领会对象的存在,与其说它是在走向对象,毋如说它是在通过对象走向它自己。作为呈示而在的看的对象,实际上没有在被看的过程当中将自己呈示出去,倒是看之本身在这一过程当中得到了充分呈示。所以约翰·杜威这样写道:“耳朵同充满活力的和乐于交流的思想情感之间的联系,比起眼睛要格外密切而且更加多样。视觉只是旁观者,听觉才是参与者。”[8](P218-219)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视觉形而上学的统治局面,则在当代暴露得最为显明。古代文化的听觉优先地位,于此时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人们理所当然地从视觉而不是听觉的角度规范了文学的存在意义,把视觉消费当成了文学生产的仅有目的。建国初期现实主义写作策略的大力倡导,在相当程度上,迎合的正是这样一种生产目的。为了满足“凝视”的需要,文学生产极力依借文字将现实生活转化成某种可视的逼真图景。至此,“看”便成了鉴别和判断文学作品的绝对权威。通过“看”,人们就可以知晓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是否精确再现了现实生活的原貌,从而得出关于它们的结论性评价。这些仅供“看”的文学作品,只需满足于视觉的“揭秘”欲望,就可以轻易博得人们的普遍好感。所以,真实由此成为了决定文学价值的核心指标。于50年代中后期引致文坛广泛关注的“真实性”问题讨论,就颇能够说明人们在文学诉求层面所表现出的视觉热情。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没能正确地理解所谓真实这一概念,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向更高的视觉要求发起挑战。
对视觉欲望的不断趋从,为建国初期文学直接抄袭现实生活提供了合法借口。没有谁去质疑,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去书写现实生活以外那人们用眼睛看不到的景象?这一问题的缺席,导致了此时文学在想象方面整体呈现出的贫乏症状。[9]更为严重的是,当人们把目光牢牢地粘贴于外在的现实场面时,却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忽略了。由于听觉的放逐,那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就此消逝了。文学作品之中充斥的满目浮华,掩盖着心灵沉睡的真相。而只有听觉的到场,方可改变这一情景。因为,沉睡的心灵惟有靠倾听才能被唤醒。可是,这个时刻迟迟没有到来,心灵依然被遗忘在视觉的盲区。加之这一时期理想主义激情之于文学写作的感染,人们迫不及待地把本属于未来的可能场景,强硬地拉到了现实中来,从而经由视觉上的幻觉,消弭了时间层次上的差异。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呈现在自己眼前的这一片真实视景,其实都已变形。当听觉的时间性被取消之时,视觉因之也就无法正确识别其空间性的真伪了。这一情形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于五六十年代,包括“文革”期间,会有那么众多的作家,竟然对周遭现实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浑然无觉。我以为这不单纯是什么勇气抑或人格的问题,听觉丧失引致的精神失聪,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心灵麻痹,可能更能够恰切地从艺术角度解释当时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不幸。
即使到了80年代,人们之于文学领域里的视觉中心主义倾向,依然匮乏最起码的反思。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关“朦胧诗”展开的激烈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场争论的引发实在是中国当代文学里程上的又一次大倒退。因为它为维护视觉中心主义的艺术原则,竟把矛头随意指向了现代听觉审美范式于多年之后的艰难复出,以作为看之障碍的“朦胧”为充足理由,对40年代著名诗人杜运燮的新作表示了不满,并进而得出结论:“固然,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0]好在随之而起的针锋相对的批评,开始表明多少已经有人认识到了不应再单从视觉的理解效果,去评判诗歌的价值水准了。用“看懂”或者“看不懂”来说明诗作的品位,即使不意味着读解者的鉴赏惰性,至少也昭示了视觉诉求对于审美选择自由的武断干预。
倘若说“朦胧诗”显现出的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1],那么此种美学原则正是符合听觉范式的艺术审美品格。“朦胧诗”的崛起,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其特殊意义就在于,它使以往文学写作的外部凝视模式,突然转向了发自于内部的倾听。写作者们因此得以把自我过久滞留于外在世界当中的目光,拉回到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的心理现实。这时,他们发现,远不如外在世界明朗的心理现实,继续用眼睛观看根本就是无效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就此恢复倾听的耐心。事实上,也只有藉助于倾听,他们才能真正走入自己的心灵空间。基于此,“朦胧诗”致力传达的不再是一幅图景,却是一种声音,是一个蕴藏有无比丰富意义资源的能指世界的营建,而“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12](P106)。所以,它不需要人们的凝视和对照,要的只是人们的倾听与想象。其所谓“朦胧”,那只是针对视觉而言;对于听觉来讲,“朦胧”并不存在,只要人们不是怀着急切的视觉欲望企图去剥开这层“朦胧”的面纱,它就不会成为被斥责的重心。可是,“朦胧诗”这种反视觉范式的美学价值重建,并未得到时人的很好理解。即使是那些为之摇旗呐喊的人士,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朦胧诗”在此方面所拥有的革命性意义。因此,他们围绕着“朦胧诗”奋力进行的反击行动,显得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始终缺乏理论层面的说服力。这也就难免有人仍然理直气壮地强调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尽管有些人不同意——写看不懂的诗的人不同意——我还是坚持着:首先得让人能看懂。”[13](P684)事实最终证明:“朦胧诗”的艰难出场,并没能从此确立起听觉审美范式的价值地位。之所以随后会有大量为朦胧而朦胧的“仿朦胧诗”出现,恰是由于这些仿造者压根就没有领悟到朦胧诗所蕴涵的可贵听觉魅力。由此而生的一个诗界恶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把诗歌推回视觉审美范式的老路,将其拼凑成一行行仅供观看却毫无内容可言的文字图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
中国当代文学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小说里,则具体还表现于人物的设计上。即作家们总是习惯于用视觉的被剥夺来彰显人物命运的不幸程度。在他们眼里,视觉的丧失显然要比听觉的丧失更加痛苦和可怕。所以,在小说当中,我们最容易目睹到的是因失去视觉而饱受折磨的主人公。曾在80年代初引起普遍注意的小说《明姑娘》(航鹰),便是这样一篇借视觉丧失遭遇,突出人物于逆境中不甘沉沦这一时代性主题的作品。作者为了反衬主人公赵灿后来的精视转变,首先极力渲染了其在失明时的痛苦情状:
终日呆坐,只从广播电台播音员报时中,才能体会到朝朝暮暮。他听完了连绵的秋雨声,又听呼啸的寒风声,心中常常感到窒息,像有一块大石头压住胸口,喘不过气来。烦闷得厉害而发作时,他便如困兽要冲出牢笼似地东撞西撞,到后来竟发展成忽哭忽笑,捶胸撕发,非得姐姐给他吃下安眠药睡上两天方能平静。眼病未除,心病又添,他就暗暗下了慢性自杀的决心,开始糟踏自己的身体。每天晚上姐姐走后,他就蹬开被子或干脆睡到水泥地上,喝生水,不吃午饭,想让自己消瘦生病,早点死掉。为了慢慢地冷了姐姐的心,使他死后姐姐不过于悲伤,他对姐姐发脾气,挑三骂四,摔盆打碗。但是,无论他怎样恶语冲撞,姐姐总是温柔地扶他坐下,拧一把热毛巾为他擦汗,或是轻轻抚着他的头发。姐姐一上班去,他就嚎啕大哭,打自己的耳光,叫着:“姐姐——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可是,一听到姐姐拧开大门碰锁的声音,他立刻又摆出一幅凶神恶煞的模样。黑暗的魔鬼啊,能扭曲人的灵魂。
我无意指责作者将失明当作最痛苦的感官丧失形式来书写,我只是想指出,这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说,由于涉及到视觉的被剥夺因而有了重新发现听觉的可能,但是,它却根本没有理会这种可能。相反,它一直流露出的仍旧是对于重见光明的渴望:如“明姑娘对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大见光明总是抱着幻想,那幻想是热忱的,执著的。”可见,视觉的丧失,在这里只是为了反证视觉的宝贵,而非出于发现听觉价值的动机。故此,在作品里我们看到,主人公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声音转换成某种可见的画面:“他感到那声音分外澄澈,分外明亮,澄澈如中秋的月光,高远,透明,抚慰着他的心田;明亮如早晨的霞光,清爽,艳红,照耀着他的脸颊。”当明姑娘用听觉语言描述完她对绿色的感受时,赵灿赞叹说:“你说得太好了!你想象中的绿比人们看到的更美!”而明姑娘的反应却是“委屈地申辩:‘谁说我只能想象?那未免太虚无缥缈了……’”看得出,在明姑娘这里,听觉所带来的丰富想象,并不足以抵偿视觉障碍产生的实在遗憾。之于听觉,明姑娘明显还是缺乏认同感的。
无疑,《明姑娘》依然是视觉形而上学体制下的产物。由于作者对听觉这一荒芜区域的继续冷落,小说之于人物的处理因此只能原步停留在观念的层次上,而最终无法落实到人物的真实感觉上来。感觉的匮欠,也正是建国以来学作品中存有的常见弊病。这种弊病招致的一个致命结果就是,作品因为拒绝了倾听的可能,从而也拒绝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换言之,作品同读者的间距,并没有经过阅读获得解除。
与《明姑娘》截然相反的一个例证,是《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于几年之后的出场。从该作中,我们不难见出,莫言之所以能够写出写活人物的身体感觉,其原因就在于莫言开始注意到了听觉领地的存在。莫言有意将主人公黑孩设计成一个始终坚守沉默的孩子,无非是为了有力凸显听觉对于他的重要意义。黑孩拒绝说话,是因为那个世界没有给弱者以说话的权力,而黑孩就属于这样一个弱者。他没有倾听者,所以只好让自己作一个忠实的倾听者,栖息在声音的世界里。无法言说的处境,让黑孩学会了用耳朵同身外的世界对话。他那“长得十分夸张”的双耳,通过不停地抖动实现着自己和外界的交流。并且,倾听在黑孩这里,还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措施而在的,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黑孩逃避他人的伤害:“后娘让他去河里挑水,笤帚打在他屁股上,不痛,只有热乎乎的感觉。打屁股的声音好像在很远的地方有人用棍子抽一麻袋棉花。”由于这打屁股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疼痛也便因此随声音远离了自己的身体。依靠听觉,黑孩竟然淡化了暴力强加于己的痛苦。与此同时,倾听也为黑孩子提供了一个通往精神自由天地的出口:“刘副主任的话,黑孩一句也没听到。他的两根细胳膊拐在石栏杆上,双手夹住羊角锤。他听到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逃逸的雾气撞着黄麻叶子和深红或是淡绿的茎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蚂蚱剪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在此可以看到,倾听之于黑孩是完全自由的,他能够通过拒绝倾听(刘副主任的话)来摆脱现实的约束,将自己融入大自然的和谐之境;而且,也恰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把黑孩引领进一个安全、美妙的所在。
听觉不仅为黑孩提供了某种庇护,并且还丰富了他贫困的生活,但这首先是因为听觉令其感觉包括视觉获得了丰富:“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夜已经很深了,黑孩温柔地拉着风箱,风箱吹出的风犹如婴孩的鼾声。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尖细的趾爪踩在细沙上,声音细微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有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黑孩不仅仅听到了别人听不见的东西,还看见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那个自由有限的年代里,黑孩藉借听觉收获了要比他人多得多的自由。他的生存状况,向我们演示了一个弱者依附听觉渠道超越现世苦难的动人过程,并同时告诉我们,倾听远比倾诉更为重要。
《透明的红萝卜》借黑孩这样一个卑微者,演绎了听觉的高贵,进而成功瓦解了文学中的视觉形而上学传统。确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莫言是新时期小说中出色的写家之一,而且,整个新时期青年小说家对感觉的注重似乎还是从莫言等人开始的。莫言的叙述以对象唤起的感觉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或‘刻划’,以感觉的奇异取代了描划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相似与相异、变幻与重复组织情节——故事的本文形态。”[14](P93)不过,《透明的红萝卜》本身并未就此成为一个新的传统,因为它有幸遭遇的知音实在过于稀少。先锋文学突起之时,虽带有鲜明的听觉审美范式品格,但却丝毫发现不了其与《透明的红萝卜》有何内在联系。可以断言:先锋作家们在尝试听觉审美范式的写作时,同样没有认识到莫言在这一方面显露出的自觉。基于此,他们对于视觉审美范式的突破只能是有限的。很快,新写实、新体验等等旨在强调视觉审美范式的文学主张,便又把中国当代文学拉回了视觉中心主义的旧有传统。至今,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认识还是相当匮缺的。大量以“凝视”为指归的文学叙事,越来越倾向于繁冗、复杂,啰嗦之类的“细描”式书写,致使整个阅读过程被迫耗去过多的视觉精力。认识大于审美,理性强于情感,激动多于感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惯常现象。这意味的不只是文学朴素、单纯个性的丧失,更是作家心灵朴素、单纯品质的丧失。然而,又有多少人能洞察到这深隐于其中的危害呢?我以为我们委实该倾听一下这样的提醒了:“两千五百年来,西方知识界尝试观察这世界,未能明白世界不是给眼睛观看,而是给耳朵倾听的。它不能看得懂,却可以听得见。”[15](P1)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问题,我们务必要清楚这样一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或超越,必须仰仗于审美范式由视觉向听觉的转换方有可能被实现。当然,视听审美范式的转换,关系到的不仅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前途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命力问题。况且,单纯视觉审美范式的现实主义,也极易陷入对于现实话语的盲目透支,而只有借助于听觉审美范式才有可能不断对这种透支进行补充,甚至重新开辟出可能的现实资源。在这个充满喧嚣浮躁、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过度的视力消费令人们普遍患染上了“视觉高度紧张”[1](注:可参阅约翰·厄普代克的短诗《视觉高度紧张》,该作形象地摹描了现代人的视力极度疲劳症状,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第65页。)症,致使“倾听”已愈来愈深刻地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种境遇之下,“倾听”究竟该如何发生呢?
收稿日期:2002-09-21
标签:文学论文; 听力论文; 朦胧诗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范式论文; 艺术论文; 透明的红萝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