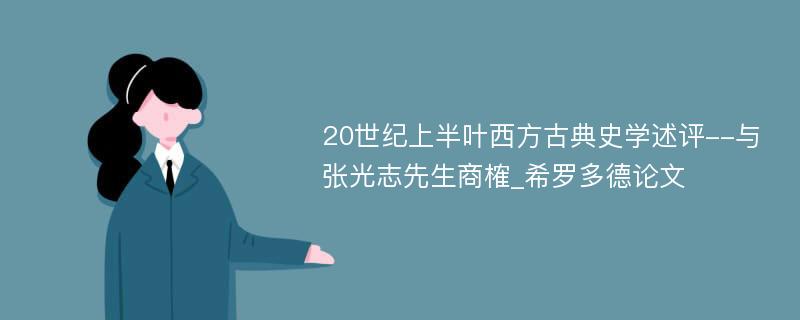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兼与张广智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古典论文,张广智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广智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 期上发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 还有待继续查考。 ”张先生又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下面我根据已查到的资料,说明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对张先生在论文中未涉及到的有关情况,做些补充,并纠正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这一看法。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孙宝瑄在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所记的日记中写道:“泰西著名史学家,一曰希罗多都(今译希罗多德),一曰都基底德(今译修昔底德),一曰伯路大孤(今译普鲁塔克)。”孙宝瑄还将西方古典史学与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对比,指出上列三位史学家“至今后学仰而师之如中国人之俯首于班(固)马(司马迁)也。”〔1〕孙氏交待他这些记述是根据《西学述略》一书(传教士艾约瑟用汉文编写的介绍西学的书籍,1886年在中国由总税务司出版,共七卷。曾被列为启蒙16种书籍之一)。
继孙宝瑄之后,严复介绍了西方古典史学发展的概况, 见于他1909年(宣统元年)2月25日写的《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严复简明扼要地评述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史学著作的主题,写作的特点及两位史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全文如下:
尝谓泰西史学始于晚周,希腊喜洛多图(希罗多德)、刁锡大智(修昔底德)二家所为,后代诵习崇称,无殊吾国迁固。顾二史之为绝作相同,而著述之旨大异。喜洛多图记述波斯之战,中及埃及国风,审瞻包罗,蔚为鸿制。但浮夸钩奇,或畔事实。论者以谓作者意存美术,偏工文词,其脍炙人口以此,而其有遗议亦以此。至于刁锡大智纪白罗波尼战事,文辞深美固矣,然而谨严斟酌,事变常疏其因由,举动必推其效果。论者谓其书非仅历史而已,乃群理哲学之深切著明者也。自兹以降,国有实录,种有宝书,若芝诺芬(色诺芬)、李费(李维),则循喜洛氏之轨而作者也,其用刁锡大智义法者,则希腊有波理表(波里比阿),罗马有挞实图(塔西陀)。凡此六家,皆西文中之江河不可废者矣。〔2〕
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在中国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不仅见于国人写的史学理论这类书籍中,还见于文学史专著和历史专业刊物上。
周作人在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之三),对西方古典史学做了较详细的评述。涉及的史学家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凯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托尼厄斯。〔3〕周作人在评述希罗多德的史学成就时, 介绍了他的史著九卷书的内容,称赞他为“历史之父”。周氏对希罗多德的史学观点也有评述,认为他“生于边塞,长而浪游,过欧亚非洲诸地,阅历既多,识见益广,爱其故乡,而对于异邦文化,亦能鉴识,不没其美。”周氏在评述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时,采取了与希罗多德对比的手法,周氏认为修昔底德晚生于希罗多德20年,而著作迥异,希罗多德史书多载传说、类于说部。修昔底德史作则体例谨严,纯为统系之历史。希罗多德作史,于胜负之数,恒归之天意,修昔底德则俱以人事。周氏称赞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史》“次序井然,语必证实,凡神异之事,传闻之词,皆置之不顾,意在资考镜,而非以广异闻”。关于色诺芬,周氏在列举其多种著作之后,评论他“本非文人,唯以馀力著作,又率模仿当时作者,不自成家,然文章简明优雅,后世多师法之。”关于凯撒,周氏列举了他的史著《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并说明了他写作《高卢战记》的动机。周氏还转述了西塞罗对凯撒史著文笔的评价,“不假修饰,自然优雅,如倮露之石象。”关于萨鲁斯特,周氏给以高度评价:“废编年体例,作史五卷,修饰文词,益近雅正,又致意于观察,申明因果,不专以记录为事,较之以前史家更有进矣。”关于塔西陀,周氏在列举了他的四部历史著作之后,着重评述了他的史学思想,认为他作史“意在标揭善恶,为世惩劝。唯恶每多于善,故常不胜感慨,而于内乱尤所痛心。”为了说明这些思想,周氏还列举了两项例证。关于苏托尼厄斯,周氏则采取了与塔西陀对比的手法加以评述,认为苏托尼厄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记凯撒至多米沁诸帝行状甚详。可与塔西陀的史著互证。“塔西陀作史最重义法,慎于取材,尝谓琐屑细故,不能入史,止足登之日报。而苏托尼厄斯则掇拾浩博,饮食谈笑之微,亦并详录,别有可取。又记诸人容貌极详尽,后世据以考证古罗马诸帝造象,甚得其益。”
1926年出版的由中国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学与地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了近九千字的专文《希腊四大史学家小传》。专文系陈训慈参考英文版《国际百科全书》和其他书籍写成的。《小传》的引言部分系统评述了古希腊史学发达的概况,指出:“希腊史学滥觞于荷马之史诗。纪年作者,多无足称,公元前五世纪初,希罗多德氏著《史记》九卷,荡涤旧失,自树新帜,希腊史学自兹始昌。修昔底德继之,著《伯罗奔尼撒战史》,记述之外,更重理解,色诺芬与修氏同时,既显名于武绩,又循其经验以纪时事。其后二百年,波里比阿著《史记》40册,推究因果,以昭示希腊文化所以转移于罗马之故,论其成就,实为希腊史学之后劲。”陈氏还特别综合评述了古希腊这四位史学家可资借鉴的成就,认为他们“从政论世,发之著述,经世致用之精神,昭昭可稽。”这也是陈氏评述古希腊史学的用意所在——借鉴古希腊关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在《小传》正文部分,陈氏分别较详细地评述了四大史学家的生平身世,史学著作的内容及其成就。陈氏高度评价希罗多德的探索精神,指出希罗多德“独其博咨穷求之精神,实为后世搜求史源之工夫导其始也。”陈氏对希罗多德著史的文采十分敬佩,认为他的《希波战史》“全书生动,能令读者如身与其境”,为了表现其文采,陈氏特别引述了希罗多德关于萨拉米海战后泽尔士退兵和泽尔士临观军容的两段记载。在评述希罗多德史学的历史地位时,陈氏进行了中外史学综合对比,认为只有2300年前中国的《尚书》《春秋左传》与希罗多德的《希波战史》在世界上可称之为“史学著作”。陈氏也高度评价了修昔底德的求真精神,认为他“叙次之中,能洞察事理,务求其真。又以天性和平,持论中正公私,是以论述之中,亦无过于偏袒雅典之弊”,“辨析史料,力求审慎,后之论史者称修昔底德为第一批评的史家盖以此也”。陈氏对修昔底德的文采也很欣赏,说他“文采生动有致”,穿插演说辞的写法,很能突出人物的特性。关于色诺芬,陈氏认为他的史学著作“未为精善(文体平易、字句亦多未审),然其为时代留纪实,固大有功于史学也”。关于波里比河,陈氏指出他的史著“体大思精,向使留遗勿失,信足为希腊末叶罗马初期存精详之事迹”。又认为他“叙述一事,常能溯述其事之起因,推明其对于未来之关系”,因此“被人称为运用实验方法作史的第一人”。
在这篇《小传》中,陈氏除了这四位史学家之外,还简要介绍了史学家提奥庞普士、阿里安、戴奥尼素、戴奥多拉斯等人的生平及其史学著作。陈氏在《小传》的末尾,对希腊史学家的成就做了综合评述,认为他们都具有高水平的“史识”,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资料,在这些方面可与我国的《尚书》、《史记》、《汉书》互相媲美。在《小传》临结束时,陈训慈倡议,为了提高学风,推进外国史的研究,务需研读与翻译外国史学名著。大概也是出于这些考虑,陈氏在评述西方古典史学家时,向读者详尽介绍了他们著作的各种外文版本及研究论著。
《史学与地学》第一期上,还刊载有裴复恒译的《伯罗奔尼撒战史》的第一卷第一章,系译自1876年出版的克劳来(Crawley)英译本。 在译者前言中,裴復恒特别提示, 要清楚地了解修昔底德的史学方法、史学思想和他的著作的价值,最好是先读他的原著,然后再看各家的评论。裴復恒的这个意见与上述陈训慈的倡议,同出一辙,旨在推进对西方古典史学的科学研究。
在20世纪上半期,有的中国学者也发表了研究西方古典史学家的专文。阎宗临在1946年9月出版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丛刊》创刊号上, 发表有《李维史学研究》。阎宗临1929~1936年在瑞士伏利堡大学文学院留学,专攻世界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获博士学位。写作此文时,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世界古代史。阎宗临根据多种外文资料与李维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写了这篇对西方古典史学家个案研究的论文。论文共分六部分:时代特征;李维的史学思想;李维著述的目的;李维自成一家之言;李维写作史著的特点;李维的史学成就。阎氏把李维的史学著述置于罗马帝国初期这一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指出:“我们不能以现代史学观念,批评李维的著述,须要了解他的时代与环境,始能明白他的价值。罗马精神寄托在政治上,李维利用传述,表彰过去的史事,将历史变成一种教育的工具,深合时代的要求”,“而罗马史也从此有了定形”。阎氏在论文中不止一次地与其他学者论辩,他说:“现在研究李维者,只看他的史著是一种史料,那完全错误的,李维有他的历史观念,并非没有尽史家的职责”。对此,阎氏做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李维的历史观念,便在适用。他的罗马史缺点很多,没有严密的方法,常时夹着情感的冲动,可是他能握住史实的重心,用心理分析。使过去的史事,再现出来。他在叙言中说,倘使历史知识是有用的,便在静观过去壮丽的遗址,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国家,使众人有所法。”阎氏还把李维和前辈史学家做了对比,指出他超过了前辈之处:“老加图著《述源》一书,教其明白罗马的伟大,萨鲁斯特的著述,在反抗贵族,赞扬平民;凯撒的《高卢战记》,那是一种自我的赞扬,而李维在使罗马整个复活,使每个罗马人得到一种政治教育,这与奥古斯都的政治理想非常契合的”。
综上所述,西方古典史学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引起了最初的反响,而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引发了进一步较大的回响。这时既有西方古典史学发达的概述、史家生平介绍、著述内容分析,又有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论述,其范围涉及西方古典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方面(即求真精神、人本观念、宽宏视野、注重借鉴、讲究文采)。这些评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力求把西方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与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精华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学者的这些努力,对中国新史学的兴起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张广智先生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介绍是简要的,不全面的”,“没有具体的研究”,显然这种估计有些偏低。
行文至此,笔者联想到中国史学界有广泛深入研究近代各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历史回响的必要。中国自近代以来,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进步学者,在不同程度上,不但熟悉本国的历史传统,而且还比较了解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很注意学习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为本国争取进步、独立或改革的借鉴,其中包括对外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引进。这些方面是有待深入探索的一系列科研课题,而起步的工作则是按照专题进行资料的搜集。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对近代中国关于世界史的了解与研究,估计偏低,认为是个“空白”,“零碎、片断”,“微不足道”。我认为结论要产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论从史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俞旦初研究员生前曾在《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 期上发表有《关于加强“世界历史与近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为了完成这项系统工程,需要投入人力,广泛展开协作,以便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责任编辑注:张广智《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一文见本专题1994年第10期79页。
注释:
〔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诗文(下)1986 年中华书局版,第269页。
〔3〕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1989年岳簏书社版第32—34、82、93~94、10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