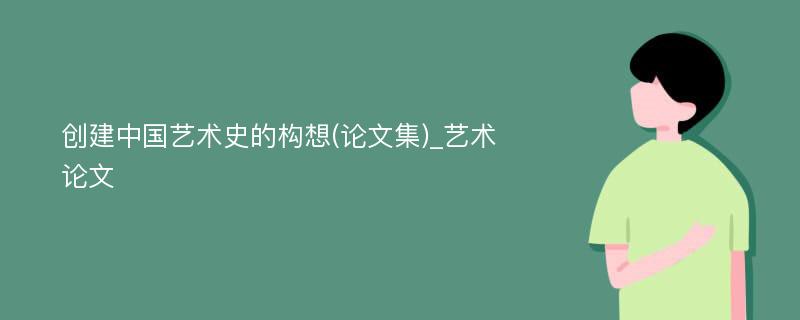
关于建立中国艺术史学的构想(代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序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构想的缘起
我平时喜好美好,设想用美学观点来审视一下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轨迹。于是想寻找一本中国艺术通史类的著作来参阅,即使是简单的小册子也可,只要将中国艺术史的几大门类如绘画、书法、雕塑、文学、戏剧、音乐等综合在一起论述即可。
带着这个愿望,我来到了上海最大的一家图书馆,在目录查寻处整整泡了一天,但结果是个空白。我在感到失望的同时,又带有一种惆怅:我们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瑰丽的艺术,但与之不相称的是至今连一种艺术通史也没有。后来,我到图书馆的内部书库寻找,总算找到了一本台北南天书局发行的《中国艺术史》,系英国人苏立文著,曾堉、王宝连编辑。我内心的感觉是复杂的(怎么我们的艺术史却要外国人来写?),但毕竟总算找到了一本,还是颇为喜悦的,但当我翻开这本装帧精美的《中国艺术史》时,才明白这实际上是一本中国美术史,所述的内容,仅是绘画、雕塑、工艺等,而且材料并不丰富,主要是依靠国外一些博物馆的藏品。我不想贬低这本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本书连一本完整的中国美术史也谈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毅然决定自己动笔来写一部《中国艺术通史》。与此同时,我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而充满坎坷的道路。但在中国艺术史这块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上,如我能留下几个耕耘的脚印,这就是最好的精神慰藉、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是冬寒春晓,还是夏夜秋晨,我埋首笔耕,耐得寂寞。
二、“艺术”的界定及建立艺术史的紧迫性
要建立艺术史学,首先应基本界定“艺术”这一概念,对此历来众说不一。但我就接触到的观点来看,前苏联美学家莫伊谢依·萨莫伊络维奇·卡冈在《美学和系统方法·艺术》中所作的解释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人类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特殊种类。在这方面属于艺术的有一组人类活动的形式——绘画、音乐、戏剧、艺术文学(有时把他们单独划分出来——试比较‘文学和艺术’的说法)等,它们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乃是因为它们是再现现实的特殊的——艺术形象的——形式。‘艺术’这个词在较广的意义上属于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如果这种活动不仅在工艺学涵义上,而且在审美涵义上有技巧地、精致地、娴熟地进行的话。”卡冈的这段话有三个层次:一是统指性,即“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二是实指性,即艺术包括了绘画、音乐、戏剧等;三是社会性,即“属于任何一种实践活动”等。从而清晰地阐明了艺术的涵义。另外,卡冈在这段论述中还指出了艺术的大概念与小概念之分:从大概念上讲艺术包括了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等一组人类活动的形式;从小概念上讲艺术又是和某种艺术样式相结合的,如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文学艺术等。由此可见卡冈的艺术说要比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要清晰得多。
历史地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空缺,可能是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有关,即擅长于一种发散式的思维,而非是系统性的思维。所以,我国历史上对艺术的研究大都是“举要”、“艺概”、“诗话”式的。而近代对于艺术的研究又大都着重于分类史的范围,如绘画史、文学史、音乐史、戏剧史、雕塑史、书法史等。对此,我们不必苛求,至少以前这些研究为今天建立中国艺术史作了历史的积累与现实的准备。同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具有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原因。因此,在当代这个文化背景上,建立中国艺术史学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已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其意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历史的。
长期来,由于中国艺术史的空缺,使我们对整个中国艺术的发展缺乏一种系统思想与宏观了解,对不少艺术现象不能进行深刻的历史把握与能动的现实审视,因而常常不能正确地解释或揭示某些艺术发展的内在要素与外在成因。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艺术史在整个世界艺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空缺,也为世界艺术史的研究造成了断裂。因此,可以这样讲,建立中国艺术史学,是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重点工程。
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艺术史是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实的。”格罗塞的观点在世界艺术史家中具有权威性,常常成为一种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我却认为他的这种从考察史实为唯一目的的艺术史观是低层次的,从观念上讲是保守的,从方法上讲是消极的,从效应上讲是静态的。因为在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考察艺术史实,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进行多元的探索与多向的开拓,对静态的史实进行动态的研究。即在尊重史实的过程中,以新的史学观念来重新审视艺术史的发展,以新的审美觉悟来重新评判某些艺术现象的衍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史学的建立,应采取史与论的动态结构、纵与横的比较方法、点与面的开放体系、新颖而独到的研究视角。
三、史与论的动态结构
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是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篇》)式的超稳态结构,因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囿于琐碎的考证与玄乎的索引,所以,中国艺术史的建立,应打破这种超稳态的结构,采取史与论的动态结构,即以史实为客观依据,以论为探幽抉微,从而使某些艺术现象内蕴的意义凸现出来。
如原始彩陶纹饰,作为纯史实来看,这仅是原始先民美化装饰的一种常规现象,但以论的方法来评判这一艺术现象,就会发现原始彩陶上的各类纹饰(从鸟纹、蛙纹到人面纹、鱼纹等),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单的美化装饰,它包含了原始先民的思想情感,积淀了原始宗教与原始图腾的远古信息。就以马厂型彩陶上的蛙纹来分析,其表现手法是抽象的便化,除了形体像蛙外,其它几乎都线条化了,但从先前的半坡型、庙底沟型、马家窑型具象蛙纹来看,显然是有着内在的沿袭衍变,其中隐蔽着的是也许正是蛙逐渐演变成为代表月亮的蟾蜍而成为原始先民崇拜的月亮神图腾意味。这种图腾标志作为一种情感、观念、意识的符号,象征的是宗教对艺术的渗透,传递的是艺术对生活的反映。
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艺术史仅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它的发展既受着历史的制约,又遵循着自身固有的规律。因此,历史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时而协调,时而反差。所以,如果仅以史实为依据,那么我们在面对一些特殊的艺术现象时,就会陷入无可适从的茫然境地。如春秋战国是个战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年代,然而在艺术史上又是一个充满着活力与生机的创造时代,它对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培育、艺术观念的铸造,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边是兵刃相见、血流成河,一边是文化灿烂、艺术辉煌,这不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吗?然而,诚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好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春秋战国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文化艺术氛围,为艺术的发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开辟了一个宽松的文化时空,从瑰美的《诗经》、庄丽的壁画、奇逸的帛画、峻穆的青铜、劲健的铭文到孔子的文化思想、庄子的艺术哲学、屈原的《离骚》精神、公孙尼的《乐记》观念、左丘明的《左传》风格等,对我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历史辐射作用。
一个时代的艺术由于其分类的不同而常常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如果仅以平面的方式来分析,很难窥见其内在的美学精神与共同的艺术走向,因此需要引用史论结合的动态结构来作多维透视。如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尽管其绘画、雕塑、书法、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工艺等都呈现着不同的风格,但是把它们各自所内涵的审美追求集中在唐代的美学精神这个聚集点上,那么人们就会豁然明白它们的艺术走向是一致的,如唐诗的丰彩、唐塑的丰满、唐画的丰丽、唐书的丰腴、唐乐的丰韵、唐舞的丰艳等,都是与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弥散着浪漫主义气息,表现了唐人那种健康丰满的文化心态与豪放丰华的艺术情趣。
四、纵与横的比较方法
艺术有着门类之分,但艺术门类之间又常常是互为联姻的,从而形成一种交融变通的关系。因此,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不应采取一种单一、狭隘的方法,而是可以采取一种纵与横的比较方法,通过比较来拓宽研究视野、强化研究机制。如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塞舞蹈形陶盆,画的是一种五人集体舞,头上有发弁或头饰,而下腹也有装饰兽尾,手臂牵连在一起,双脚轻盈敏捷地跳动,表现了婀娜的舞姿与明快的节奏,他们头上的发弁或头饰及腹下的兽尾,亦带有明显的图腾装饰意味。据《吕氏春秋》中关于原始歌舞起源的传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来看,这种原始歌舞大都是伴歌而舞的,所以《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可见原始歌舞最初是集诗歌、音乐为一体的。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情况是原始歌舞亦包含了原始戏剧的萌芽。岑家吾在《图腾艺术史》中曾指出:“图腾跳舞的形式,于戏剧发生史上的影响,为我们不能忽略。一切模仿动物动作的跳舞,可视为原始戏剧之萌芽。”正是通过这种纵与横的比较,从艺术发生学上,我们较全面地了解了舞蹈与诗歌、音乐及戏剧之间的渊源关系。
在审视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如对某一艺术现象或艺术问题仅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往往是难以展开与深化的,这是“注经”式思维横式的局限。如甲骨文仅就该文字的本身来看,不过是殷商时代用来占卦的文字纪录,再介绍一下甲骨文发掘的经过就可以了。但如果从横向方面来看,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来作一番比较分析,至少可以挖掘出储存于甲骨文中的这样几点信息:1.甲骨文不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文化的积淀;2.如果说原始彩陶上的文字刻划符号还是那么随便简陋,那么甲骨文上的文字契刻就没有那么草率随意了,它需要相当的功力与技巧,书法艺术的技法训练由此而产生;3.通过甲骨上技法训练这一事实,说明殷商对于契刻文字有了相当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了朦胧的审美追求,书法艺术美的历程由此迈出;4.由于大量的甲骨契刻,使书法的物态化手段——线条日趋净化与成熟,由此而确立了书法艺术美的特性要求——线条;5.甲骨上常有贞人的签名,亦相当于后世书法家的落款,这些贞人也许就是当时的专业书契者,这种社会化的分工,归属于奴隶时代的上层建筑范畴,从中也可见书契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后历代皇家书法家地位之高亦渊源于此。
对于艺术史上常有争议的一些艺术现象与艺术家,如展开纵与横的比较研究方法,跨越艺术时空,运用现代审美观念来作横向分析,那么也许会有新的价值发现与新的观念认同。因为有些艺术现象在当时来看是超前的,因此当时对其认识的“滞后”性是不足为奇的。如董其昌的南北宗山水画派说,尽管从理论上讲有偏颇之处,但作为一种绘画理论学说的建立,有着理论上的建设意义与美学上的开拓意义。山水南北宗说把禅宗中“南宗”的“顿悟”与“北宗”的“渐修”融入具体的分析中,至少是一种新的创作心理与审美心理的分析法。因为禅宗的思想观念与文人士大夫画家的心理结构有着某种共通性。正是在这个参照系上,可以这样讲,董其昌的山水南北宗说其价值不在于理论上的精密性与完善性,而是在理论上的开创性与更新性。唯其如此,山水南北宗说引起日本、美国等艺术界的注意是有其原因的,并非猎奇,如果我们对此或照旧说,或回避,都是不理智的。
五、点与面的开放体系
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无疑应从宏观上把握,但在进行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有时也可从微观上入手,从个别到一般,从而形成一种点与面的开放体系。如原始彩陶上的原始书契,如作直观的论述,仅是原始先民的一种造字活动,但如把它放在整个文字学系统这个方面上来看,其意义之重大至少有这样几点:1.古文字起源说中造字者庖牺氏、神农氏、仓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生活的时代约是新石器时代,从而与彩陶上的原始书契的出现相契合,即彩陶上原始书契的出现与古文字起源说中造字者活动的时间基本相符;2.最初的原始文字主要有象形、指事二大类,而彩陶上的原始书契也基本上是象形、指事二大类,从而为古文字起源说提供了实物佐证;3.彩陶的原始书契构造形态是线条,并依稀可见某种笔触感,因此,原始书契的线条形式为今后文字特定的书写工具——毛笔的功能发挥,提供了施技对象。正是把彩陶上的原始书契这个文字发展史上的点投放到整个文字发展史这个面上来分析,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驱除了文字起源说中的迷雾。
实行点与面的开放体系来建构中国艺术史,主要是为了激活整个艺术史的研究系统,以便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来审视艺术史的发展规律,以提高研究效应。如果宋杂剧的演出仅从形式上看是滑稽、诙谐、幽默的,是轻松、喧嚣、舒心的。但事实上,中国戏剧的美学精神是充满时效性、讽谕性的,它具有丰富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从春秋战国时的“优孟衣冠”到唐代的“参军戏”都是以戏谏诤、干涉时政的,而宋杂剧从本质上也继承了这一戏剧传统,并贯穿于南北二宋。所以,把宋代杂剧放在整个戏剧史的层面上来看,宋杂剧的戏剧精神是在滑稽中进行嘲讽,在诙谐中进行谏诤,在笑声中进行抨击,为此也有一些怜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因讽刺、抨击秦桧而被杀。由此可见,宋杂剧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批判现实主义之路,从而为中国戏剧艺术高峰的到来——元杂剧作了精神上的准备与艺术上的奠基。代表宋代艺术最高成就的也许是宋词,宋词有豪放派、婉约派之分,但在这些作品中很少有直接讽谕皇帝、正面抨击权贵之作,而这一任务却由教坊里的伶工们来承担了,这不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戏剧文化现象吗?又如明代花鸟画的文人特征,明代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清代画坛的群体出现,扬州八怪的创作倾向与审美意识等,放在点与面这个开放体系中来重新审视一番,也许将为人们提供新的启示录。
六、新颖而独到的研究视角
对于历史的研究常常因不同的时代而产生不同的认识。这并不是说历史像橡皮泥,任你怎样捏,而是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因不同的思想水平与文化背景而产生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年青的。历史的过去时是凝固的,历史的现在时是能动的。艺术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应体现当代的思想水准与文化意识,具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观念的渗透,并且敢于突破旧说,不囿规范,寻求一种新颖而独到的研究视角。如女娲补天、羿之射日、大禹治水等都是原始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不仅有着生动的情节、美丽的描述、丰富的想象,涵养了后来的文学创作,而且反映了我们原始先民不畏艰辛、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原始先民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对开拓精神的讴歌、对先驱者的崇敬。这作为积极的一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应当看到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也潜藏着一种消极因素。即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也积淀了一种浓郁的英雄史观与虔诚的个人崇拜,这对以后整个华夏民族的思想观念及心理素质都有消极的遗传基因。
以往在研究某些艺术现象产生时,常常局限在艺术本体内寻找成因,忽视艺术外的社会原因与文化环境,从而使研究难以取得高层次的突破,这是研究视角单一所产生的逻辑结果。所以,如从社会学、文字学、现象学这些视角来研究分析某些艺术现象,会使人进入一种豁然开朗的境地。如秦汉之际的雕塑除了技法上的原因外,其创作思想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辐射,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气势力度雄浑豪放的崇尚,是人的力量对象化的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文化心理时空中,秦汉之际纪念碑式的雕塑作品出现了,从秦皇陵威武雄迈、阵容壮观的兵马俑到汉武帝时大将霍去病墓前那气势古拙、浑穆质朴的石兽雕,都艺术地再现了那种“秦王扫六合”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时代精神。也正是从这个视角上,使人们把握了秦汉雕塑内在的美学思想。又如宋、元的音乐活动,可以放在整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中来加以新的考察,由此可凸现出二大特征:这就是城市性与综合性。宋代的城市发展规模要超过唐代,元代也不逊色于宋,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市民文化消费的需求,城市音乐也相应地活跃起来,从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到杂剧、南戏等,在城市的瓦舍勾栏演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音乐创作表演群体与音乐欣赏观众群体。同时,宋、元音乐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与文学、戏剧等艺术的横向联系,显示出较强的艺术综合性,如宋词中的按乐填词、合乐歌唱、元曲中的小令、套曲以至杂剧,南戏的声腔运用、音乐伴奏等,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综合性的出现,是音乐艺术社会化的拓展,与文学、戏剧形成了一种互动型的结构,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音乐文化现象。如宋词人周邦彦、姜白石、张炎等,元戏剧家关汉卿、马致远、沈和等都有着十分深厚的音乐造诣,其艺术智能结构的完善性与高层次性,在历代艺术家中并不常见。
诚然,艺术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但以往却是对作品的研究大于对艺术家本人的研究,也就是说对被创作对象的注意大大地超过了创作对象本身,这是一种作品与作者倒挂的关系。因此,不仅要强化对艺术家本人的研究,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如心理学、现象学、人才学的重精神分析法等。如有不少作出杰出贡献的大艺术家,他们的性格都是不同寻常的,常常带有怪癖或变态。如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米芾,都是一代书法大家,但都有“张颠”、“素狂”、“米痴”之称。也正是这样的性格基因与心理势态,往往导致他们在艺术上不拘一格,自辟蹊径。像徐渭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曾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他在精神失常时误杀其妻而坐牢七年),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峰巅状态是他出狱后重返“青藤书屋”所作出的。他的写意花鸟画开风气之先,从形式上已超越了对现实的摹拟,而是通过笔墨的组合后展示出相应的审美形象,在内容上则摆脱了观念的直接流露,通过笔墨的意象构造展示出多元的审美意义。而且在他的挥毫运笔间,常常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意识渲泻,表现为某种骚动焦灼情绪或某些惆怅愤然的心态。这些心理现象与他在精神上的创伤可能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上所举的仅是个别的例子,而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有许多问题是可以从独特的研究视角来重新评价、反思的。如唐代的宗教“俗讲”,以往大多数人认为是宣传佛教迷信活动,但从风俗学意义上讲,唐代的宗教“俗讲”则开后世文化庙会的先河,成为一种促进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商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又如在以往的一些画学史论中,对文人画曾作了一些简单化的评述,认为其仅注重笔墨形式,因而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形式与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形式可以积淀转化为内容,内容也可以积淀转化为形式,它们是一种互变机制。而文人画的美学精神往往不太注重技法的精湛工致(这样就避免了匠气),而是注重抒情性与趣味性,因而笔致超逸、气韵生动、意境内蕴,从而为绘画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与创作手法。值得一提的是:既是单纯的形式美,也是一种艺术审美现象。唯其如此,文人画的美学精神还是应当作出客观评说的。
以上几点关于建立中国艺术史学的构想,也是我写这本《中国艺术通史》的宗旨,其不完善与不正确之处,恳请艺苑前辈与同道们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