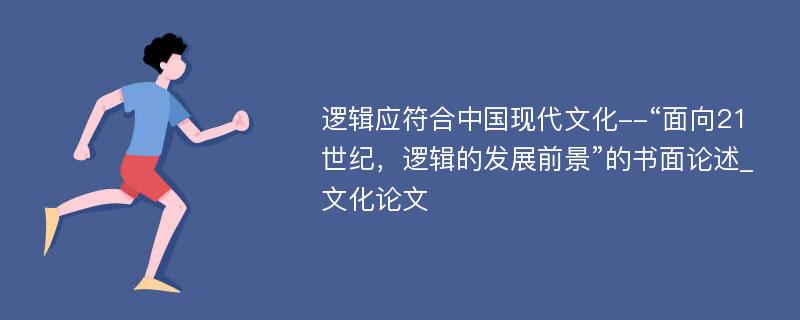
逻辑要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面向二十一世纪,逻辑学发展前景”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逻辑学论文,发展前景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是文化的一部分,我国逻辑学在21世纪的前景也必须在我国现代文化的背景中展望。
逻辑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而只有逻辑理论的萌芽,后来也没得到发展。逻辑萌芽见于先秦诸子的名辩学。但名辩学有别于逻辑学,二者并非同构,很多地方难以互译。中国古代也有逻辑思维,但由于没有逻辑学作为规范,那是不自觉和不发达的,更没有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主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重直觉而轻论证,好综合而恶分析,善于类比而拙于演绎,见长于形象思维而不见长于抽象思维。总之,中国文化缺乏逻辑的传统,而一个没有逻辑传统的文化是开不出科学、民主和法治的。同时,在一个科学不发达,只有专制而没有民主,只讲人治而不讲法治的社会里,也不需要逻辑学。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明代刊行的第一部西方逻辑译作《名理探》,在我国文化史上竟掀不起一点风浪,甚至几近于毫无影响。
西方逻辑介入中国文化起因于中国的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以“武化”的方式迫使中国卷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引起的震惊之中,人们发现了科学的重大价值。逻辑则作为科学的不可拒绝的陪嫁品进入中国,成为现代化的一个精神支点。严复此时翻译的西方逻辑著作《穆勒名学》得以大行其道,与《名理探》的被冷落形成强烈的反差,乃是由于历史的遭际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不需要逻辑,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逻辑。不但科学要以逻辑为工具,而且民主和法治也要以逻辑为前提,因为民主和法治都是建基于理性之上的,而理性则以合乎逻辑为其必要条件。可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初步地形成了第二个文化传统即现代文化,它与第一个文化传统即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引进了西方逻辑。中国现代文化论坛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严复、孙中山、王国维、胡适、金岳霖、章士钊、冯友兰、牟宗三、毛泽东,乃至后期专注于美学的朱光潜,都对西方逻辑作过有力的推介或者以它作为工具构造自己的学术体系。有了西方逻辑作为参照系,人们才发现长期埋没于故纸堆中的先秦名辩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由于吸收了逻辑的成果和方法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定义和划分的运用,推理和论证的讲究,成了现代学术著作有别于古代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不过,至今逻辑在中国现代文化中还是根不深而蒂不固。必须正视,逻辑的渗透力远未达到世俗文化的广大领域,只是局限于精英文化的小圈子,而在文化精英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或自觉地把逻辑当作思维的规范,传统的思维方式依然冥冥中支配着现代的芸芸众生。君不见时下的热门话题是“直觉”和“顿悟”,流行的口号是“跟着感觉走”,而在市场上走俏的则是把占卦算命家宅风水气功等“国粹”加以现代包装的神秘主义。
展望21世纪,逻辑能不能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还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逻辑与中国当代文化脱节的不祥之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提倡而虚热过一阵之后,于今已冷落到冰点。这种冷峻局面的形成包含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两点与当代学术思潮有关。
一、在我国人文学者中流传着一种消解逻辑的理论,我称之为逻辑解构主义。有人公然号召:“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打破逻辑法则的专横统治,争取思想的更自由呼吸”(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代序)》,见卡西尔著《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页)。同大多数时髦的理论一样,逻辑解构主义也不能算作国人的发明,它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某些观点的发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如果我们把欧陆人文学者的这些理论看作是对于西方自现代化以来由于过分偏重逻辑与科学而造成的文化结构失衡现象的一种反抗,则其良苦用心尚不难于理解,但是,把西方这种理论移植于缺乏逻辑与科学传统而现代化尚举步维艰的中土,却不免令人困惑,这岂不是历史的错位?这位逻辑解构主义的代言人对历史却别有见解,他写道:“有趣的是,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这些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的……而与此同时,欧陆人文学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的最大束缚和弊端而力图加以克服。”(同上书第25页)更有趣的是,当年胡适由于赞同日本人的断言“东亚无逻辑”而屡受讥讽,今天的逻辑解构主义者却以“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而深感自豪。难怪近年已有人怪罪严复把西方逻辑输入中国。逻辑解构主义者似乎在暗示,中国人也应当跟在那几个欧陆人文学者后面“反向而行”,回到无逻辑的文化状态。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等于开倒车?在消解逻辑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以什么为依归呢?“打破逻辑法则”的后果必然陷入自相矛盾,在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争取思想的更自由呼吸”,又何啻痴人说梦?逻辑解构主义不但威胁逻辑在中国的存在,也不利于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
二、在逻辑学者中存在着一种自外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孤立主义倾向。回顾80年代以来的几次“文化热”中,逻辑学界始终是个冷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学科都介入中国文化问题的大争论,逻辑学界却“岿然不动”,连逻辑解构主义咄咄逼人的威胁竟也不闻不问,更没有人对逻辑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发表过引人注目的意见,反而忙于与哲学划清界线,与文科脱离关系。一个对中国文化建设漠不关心的学科,自然也得不到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甚而至于使人产生一个错觉:在中国的文化重建中,与其他学科相比逻辑是最无足轻重的。
逻辑学界的孤立主义来源于逻辑形式主义,即认为逻辑研究的是一种与事实真理或思维内容绝对无关的纯粹形式。有的逻辑学者对这个主要来源于康德并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强化而终于被奎因彻底动摇的观点,仍然深信不疑。逻辑形式主义使逻辑学界安于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绝缘的状态,因为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逻辑与思想文化无关的结论。我不赞成逻辑形式主义。我认为逻辑以满足正确思维必要条件的思维形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这点上,以形式化为手段的现代逻辑和非形式化的传统逻辑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所以,逻辑决不是一种与事实真理或思维内容完全无关的纯粹形式(这里不详论,请参阅拙著《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392页)。逻辑形式主义只会限制逻辑的发展,使逻辑的生命力萎缩。
逻辑界本身的孤立主义和来自其他学界的逻辑解构主义的内忧外患,导致逻辑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互相脱节,这种状态才是逻辑备受冷落的根本原因。逻辑要走出“冷宫”不能单靠领导提携,行政上的支持无疑是重要的,但学术地位问题终究不能用行政命令解决。逻辑在中国的前途主要取决于逻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逻辑要走出“冷宫”,关键性的步骤是改变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脱节的状态。
在我看来,21世纪面临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使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对我国逻辑的发展还是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赞成张家龙先生的一个提法,就是以“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作为未来的“战略目标”。但是,展望21世纪,单单树立这个目标也是不够的。逻辑如果不能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国内逻辑研究即便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于一时,也难保其不再脱节。如果逻辑在国内尚难以立足,又如何能持久地在国际上与外人比肩呢?私意以为,我国逻辑者在下一世纪的全面战略目标是实现两个“接轨”,即逻辑研究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同时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
实现逻辑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这不但是逻辑界的历史任务,而且是整个学术界或思想界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需要由我国各个领域的文化精英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对逻辑界来说,为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一部分有条件的学者“破门而出”,进行跨学科研究,不研究与逻辑有关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且研究与逻辑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关系重大的问题,从而建立逻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以扩张逻辑的生命力,使逻辑的分支得以丰富和发展。过去有人只看重逻辑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而视逻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其实人文社会科学是文化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逻辑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只会使逻辑更陷于孤立,成为思想界无人问津的纯技术。
对其他学界来说,则期望有识之士自觉地应用逻辑的成果和方法处理本学科的课题。根据逻辑的对象和性质,应该坚信逻辑不但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且可以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尽管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缺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性,但它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理性,有理性就必有逻辑。在被视为人文科学方法的解释学的研究中,与伽达默尔带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所谓本文原意不可知论相抗衡的赫施,其理论的构成就借重于逻辑,所以他说:“解释学理论也受益于逻辑”(赫施:《解释的有效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5页)。 我国过去有的学者就由于将逻辑应用于知识论和方法论而获得成果,近年来某些学者的工作表明将逻辑应用于价值论也可以取得进展。我相信,如果将逻辑应用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其学术话语也将会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