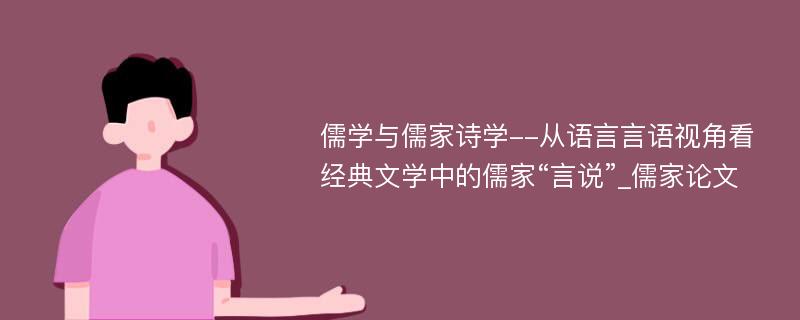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经学论文,诗学论文,透视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一、儒家阐释主体的生存渴望与语言家园的“建立”
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之途》一文的开端,曾把思考驻留在德意志短命天才——诺瓦利斯对语言的神秘体验上:“语言仅仅关切于自身,这就是语言的特性,(但这一点)却无人知晓。”〔1〕东西方的智者哲人对语言本质问题曾投入了无尽的思考:早在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语言即在智者的沉思中被推誉为理性的人所使用的工具;而早在东方的春秋战国时期,语言即在诸子的思考中沉沦着且转移着其价值取向。的确,整个人类也正是在语言的诱导下远离感觉观照的朦胧世界,从而迈进了辉煌的人文理性之门。
海德格尔的诗学在讨论“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时,曾把语言设定为生命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这一陈述并非意味着人只是伴随着其它能力而也拥有语言的能力。它是要说,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言说者的人是人。”〔2〕海德格尔把语言诗意地描述为阐释主体安顿自我栖居和生存的家园。而在古代中国的儒家学术宗教——经学中,也把语言认同为生命主体存在的前题:“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原来,儒家诗学也把语言设定为阐释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
为什么东西方的智者哲人都将语言作为主体栖居和生存的家园呢?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认为,阐释主体作为存在,唯有在语言中才能敞开且显现自我:“语言凭其给存在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的确,语言不仅是生命主体栖居的家园,语言也更以显现、敞开、照亮的方式呈现了整个人类世界。儒家诗学也把语言视为使存在呈现和敞开的家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引孔子的话说:“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这里,《左传》认为语言是足以呈现阐释主体及其思想的,并且进而在逻辑上反推,认为阐释主体及其思想如果不借助语言,就无法被他人理解。扬雄的《法言·问神》在文学创作论上,也把儒家“立言”的经典文本认同为栖居和存在的空间:“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与?’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在这里,扬雄以“郛”和“郭”对举,隐喻栖居和存在的“空间”:“天地”是盛载“万物”栖居和存在的“郭”,而儒家的“五经”则是囊括“众说”的“郛”。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举赞的“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韩愈《送孟东野序》推崇的“人声之精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周敦颐《通书·文辞》张扬的“文以载道”:“文,谓文字也;道,谓道理也。而载取车之义。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文之与车,皆世之不可无者,且无车则物无以载,而无文则道何以载乎?”这些表述虽然都是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和批评的诗学话语,但在中国古代大文化的语境中,这三者均把语言认定为存在得以栖居和呈现的家园。
如果说儒家诗学把语言作为阐释主体栖居和存在的家园,这是儒家阐释主体生存渴望的第一个深层目的;那么,当我们跨过海德格尔“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的命题,走向儒家诗学关于语言沉思的纵深处,就会发现,儒家诗学把语言视为阐释主体栖居和存在的家园还有第二和第三个深层目的。第二个深层目的即是:在语言的家园中规避死亡和追寻永恒;第三个深层目的即是:把语言的家园建立在中国古代学术宗教——经学的经典文本形式上。
儒家阐释主体栖居和存在于语言的家园并获得呈现和敞开后,进而渴望在语言的家园中规避死亡而追寻永恒。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家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严格地讲,儒家阐释主体正是基于后两个目的而把语言作为自我栖居和生存的家园。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阐释主体在生命面对死亡的规避中,张扬一种“三不朽”的精神: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废,此之谓不朽。’”作为形而下的生命肉体是无法抗拒死亡的,生命面对死亡必然产生一种内在的心理恐惧,而主体平衡内在心理恐惧的唯一路径就是超越肉体生命生存的短暂和有限,规避死亡而归向永恒。但是,形而下的生命肉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自我生存的极限,因此,生命规避死亡而追寻永恒的生存渴望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取向在形而上的精神空间兑现。但是,思想和精神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往往在主体的运思中转瞬即逝;因而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一中介来存在和呈现于这个世界。正是这种在语言家园中的“立言”,使儒家阐释主体在精神和思想上超越了自我,获取了永恒。在儒家诗学体系中,“立德”和“立功”等功利性的价值最终必须落实在“立言”上,才能超越主体自我归向不朽的永恒。儒家阐释主体及其诗学体系也正是在经学的经典文本形式上“立言”,才能够在历史的代际传递中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空间的精神不朽者。
纵观中国古代诗学漫长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儒家诗学始终是宗教般地执著于主体在文学创作中归向不朽的“立言”。曹丕的《典论·论文》对这种“立言”的渴望有着再度的阐释:“盖文章,经国家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与其说《典论·论文》对文学作用和文学价值的评估体现了魏晋间的时代精神〔3〕;不如说这种评估再度强调了儒家诗学对语言家园的建立,从而显露了儒家阐释主体在语言的家园中追寻生存永恒的渴望。因此,在儒家诗学的阐释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也必然像曹丕阐释的那样,成为“不朽之盛事”。
第三个深层目的就是儒家诗学渴望把语言的家园建立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上,从而占据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兑现其追寻永恒的欲望。经学是支撑中国古代文化大厦的官方学术宗教,而经学的文本形式为儒家诗学在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上建立语言的家园提供了可能性。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是指书写的文本(writing),而不仅仅指主体在场时的“对话语言”(saying)。在先秦时期,“文学”就是泛指学术文献的经典文本。这也正如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一时期“文学”概念的阐释:“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4〕因此,在儒家阐释主体建立语言家园的渴望中,主体及其诗学体系存在和追寻永恒的“语言家园”即是指“书写”的文本形式。而当儒家阐释主体把语言的家园建立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上时,也即标志着儒家诗学对经学的学术宗教地位的获取。可以说,儒家诗学的整个体系、全部范畴、最高批评原则和在价值论上设定的最高文学范本均肇源于经学的经典文本,并且也正是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中传承下去的。
海德格尔曾把语言设定为阐释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企图为西方诗学建立存在的语言家园张目;而儒家诗学也把语言设定为阐释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并且在上述三个深层目的中,渴望在经学的经典文本上建立阐释主体安顿自我的语言家园。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诗学最终是把第一个深层目的和第二个深层目的置放在第三个深层目的上实现的,这就在获取学术宗教的神圣地位上,满足了儒家阐释主体建立语言家园的一切功利性欲望。
二、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与经典文本三个层面的涵义
为什么儒家诗学崇尚以“立言”在学术宗教——经学上建立自我栖居和存在的语言家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首先从设问和界定“经学”这个概念展开思路。
经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说与三千年中国古代文化史同步。经学发端于上古时期的周公时代〔5〕,随着最后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和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寿终正寝,走完了其三千年的学术文化专治历程;与此同时,经学也在历史敲响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丧钟之际,走向了辉煌的终结。从认识论上审度,经学是统治中国古代社会始终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及其诗学取得了经学的地位,经学被明确地认定为以孔子为始祖的官方学术宗教。从本体论和价值论上审度,经学又是主体以“经”为价值终极的本体论。因此,与其说儒家阐释主体是在经学的文本形式上建立起其生存且追寻永恒的语言家园,不如说儒家阐释主体是在“经”的本体范畴上建立起其生存且追寻永恒的语言家园。而在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上,经学所运作的文化行为,是作为一种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语言阐释的古典阐释学而兑现的。因此,经学又是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语言阐释从而建构自我理论体系的古典阐释学;在这个意义上,经学必然表现为一种对语言艺术——文学进行阐释的诗学理论形态。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的学术宗教意识形态,经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儒家阐释主体是在“经”的本体范畴上建立起其生存且追寻永恒的语言家园呢?“经”作为一个能指符号,阐释主体赋予它的涵义有三个层面:一是指本体范畴,这是“经”的第一个层面的涵义;二是由第一个层面的涵义引申出的文本形式——典籍;三是由第二个层面的涵义再度引申出的专指儒家的“六经”或“十三经”的经典文本。西方分析哲学的先驱戈特洛布·弗雷格在《论涵义和指称》中曾设定了一个完善的指号构型:“指号”——“涵义”——“指称”。“指号(能指符号:即范畴、概念或语言表达式),它的涵义和它的指称之间的正常关系是这样的: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对象)。”在戈特洛布·弗雷格的指号构型中,“涵义”是组接“指号”和“指称”两者逻辑关系的中介,三者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表达式。那么,“经”作为一个“指号”,其所对应的“涵义”和“涵义”所对应的“指称”又形成一个怎样的完整的语言表达式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经”这一本体范畴作语言的释义。
“经”作为一个“指号”的使用,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经”的原初“涵义”是“织物的经纬线”。这一释义实际上是承继许慎和段玉裁对“经”的释义而来的。《说文》:“经,织,从丝也。”段注:“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天地之常经。”值得注意的是,“经”在周代铜器铭文和周代典籍中的使用,有一个从实物名词向动词和抽象名词转型的过程;“经”也正是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阐释主体在理论思维形式上的蜕变,并且体现出阐释主体在诗学体系的建构上的终极关怀。把“经”的原初意义——“经纬”作为动词使用,“经”在指号的涵义上就被阐释主体赋予了“涵盖”、“统摄”、“包容”、“囊括”、“占有”和“治理”等等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这在先秦典籍中最为常见。《周易》:“君子以经伦”,《左传》:“经国家,定社稷”、“经纬天地曰文”、“以经纬其民”,《吕氏春秋·求人》:“终身无经天下之色”,这里所运用的“经”,都是在上述意义上完成的。但是,理论思维形式的发展使阐释主体并不满足把“经”仅仅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从而仅仅表述主体在运思的瞬间显露出的终极关怀。“经”必然在语言表达式的使用中从动词向抽象名词转型。因为动词所表示的主体对时空的“涵盖”、“统治”、“包容”、“囊括”、“占有”和“治理”等具有终极关怀的涵义,只有借助于抽象名词才能凝固下来而趋于恒定。《周礼》的“以经邦国”和《左传》的“天之经也”、“天地之经纬也”,就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完成的。
“经”作为动词向名词的转型,标志着“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的形成。“天之经也”的“经”,就是作为一个本体范畴被阐释主体所使用的。可以说,阐释主体在诗学体系的建构中只要抓住一个“经”字,就可以“拎”起一方博大的天地。在本体论的理论形态上,这方博大的天地就是阐释主体在“经”的本体范畴上建构起来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家园。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经”曾作过本体论的阐释:“(经)覆而无外,高而在上,运行不息,日月星晨,温凉寒暑皆是天之道也;训经为常,故言道之常也。(经)载而无弃物,无不殖山川,原阳刚阴柔、高下,皆是地之利也。”正是“天之道”和“地之利”构成了儒家诗学所言指的“大全”,而“涵盖”、“统摄”、“包容”、“囊括”、“占有”这个“大全”的终极本体就是“经”。
罗素在思考智者哲人无法逃避对本体论的建构的原因时,曾把这一疑惑归结为生命主体对“永恒”的追求:“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6〕在修辞学意义上,“经”作为一个抽象名词,是阐释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设定的一个具有恒定意义的本体范畴。倘若把东西方智者哲人的运思在诗学的本体论意义上做一次比较,“经”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存在”(bing)、柏拉图的“理念”(idea)、圣·奥古斯丁的“上帝”(God)、 康德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因此, 当儒家阐释主体立足于“经”的本体意义建立起自我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并把自己庞大的诗学体系建构于这个语言家园中时,他们必然把“经”认同为是一个恒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真理。班固认为:“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白虎通》卷四)刘熙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释名·释典艺》)刘勰认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孝经序疏》引皇侃言:“经者,常也,法也。”王应麟《玉海》卷四一引郑玄《孝经序》:“经者,不易之称。”在朱熹的诗学思想中,“经是万世常行之道。……经者,道之常也。”(《朱子语类》卷三七)在王阳明的诗学体系中,“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所谓“五常之道”、“常道”、“常典”、“恒久之至道”、“不易之称”就是指“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的恒定性。“如路径无所不通”、“不刊之鸿教”即指“经”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终极真理和垂教万世的大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锡瑞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迷狂把儒家诗学体系栖居和生存的本体——“经”崇奉为“圣经”,认为“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7〕。 对本体的追寻是东西方诗学阐释主体无法逃避的劫数。在理论的思维价值取向上,古希腊诗学以理性瞩望着沉默的宇宙,从而命定于宇宙本体论;而儒家似乎认为宇宙太遥远,更着重在中国古代学术宗教的终极本体——“经”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用语言文字凝固成的文本形式,即语言家园,从而在这个语言家园中来“立德”、“立功”、“立言”,以此追寻精神和思想的不朽。
由于“经”的本体地位,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的各脉诗学思潮的冲突和碰撞常常表现为阐释主体对“经”的神圣地位的争夺和攫取。从阐释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看,就是为了在“经”的神圣地位上“立言”,企图借助“经”在本体论上的学术宗教性,追寻理论和思想的正统化,从而迫使中国古代诗学沿着自我诗学体系设定的理论方向而行进。因此,各脉诗学思潮在对“经”的神圣地位的争夺中,往往用“经”来指称自己“立言”的文本形式,以强调自己诗学思想的神圣性。这是从“经”的第一个层面的涵义引申出的第二个层面的涵义。《诗》、《书》、《易》、《礼》、《乐》、《春秋》被称为“六经”后,便成为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批评原则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范本。墨子的“立言”文本称为《墨经》,《庄子·天下》载后期墨家三派“俱诵墨经”。老子的“立言”文本称之为《道德经》。庄子的“立言”文本被后人称之为《南华经》。《论语》、《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也被后人列入十三部儒家之“经”。仅这些被尊称为“经”的“立言”文本形式已涵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重要的典籍。把一部“立言”的文本形式称之为“经”,在价值取向上意味着赋予这部“立言”的文本形式以正统而神圣的学术地位。因此,我们只要明晰了“经”的第二个层面的涵义,便可以体验出一部被赋予“经”之地位的典籍在诗学体系中有着怎样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中,阐释主体在各脉诗学思潮的汇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以思想“经天纬地”,就必须在“经”的这一本体范畴上建构起“立言”的文本形式。这也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言:“经纬天地曰文。”这个“文”指的就是“立言”的文本形式。杜预注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纬相错,故织成文。”而孔颖达正义又进一步把“经天纬地”的文本形式直接阐释为“文章”:“如经纬相错故织成文章,故曰文也。”因此,在“经”的第二个层面的涵义上,“经”就是“文”,就是“立言”的文本形式,就是“立言”的文章和典籍,就是主体建立的语言家园。
这种在文本的形式中“立言”从而追寻本体的终极关怀,成为儒家诗学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因为任何诗学体系的建构必须要有一个基点——本体。
如果说柏拉图诗学体系用理性瞩望着宇宙的最遥远处,在宇宙的本体上设定一个“理念”,从而开始了西方古典诗学史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么,孔子则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精神执著下删定“六经”,从而启开了儒家诗学史上的经学中心主义。克罗齐认为:主体思想运作的“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8〕在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诗学也正在“孔子删‘六经’”的复古精神中被创造着,成为全部过去历史的必然结果。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阐释孔子的诗学思想时,已指出孔子“追修经术”是为了“垂六艺(‘六经’)之统纪于后世”:“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这是一种怎样的真知灼见啊!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在各脉诗学思潮的汇流中选择了儒家诗学时,儒家诗学同时也在学术思潮的汇流中选择了历史。这是一个必然的、无可回避的双向选择。“经”作为一个能指符号,它的第三个层面的涵义即指儒家诗学“立言”的经典文本,这是从“经”的第二个层面的涵义再度引申出的专指儒家经典文本的涵义。在儒家诗学体系中,阐释主体存在与追寻永恒的语言家园,即是在“经”的第三个层面上引申出的“六经”的经典文本形式。儒家诗学认为,阐释主体作为思想者,其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必须在语言的家园——“六经”的经典文本中才能够显现出来。这正如《论语·宪问》所申明的:“有德者必有言”,也正如《周易·系辞下》所指出的:“圣人之情见乎辞”。反之,不强调在“六经”的经典文本形式上“立言”,阐释主体便失去了生命存在的家园及其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从孔子删“六经”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古代诗学由于受到学术宗教——经学的影响,直到经学的玄学化阶段——魏晋时期才开始走向自觉。因此,先秦两汉时期,在儒家经典文本中栖居和生存着的儒家诗学理论还没有完全在文本的形态上与母体分离开来,以独立的文本形式作为自我存在的精神家园,这意味着儒家经典文本即是儒家诗学存在的文本形式。正是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从而获取经学的学术宗教的神圣地位,儒家诗学才可能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官方文学批评语境,并且雄霸中国古代诗学史两千年之久。
三、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与文学的崇高地位
德里达在拆解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体系时,发现形而上学的根本迷误在于:主体设定了世界存在的一个本体中心——终极价值或终极真理,形而上学必须把语言当作不幸而必要的透镜,透过语言去洞视这一终极价值或终极真理。儒家诗学的迷误也在于为此在世界设定了一个本体中心——“经”,其所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终极真理正是设定在“经”这一本体范畴上。儒家诗学恰恰是将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作为语言透镜,通过这一语言透镜去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和批评,因而必然导致主体在阐释和批评中追寻一种政治教化的深度模式,并且赋予文学崇高而神圣的学术宗教地位。
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所追寻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最突出的影响,即是在创作论上把儒家经典文本“六经”(或“五经”)尊崇为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且不可超越的最高文学范本,并且把它渗透到每一位接受儒家诗学阐释原则的主体的灵魂深处,并外现于他们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和批评各个方面。只要对中国古代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作一次粗略的扫描,便可以捕捉到这一点:
班彪在讨论司马迁《史记》的诗学思想时认为,《史记》在文学创作上之所以做到了“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是因为“迁(司马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列传》)王逸在评价屈原《离骚》的审美价值取向时,认为“夫《离骚》之文,依《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颜之推在讨论文学的文体起源时,认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议论,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篇》)刘勰带着极端的功利性把“宗经”、“征圣”、“原道”列为“文之枢纽”,并且认为,文学的本体就是“五经”:“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文心雕龙·诸子》)诗圣杜甫在《又示宗武》诗中,把诗句创作的出新归因于饱食“五经”:“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在唐代诗学中,尽管咬然是一位“禅栖不废诗”的僧人,但他在“妙悟”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时,开宗明义地把诗的审美本质归统于“六经”:“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诗式序》)白居易认为“六经”就是文学的渊薮,他对这一观点的陈述就像他的新乐府诗一样直白:“人之文,‘六经’首之。”(《与元九书》)韩愈在表述古文运动理论时认为:“士不通经,果不足用。”(《送殷员外序》王禹偁)把“远师‘六经’”认定为提高文章写作的途径(《答张扶书》)。朱熹在讨论“文以载道”时认为:“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论文上》)李东阳在“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的理论旗帜下,张扬一股诗学理论的复古思潮,把“六经”认同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古之‘六经’,《易》、《书》、《春秋》、《礼》、《乐》皆文也,惟《风》、《雅》、《颂》则谓之诗,今其为体固在也。”(《春雨堂稿序》)茅坤在剖解文学创作主体的深层心理结构时认为:“……窃谓天地间万物之情名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吾心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廷尉书》)谭元春在讨论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时,认为“六经”就是最高的审美参照范本:“私谓‘六经’无不美之文,无不朴之美。”(《黄叶轩诗义序》)艾南英虽然在其诗学体系的创建上致力于时文改革,但他还是把“六经”文本设定为文章撰写的最高范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陈大士合并稿序》)而钱谦益则直截了当地把“六经”设定为文学的最高范本:“‘六经’,文之祖也。”(《袁祈年字田祖说》)桐城派诗学的基础就是“义法”说,方苞在《古文约选序》讨论唐宋八大家文学作品时,把文章“义法”形成的根源追溯到“六经”、《论语》和《孟子》:“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叶燮的《原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叶燮以“才、胆、识、力”和“事、理、情”建构起他的整个诗学体系的框架,而《原诗》的全部要义就在于把“六经”之“道”视为三千年来文学创作无法超越的恒定的终极真理和基本规律:“夫文之本乎经,袭其道非袭其辞。如以其辞,则周秦以来三千余年间,其辞递变,日异而月不同。然能递变其辞,而必不能递变其道。盖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知差万别,总不可越。”(《与友人论文书》)袁枚的诗学理论主张在“性灵说”中“著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认同了“六经”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范本对两汉、六朝和唐宋文学创作的渗透和影响:“‘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而阮元则带着宗教般的崇圣心理,把“六经”尊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范本:“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经’。”(《四六丛话序》)……仅这些个案列举所呈现出的对“六经”宗教般的崇奉就足以证明,儒家诗学通过在“六经”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这一语言透镜所追寻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乃是要求文人墨客在文学创作中把“六经”尊奉为必须遵循且不可超越的最高文学范本。“六经”是儒家阐释主体“立言”的经典文本形式,是儒家阐释主体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而文学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儒家诗学通过“立言”这一语言透镜把“六经”的文本形式认同为最高文学范本,这在理论的逻辑推导上,也是自然和必然的终结。但是,儒家诗学偏执地把文学创作导向追寻政治教化的深度思想模式,也就忽略了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其自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在日内瓦语言学派和胡塞尔现象学影响下崛起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批评家,为了把文学从政治教化的泥沼中拯救出来,曾把文学界定为一个独立有序的自足体,认为文学独立于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甚至独立于社会生活。什克洛夫斯基曾以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向世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9〕与“艺术永远独立于生活”这种偏激观点截然相反,儒家诗学恰恰是通过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这一语言透镜,把文学存在的价值观投影和聚焦在国家学术宗教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上,让文学这种语言的文本表达式普泛地覆盖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道德和宗教之中。因此,在儒家诗学崇尚“立言”的阐释方法操作下,文学的文本形式往往映衬出官方意识形态的浓烈的政治色彩。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吟咏“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王安石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把文学认同为主体纯粹的“立言”文本形式:“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在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并进而要求“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上人书》)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阐释和批评的方法论,必然把文学认同为纯粹的“立言”文本形式,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剥夺了文学自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这也正是在儒家诗学理论话语下的文学现象最鲜明的特征。因为“六经”作为儒家阐释主体栖居和生存的语言家园,其在“立言”的经典文本形式中承继和负载了儒家思想设定的最高道德伦理准则;这些最高道德伦理准则在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批评中,必然把文学导向追寻功利性和思想性,使文学表现为重政教,重言志,在创作风格上表现为写实主义,在文学思潮的兴起上表现为复古主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诗学的深层内涵。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了悟《毛诗·序》为什么要把感情真挚的爱情诗《关雎》阐释为“后妃之德”。
初唐四杰在对文学的阐释和批评中也主张“立言”,要求借助语言的承继性和达意功能复归先秦儒家的诗学观念和诗学原则。王勃认为:“《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平台秘略论·文艺》)杨炯认为:“大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垂其范。”(《王勃集序》)卢照邻指出:“文质再而复,殷周之损益足征;骊翰三而始,虞夏之兴亡可及;美哉焕乎,斯文之功大矣。”(《南阳公集序》)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并设定了诗歌的社会功能:“……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韩愈在初步建立“道统”的诗学理论时认为:“学生或以通经举,或以能文称。其微者,至于习法律、知字书,皆有以赞于教化。”(《省试学生代斋郎议》)。在理论上,韩愈强调作品的思想深度,把散文从六朝的形式主义诗学理论中剥离出来,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他最终把文学阐释为主体为了政治教化而必须借助的纯粹语言文本表达式。为此,韩愈以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六朝骈文的形式华美,以“宗经”、“征圣”、“原道”作为古文运动的政治信条,从而推动这一脉文学复古思潮向政治教化的深度模式拓展。古文运动发展到宋代,石介在反对西崑体的形式主义文学倾向时,把文学创作推向了追寻政治教化深度模式的新的高度:“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圣人,识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上蔡副枢书》)石介之后,以欧阳修为传导中介,从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到朱熹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儒家诗学追寻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在宋代经学大师的偏激理论推动下走向了极致。他们完全颠倒了“文”与“道”即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把文学作为主体为追寻功利性而纯粹“立德”、“立功”、“立言”的文本表达式。刘大杰在讨论宋代的文学思想时认为,宋代的经学大师“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一点生机,全被这道学压死了。”〔10〕在这里,与其说文学艺术的一点生机是被道学压死了,不如说是被儒家诗学苛求政治教化的深度模式压死了。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和对政治教化深度模式的追寻,必然导致苛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文学首先是审美的艺术这一大前提。在儒家诗学的运作空间,阐释主体永远无法摆脱那似乎是命定的功利性——“立德”、“立功”、“立言”。儒家诗学崇尚的“立言”作为一种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其在历史的惯性推动下和儒家阐释主体的操作下凝固成特有的理论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下生存的文学必然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政治忧患意识。倘若我们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衔远山,吞长江”的抒怀中,为什么要把全文的主题落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忧乐观上。
文学需要思想性。我们不否定儒家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赋予文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创作导向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使作品走向丰厚。乔姆斯基在《语言沉思录》一书中认为:“语言是心的镜子。”〔11〕而通过“立言”这一语言透镜折射出儒家诗学的深层心理结构即是,儒家诗学把文学置于崇高而神圣的学术宗教地位而最终是政治教化的深度模式中,从而使创作主体失落了思想自由。这实际上还是从“中庸”走向了偏激。儒家诗学的经学中心主义让人们倍感文学的崇高与神圣,同时也让人们的思考停滞在政治忧患意识之下而倍感步履沉重。但这绝对不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阐释方法和批评方法的整体特色;因为道家诗学体系崇尚的“立意”作为儒家诗学体系崇尚的“立言”的对立面,其以“立意”于瞬间所追寻的直觉体验消解着儒家经典文本,颠覆着儒家诗学体系的经学中心主义,从另外一个方面推动着中国古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这就是儒道诗学理论的冲突与互补。
注释:
〔1〕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文化与艺术之途》, (香港)艺术潮流杂志社1992年版,第166页。
〔2〕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中译本,第165页。
〔3〕参见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4〕章太炎:《国故论衡》,浙江图书馆校刊本。
〔5〕本文赞同古文经学关于经学缘起的界说。
〔6〕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4 页。
〔7〕《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2页。
〔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第13页。
〔9〕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 转引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第586页。
〔11〕N.Chomsky:Reflections on Language,Pantheon Books,ADivision of Random House,New York,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