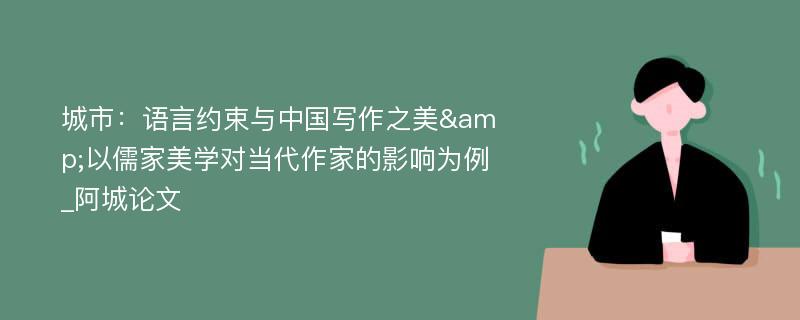
阿城:语言节制与汉语写作之美——儒家美学对当代作家影响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城论文,儒家论文,汉语论文,个案论文,之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城20世纪80年代中期跃上文坛以后,人们纷纷从道家文化角度给予解读,实际上对于受传统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儒道互补是其基本的人格遗传基因,阿城其人其文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棋王》中王一生由道家的虚静进入到儒家的壮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语言是构成阿城小说异样的特殊的审美感受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经常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存在凸现于读者面前。语言是有文化内涵的,阿城语言体现了很多儒家语言审美要求,本篇文章试图集中探讨阿城小说语言的儒家美学积淀,当然这不是说阿城小说语言中没有道家审美的因素,只是由于论题的限制不再展开。
从语言的内在结构来看,夯实的白话语言加以古汉语成分的杂糅调和是阿城小说语言的基本面貌。
阿城的小说语言以最平实的白话语言为基础。他用的字是最常用的字,绝无险字怪字,阿城自己曾经说过“他的用词绝对是在常用词里的,他的用词绝对不超过一个扫盲标准的用词量。”[1]形容词、成语、比喻等等可以在语言中形成夸饰、华美风格的语言要素在阿城的小说语言中一律用得极为俭省。阿城对此似乎还不满足,他又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即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加以夯实,语言显得更为节制。我们仅看他在人称代词和标点符号上的应用即可窥见一斑。
我们看到阿城经常省略人称代词:
1)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棋王》)
2)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起绑了,由造反队审。(《棋王》)
句子之间的人称代词的省略,经常需要读者停顿下来去分辨动作的发出者到底是谁。
因为要做到语言节制夯实,阿城甚至在标点符号上也作了一种处理。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以逗号、句号为主干,按照现代汉语规定,句子之间的停顿用逗号,一个意思完整用句号。我们看到阿城的句子非常短峭,他在一般人使用逗号的地方使用了句号,使句子更为夯实,随之表达的意义也更为丰厚: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不下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棋王》)
平常人们会在“王一生便很沮丧”前面用逗号,表明一个意思,即对方不敢再下了,王一生很沮丧。但当“王一生便很沮丧”独立成句时,它便突出、强调了两个人各自的状态,而不是作为对手的两个人的一种状态。
此外,阿城还在夯实的白话语言基础上吸收了古汉语的成分。古汉语与东方传统的非逻辑思维方式相联,具有含混、多义、富有弹性等特点,适合表现现代汉语难以表述的人的微妙、复杂、朦胧,甚至是神秘的主观感受。古汉语的美,一是它的简洁,二是它的表现力。大家经常称道的《棋王》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王一生已经睡死。我却还似乎耳边人声嚷动,眼前火把通明,山民们铁了脸,掮着柴火在林中走,咿咿呀呀地唱。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一些现代汉语已不多用的古汉语单字,如“掮”、“荷”、“囿”等等,而且即使是现代汉语,阿城也有意识地节缩了文字。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居多,但在这段中,阿城有意识地节缩双音节现代汉语变而为单音节字,使之既是现代汉语的常用字又成为古汉语似的单音节字,每句话都写得很结实。加进古汉语的成分,不仅使文字显得简洁,而且使文字富有了一种特殊的风趣。现代白话文运动之初,周作人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方面就已经注意到,纯粹口语体具有细腻流丽的特点,比较适合文学语言的说理、叙事功能,但是纯粹的白话文体不能够完满地实现文学的抒情功能,好的抒情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纯粹的口语体不能满足现代文学语言的需要,而必须有文词上的相应变化:“以现代语为主,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使他丰富柔软,能够表现大概感情思想。”[2]
阿城的这种语言面貌最突出的特征是语言的节制。而语言的节制正是儒家中和审美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儒家中和审美意识要求艺术的各种要素中庸平和,在对立的两端寻找“中”,节制而不逾矩。落实到语言方面,儒家一直对单纯的脱离了内容的华美语言保持警惕与反感,要求节制语言。个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基于儒家对语言与生命的关系的思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当然是人生的最好状态,但是儒家很早就注意到人们很容易夸夸其谈,言行不一,“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实问》),“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儒家在根本上似乎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戒心,对语言总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尤其是厌恶对语言的过分使用。在儒家看来,真正的君子应该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儒家对人的考察也是“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与其言行不一,儒家宁要求人们行重于言,行是第一位的,言是第二位的,所以儒家要求君子“慎言”、“寡言”。尤其是在《论语·阳货》中,“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的一再发问中,孔子透露出他对语言功用的深度思考:与无言的但包容性很大的天比起来,喋喋不休的人类是多么的渺小,语言根本无法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只有“行”才能够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价值。正因为儒家在对语言与生命的关系思考中把语言放置在“行”的后面,是第二位的,时时要求着言不得超越“行”,形成言过其实,从君子变为伪君子,所以儒家对一切语言运用都要求谨慎、节制和实在,所谓“辞达而已矣”。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决定了儒家的语言观首先是节制,是慎言是寡言,是摈弃单纯的脱离了内容的华美的语言。
正如儒家节制语言的中和审美观来源于其对语言与生命的关系的思考,阿城的语言面貌也与其人生态度直接相关。我们看阿城的自我介绍:
我叫阿城,姓钟。1984年开始写东西,署名就是阿城,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我出生于1949年的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仅十多年。1979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过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大家怎么活过,我也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棋王》扉页小传)
这样的自我介绍很是别开生面,不媚俗,不粉饰自己,而是作了一种相当低调的处理,诚实得如同脚下的土地。但是这种诚实是以坚实的人生信念作根基的。阿城七八岁时就受到家庭的牵连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后来谈到他从小的生活状态是“没有谁点拨我,自己点拨自己”,“孤寂,那种孤寂是一种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状态。孤寂一般人理解为没人理他,但他自己理自己,他就会自己充分调动起来。”当被问到是否也会为名所动时,他的回答是:“毫无所动。我的经验足够排除这些。因为我已经知道这种东西不是事情本身,有名没有名不是事情本身。”[3]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立定脚跟,认认真真地做人是阿城独特的做人风度。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孩子王》中的“我”对教书的感受:“觉得这两节课尚有收获,结结实实地教了几个字,有如一天用锄锄了几分山地,记工员来量了,认认真真地记在账上。”教学生写作文也是“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诚实、朴素、认真,但有内在的骨气。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古典儒者的风骨,甚至还有些儒道互补的韵味,在这里恰好可以用“文如其人”来概括阿城的“人”的价值观和“文”的价值观。
节制语言,摈弃脱离内容的华美语言是儒家对语言的基本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儒家不讲究语言的美,出于教化宣传的功利性考虑,孔子甚至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要求语言美,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什么样的语言是儒家认为的美的语言?根据我们的考察,起码有两点,一是有风骨,一是具有无限生发性。
儒家从孟子开始就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说。正如孟子所言,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它在内焕发了一种感性生命力量,向外焕发了一种深厚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孟子开始的这种养气功夫一直贯穿在儒家的人格修养中。文学作为生命的映射,中国文学、艺术中也特别重视“气”的问题。从曹丕开始就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魏晋以后广泛出现的美学范畴“风骨”即是气——作家内在的精神气质、生命力量在文学中的灌注,所以纪昀有:“气是风骨之本”的说法。“风骨”这一美学范畴,虽然在不同的文论家那里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意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受儒家影响深的文论家对于风骨的提倡中都含有了在创作中灌注儒家纯正思想而焕发的一种刚健劲实的生命力量。这种刚健劲实的生命力量灌注在文章的各个方面,语言也不例外。讲究风骨,必然使语言含蕴一种内在的力度,显示刚健之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语言审美的正面提倡“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捶字坚而难移”,唐代陈子昂有感于“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衰颓,提倡“汉魏风骨”,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4]的文章标准,都可以看出对语言风骨之美的追求。
阿城的语言面貌在节制之中显现一种内在的骨气,即显现了儒家语言审美的一些精髓。当年胡河清就已经注意到阿城的“小说近于谨严的线描”,“特以骨力见胜”[5],他讲的是阿城小说的总体风格,运用到语言评价上也一样恰当妥贴。语言节制夯实,增加了语言的内在密度,同时也就充分地调动起了文字的表现力,使每一个字都立起来,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作用,显得非常有力度。在《孩子王》中,“我”喜欢翻阅字典,“慢慢觉得比小说还读得”,正是感觉到了每一个文字所具有的隽永丰富的魔力。他的语言有“骨气”,充满了一种力量感。当然可以看出阿城语言的内在力度,是在内敛平和中显现的内在力度,与儒家劲气纵横的刚健之气还是有些区别的,这可能与阿城做人的平民态度有关,也可能与道家文化的影响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种文化的复合影响、作家自身的个性,都决定了一种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影响不可能是复制、克隆似的确定,而是带有了个体的特征。
其次,儒家对语言的审美追求除了刚健有风骨之外,还讲究在节制朴素的语言中含有无限的生发性。《毛诗序》继承《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把儒家经典《诗经》分为“六义”,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赋比兴是作诗的方法。而在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中,比、兴尤其是“兴”,都是要利用不同事物间某点相类似的关系,连类比物,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这类似于艺术思维中的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语言运用上,也产生以有限的语言追求无限生发性的效果。《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它的语言简洁、质朴,但是在那简练的语言中却能令人想像或体验到说话人的神态或语气,具有体会不尽的深长的韵味,有无限的生发性,具有写意的特点,简洁质朴的语言直接通向的是诗。儒家以经典立教,以经典为文学的最高标准,《论语》历来被视为古文的典范,其特点势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儒家的语言审美。
阿城领悟了儒家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对有限的语言所具有的无限生发性的审美追求,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一种有益的尝试:抛弃人们运用得烂熟的语言,重新使用最质朴节制的语言,企图恢复语言、事物的质感,让人们回到原初,以最质朴的形式重新感知世界,恢复世界的生动性,从而使语言产生无限的生发性。
阿城在他的创作谈中强调了“质感”这个词。他说插队十年“我得到的知识很少、概念很少。完全是跟环境、跟人这种质感的接触”,“现代人,也许中国人非常愿意用
概念,过多的使用概念就会把活生生的东西和我们能够感到的更多的东西失去掉,传达不出来。”[8]阿城的文字尽量不用成语、形容词等,实际上是在力图避免文字及事物质感的被遮蔽。成语、形容词等等在我们越来越频繁的使用过程中,它的意义越来越被我们明晰地掌握,以至于形成类似概念式的胶着,遮蔽了我们通过语言对事物质感的真实感受与触摸,不容易产生生发性、再生性。最普通的字眼也就是最富有质感的字眼,它能够把我们重新带入到对事物的最原初的感觉,从而产生无限的生发性。阿城可谓深得其中的真谛,用最普通的字眼描绘事物的原初质感成为阿城的美学追求,而且他找到了通往这种美学理想的方法,首先就是用最素朴节制的文字,恢复事物当时的情景感,让事物自身在作者的笔下来一个明朗的呈现:
刚一进门,猛然听到一声吆喝:“起立!”桌椅乒乒乓乓响,教室里立起一大片人。我吃了一惊,就站住了。又是一声吆喝,桌椅乒乒乓乓又响,一大片人又纷纷坐下。一个学生喊:“老师没叫坐下,咋个坐下了?”桌椅乒乒乓乓再响起来。我急忙说:“坐下了。坐下了。”学生们笑起来,乒乒乓乓坐下去。(《孩子王》)
音响效果、视觉效果都非常强,可谓是一幅有声有色的画。然而绝不是一幅简单的普通的画面,它引起我们无限丰富的联想。这应该是传统诗学中的“兴”的审美手段在新文学作品中的创新。类似的情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比如:
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起他自己的水烟筒。(《孩子王》)
蹲在门槛上,已经是乡下人的习惯了,急忙捡烟的动作、抬头笑笑的动作可以理解成亲昵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讨好,这些动作都含有一些让人伤感的成分,他用最质朴的语言写出了自己当时的难以明白表达的生存状态,是用“当下感”很强的情状表现而不是使用自己的第二重叙述。
其次,阿城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人的“状态”的混沌,具有了无限的生发性。当有人问到阿城“你在小说上想表达甚么?”阿城回答“表达我的状态,把我的状态表达出来。主题是很枯燥的”,状态本身是一个难以清晰表达的事物,而且一个人可以有生活状态、情感状态、人生境界状态等等不同层次的状态,所以阿城说“状态是一团的东西,逻辑是一个线性,不能够表达它,所以好的表达方式,一定是多逻辑的,起码有两个逻辑,两个逻辑就能够参照出一个状态。一个逻辑很难说出一个状态,语言有时觉得太不够了。”[8]这种对语言的深度思考,简直是孔子“天何言哉”和《庄子》“道不当名”的新版本。人们在写作中总希望自己能够清晰地表达意义,但在清晰表达的时候已经在失去意义的毛茸茸的丰富性,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中的悖论。阿城的好处在于当他意识到不能用线性逻辑的清晰去斩断朦胧的意义的丰富性时,他干脆用最坦诚的态度,把他无力用线性逻辑表达的东西以最朴素的语言呈现出来。在写作中,阿城用大实话式的素朴节制的语言把状态、尤其是人物的心理状态情感状态的混沌呈现了出来,反而具有了很大的可再生性。我们可以看看阿城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呈现:
大约是我脸上有种表情,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我还是喜欢他的,就说:“好吧,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听过吗?”(《棋王》)
这是“我”在火车上给王一生讲故事的情景。“我”和王一生一开始不在一个状态上,“我”关注的是“我”讲故事中的“生命”状态,王一生关注的是“我”讲故事中“吃”的状态,我的反应包含了种种内容,不屑?生气?无奈?等等,但这种状态肯定是不能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的,所以阿城只说“我脸上有种表情”,而王一生那样善良的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一定也产生了尴尬,而这种状态用“尴尬”这个词来表现就把意思限定死了,没有让读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所以阿城用“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这句来表示,这句就可能包含了不仅是心理的内容,还有形体的内容,比如人在尴尬时的表情、肢体动作。接下来的一句“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这种情绪就可能包含了怜悯的?宽容的?喜欢的?等等特征,这也照样是不可能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现的,所以他只用了这一句话。而且我们从整体上看这几句话,它不仅表现的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多义性,“一团的东西”,而且他还呈现的是一个线性的情感流程,由否定状态到肯定状态,由不满到喜欢。我们看到他用短短的几句话表现了多么丰富的意义!
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汉语言与现今世界别的拼音文字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力。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区别是语体的不同,而不是语言的差异,汉语言的一些最为内在的美的因素不仅在古汉语中存在,也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对于以语言为手段为原材料的文学来说,语言的本质规定决定了汉语写作的最深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承继关系,决定了汉语写作的审美传统的存在。有才能的作家可以让已经成为历史的美的东西重新激活,并放射出灼目的艺术之光。阿城的小说语言正是激活传统,让传统获得新的生命力,熔炼或改铸出新的艺术精品的一次新颖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