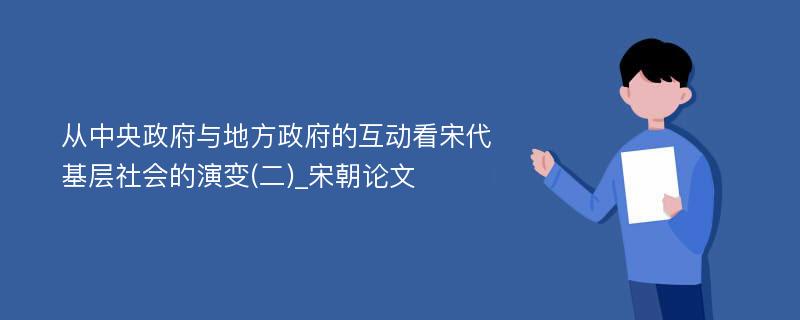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之二论文,宋代论文,基层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大量财赋集中到中央后,地方的负担越来越重。中央政府透过财政征收的手段,对全国资源独占的现象,从北宋到南宋持续增长,而且在集权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形成一种上级对下级资源独占,阶层性集权的现象。(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322页。)如此一来,使北宋原归地方财政的税款,多归入中央的岁入之中;而由地方政府征收的赋税,如商税、酒课等,则按比例由中央与地方分配。即使归于地方的收入,也要负责厢禁军、归明、归正人薪俸及地方官员馈送之用。(注:高聪明:《论南宋财政岁入及其与北宋岁入之差异》,《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225页。)在地方财政受到挤压的情况下,处于行政最底层的县府,财政的困难度是非常明显的。(注: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266—267页。如福建地区科派僧院的税目有助军钱,有圣节、大礼二税,有免丁、醋息、坑冶、米面、船甲、翎毛、知通仪从等,又增加修造司需求、僧司借脚试案等诸邑泛敷的杂税。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荐福院方氏祠堂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页。)赋税名目屡增,税额加多,不仅形成百姓沉重的经济负荷,征税也是地方官的艰难任务。州县地方官上任之后,既要在短暂的任内筹措上级政府所需的财税,又必须为地方政府本身的开支寻找财源,充实地方经建费用,十分难为。(注:梁庚尧:《宋代财政的中央集权趋向》,第561—581页。)地方政府既不易开辟新的财源,自然难以推动地方建设。彭龟年就指出:“今日之县令之所以难为者,盖以财谷之出入不相补耳,岂特不相补,直有铢两之入而钧石之出,甚相绝者。”(注:彭龟年:《乞蠲积欠以安县令疏》,《历代名臣奏议》卷259,第3385页。)理宗时,袁甫在知徽州任上,就指出所属婺源县介乎万山五岭之间,邑最壮、民最犷,而财计最耗,以至有官吏出阙,无人敢任,“县佐摄官,苟求免过,指正税以解别色,挪新钱以掩旧逋,措置既无他方,豫借是为良谋。才一二年,不知几万,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追呼而重纳产税”。为朝廷征收财税是县政的要务,都难以达成,也就没有多余的经费去推动建设,以至出现“学舍库务,几无孑遗,井里市廛,莽为瓦砺”的窘境。(注:袁甫:《蒙斋集》卷2《知徽州奏便民五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3页。)
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势,为地方势力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从北宋晚期起,朝廷不断加强财政中央化的种种措施,不免会影响地方政务与建设的推动。不过,检视相关史籍,特别是南宋的文集、地方志等资料,却会发现从北宋到南宋,江南地区各州县诸多有形的硬件建设,如城墙、官衙、学校、书院、贡院、寺庙乃至桥梁、渠堰水利等不断兴修或重建,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诗社、乡饮酒礼、法会等社会文化宗教活动及乡曲义庄、社仓、义庄、赈灾、施药、施粥、育婴等慈善公益活动也不断出现,而且愈来愈多。这些事实充分显示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建设,并不因财政中央化而萎缩、衰退,反而呈现相当蓬勃、极具活力的景象。因此,宋代官员批评宋朝财税制度不合理,强调财政中央化导致地方出现许多政治、社会难题,可能只是反映事实的某些侧面,即士人官员批判朝廷财政结构及执行偏差,造成社会失衡的现象;目的在对朝廷举措施以压力,以减低百姓负担,甚至是表达对民生福祉的关怀之情。既不能反映宋代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面貌,也不能据此认为宋代,尤其是南宋,地方经济凋敝,毫无建设。
(二)以士人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兴起
宋代各地的公共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当地的土人与富豪,而富人是主要的赞助者。宋代都市化日益发展、金融组织的发达、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促使商业活动活络、贸易勃兴;加上农业生产力与新品种、农技的发展,使得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超越前代,经济稳定成长。(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尤其江南地区,在北宋初期较宽大的财政政策之下,经济迅速发展,产生了相当多因经商致富的人。这些富人透过制度或非制度的途径,逃避或减轻赋役负担,而将所积聚的大量财富,在乡里置产,成为地主。他们期望商而优则仕,来提升家声门望,因而采取购书延聘教师等方式,积极鼓励子弟读书应举,希望下一代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即使无法达成愿望,他们仍是财雄一方的地方富豪。
这些富人家族,藉由人际网络或参与社会活动等方式,在乡里社会贡献人力、物力。经营产业有成的富人,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更藉由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家族、社群建立绵密的社会关系,以厚植社会影响力。同时也透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来提高其社会地位。(注: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278页。)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的公益活动,缓和了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注:参见梁庚尧:《南宋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梁庚尧:《南宋的社仓》,《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427—473页。)一方面也参与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效化解了因财政中央化后,地方官府无力从事建设及推动文化活动的窘境。如在明州州学、奉化、鄞县、慈溪、定海县学的兴修、重建过程中,当地富室与士族都扮演着参与或捐助的角色。其中奉化县富民汪伋、汪份兄弟最具代表性。汪氏兄弟都是陆学门人,在县府经费窘困、无力修建县学时,出资建大成殿,更新县学,重建广济桥,建造船舶,便利奉化与鄞县的交通,(注:袁燮:《絜斋集》卷19《从仕郎汪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页;参见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第657—658页。)为宋代四明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富豪在地方建设中既有参与,也有付出,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自然显露出来。
除了商业发达造就一批在基层社会贡献财力、发挥影响的富人之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大批致力举业,跻身仕宦的士人,更是基层社会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群体。宋廷在文治的政策下,透过开放式的考试制度,大规模开科取士,让有志仕途的士人进入官僚体系,并建立文官体制,尊崇文臣,使功名利禄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而通过教育是达成仕进的重要途径,于是官办的学校或私人兴建的书塾、书院都成为传递知识、学习举业的场所。朝廷又以优惠学子税役的方式促进教育的发展。加上雕版印刷发达,使书籍出版、流传更为容易。创业有成的小康之家,为了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采取种种有利于发展的策略,创造教育条件,鼓励子弟从事举业,以期晋身为仕宦之家。
在此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的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从北宋到南宋,士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其速率甚至可以用膨胀来形容。(注:参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306页;包弼德:《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47—286页;梁庚尧:《南宋的贫士与贫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6期;《南宋的贡院》,《中国史学》第1卷;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文化公司,1980年。)以福州为例,乾道元年福州解发额当为六十二人,参加解试的人为一万七千余人,次年录取进士五十二人;淳熙元年(1174)参加解试者增为两万人,录取进士者为四十二人;录取率均在百分之一以下。从这份资料和其他研究结合来看,在南宋大约超过百分九十九以上的士人,仍被排挤在仕宦大门之外。(注:参见佐竹靖彦:《唐宋期间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闽王朝の形成から科举体制の展开きで》,《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4月,第419—466页;梁庚尧:《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东吴学报》第11期,2004年6月,第189—192页;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可见读书业儒的士人在南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定期的科举考试,不断吸引着新成员的加入,使士人的阵容不断扩大,其中虽然只有少数人能当官,绝大部分的人则为谋生计,需要暂时或永久放弃举业。一如袁采所说:“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注: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当习儒业》,第105页。)他们进入职场的途径很多,譬如在商业活动中担任牙人,从事法律公证事物的书铺,甚至从事医生、工商活动等;但多数仍以知识谋生,如被延聘在书塾、书院教学,或担任启蒙工作的乡先生等。像苏州人龚明之以授徒为业,同时致力举业,为期三十余年,到八十多岁才得以特恩授官。(注: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1997年,第81—83页。)四明袁氏中的袁章、袁方、袁槱也是在大半辈子中一面教书,一面准备考试。袁章五十岁才中进士,袁章则五十六岁才举特奏名进士。(注: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宋史研究集》23辑,第485—490页。)知识成为士人的谋生工具,各有专业发展,但在科举社会中“士人”所从事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儒业,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可以突破职业樊篱与官民的界限,出入县衙。而且,由于学识相当、求学背景相同的同乡、同学交游结社,相互来往,在基层社会自然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优势群体。
中举入仕的官员更是基层社会的代言人。在众多举子竞争中,只有少数资质优异、努力不懈或幸运者,才能中举入仕,成为官员。在宋代重视文官的政治传统中,进士出身除了可望晋升高位外,也获得社会的尊崇。不过,由于官多职少,要谋求高位,也要面临许多竞争与挑战。大多数的官员只能随宦海浮沉,或在地方担任基层的亲民官、州县学教授等职,久居下僚。有的官员在此时急流勇退,回到乡里从事教学及启迪后学的工作。像开启四明学风的楼郁,中进士后在家乡教书三十多年;(注:参见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第630页。)苏州士人朱长文中进士后,以疾不仕,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并与同时退居苏州的士人崇大年、卢革、徐积等,一齐推动地方文化活动。(注: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两宋之际江西吉州士人王庭珪,及南宋中期金坛人刘宰,也都只短暂任地方官,即因与当道不合,退隐回乡,从事乡里教化与救济活动。(注:王庭珪事迹见周必大所撰《行状》及胡诠撰《墓志铭》,《卢溪文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上—12页下。刘宰事迹见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之《刘宰和赈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307—359页。)
即使是出任高官的士人,晚年也回到乡里。在官场的激烈竞争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才能卓越,或因缘际会,才得以平步青云,获致高位;即使如此,这些官员也会遇上待阙、丁忧、贬斥,甚至自愿辞官或年老致仕,而要回归乡里。从元祐起,士人因政见不同,相互攻讦,掀起激烈党争,官员或斥或用,变易无常,士大夫难以久居高位,被贬或居乡,成为常例。南宋以来,先是和战形势丕变,主政者更迭不已,等到秦桧主和专权,大肆排斥异己,异议者相继被贬或罢归乡里,像张浚、赵鼎被贬,受到牵连而贬谪归乡的官员为数颇多。(注:柳立言举出因赵鼎受牵连的南宋士人与官员达34人,见《从赵鼎〈家训笔录〉看南宋浙东的一个士大夫家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4—545页。张浚因郦琼兵变被罢,受牵连的党人也不少,见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0年,第78—79页。)孝宗即位后,独断朝政,宰职难得久任,旋即外放或罢归。可以说从北宋晚期到南宋中叶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政局变动频繁,官员除极少数人外,难以长期秉政。况且南宋以来,官多阙少的问题愈益严重,待阙的官员愈来愈多,而且年限更为延长,使得高官或名宦赋闲在家的现象相当普遍。(注:参见竺沙雅章:《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1号,1982年。)史浩即说“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像史浩、汪大猷、楼钥、朱熹、吕祖谦、袁燮等名臣,都曾长期乡居。退出朝政,虽不免难伸壮志,但他们拥有高官、名士的威望,在家乡仍是地方上领袖一方的耆老,主导或推动地方事务;而且乡贤的身份与仕宦的经验,既是朝廷了解吏治、掌握舆情的重要管道,也是地方官征询政务的重要对象。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在乡里,仍然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乡居的官员或在乡谋生的士人,都是地方的菁英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环境,举业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乡谊、同学等关系,交流互动频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但获得知识与文化,有利于举业的竞争,而且这一学习知识的氛围,使他们彼此对身为“士人”的身份有所认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虽然在科举上际遇不同,在仕途上荣枯有别;但对乡里的共同关怀,使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援引,而且习于以乡里事务为话题。一旦辞官回乡,乡里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以彼此认同的身份、共同的文化为基础,不叙年齿、穷达,结成一个群体,以诗文结社,相互游赏酬唱。更重要的,他们是地方的表率,在推动文艺活动之外,还负有教化的责任,(注: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国学研究》第3卷,第479—480页。)于是,他们或以个人或藉群体的力量,从事慈善救济、公共建设,推动公益活动或排纷解难,成为乡里长者。史浩、汪大猷、楼钥等人,先后在家乡组织诗社、推动修建学校、乡曲义庄、乡饮酒礼等公共建设和社会公益文化活动,为四明作出重要贡献。(注: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第4卷第4期,1993年,第45—93页;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其中像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社会救助活动,不仅由士人出面组织,而且有规章与制度性的管理,以及长期的运作,成为地域性的互助团体。这种经由士人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地方意识,超越个人与家族,其所发挥济世理念的群体意识,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南宋时代乡居士人、官员乃至富人,关怀乡里,除出钱出力,共同推动地方官学乃至书院的兴建外,更积极与地方长官合作,争取书院赐额。书院获得朝廷赐额,表示官方承认其地位,是地方的一项荣誉。宋代书院虽盛,但除北宋初年嵩阳、岳麓、石鼓等书院获朝廷赐额外,鲜见赐额之事。直到朱熹兴建白鹿洞书院,获得朝廷赐额、赐书之后,书院申请赐额成为地方要事。不过,在宁宗之前,宋廷赐额不多,如清湘书院前后费时数十年,到宝庆元年(1224)才获得赐额。(注:程珌:《洺水集》卷7《赐名清湘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5页。)理宗一朝书院趋于普遍,赐额数量也加多,其后更将赐额变成荣宠大臣的一种方式。从争取书院赐额的过程中,更能显示地方菁英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注:如理宗淳祐年间赐参知政事应繇为宗族子弟所建书院为翁州书院,即是一例,见冯福京:《昌国州图经》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下;参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第166—170页。)
地方权势之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也表现在祠庙制度上。祠庙制度,是由朝廷透过严密的审查程序,利用庙神的灵验,给予赐额、赐号,列入祀典。除了收揽人心之外,也是朝廷利用宗教,将中央的权威延伸到基层,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确立中央对地方末端控制的一项政策。据学者研究,唐、五代对祠庙的赐额、赐号并不多,民间祠庙尚得不到朝廷的正式认同。宋神宗以后,祠庙制度有进一步发展,至徽宗时期祠庙赐额的数量激增。徽宗朝祠庙赐封赐额增多的原因之一,显然与地方秩序有关。当宋金联盟灭辽,进而爆发战争时,境内又因花石纲引发江浙地区变乱,在官府无力平定乱事的情况下,地方大族起而组织自卫武力,借着神力凝聚人心,抗拒入侵者,稳定了地方秩序。于是地方豪强乃以神灵庇佑地方有功,通过州县向朝廷请求赐封,藉以保持或提高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因此徽宗一朝,祠庙赐额数量的加多,既有朝廷增强对地方控制的用意,也体现了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滋长的声势。(注:参见须江隆:《从祠朝制度的新局面来观察地域社会:唐宋变革论を考える》,日本第53回东方学会议论文,2003年11月。)
此后南宋在庙宇兴建与祠庙赐额的过程中,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共同完成是主要形式,豪民巨族的作用尤其重要。地方家族在基层社会的宗教活动中,不仅角色重要,而且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像福建莆田方氏家族自神宗元丰六年(1083)以来,特别是南宋时期,在祥应庙的赐额和庙宇重修上一直居于主导者地位。(注:参见方略:《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第646—649页;参见须江隆:《从祠朝制度的新局面来观察地域社会:唐宋变革论を考える》。)其他地方大族在南宋推动建庙与申请赐额上的贡献,韩森教授(Valerie Hansen)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不拟赘述。(注: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皮庆生在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这一方面也有深入的探讨。)除民间神祠外,也有地方豪族为自己祖先立庙并向朝廷争取庙额,嘉定二年,鄞县人汤建中等地方人士,向宋廷请赐予政和年间废湖为田的楼异祠为丰惠庙,此事显然与其孙楼钥的角色有关。(注:王元恭修:《至正四明续志》卷9,《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页下。)理宗绍定年间,程珌辞官回休宁后,在家族中倡议买地立庙,祭祀程氏先祖程灵洗,并以保障乡里有功向朝廷申请赐额,获得“忠壮”的庙额。(注:参见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家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台大文史丛刊之124,2004年,第60—61页。)
从地方大族为民间神祠或家族祖先立庙,争取赐额、赐号,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的延续性,而地方大族则在筹措经费、组织信众、兴建庙宇、举办庙会、申请赐额等活动中,主导推动,活动频繁;反之,对于官方祀典的神灵,其参与程度则有衰微之势。这种现象也说明地方势力借着争取本地祠神信仰合法性的同时,发挥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注:参见皮庆生:《宋人的淫祀观——宋代祠神信仰的合法性研究之一》(未刊)。)
乡居官员、士人等地方乡贤,在基层社会既有积极参与建设、教化的活动,也有凭借威望、权势,勾结官员,唆使胥吏,侵夺官府或民众财物,为祸乡里的现象。这种例子在宋代典籍中颇多。如孝宗一朝曾任次相的大臣洪适在告老返乡后也曾侵占墓地,辟作园圃,以致遭人控诉;他甚至谋图将城旁的州学旧址作为园圃,遭到知州王十朋的拒绝。(注:何晋勋:《宋代士大夫家族势力的构成——以鄱阳湖地区为例》,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6月,第57—59页;《盘洲文集》卷7,四部丛刊本,第6页;《宋史》卷38《王十朋传》,第11882页。)淳熙二年,观文殿学士钱端礼也被检举“居台州,挟持威势,骚扰一郡,营治私第,凡竹木皆自取于民”。(注:《宋会要·职官》72之12。)朱熹记录他在南康军任满前,处罚违法士人及胥吏包庇的案件时,有人告诉他犯者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注:朱熹:《朱文公政训》,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6页。)袁采也记载地方豪强违法乱纪的事例,说:“居乡曲间,或有显贵之家,以州县观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资之家,以贿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势之时,州县不能谁何。”这些人在乡里把持短长、妄有论讼,或结集凶恶,强夺财物,侵占田产,州县不敢治罪。他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却没有办法,认为不必穷治,只好期待报应。(注: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小人作恶必天诛》,第87页。)到宁宗时期,平江府昆山县所辖的地区仍见豪民怙资凭强,轻死犯法,或慢令县政,致使“役次难差”,形成治安死角。嘉定十年宋廷分创嘉定县以后,在官府努力下,情况才获得改善。(注:《请创县省札》,收入范成大编:《吴郡志》卷3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2页; 参见方诚峰:《统会之地:县学与宋元嘉定地方社会秩序》(未刊)。)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法律诉讼的势力,都为地方豪右武断乡曲所致,是基层吏治纷扰的所在。(注:参见陈智超:《南宋二十户豪横的分析》,邓广铭、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8—266页。)
地方大族倚仗权势甚至也干预地方政务。像苏州地区聚居许多衣冠侨寓的士人官员,习于干请,被认为是地方难治的根源,因此,乡居高官“不入州县”或“不造官府”,还特别受到表扬。(注: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国学研究》第3卷,第479—480页。)
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乡居官员、士人或富豪,由于角色扮演的差异,形象有别。有的被乡里或官府视为排难解纷的长者,有的则被当作武断乡曲的豪横。(注: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这种看似对立的类型与评价,其实都显示他们在基层社会拥有政治权力、人际网络、经济资本和教育文化资源,既协助官府,也代表地方,扩充自身的利益。因此,既可在不同的场域看到他们的身影,也可以从不同立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他们领导或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是势所必然的。在宋代,由于财政中央化日益加强,使地方权势之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宋代财政中央化发展到极端,却造成地方财力的不足,地方官难以推动地方建设,加上宋廷对地方官员回避和轮调制度的实施,不仅扩大胥吏在基层政治运作的影响力,也让代表地方势力的社会菁英,得以藉由推动公益活动、公共建设乃至争取寺庙学校赐额等机会,介入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这些制度与运作的发展,说明宋朝在推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由于内外情势的转变,使原有的规划发生变化。到南宋,以地方菁英为主的地方势力,逐渐彰显其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
四 结论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从政治社会的互动情况,我们看到赵宋君臣鉴于前朝的教训,运用各种方式,建立有利于中央与皇权的统治体制。一方面,将乡里虚级化,使县成为行政基层单位,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亲民官,负责催税劝率、民讼刑禁等政务,使中央的政令得以贯彻。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央统治力,在县一级设置巡检、士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及藉由职役的负担,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这种统治方式,其影响之深广,是以往朝代无法比拟的。此外,宋廷在推行重文政策的同时,也强化忠君思想,藉由科举考试,拔擢了大量士人担任官僚,成为伸张皇权、贯彻国家意识的利器。不过,到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境内治安问题与社会秩序日趋严重,而国防军备仍不能松懈,正规军既无法兼顾地方治安,于是由当地人维持地方秩序的现象就愈趋明显、重要。而自庆历、熙宁以来教育日益普及,读书识字的士人日益增多,使得士人与官僚,逐渐形成地方上的菁英群体;商业活动的发达,也造就了许多创业有成的富人。地方富豪、士人、官僚乃至胥吏,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在地方事务与建设中,逐渐扮演重要的角色。
宋朝的财税制度配合集权体制,明显呈现中央化的趋势。到徽宗时期,由于朝廷推动各项耗费巨大的事务,需财孔急,急切地向地方征收财税,不仅使财政中央化的情况十分明显,也造成过度役使民力的现象,引发方腊等规模大小不一的民乱。在变乱中,地方豪族藉助神力,凝聚人心,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借机向中央争取寺庙赐额、赐号。另一方面,由当地人为士兵、弓手,担任基层武力的体制也告确定,人数增多。这些现象,都说明宋初设计要强化中央权威的各种措施与制度,随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增强,到徽宗一朝,在形式上可以说是中央化最强的时候。然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基层社会转变之时。长期酝酿、蓄积、培养出以士人为代表的地方菁英,与财富雄厚的富豪、熟悉业务的胥吏等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地方财政窘困的时候,出钱又出力,协助官府推动地方建设及推行教化的工作,在国家权力向基层延伸的时候,出面协调与配合,使基层政治顺利运作。地方势力既适时地提供了财力与人力资源,填补了州县政府的不足,在基层社会中自然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群体。
南宋时代,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更为明显。宋廷南迁以后,凭借东南半壁江山,长期与强敌相抗,地方乱事增多,社会治安及法律经济等问题层出不穷,困扰地方政府;朝廷财政支出不断膨胀,只得利用各种名目加强征收,造成地方政府征税的压力与财政的窘困。这些现象都使得地方官员对地方的依赖加深。地方治安既是由当地人所组成的弓手、士兵来维护,地方事务也要借重担任职役的吏员来执行,而且业务日趋专精,胥吏取代职役,成为在基层社会介于官民之间实际操持业务的群体。此外,地方建设和地方教化更需要仰赖以乡居官员、士人和富人所形成的权势之家,共同协助,于是地方上出现以个人或透过家族间组成不同形式的群体,在书院、贡院等地方公共建设和乡曲义庄、社会救济等公益活动,配合官府活动贡献心力,乃至主导具地方色彩的诗社及乡饮酒礼等文化活动,并共同争取书院、寺庙的赐额及举办宗教活动。地方权势之家与朝廷命官的州县长官,共同合作,相互交流,一齐推动地方政务,成为基层社会政治运作与人际网络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中央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政策,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中央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中央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士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中央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体制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官员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中央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官员、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官员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警察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政策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地方行政长官——知县的重要性。即使由于他们个人的贤愚、贪廉之别,对地方吏治造成极大的差异,而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