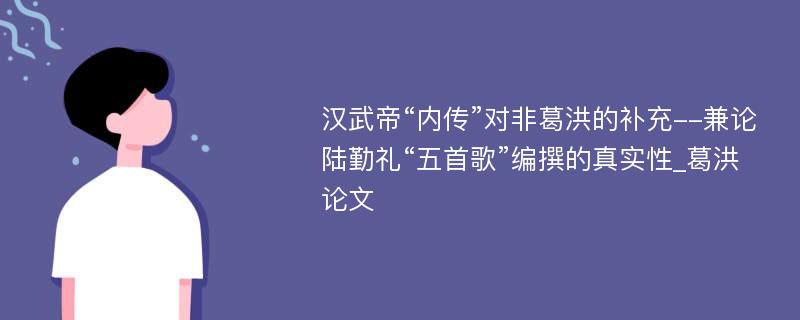
《汉武帝内传》非葛洪之作补证——兼论逯钦立辑录五首葛洪佚诗的真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武帝论文,之作论文,真伪论文,葛洪论文,兼论逯钦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对道教和道教文化的偏见,以余嘉锡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两晋之交的葛洪善于作伪①,《汉武帝内传》(以下简称《内传》)就是葛洪虚构伪托之作。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葛洪和以《内传》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杂史杂传小说研究的日渐深入,《内传》非葛洪之作的证据也越来越多,结合从《内传》与《抱朴子·内篇》、《神仙传》的文本比较中发现的一些新证据,余嘉锡等人的论断应该重新反思和辨正。
《汉武帝内传》又称《汉武内传》、《汉武帝传》。就文献记载看,《齐民要术》卷十、《三辅黄图》卷三已有征引,说明此书写成于唐前。唐宋时期的史志目录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等均有著录,但都未署明作者;一些小说总集如《续谈助》、《类说》等亦不署作者姓氏;唯唐人张柬之《洞冥记跋》(《续谈助》卷一引)称“葛洪造《汉武内传》”,日人藤原佐世(唐昭宗时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著录《汉武内传》二卷,亦云“葛洪撰”②。明清以来,关于《内传》的作者,众说纷纭,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班固说。明清刊本如《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墨海金壶》等大都题汉班固撰。李剑国认为“盖误传班固作《汉武故事》,又连类而及《内传》”③。
2.葛洪说。清代学者孙诒让《札迻》卷十一据唐人张柬之的《洞冥记跋》,谓此书出于葛洪依托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据《洞冥记跋》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记载,认为此书为葛洪撰⑤。逯钦立据而认定其中所载《法婴玄灵之曲》二首、《上元夫人步玄之曲》一首、《四非歌》一首为葛洪手笔⑥。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同之⑦。
3.王灵期等上清派人士说。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经过详尽细密的分析考证,认为《内传》的成书与上清派道士有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撰人⑧。台湾学者李丰懋进一步从王灵期的才学志向、师承渊源、造构经目及流传情形等四个方面来论证《内传》是王灵期等上清派人士造构上清经时的产物⑨。卿希泰先生也根据《内传》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认为“此书作者当为早期上清派道士”⑩。
4.原始作者为周义山之门徒,后经楼观派道士的加工与增饰。王青在小南一郎、李丰懋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内传》作者“把上清派祖师级的仙真王子登贬为西王母侍女”、“陶弘景作为正统的上清派道士在编写《真诰》时无一字提及《汉武帝内传》”等疑问,认为《内传》“不是嫡系的上清派道士所作”,它反映的是上清教派的前身即其南渡以前的教团活动,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而是屡有增饰;其原始作者当是周义山之门徒,后来在楼观道内传播,并经过了他们的加工与增饰(1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没有直接指明撰人,但推测了此书作者的时代,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1.东汉人所作。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说:“《内传》作者已难考知,然产生时代却有迹可寻,我以为时在东汉末年至曹魏间。”(12)但并未作详细论证。
2.六朝文士所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下》云:“《汉武内传》,不著名氏。详其文体,是六朝人作,盖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据张华《博物志》、郭璞《游仙诗》、葛洪《神仙传》文字与本书有相合处,以为“其殆魏晋间文士所为”(14)。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汉武帝内传〉校勘记序》则据《内传》与《汉武故事》、葛洪《抱朴子》相涉处及用《洞冥记》文,认为“大约东晋以后浮华之士造作诞妄”(15)。
3.唐人所作。北宋晁载之在《续谈助》卷四《汉孝武内传跋》中,根据宋代流传本《内传》卷上末有唐天宝五载终南山道士王游岩跋语,遂以为“此书游岩之徒所撰也”。南宋张淏《云谷杂记》卷二引韩子苍语亦云:“《汉武内传》盖唐时道家流所为也。”但正如李剑国先生所说:“《内传》著于《隋志》,引于《齐民要术》,其出唐前无疑。”(16)宋人所谓唐人所作之说显然不能成立。
虽然《内传》的确切作者与作期尚难论定,但经过学术界的反复论证,目前,《内传》为六朝人所作的提法基本上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六朝人所作”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葛洪、王灵期等上清派人士、周义山之门徒、楼观派道士、无名氏等,究竟哪一个是《内传》真正的作者?《内传》是否确为葛洪著述?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一辑录的五首葛洪佚诗,是否确为葛洪手笔?又据陈国符先生考证,“《汉武帝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17),这一论断能否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如前所述,由于张柬之《洞冥记跋》和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都有葛洪撰《内传》的记载,所以清代以来,孙诒让、余嘉锡、逯钦立等人都认为《内传》为葛洪所作。对此,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并不认同,认为张柬之系据葛洪《西京杂记跋》而误记,故葛洪依托之说也不可靠(18)。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以《内传》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杂史杂传小说研究的越来越深入,尤其是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真第四章为《〈汉武帝内传〉的形成》)、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其第二章为《〈汉武内传〉研究——〈汉武内传〉的著成及其衍变》)以及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等专著的问世,使得葛洪造作《内传》的疑问越来越多:
其一,据小南一郎、李丰懋等人考证,《内传》所记载的“灵飞六甲十二事”系统的道书经籍,两晋时期基本上是在上清派道士手中传授,且与《紫阳真人内传》、《真诰》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等的记载大同小异;《内传》的内容与《茅君内传》有密切关联(如其中的诸天妓乐等片段有明显的因袭痕迹),整体采用古上清道经《消魔智慧经》的服食说;《内传》的行文风格与《真诰》、《紫阳真人内传》、《茅君内传》等十分接近,所以,《内传》的成书与上清派道士有密切的关系,李丰懋明确指出《内传》乃王灵期等人造构上清道经时的产物(19)。今按:小南一郎等人的结论切实可信,基本上排除了葛洪造作《内传》的可能。因为据陶弘景《真诰》卷十九《真诰叙录》以及《云笈七签》卷五李渤撰《真系》等记载,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南岳夫人魏华存等众仙真下降,将清虚真人王褒所授“上清”众经三十一卷并诸仙真传记、修行杂事等传授于弟子杨羲,杨羲用隶书写出,再传于许谧、许翙等人,此后又辗转相传,流传甚广,于是,一个以皈依上清经箓为标志的新道派——上清派渐次形成(20)。但是,陶弘景《真诰叙录》明确记载,“《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364年)”(21),此时葛洪已经去世,所以根本不可能参与《内传》的敷演造作(22)。
其二,据王青先生考证,《内传》可以看作是一次传经仪式的实际记录,文中提到的《五岳真形图》、“灵飞六甲十二事”、《消魔服食经》、《四极明科经》等多种道经符图,除《五岳真形图》外,其他几种,《抱朴子·内篇》根本没有提及,说明葛洪对这一系统经籍很不熟悉,所以葛洪造作《内传》的可能性极小(23)。小南一郎也认为“灵飞六甲十二事”的传承,是“寻求中国西部神山的大概是起源于中原地带的”另一个传承,这与“主要是在江南发展起来的《五岳真形图》的传承”形成了对照(24)。今按:王青、小南一郎等人的观点对于论证《内传》非葛洪所作很有说服力。众所周知,葛洪是道教史上有名的目录学家,所撰《抱朴子内篇·遐览》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记载了葛洪所见的所有道书经籍,“灵飞六甲十二事”等不被著录,说明这几种道经确实属于另一个传承体系。同时,由于受家世、师承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魏晋时期江南土著的学术传统,在葛洪身上有明显的体现,作为两晋之交固守江南学风的土著士人(25),其不熟悉或拒绝接受来自北方的另一种传承,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灵飞六甲十二事”等道经在《抱朴子·内篇》中根本没有提及,说明葛洪造作《内传》的可能性确实很小。
其三,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通过纵向考察汉魏六朝杂传小说文体形态的历史变迁,认为《内传》“是神仙道教的教理神谱形成期急于向世人宣传的作品”;“中国自有小说以来,未尝有如《汉武内传》那样,对一代雄主采取如此神仙式的居高临下的叙事角度。汉武帝于此已脱去帝冠龙袍,西王母、上元夫人与他的关系已变作天仙与俗物的关系”;“《汉武帝内传》的靡丽辞采,当非写《抱朴子》、《西京杂记》的葛洪的手笔,《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宏景《真诰》体格相同’,是有眼光的”;“西王母、上元夫人出场,群仙数千随行的那副排场,尤其是仙人名目繁多的头衔,如上元夫人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箓者’之类,也是被人称为‘神仙家之汉学’的《抱朴子》作者不敢设想的,这大概是《四库全书总目》称《内传》与《真诰》‘体格相同’的原因”(26)。赵益在系统考察六朝神仙传记的发展演变时也说:“从《列仙传》、《神仙传》的较简短叙事发展到上清系诸真传记的长篇描述,从单纯的仙人故事发展到越来越着重于人物的修道历程与修道进阶乃至更多教义的记述,可以明显看出新道教义理化的痕迹和发展趋势。最重要的是,叙述者已经从《列仙传》、《神仙传》的教外人士转向了教内之人(无论是刘向还是葛洪,他们严格上都属于教外之士,与上清经传的作者迥然不同),从而在撰作缘起、叙事角度乃至深层动机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仙传再也不是单纯证明‘仙道不虚’的工具,而变成了喻教乃至布道传教的重要手段。”并且认为:“当神仙传作品越来越倾向于某种特殊内容时,也就是当其突破了‘史传’的内容属性而增加其世俗性及宗教虚构性内容时,一言以蔽之,亦即当神仙传作品呈现出‘小说’的面貌时,其内在结构便随之而发生变化。……而《汉武帝内传》则是这一过程中由内容变化而引起结构突破的最典型例子。”(27)今按:学界普遍认为《内传》具有明显的小说结构与虚构性内容等文本特点,这也是《内传》非葛洪所作的重要证据。因为就现存著述看,葛洪有相当自觉的著述意识,治学态度也比较严谨,其著述一般有自叙,说明撰述缘由及编撰体例,而且一旦引用别人的言论,一般都注明出处。又据《神仙传序》(28),葛洪编集《神仙传》,是因弟子滕升之问,有感于“刘向所述,殊甚简略”,所以“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不难看出,《神仙传》旨在证明“仙道不诬”,又以典籍所载与先师耆儒之言为依据,所以不允许随意虚构敷衍,不论写作意图还是文本特点,都与《内传》明显有别,二者同出一人之手,显然不大可能。
其四,在深入探讨《内传》与上清派关系的过程中,学界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陶弘景作为正统的上清派道士,在整理编撰《真诰》时竟无一字提及《内传》;在梁以后的上清派经籍记载中也不见《内传》的影子(29)。今按:陶弘景在著述中不提《内传》,也是《内传》非葛洪所作的旁证之一。据《梁书》、《南史》以及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等记载,陶弘景笃信神仙道教,也十分尊崇葛洪,他“年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梁书·陶弘景传》),此后不仅增补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而且撰著《抱朴子注》二十卷,由此可见葛洪及其著述在陶弘景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据王家葵先生考证,在陶弘景整理的《真诰》中,有不少文字直接引自《抱朴子·外篇》,而且直接借用《神仙传》中的人物杜撰若干炼养口诀,对“道”的本体的认识,《真诰》与《抱朴子·内篇》也有一致之处(30),这说明早期上清派道士杨羲、许谧等人和陶弘景都比较重视葛洪的著述,并适当予以引用和借鉴。如果《内传》确为葛洪所作,《真诰》偏偏对文体风格更为接近的《内传》绝口不提,显然不合情理。
其五,陈国符先生根据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以及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的韵部分合,结合《内传》中韵文的用韵情况,得出“《汉武帝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的结论(31)。又张华《博物志》卷八所载“汉武帝好仙道,西王母七月七日夜漏七刻乘紫云车来”云云,与《内传》相合;郭璞《游仙诗》之六“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与《内传》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语也相合。如果确如《四库提要》所言,《博物志》和《游仙诗》乃承袭《内传》之语,那么《内传》原始文本的出现应在东晋初年以前,葛洪所作之说也难以成立。
总之,虽然目前关于《内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但是综合各家之说,葛洪造作《内传》的可能性极小。
《内传》非葛洪所作,还能从《内传》与《抱朴子·内篇》、《神仙传》的文本比较中发现更多的证据。
首先,《内传》大肆渲染的西王母会汉武帝传说,《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都只字不提。
与其他仙传相比,《内传》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在传统的西王母会汉武帝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增饰,构造新的传经神话。与《博物志》和《汉武故事》等作品的同类记载相比,《内传》中西王母的形象、西王母侍女的名称以及诸仙真侍女的服饰都更加具体,而且增加了传授经籍的情节和诗歌互答的内容,其文本主体围绕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授武帝道经,以戏剧模式层层推进,把仙界领袖与人间帝王的一场会晤渲染得绘声绘色,极具戏剧效果(32)。但是,在葛洪亲自撰述的《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中,却从未提及西王母会汉武帝这一传说故事,《内传》的主角之一西王母以及上元夫人、青真小童等重要仙真,在葛洪“抄集古之仙者”,旨在证明“仙道不诬”的《神仙传》中也没有任何踪迹。胡孚琛认为:“葛洪在《内篇》的写作中,参阅和征引了前代流传下来的数以千计的仙经符书,继承其师传和道统,采撷前人成说,汲取汉魏以来方士修仙理论和方术的精华融入魏晋的神仙道教之中。”(33)但就在这样一部集战国秦汉神仙思想和方术之大成的道教典籍中,仅在《仙药》、《杂应》、《登涉》等篇共四处提到西王母(34),而且与汉武帝没有任何联系。在《论仙》篇,葛洪广征博引,反复论证神仙实有、神仙可学的观点,针对秦皇汉武的求仙不获,葛洪从君主存在本身与“仙法”相矛盾的观念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了帝王学仙的可能性。为了探究汉武帝学仙失败的现实原因,葛洪反复提到与汉武帝往来的方士如李少君、栾太、齐少翁等人的事迹,但从未提及西王母等仙真降临授经之事。与之相应,在《神仙传》里被提及的帝王中,汉武帝出现的次数最多。虽然武帝本人《神仙传》未立有专传,但在卷二《伯山甫传》,卷三《王兴传》,卷四《刘安传》,卷五《泰山老父传》、《巫炎传》、《刘凭传》,卷六《李少君传》,卷八《卫叔卿传》、《墨子传》等篇章中,都有武帝的名字及其求仙问道之事,然而其中从未涉及西王母等降临授经之事。学界普遍认为,《抱朴子·内篇》与《神仙传》相辅相成,后者所传述的神仙事迹,处处都在为前者“长生可致,仙道不诬,神仙可求”的基本思想服务,而且是自成体系的神仙传说,并非只是零散的仙真传闻的汇集。尽管由于《神仙传》版本流传等原因,《抱朴子·内篇》与《神仙传》在有些事实的记述上也存在矛盾和差异(如李阿、李宽、李八百事),但二者对神仙事迹的记述仍有不少重复,《神仙传》中有相当多的神仙,如魏伯阳、沈羲、王远(王方平)、玉子、卫叔卿、壶公、费长房、蓟子训、介象、王仲都、李阿、赵瞿、李少君等,又见于《抱朴子·内篇》,这表明它们在神仙传说上有着共通的基础(35)。正是基于这一文本特点,《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都未提及西王母会汉武帝这一传说故事,就为我们推断《内传》是否为葛洪之作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总之,对于西王母会汉武帝这一传说,《内传》大肆渲染,《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只字不提,三者同出一人之手,显然不大可能。
其次,《内传》多处引用佛教术语,明显杂糅佛教思想,而《抱朴子·内篇》论神仙道教之事,无一语涉及佛教,基本保持着中国本土宗教的民族文化风格(3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内传》“窃取释家言”,小南一郎亦称“《内传》的文章可见到几处直接受佛教影响的词语”,并附注云:“例如‘十方’的方位计算方法,‘五浊’之人的说法,以及‘身投饿虎’等用语,都是易见的例子。”(37)就文本内容看,《内传》确实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大,并且大量使用了佛教术语。如上元夫人一见武帝即云:“五浊之人,耽湎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五浊”即佛教所谓“五浊恶世”,佛教认为尘世中烦恼痛苦炽盛,充满五种浑浊不净,故有此说(38)。此外,《内传》还用“乱浊”、“尘浊”、“臭浊”等术语指称人世,用“下土浊民”、“淫浊之尸”等指称汉武帝,显然也是由“五浊恶世”引申而来。又如《内传》表示空间方位,前后四次使用“十方”一词:
侍者天皇扶桑大帝君,及九真诸王,十方众神仙官。
上元之官,统领十方玉女之名录者也。
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于玄都之墟,迎女于昆阙之中,位以仙官,游迈十方。
然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39)
佛经称东、西、南、北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十方”(40),《内传》的空间方位观念,与中土传统的“四方”、“六合”或“八方”不同,显然也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内传》使用的佛教术语,还有表示时间观念的“劫”或“万劫”,如西王母罗列的仙药中有“空洞灵瓜,四劫一实”,《上元夫人步玄之曲》歌辞曰:“挹景练仙骸,万劫方童牙。”“劫”为梵语“劫簸”(kalpa)之略,佛教认为世界经历若干万年就毁灭一次,重新再开始,这样的一个周期为一“劫”(41),一“劫”包括“成、住、坏、空”四个时期,叫做“四劫”。“万劫”犹如“万世”,形容时间极长。《内传》中提及的仙果珍肴,如三千年一结实的仙桃、万载一生的八陔赤薤以及四劫一实的空洞灵瓜等等,都有超现实的生长周期,用“劫”或“万劫”来计量时间,无疑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此外,《内传》中西王母与上元夫人讨论武帝的求仙志向,还引用了佛经“身投饿虎”的典故(42)。总之,《内传》铺陈敷演的虽然是道教的传说故事,但在行文过程中又大量借用佛教术语,说明其作者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既是《内传》的文本特点之一,也是判断《内传》是否为葛洪所作的重要依据。
葛洪有无佛教思想,王明先生曾有专文予以探讨,认为“葛洪神仙道教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里并无佛教思想”,“葛洪的一生,初则醉心儒学,继则提倡神仙道教。为了大力宣扬神仙道教,长时间从事搜罗丹方和制炼金丹,并且精研医药学,撰成巨著。主要原因,道与佛的信仰宗旨相连,神仙道教刻意希求长生,佛教则主张涅槃无生,兼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礼俗亦与佛家相抵触,所以他对于佛教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43)。王先生的论断,在胡孚琛的专著《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作为国内第一部以《抱朴子·内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书全面探讨了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渊源、内容及历史特点,在论及魏晋神仙道教与佛教的关系时,胡氏认为“葛洪著《抱朴子内篇》论神仙道教之事,竟无一语涉及佛教,这说明至少在葛洪在世时,佛教对神仙道教影响还不大,当时的神仙道教还没有积极吸取佛教的宗教形式”(44)。从文本内容看,《抱朴子·内篇》确实没有引用“五浊”、“十方”、“身投饿虎”等佛教术语和典故,“劫”字共出现五处(见《畅玄》、《微旨》、《遐览》、《自叙》等),但均与“劫盗”、“抢劫”之义相关联,与佛教表示时间观念的“劫”迥然有别。值得注意的是,《抱朴子·内篇》之《对俗》篇说“布施”求报,不算善事;《地真》篇又详细论述“守一”之法。汤用彤先生在论述《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时认为,《太平经》中的“布施”与“守一”似均受佛教的影响(45)。但据王明先生考证,“布施”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引《诗》及《文子·道原篇》,葛洪所谓“布施”不求报,“当属道教积善修仙的固有思想,与佛教无涉”(46)。关于“守一”之法,卿希泰等先生认为源于《老子》的“得一”、“抱一”和《庄子·在宥》的“我守其一”的思想,其后“守一”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重要的修炼方术,《太平经》对此有反复论述,“葛洪的一和守一思想乃是对这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47)。
王明在探讨葛洪有无佛教思想时,还提出《神仙传》卷四《阴长生传》载阴长生诗云:“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48)其中的“五浊”显然是佛教术语。对此,王先生认为“盖或偶用释家个别术语,只是表示避世遁俗的意思”。事实上,《阴长生传》载诗之“委放五浊”一语,并不能成为判断葛洪有佛教思想的确证,原因有三:其一,就今传诸本《神仙传·阴长生传》的文本看,其中“阴君《自叙》云”之后的内容(包括阴君诗三篇),疑为后来所增补,因为此传开始介绍阴君的籍贯出身,然后叙述其学仙求道的经历及“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的结果,紧接着交代了其著书情况以及葛洪关于“神仙实有”的感慨。按一般史传的体例,传文应该至此结束,但此后又附录了阴君《自叙》及其诗三篇,末尾又云“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与前面所说前后矛盾。传文之所以不合体例且前后矛盾,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其后半部分为后世所增补,因为葛洪本人擅长著述,且被干宝誉为“才堪国史”,一短篇传记不可能出现如此多的低级失误。其二,阴长生其人,《抱朴子·内篇》之《对俗》与《金丹》篇均有记述,《金丹》篇云:“近代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诗及丹经赞并序,述初学道随师本末,列己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余人,甚分明也。”(49)这段记载与《阴长生传》互相印证,说明葛洪《神仙传》原始文本中确有《阴长生传》,当无疑问;今本《阴长生传》所附阴君《自叙》及其诗三篇如果为后人增补,当是据《金丹》篇所述按图索骥,如果这种推论成立,阴君诗之“委放五浊”云云,当非葛洪《阴长生传》原本内容;退一步讲,即使阴君诗三篇为葛洪《阴长生传》原本所有,也只能说明阴君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神仙传》仅仅是照抄原文,并不能说明葛洪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不辑录为葛洪佚诗,是有道理的。其三,《太平广记》卷八引录《神仙传·阴长生传》全文,其中“委放五浊”一语,明钞本作“悉放五经”(50);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三《阴长生传》此句又作“委放五经”,则“五浊”又作“五经”,联系上下文,“五经”比“五浊”更符合文意,如此则与佛教无关。
总之,就现存葛洪的著述看,其思想体系与佛教并不相协,也无一语涉及佛教,说明《内传》的作者绝不是葛洪。
第三,《内传》与《抱朴子·内篇》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也有明显的区别。
就文本内容看,《内传》主要借西王母会汉武帝的故事论述修道养生之方和道经道法之传授事宜。在西王母告诉汉武帝的修仙之方中,除叙述其师元始天王所言守三一之法外,还详细论述了诸种不同层次的仙药及其功效。《内传》将药物区分为太上所服、天帝所服、飞仙所服、地仙所服四个等级,包括植物、矿物、动物等不同的种类。太上所服之药指生长于仙界的金瑛夹草、广山黄木等,以天界仙岛的天然植物及动物药居多;天帝所服之药指生长于灵山圣地的奇珍异兽所形成的药物;飞仙所服之药包括人工合成丹药和仙岛所生仙药两类;地仙所服之药为人间常见的养生药物,大都属于草木药。总体来看,《内传》所谈的药物,以仙岛自然形成的植物、动物、矿物药为主为上,以人工合成丹药为次,以俗世常见的草木药为下。与《内传》相比,《抱朴子·内篇》则非常重视人工合成的金丹大药,在《金丹》篇,葛洪从企求修炼成仙的现实愿望出发,反复申述只有金丹大药才是上品神药:“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51)在《仙药》篇,葛洪还按照自己的思想将各种所谓仙药分为若干层次,认为“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52)。与《内传》所载仙药相比,《仙药》篇所载以《内传》所列第二等以下、属于人世间所见所有之矿植物居多,显然较为低下(53)。从文本体现的叙述视角看,《仙药》篇所述局限于现实世界实际存在的矿植物,而《内传》却超越了现实,扩展到了想象中的仙界。对于被人称为“神仙家之汉学”(清人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撰写神仙传记都要讲究出处和依据的葛洪来说,《内传》仅凭想象罗列的仙界神药,显然太不切合实际了。总之,《内传》与《抱朴子·内篇》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有明显的区别,这也是《内传》非葛洪所作的重要证据。
综上所述,《内传》大肆渲染的西王母会汉武帝传说,《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都只字不提;《内传》多处引用佛教术语,明显杂糅佛教思想,而《抱朴子·内篇》论神仙道教之事,无一语涉及佛教;《内传》与《抱朴子·内篇》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也明显有别。这些文本方面的依据和前人发现的种种疑问相辅相成,足以证明《内传》绝非葛洪之作。
葛洪是两晋之交著名的道教学者,《晋书》本传称誉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据《抱朴子外篇·自叙》、《晋书·葛洪传》、《道学传》等记载,葛洪著有“碑、颂(《晋书》本传“颂”作“诔”)、诗、赋”百卷,说明葛洪也有诗歌作品传世,但至今已散佚殆尽。
葛洪佚诗,前人共辑有五首。明人冯惟讷《诗纪》卷三十二、近人丁福保《全三国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五辑有《洗药池》诗一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一又据《汉武帝内传》补辑四首:《法婴玄灵之曲》二首、《上元夫人步玄之曲》一首、《四非歌》一首。
《洗药池》诗辑自《金陵玄观志》,诗前有序云:“池在赣州兴国县,洪过境,见山灵水秀,遂结庐筑坛,凿池洗药,留四言诗一首。”全诗仅四句:“洞阴泠泠,风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长荣。”(54)逯钦立《晋诗》卷二十一说:“诗殆后人伪托。”然未加论证,也未言所据。徐公持《魏晋文学史》认为:“葛洪晚岁由建康赴广州罗浮山炼丹,途经赣州可能颇大,固不得遽言其伪也。”并且说:“‘仙居永劫’乃佛道结合之句,可知葛洪亦涉足佛理。”(55)今按:此诗可确定为后人伪托之作,理由如下:其一,“仙居永劫”与“花木长荣”对仗,“永劫”意即“永世”,正是佛教表示时间观念的术语(56),而现存葛洪的著述无一语涉及佛理。其二,在《抱朴子·内篇》之《对俗》篇,葛洪认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由此可见葛洪修道求仙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生欲望,而背离亲人、隐居山泽,显然不是他孜孜追求的仙居生活。葛洪的这种思想,可能受了司马相如等人的影响,《汉书·司马相如传下》云:“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其《大人赋》亦云:“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57)从中可见两汉以来,传说中西王母的仙居生活,并非随心所欲,理想完美,这可能也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中很少提及西王母及其神仙生活的主要原因。
由于《内传》不是葛洪所作,所以《法婴玄灵之曲》等四首诗不是葛洪之作,也无须重复辩驳。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首诗也为学界确定《内传》的成书背景与作者信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依据。首先,《上元夫人步玄之曲》歌辞有“万劫方童牙”一语,其中“万劫”就是典型的佛教术语,也是判断《内传》非葛洪所作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据小南一郎、李丰懋等人考证,《无上秘要》卷二十有《道迹经》的一条佚文,是早期《茅君内传》的一部分,主要描绘西王母为茅盈作诸天妓乐,其文本内容与《内传》中“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以下奏乐、唱歌一段基本雷同,有明显的因袭痕迹(58),这一证据与道经传承、服食观念以及传经风格等方面的证据相结合,说明《内传》的成书与上清派道士有密切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排除了葛洪造作《内传》的可能。
关于《法婴玄灵之曲》等四首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进一步探讨。陈国符先生根据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以及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的韵部分合,得出“《汉武帝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的结论,其具体理由如下:《玄灵之曲》“姥”、“马”二韵合用,为汉代之鱼部;二曲“歌”、“戈”、“麻”三韵同用,两汉有例,魏晋宋例多,齐梁陈隋无此三韵通用例;《步玄之曲》“麻”韵、“歌”韵同用,两汉有例,但极少,魏晋宋亦有例,至齐梁陈隋几全为“麻”韵独用;《四非歌》(又作《田四飞答歌》)“寒”、“桓”、“元”、“谆”四韵合用,即汉代之真部、元部合韵(59)。这种说法,与学界普遍比较认同的《内传》为六朝人所作的观点存在很大的距离。
事实上,根据作品文本的用韵情况推断其写作年代,除遵循某一时期诗文押韵的普遍规律外,还必须考虑到由方音等问题而造成的特殊现象。李丰懋认为:“古人用韵较宽,且江南地区并不一定与其他地区一致,何况在古声韵学史上,汉魏晋的韵部分合,常有一致之处。今即将《汉武内传》的歌辞定于汉代,自是只有部分合理,不如将其定为东晋前后、上清经编撰行世的时期,较合乎古人用韵的道理。”(60)李丰懋的观点虽然缺乏详细的论证,但是已经考虑到方音对诗文押韵的影响,而且也不断得到与之相关的音韵学研究成果的证实。周祖谟先生在《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一文中,多次提到魏晋时期以陆机、陆云为代表的吴郡人,其诗文用韵“在各部里比同时代一般的人都宽泛”,但是鱼部“模鱼虞三类分用很严格”;侵部除《广韵》侵韵字相押外,还和盐韵的“潜”、咸韵的“掺咸”、覃韵的“南潭”等字相押,这些都不是与作家审音精粗有关的偶然现象,而是与江南吴地的方音有很大的关系(61)。丁邦新在《魏晋音韵研究》一书中,根据大量资料对魏晋时期各种主要方言的特征进行详细考察,其中关于吴语的考察结果,与周祖谟的观点基本一致,如鱼部中“鱼”韵分用,“模”韵与“虞”韵同用;侵部与“盐”韵字“潜”通押;歌鱼二部音值接近;真元二部音值接近等等(62)。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赤松祐子详细地考察了《真诰》的诗文押韵情况,结果发现“《真诰》虽然成书于南北朝齐梁之间,但其中的韵文则呈现和编者陶弘景身处的南北朝时期那种讲究的押韵风尚不同,大体上比较倾向于古代做法,而且和丁书中归纳所得有关魏晋时期的一般音韵情况亦颇为不同。该书中的各种语音现象和以陆机、陆云兄弟为代表的吴地诗人既然有很多相通之处,当是反映了吴方言的特点”(63)。《真诰》的诗文押韵之所以有吴语特征,与其原始文本的作者及写作年代有密切关系。据《真诰》卷十九、卷二十之《真经始末》、《真胄世谱》等记载,《真诰》一书虽为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整理编集,但其大部分内容为东晋兴宁、太和年间(363-371)杨羲、许谧、许翙等人的“通灵”记录。杨、许等人死后,这些“通灵”记录流播江东,历经数代,至公元5世纪末才由陶弘景编纂成书(64)。而参与降神“通灵”的杨、许等人,都是江南的土著士人,《真诰》的诗文押韵反映江南本地的语言特征,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当然,随着永嘉之乱以来北人南渡的历史越长,北方文化与南方本土文化的融合越来越深入,尤其是南齐永明年间(483-493)沈约等人发现四声,提出声律论之后,对诗文押韵的要求就更为严格,这可能就是《真诰》的用韵和南北朝时期那种讲究的押韵风尚不同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陈国符总结的《内传》韵文的押韵特点,与丁邦新和赤松祐子考察所得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也几乎完全一致。具体来说,《玄灵之曲》二曲的“歌”、“戈”、“麻”三韵同用与《步玄之曲》“麻”韵、“歌”韵同用,正与赤松祐子所列吴语特征的第一条“歌戈麻三韵同用”相符;《玄灵之曲》的“姥”、“马”二韵合用即歌鱼二部上声同用,与丁邦新总结的“歌鱼二部音值接近”和赤松祐子总结的第七条“鱼虞模三韵跟歌韵通押”也完全相合;《四非歌》的“寒”、“桓”、“元”、“谆”四韵合用,与丁邦新总结的“真元二部音值接近”和赤松祐子总结的第十条“真谆欣文痕魂韵同用,山仙元先韵同用,而且这十韵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同用”也基本相合。总之,《内传》韵文的押韵特点,与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几乎完全一致,结合《内传》的行文风格与《真诰》、《紫阳真人内传》、《茅君内传》等十分接近,《内传》的成书与南方神仙道教上清派有密切的关系等已有的结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内传》的诗文用韵同样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其作者应该是魏晋时期的江南士人。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关于《汉武帝内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但是综合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对西王母会汉武帝的传说只字不提,《抱朴子·内篇》无一语涉及佛理,对所谓仙药的认识和等次划分与《内传》也明显不同等文本方面的依据,可以推断《内传》不是葛洪所作。逯钦立《晋诗》卷二十一辑录的五首葛洪佚诗亦非葛洪之作。《内传》的诗文用韵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吴语特征,陈国符关于“《内传》韵文于汉代出世”的结论值得商榷,不能作为判断《内传》写作年代的确证。
注释:
①洪业即云:“我看了《抱朴子》全书,知道葛洪是个博学能文之士,同时也知道他是个妄信、妄说、妄引、妄辩之人。”余嘉锡论及《西京杂记》时也说:“其书题为葛洪者本不伪,而洪之依托刘歆则伪耳”;“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徐公持、程章灿等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详见洪业:《再说〈西京杂记〉》,《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9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07-1017页;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07页;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中国文化》第9期,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93-96页。
②[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丛书集成新编》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76页。
③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④孙诒让:《札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1页。
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32页。
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093页。
⑦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文史》第三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3-54页。
⑧[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420页。
⑨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76-85页。
⑩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三),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43页。
(11)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
(1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197页。
(1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14)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6页。
(15)钱熙祚:《〈汉武帝内传〉校勘记序》,转引自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第1131页。
(16)以上俱引自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第197页。
(17)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1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372页。
(19)参[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1-359页;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76-85页。
(20)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第102页;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1)[日]吉川忠夫等编:《真诰校注》,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2页。
(22)关于葛洪的年寿及卒年,史籍记载不一,《晋书·葛洪传》等称葛洪享年八十一岁,当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引袁宏《罗浮记》称葛洪享年六十一岁,当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笔者通过详细考辨《神仙传》、《世说新语》、《高僧传》、《晋书》、《道藏》以及敦煌遗书等所载有关葛洪卒年的各种文献,认为葛洪实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岁。详参丁宏武:《葛洪卒年考》,《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3)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
(24)[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8、359页。
(25)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361-381页。
(26)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9、100页。
(27)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7、214页。
(28)此《序》严可均辑《全晋文》不录,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据《汉魏丛书》本补入,文刊《文史》第三十七辑,1993年。
(29)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
(30)王家葵:《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195页。
(31)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第126页。
(32)详参王青:《〈汉武帝内传〉研究》,《文献》1998年第1期;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第214页。
(33)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34)《仙药》:“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杂应》:“或问辟五兵之道……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登涉》:“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艺文类聚》卷九十八引《内篇》佚文云:“火芝常以夏采之,叶上赤,下茎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随风上下,往来东西。”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6、270、304、360页。
(35)参[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第244-246页;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第188页。
(36)王明:《葛洪有无佛教思想的探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第72、73页。
(3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3页;[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第273页。
(38)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第二》:“诸佛出于五浊恶世,所谓劫浊、烦恼浊、众生浊、见浊、命浊。”(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卷,台北:世桦印刷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7页)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二卷,第348页)
(39)王根林等校点:《汉武帝内传》,收入《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147、148、152页。
(40)宋子璿集《首楞严义疏注经》卷四:“阿难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方位有十,流数有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九卷,第885页)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二卷,第272页)
(41)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三十八:“时中最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念,大时名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五卷,第339页)《慧苑音义上》曰:“劫,梵言。具正云羯腊波,此翻为长时。”(转引自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13页)
(42)佛经关于“舍身饲虎”的记载有异,据北凉高昌沙门法盛译《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梁释宝唱等辑《经律异相》卷三十一等,舍身饲虎者为乾陀尸利国王太子栴檀摩提;而据《贤愚经》卷一《摩诃萨埵以身施虎缘品》以及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等,其人又是释迦牟尼的前身大车国的第三王子摩诃萨埵。萨埵王子舍身饲虎之事,在后世大乘佛教里评价非常高,天台、华严、法相等宗都有引用,与尸毗迦王割肉济鹰,都被作为“布施极限”的代表。
(43)王明:《葛洪有无佛教思想的探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
(44)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抱朴子内篇〉研究》,第72、73页。
(4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3、75页。
(46)王明:《葛洪有无佛教思想的探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
(47)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125、311页。
(48)此处引文据《太平广记》卷八引录《神仙传·阴长生传》,《汉魏丛书》本与此全同,《四库全书》本则大同小异,“委放五浊”作“委于五浊”。详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3-55页。
(49)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7页。
(50)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5页。
(5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0、77页。
(5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96页。
(53)萧登福:《〈汉武帝内传〉中所呈现的服食与养生思想》,《中国道教》2009年第4期。
(54)引文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页。
(5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511、501页。
(56)僧肇《注维摩诘经》卷六《不思议品第六》云:“截人手足,离人妻子,强索国财,生其忧悲,虽然有目前小苦,而致永劫大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八卷,第383页)
(5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92、2596页。
(58)[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第386页;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第28-31页。
(59)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第126页。
(60)李丰懋:《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第34页。
(61)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7、107、110、114页。
(62)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英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65种,1975年。转引自[日]赤松祐子:《〈真诰〉诗文押韵中所见的吴语现象》,见徐云扬编:《吴语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5年,第332页。
(63)[日]赤松祐子:《〈真诰〉诗文押韵中所见的吴语现象》,见徐云扬编:《吴语研究》,第329-344页。
(64)王家葵经过详细考证,认为《真诰》的撰著年代在齐建武三年至永元元年之间(496-499)。详参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210-214页。
标签:葛洪论文; 汉武帝论文; 汉朝论文; 五岳真形图论文; 抱朴子论文; 神仙传论文; 陶弘景论文; 博物志论文; 上清派论文; 道士论文; 王母娘娘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