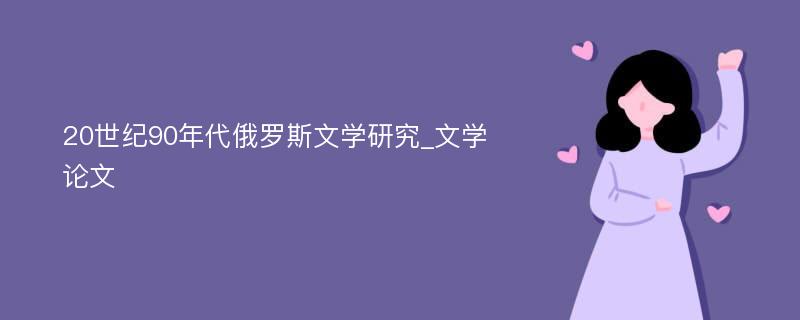
九十年代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面对较为浮澡的社会心态,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显示出一种比较成熟的冷静务实的姿态。在学术著作出版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有一些扎实的新意迭出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些以中青年学者为撰写主体的成果表明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仍充满着活力,并在一系列重要的领域中有了新的进展和开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以俄罗斯文化为大背景来研究俄国文学。文化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有意义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学以文化为根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以往俄苏文学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甚少,任光宣的《俄国文学与宗教》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这两本著作的出现,显然很有意义。
任著选择了俄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论述对象。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过特殊的作用。宗教和文学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某些相通,各国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几乎都与宗教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俄国文学更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任著以周密详实的论证阐明了宗教对俄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及其消长的过程,论及了古罗斯的多神教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关系、基督教的传入和俄国笔录文学的产生、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和仿宗教文学、古代俄国的世俗文学、俄国文学中的宗教自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果戈理的宗教意识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与宗教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任著的第一章仔细分析了古代罗斯的多神教信仰以及它与民间创作的关系,并据此批驳了某些神学家为突出基督教的地位而故意否定多神教对罗斯文化的影响的论调,以及某些斯拉夫主义者无端抬高古罗斯的多神教文化的作用的做法。第八章则从一个侧面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人和神人”的问题。作者认为,陀氏创作所研究和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基督教意识里的人;陀氏在文学形象中所表现的人性恶,是基于作家对人的本性中恶以及由恶导致犯罪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源于基督教的善恶观;基督教的“原罪”论认为人生而有罪,陀氏也认为人的本性不可能是理性的,人的非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并主宰人的行为;但陀氏又认为人生是向完美的一种不断的运动,生活的深刻本质在于爱,爱的力量能驱走并战胜恶,这种认识导致了他的“人神”和“神人”的观念:“人神”是具有人性的神,是超人,是恶魔,是反基督者,而“神人”是具有神性的人,是理想的人,能拯救人类;陀氏作品中的“神人”形象是与基督相象的形象,他们与基督相比,神性不足而人性有余,这些人物为了成为真正的基督那样的“神人”,就要沿着基督的路走下去,完善自己的道德,这就是陀氏笔下的“神人”形象的深刻内涵。结合陀氏创作实践而展开的这些论述富有新意和力度。而且可贵的是,书中的论述都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在“后记”中谈到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期间,“跑遍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各个图书馆、书店;与众多的学者、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参观了东正教堂和寺院,倾听了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对俄国文学与宗教联系的看法”,而后才着手进行研究,该书的学术价值也正是由此奠定的。作者用全书的一半篇幅(前五章)深入分析了十七世纪以前俄国文学与宗教的种种联系,这是中国学者过去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很值得重视。
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虽然是作家研究,但就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作家的创作和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关系这一点而言,它与任著在方法论上有接近之处。一位评论者曾这样指出文化阐述对于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作家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乃是俄罗斯社会思想和俄罗斯文化思想的一个独特的来源和宝库。不论在普希金和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谢德林、尼克拉索夫和冈察洛夫、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中,还是在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涉及到了那些牵动时代发展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基本问题”,“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文化的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困惑、犹豫和矛盾、所走的曲折、复杂和独特的道路,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来阐释陀思妥耶斯基的创作经历及其作品”。〔1 〕何著的特色不在资料的详实,而在视野的开阔、架构的严整和论述的深入。作者的目光关注着陀氏但又不囿于陀氏,如他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大地孕育了陀氏的生命、个性、思想及整个创作,对陀氏的探寻,同时也就构成了对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寻访。全书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完成这种寻访的:陀氏的文化心理构成、陀氏与宗教、陀氏与城市、陀氏笔下的家庭等范式中的文化隐喻内含、陀氏与“西方”、陀氏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与陀氏、陀氏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等。这里不妨也选择宗教这个角度,来看看何著架构的严整和丰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宗教”这一总题下,作者从三个角度切入:(一)宗教特质:1.人道宗教——( 1)原罪说,(2)救赎论;2.民族宗教——(1)神圣君王,(2 )神圣人民,(3)神圣民族,(4)神圣使命。(二)宗教皈依:1.道德需要——(1)外在认识,(2)内在渴望;2.情感需要——(1 )受虐快感,(2)心灵解脱。(三)宗教影响:1.地狱与天堂——(1)魔幻世界,(2)启示世界;2.炼狱——上帝与魔鬼的交战;3.耶稣原型的变体——(1)救世者基督,(2)历难者基督,(3)真纯者基督。 凭借这一构架,作者层层深入地剖析了陀氏宗教意识的性质、形成原因,以及对创作的影响,揭示了陀氏宗教意识与俄罗斯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这部论著中还相当清晰地显示出作者进行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和扎实功力,不少章节都贯穿了作者以陀氏为基点对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思考。
二是对作家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俄国经典作家的研究上。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可推汪介之的《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和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两书。
尽管近年来我国读者对高尔基的热情似乎有所下降,但是研究者仍以科学的态度并根据新发表的档案材料进行着切实的研究。汪介之的著作就是明显的例证。此书沿着高尔基一生创作发展的轨迹,考察了各个时期作家的思维热点和创作内驱力,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作家创作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以及作家艺术风格的演变。这本突破以往批评模式的著作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高尔基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可以看看其开首的一章。这一章似乎只是谈了高尔基创作的分期问题,但是它却是全书的逻辑起点和论述基础。作者首先列举了以往高尔基研究中依据不一(或依据描写对象的变化,或依据体裁样式的更迭,或依据革命发展的阶段等)的一些典型的分期方法,指出了它们的不科学性,以及对我国一般读者认识高尔基的误导。而后,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建立在“外部条件与主观因素兼顾,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的分期方法。作者认为,从1892年至到1907年是高尔基创作道路的第一阶段,“人应当成为人,也能够成为人!”是这一时期高尔基创作的核心内容,社会批判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其作品的基调高昂;1908年至1924年是第二阶段,这时期高尔基转入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提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重大课题,十月革命后又进而思考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其作品的基调清醒,风格沉郁,是高尔基创作最辉煌的阶段;1924年至1936年是第三阶段,回眸历史、探测未来是高尔基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其作品的艺术视野开阔,历史感强烈。这样的新的分期方法为作者随后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诸如《母亲》不是代表高尔基的最高成就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的基本主题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而不是“新人”的成长等,作了有力的理论铺垫。此外,书中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分析也值得注意。《不合时宜的思想》曾经被苏联高尔基文献档案馆封存了70余年,八十年代末在苏联重新面世后立即受到中国研究者的关注。除了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外,该书中的有关评述可以说是比较严肃而全面的研究了。作者从高尔基的“论著本身出发,联系它所由出现的社会背景和作家思想发展的实际进行考察”,并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高尔基所提的问题尽管具有尖锐的现实性和论战倾向,但他思考的重心是革命与文化的关系;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他对十月革命的立场,首先是一种文化的、道德的、精神评判的立场,他是出于对文化命运的担心、对革命本身命运的担心而发言的;他的全部观点又是以他对俄罗斯民族历史、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特点的理解为基石的;他的全部贡献与失误,全部清醒与偏激,都来源于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痛苦而不安的爱”。可能会有人对该书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本身的价值和魅力。
屠格涅夫是一个广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俄国作家,八十年代孙乃修的著作《屠格涅夫与中国》梳理了屠格涅夫在中国的接受史。但是,时至今日,能够称得上从作家作品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屠格涅夫的专著,国内似乎还只有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一书。这部著作涉及了屠格涅夫思想和创作的方方面面,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作家的艺术风格的探讨。例如,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样式、叙事角度和结构安排,关于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的诗意的“瞬间性”、叙事时间的“断裂”和“抒情哀歌体的结构”,关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及其美学原则等,都颇有新意。朱宪生近年来在俄国作家专题研究上化了不少功夫,在这部著作出版后两年,朱宪生还推出过一部名为《俄罗斯抒情诗史》的著作,这虽然是一部风貌独具的文体史,但是纵览全书,不难发现其基本上由重要的抒情诗人的专论串联而成,而这些专论中不乏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介绍和评论,如关于丘特切夫和费特,关于“白银时代”的诗人(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本文将在下面专题介绍)等。
三是对俄国“白银时代”(1890—1917)的文学,特别是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更具力度。九十年代在这一领域中已有多部著作问世,如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和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等。此外,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和刘亚丁的《苏联文学沉思录》等著作中也均有章节谈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现象。
周启超的《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一书显得颇有理论气息和深度。俄国象征派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过去它被视作颓废文学而遭排斥,新时期的中国对此虽重作评价,但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却仅此一部。不仅国内如此,就是在目前的国际学术界,“对俄国象征派文学整体的艺术个性特征的‘正面考察’与‘本位研究’”,都还“处于开始的阶段”,〔2〕因此, 作者在这一学术前沿阵地所作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该书首先对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内在发展轨迹、一般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基本的哲学思想渊源等内容作了评述,而后就将重心转向揭示俄国象征派文学的艺术个性。书中搭建了这样的论述框架:俄国象征派文学的“理论形态”(“审美至上”的取向、“象征最佳”的认识、对“词语魔力”的感悟),俄国象征派文学的“艺术形态”(诗的境界、剧的特色、小说的风貌),俄国象征派文学的“存在状态”(扭曲的图象、倾斜的投影、尚待开发的一片森林),俄国象征派文学的“文化价值”(诗学的创新、文学的自觉、文化的自省)。本书的主体则是关于“理论形态”和“艺术形态”的探讨。在这两部分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俄国象征派文学创新的根本动因,象征派文学家执著于其中的诗学思想原则、美学理论轴心,他们对文学语言的创造性机制与功能的认识与思考,以及在艺术上的建树(例如,分析象征派诗歌所达到的境界,评价象征主义小说在叙述形式、结构方式和语言表现力等方面的开拓意义等)。作者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和完整的理论形态把握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可以说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郑体武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是一部论文集,它的特色不在于理论构架的完整,而在于敏锐的观察和灵动的思想。作者是国内比较早的涉足“白银时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郑著的论述重点放在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上。《俄国现代主义流变》一文就为我们系统而又准确地描述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诗坛上占主导地位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三大诗歌流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流程。这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里面有大量鲜活的诗歌例证和对作家言简意赅的评价。如文中这样谈到阿赫玛托娃早期的爱情诗歌:“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有时被称为室内抒情诗,意思是题材狭窄,远离社会生活,缺乏时代精神,爱好者和鉴赏者只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陕小的圈子。然而,这室内性是很相对的,因为诗人的诗反映的是全人类的普遍情感——爱。如果说,阿赫玛托娃谈论爱的痛苦多余爱的欢乐,那么,这也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在私生活方面有着不幸经历的女人的自白。从另一方面讲,由于具有高度的艺术性,阿赫玛托娃的诗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而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室内性的表现”。“阿赫玛托娃的才华使她的诗超越了阿克梅主义的狭隘‘车间’。她的感染力在于,她的诗表达的是活生生的人的感情。诗人既没有去史前时代寻找灵感,也没有到异国风情中获取题材。虽然使用的是狭窄的生活材料,但却为俄国诗歌恢复了澄明世界和具体形象,不但克服了象征主义的朦胧晦涩,也克服了古米廖夫的自命不凡”。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以其感情的真挚细腻,诗句的富于乐感,形式的纯净透明而具有无穷的魅力”。这样的评价是颇有见地的。郑著中还有不少视角新颖和分析入理的作家作品论,如关于勃洛克与别雷的诗歌对话,关于勃洛克的长诗《夜莺园》,关于勃洛克的哈姆雷特组诗,关于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和洛扎诺夫等作家的研究。这些评论和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这部著作(包括近年来出现的同类研究著述)为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四是继续关注苏俄当代文学,特别是解体前后的文学。九十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又陆续推出了几部苏俄当代文学方面的著作,如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第三卷和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3 〕中的当代部分、黎皓智的《苏联当代文学史》、许贤绪的《当代苏联小说史》、倪蕊琴和陈建华的《当代苏俄文学史纲》〔4〕等, 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比较全面地对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作了描述,同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苏联解体前夕的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特别是“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的问题。而张捷的专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是对这一问题作专题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一书的主要论述对象是1985年至1991年的苏联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正如作者所言:苏联文学的这最后七年“是很不寻常的七年”,“是苏联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动荡不安的七年,是文学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七年”,这“最后七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极其复杂”。〔5 〕作者首先以“文学界的‘内战’”为主轴,介绍了在这不寻常的七年中苏联文学界的重大事件、两大派的主要分歧,以及苏联文学走向终结的艰难历程。而后,作者从三个方面有重点地考察了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一是文学思潮和理论论争,特别是其中的热点话题,如关于“写真实”论和“全人类价值优先”论,关于文学“私有化”的口号,关于民族文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二是文学创作的现状,涉及了前后二个阶段的创作概貌,以及对这一时期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三是有关“回归文学”的问题。中国学者在八十年代下半期已经开始对“回归文学”进行研究,进入九十年代,在“回归文学”潮走过了兴起、高潮和逐渐回落的历程以后,中国学者介绍和研究的视角显得更为客观和全面了,张捷的这本著作就反映了这种趋向。作者首先对苏联的两次“回归”潮作了回顾与比较,然后按“被耽搁的文学”、“返回的文学”和“侨民文学”三类进行考察,涉及的作家和作品很多但又有所侧重。譬如侨民文学,作者谈到了侨民文学三个浪潮的来龙去肪,相关的数十位作家及其作品“回归”的情况,并重点介绍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的“回归”和苏联文学界的不同态度。在此基础上,作者用专节对“回归文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作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回归文学”浪潮,它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让“一大批过去被禁遭贬、流入地下和传到国外的作品回到了读者手中,使得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苏联七十余年文学发展的整个图景,其中某些有价值的作品将成为人民的财富”;它的不好的一面是“大量否定十月革命、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集中出现,无疑为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起了造舆论的作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回归文学’中那些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刚刚走完了第一圈,它们能否在文学史上牢牢站稳脚跟,似乎现在还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可以相信,真正的艺术珍品不会因为蒙上历史的尘埃而失去其价值,而思想倾向反动、艺术上平庸肤浅的趋时之作尽管红极一时,必将被时间所淘汰而沉入忘川”。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本书的特点是材料丰富,观点鲜明,不过作者较浓的感情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中的某些结论,有些提法和对有些文学现象的评价是可以商榷的。
五是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中,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无疑是最为密切的,因而它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重视。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从五四时期已经开始。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收获。出版的著作除了戈宝权的《中外文学因缘》属以往研究成果的集锦外,倪蕊琴和陈建华主编的《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王智量等的《俄国文学与中国》、汪介之的《选择与失落》和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等几本著作都是九十年代新推出的研究成果。这几部著作在文学思潮比较研究、作家关系研究和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有不少颇见深度的文字。
如果说长时期来中俄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局限在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之间的话,那么《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一书则在这方面有了突破。著名学者陈先生用“开拓性”一词来评价这部著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据我所知,苏联文学理论界没有就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他们实际上还难于胜任这个课题。我国有人对中苏文学中的个别问题作过一些比较,但系统的全面的比较研究应以该项成果为首次。它确实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程。”他还认为,该书“是文学比较研究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而由于它从两国各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探索两种文学各自发展和变化的异同及其规律性,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这足以矫正那种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断定文学的独立性的理论的偏颇。”该书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15篇文章构成,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如对中苏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的描述,对“解冻文学”与“伤痕文学”、70—80年代中苏文学的比较思考,对中苏当代文学理论异同的考察,对中苏社会主义时期诗歌发展的研究等。该书的价值就在于它首次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当代中苏文学关系这个极为重要但又缺少认真研究的领域,而且尽管是论文集但也顾及了论述的系统性。与《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同年推出的《俄国文学与中国》一书也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成果。作为一部论文集,它分别论述了果戈理、屠洛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别车杜等俄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该书论述的主要篇幅虽然仍放在前三十年,但它体现出了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研究者在中俄作家比较研究这一传统领域里的所达到的新的水准。与上述著作不同的是,李明滨的专著《中国文学在俄苏》第一次以详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了俄苏对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接受的历史,标志着中俄文学关系的双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
六是关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取得更有分量的成果。中国对巴赫金的关注始于八十年代初期。从那时开始至今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如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赵一凡的《巴赫金:语言与思想的对话》和《巴赫金研究在西方》等;翻译界还将巴赫金的一些论著译出,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九十年代,董小英、刘康和张杰等几位比较年轻的中国学者相继推出了几部研究巴赫金理论的学术著作,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这里看看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和列入“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的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两部。
这两部著作都不是全面评述巴赫金的思想和文化理论的著作。董著瞄准的是巴赫金理论的核心,即对话理论。而这一理论是当代语言学、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的跨学科命题,也是国际学术界的讨论的热点之一。选择这一课题作研究的意义和难度都是显而易见的。该书首先从对话基础、对话模式、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对话原理、对话体来源和对话生存的空间等角度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分别讨论了对话性的先决条件、叙事文本中各种对话性关系及对话性形式、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对话性原则(即“复调艺术思维”)等理论问题,最后该书对对话性的交流全过程作了描述,对巴赫金与现代小说的关系作了分析,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得失及其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该书在论证中参照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等不同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作者的视野没有局限在对巴赫金及其理论的泛泛评述上,而是努力揭示对话理论的本质,在学科研究的大背景上寻找巴赫金的位置和价值。这种开阔的视野使该书获得了较以往研究更高的学术价值。
刘著的视角与董著有所不同,它将巴赫金定位在本世纪文化转型时期杰出的文化理论家这一基点上,并由此确定了全书的基本论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转型时期的文化理论。作者这样表述道:“这个观点来自于两方面的思考。首先,我认为马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的是理论与批评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和对话性,而对话的关键是要有自我与他者两个声音。我提出一个文化转型的理论问题,正是为了确定我自己的声音,来与巴赫金的理论对话。其次,把巴赫金理论对文化转型问题突出和强调,是出于我对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化(主要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认识。我觉得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小说话语理论等等,都是他对于文化断裂、变化和转型时期的语言杂多现象的理论把握。而这种把握用来了解和认识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文化的转型也是十分贴切的。”刘著的特色与作者的上述表述是吻合的,该书在对巴赫金的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作出自己的评析的同时,十分注重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甚至还拨出专门的章节来谈诸如“狂欢节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这一类的话题。这些分析并非无瑕可击,但是它的探索精神却值得重视。董、刘等人的著作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预示着中国的巴赫金研究的可喜前景。
七是关于“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新架构”的讨论。1993年《国外文学》第四期上刊出周启超的《“二十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作了如下界定:“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它与我们习惯的‘二十世纪俄苏文学’、‘苏俄文学’以及‘苏联文学’相比,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与外延。它拥有独特的涵盖面与包容面。在时间跨度上,‘二十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1890年以来将近一百年来的俄语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出现过的全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实践。它不以1900年这一自然的纪元年度为起点,更不以1917年十月革命这一社会政治事件为界限,而是以上世纪最后十年间俄罗斯文学新格局的生成为开端,即以古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以及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新生的现代主义文学所普遍表现出的对‘文学性’的空前自觉为标志,俄罗斯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在空间范围上,‘二十世纪俄语文学’指的是运用俄罗斯文学语言、渗透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所有文学创作,它不以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现象为局限(即狭义的苏俄文学),也不等同于苏联文学(即广义的俄苏文学),而是包容着苏维埃的与非苏维埃(俄侨文学)的俄罗斯文学,还包括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运用俄语写作的非俄罗斯作家(例如,艾特玛托夫、加姆扎托夫等作家)的创作。”《俄罗斯文艺》随即对此展开了讨论,尽管讨论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它却表明中国文坛传统的俄苏文学史研究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层次。中国的研究者已经普遍意识到,有重构俄苏文学史的必要,但是这种重构并非是简单的章节调整,它也许更有赖于参与者思维定时的改变。周启超提出的“二十世纪俄语文学”概念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注释:
〔1〕见《陀思妥耶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序”(吴元迈)。
〔2〕见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的“引言”。
〔3〕该书为三卷本,总字数超过一百万, 其中论述当代苏联文学的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4 〕该书的“苏俄”之意特指五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和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
〔5〕见《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引言”。
〔6〕九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的还有一些, 此外如宋绍香的《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译著(或译文)也值得重视。
标签:文学论文; 高尔基论文; 巴赫金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读书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