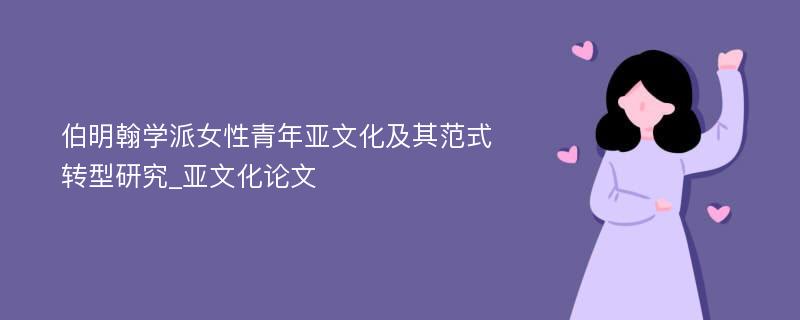
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及其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明翰论文,范式论文,学派论文,青年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按照该学派的看法,亚文化通常与种族、移民、性别、年龄与异常行为等有着密切关系(黄瑞玲,2007:77-81)。到了60年代,其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试图用来解决当时英国急剧变化的文化态势,而之前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青年亚文化自然也成了伯明翰学派研究的题中之意。1972年,伯明翰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菲尔·科恩(Phil Cohen)的文章《亚文化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y)的发表,拉开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有关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大幕。自此以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成为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标签”与重要研究项目,对整个20世纪后半期乃至如今全球的亚文化研究都影响深远。相较于之前的芝加哥学派,这一时期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摆脱了越轨社会学总是集中在犯罪、越轨等社会学领域研究亚文化的定势,而是转向媒介、消费和大众文化”(斯道雷,2010:68)。同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为英国新左派成员,因此他们尤为强调青年亚文化的阶级属性,即将研究重点放在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文化上。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会做工》(Learning to Labour)与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等都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阶级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用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男孩对不同亚文化的选择上非常合适”(默克罗比,2011:3)。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既不同意“文化与文明传统”的代表人物利维斯(F.R.Levies)、马修·阿诺得(Matthew Arnold)等人所持有的文化精英主义观点,也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贬斥为文化工业的做法,他们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通过研究杂志、电影、音乐等大众文化形式,试图发掘出大众文化的价值与能动性。但不难发现,在早期的亚文化研究中,在以“阶级”为研究关键词的时候,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憾,即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描述他人的文化预设时可能是伟大的,但在关系自身的时候,他们同样缄口不言”(罗刚、刘象愚,2003:26)。中心的早期研究者在进行青年亚文化研究时,无意识地选择自动忽略自己的男性立场,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等同于工人阶级男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女性在这里受到了忽视。她们或被轻视,或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或处于边缘地位,从未登上过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中心。 一、70-80年代中期性别进入青年亚文化研究 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其内部一直秉持着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对于亚文化抱有绝对的相信态度,认为亚文化乃是作为受支配的社会集团与社会阶级真实心声的最具反抗性的表达。这种研究范式虽然立足于英国本土“活生生的文化”,但难免在本质主义的局限下步履维艰,因为它无法从整体上对英国亚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意义作出回答。随着结构主义的强大旋风横渡英吉利海峡,其原有的思维模式与研究视角受到巨大的冲击。尤其自1970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接任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出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后,结构主义在霍尔的大力推行之下全面渗入亚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的核心词汇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该范式更多的是将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此格外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亚文化的“规训”和调整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在主体内部建构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纵观这一时期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结构主义的这一特征所规定的。此外,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涌起,范围与影响力均远超19世纪中期至20年代初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1963年,美国女性主义主义领袖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了《女性的秘密》(The Mystique of Female)一书。所谓“女性的秘密”,即是指社会使女性安于做母亲与妻子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女性在丧失个性的同时也丧失了人性。该书的观点在女性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打破了之前理想女性的存在神话,使女性主义运动进而迅速扩展为席卷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声势浩大的解放运动。而该运动对英国的影响之深,从当时英国成立的妇女组织位居世界之最就可得到明证。此次运动的中心从之前的要求获得各种政治权利转换为要求获得真正的性别平等,反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塑造,同时要求克服自身的女性气质,来发展自身的男性气质。这种思维逻辑在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中得到清晰的展现,反对女性气质的塑造成为此一阶段妇女研究小组对女性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诉求。该时期的这两种思潮,在不断渗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双重影响,基本勾勒出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图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伯明翰学派内部的女性主义研究崛起,随之在1974年宣告成立妇女研究小组(Women' Studies Group,WSG),令以前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未曾触碰到的性别命题第一次得到严肃的讨论。她们的讨论成果主要集中在1978年女性研究小组的集体之作《妇女走向前台: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Women Take Issue: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该书在第二部分着重对少女文化、被塑造的女性等方面做了重要解读。这一转向的重要意义正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在《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说的那样:“第一次,意识形态问题由于对文本的技术分析的发展被极大地精细化了。这一分析已经质疑了真理与谬误、意向性与阐释的概念。它不断地提出棘手却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二次,也是关键性的一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也包含种族和性别。现在,敌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菲斯克所说的‘白人的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加恩海姆,2005:1-6)。在这一时期,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作为妇女研究小组的领军人物,在70年代中后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性青年亚文化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中,默克罗比提出了诸多有关女性青年亚文化的问题,并尝试给予了解答。首先,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传统亚文化民族志研究、大众文化历史、个人记事和新闻调查领域,她们都是缺席的”(默克罗比,2011:1)。女性青年的长久不在场使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男性青年在几乎所有亚文化领域,不论是嬉皮文化(hippie)、朋克(punk),还是莫德青年(mods)或无赖青年(teddy boy),都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使青年亚文化从表面看来,是由工人阶级男青年一手创办的一样。这种种现象使得默克罗比提出了女孩与青年亚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女孩在青年亚文化中为什么在场却不露面,而她们又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默克罗比,2011:2)?之后她通过对十几岁少女的详细观察与深入调查,研究了女孩与青年亚文化的种种联系,从而得出了她们构造了一种不同于男性亚文化的女性亚文化的结论,只不过这种女孩亚文化一直隐而不显。其研究的两个特点可以大致表明此一阶段的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走向。 首先,默克罗比的研究一改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一直以阶级为变量的做法,将坐标明确定位于性别之上。在界定何为女孩亚文化时,她批评赫伯迪格将“抵抗”作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因为和男性青年相较,女孩们被更多的束缚在家庭和学校之中。而在这一空间之内,如果想创造出如赫伯迪格所论述的那种外在空间的“反抗”亚文化,则无疑是纸上谈兵。赫伯迪格所说的青年们在创造自己的亚文化时用日用品传达出不一样意义的做法,也不适用于少女。因为社会能够提供给她们并让她们占有这一文化形式最后予以重新创造的机会少之又少。同时,默克罗比也不同意霍尔将亚文化阐释为“为工人阶级青年(尤其是男孩)提供了一个协商他们集体存在的策略”(Hall & Jefferson,1976:47),因为这一说明带有明显的父权制色彩。按照他们这样的思路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分析,女孩永远只能旁观抑或缺席。其后在反对之前男性研究者的说法上,默克罗比提出:女孩们的青年亚文化更多地是在消费主义的洪流中创造出来的,她们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巧妙地安排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即依靠父母与老师不赞同的穿戴、化妆等消费主义的方式构建一种团体式抗拒。因为基于主流的商业利益,她们不用像男性所创造的那些诸如摩托少年、光头少年的亚文化一样,承担那样高的风险,而可以在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亚文化。 其次,默克罗比积极关注了大众文化中媒介问题与女性青年亚文化的内在联系。1977年,她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杰姬:青春期女性气质意识形态》(Jackie: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该文详细探讨了大众文化中媒介对于女性青年亚文化构建的影响。这其中不难见到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的著名观点,即女性并不是生下来即为女性的,而是在生长过程中逐渐被塑造为女性。在默克罗比看来,《杰姬》这本杂志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国家意识形态,但依然起到让十几岁女孩在文化层面上服从于主流秩序的巨大作用。阅读该杂志的活动使她们在无意识中建构了女性气质,成为了“永恒的女性”。这既为她们在日后成为妻子与母亲做了准备,同时也令她们的小团体得到了一种破坏。因为杂志明确地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所谓的女性友谊并不真正存在,女孩们的“成功”取决于找一个丈夫,同时通过种种手段“保护”她们的丈夫,让他不被她身边的女孩抢走。这所传达的逻辑,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父权制”社会的特点,女孩们并不能和男孩们一样,创造一种“哥们”式的团体性的青年亚文化。 此时不难看出,默克罗比对于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她在与珍妮·嘉博(Jenny Garber)合著的《女孩与亚文化》(Girls and Subcultures)中宣称女孩们创造了一种与男性青年亚文化截然不同的女性青年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通过女孩之间的小团体与不被学校、父母认同的消费目标而建立的;另一方面她又对女孩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小团体表现地忧心忡忡。因为在她看来,女孩们的友谊并不存在稳定性与长期性。对她们来说,只有永恒的丈夫,没有永恒的朋友。同时,这种亚文化的创立方法又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强调了她们的女性特质,使她们默默地顺从着主导的意识形态。此外,女性青少年在阅读杂志后的消费与行动,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富有自主意识的“反抗”,但从根本上却是“顺从”了主流的商业消费,被定格在“女性气质”的建立之上。因此,这种矛盾态度使得她在回答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青年亚文化”时显得颇为踟蹰。 到了8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的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之前更为深入的阶段,即在区分性别的基础上去思考不同种族的女孩们在创建亚文化时的不同。其实,种族问题在70年代至80年代前期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斯图亚特·霍尔《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保罗·吉尔罗伊《帝国反击:70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The Empire Strikes Back: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等男性研究者的书中已经得到重视与讨论,但此研究视角在当时却并未进入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可以说,以默克罗比为代表的妇女研究小组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进行有关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时,将阶级悬置的做法使其性别研究策略得到了最大化的扩展。但她们在专注于性别研究的时候将政治经济学抛诸脑后,则未免有些顾此失彼。直至80年代初期,开始有学者对中心之前的女性青年亚文化视角提出质疑,“默克罗比的研究主要关注白人阶级的工人女孩,而缺少关于黑人和中产阶级女孩的例证以供对比”(鲍尔德温等,2004:352)。有关女孩的研究这才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细化了不同种族少女的特点与差异。该转向有着显而易见的种族主义特色,以瓦莱丽·阿莫斯(Valerie Amos)与普拉蒂尼·帕尔默(Pratibha Parmer)的论文《抵制与反应:英国的黑人女孩的经历》(Resistances and Response:The Experience of Black Girls in Britain)为显著标志。在两人后来的研究中,又提出了“黑人妇女活动家自发地迫使自人妇女运动放弃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赞美,开始关注妇女的不同经历具有的影响并理解造成这种不同的政治因素”(Amos & Parmer,1984:3-19)的看法。此时,已经昭示着70年代至今的研究范式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同时预示着新的理论范式的到来。 总的说来,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是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已在文化研究中心占据领导地位时出现的。此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研究中心在霍加特领导时所产生的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使文化研究迈入了理论系统化的新阶段。在该范式影响下的WSG所展开的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分析。例如默克罗比对于杂志《杰姬》的分析,就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色彩,她详细分析了这本杂志如何令阅读者在“无意识”中完成对自身女性气质的建构,这与结构主义所持的“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它从外部构建我们的自我,使我们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所谓的主体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建构起来的”(付德根、王杰,2012:227)思路其实并无二致。但结构主义的方法也使得文化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该范式过分强调结构整体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个体经验的具体性与差异性,对个体能动的反作用视而不见。这种问题也鲜明地体现在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之中。在此时期,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着一种研究路径,即将女性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无差别的统一整体,以此来对抗男性青年亚文化所占有的绝对统治地位。虽然后期所探讨的不同种族的青年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期研究的不足,但这种衡量标准也是极其宽泛的,强调整体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学者们尤为强调青年女性所遭受到的来自男性统治的共同性,而没有考虑到女性个体之间丰富的差异性。这种显而易见的理论盲区,成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伯明翰女性主义青年亚文化研究者力图扭转的重要问题。 二、80年代中期-90年代研究范围的扩大及其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在70年代末曾踌躇满志地发表未来宣言:“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利奥塔,1996:211)。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并于80年代基本发展成熟。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70年代女性主义者反对“父权制”的呼声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打破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新倡导。新的理论转向导致了往日研究视角的巨大改观,起到了改变文化研究范式的巨大作用。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也随之改变了往日风貌。按照研究中心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的说法:“如果默克罗比和麦克卡比(McCabe)标志着女性主义和CCCS遭遇的第一阶段的结束,富兰克林(Franklin)、吕里(Lury)和史黛西(Stacey)则标志着比第二阶段更多的东西”(Brunsdon,2005:284)。在这一阶段,亚文化研究风貌与前两个阶段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前两阶段虽然有着差异,但立场并未出现很大变动,但到了第三阶段,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出现了种种需要解答的新问题,就像默克罗比提出的问题那样“当女性主义面临差异和零散化等问题时,当其作为一场普遍主义的运动却遭到那些要求指陈自身差异性的妇女的攻击时,女性主义该怎么办”(默克罗比,2011:11)?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如布伦斯登指陈的那样,主要集中在伯明翰文化研究系于1991年出版的《远离中心: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Off Centre: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这本文集中。 这本文集突出地展现了在后现代主义时代背景中,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所产生的新的张力。回顾此前伯明翰学派70年代与80年代的女性主义研究,可以说,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并不尽如人意。女性主义要求将一些属于政治领域的概念纳入文化研究之中,宣称当时的文化研究秩序压抑了女性在亚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必然会导致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既有秩序的损坏,因此遭到霍尔等人的强烈抵制并不意外。到了90年代,这本文集的出版揭开了二者关系新的大幕。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裂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弥补,它们一起探索在媒体、文化、科技等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新状况,同时也都将关注重心放在了沉默的、边缘的、个体的以及被压迫者的现实状况。此书开篇表明:“这部著作关注的是知识、权利和政治的各种形式”(Franklin et al.,1991:1)。要“批评那种因果论和铁板一块的总体性的观念,挑战那种线形的演进的历史观”(Franklin et al.,1991:5)。而这一关怀正是后现代研究的题中之意,因为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不确定性”、“模糊”、“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不可化约”等精神状态和思想品位”(冯俊等,2003:7)。不难看出,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她们不再强调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制的统一性,转而去关注每一个女性个体在受压制方面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这恰好回答了默克罗比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在后现代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伯明翰研究者们赖以建构的“阶级”在当代世界的消失以及如前所述的对于女性个体而不是群体的关注,使得这些女性研究者们不再对发展以前的“女性青年亚文化”理论有那样浓厚的兴趣,而是把女性亚文化研究转化为对女性在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新状况的关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之前的女性亚文化研究进行了反思与重建。 该书的三大主题分别为“表征与身份”、“科学与技术”、“撒切尔主义与企业文化”。虽然这三方面论述重点不同,但却明显体现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该文集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放弃了之前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第一阶段“女性应该成为男性”、“反对被塑造的女性气质”的固有价值立场。在她们看来,女人正应该成为女人,男人正应该成为男人。之前伯明翰学派妇女研究小组要求女性青年亚文化在场的呼喊恰恰体现出了男权主义的思维逻辑,而非真正对父权制的反抗。每一个女性都有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具体经验,站在每一个女性的视角上去观察、探讨女性主义与文化的影响,再建女性气质,并将之作为超越男性统治而非推翻男性统治的根本路径,才能思考在现阶段如何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或者按照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目标正是要超越“性/社会性别”的二元论,建立以多元差异为本的女性呼声(巴特勒,2009:11)。 具体来说,该书第一部分对媒体与文化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不同于之前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极度浪漫化工人阶级的文化情怀的研究视角,此时的研究者更多倾向于将她们作为文化生产者来看待,即女性在进行大众文化消费时,并不如之前所论述的只是在无意识中被主流文化所收编,她们也在消费中扮演了更为复杂的角色。例如,安吉拉·帕灵顿(Angela Parrington)立足于详细的历史分析与民族志研究方法,探索了畅销文化如何帮助英国战后的工人阶级妇女消费者,使她们能够抵抗文化社会化将她们变为家庭妇女的角色,这无疑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女性文化研究的具体应用。冯伊·塔斯科尔(Yvonne Tasker)的文章则从理论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长期以性别作为区分界线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诘问。在她看来,以往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混淆了“女性”、“看肥皂剧的女性”与“女性气质”,导致她们在研究时只去关注那些直接以女性为指向的类别,而忽略了其他对于女性文化研究更为重要的类别。第二部分借鉴了之前文化研究对于科技维度的强调,特别探讨了奥尔顿(Alton)法案旨在限制合法堕胎的意图。女性文化研究者们从此法案的国会辩论记录、法案细则、大众媒介宣传等方面的仔细阅读中找出了富有意义的争论点,将之作为探讨生育意义的斗争场域。最后一部分则把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借鉴到对当前文化研究的领域。这两部分的互相补充呈现出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在新时代握手言和的态势,较之前阶段的视角与方法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与提升。在这部分中,论文集中讨论了当代美国不发达的文化政治方面,即私人企业的意识形态问题。 与此同时,默克罗比在90年代也并未停止对女性问题的关注。90年代更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也使她认识到自己在70年代努力在亚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划分界限的做法已经过时,“亚文化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青年文化的活动范围,成了更宽泛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默克罗比,2006:200)。基于这种认识,她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了时代变化下的亚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流变上,并且积极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 在《闭上嘴,跳舞吧:青年文化和变动中的女性模式》(Shut up and Dance:Youth Culture and Changing Modes of Femininity)这篇文章中,默克罗比试图探讨在如今种族、阶级与性别意义变动的情况下,青年文化如何对这些新情况加以运用。她明确意识到了当今亚文化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性,并对过去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在我自己的早期著作里,我花了很大力气去研究青年女性在青年文化里的边缘性存在,却没有更进一步去检视她们每天的活动”(默克罗比,2006:205)。因此,她同富兰克林她们一样,反思了之前将亚文化与消费主义两者关系浪漫化的做法。她认为,早期的研究者(包括她自己)对于亚文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想法过于浪漫化与理想化。亚文化既不是对商业文化大加排斥,也不是最终通过消费丧失了自己的抵抗作用。它们之间有着远较之复杂得多的关系,亚文化可以利用消费主义,参与到亚文化中的青年可以通过销售自己的亚文化产品赚取一定的收入,并通过这种销售去抵抗国家意识形态的收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完全不必把这些活动看成是纯粹商业性的亚文化低潮,远离对传统的反抗;恰恰相反,这些活动正好处在这种离经叛道的中心”(默克罗比,2006:20)。这种想法有着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特色,为如今声称亚文化已然没落的声音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解读方式。 在这种改变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默克罗比对女性青年亚文化问题也有了新的考量。从她早期的研究中不难看出,默克罗比将女性气质的塑造视为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地位的压制,社会通过种种“罗曼斯”的描述,使她们在商业消费中进入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里,进而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但随着时代的变动,“过去那种把女性化和女性主义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式分化已经不再是定义年轻女性经验的最好方式了”(默克罗比,2006:202),也就是说,具有女性气质与选择不抵抗已经不再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了,女性气质的塑造也可以是女性主义反抗的方式。自然,女性气质的塑造途径之一——消费的选择也不再是被动消极的。90年代的默克罗比,似乎更加坚定地站到了消费主义也可以作为表达亚文化方式的一边,这与《远离中心》这本文集所表达的价值立场基本一致,展现出了90年代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面貌。通过对80年代后期取代《杰姬》杂志的《十七岁》(Seventeen)杂志的分析,默克罗比认识到,追求罗曼斯式爱情的少女肖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女性成了有人格尊严,在爱情中具有同男性相当地位的新女性。这份杂志充斥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深切影响了90年代以来女性气质的建构。 三、伯明翰学派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启示 近几十年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迅速迈进了商品经济时代,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缠绕的关系,各个场域相互影响。在这一市场化的过程之中,中国虽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不少差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了“消费主义”时代,对于物的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种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论述的主体意识建构与国家政府、学校、教会、警察等关系显然已不能用来解决这一大众消费时代的问题。因此,伯明翰学派所开创的大众文化研究,可以为我国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提供不少借鉴之处。研究界显然已经发现了这一新的视角与领域,有关文化研究的讨论在学界如火如荼,相关的研讨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召开。但对于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相较于对大众主流文化的关注,却显得颇为冷清。对于本文所论述的有关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更是鲜有关注。实际上,伯明翰学派对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知识资源。 (一)对于性别的关注: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作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路径 伯明翰学派对于女性主义的进入所抱有的始终是“不合作”态度。主要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90年代回顾伯明翰文化研究历程时还是对女性主义介入文化研究持相当大的敌视态度:“它就像一个贼在夜晚破门而入,扰乱安宁,制造了不适宜的噪音,伺机在文化研究的桌上胡闹”(Brunsdon,2005:278)。但在如今绝大部分研究者看来,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耦合对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义甚大,对于文化研究本身的父权制理论,应该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性的。但男性研究者却自始至终是抵制的,他们虽然知道女性研究者对于自己的批判,但却并未真正正视过这一问题。 中国如今对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看法已有所扭转,一大批专家学者不再认为青年亚文化是消极的、堕落的、反文化的,也不再将之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而将之作为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有关青年亚文化的重要部分——女性青年亚文化的研究,真正有价值的文章较少,也缺乏更加广泛公开的讨论。中国研究界对于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忽略的这种现状,使得由男性主导的青年亚文化有了一些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却无力从整个青年亚文化的高度去说明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从目前的形式看,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联合,为探讨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路径。 (二)文化研究介入实践:民族志与参与调查方法的借用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教育自己的学生时,用一段话概括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坐在豪华旅馆的大堂里,也坐在廉价客店的门阶上;坐在庄严堂皇的大音乐厅里,也坐在粗俗下流的歌舞厅中。简单说吧,去做实际研究,把你屁股的裤子坐脏”(特纳,2003:242)。这种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倡导去做实际的田野调查,而不是拘于书斋仅从理论上侃侃而谈。此方法被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在研究青年亚文化时所沿用,产生了一大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代表著作。如保罗·威利斯花费了3年6个月的时间做了关于学校里工人阶级男孩的民族志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学会做工》。而文化中心在女孩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方面,无疑也出色地运用了这种参与调查的方法。如默克罗比通过观察、访谈、非正式讨论、日记与深入讨论等方法探讨了工人阶级的女孩文化,显得翔实而有说服力。多罗西·霍伯森(Dorothy Hobson)详细调查了工人阶级妇女如何通过观看电视来认同自己的经历。这种将理论与深入实践相结合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无疑对女孩们所创立的亚文化有一个更为清楚真实的理解,而不总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去推断猜测被研究者所处的状态。 但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现实来看,有关男性青年亚文化的参与式研究已经初步反映在各种期刊论文上,有关女孩的却甚少出现。这种参与调查的严重缺失成为了阻碍我国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发展的一大障碍。我国许多研究者一直专注于学习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文化视角与文化批评方法,却并未得其精髓。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以对英国亚文化的实际考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如今我国一些研究者却忙于将其结论嫁接到对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分析批判上,不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去实地参与调查我国当今涌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女孩亚文化,这未免有点买椟还珠之嫌。 (三)研究视角的拓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双向应用 伯明翰学派在进行大众文化研究时,采取的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作为无意识的被动接受者,这才有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人将大众文化斥为“文化工业”之说。而按照以霍尔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中心的看法,“流行音乐、服装和电影等流行文化不但不是应该被贬抑、被批判的‘大众文化’,它还是表达阶级和世代抗争意味的‘青年亚文化’”(胡疆峰,2012:73)。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多数为中产阶级出身,而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却多数为工人阶级出身,这种阶级的差别导致了两者分析问题视角的不同。因此,尽管两者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但后者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不再从精英文化的立场将文化接受视为单向的传递过程,而是将大众视作能动的主体。在分析中,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中所蕴含的“抵抗”意味足以作为个中代表。 从我国当前实际看,学界呈现向法兰克福学派一边倒之势,仅从相关研究论文数量之大就可见一斑,但对于伯明翰学派的方法视角研究,在比照之下显得颇为冷清。这种局面与当前占我国学界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颇有联系。精英文化的观点在当今大众文化蔓延的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不论是小说网站上点击量猛增的耽美小说,或是沉迷于网络世界的网瘾少年,如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去解决,则青年亚文化势必被解读为霍尔等人所说的“道德恐慌”。这对于青年人来说是对他们心理的误读与能力的极大低估。大众文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论是生产者或是消费者,其身份都不是绝对的。两者都具有能动性。前者强调主导意识形态自上而下所起到的“规训”的强大作用,后者则论述了青年如何通过亚文化的创制表达了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或者用相同的文化制品传达出不同之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说过:“在任何时代,青年文化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埃里克森,1998:12)。而作为青年亚文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青年亚文化研究,其重要性在我国却长久未得到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反思,以便在将来对我国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标签:亚文化论文; 伯明翰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化消费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