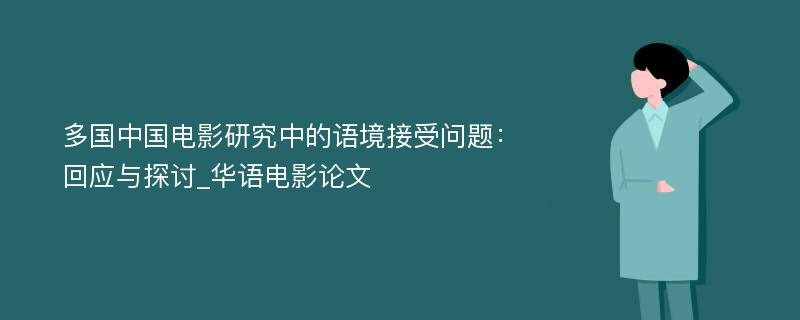
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的接受语境问题:回应与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语论文,语境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电影》杂志2014年第4期刊登了笔者和李焕征教授的访谈录。2014年第8期又刊登的几位电影学者对访谈的回应。笔者仔细拜读了这几篇回应文章,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大家开诚布公,各抒己见,理性交流,一起催发电影研究的良性互动。如果笔者对某些情况掌握得不确切、不全面,我感谢同仁们对我的提醒和纠正。谢谢编辑刘桂清老师,回应人郦苏元老师,丁亚平,李道新,石川,孙绍谊。经过这轮回应后,笔者总的感觉是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大中华文化圈内的电影史学界人才济济,成果斐然,在研究方法、课题、观点等方面不断创新,视野愈加开阔。“重写电影史”的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取得很大成就。 现在笔者想继续讨论一些有关华语电影和跨国电影的问题,以及他们和国族电影(民族电影)模式的关系。这涉及到几个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磨合、交往的问题。我提到华语电影研究的三大圈子:港台中文学术界;海外英文学术界;中国大陆的中文学术界。有时这几个学界是交叉的,因为有些学者同时活跃在几个学界里。 应当说,每个学界都有自己的学术语境、知识系谱、研究规范和文化气氛。一个理论或话语出现时,每个学界有自己特殊的反应。当某个研究模式从一个学界被传播、介绍、翻译到另外一个学界时,有时会顺利通行,有时会引起质疑、不被接受。 首先,笔者想澄清一个误解、误译。因为这个误译,导致一些学界同仁觉得我在宣讲“中国和中华性的崩溃”。没有这回事。我曾经写过一篇英文文章在美国发表。①此文的初稿被翻译成中文,最早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13卷第4期,第13—18页)。后来被收入一个文集。②中译文题目是“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其中有这么一段论述: 大中国并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殖民的、压迫的地缘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先天保守的概念。边缘地区的汉语文化生产也并非先天就是一种后殖民、反霸权的话语。电影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取决于对权力和语境的特定断想。在现存状况的背景上重新审视殖民和后殖民的老问题可能是有用的。这种状况就是,新一轮全球化已经在后冷战时期得到加强。跨国/越界汉语电影与全球化携手并进。它本来就是全球化的副产品。中文电影不仅诉诸中国观众,同时也诉诸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海外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汉语电影由此占据了一个相对于民族身份和文化关系而言十分灵活的位置。在此领域内,没有一种统治性声音。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被用于汉语电影,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按:这次新加黑体字)。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各种异质形式的众声喧哗中,每一个方言讲述者都是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言人,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现代化水平。口音的丰富多样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泛中文世界,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实体难以涵盖的不同身份和位置的集合体。世界或者天下不是一个只讲一种通用语的独白的世界。汉语电影世界是一个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领域,一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和国家关系的领域。 文中的一句话(黑体)被翻译成“这证明了中国和中国性的崩溃”。“崩溃”是误译,而且有悖于这段文字的上下文关系。英文原文是“fracturing”(fracture的动名词)。打开英汉词典,意思是“断裂”。笔者的本意是说大中国文化圈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裂缝”、“缝隙”,是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大家各有自己的声音和诉求,没有“一言堂”。可是学界以讹传讹,误解了笔者的原意。现在看来,“断裂”这词或许也没准切地表达我的想法,可能会有更切当的词。无论如何,笔者要重申:我本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华语电影理论绝无“去中国”的含义。笔者其实是在海外特定的语境中与那些持这种观点的同事和学者论争。在2013年12月上海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华语电影论坛上,笔者发言时当众澄清了这个误译。与会代表都应当听到了。会后,我和文章的译者向宇也有交谈。他也参加了会议。(向宇是译者,不是文章的同作者)在另外一篇译文中,冯雪峰同学把那段话译为:“出现在华语语系电影中的不同口音和方言无不证明了‘中国’以及‘中国性’中存在的裂隙。”(《中文电影研究的四种范式》,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第126页)这个翻译更准确、更符合原义。 笔者没有讲过“中国和中华性的崩溃”,也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里讲过“国族电影史范式的崩溃”。笔者反复强调,国族电影模式和华语电影模式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不是拿一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案例用国族电影模式分析更清楚,而有些案例用华语电影模式分析更恰当。北京大学的李道新教授也说,“华语”这个用法已经被中国各界广泛接受和使用。我再打几个比方。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播放“中国新闻”,而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凤凰卫视播放“华闻大直播”。这两家新闻的风格相当不同,观众对象也不同,但不能拿一家新闻取代另一家新闻。如果观众愿意,比如我本人,也可以两家新闻都看。我听一个同事说,在汉语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界,“华语”一词也用得越来越广泛,还有学者提出了“大华语”的概念。他正在参与编纂《全球华语大辞典》,这是中国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这个计划是李光耀向中国提出来要做的。那么未来的《华语辞典》是否要取代《汉语辞典》呢?我想不会的。国族电影与华语电影,中国新闻与华闻大直播,《汉语辞典》与将来的《华语辞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互补、乃至交叉,不是有你没我。 国族电影的核心是“国族”。国族和国族电影有其合理性。尤其当一个国家被侵略、民族被凌辱时,国族是一个神圣的东西。国族或曰“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但是,它并不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东西。它起源于近代西方。学者大多认为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最终形成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局限大家有目共睹: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界线、界碑、铁丝网)生硬地把历史上形成的族群分割、拆散。享有一个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被划分在不同的国家。华语电影和国族电影研究中遇到的语言问题上的死结,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境内和中国的周边有很多民族、语言、方言:汉语、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等等。“华语”是什么?应当如何定位呢?华语电影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当时它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岸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业界合作、电影合拍。华语的提法绕过了国族政治的尴尬,促使了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沟通和交往。二十年过去了,华语电影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问题产生了,华语的概念面临危机和挑战。它需要得到反思、发展、修正。 现代历史上,有不断的思潮和实践企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比如世界主义,世界语,共产主义,甚至康有为的大同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又一次给超越民族国家桎梏的尝试提供了新的机会。跨界的区域化出现了。欧盟,大中国经济圈,等等,便是例子。“跨国主义”呈现在各个层子和方面:经济、商业、旅游、文化,影视,等等。跨国电影现象以及伴随的跨国电影研究是合乎情理的必然产物。这里当然有美国因素,因为迄今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好莱坞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工业和发行体系。但是美国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进行跨界的文化产业整合。我得知,西安举办首届“丝绸之路电影节”,观众有机会看到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约旦、叙利亚等国的影片。这也是区域组合的一个例子。美国能主导这个区域的文化组合吗? 李道新教授说,华语电影论述是“美国中心主义”。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华语电影的概念最初在台湾的中文学界提出,如今在中国大陆的中文学界广泛展开,应当和美国中心主义没关系。就美国的情况而论,也要区别对待。美国的政界、军界是一回事,他们毫不掩饰地维护美国利益、宣扬美国价值。电影业界当然要赚钱,要尽量把生意和产业做大。但是在美国高等学府里的人文学界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文学科(包括电影研究者)的职责是反思社会。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警惕全球化给人们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抵抗任何形式的霸权和“中心主义”,包括美国霸权。西方学院里的人文学科的主流思潮是“左倾”的、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与社会的主流媒体背道而驰。不可想象哪个人文学科的老师胆敢在美国大学教室里鼓吹美国霸权主义、美国中心论。学生、学校、同事都不能接受那样的行为和理论。 从事华语研究的学者包括用中文写作的大陆学者,用英文或中文写作的香港和澳门学者,以及用其他语言写作的海外学者。一些身居海外的学者是从大陆出去的,他们有时也选择用自己本来的母语中文写作。诚然,当这些海外学者用外文著书立传时,他们要按照国外的学术规范写作和从事研究,在西方的学院话语体系内运作。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将整个跨国华语电影研究说成是“美国中心主义”。华语电影研究领域更像是一个杂糅、交融、多元、对话的场景。如前所述,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当今的美国人文学科风格,往往是要解构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包括美国中心论),抵抗各种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弱势群体和族裔。海外的中国学者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参与这样的学术语境。 在海外英文学界,跨国电影研究和华语电影研究已经广泛流行。如果这些概念和视角刚出现时还有新鲜感,现在已是家常便饭了。比如说,有个学术杂志名为《跨国电影研究》(Transnational Cinemas)。有一本书名为《跨国电影读本》(Transnational Cinema,The Film Reader)。以“跨国电影”命名的文章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有些学者会对跨国电影研究和华语电影论述提出一些质疑和建议,但是他们基本上认可这些模式的大框架,是希望这些研究模式能更加完善。 1997年在我编的一本文集中,笔者提出“跨国华语电影”的概念。这种模式不囿于国族的框架,而是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中文电影整合起来,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探讨。迄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对笔者的论述的最犀利的批评,来自任教于加拿大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的日裔加拿大学者Mitsuyo Wada-Marciano(美津代·和田—马奇阿诺)。她不反对跨国电影研究,但是她批评笔者所论述的跨国华语电影研究。简言之,她认为笔者的论述是伪装的中国中心主义。在她的书《数码时代的日本电影》(Japanese Cinema in the Digital Age,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和田—马奇阿诺教授用了不少笔墨批评笔者的观点。她写道:“的确,由民族国家疆界的构想所代表中国人或中国性的凝聚力被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统一体所隐藏或替代,即鲁所界定的‘华语电影’。”("Indeed,the territorial construct of a nationstate representing a cohesive vision of the Chinese or Chinese-ness is concealed or replaced by the higher level of unity that Lu demarcates as 'Chinese-Ianguage film.'" 第99页)。她又写道:“鲁提出的这种泛中华的种族性几近于支持在当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普遍流行的种族中心的凯旋论。”(This kind of pan-Chinese ethnicity that Lu puts forth comes awfully close to supporting the ethnocentric triumphalism now commonplace in nationalistic discourse.第100页)她还说,鲁的华语电影论述出于他“倾心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帝国,‘中国”。(a preoccupation of an indivisible empire,the“Middle Kingdom.”第101页)。意思是说,笔者的华语电影论述不但没有解构中国和中国中心主义,反而把本来分散的大陆、台湾、香港重新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中华。 在美津代·和田—马奇阿诺教授的眼里,笔者所论述的跨国华语电影研究是“泛华人种族中心主义”,是帝国情结,是大中华主义。应当指出,她对笔者的观点的理解(曲解)和严厉批判,是她的一家之言。在英文学界,笔者没有看到其他学者这么说。 李道新教授说跨国华语研究是“美国中心主义”。这就耐人寻味。一方面,在北美英文学界,日裔加拿大学者说我的版本的跨国华语话语是大中华中心主义,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在中文学界,中国大陆学者说它是美国中心主义。这两个评价完全相反。孰是孰非?华语电影简直成了变色龙,其真相因人而异。笔者不赞同这两种说法。跨国华语电影研究既不是大中华主义,也不是美国中心主义。 至于一个学者有无“自信”,好像不是学术问题。但是既然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笔者也随意回应几句。笔者如果有一点点学术自信,不是因为笔者喝洋墨水,写洋八股,在美国的所谓的强势语境下写作。我的自信来源于自己些小的中国文化底蕴。自己生长于两个皇城(西安,北京)(鲁的“大中华主义”?!),父母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中学就读于北京市第171中学。“文革”期间,笔者6岁到9岁时,随家庭去江西农村生活了三年,历经磨难。笔者的身份其实更适于民族电影研究。笔者的母语是中文,英文是后来学的,所以笔者这类学人也不应当完全划分为海外学人。我听说国内有“三自信”的说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电影研究领域,“重建主体性”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笔者无意“指导”中国电影研究。笔者目前不在中国的高校任职,没有“博导”资格,不能指导大陆学者的研究。 笔者不认同这样的二分法、二元论:一边的是西方强势话语权主导的跨国华语电影研究,另一边是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和亟待重建的中华主体性。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杂糅共生、多点多线、开放交叉的势态。李道新教授说得好,国内和海外的学者应当“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和对话”,以共同推动电影研究。 ①原文“Dialect and Modernity in 21st Century Sinophone Cinema”发表于英文网络杂志《跳跃剪接》,Jump Cut: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Media(No.49,Spring 2007)。见网址http://ejumpcut.org/archive/jc49.2007/Lu/index.html。任何读者都可以随时查看原文。此文的英文初稿也是我的书的一章。见《中国现代性和全球生命政治》Chinese Modernity and Global Biopolitics: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p.150-163. ②见陈犀禾、彭吉象主编《历史与当代视野下的中国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