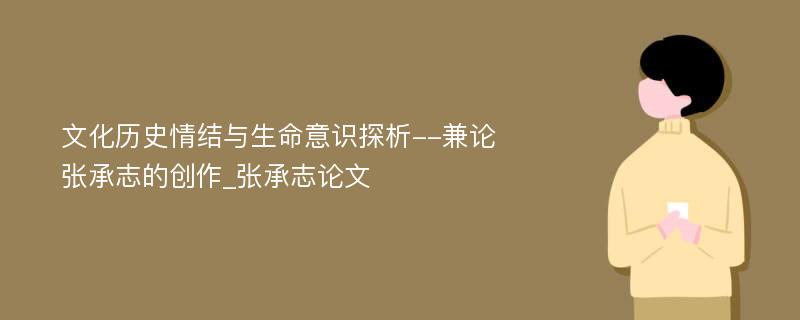
文化历史情结与生命意识的探寻——论张承志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意识论文,生命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张承志的文学审美,明显的有一个文化历史情结,即对回族的寻根与认同,对哲合忍耶宗教的倾心;张承志创作的基调和母题,是寻找苦难,探寻生命意识并企望自我的超越;张承志受儒家文化思想的浸润,他的中后期创作,有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有强烈的理性成分。
关键词 文化历史情结 生命意识 寻找苦难 哲合忍耶 形而上追求 理性成分
一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新时期文坛涌动着一股“原始主义”的文化寻根思潮。跨着奔驰的神骏在内蒙大草原、黄土高原大西北“寻找”的张承志,是令人瞩目的弄潮儿。雄浑苍莽的大草原,滚滚的长河落日,云霞明灭的长空,铁灰色的戈壁,深邃的山谷,忧伤深沉的高原古歌,在张承志的笔下升腾起无与伦比的美妙的旋律。它使人热血奔涌,感受到一股洞彻的悟性和睿智;它使人欲歌欲泣,唤起了一种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并且,由于作家在民族史、宗教史方面的知识和造诣,使得他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凝重的历史感、独特的个体情感的内审和自我肯定的历史性深化,渗透着对民族文化的哲理性思索。可是,你不能不注意: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从《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张承志永远是一个孤独的骑手。越到他后期的创作,越是一个“不屑于与俗界对话”的忧郁歌者,是一个“沉醉在一切哲学最深奥最古老的概念中的智者。”[①]毫不隐讳的说,在张承志“寻找”苦难的壮丽歌唱背后隐藏着很深很深的忧郁;有着对生灵被苦难磨砺的沉重叹息。有着对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诚挚同情,更是有着对民族历史文化所进行的解剖、分析、重构和对生命意识的探寻、还原、再造。
美国学者阿诺·理德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②]对于张承志来说,他有他那一代青年人的蹉跎岁月与迷茫,也有他那一代青年人的转折机遇与拼搏。作为回族的后代,他散居北京,又曾插队落户在内蒙古大草原的纵深,尽管一开始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不太熟悉,但内心深处潜藏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心理素质。经过多年的艰辛跋涉,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意识逐渐成熟,一种民族认同的驱动力促使他不能不把目光投向大西北、投向八百多万沉默地居住着的母族。为此,他沉雄苍凉的艺术风格的重要特点,是他主动直接地感受和复呈事物的艺术直觉能力,一种处于积极定势效应中的能够充分调动主体关于对象的全部经验和情绪,关于自身全部丰富艺术积累,以至将自己整个身心、艺术个性投入创作劳动的艺术感受和艺术知觉能力。
“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的艺术。”[③]作为拥有学者、作家双重身份的张承志来说,昨天的生活与现实的思考是严肃迫切的。他把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作为自己创作的母题与基调;他把内蒙大草原、大西北广阔纷纭的万象世界吸收到他的自我中去,以深刻丰富的内心体验,让它们充满观照和感受的活力。那种追求磨难、崇尚牺牲、探究心灵奥秘的精神境界,其实是充溢着浓厚宗教色彩与意味的。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只有在它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④]确实,只有按照黑格尔阐述的审美方式去表现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作品才会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艺术张力。
二
民族的文化历史有如一支节奏不定,变化纷繁的变奏曲,更象一种多向多层,复杂曲折的螺旋运动,它是民族魂的源泉。英国学者爱德华·B·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⑤]对张承志来说,“寻找”苦难,回归母族,是想达到对人类真善美最高境界的寻觅。纵观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从民族文化历史的角度楔入人、刻划人、表现人。即使是辽阔苍莽的自然景观,也是人化、社会化了的自然。《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抒写着他的生命意识,他的灵魂秉承着草原母亲一样的圣洁和高贵;《北望长城外》礼赞挺着倔强脖子,踏着大漠流沙大步走去的西北硬汉子;《黑骏马》讲述的是一个蒙族青年九年后重返草原去寻找心爱姑娘的悲怆故事;《黄泥小屋》铺叙在神秘宗教氛围中沉重哀伤的精灵的艰难生存;《金牧场》表达的信念是:“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心灵史》则以被人称之为“血脖子教”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几十万群众和他们的导师为主人公,揭示和讴歌了他们在非人的生活环境里与极致的政治压迫下,那种“让心先自由,让心灵痊愈,让心灵呼吸喘息,让心灵先去天国——舍了这受苦人的身子给这坑人的世道,让心沾一沾主的雨露”的深深企盼与坚韧不拔精神。维特根斯坦曾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⑥]毋庸置疑,在张承志的灵魂深处,黄土高原的大西北,辽阔的乌珠穆沁草原,那是一堆令人魂牵梦萦的灰土和令人时时企望回归的精神家园;是知青年代想挣脱出来寄身现代都市后想陷回去的记忆沼泽;是不甘失败,九死不悔追寻的“金牧场”。在艺术的感悟中咀嚼生活的苦涩,在追忆的灰土上揭开几百年来尘封的历史,那是张承志对人的生死归宿以及生存意义等等终极关切所作的思考与回答:
“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体察生活,领悟历史,琢磨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的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⑦]
张承志早期的草原小说,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同草原的辽阔、纯朴、温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赞美自然朴实的美,他崇拜生命,因为生命就是希望,而希望会升腾着诗情与理想,甚至他渴望一种承受苦难的认同与超越,期待拥有心灵彼岸的神圣与辉煌。问题在于,这种背负着人间苦难却保持着心灵的圣洁,这种化苦为乐的宗教化人格心理和生命形态,究竟是堂吉诃德式的空幻意愿抑或是对人性奥秘与生命苦难的探寻与反抗?细心考察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同归母族,皈依伊斯兰宗教,又脱离不了懦家文化思想浸润的张承志,他的全部创作凸现着强烈的悲剧感、忧患意识,充满着宗教式的乐观。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的母亲额吉,有着热爱生命、保护弱者的爱怜之心。在席卷着草原的白毛风中把毛蓬蓬的达哈(羊毛蓑衣)让给插队知识青年,却招致自己下肢瘫痪。这种承受苦难的崇高母爱和人性暖意,实则是对宗教博爱思想的褒扬,它也是作者自身生活和感情之泉酿成的醇醪。《黑骏马》古老民歌低徊悲怆的旋律,由于注入了白发老奶奶与索米娅二人生活道路的思索,升华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命运之歌。小说兼有弃恶扬善,保护生灵,主张宽恕的《古兰经》的经典教义和儒家文化思想从一而终的贞洁观。索米娅传承着蒙族老一代妇女坦诚坚韧的秉赋与性格,尽管草原上卑鄙丑恶的东西玷污过她,而索米娅饱尝痛烈的精神摧残,几遭劫难终不毁灭,并且在早熟而又强烈的母爱支撑下走过了最艰难的历程而获得了新生。忍受命运捉弄却保持心灵的高贵圣洁,为了别人的幸福却心甘情愿地走向恐怖的地狱。炼狱愈烈,信念弥坚。如此可贵的人生态度,正是千百年来草原母亲一脉相承的女性自强与尊严,熔铸着对现实的反抗与热爱生活的执着,映射出伟大母性深厚炽热的爱。坚固的沉默得到敬重与景仰,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充实的象征。寻找了九年的年青人,在超越了平凡和至善的圣像面前滚下鞍来,热烈地亲吻着苦涩的草原,渴望得到仁慈的宽恕与灵魂的洗礼,还给自己一个记忆的悲怆。
老奶奶正视生活的挫折,对人生豁达通脱的态度极具宗教性,我们可以解读到张承志所倾心的哲合忍耶教派某些精神气质。哲合忍耶教是伊斯兰教中一支极为朴素的宗教。因为贫穷,因为没有土地、没有商品市场,这个教派几乎没有固定的讲经布道的聚集地。几百年来,哲合忍耶教派的教徒们在对真主的虔诚信仰中始终体现出善良、厚道与信义。贫穷中他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拥有宗教理想,同时更拥有英勇的反抗。坚韧与流血、执着与反抗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老奶奶保护孙女和新生婴儿的生命,反对因索米娅受辱去复仇,这种独特的生活态度与民族心理,透露着忍让包括了负重。
三
《北方的河》,是张承志继《黑骏马》之后的又一篇力作。他以哲学家的抽象思辨,历史家的宏观视野赋予作品一种深刻的内涵,使小说达到了形而上的艺术层面。主人公怀着终极关切意愿,从一条河流奔向另一条河流,从一个目的地跑到另一个目的地,精神之旅永不停歇,他要去“寻找”贫脊中闪烁的高贵,枯焦黄土中埋藏的瑰宝,要去找到那个冥冥中的终点,达到与文化历史的默契对话。这个人物是《大坂》里那位青年形象的深化与发展,他不再是《绿夜》重返草原的汉族知识分子“他”。因为绿夜的草原,“生活透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可以说,《北方的河》标志着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已经由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苦苦思索,突进到将理想付诸于“寻找”的飞跃。作品是以北方的几条河作为抒情描写的客体,来袒露作者“寻找”的心路历程的。北方的河,是养育主人公的一方水土,是主人公的血脉和生命的精灵。整部作品呈现出完整的象征对应:一边是无定河、黄河、湟水、永定河和追忆的额尔齐斯河与黑龙江;一边是那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足迹。六条滔滔奔腾的大河,一个个自然景观的闪现,把主人公带入了雄壮之美的风景中,去追赶着冥冥太空的宇宙之音,给读者一种强烈的视觉感受。整部作品抒写描绘抽象成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气质,给读者以形而上知觉美的感受,主人公及其他几个人物在历史文化苦旅中苦乐得失的思索与心路变化转迹相契合相对应。所以,“北方的河”,象征着民族文化历史和人格力量永往直前,奔腾不息的历史必然;象征着破碎过而又萌发了新的希望和力量的生活。从作品强烈的人文精神、深厚的哲理意蕴,让人感受到张承志承受中西文化碰撞与融汇的痕迹。它有着对屈原上下求索精神的崇尚;更有着浮士德始终怀着崇高目标、从错误中获得教训向着更高境界探寻、追求人生真理的悲剧价值的影响。跨过混沌的历史误区,张承志带着沉重的翅膀,进行着艰难的文化历史的探索。他凭借滚滚长河,企望揭开人生秘谛,谁能说不是一种崇高圣洁的境界呢?
张承志,是一个文化修养较高的学者型作家。长年累月的东方文化精神熏陶,使他的思维火花明显积淀着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文化心理定势和认识思维机制。他把一代青年的奋斗精神表现为不断进取的求索精神、民族骨气、审美品格。“北方的河”,最终是一种华夏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合。
四
从《黄泥小屋》开始,民族血统、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感情影响着张承志转变了创作方向,他把顽强追寻的目光,投向了母族世代生存斗争的最大聚居区域——大西北的黄土高原,继续他的文化历史寻根苦旅,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精神之旅。伊斯兰教是回族穆斯林重要的精神纽带和支柱。无论在朝圣路上,在旅途中,在马背上,在黄土山坡荒野丛莽间,张承志都在揣摩体味着回族在历史进程中,与汉文明撞击与融合的心理底蕴、心灵奥秘;创作的驱动力又牵动他选择以回族的生活为题材。从而,他写出了《黄泥小屋》、《终旅》、《残月》、《湟水无声流》等小说和《心火》、《背影》等散文。此后,张承志又撰写了《金牧场》、《心灵史》两部长篇小说。
民族感情的萌动,宗教信仰的认同,当然产生于民族整体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得以诱发,就决定了张承志创作主体的知觉和行为的某种选择。怀着“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他的心中充盈着一种被宗教净化过的冲淡、静寂、平和的情感和气韵。正因为如此,《黄泥小屋》才那样从容裕如。那些“穆斯林庄稼汉”,“念想”的是一座黄泥小屋,一堆心灵净土:“真主为磨炼人们的诚心,给了人们几辈子的苦难。可是真主知道这些庄稼汉心里有处怕撞的肉,所以给了他们这种黄泥屋。若是寻不见天堂,又害怕火,主是能让他们寻一块场地的。在那泥屋里,哪怕是背着再沉的罪,也能躲风避雨。劳累了能休息,浪远了能回来。能躲在那低低的泥屋里护住自己,护住自己的心里那块怕人遭辱的地方。”张承志,经由审美文化的文学来寻找精神血缘的宗教信仰,这种文化历史的寻根苦旅,其潜意识中,有着个体对自己所从属的民族的自觉认识及民族亲近感,还有伊斯兰教文化的认同与归依,甚至也有对回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认知欲需求,当然也有对时下商品经济大潮中某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反感与对商业文学浅薄、庸俗、低下的不满。还一个高雅文学的朗照,张承志认为他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应该去迎接文化的挑战。
“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农民们在深夜和清晨进行着自我磨炼,他们沿崎岖山径挑来清净的水,再唯恐玷污地把井盖锁上;他们跑在泥屋炕上,面对黄土崖遍遍诵祷;他们长途跋涉,奔向一些谁也不知晓的荒野地点;他们避开黄泥屋里用枯叶和牛粪燃起的温暖,凿一孔孤窑于无人绝地,独身静坐,忍受寒苦,节减腹食,他们用古典调的波斯——阿拉伯语开始动情地吟诵,配以调节有法的呼吸。在高潮降临时他们获得了天上的愉悦,他们激动得老泪纵横。然后他们回到村庄,日复一日地苦苦思索着当时的感觉”。[⑧]
由此观之,张承志的黄土地小说,的确突破了他草原小说母爱的狭隘边界,已经脚踏实地地进行着宗教精神的巡旅,这是孤独漫长执拗地寻找精神血缘、人格仪范的长旅。然而,理性成分的累积,已在慢慢磨损着他艺术的触觉、审美的灵性。我们的这种审视,并非是强加与责备。我们可以从他后期创作的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明。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宣称将为自己“寻找一种方式”,寻找自己“今后存在的形式”。这种宣称与他早期强调的“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誓言,演绎成一条探寻生命意识的轨迹,其中不乏虔诚,并且存有蔑视流俗的放达和傲气:
“让激流抛弃和超越我吧,
我以真正的异端为骄傲。”[⑨]
在《金牧场》中,人物苦苦求解的是关于“黄金牧地”的残破文本,是一个劫余的穆斯林寻找天国的故事,作为故事中的故事,与套在其外层的草原牧民大迁徙的故事互为诠释,互为生发。《黄金牧地》的文本,是整部作品中所有其他故事的象征譬喻,因而又是作品的自我诠释。不难解读,《金牧场》中许多不同的字体,代表着自我意识和自我生命的不同层次,在通往孤独骑手、忧郁歌者的寻找文化历史、宗教意味的长旅意义上,“自我”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生命出发点。它是张承志心路历程的记录。它是一部促发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书。
《金牧场》笼罩着许多沉重的苦难意识:那些穆斯林都有渴求苦难的悲壮情感,为了体验一种超凡脱俗的崇高情感,宗教信徒们往往采取甚至消极的反抗,甘愿自虐,甚至受难。不信你看,《金牧场》就描述了殉道者的血河给作家主体的深深震撼和色彩斑斓的视觉感:“那时辰是礼邦达的时辰,满川满滩的人们都盼着死呢;那时辰殉了教门能甩手直直地进天堂!”“我不能殉了主道,我只有守在红河滩边上受苦……,主啊!”“生命,你将要开始怎样的旅程呢?……你难道不怕最终你将牺牲,最终你将成为你理想的殉物么?”
五
长篇小说《心灵史》,张承志把它作为心灵追寻疲倦后,暂时歇脚的封笔之作,他为自我的寻找、为自己倾心的哲合忍耶献上了一份隆重的祭奠品。这部记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徒们战斗和流血历史的小说,倾注着作家的一份虔诚膜拜的心血。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是他皈依宗教后,“我的文学的最高峰”的“毕生作”的大作。其中极为重要的是,文本所贯注和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精神,“让心灵渴望理解”的宗教热情、宗教情绪、宗教理想,博大深远。小说出版后,人们争相传阅,被回族抢购一空,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小说将“几十万民众把自己的故事划分在一代一代穆勒什德(导师、领袖)的光阴里”,它其实是回族民间史书体例的采用。张承志“把此书划为七代,每一代故事都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抄本作为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称为章和部”。文本有极强烈的宗教气息、宗教神秘,理性成份也陡然剧增。人们众说纷纭,引起极端反应。有的论者用“惊人的真实,惊人的偏执”给予评价。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诚然,把握历史或反映现实可采用不同的门道和途径,但文学是审美的文化,宗教是信仰的文化,他们都是根于社会存在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头脑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宗教尽管有精神鸦片的恶名,也有启迪人们经由苦难达到精神圣洁的美妙。只不过让过多的宗教教义在文学作品里演绎,会导致文学形象思维的枯竭。大西北是宗教感较强的区域,几百年来,中国回族农民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承受过大自然的肆虐,承受过外族的杀戮,还有此起彼伏的流亡似的迁徙。他们贫困落后,生产方式低下,加之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特殊,所以他们的生活板滞而苦涩,他们的文化凝滞而古朴,宗教就是加强和巩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精神膜拜更多是承受苦难。张承志的伊斯兰教的皈依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他对大西北苦难的敏感有关,还与他对生命意识的探寻紧紧相联。书写大西北回族惊心动魄的文化历史演变,挖掘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神韵和品格,尽管《心灵史》的理性增强,审美情感锐减,谁也不能忽视花了六年心血的张承志,是为了四十万哲合忍耶信徒的期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渴望,是为了民族的尊严、自强。正如作家如是说:“宗教的人是一些努力在‘圣’的空间中求存活的人,理解宗教型人类的状况及其精神,意味着人性和人道的成熟和进步”。[⑩]
张承志,与其说是提倡一种宗教式的苦难解脱,还不如说是高扬一种审美式的人生自由境界,潇洒地走向一种既现实又超现实的审美超越。
注释:
①⑧⑩张承志《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读书》1988年第4期p25—29
②《美学译文》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p10,商务印书馆1979
⑤《文化与个人》,p3,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⑥《文化与价值》,p5,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⑦张承志《美的沙漠》,《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⑨张承志《金牧场》
标签:张承志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回族论文; 北方的河论文; 黑骏马论文; 大西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