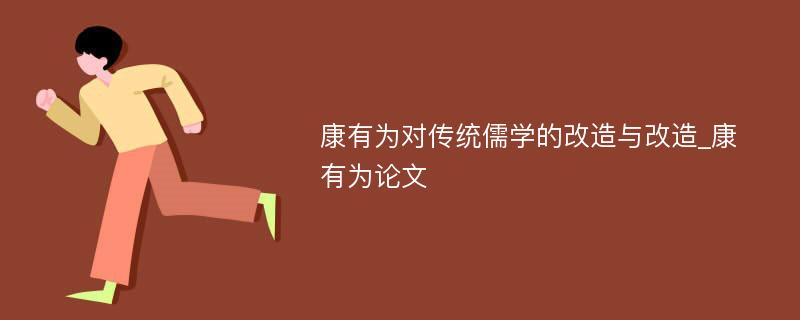
纳儒入教——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重构论文,康有为论文,传统论文,纳儒入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有为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可谓波澜壮阔,恣意汪洋,但其主体或主干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这种改造和重构,基本上是按照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条是援西入儒,推动儒学近代化。一条是纳儒入教,推动儒学宗教化。对于这“两化”,如果用传统儒学的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的话,那么前者是“外王”,旨在维新变法;后者是“内圣”,意在整肃人心。对于前者,笔者曾作过一些研究①,本文仅对后者展开讨论。
一
儒学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与历史大潮同潮共涌,互相激荡,呈现为一种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正如梁启超所言:“寝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寝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寝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②。不过,在康有为以前,儒学无论怎样演化变迁,都没有离开此岸的人文天地。但经康有为的改造与重塑,孔子寝假而为天,寝假而为神,寝假而为耶稣,寝假而为通天教主,几乎将儒学推向了彼岸的宗教世界。康有为将儒学宗教化,既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耐人寻味。
作为一代改革大师的康有为,为何要纳儒入教呢?原因固然多重多样,但择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以下三端。
一是对儒学、佛学和基督教的顿悟体察。
康有为一生治学,主要驰骋在儒学、佛学和基督教三大领域。早年时期,“予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③。1876年,康有为又拜学于朱九江门下。朱氏“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而以“发先主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于是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从此谢绝科举之文,士芥富贵之事,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④。披阅群籍,宗法今文,康有为不仅从儒学中体察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和经世致用的微言大义,而且认为,举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伦常,鬼、神、巫、祝之风俗,诗、书、礼、乐之教化,蔬、果、鱼、肉之食物,儒学几乎无所不包,是任何国家治理人民都不可或缺的信条。对此不可等闲视之,理应奉为宗教。
朱九江辞世后,康有为隐居西樵山白云洞,究心佛典,常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⑤所谓“自得”即认为:“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况又有五胜、三明之妙术,神通运用,更为灵奇”⑥。对此,梁启超曾指出:南海“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以故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⑦。康有为尊孔不舍佛,而信佛反过来又强化了他纳儒入教的襟抱和情怀。
此后,康有为又受到了西方传教士所宣传的基督教的影响。例如,李提摩太曾大谈孔教与基督教“实相通”⑧。安保乐亦宣扬“孔子基督为友”,“凡孔子之善道,基督教无不乐而扶持之”⑨。这些宣传和影响,不仅使康有为对基督教产生了误读,而且对他的儒学宗教迷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于是,康有为决心把儒学提升为宗教,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合天意,下齐民心,使儒学道统不衰,使中华民族不亡。二是对内忧外患的追根溯源。康有为是一位敏时之士,对内忧外患有着深切的体会。中法战争以后,他指出:“外夷交迫,……将及腹心”⑩。甲午战争以后,他又指出:“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11)。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他进一步指出:“瓜分豆剖,渐露机牙”(12),“诸国环伺,岌岌待亡”(13)。那么,形势为何会如此江河日下呢?康有为认为,原因就是外国有宗教,而中国没有宗教。他指出:“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14)。而现在,“彼教堂遍地,随在可以起衅,彼我互毁,外难内讧,日日可作,……而彼动挟国力,以兵船来,一星之火,可以燎原”(15)。例如在中越边界,“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16)。外国列强兵教结合,双管齐下,中国岂能抵挡。相形之下,中国不但兵弱,而且教衰。康有为分析道:中国“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大臣托于畏谨,而苟且废弛之弊作。而六经为有用之书,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17)经此比较研究,康有为最后得出的解决办法是:“扶圣教而塞异端”(18),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三是对大同世界的热切向往。
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流脉。以往学术界一般皆认为,康有为勾勒的大同世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它亦是一个宗教的理想境界。在康有为看来,在政治上可以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逐渐达到这一社会,但在精神上则必须以人们的“不忍之心”为阶梯和渡桥。因此,他在《大同书》中,反反复复地阐述“不忍之心”:“山绝气则崩,身绝脉则死,地绝气则散。然则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乎,人道将灭绝矣”(19)。“不忍之心”即“仁”,是“人道”赖以存在的基础。“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乐利”(20)。那么,怎样才能将人们的“不忍之心”和“人道之质”呼唤出来呢?康有为认为,人的仁爱精神是从“元气”分离出来的,“众生本一性海,人类皆同胞”,只因“妄生分别”,才造成了“九界”,酿成了“三十八苦”。解决之途,只有依靠宗教。也就是说,人的仁爱精神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只有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才能廓除人们心中的迷惘,把仁爱精神发挥出来。因此,康有为极力主张将孔子设为人道教或神道教,尊孔祀孔,依照孔子的仁道行事,普度芸芸众生,步入大同之境。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原因,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演出了一幕纳儒入教的活剧。
二
康有为为将儒学纳入宗教,挥毫泼墨,奔走呼号,几乎拼搏苦斗了一生。从宏观上考察,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85年至1895年,是其纳儒入教的发轫期。
经过20余年的思想酝酿和文化储备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康有为正式拉开了纳儒入教的帷幕。1885年,他“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21),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前后,又完成《公理书》、《人类公理》和《康子内外篇》等书。在前三部著作中,康有为叛逆世俗,将宗教与名、刑、礼、法相提并论,表现出了对宗教理想的绵绵痴情和强烈追求。在后一部著作的《理学篇》、《性学篇》、《不忍篇》和《肇域篇》等篇章中,他不仅高谈阔论设立孔教的重要性,而且将孔教与佛教进行比较论证:“孔教极自然,佛教极光大。无孔教之开物成务于始,则佛教无所成名也。……人治盛则烦恼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教无佛教也。……二教者终始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也”(22)。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孔教与佛教各居其位,各司其职,缺一不可,现在佛教已成,孔教焉能不设。
进入90年代以后,康有为返观历史,将纳儒入教工作做得更为扎实深入。他先后著成《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周礼伪证》、《尔雅伪证》、《史记书目考》、《国语源本》、《孟子大义考》、《魏晋六朝诸儒杜撰典故考》、《墨子经上注》、《孟子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春秋考义》、《日本书目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对孔教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其中,《孔子改制考》堪称是这一时期康有为纳儒入教的代表著作。该书从孔子创教,论及托古改制;从“万世教主”,论及大同之世;从“三统三世”,论及当代政教,以重塑孔子和设立孔教一以贯之,并对孔教的内容、形式、仪式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此,就连宗教思想极其淡薄的梁启超都不得不承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23)。
第二阶段从1895年至1898年,是其纳儒入教的发展期。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伴随变法高潮的到来,康有为亦加快了儒学宗教化的脚步。1895年5月,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直截了当地将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归结为“由于无教”;极力主张“立道学一科,……发明孔子之道”,“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并明确指出:“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藉传教为游历,可诇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24)。这样,康有为不仅将孔教思想具体化了,而且将孔教作用扩大化了。
1897年,康有为在桂林组织成立圣学会。圣学会虽为一学术团体,但却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当时,康有为目睹外教入侵,流毒四方,在《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中深为忧虑地指出:“梧州通商,教士蝟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令布濩流衍于四裔,此士大夫之过也”。因此,他所成立的圣学会,以“广大孔子之教”为旨趣,以“尊孔教救中国”(25)为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圣学会的成立,是康有为将其孔教思想付诸实践的尝试与开端。
1898年3月,康有为紧紧抓住即墨文庙被外人所毁事件,指使其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等,组织起800余人,发布公呈,广泛宣传他的孔教思想。公呈指出:“顷乃公毁先圣、先贤之像,是明则蔑吾圣教,实隐以尝吾人心,若士气不扬,人心已死,彼即遍毁吾郡邑文庙,复焚毁吾四书六经,即昌言攻我先师,即到处迫人入教,若人咸畏势,大教沦亡,皇上孤立于上,谁与共此国者?”“若大教既亡,纲常绝纽,则教既亡而国亦从之”(26)。公呈将教亡国亡、教兴国兴巧妙而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拨人心弦,极大地增强了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宣传力度。
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康有为主张设立孔教的文字,是他在百日维新期间呈递给光绪皇帝的《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该折明确主张:开设孔教会,以衍圣公为总理;由入会士庶公举督办、会办、乡办,分别管理各级孔教会事务;皇上举行临雍之礼,令礼官酌订尊崇之典;天下淫祠皆改为孔庙,士庶男女膜拜祭祀;选生员为乡县孔子庙祀生,专司讲学,日夜宣讲孔子忠爱仁恕之道;孔教会与礼部关系,如军机处与内阁、总署与理藩院之关系;厘正科举及岁科试四书文体,废除八股,为发明孔子大道开辟路径。(27)该折不仅将有关孔教的具体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将康有为的孔教主张陈于庙堂,使其纳儒入教活动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第三阶段从1898年至1918年,是其纳儒入教的峰巅期。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避居异国,遍释群籍。1900年他在槟榔屿书成《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1911年在日本写成《救亡论》、《共和政体论》,《大学注》、《论语注》、《孟子微》等书也大体在此前后完成。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心志益发坚挺。如在《共和政体论》中,他将“虚君”释为“素者,空也,素王素帝,真虚君也”(28),而推孔子为素王,为教主。如此之论,在上述著作中在在可见。
1913年,随《不忍》杂志创刊,康有为关于孔教的鼓荡亦掀起了新的波澜。在《中国学会报题词》等文章中,他极力宣传设立孔教的重要性,认为:孔子是改制之圣王,创教之教主,自孔子创教立说以后,中国饮食男女,生作行持,政治教化,矮首顿足,无一不在孔子思想范围之内,如果孔教一旦被弃,“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也”(29)。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他更主张以孔子配上帝,以孔教为国教,提出在天坛明堂由总统率百官行礼,在地方乡邑各立庙祀天以孔子配之。至此,孔子已与天齐、孔教已至国上了。
孔教会成立后,康有为以总会长的名义,两次为其作序,极力赞扬孔子,大肆鼓吹孔教。他指出:“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其道无乎不在。故在中古,改制立法,而为教主。其所为经传,立于学官,国民诵之,以为率由,朝廷奉之,以为宪法,省刑罚,薄税敛,废封建,罢世及,国人免奴而可仕宦,贵贱同罪而法平等,集会言论出版皆自由,及好释、道之说者,皆听其信教自由。凡法国革命所争之大者,吾中国皆以孔子之经说先得之二千年矣”(30)。“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31)。因而,他号召孔教会同仁,“以演孔为宗,以翼教为事”,高高举起崇圣立教的大纛。在康有为的摇旗呐喊下,一时间,举国上下,孔教会纷纷成立,“其会友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32)。康有为纳儒入教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物极必反。1918年康有为辞去孔教会总会长职务,其纳儒入教活动偃旗息鼓,烟消云散。
三
对于康有为纳儒入教的思想及活动,以往学术界一般皆认为是唯心、反动、复古、倒退的。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免简单武断且偏颇失误。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既不是一位书生脱离实际的空泛议论,也不是一个宗教徒对彼岸世界的盲目追求,而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积极地有意识地对儒学的重构,并用自己重构的儒学来变革中国的现实,只不过在历史大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它前后有着正负不同的作用罢了。
首先,康有为呼唤和建构的孔教与佛、耶、回、道等教不尽相同。何谓宗教?梁启超曾指出:宗教“以起信为第一义”,反对怀疑,“迷信宗仰”,以使人脱离尘世到达天堂为目的。他还借西人口说:“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蘖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福祸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33)“其概则一也”,是说各种宗教尽管有“精粗大小”的区别,但它们“迷信宗仰”,其本质是相同的。而康有为主张的孔教则别具旨趣。对此,梁启超曾指出:“先生者,孔教之马丁路得也。其所以发明孔子之道者,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五、孔教者,强制主义,非巽懦主义;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34)。如果说梁启超概括得过于抽象朦胧的话,那么肖万源先生对此则做了具体确切的论述。肖先生指出:孔教与其他宗教之不同,可归纳成以下几点。第一,孔教重人道,“不尚离远,专为于行”(35),“敬天而爱人,尚公而亲亲,忠孝信义,爱国亲上”,治教兼备,人人可行之。佛耶诸教都不循天理,远于人道,“大怨亦报以德,人杀其父彼亦孝事之如父母”,悖于人心,违背公理,“诸子创教,其大谬多类此”(36)。第二,孔教讲天与父母并重,仁与孝兼举,魂与体交养,性与命双修,且“讲魂而远于人道之内”。而诸教只尊天、修魂,道教只修魄,佛耶二教“寡及父母,言仁而寡言孝,尊魂而少言修身”(37)。第三,孔教极重人道之繁衍,“以生为道,以仁为道,故以父子夫妻为重”(38)。而佛耶“不嫁娶独尊天”(39),不合人情,人人皆如此,“则生人久绝矣”(40),因此“不能为人人共行”(41)。第四,孔教“主进化”、“主维新”(42),倡三世大同之道,为他教所不及。第五,孔教尊天兼敬祖,仁孝并重,“久于其习,宜于其俗”(43),深入人心,已成“人心风俗之本”(44)。佛教尚慈悲明罪福,虽高妙深远,“然多出世澶漫之言”(45),“于人道之条理未详也”(46),只行于蒙、藏等地,不能行于全中国。耶教尊天尚仁,“养魂忏罪,施于欧、美可也”(47),而不可行于中国。“然今在中国,欲立废祠墓之祭扫,弃祖宗之系,恐未能也”(48)。第六,孔教治与教兼备,既能治国又能教化天下。一国虽有基督或佛,照样会“供人宰割之具、奴虏之用”,“不观耶稣之生于犹太乎?不数十年而犹太为墟,……夫耶稣能为欧人之教主,而无救于犹太之灭亡;佛能为东亚之教主,而无救于印度之灭亡”(49)。而孔教则具有救国治世、教化天下的功用(50)。因此,我们对康有为纳儒入教的思想和活动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康有为奔走呼号三十余年,依据历史风俗、针对内忧外患,是想建立起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第二,康有为的孔教是以人设教,神化先贤,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第三,康有为的纳儒入教,实质是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重构。他试图以宗教化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正人心,移风俗,改造国民性;作为一种精神屏障,拒异端,排邪说,阻止西方文化侵略;作为一种历史渡船,挽中华,救众生,最后步入大同之境。
其次,康有为建构的孔教与其政治主张紧密相联。康有为将孔子改造为天,改造为神,改造为耶稣,改造为通天教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一)他试图用孔教来统一人们的信仰,抹掉西方耶稣头上的光环,抵制西方传教士的宗教蛊惑,具有反侵略的意义。(二)他旨在说明皇帝和人民都是“天之子”,都应尊孔祀天,这不仅破除了只有皇帝是“天之子”的独尊地位,也剥落了皇帝是“天之子”的神秘外衣,从而为其“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三)他以孔子为大旗,对世俗迷信进行了激越的批判。他指出:由于中国“尚多神话之俗,未知专奉教主”,因而“惑于鬼神”,膜拜“妖巫神怪”,致使“淫祠遍地”、“妖庙林立”,“而牛鬼蛇神,日窃香火,山精木魅,谬设庙祀,于人心无所激厉,于俗尚无所风导,徒令妖巫欺惑,神怪惊人,虚靡牲醴之资,日竭香烛之费”(51)。因而他主张禁淫祀,废淫祠,匡谬正俗,只祀孔子,奉为教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出“改诸庙为学堂”,变“淫祠遍于天下”为“学堂遍地”,“以公产为公费,上法三代,旁采西法,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者”,都必须入小学读书,学习文字、语言、图算、器艺,其中一些人再入由各省书院改成的中学堂、大学堂,“兼习中西”。这无疑具有反对世俗迷信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康有为的孔教“明扬鬼神,幽含政治”、“鬼神”为政治服务。
第三,康有为纳儒入教开导了现代新儒学的先河。在现在的新儒学史上,虽然还没有康有为的名字和地位,但详加考察,现代新儒学与康有为的孔教有着许多维妙维肖之处。从形上看,它们都“似宗教而非宗教”,非理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交存杂处。从神上看,它们都融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于传统儒学之中,极度推崇儒学唯心主义。从终极关怀上看,它们都积极入世,述而且作,希图重振儒学雄风,解释和解决中华民族的精神问题。例如:钱穆在《孔子与心教》中高唱:“只因有孔子的心教存于中国,所以中国能无需法律宗教的维系,而社会可以屹立不摇。此后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实有盛唱孔子心教之必要。”(52)与康有为的创教言论如出一辙。牟宗三在《作为宗教的儒教》中强调:“一个文化不能没有它的最基本的内在心灵。这是创造文化的动力,也是使文化有独特性所在。依我们的看法,这动力即是宗教,不管它是什么形态。依此,我们可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53)。这说明,现代新儒学亦存在着纳儒入教的冲动与倾向。因此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是现代新儒学的鼻祖和先师。梁启超将其业师康有为称为“先时之人物”,大概也包括这一缘故吧。
注释:
①参见拙文《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载《求是学刊》1992年第3期。
②(23)《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85页、第79页。
③⑩(11)(12)(13)(16)(17)(18)(22)(25)(28)(30)(31)(37)(39)(43)(44)(45)(46)(47)(48)(49)(51)《康有为政论集》第192页、第52页、第20页、第202页、第211页、第54页、第132页、第132页、第13页、第187页、第692页、第732页、第740页、第1100页、第1100页、第842页、第864页、第864页、第842页、第864页、第726页、第569页、第279-280页。
④⑤(21)《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112页、第114页、第117页。
⑥(19)(20)康有为:《大同书》第301页、第3页、第258页。
⑦(3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61-70页、第300页。
⑧《救世教益》第6章。
⑨《孔子基督为友论》第8页。
(14)(15)(27)《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24)《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50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广东举人梁启起等八百三十二人陈《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呈》。
(29)《不忍》第4册。
(32)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第19页。
(33)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2页。
(35)(36)康有为:《论语注》第27页、第220页。
(38)(40)(41)(42)康有为:《孟子微》第64页、第61页、第64页、第86-87页。
(50)肖万源:《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和鬼神观》第60-61页。
(52)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408页。
(53)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上)第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