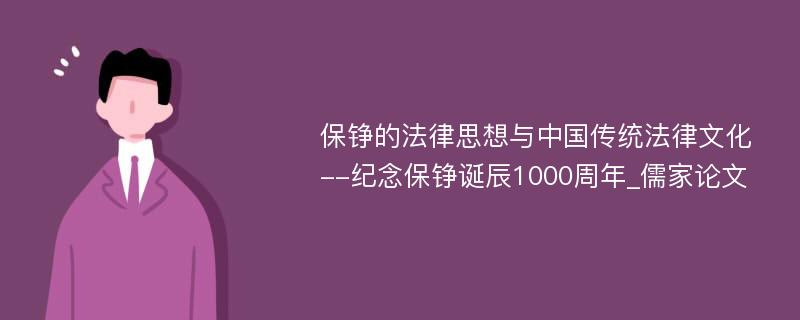
包拯的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纪念包拯诞辰一千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拯论文,法律论文,诞辰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包青天”、北宋名臣包拯生于公元999年, 今年是包拯诞辰一千周年。有关“包青天”的各种传说也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近千年。包拯这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的普遍赞扬?只要对包拯的法律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就会发现,“包青天”的美名,并不是仅仅靠《包公案》和几出包公戏唱出来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拯本人具有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等可贵精神。这种包拯精神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人本主义;二是伦理主义。这两大特点在包拯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我们把包拯这一历史人物置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研究,会加深对包拯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认识,这也正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人本主义与“民为国本”
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粗略说来,它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人在自然面前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人间治乱兴废在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这种思想散见于我国古代大量典籍中。如:“人为万物之灵”;(注:《尚书·泰誓》)“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注:《列子·天瑞》)“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注:《礼记·礼运》)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张载:《论语说》)荀子对此说得最为透彻:“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注:《荀子·天论》)治理国家不能靠天,只能靠人类自己,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德、政、刑,就能战胜自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注:《刘禹锡集·天论上》)法律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手段。二是人与神的关系。在我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注:《尚书·君奭》)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努力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朝的国运长久。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注:《左传》昭公十八年)表达了他注重人事,轻视天命鬼神的思想。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注:《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注:《论语·述而》)“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注:《论语·先进》)这些话都表达了他在人事与鬼神的关系上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人间的事,只能靠人来处理,而不能寄希望于鬼神。儒家不是儒教、儒学也不是神学。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就是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这种重人事、轻鬼神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后人所效法。三是国与民的关系。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重民思想。周公在《尚书》的有关篇章中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并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注:《尚书·酒诰》)春秋时期形成了一股重民的思潮。《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注:《管子·牧民》)儒家就是这种重民思潮的集大成者。如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哀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注:《荀子·大略》)儒家这种重民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强调民为国本,国家的治乱安危皆取决于民心的向背。西汉时期贾谊对此说得最为精辟。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也。”(注:《新书·大政》)儒家正是从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出发,重视民心的向背,主张关心民间疾苦,先富后教,敛从其薄、刑罚适中,反对苛政和滥用刑罚。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传统对包拯的法律思想影响很大。
应该说,包拯是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继承者之一。他一生注重人事,罕言鬼神。一次,中原地区大旱,他向宋仁宗上书说:“亢旱之灾,天之常数,固不足贻陛下忧,惟陛下留神省察”。(注:《包拯集·上殿劄子》)旱灾是自然现象,不值得深忧。国家的治乱在于人事。“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只要法纪严明,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他一再向宋仁宗申明“民为国本”的道理。“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注:《包拯集·请罢天下科率》)“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注:《包拯集·言陕西盐法》)民心向背是国家安危所系,如果当权者不能“恤民”、“安民”,国家就不可能治理好。“大本不固,则国家何从而安哉。”(注:《包拯集·论赦恩不及下》)如何“恤民”、“安民”呢?包拯多次深入民间,体察民间疾苦,并为民请命。他针对当时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民不堪其苦的现状,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若乃横敛不已,人怀危虑,或因岁之饥馑,以吏之残酷,相应而起,涂炭海内,此乃心腹之患。”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主张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加派。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为了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包拯主张节省官府开支,并裁减冗员、冗兵。他认为:“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治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注:《包拯集·论冗官财用等》)
包拯从“民为国本”的思想出发,在立法方面,主张遵循“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举例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若复旧日禁榷之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久而不胜其弊,未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许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额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先有小损而终成大利也。”(注:《包拯集·言陕西盐法》)为了恤民、安民,立法应兼顾国家与民众、公和私两方面的利益,不应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他认为当时的盐法、茶法、冶铁法都有只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问题,此法不改,后患无穷。
包拯这些恤民、安民的主张是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的体现,和先秦儒家“敛从其薄”、“使民以时”、“先富后教”、“节用裕民”等仁政思想一脉相承。
二、注重伦理、严于律己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特征是注重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也因此而被人们称之为伦理主义文化。这种伦理主义和上述的人本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人本主义是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
第一,伦理与法律相结合。这一点,在西周初期已充分显露。《尚书·康诰》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刑兹无赦。”意思是:“不孝不友”是罪大恶极。对“不孝不友”者必须以严刑惩处。违反宗法伦理就要“刑兹无赦”,这就开创了“出于礼,入于刑”的先河。战国时期李悝制定《法经》,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一度出现了轻视伦理道德的倾向。但自西汉起,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法律逐步儒家化、伦理化,伦理与法律融为一体,法律制度成为典型的伦理化的法律制度。
第二,重视道德教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向来有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西周初期已露端倪。如《尚书·康诰》说:“明德慎罚”,《酒诰》说:“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后来《吕刑》又提出“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刑罚与德教相结合的倾向已很明显。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称赞说:周公提出的刑罚与道德相结合的教化主义是“法律观念上的一大进步。”(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儒家更是以重视道德教化著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孟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注:《孟子·公孙丑》)《礼记·经解》:“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西汉时期董仲舒更明确提出“德主刑辅”,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很少有人真正实行“德主刑辅”,但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主张标本兼治,作为一种法律学说在历史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价值。
第三,要求当权者严于律己。儒家讲道德、说仁义,不是只讲给别人听的,而是主张修德必须从自身做起。儒家一套修、齐、治、平的理论就是以自己正心、修身为起点。正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儒家提倡的为人、为政与处世的哲学。孔子关于正人必先正己的言论很多。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注:《论语·子路》)“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注:《论语·卫灵公》)儒家提供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贤相良臣都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诸葛亮、范仲淹、包拯、海瑞等人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包拯深受儒家伦理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
1.恪守孝道。“孝”是儒家倡导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十分重视孝道,主张“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注:《论语·里仁》)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注:《论语·为政》)后来,《孝经》又提出:“孝为百行之首”。儒家提倡孝道是为了巩固宗法等级制度,其中含有一些消极与陈旧的东西。但提倡孝道,重视亲情,注重亲子之爱,却是可取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拯对孝道身体力行,恪守不失。《宋史》记载:包拯二十九岁中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在,辞不就。”后改任和州,其父母又不愿离开故土,包拯毅然弃官不就,在家奉养双亲。数年后,父母双亡,包拯在乡里的劝说下,才登上仕途。
2.重视教化。在法律思想方面,包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他认为:“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注:《包拯集·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他引用董仲舒的“阳为德为春夏,……阴为刑为秋冬”的说法,并进一步发挥说:“以此见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宜当上体无道,下为民极,故不宜过用重典,以伤德化。昔暴世法网凝密,动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致溃乱。”他认为老子所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很有道理,并奉劝宋仁宗当“鉴于此言而无忽焉。”可见他的恤刑慎杀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的德主刑辅说,但也吸收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
3.严于律己。包拯一生以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严于律己,一丝不苟。这是他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关键所在,也是他最受后人称道之处。他初登仕途,曾赋诗一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此诗不同于封建士大夫舞文弄墨的文字游戏。“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是包拯为官做人的基本信条和实际行动的指南。他把“清心”、“修身”作为自己仕途的起点。他坚信只要自己能廉洁自奉,就能无畏无虑,敢于直言,勇对邪恶。正如《宋史》所说:“拯性峭直,……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他牢记史册上前人的遗训,立志做一个为百姓拥戴的清官,决不因自己行为失检而愧对后人。《宋史》中记载包拯严于律己、自奉清廉的事迹很多。如:包拯在天长县任职三年后,徙知端州。端州盛产名砚,前任太守强征,超过贡数数十倍,并以端砚馈赠权贵,致使砚工苦不堪言。包拯到任后,下令只按贡数征砚,严禁多征。当任满后,“不持一砚归”。《宋史》称赞包拯“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虽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卒后赠礼部尚书,但一生生活俭朴,一如寻常百姓。他还立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注:《宋史·包拯传》)他不仅廉洁自律,而且严格要求子孙后代,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三、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在执法方面,我国历史上一直有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良好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孔子主张执法不阿。他为鲁国司寇时,就以直道执法,“据法听讼,无有所阿”。(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他称赞“治国制刑,不隐于亲”的叔向是“古之遗直”(注:《左传》昭公十四年)。法家更重视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主张令行、禁止,执法不阿。慎到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注:《慎子·君臣》)“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注:《慎子·佚文》)。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注:《韩非子·有度》)从西汉起,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也吸收了法家的重法思想,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传统得以延续。连贾谊这样极力推崇儒家的儒生也主张执法应“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注:《汉书·贾谊传》),以“科教严明”著称的诸葛亮也是“赏罚必信”,公正执法,包拯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加强法制。他说:“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注:《包拯集·上殿劄子》)在执法方面,包拯一贯是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他在这方面的事迹也很多。如:张尧佐是宋仁宗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他依仗裙带关系掌握了财政大权。此人昏瞆无能,贪婪成性,在任期间对百姓敲骨吸髓,使得“诸路困于诛求,内帑烦于借助”,民怨沸腾。包拯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上书弹劾。尽管宋仁宗有意庇护,但在事实面前,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张尧佐的职务。又如,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此人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刻剥百姓。百姓被逼逃入山洞。包拯一连七次上书弹劾,迫使宋仁宗免去王逵的官职。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在任职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包拯认为张可久身为朝廷命官,竟敢“巧图财利,冒犯禁宪”(注:《包拯集·请重断张可久》),他要求宋仁宗对此人从重论处,把他发送边远地区加以编管,以观后效。又如,包拯在任开封知府时,正遇水灾。开封的一些达官贵戚在惠民河上任意修建花园亭榭,致使河道堵塞,影响防汛。包拯下令拆除一切违章建筑。有人拿出地契争辩。包拯让人从地下挖出界石,查明地契“伪增步数”无效。由于包拯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使得达官显贵的恶行有所收敛。《宋史·包拯传》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开封的百姓称赞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四、从严治吏,贤良执法
在我国法律文化史上,精选官吏和贤良执法的思想早已出现。《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饮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告戒成王,不可任用奸邪,“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注:《尚书·立政》)只有贤良吉士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必须选拔贤者充任准人、牧夫来管理行政与司法事务。后来,《吕刑》更明确提出:“非佞折狱,惟良折狱”。“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执法官吏在审案中如果有仗势营私、挟怨报复、内亲用事、勒索财物、受贿枉法等罪过,要严加惩处。
先秦儒家从伦理主义思想出发,都极力提倡贤人治国,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才能行仁政于天下。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注:《礼记·中庸》)“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注:《论语·为政》)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惟仁者宜在高位”。(注:《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这就是说,治国需要良法,但更需要有良吏。没有贤良执法,再好的法也起不了作用。儒家这种贤人治国论,过分夸大当权者个人在治国中的作用,并有明显的道德万能论的倾向。但儒家重视当权者的道德品质,主张贤者当权,应由品德高尚的人执法,这种见解值得重视。包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他把选拔官吏、知人善任视为治国的根本大计。他说:“治乱之原,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注:《包拯集·论取士》)“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无旷矣。”(注:《包拯集·晏殊罢相后》上)包拯认为治国需要有良法,而法律的执行则需要有贤臣良吏。他特别重视对司法监察官吏的选拔,认为:“转运使、提点刑狱,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狱讼之冤滥,以至生民利病,财赋出入,莫不莅焉。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蔽。”(注:《包拯集·请选用提转长吏官》)转运使、提点刑狱,肩负司法监察之要职,权势至重,应选拔清正廉明之士充任。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转运使既无德,又无才,“皆知识庸昧”、“素非干敏之才,又无廉洁之誉”,用人失当,民受其害。为此,包拯上书,要求宋仁宗精选司法监察官吏,“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注:《包拯集·再请选转运提刑》)对司法监察官吏中不称职者和腐败分子,包拯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上书弹劾李熙辅、张经等人“居按察之任,当一路之重”,但不忠于职守,“挟私逞憾,无所畏惮,妄构刑狱”。对这种人,包拯主张“重行黜降,以警将来。”(注:《包拯集·再请选转运提刑》)
北宋时期,官场腐败,贪污成风,污吏遍地。包拯对此痛心疾首。为了维护法纪,减少冤案,他力主加强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向皇帝上书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摘发,无日无之。……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对这种贪赃枉法之徒,包拯主张从严惩处,“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注:《包拯集·乞不用赃吏》)他把贪官污吏视为害民的蠹虫,蠹虫不除,民无宁日。“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蠹,则俗阜而财丰,若蠹原不除,治道何从而兴哉。”(注:《包拯集·请置鹿皮道者》)
为了减少与防止冤狱,包拯还改革诉讼制度。按旧制,“凡诉讼不得迳造庭下”,告状人的状纸必须由门吏牌司收转,门吏牌司从中敲诈勒索,营私舞弊。包拯上任后,一改旧制,撤掉门吏牌司,告状人可直接上庭送诉状,当面陈曲直。这样,可防止门吏敲诈勒索,使“吏不敢欺。”(注:《宋史·包拯传》)
由于包拯疾恶如仇,严惩贪官,执法如山,使一帮贪官污吏“闻者皆惮”,而广大黎民百姓对他却同声赞扬,“包青天”的美名久盛不衰。合肥包公祠的楹联赞扬他:“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正气耿光昭日月,廉洁清栎妇孺知”。“包孝肃公墓园”的楹联是:“庐州有幸埋廉相,包水无言吊直臣”。这都表达了后人对包拯的崇敬与怀念。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是对我国历史上包括包拯在内的诸多清官最高最公正的评价。十年“文革”中,姚文元、戚本禹之流,批判“清官论”,说什么“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反动。如今,“四人帮”已成粪土,而包拯至今仍备受百姓赞扬。包拯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也受到我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贤相良臣代有人出,包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包拯这一历史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沃土。包拯的法律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结晶。从思想来源看,包拯的法律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儒家的人本主义、民本思想、伦理思想、仁政思想、德主刑辅说与贤人治国论,也吸收了法家的“以法治国”与“信赏必罚”思想,而儒家的法律思想则是包拯法律思想的主干。包拯的法律思想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一样,也有一些缺点与消极因素,但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包拯法律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一再强调的民为国本、立法要利民、重视道德教化、正人先正己、从严治吏、贤良执法等思想都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他的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和执法如山的精神,在我们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进行司法改革和反腐倡廉的过程中都很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与弘扬。
包拯诞辰一千周年已经过去,可以预料,再过一千年,包拯精神将依然受人们崇敬与赞扬,包拯的名字将流芳百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