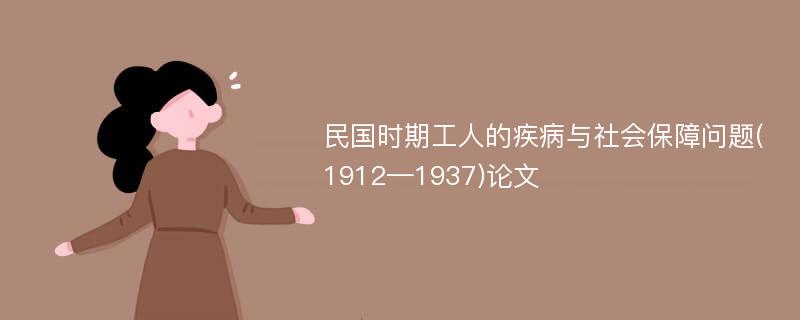
民国时期工人的疾病与 社会保障问题( 1912— 1937)
刘秀红
摘 要 民国时期,工人所患疾病与其职业身份有关。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工作环境不良、居住环境差、营养不足都影响工人的身体健康,感染疾病。疾病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工人群体呼吁实行相关立法并通过罢工表达疾病社会保障需求。北京政府时期开始出台有关疾病保障的法律条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明确了企业的疾病保障责任:对于特殊的行业,企业负担工人一切疾病的医药费及病假工资、病故抚恤等费用,对于普通工矿企业,则只负责和职务有关疾病的保障。立法体现了政府对劳工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重考虑。实践中,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效益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选择对工人疾病提供何种保障。此时期工人疾病保障受益群体面较窄,待遇水平差别较大,但它是疾病保障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 民国工人;疾病;保障
民国时期,大量工矿企业建立。工人所接触的劳动原料、所处的劳动环境与传统社会不同,导致其所患疾病有新的特点。但承担疾病风险的仍是家庭。在劳动保护思潮和劳工运动的影响下,工人疾病的社会保障问题受到社会关注。而对此问题社会各界做了哪些努力,结果如何,目前学界尚无专题研究。[注] 目前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较为重视,研究成果很多,研究重点在于传染病、公共卫生机制、疾病观念等内容,较为重要的著作有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项医疗社会史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但是对工人这个新兴劳动群体的疾病研究仍属空白。有关工人疾病的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刘秀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27-1937)》(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中有所涉及。 本文通过挖掘原始材料,考察工人疾病发生的情况、影响疾病产生的因素,政府、企业、工人及其团体等各社会主体在疾病与保障方面的态度、行为及措施,并分析探讨此时期疾病社会保障的特点及意义。
一、民国时期工人的疾病情况及社会归因
疾病是由内部或外部因素造成的生理异常。由于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卫生习惯、生活环境不同,在传统社会里,个体患病一般被认为是私人事务,除传染病外,患病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民国之后,随着疾病知识的增加与劳工保护思潮的兴起,人们认识到工人所处的工作环境,对其健康也有重要的影响:“生理卫生学者公认,影响于人体健康的因素有三:(一)父母遗传的本质,(二)生存的环境,和(三)所操的职业。这三个因素是相互的连锁的影响到人体的健康。”[注] 李维鑅:《城市与乡村死亡率与疾病率的比较》,《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2年第28卷第11期,第386页。 民国时期对劳工生活和职业的调查中,涉及工人疾病的,都用不同的篇幅探讨了疾病和职业的关系,如对纺织业工人、地毯业工人、印刷工业工人、镀铬业工人等。调查显示,工人常患疾病一方面和普通民众有相同之处,如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等[注]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第18页。 ,另一方面,其所患疾病又与职业因素密切相关。包括:
第一,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导致的疾病。民国时期,人们已了解职业病是“因做一门专门工作而发生的病”,认为有六种原因可导致职业病:有毒或无毒埃气体烟雾酸或碱、有害细菌或微生物、过高或过低的气压、不适宜之采光、过热或过冷之气温、过度劳力。[注] 王世伟:《职业病之研究》,《劳工月刊》1934年第3卷第3期,第37页。 此时对职业病的研究还不充分,没有对职业病病种的具体界定,但人们已认识到因职业中有毒有害物质而导致的疾病属于职业病。此时期调查中认为各业所得的职业病包括:在地毯业中有因接触到动物皮毛上的炭疽杆菌而感染的炭疽病[注] 李廷安、杨建邦:《地毯工业中职业性疾病之研究》,《工业安全》 1934年第2卷第5期,第307页。 。在矿业中有工人“处于闭窒郁闷的饱含煤灰及温度不调的空气中”[注] 《全国矿山工人的现状》,《劳工月刊》1934年第3卷第7期,第2页。 而得的尘肺病。印刷行业的职业疾病有金属铅所导致的铅中毒和鼻炎。1935年对上海印刷工业189名工人的调查显示铅中毒的发病率为10%,鼻炎发病率为17.5%,因为“此种工场,熔铅手续亦在其中举行,且因换气不良,致铅气满布于室之内外;倒熔锅中之铅时,铅物常泼溅四周;在割铅片之际,铅粉满播空气中。”[注] 吉尔等:《上海之工业卫生:印刷工业之调查》,《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年第21卷第10期,第1160页。 镀铬业工人的职业病有金属铬所导致的尘肺病和鼻、眼等疾病。在上海200名镀铬工人的体检中,尘肺病占8%,鼻炎占68%,鼻中隔溃烂和漏孔占17.5%,鼻衄占28%,结合膜炎占28%。[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第22卷第8期,第676-678页
1.5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宫腔镜诊断的粘连程度为金标准。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分别以超声综合评分法评分S≥轻度、S≥中度、S≥重度为不同研究终点分组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马尿酸标准曲线的绘制:分别配制马尿酸浓度为0.05,0.1,0.2,0.3,0.4,0.5 mmol/L的标准溶液,过0.22 μm的滤膜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马尿酸含量,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马尿酸浓度(x)为横坐标绘制马尿酸标准曲线。
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不良的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饮食中的营养不足等因素所致工人的疾病,无一不与其职业身份相关。民国时期,工人工资低下,无法在食物上讲究营养,造成身体羸弱,免疫力差。收入不足、城市里房租高昂,造成住房狭小,卫生条件差,空气及饮水都不洁净;工厂卫生条件不健全,造成职业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害;过长的劳动时间,造成工人的疲惫,抵抗疾病的能力降低:“生活状况低劣、空气恶浊、工作时间过久、饮食不良及一般卫生不讲求等,实为影响工人健康之主因也,而工业本身之特种危险,反成次要也。”[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81页。
光线不足、污染使结膜炎也成为工人常患疾病。1935年上海印刷业工人体检中患有结膜炎者有27.5%,“与工作室之幽暗与污秽有关,如排字等事项,甚费视力,故视力损坏之发现于此类工人,亦无足奇。”[注] 吉尔等:《上海之工业卫生:印刷工业之调查》,《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年第21卷第10期,第1153页。 在镀铬工人那里,结膜炎占28%,除灰尘和金属铬对空气的污染外,光线不足也是重要原因。[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76页。 1933—1935年,对北京燕京工厂和仁立工厂的工人疾病治疗中,急性结膜炎占疾病总数的1.5%、1.2%、2.7%。[注] 根据以下计算:《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 1933年第8期,第93-97页;《北平市卫生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4 年第9期,第110-114页;《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5 年第10期,第68-70页。
真的,什么革命,什么转折点,什么历史的剧变。想想陆地开垦那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那无休无止而意义不明的过程——人类淤积的过程[2]9。
厂内温度过高导致的中暑在纺织、缫丝、食品、冶金、玻璃等行业中频繁发生。(上海纺织业)“夏日纱厂中热度高至九十四五度……暑中女工之出勤者比率,降至百分之三……”[注]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557页。 。(上海缫丝业)“工作室中,因有煮茧盆之热水,温度颇较平常为高,空气亦较潮湿。据人报告,夏天晕倒者,颇不乏其人。”[注] 同上,第567页。 (上海饮食品业)“在盛夏的时期,机器室中发现痧症者,每日必数十起,因而致命者,每年必有好几个”。[注]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292页。
工厂卫生不良又会加剧病毒的传播与流行。工厂中最常见的传染病是沙眼与结核病。1933年对地毯业999名工人的体格调查显示,89.3%的工人患有沙眼,[注] 李廷安、杨建邦:《地毯工业中职业性疾病之研究》,《工业安全》1934年第2卷第5期,第303页。 1935年铁路工人体检,患沙眼者39%[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76页。 。沙眼一般急重患者才去医院治疗。1933—1935年,对北京燕京工厂和仁立工厂的疾病治疗中,沙眼疾病占总疾病总数的11.0%、10.0%、8.9%。[注] 根据以下计算:《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 1933年第8期,第93-97页;《北平市卫生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4 年第9期,第110-114页;《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5 年第10期,第68-70页。 上海镀铬业工人急重患者占12.5%[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76页。 ,印刷业工人9.5%。沙眼“以接触公用物品如手巾之类而导致传染”[注] 李廷安、杨建邦:《地毯工业中职业性疾病之研究》,《工业安全》1934年第2卷第5期,第306页。 ,充满灰尘的空气也会刺激眼结膜使之易受病毒侵入。结核病的流行更为惊人。据估计,1932年中国每年死亡于结核病者为170万人,患病者约为一千万人。在对重庆市各团体的调查中,工厂的患病率最高。[注] 王明聚:《重庆肺结核检查报告》,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3、85页。 对各种工业的调查中,结核病都是其中重要疾病。纺织业中住院病人肺结核住院者占9%。[注] H. W. Decker、哲隐:《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诊案的检讨》,《工商管理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61页。 印刷工业体检中,患病者及疑似病患者占5.3%。[注] 吉尔等:《上海之工业卫生:印刷工业之调查》,《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年第21卷第10期,第1153页。比例为计算得出。 镀铬业工人体检中占6.5%[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76页。比例为计算得出。 。肺结核依靠飞沫染,“当病人咳嗽之时,其含菌之痰唾成为细尘弥散于空气中,言谈之时,其口津亦能同时散布,故与病人谈话或接近时,每将患者之病菌吸入体内。在公共娱乐场所或工场商店等处,大量病菌亦可随其所附着之尘土达到人之呼吸管道。”[注] 沈恩衍:《工厂疾病:漫谈结核病(痨病)》,《机联》1948 年第224期,第18-19页。 工厂环境加重疾病的流行。“多人麇聚一室,睡眠、饮食、起居于满布沙尘毒烈气质之空气中,随地吐痰及鼻涕尤为常事,故极易传染”[注] 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8期,第678页。 。结核病传染性极强,当时又无有效的治疗办法,对工人的健康影响尤其严重。
第三,居住环境不良所导致的疾病。工人除本地人有自有住房以外,一般租住市房、工房,而一些贫苦工人无钱租房,便搭竹棚草屋居住。大城市内房租昂贵,工人住处往往拥挤不堪。如上海工人所居住“上等住屋”,经常四五家合租,一家四五口居住一室,“无所谓卧室、无所谓厨房,亦无所谓厕所”,屋内嘈杂秽浊,户内外废物堆积。其共用的厨房“污水垢物,残羹败饭,狼籍满地,日积月累,蒸腾腐化。”[注] 郑鹤:《我国厂工的居住概况》,《民生》1932年第17期,第7页。 一至夏天,苍蝇遍地,臭气熏天。其他等级的住房则更差。单身工人住在厂内宿舍,宿舍“有的就设在工场的楼上;有的设在楼上和工场之间,添上一个阁楼;有的就在楼上隔做二层;有的在楼下地窖里,有的在工场左右的堆栈里,栏出几间平房。”[注] 同上。 因为空间狭小,工人或打地铺,或住双层床铺。光线与空气流通自不在考虑之列。更有一些工厂为了节省空间,工人即住在工作室内,北京地毯业“工人艺徒住宿之所,即为日间工作之处。……在夏季蚊虫侵虐,臭虫为患;冬令则地上寒气逼人,实难忍耐。……随便设置大小便所,臭气扑鼻;每届夏令,则蝇类狼集。”[注]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397页。
这种卫生条件下,食物饮水最易受细菌污染,加重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1924年北京地毯工厂诊疗所治疗的疾病中胃肠病占16.6%,包括痢疾、吐泻与肠炎、寄生虫病等[注] 李廷安、杨建邦:《地毯工业中职业性疾病之研究》,《工业安全》1934年第2卷第5期,第304-305页。比例为计算得出。 。上海工业医院住院的纺织工人寄生虫患者占19%。[注] H. W. Decker、哲隐:《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诊案的检讨》,《工商管理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61页。 1933—1935年燕京和仁立工厂工人中痢疾占总疾病的3.3%、4.8%、2.2%[注] 根据以下计算:《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3年第8期,第93-97页;《北平市卫生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4 年第9期,第110-114页;《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5 年第10期,第68-70页。 ,是外伤炎症、上呼吸道感染、沙眼外最重要的疾病。
这种城市环境中,传染病也易流行。李维鑅对20世纪30年代北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率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因肺结核病而死亡的比例为每十万人口360,农村为176,高出一倍。一般人看,“北平市的卫生设备当较定县实验区为完备,居民的经济状况亦当以北平市为高,一般民众知识农村定较城市为低”,城市居民的发病率应该较小,但“农民生活的方式和工作环境是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农民工作在天然环境中,空气阳光等利益较卫生设备为多,饮食的新鲜亦非居民可比。这几个简单的卫生原则已公认为治疗和预防肺病的最好方剂。这或是定县农民肺病死亡率低的原因。”[注] 李维鑅:《城市与乡村死亡率与疾病率的比较》,《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2年第28卷第11期,第387-388页。
第四,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1936年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的上海工人饮食调查报告显示,工人饮食中碳水化合物过多,动物脂肪及蛋白质成分不足,矿物质中钙磷不足,维生素缺乏,其体重与身高较上海学生群体不如。而童工则为营养不足的重点:“童工之饮食在质与量方面俱在标准需要限度之下,并较上海其他各种工人之饮食更为不如。”[注] 《上海工人饮食调查》,《卫生月刊》1936年第6卷第11期,第52页。 对北京、上海等地工人生活状况的多次调查也证明这种观点[注]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28页。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277页。伊博恩等:《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 年第22卷第8期,第682-694页。 。营养不足对健康影响很大,并会发生多种疾病。“蛋白质不足时,日久则年长者柔弱,年少者生长迟慢,甲种维生素缺乏时,经久可致干眼,夜盲等病。乙种维生素缺乏时,始则胃口不良,消化力顿减,继则周围神经衰萎,终则成为脚气。丙种维生素缺乏时,易成坏血病,膳食中若钙与磷不甚充裕,而丁种维生素双缺乏,则成佝偻病。……此各种营养素缺乏病……在中国极为常见。”[注] 李涛:《中国人常患的几种营养不足病简考》,《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6年第22卷第11期,第1027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系统的劳工立法。工业工人疾病保障的内容,包含在《工厂法》内。1929年12月《工厂法》出台,其疾病保障的内容,改变了大革命时期一切疾病都由企业保障的原则,企业只负担和职务有关的疾病:“工人因执行职务而致伤病或死亡者,工厂应给其医药补助费及抚恤”,伤病期间工资为原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二,半年后减至二分之一,以1年为限。因伤病致残,根据残疾程度给予1至3年工资,死亡时给予50元丧葬费和300元及2年工资的遗族抚恤费。[注] 《工厂法》,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第5-6页。 但这仍然引起企业的担忧和反对。“我国生产落后,工人效率过低……属会各厂,对于本法虽欲敬谨奉守,而成本加重,亏累难支,势必出于辍业一途,彼劳工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注] 《关于八月一日实施工厂法鄂省棉业界致当局函》,《纺织时报》1931年第819期,1931年8月3日第1版。 “工人生病不能照给工资与医药也。查工人生病给予工资与医药费,原为体恤起见……但是工人智识薄弱,不道德尤居多数……各厂工人借口生病者不仅半数,既有工资又得医药费,谁人肯来上工……所持药方亦大都向厂方指定药店卖钱。药店狼狈为奸,不出药而向厂中领款,亦得因缘作弊。种种不情言之痛心。”[注] 《湖北纱厂联合会对于劳工法条举妇见》,《纺织时报》1928年第566期,1928年12月27日,第261、262、263版。
1933—1935年北平公安局(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北京燕京和仁立两工厂进行诊病时都发现了干燥眼症,病因是工人食物中缺乏甲种维生素。它指出此类营养不良疾病与经济形势的关系:“数年来工人患此病者甚多,其后改良食料,遂逐渐消灭。近年来市面萧条,物价增涨,厂方未能照旧给予工人饭费,于是因食料不良,眼干燥病随之而复现。”[注] 《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3年第8期,第94页。
营养缺乏造成工人体质孱弱,更易感染其他疾病,如结核病。“结核病之传染,亦因个人体质及环境而异。体格素强者,感受传染较难,环境不良者,(如因贫血阳光,营养不足)则感受较易”[注] 沈恩衍:《工厂疾病:漫谈结核病(痨病)》,《机联》1948 年第224期,第18页。 上海工业医院病人中,男工患肺结核的为5%,女工为14%,童工则有22%。[注] H. W. Decker、哲隐:《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诊案的检讨》,《工商管理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61页。 体质弱的童工,成为肺结核病的重灾区。
第二,工作场所的卫生不良所导致的疾病。民国时期大部分工厂卫生条件极差,“工场环境之恶劣,如拥挤、换气不良、采光不合及居所不卫生”,[注] 吉尔等:《上海之工业卫生:印刷工业之调查》,《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35年第21卷第10期,第1162页。 在各业中普遍存在。空气中弥漫与原料相关的各种灰尘与碎屑。在纺织厂为原棉纤维,烟草业中有烟草的碎屑、地毯业中有羊毛碎屑等。还有生产原料所带来的气味,如纺织业中漂白粉气味、印刷业油墨的臭气与铅里面发散出来的有毒气体,火柴业中牛胶和磷的气味,煤矿中煤气、水汽、硫磺气等。污浊的空气使呼吸道疾病成为各业工人多发疾病之一。上海工业医院住院工人中,除结核病外的呼吸疾病仍占全体住院工人的9%。[注] H. W. Decker、哲隐:《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诊案的检讨》,《工商管理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61页。 北平地毯业工厂诊所治疗的上呼吸道感染病占全部疾病的10.4%。[注] 李廷安、杨建邦:《地毯工业中职业性疾病之研究》,《工业安全》1934年第2卷第5期,第305页。 1933—1935年,对北京燕京工厂和仁立工厂工人的疾病治疗中,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占总疾病总数的13.5%、11.4%、20.6%。[注] 根据以下计算:《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 1933年第8期,第93-97页;《北平市卫生处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4年第9期,第110-114页;《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年报》1935年第10期,第68-70页。
《工厂法》中的疾病保障待遇,适用于使用发动机器,平时雇用工人在30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注] 《修正工厂法》,《实业公报》1933年第117、118期合刊,《法规》,第1页。 关于矿业工人,根据1931年实业部的解释[注] 《劳字第803号 呈一件为据鲁大矿业公司呈矿山工人是否适用工厂法施行条例,其适用范围是否包罗坑内坑外全体工人,请核示等情具文呈请鉴核示遵由》,《实业公报》1931年第42期,第19页。 和1936年颁布的《矿场法》[注] 《矿场法》,《实业公报》1936年第289期,第14页。 ,其保障待遇和工厂工人相同。至此,工矿业工人所患和职务有关的疾病,依照法律,应由企业提供保障。
二、疾病压力下的工人群体及其疾病保障目标
(一)工人家庭的疾病压力
民国时期疾病发生的社会因素为社会所渐知,但在没有社会保障的社会中,无论是何处归因的疾病,最终还是由家庭承担责任。疾病治疗需依靠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但相关费用却是工人家庭难以承受的。以上海医生的诊疗费为例,1926年,西医门诊费用一般1.2元,出诊5—7元。中医中“时髦一些”的,门诊2元,出诊七八元至十几元不等。[注] X.Y.Z.:《上海的医生》,《上海生活》1926年第2期,第31页。 此时工人月收入一般在10—25元之间。[注] 《上海特别市各业工厂工人平均月入数》,《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市政公报》1929年第19期,第110-116页。 为了控制医疗费用,1929年8月14日,上海卫生局制订诊金标准,给予诊疗费以最高限价,[注] 《上海市卫生局规定诊金标准》,《无锡市政》1929年第2期,第167页。 但因触动了医疗团体的利益,出台后即遭到反对。[注] 《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规定医师诊金呈卫生部文》,《上海市医师公会年鉴》1932年6月,第156-158页。 1935年上海市医师公会制订诊疗费参考表,作为自己的行业标准,其中门诊1元以上,出诊5元以上,夜诊3倍,急诊2倍,手术费每次1元至数百元不等,并公告“本会会员不应故意滥订过低诊例,效减价贱卖市侩式之竞争”,公会会员诊费可高于此标准,但不能低。[注] 宋国宾:《上海市医师公会诊疗费参考表》,《医药评论》1935 年第121期,第66-80页。
过高的诊金将大部分工人及其家庭成员阻挡在正规医疗机构之外。“受诊金的影响最甚的,是那些比较穷苦的人,他们平常所入,原不过糊口,一旦患病以后,当然无从得入这种身价高的医师之门”。[注] 《疾病的社会性》,《华年》1934年第3卷第17期,第2-3页。 工人家庭大都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工资低下,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已实属困难。1929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对305个工人家庭调查,工资收入占收入总数的87.3%。“若仅以工资来维持生活,十家之中,亏短的有八九家之多。若以全部收入来维持生活,也有2/3的家庭入不敷出。[注]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426-427页。 工人得病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快速治愈,而是如何节省医药费:“于是小病他们就拚着过了,如果病重,则大约不是求神拜佛讨仙方吃,便是请教于那些只读汤头秘诀或在看护学校读过书的医生。”[注] 《疾病的社会性》,《华年》1934年第3卷第17期,第2-3页。 “……穷乏之家,或就中医,服中药,可省住院之费,或用土方,抓草药,所费更微;赤贫之家不幸患病,往往依仗平日抗病的能力,略事休养或竟力疾而作,希望自然复元,也有往慈善机关施诊之处,就诊乞药可免费用”。[注] 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08页。
从工人家庭医药开支看得出其在疾病面前的忍耐力。1927—1928年间,上海工人家庭平均全年药费1.98元,医费1.12元,医疗费支出仅占年支出的1.4%。[注]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292、266页。 1929—1930平均每家全年医费3.17元,药费2.88元,医疗费支出占年总支出的1.3%[注] 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423、426页。 。1937年对成都不同行业的213个家庭调查显示,相比于商贾店主界、军政教育界,劳动负贩医药费最低,每成年男子单位全年平均为1.65元。[注] 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108页。 工人家庭一般为3—6口之家,有老有小,而老人孩子患疾病的比例更高,所以这点医药费真正能花在作为青壮年的工人自身更是少之又少。
今天是竹韵到威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以来的第一次领工资,连工资加奖金领了2000多元,比下岗前的工资高得多,特别高兴,马上给龙斌的姐姐打了电话,要请她一家夜晚去她家吃饭,好好庆贺庆贺。这时,海力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要她马上去他办公室打一转,有重要事情要跟她谈。
联网收费是高速公路运营中的一项基本业务,征收的费用主要用来偿还修路贷款和改善公路路网条件,是高速公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高速公路收费业务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路网的规模越来越大,车辆的单次通行费用越来越高。部分车辆受利益驱使,往往会采用多种方式偷逃通行费并从中获益,如利用加装的假轴来减少通行费,而采用传统的稽查方法已较难发现这种隐性逃费行为,不能满足高速公路收费工作的管理要求。因此,利用高速公路收费数据甄别疑似假轴车辆成为一项重要且具有实际意义的课题。
即使如此,家庭成员发生大病,仍是家庭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工家庭的收入,多属入不敷支出。如遇发生临时事故,需要大宗款项时,则向外借债。……偶然事故如疾病丧事等,亦常陷劳工于不能不负债的地位。”对广州311家劳工家庭调查显示,现有借债的有151家,其中因疾病而借债的有19家,占12.58%。[注] 余启中:《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第636-638页。
(3)专业注重实验和实训课程,每学期开设3-4周课时集中实训,还将部分课程以“理论+实验”的方式教学,培育学生实务以及应用技术的能力。
对于以工资为收入主要来源的劳动者来说,疾病对其打击更大的还有工资的丧失而导致家庭经济来源的断绝。此时不但医疗费是额外开支,无法负担,整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也无法应付,这迫使工人不得不带病工作。“每日工资大多数仅敷全家一日之食用,毫无积蓄,除非不能支持之伤病,不愿任意休息,致绝全家食用费之来源而挨饿”[注] 陆涤寰:《几处工厂工人伤病调查之研究》,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385页。 。而这种情况又加剧工人身体疾病。
Application of Continuing Action Recognition with BP Neural Network in Desilting Equipment
(二)工人群体的疾病保障目标
在工人个体对疾病无奈忍受的同时,组织起来的劳工团体为解决疾病保障问题做了一系列斗争。劳工团体的目标是促使政府像西方国家或苏联一样建立疾病保险,由社会承担疾病保障的责任。疾病保险为德国1883年首创,至1910年,疾病保险在奥、匈、英、俄、波、捷、卢、塞等国先后实行。[注] 陈振鹭:《劳动问题大纲》,上海:大学书店,1934年,第589-590页。 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国家保险。这些措施在五四运动后伴随劳工保护的思潮传入中国。192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目标之一是促使北京政府建立由雇主和国家分担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制度。[注] 《劳动法案大纲》,《先驱》1922 年第11期,第1—2页。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促进政府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作为当前任务之一[注]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13-114页。 。1925年4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的未来斗争目标包括促进企业办理包括疾病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一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19-23页。
对于贫困工人来说,渐进的立法毕竟遥远,让所在企业负担自己疾病的责任更为实际。他们通过罢工方式要求企业给予疾病保障。王精彬《第一次劳动年鉴》中收集的1921—1926年37次影响较大的罢工事件中,[注]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283-335页。 有13次工人有对企业提供疾病保障的要求,占案例的3成多,内容包括病假工资、疾病治疗与死亡抚恤。13次罢工中9次有关病假工资要求,其中有6次要求病假中发全额工资,包括1921年12月水口山第一次罢工、1922年9月奥汉铁路湘鄂线全路工人罢工、1922年10月京奉铁路唐山工厂工人罢工、1923年1月大治铁山工人罢工、1924年4月奥汉铁路广东线工人罢工、1926年8—9月上海华商电车工人罢工。[注] 同上,第301、311、317、304、315、334页。 其余3次罢工要求发部分工资:1921年10月陇海路同盟罢工要求病假期间给半额工资,1922年10月京奉铁路山海关工厂工人罢工要求,病假第一月给全数工资,第二三月给半数工资,以后停给; 1926年3月杭州机织工大罢工,要求工人病时,公司每天给生活费5角。[注] 同上,第319、316、297页。 有1次罢工要求企业在工人得病时给予治疗,即1924年4月奥汉铁路广东线工人罢工[注] 同上,第315页。 。有6次罢工工人要求数额不同的病故抚恤: 1921年10月陇海路同盟罢工要求为半年工资,1922年10—11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为5年工资,1922年10月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为1年工资,1924年4月奥汉铁路广东线工人罢工为1个月工资,1926年11—12月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为6个月工资,1926年3月杭州机织工大罢工只要求公司给恤,无明确数额要求。[注] 同上,第319、302、305、315、292、297页。 可以看出,和工人家庭医药费低支出相对应,工人最关心的不是身体康复,而是生病期间的生活费问题。
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罢工的主要要求是增加工资,关于疾病保障的内容并非普遍,但它的出现反映了工人对于自身社会权利的重视。在当时的环境中,上述罢工中大部分疾病保障的要求得到满足,包括陇海路同盟罢工、京汉铁路北段工人罢工、奥汉铁路湘鄂线全路工人罢工、株萍铁路全体路矿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工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全体工人罢工、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武汉印刷工人罢工、上海华商电车工人罢工等11次。罢工的胜利给工人以信心,也让其他工人懂得疾病保障是可争取到的社会权利。
三、民国时期的疾病保障立法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疾病保障立法
当政者对工人疾病问题的重视,是在劳工保护思潮和劳工运动兴起的背景之下。五四运动后,劳工神圣的思想深入人心。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后,开始督促中国进行工厂立法以保护劳工。北京政府对内为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外显示政府的开明与合法性,开始制定劳工法,疾病保障是其内容之一。1923年3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暂行工厂通则》,规定工人“其因工作致伤病者,工厂应负担其医药费,并不得扣除其伤病期内应得之工资”[注] 《暂行工厂通则》,《农商公报》1923年第9卷第9期、第105期,政事门法规,第68页。 ,对工人的疾病保障虽只限于因工作导致的疾病,但明确了企业在保障方面的责任。由于北京政府管辖能力有限,法律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厂法,这些内容体现了政府对工人疾病保障的认知。
大革命期间,一些地方政权响应工人的要求,进行了工人保护立法,其中包括疾病待遇。1926年12月《湖北临时工厂条例》规定,工人生病(除花柳病外)后经过医生诊断,工厂须给予半薪和医疗费,因病死亡,根据在工厂的工作年限,给予抚恤金。抚恤金数目由工厂主和工会协商而定。[注]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一册),第698-699页。 相比《暂行工厂通则》,它对工人的疾病保障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保障不仅仅只针对和工作有关的疾病,而是包括了普通的疾病。保障项目包括了疾病的治疗,患病期间的工资以及死亡后的抚恤。1927年4月广东省农工厅受国民政府饬令拟定《工厂法草案》,规定对于工人的伤病(除花柳、肺痨、神经等病及争斗殴伤外),工厂应负担医治,至治愈为止,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并且治疗期间不得扣工资。[注] 《广州之工厂法草案》,《银行周报》1927年第11卷第15期,第8-9页。 疾病保障的范围同样包括和工作有关的疾病与普通疾病。同年冯玉祥在西安公布《临时劳动法》,工人患有包括痨症、白血症、喉症、重的胃症在内的16种疾病可以请假休养,期限不超过两个月,病假期间工资由劳动保险支付。[注]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191-195页。 这是政府首次响应工人团体建立社会保险的要求,以此来解决疾病保障的资金问题。由于政权更迭,这些法规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但它使社会各界对工人疾病治疗的社会责任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1930年3月铁道部《铁路员工服务条例》规定铁路工人无论是因执行职务原因而致病还是普通疾病,都由路局或路公司承担医疗费。治疗期的工资依据病因有所不同。若是因执行职务而致病,3个月内全薪资,此后减至一半,以一年为限。若普通疾病,第1个月全薪,第2个月半薪,第3个月则停发薪资。[注] 《铁路员工服务条例》,《立法院公报》1930年第16期,第3-5页。 同年5月《国有铁路员工抚恤通则》规定了病故待遇,在职满3年者积劳病故者,按照服务年限给予遗族抚恤金,最低为1个月工资,最高为1年工资。[注] 《修正国有铁路员工抚恤通则》,《铁道公报》1931年第133期,第4-5页。 1932年7月,铁道部发布《铁路医院及诊疗所组织规程》,规定铁路管理局得于该路适当地点设置医院及诊疗所,专司本路员工警察及其家属暨乘客之治疗救护等事宜。[注] 《铁路医院及诊疗所组织规程》,徐白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184-5185页。 1937年《国营铁路医院及诊疗所医药收费通则暨各铁路医院暨诊疗所征收医疗费办法》规定,国营铁路医院及诊疗所对于铁路工人除患疾病,除花柳病及使用X光外,都免费治疗。[注] 《国营铁路医院及诊疗所医药收费通则》,《铁道公报》1937年第1701期,第1-3页。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疾病保障立法
1.工矿工人的立法
回家的路上,媳妇被烧烤店老板留下的话把儿,飘飘荡荡地带进了五里云雾中。她想烧烤店老板要说什么呢?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话里有什么含义?难到那租住的房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掂量着,她想起一件事情。上午收拾屋子的时候,里屋房旮旯堆着的几块砖引起她的注意。平平常常的几块砖,上面粘着干枯的泥土,看着像是从哪个建筑拆下来的。但屋里的墙壁都好好的,没有破损。看来是以前的住户或是房东从别处搬来的。这里放几块砖干什么呢?她想。她嫌它们碍事,打算把它们搬到院子里去。就在她拆砖的时候,发现砖底下压着些烧焦了的黄纸残片。纸片上面依稀用红笔写着些稀奇古怪、字不像字画不像画的符号。
调查中,因维生素B缺乏所致的脚气病为工人多患疾病。上海公共租界公部局认为,“脚气病……为男性童工之通病。……在小工业之工人中最为普通。……食宿为童工之唯一酬报,今其所得饮食,乃致匪特营养不足,且为致病之原,诚为惨酷。”[注] 《关于工厂事宜报告:筹拟改良童工饮食以免发生疾病之计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报》1937年第8卷第5期,第6页。 1919—1923年上海工业医院住院的纺织工人,脚气病占5%。[注] H. W. Decker、哲隐:《八百八十件纱厂工人诊案的检讨》,《工商管理月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61页。 上海美亚织绸厂四厂工人患脚气病者居半数。[注] 湘:《四厂消息》,《美亚期刊》1927年第16期,第2页。
《工厂法》颁布后,企业、地方工会及地方政府纷纷提出意见。企业和地方政府要求国民政府对“伤病”及“执行职务”等范围进行严格界定。上海市社会局认为:“盖工人在工作时而受伤,此显见之事。若致病,则若无标准,便使牵强解释。不但工人有所误会,实易引起纠纷。故何种疾病乃因执行职务所致,似有明定之必要。”[注] 《函行政院秘书处(劳字第766号),准函奉兼院长交下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呈拟请求解释工厂法及施行条例意见书,转呈核示一案,谕交实业部审查具复函达查照等由,经详加审查,拟具意见,书送请查照转陈由》,《实业公报》1931年第43期,公牍,第47-48页。 上海市政府则认为如果工人的一切疾病都要求企业给予补助医药费,太不近情理。[注] 《函行政院秘书处(劳字第766号),准函奉兼院长交下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呈拟请求解释工厂法及施行条例意见书,转呈核示一案,谕交实业部审查具复函达查照等由,经详加审查,拟具意见,书送请查照转陈由》,《实业公报》1931年第43期,公牍,第44页。 上海永豫和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担心:“如本条第一项规定而不加之限制,窃恐工人中或有利用法文情事,而冒称有病,冀可依法请领工资,则厂方无以救济,而所受之损失实非浅鲜也。”[注] 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二续)》,《劳工月刊》1932年第1卷第3期,第70页。 上海总工会则要求增加伤病时工资、残废津贴、丧葬费与遗族抚恤金:工资由按比例发给改为全额发给,残废津贴由1—3年工资,修改为2—5年工资。丧葬费由50元增至100元。遗族抚恤费由300元及2年工资,增至为500元及3年工资。[注] 王莹:《各地修改工厂法意见(三续)》,《劳工月刊》1932年第1卷第4期,第131-132页。
1932年12月《工厂法》进行修订,有关疾病保障的内容并没有修改。至于何种疾病和职务相关,则由司法部给予司法解释:“伤病是否因执行职务而致,可由医师诊断定之。”[注] 《解释工厂法条文疑义咨(附工厂法奉行困难各条意见)》,《司法院公报》1932年第38期,第7页。 “所载工人因执行职务而致伤病云云,应其受伤或受病与执行职务有直接因果联络之关系为限”。[注]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五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为了使企业对职业病有所了解,1934年中央工厂检查处制定《主要工业品及职业病简表》,列举了工业毒品的种类、工人中毒后的症状、涉及工业的工人名称等内容。[注] 《主要工业品及职业病简表》,《察哈尔政府公报日刊》1934年第457期,第4-7页。 此表为工厂防范职业病提供了参考。
他跪伏着,听到天葬师的喉咙里发出了一连串怪异的咒语,繁琐而冗长。咒语结束后,周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除了桑烟经过骷髅头的呜咽声,再无其他声响。在这种单调的声音中,青辰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这种状态,令他在事后一度觉得非常困惑。按理说,那时的他在满怀期望地等待着神明的到来,怎么会睡呢?后来,他从其他人的口中了解到,那一刻,不只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过那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他推测,是有什么东西在那段时间降临了,它的到来,让人们的精神高度恐惧,为了防止精神崩溃,大脑及时开启了自我防御机能,选择性地屏蔽了它,让人们以昏睡般的麻木状态来度过那段时光。
对于工人职业身份对疾病的影响,可与农民进行对比了解。李维鑅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高桥农民与上海纺织工人的疾病率进行比较,发现除耳鼻喉病外,每种疾病工人疾病率都超过农村居民多倍。如法定传染病,农民为0.7‰,工人为59.4‰,内科疾病农民为38.0‰,工人为400.0‰。眼病分别为17.5‰和163.0‰,外科病分别为20.8‰与326.0‰,耳鼻喉病分别为6.7‰和17.6‰,皮肤病为42.4‰和344.0.‰。调查中的工厂的工人大都来自上海四郊,“地区、气候、风土等天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差异减到乌有。……在乡村为农民受农村天然环境支配,在城市受工业环境影响,疾病的发生率全因职业和环境的不同而差异。”[注] 李维鑅:《城市与乡村死亡率与疾病率的比较》,《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2年第28卷第11期,第388-389页。 农民和工人的就医意愿有可能不同,数据有可商榷之处,但职业身份对疾病的影响却是肯定的。
2.铁路交通工人的立法
铁路工人与交通工人是工人群体中较为特殊的群体。由于铁路与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其企业大都是属于国有。工人由各行业单独管理,有专门的规章制度。铁路交通企业经济效益稳定,铁路和交通工人的疾病保障,更能体现了劳工保护性质,其内容不仅包括和职业有关的疾病,还有普通疾病。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立法往往只满足现实迫切的需要,缺少社会各阶层有关利益者的参与,仓促出台。这也体现在疾病保障的相关立法中。由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工人势力的强大,立法内容更多体现了劳工保护的原则,以满足工人群体疾病社会保障的需求为主,而法律是否有实施的物质基础,即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本企业工人一切疾病的保障,也即法律的可实施性,却没有考虑周全。
邮政、电政工人由交通部管理。1928年10月颁布的《邮务职工请假章程》规定,员工凭医生证明,根据服务年限可享有不同时长的病假及病假工资待遇。其中服务不到1年者,可有2周全薪,2周半薪,2周无薪病假。服务10年以上者,可有4个月全薪、4个月半薪,4个月无薪病假。[注] 《邮务职工请假章程》,徐白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375页。 同时公布的《邮政职工抚恤金章程》规定员工在服务期间死亡,按照服务年限与级别发给家属抚恤金,其中工人级别的“信差、邮差、杂役”,服务未满3年者,给予3个月工资,服务期限3—6年者,给予4个月工资,6年以上者为5个月工资。抚恤金最低额为80元。[注] 《邮政职工抚恤金章程》,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五编),第98-99页。 电政工人的疾病保障也包括病假工资及病故抚恤,但保障水平不同。1928年12月颁布的针对机械线路的电政技工的《技工章程》规定,病假1个月不扣薪,在职积劳病故或离职半年内病故,按照服务年限和病故时的工资发给抚恤金,每服务1年,发给半个月工资,最高为15个月工资。[注] 《技工章程》,《交通公报》1929年第5期,第5-19页。
南京国民政府在劳资关系上主张劳资协调政策:“我国近奉遗教,以全民主义立国……政府为预防工农斗争,并维持工业健全发达起见,亟宜采用劳资协调政策,对于劳工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注]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66页。 政府宣称会保护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国民政府为民众之政府,乃为全民众谋利益的,并非为某一部分人民谋利益的。劳资两方,皆为民众之一部分,在一方面,政府固然要为工人解除痛苦,并提高其地位,而在他一方面,政府亦当维护厂方之机能,使其得以发展其营业,而后我国经济垂绝之生机,始有回苏之希望”。[注] 《工商法规委员会委员之讨论工厂法草案重要谈话》,《申报》1928年9月10日第13版。 这原则落实在疾病保障上,对于经济效益好的铁路交通等特殊行业,立法强调劳工保护和福利,企业负担工人一切疾病的医药费、病假工资和病故抚恤。而对于数量占多数的效益微薄且用工较多的企业,则仅负责工人和职务有关疾病的保障。一方面体现了基本的公平,一方面维护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1989年,曾被命名为“Project Jay”的研发计划正式走入公众的视线。一辆中等尺寸的SUV带领着路虎品牌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而它被命名为路虎发现。
四、企业的疾病保障规则与实践
由于政府对于工人疾病保障的立法较晚,而立法后实施的强制性不足,所以工人在患病时是否得到企业的保障,主要依靠企业的自觉。企业往往统筹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疾病待遇。
(一)国营企业的疾病保障规则和实践
国营企业因经济上的特殊地位而有较好的效益,且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所以在工人的疾病保障方面做得更多。如铁路企业,为了方便职工疾病的治疗,遵循《铁路医院及诊疗所组织规程》的规定,各铁路普通开办医院与诊疗所,至1936年,铁路部门有自办医院43所,自办诊所45处。每年各路经费共计大洋160余万元。[注] 王畏三:《各铁路卫生医务过去及现在之概况与将来之展望》,《铁道公报》1936年第1402期,第10页。 工人在本路医疗机构诊病,除花柳病外,不收医药住院等各项费用。这种福利甚至扩大到工人的直系家属,包括55岁以上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儿女,18岁以下的弟、妹。他们在铁路医院或诊疗所看病,挂号费、种痘费与防疫针免费,出诊费、住院费半价收费。药材费、处置费、手术费等减收四分之三。[注] 《国营铁路医院及诊疗所医药收费通则》,《铁道公报》1937年第1701期,第1-3页。 工人在规定的病假期间照发工资,这种待遇非常普遍,甚至出现因管理不严,有的铁路出现请病假人数过多的情况。1934年4月2日京沪沪杭甬路总务处卫生课通饬各诊所医师,签发请假单时务须审慎。实施两周后效果明显,员工请病假人数大减。吴淞段请假员工由每天60余人,减至8人。[注] 《两周来员工请假人数锐减》,《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4年4月第938-962号,第112页。 1935年11月14日,铁道部指令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转饬各级主管人员,对病假要严格审察,如有虚报事件,对请假职工及开证明书的医务人员都要一并严厉惩处。[注] 《部饬防维员工病假流弊》,《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5 年第1440期,第139页 奥汉湘鄂线也有同样规定。[注] 《本路员工因病请假难免流弊:医务员出具证明书加以考察》,《铁路旬刊:粤汉湘鄂线》1935年第120期,第21页。
2018年 6月 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6月29日起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中国人大网站的数据,截至7月28日,共收到意见131207条,参与人数67291人。
在工厂矿场中,国营厂矿工人的疾病待遇也相对较丰厚。本来依《工厂法》,工人因职务有关的疾病才能得到保障,但何为疾病和职务有关,本身无关严格的标准,“工人生病……是否积劳抑或某种职业病所致,颇难断定”[注] 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157页。 ,企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自由权。一些国营企业通过工厂规则,将一切疾病都给予保障,职业病及普通疾病都有相关待遇,这就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如军政部所属军需工厂、军政部兵工署直辖工厂,建设委员会所属一些工厂矿场等。军政部要求各军需工厂内设有医务室,职工发生疾病时予以治疗或给假医治。[注] 《军政部军需工厂工场管理规则》,《军政公报》1929 年第36期,第18页。 职工因病请假,病假内30日内照支工资,此后给予半额工资。[注] 《军政部军需工厂职工雇佣规则》,《军政公报》1929 年 第36期,第23页。 兵工署直辖各工厂工人患病根据服务年限给予病假工资,因积劳成疾死亡者给丧葬费100元,并按其继续服务年数给予1—6个月工资的恤金。[注] 《军政部兵工署直辖各厂工人待遇暂行简章》,《军政公报》1931年第123期,第10-13页。 建设委员会为方便职工诊病,聘任医官坐诊,职工与家属诊治不收诊金。此外,和中央医院签订就诊办法,职工在中央医院就诊仅自付超过规定的费用。[注] 《建设委员会职工就诊规则》,徐白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239-3240页。 建设委员会模范灌溉局及所属机关工人、首都电厂工人和戚墅堰电厂工人生病时医药费由机关或工厂负担,30日以内的病假内工资照给。[注] 《建设委员会模范灌溉管理局及所属机关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4年第41期,第136页;《建设委员会首都电厂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0年第4期,第92页;《建设委员会戚墅堰电厂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0年第4期,第95页。 电机制造厂工人生病时医药费自理,30日内工资照给。[注] 《建设委员会电机制造厂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0年第4期,第98页。 长兴煤矿局工人生病时,2日内不扣工资,医药费由矿局负担。[注] 《建设委员会长兴煤矿局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1年第18期,第240页。 淮南煤矿局工人生病时,由矿局负责医药费,工资照扣。[注] 《建设委员会淮南煤矿局工人管理规则》,《建设委员会公报》1931年第18期,第244页。 以上疾病都排除花柳病。
(二)民营厂矿的疾病保障规则和实践
民营厂矿的疾病保障情况则比较复杂,对于大多数工厂来说,规模小且利润薄,生存本来艰难,工人的疾病保障往往不在其考虑之中。1936年中央工厂检查处对南京、青岛、天津、汉口、北京等工业区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工厂并不能依照工厂法的规定在工人伤病时给予津贴与抚恤。[注] 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中国工厂检查年报》,(南京)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1936年。 但仍然有一些厂矿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下,制定了明确的疾病保障规则。工厂中有永利制碱工厂、久大精盐工厂、华新纱厂青厂、永裕精盐工厂、福星面粉工厂、恒源面粉工厂、光明实业公司、启明电灯公司发电厂等。矿场有中兴煤矿公司、富源煤矿公司、湖南水口山锌矿局、保晋矿务公司、六合沟煤矿等。保障项目包括医药费、病假工资、丧葬费、病故抚恤等类别,各企业所采纳的项目不同,标准不一。待遇较好的工厂如永利与久大,工人疾病治疗期间给本月全月工资,病故后给棺殓费40元,抚恤金根据服务年限为最低3个月、最高15个月的工资。矿场中以中兴煤矿为最高:里工患病,由矿场负担医药费,治疗期工资折半发给;未能治愈,工作1年者给予1个月工资,以后每多1年多给1月工资,以半年工资为限。死亡时,棺殓费50元,抚恤金根据工作年限为3个月至1年工资。[注]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五编),第287-288页。
疾病保障待遇包括疾病的治疗(医药费补助)、病假工资和病故抚恤。在这些项目中,企业较重视的是工人疾病的治疗。一些厂矿为了方便工人伤病的就医,在北京政府时期已开始举办医疗机构。大型的矿场由于远离城市,不能共享城市中的医疗设施,而且工人众多、矿业危险大,伤病问题不容忽视,所以一般都自建医院。如开滦煤矿、中兴煤矿、抚顺煤矿、柳江煤矿、本溪湖煤铁矿、大窑沟煤矿、淄川煤矿等。这些医院不但能够为工人诊治伤病,还能服务附近的居民。还有一些管理较为先进的工厂,如塘沽久大精盐公司及永利制碱公司、商务印书馆、裕元纺织、华新纺织等也建有医院。另有一些小企业,办有药室或病室,聘请医生坐诊。[注]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1-12页。 1930年12月颁布的《工厂法施行条例》要求雇用300人以上的工厂,应当设置医药室、储备救急药物、聘请医生。[注] 《工厂法施行条例》,邢必信等:《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第9页。 此后企业的医疗卫生设施得到较快的发展。实业部1933年调查的31个县市483家较大的工厂(包含有国营工厂),其中占总数的8%自设医院,14%自有医药室。更多的小企业则通过签约医院为工人治疗疾病,在调查中占比有72%。[注] 吴至信:《中国劳工福利事业之现状》,《民族》1936年第7-12期,第1702页。 工厂、矿场举办的医院或诊疗所,对于本企业的工人治疗疾病,除花柳病外,一般不收费。[注] 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196页。 治疗的疾病并不限于和职务有关的疾病,也包括普通疾病。因此,企业的医疗机构是工人疾病治疗的重要保障。
疾病保障的另一个项目——病假工资,各企业的待遇差别较大。1937年,吴至信调查的规模较大或管理比较进步的厂矿中,有23个民营工厂和8个民营矿场,其中仅有6厂(占比1/4强)工人和2矿(占比1/4)的里工有病假工资的待遇。所有矿场的外工都没有。病假工资的标准各不相同。吴至信考察了各厂矿不付病假工资的理由:“彼等并非不同情于工人罹病后之苦况。惟事实上因厂属医院或指定医院之医生不愿结怨工人,随便签发病证单,猾懒工人遂得藉此作弊。”[注] 同上,第149页。 这和《工厂法》制定过程中一些企业对疾病保障的担心相同。
相对于病假工资,病故抚恤更为普遍。吴至信调查的民营厂矿中,有16厂(占比2/3强)工人和3矿(占比1/3强)的里工有病故抚恤。[注] 同上,第117-118页。比例为计算得到。 病故抚恤有的为定额,有的按服务年限计算,有的酌量给予。“均视同一种赠与之补助,为数恒较公亡恤金为小。”[注] 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第157页。
工人的疾病待遇,当时被认为是工厂的救济或福利。企业举办福利设施或发放津贴的目的不同,有的从生产角度考虑,认为是“促进生产之一必要条件”;有的是从管理方面考虑,认为“使工人安心工作,不思‘跳厂’或转业”;有的则从社会责任方面考虑,认为是“工人应该享受之种种权利”[注] 同上,第196页。 。工人是否取得保障,是企业对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两方面权衡的结果,而与政府的推动关系不大:“其成功之主要关键,以雇主自觉为最要。政府督促或工人要求,虽不能否认其力量,但常只获得表面或暂时之设施,有时反而阻碍其他惠工事业之正常发展,引为吾人至堪寻味也。”[注] 同上,第117页。
本文所用的EP原理图见图1,EP电解液采用HF(40%):H2SO4(98%)=1:9(V/V)的混合酸,超导铌腔作为EP正极失去电子,高纯铝棒作为负极使氢离子转化为氢气,EP反应见方程式(1):
总结
民国时期,为了应对工人疾病问题,工人群体、政府和企业等社会主体都做了努力。工人群体在家庭保障不足,不得不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保障目标。北京政府在劳工保护思潮、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出台疾病保障的相关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则在劳资协调原则的指导下,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制定了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的疾病保障立法,旨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承担工人的疾病保障责任。企业则在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两者间综合考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给予工人以不同的保障。
从社会保障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工业化早期的社会保障模式——雇主责任制社会保障模式。其特点是,在国家立法提供原则的基础上,由企业来负担疾病保障所需要的资金。由于筹资机制没有实现社会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所以保障水平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保障的覆盖面窄,仅包括铁路交通行业十万余工人和六七十万工矿工人[注] 据统计,1933年国有铁路工人为8万余人,交通工人职工为2万余人。20世纪30年代铁路交通行业受益人群有10余万人。1934年适用于《修正工厂法》工厂工人人数为52万余人。1936年适用于《修正工厂法》的矿场矿工数13万余人。20世纪30年代工矿业受益人群有六七十万人。(《中华民国廿四年国有铁路统计》(第一种),《国有铁路劳工统计》1934年第1期,第7页。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一编),第289-295页。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中国工厂检查年报》,南京: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1934年,图表第44页。实业部中央工厂检查处:《中国工厂检查年报》,第655-663页。) ;保障的水平差别大,只有铁路交通及部分工矿业国有企业及少数民营企业工人的一切疾病都有保障,大部分工矿业工人只有和职务有关疾病的保障,而且实施起来随意性大。但疾病的企业保障本身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是在工业化经济背景下、工人疾病导致的社会问题出现后,政府、企业与工人群体多方博弈的结果,代表了疾病保障责任从家庭到社会的转移,是疾病保障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实践。
作者简介: 刘秀红,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劳动灾害预防与赔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1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7-0035-16
责任编辑: 王望
标签:民国工人论文; 疾病论文; 保障论文;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