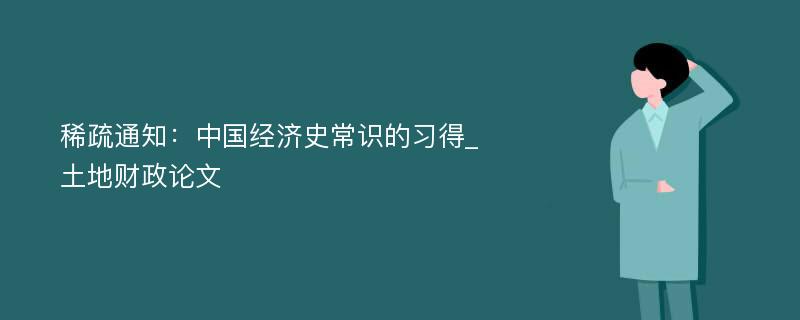
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1873(2006)05—0144—06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虽是一本论文结集,写作于不同的时间,但前后脉络一贯,作者关怀的重心始终放在“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经济历史变迁的关系上,对土地制度、财政赋税、小农经济三大问题作了联动式的梳理,恰如书名展示的那样,特色显著,有自己的独立思路。这一论题也是我个人科研的兴趣所在,与作者往来切磋甚多,算是知音者中的一个。如今搏非兄既有意乐成之,① 自当略仿“我辈从来文字饮”的古谊。
念祺决非高产学者,自嘲曰:“所著甚少”(《自序》)。若著作等身者与之较劲,与倚马立章者搏出手,念祺的少与慢就成了软肋。继云“人又散漫”,则自谦过当了。人之兴趣各别,思维的习性往往相差甚大。有勤于耕耘者,连作细耕不辍,收获不断。也有用心观察,静时多而动时少。然凡有中意的猎物出现,猛然一跃,必有大的斩获。念祺似属后一类,不了解的以为偷懒,知己者则赞其沉潜多思,猎狗有道。
这几年学位论文比GDP增长还快,看的论文不少,但读念祺的文章常常使我产生异样的感觉。他对史料稔熟,大学一年级就已经把《资治通鉴》遍读一过。此后自立家室,对先秦、秦汉诸书更是异常酷好,时时咀嚼,已内化为己身的学养,浸润出一种境界。这些,都可以从文章里感受得到。另一特点是行文承乃父“优美白话”风格,俗而兼雅,考据从大处着眼,征引则要言不烦,但求文意连贯,陈述流畅,故史料多经消化融解,绝不显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顾驰骋思辨,玩咏自得,以为别人也烂熟于掌故,省略去许多常识性的交代,有点像鲁迅说的,可以写成短篇小说,决不掺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长篇小说。有相当中国通史基础的,我想读本书必能深味其疏通知远、以索贯钱的不易。
念祺始入大学历史系,已是1979年夏秋之交,属“老三届”有幸进入高校的第三批。其时,我才过不惑之年,谬忝授业老师,一样蹉跎了十余载青春岁月,年龄相差不大,同命相怜,感情不一般。记得连续聆听赵俪生讲授“土地制度史”,皆为才子型的翩翩风度醉倒,方始知道天下还有这样能用潇洒动情的方式表述深刻思考!念祺升三年级,我蒙系上特允,挑选一些人“脱课”作江南乡镇历史考察,一行八人,竟走了一个半月,巷尾村头,访贫探富,什么都感到好奇,收获是书本上读不到的。回想起来,启蒙我们经济史研究思路的,有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起步不久,有幸多次接触这位史界前贤。他对待年轻一辈坦诚平等。听过他讲王亚南、郭大力讲课不同风格的故事,深羡其受惠于老师《资本论》的研究,对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深悉个中三昧。其书人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学”,十分耐读。赵、胡两先生的学术影响,或显或隐地在念祺的文章里常可以见到。80年代,读书气氛极浓,思想比较单纯,交往也不掺功利心。看到什么好书,相互推荐,找来就读,无论中西与古今。即使读守实老的土地制度史,有佶屈聱牙的味道,因其深刻玄妙,也不敢丝毫怠慢。我和念祺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愉悦地走进史学园地。
如果从胡如雷书体验到了逻辑分析的力量,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长文,则为我和念祺打开了获取经济史通识的路径。翻阅旧刊,偶然见到《川大学报》上的蒙文,读后大喜过望。我的《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处女作,就是在先生此文启发下写成。文通先生尝自言其治学方向的转变道:“后寓北平(1933-1936),始一一发南宋诸家书读之,寻其旨趣,迹其途辙,余之研史,至是始知归宿,亦以是与人异趣。深恨往时为说,言无统宗,虽曰习史,而实不免清人考订獭祭之余习,以言搜计史料或可,以言史学则相间犹云泥也。于是始撰《中国史学史》,取舍之际,大与世殊,以史料与史学诚不可混于一途也。”现在蒙著《中国史学史》讲义总算面世了,新读所附《宋史叙言》,更觉文通先生以向心力与离心力通释先秦迄明清的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系,数千年间学术风气种种跌宕起伏的因缘尽数托出,赏心悦目。体验到前贤不仅要求识字(小学、经学),更追求经史事理相通,达至“疏通知远”,知所取舍。要求眼光须极远,不局促一朝一代,不满足“考订獭祭”,从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历史观察中,由大量似续似断、似是而非的史料丛林里,“迹其途辙”,察变观风,使史识不为落空,并能看出历史内在的关节,一以贯之的脉络来。那是何等地不易啊!念祺作文,大抵本此旨趣,故致数月或积年而不得动笔。我常起恻隐之心,劝其何苦呢,这不是在跟自己过不去?然而,心里明白,唯有跟自己过不去的,对前贤的心向往之,不致徒成酒足饭饱后的谈资,学问亦可能会有真长进。
蒙文通、柳诒徵、陈寅恪都盛赞一位少为人知的经史名家,他就是蜀中奇人刘鉴泉。鉴泉先生强调疏通知远就是察变观风。他说:读史有出入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气之变迁,出也。不尽力搜罗全面的史料,沉浸其中,就不可能把握过程全部,原始要终。不瞻前顾后,用心比勘,也可能被史料压垮,捉不住变迁关节,仅为两脚书柜。进得去,出得来,疏通知远的境界也就可能达到。我们常有挤牙膏式的疏通,用一段,挤一段,囿于局部所见,顾此而失彼,就是因为缺少了鉴泉先生说的那种功夫。
说到疏通知远,整理历史脉络之何以可能,就联想到中国的经络系统。此种系统,用西方人体解剖学无法对应于某物、某系统,成了一项至今还未曾被人破解的“人体科学之秘”。然中医使用于诊疗疾痛方面,痛则不通,不痛则通,对症下针,屡试而不爽,效果非常之灵验。疏通中国历史的脉络,一似发现无形的社会机体运行经络,亦须有同类的体验——无有读书时感受到的历史动态运行的“痛”与不通,获取脉络方面的灵感难以产生。因此,以寻觅历史脉络为目标,必须经历痛——不病——通、又痛——又不痛——又通,这样反反复复的史料磨勘贯通,不断注重从动态中触摸、体验历史的演变,积久才可能有总体性的领悟。这绝不是一条功利捷径,却是治史者理应备尝的炉火煎烤。赖此作底,或专或深,即使是偏隅一方的专门家,也不会滑行到前贤所痛疾的细琐杂碎、雕虫篆刻一路去。我非常钦佩苏秉琦先生。他虽是考古名家,专注新石器时代的地下发掘,却具有超常的史学通识,卓然开拓出“大考古”的新径来。
上世纪50、60年代人称“五朵金花”的争论,与本书诸多话题均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土地究属公有、国有、私有,是时各说不一,争讼难解,就像众多古碗粉碎于地,堆在瓦砾之中,随便拾取其中的几块碎片,都不难说出一通评论来。② 我一生甘为教师匠,因讲课的需要不致对争论漠不关心,也偶有评论,却易犯弃新厌旧之病。念祺则非,他的固执也在这里。旧潮已退,新浪涌动,时人以专偏争奇,对此项公案已经兴味索然,他却把这种争议看作思维之痛,偏要钻进故纸堆里,追根溯源地弄个明白。此即颉刚先生所谓之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一痛,就痛了十余年,现在总算有了反复出入的完全体验,可以向读者交代出一个“察变观风”的头绪来了。
文集第一篇,实为全书“导论”,是帮助读者进入他所描述的变迁轨迹的引子。人为群体动物,村社集体所有制,可能是农业民族最古老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孟德斯鸠、卢梭的始于个人开垦占有说,乃是私有产权逻辑化所作的理论假设,几乎不可能成为历史初端。根据姜寨村落遗址的分析,我认为至少五六千年前我们已经有公田共耕与份地分耕(分配到户)的“二元经济”格局。以后历史变化的奥秘,正如本书所疏通的,就看公田、份地的性质如何一步步异化,以及“份地”如何日益细碎化,日益的动荡不稳定(秦以后,仍把小农自耕之地看作是国家给予的份地;所谓“占田”、“口分田”之类的名称,由此而来)。
变化的动因是什么?念祺对《尚书·尧典》“食哉惟时”一段高度敏感,是谓用心读书,文字的意义会跳跃而出。由此而得启迪:从农业稳定开发与定居的需要出发,一条由部落林立、中原自保、相互联盟,过渡至国家组织形式多元分层控制、分散制衡,最后演进为专制集权的变迁轨迹,被一步一步描述出来。③ 其中各种争夺土地资源的内外战争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如同自然灾变一样,是推动进入文明时代、引起组织变迁的强大推动力,由此而早熟地催生出政治统治形式的大型化以及后来的精密化。以战争为动因,我们现在看到了念祺所揭示的一条规则,那就是:军事人力与军事费用的增长,导致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组织体制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体制的变化,反过来又引起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成功地创造出了特定的农业大国,大国一统的规模,军事——政治体制的集权与大型化,都为世界所罕见(世界上也有过一些大帝国,缺乏此类不二法门,多为松散凑合,兴也勃,亡也速)。然而由此付出的制度成本费用,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望尘莫及的。④ 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体验的识史眼法。舍此而评估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小视死去活来的顽强生命力,就是为其发展的外在视觉形象所蒙蔽,莫名自得。现今显露的缺陷,就是认不清中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是相对的,却将近代历史沉沦尽归咎于外人。历史演进内在的弱势与隐患既被掩饰遮蔽,在中外有些人的笔下,“中国中心”就走调为中国从来就是好、什么都好,可以孤立自在地继续走下去,有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意识形态。
念祺的这种研究的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众所周知,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而不是像第二热力律所说的,两极高低不同的热能由传导运动产生熵值那样,有一个能量耗散的过程。念祺冥想苦思的结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耗散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遂日形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投入仍极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关节。说实话,这一觉悟在我则要晚到些,由弗兰克、彭慕兰引起的思维之痛,才变得强烈起来: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所以我在这里要向读者特别推荐这一有特色的方法论,拨开笼罩在中国经济现象表面种种迷雾,识破内在机制的一种特别的破码技术(与王国斌的对话,对此又有深入,请参《史林》发表的座谈实录⑤)。
对中国历史知道得越多,苦恼也越深;苦恼越深,收获亦多。周武整理的柯文访谈录,很值得一读。⑥ 它非常生动地表述出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认识不断演进的心路历程。柯文的独特,就是为学不苟且,不满足既有的成绩,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停步地问自己,以什么样的角度与方法理解中国历史最少偏差?故每走一步,均有创获,不在原地兜圈子。在我理解起来,柯文“中国观”视角转换的典型例证,正好说明中国历史的侧面非常之丰富,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观察背景之下,给人的感受可以多种多样,甚且截然相反——这里不仅仅是史家的主观意念在起作用,也是历史客观方面的多面性必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斑驳杂陈,单色调、单视角的描绘不可能完美传达她的意蕴。许多不同的印象或诠释,并非一定是此对彼错,冰炭不相容。相反,极有可能它是一种很好的互补合成,有助于立体地完善对中国历史整体情景的理解。可惜的,我们有些人不像柯文那样由自我检讨而引出反思,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昨日“西方中心”还唱个不停,尔今忽成了铁杆的“中国中心”,扶得东来西又倒,少有独立的主见。
许多事情,都难于用一面说煞。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既是真实的,可底气却是虚假、病态的,这是胡如雷揭发的一项秘密。现在有念祺的“财政市场”一说,使这一论题变得更为强有力,除非皇顾左右,故意绕开,想直接否定也难。⑦ 同样,私有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史料里遍处可觅。契约、契税的存在,证明民间产权的买卖确然常见。“千年田,八百主”,常被形容为私有产权活跃的标识。但进一步追究这种属于地主、自耕农的土地产权何以如此地不稳定?他们是因为哪些原因失去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新获得者又是靠什么力量获取的?为什么私有土地可以由一纸公文遽变为国有,一夜之间民田收为官田?一系列的疑问,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私有,有自己历史的脉络与风味。从“履亩而税”的“彻”法作为始端,村社土地所有制逐渐地异变为土地国有制,即君有或王有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大变局。从此而后,土地经济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无论是地主或是自耕农申报的土地,在国家则只是作为一个赋税的单位才具有真实的意义,才会被认真对待。因为国有制在本质上把土地所有权从属于国家主权,满足于把所有制关系意识形态化(即把分地到户的原始过程普适化为终极过程,认定所有土地归根到底都是君即国家给予的),不想用心使之制度化为具体可由私人操作的铁定规则。相反,除随意赐田、夺田的政治手段外,赋税采取舍地税人,偏离地权变动实况,⑧ 直接紧抓户口人丁,不合经济对等原理,却切合国家力量的需要。因为它对国家来说较为简捷,监督成本相对要节省些,因此变相的人口赋役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即使是摊丁入亩之后。这种怪异荒诞的做法,只有用国有制意识形态解释,才变得可以理解。这就不难看到国有制的各种实施策略,只是以权力需要为根本,以财政剥夺为中心,这就决定了民间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作为一种反控制(或者叫钻空子)的应对必然出现。我认为念祺发明的“非制度化”提法,对于识破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与特色化也是一个重大关节。
在中国古代,国有制的意识形态,是专制集权盗窃领土共同体的公共需要为合法性根据,以“国家”的堂皇名义,“公共产业”虚幻的面貌出现的。因此历史上只有公私之辨,却从无国有与私有之辨。历代帝王,表面上从来不会承认国家乃是自己的私产。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老调不歇,但在儒家的解释里,已经变成“大公者,群私之总和”的意思。⑨ 因此,从“吕尚”开始,一直到康熙,治国者发现此一说可以利用,也高唱“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或借以扼杀别人营私舞弊的企图,或为取而代之挡门面。⑩ 只有司马迁故意泄密,说刘邦对其父亲炫耀:不是老责怪我不事生业,现在你可明白了,我的产业比老哥的谁大?惟因为有这个故事,黄宗羲才紧紧咬住,说出“天子实以天下为一己之产业”的狠话来。看来在古代,看穿国有制意识形态秘密的,司马迁可能是第一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做出了超乎前人的历史反思。这样的人,可能还有,需要好好发掘。例如青浦朱家角在乾隆时代出过一个人物,名叫王昶。他在给吕青阳的信里,发过一段议论,可以为念祺的论述作为旁证,抄录于下:
天之立君,理处于不得不然。而圣贤之作之君也,情每出于不得已……其至因以民力之所出献于上,君十卿禄、卿禄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劳以次而杀,则其食之也以次而差,率民之所为报也。是以唐虞名“贡”,下奉上之词也;商以“助”名,犹以下助上为言。及乎称“税”、称“敛”,始成自上取下之词,不知其义取于相报。(11)
虽然王昶还不敢直斥君主攫为私产,但能从征收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出政治组织性质的畸变,点出“天作之君”的意识形态,实是窃取早期部落以“贡”、“助”交付管理层劳务费用的“公意”(此种状况在姜寨即找得到实证),异化为“国家力量”自上而下聚敛征税的霸王规则,失掉了原来自愿的初衷。这倒无意中也为马、恩所说的“从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作了极好的注脚。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固然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使用,但毕竟空洞虚幻。自从贵族分层分治制度消失后,除帝王一人,谁有权支配“天下”这样摸不到、看不着的庞大产业呢?表面上是人人有份,实际除帝王一人而外,人人都没有自由支配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也都不会认真对待“公产”,消解不了下面“无制度化”的私有欲望。既然皇帝公然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以为天下之利害皆出于我,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随己好恶分羹于臣僚,还有什么理由禁止别人偷偷攫夺一份“私产”,甚且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因此,从上到下,各种准合法、不合法的私自瓜分与攫夺,不胜繁多,网漏于吞舟之鱼。大皇帝之下,有无数的土皇帝。记得当年赵俪生是把公与私两大因素的此消彼长,作为观察人类全部土地制度史演变的一条线索,而且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要走向公有制。然在我看来,公与私的矛盾,在国有制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定会变得尖锐与畸形,以隐蔽与诡诈的手法化公为私、以私冒公,代不绝种,渗透影响及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从未有过一清二楚的了局。悲剧或者悖论也就产生。“国家力量”认为“公意至上”,理直气壮要求所有的东西都整合在自己的统制之下。自认为国家的威权是无限的,有权随意限制和剥夺私产,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特别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占田流产,均田瓦解,抑豪强无效,均赋役失灵,有多少是完全成功的呢?
许多观念形态的东西,放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品出不同的味道。例如历代有关“不扰民”的议论,见于诏谕、奏疏、文集,不可谓不多。固然说者心态不一,也没有理由怀疑全是假话,然而国家政治——军事开支之大,时有临时增加的项目,想不扰也难。往往是叫喊不扰声音最高之时,却是国家扰民最厉、民财岌岌可危之日。最近一直在读《清经世文编》,里面有许多实情是我过去不曾体会过的。例如,明清以来,包括三大思想家指责吏胥之剥害百姓甚于官僚,犹如我们曾经狠斗地主,把旧社会的罪责全赖在他们头上,却把真正的元凶——“国家力量”放生出去。吏胥之存在,绝非任何个人意愿所致,而是上下事务日益繁复的政治体制不得不有的法外补充——除非体制改变,此病不能根治。袁枚就直言不讳地说:“夫州县之胥所以恃以剥民者,无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剥州县者,亦无他,文檄而已。”何以如此?黄宗羲剖析得最为深刻:“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黄梨洲说出“非法之法”,眼睛极尖,大可为念祺的“非制度化”作为佐证。
与此相关,明清以来愈趋严重的害民苛政之一,就是地方上各种耗费、陋规征收。此类摊派,虽多有收入私囊的,原委正是因地方行政经费严重短缺,中央爱莫能助,暗中默认,亦为非法之法。雍正“养廉银”制度的改革,连孟森老先生也多有赞扬,至今绝少有人注意到它的痛处。乾隆七年,孙嘉淦在《办理耗羡疏》里,追溯雍正设立养廉银制度原意是将各类名目繁多的地方耗羡统一为附加税则,上缴至省库,大半给地方各官为养廉(实弥补其开支缺额,并非全为个人所得),留其余以补地方公务之缺额。立法之始,即有沈近思等“以为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羡”,表示忧虑。果不其然,“黄宗羲定律”再次显灵,因此而有乾隆年间的检讨。直至咸同年间,另有厘金的发明。我近来忽然对州县官吏动起恻隐之心。这七品官不好当,尤其是经济发达、税役繁剧之区,三头六臂也满足不了上面各级各类需求,项项都得向下索取,程序繁琐,编制卡死,不搞点编外人员,不堪应付,难啊!然而编外的人不可能喝白开水过日子,上面不给费,不设法搞“创收”,行吗?于是而有一种说法,兴一事不如少一事,以立国之大,立法、行政不能尽察,即有良法美意,而推行辄生弊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欲民之自由,莫若去其泰甚,无为而治(语载柳诒徵《国史要义》)。
可惜这是一厢情愿。无为而治,律之史实,汉初曾有过,已尽非原意,以后就只是对扰民政治的一种无奈抗诉而已。由柳先生的说法,我得到启发,当中国村社共同体瓦解不久,专制集权还没有整装走向前台的时候,老子却已经敏感到:村社共同体乐其俗、安其居的小自由,必被霸道的大一统新潮吞没,万物将为刍狗。他明知重返小国寡民不可得,乃创造出一种软性哲学,曰:无为而治,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岂知历史如大河奔流,千里的凉棚已经搭就,等着盛宴的挨挨挤挤,唯恐落人之后,那大排场想收也难了。柳氏那样的文化保守之见,阐释圣贤义理尚可,于今日经制研讨就不免迂阔,至于想讲事功,那反露出百无一用的书生尴尬本相(曾、李、左肯甩掉书生气,事功有成,然柳氏颇为不屑)。新的路向在哪里?这是现代的课题,不在我们要讨论的范围。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今日,萝卜贵过米薪,苦旅成了豪华游,再沉浸在千年历史变迁的话头里,以苍生是念,忧这忧那,实是把自己拖进深渊峡谷,离世俗太远了。念祺与我已经掉进去了,有多少人理解?不知道。勉力前行,能够逐渐近道吗?也不知道。过程是一种美,经历就是人生,这可能已是坚持追求唯一的救护神了。那么,就让他继续兴奋我们的神经吧!
注释:
①编者注:此文原是王家范教授为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一书所写的书序,应《史林》之邀,先行发表。
②此一比喻取张荫麟之意略改而成。引自张之译编文《论作史之艺术》,载《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
③若有批评,我认为中原地区部族发展最为早熟,以中原为中心叙述固属不可,但对东南西北不平衡的发展就关照不够。局部地区的并合,与大一统意义不一样,强调过早,正合有些人的胃口,我向有保留。
④念祺说:秦朝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专制集权统治,其难度势必高于统一之前的任何国家,唯此秦朝必须支付的费用,因政府组织本身的规模的巨大和政府控制难度的提高而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这里,可以看到制度经济学是他借助分析的依靠,然没有通常的那样张扬“多学科渗透”,运用时了无声息。
⑤详见王国斌:《18世纪以来中国财政变迁及相关问题》,《史林》2006年第2期。
⑥载《史林》2002年第4期。
⑦其要点为:在中国古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本质上就是对财政的管理。国家的经济政策,根本上是以财政为中心的,而市场则被国家作为组织财政的工具。(赋税)以征收货币来强化国家的财政储备,以及灵活开支,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一个方面;以专利制度来弥补税人之不足,则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另一个方面。请详参《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一文。另外他对许倬云的批评,也涉及此一问题。
⑧例如占田、均田规定的数目字,是一种概念,被看作国家容许民户占有土地的限额。因此看似有数目字管理,实则自由放任,说管又不管。黄仁宇的批评,没有说清这一情景,但他对中国古代制度缺陷的判断,还是有新意的。
⑨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他们不明白,一旦小私被专制集权的“大公”总起来,不会是1+1=2,而是1+1<2;总加越多,即统的越死,一己之私的原值,便会逐渐缩减,趋近于零!
⑩吕尚语出《六韬》:“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康熙61年语见《御制文集》。现在有的人以为是明末思想家首倡,实系失检。
(11)王昶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为“吴中七子”,他的诗文结集《春融堂集》共60卷,姚鼐、俞樾曾先后为之作序。书信引语出自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