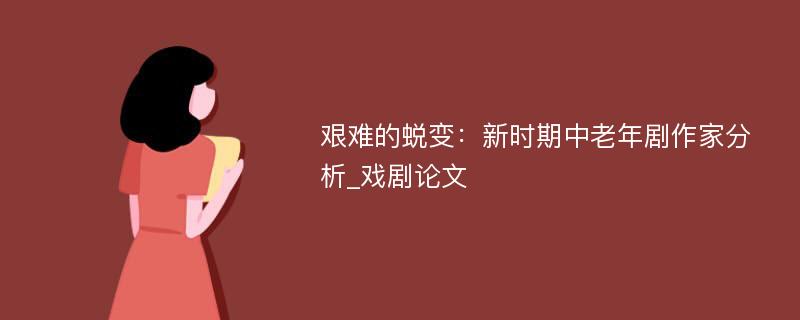
艰难的蜕变——新时期中年剧作家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家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年论文,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蜕变”的过程虽然痛苦,虽然艰辛,甚至时时挟裹着触及灵魂的巨痛,但中年一代剧作家们毕竟在新时期完成了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艺术上蜕旧变新的过程,“阵痛”之后的生机与希望便盎然地呈现出来。蓦然回首,他们在“蜕变”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有的痛苦而艰辛的心灵历程就不再属于他们个人,而属于时代,属于历史。笔者认为,把他们在新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哲学思潮、文化思潮及戏剧思潮的冲击下所经历的那场特殊的心路历程置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加以观照,并探究他们在理论及创作上的成败得失,是颇有启示意义的。为此,本文把新时期的中年剧作家群体及他们艺术上的“蜕变”过程作为观察点,进而对政治与戏剧的关系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思考。
新时期初年的戏剧创作作为对“文革”戏剧的反动,的确是戏剧史上的一大进步。剧作家们开始恢复“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把说真话、抒真情作为自己自觉的美学追求。但是,剧作家们的意识深处还未完全摆脱“左”倾戏剧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跨入了今天,可在戏剧观念上,他们仍然徘徊在昨天,“左”倾思潮仍如梦靥一般地缠绕着他们,束缚了他们的艺术思维。剧作家崔德志在《创作要有个新的突破》[①]一文中把“新”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表现新的冲突,揭示新的思想”,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干扰,把阶级斗争当作作品的主要主题,为政治服务成为作者的职责。三中全会后,我们的笔已开始转向描写新长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变成大家遵循的创作原则。今天,我们应该更加自觉地、出色地反映新时期的生活。”其二,“作品中的人物应该更新换代,建设时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要成为主要描写对象。我们写过战场上的英雄,阶级斗争中的勇士,那些塑造得准确、成功的形象曾鼓舞了人民,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他们已经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和文学史上。但是,今天作品的主人公应当是驰骋在四化战场上的风云人物。他们是要用双手在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代新人,身上闪烁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他们的面貌、姿态、理想、抱负和创造力都是崭新的”;其三,“要叙述新的故事”。文中所体现的剧作家戏剧观念的板结、陈旧不仅仅表现在对“新”的意义的阐释与理解的片面上,还表现在他对以往创作道路的回顾上。崔德志还未能认识到陈旧的戏剧观念对自己艺术想象力的束缚,他所说的创新,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为政治服务改成为现行的政策方针服务;在人物塑造上把过去塑造“阶级斗争中的勇士”改为塑造“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代新人”,所谓“叙述新的故事”,也不过是把现时的思想内容填进陈旧的戏剧结构的框架,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创新与突破。诸如此类的表述,在当时决非出自崔德志一人一文。由此可见,这一代剧作家们的主体意识还远未被唤醒。在戏剧文本的创作过程中,他们仍旧从先验的理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用观念演绎生活,而非从生活中提炼出富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在戏剧结构的安排上,用观念的冲突代替戏剧的冲突,并围绕观念的冲突设置戏剧人物,编排戏剧情节;戏剧人物缺乏鲜活的生命激情和内在的生活依据,只是表达剧作家观念的符号。从总体上说,新时期初年所涌现的大量戏剧作品是政治的戏剧而非审美的戏剧,因而,随着作为戏剧接受者的观众政治感情的逐渐冷却,共鸣的消失及接纳这类作品的总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改变,这类作品彻底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早已潜在的戏剧危机便显露出来。
戏剧危机所唤起的是一代剧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的重新发现。沙叶新开始了痛切而深刻的自我反思:
“我总感到我们这一代已步入中年的作家,有太多的责任感,有太多的使命感,……每每动笔,总是为时为事,忧国忧民,按另一种说法就是总要干预生活,这样就使得我们的作品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作品是严肃的,是忠诚的,是白居易式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品(应该说是我的作品),又有太多的理念,太多的教训,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社会内容。”[②]
沙叶新无时不在“情”与“理”,“载道”与审美之间寻求着平衡;他既不愿放弃自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不忍丢弃艺术品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审美品格。为此,他艰难地跋涉在戏剧艺术的领地中,却怎么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乐园,他一次又一次地调整着自己的审美视点。新时期初年,沙叶新先后创作《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剧。“其实这两出戏本意是一样的,一个是告诉人们共产党员不应怎样,一个是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怎样,按照过去的文学术语来说,一个是批判的,一个是歌颂的。”[③]显然,这两部剧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但比之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沙叶新通过他的艺术较为间接地而非直接地为政治服务,他的作品也决非简单被动地录制现实,而是凝聚了剧作家的审美激情。《陈毅市长》采用“冰糖葫芦串”式的结构,从多方面刻画出具有丰富性格内涵的陈毅市长形象。《假如我是真的》则用精巧的构思,泼辣犀利的戏剧语言,讽刺了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此二剧中,沙叶新初步展示了其剧作诗与政论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创作于1983年的《马克思秘史》一剧,诗情与哲理得到了进一步的结合,剧作家力图“完全按照历史的真实,以淳朴的本色把历史人物描绘出来,而不要象资产阶级史学家那样,给自己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某种圣像式的形象——“脚穿厚底靴,头绕灵光圈”,不仅如此,他还将在“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背后消失了,至少是模糊不清了”的“作为人的马克思”的“特有性格、内心世界、个人情感”写了出来,从而塑造了血肉丰满,具有丰富性格内涵的马克思形象。从《陈毅市长》到《马克思秘史》,标志着作为剧作家的沙叶新的逐渐成熟,也充分显示了他塑造戏剧人物,驾驭戏剧语言方面的杰出的艺术才能。然而,借历史人物寄托剧作家对社会、历史、人生问题的思考,对于沙叶新这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剧作家来说,毕竟太不便捷,他希望直接干预现实的社会生活。1986年,沙叶新创作了《寻找男子汉》,将自己的审美视角由历史人物转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剧中,他借舒欢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的一系列遭遇,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思考。他的思考是深刻而独到的,然而,他却未能把自己的思考凝聚为富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而是过多地将舒欢从剧中人的地位中拉出来,充当剧作家的代言人与评判者,致使全剧理胜于辞,大大冲淡了全剧的艺术韵味。与其说《寻找男子汉》是话剧,不如说它更象一部关于“中国男子阳刚之气失落及其原因”的社会学论文。
纵观沙叶新十年的戏剧道路,笔者认为,他并不是不曾找到过自己的艺术平衡。当现实的社会生活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使他从历史中而不是从现实中孕育诗情的时候,他的创作态度较为客观冷静。对于他所描写的生活,他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因而他能从总体上把握生活,巧妙地将哲理意蕴凝聚于具体的戏剧形象中去。可是,一旦他接触到具体的社会问题,那蓬勃的创作激情便如岩浆一般地喷涌出来,他有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受要借戏剧这个喷发口喷发。因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他过多地致力于哲理的思索而忽视了艺术的创造,致使剧作减弱了戏剧的审美品格,而过多的哲理内容也必然无所依附。沙叶新在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李杰也开始对自己以往走过的艺术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索:
“不知从何时开始,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缠绕着我:每当拿起笔来进入创作的时候,我便不会思考,大脑只会机械地把现成的结论化妆成‘形象’,七彩的生活顿时变得单调而板滞,一切都划归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营垒内,一切与此无关的社会人生和心理精神现象统统被拒之在戏剧创作之外,戏剧的审美实质被宣传的目的所替代,于是互相仿制代替了创造,人与生活只是某种意念的诠释和佐证。内涵贫弱的形象丝毫不能唤起人们的审美期待,于是作为艺术的戏剧轰轰烈烈地陷入危机。”[④]
他早期的剧作,如《海》《父子恨》《遗嘱》等剧,便是这种“神奇的魔力”缠绕的结果。在这些剧作中,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被简约成敌我相对的两大阵营,剧作家围绕这两大阵营结构矛盾,构筑冲突。《高梁红了》一剧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所开掘,注意在斗争中刻划出具有丰富性格内涵的人物形象,但戏剧人物仍被分为尖锐对立的两大营垒,具有明显的概念化的痕迹。此后,他调整了自己的审美视角,彻底沉入到生活中去,努力从纷纭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去挖掘富有诗情与哲理意义的戏剧意象。在《田野又是青纱帐》一剧中,他以东北某农村为背景,以富有关东风情的描写,塑造了在改革的时代幕布透视下的农民群像,充分显示了农村社会各色人等面对改革的不同心态。虽然李杰摆脱了前期作品中围绕现实矛盾冲突构筑两大对立的营垒之间的戏剧结构方式,但由于剧作家过多地着墨于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冲击与碰撞,戏剧人物还未完全从承载剧作家观念载体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对戏剧人物心理世界的挖掘也不免流于肤浅与表面化。到《古塔街》一剧,李杰彻底转变了创作方向,他不再从政治、社会或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他笔下的戏剧人物,而是从生活出发,将生活孕育出的艺术激情融化为具有审美意义的戏剧意象。《古塔街》一剧以深刻细腻的现实主义笔法,富有关东风情的艺术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古塔街的儿女们几十年来饱经沧桑的人生故事。全剧将诗意化的象征意蕴和对现实人生的挖掘,抒情与哲理结合起来,形成了李杰剧作特有的艺术风格。李杰经过十几年艺术上的探索之路,终于完成了艺术上蜕旧变新的历程,从而彻底摆脱了那个萦绕已久的心灵上的魔影,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艺术园地。
个案剖析的目的是为了由个别窥见一般。沙叶新、李杰的蜕变过程,在新时期戏剧史上是有典型意义的。中年剧作家大都经历了相同的“蜕变”过程,或快或慢地完成了艺术上的转型。但具体的“蜕变”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个中酸辛,只有经历过那场“蜕变”的剧作家本人感受最深。如果不了解他们“蜕变”过程中心灵的颤栗,就无法从根本上了解这一代剧作家。梁秉坤的自述,使笔者得以更进一步地与中年一代剧作家进行了心灵的交流:
“也许,在我们这些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作者当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在道理上完全赞成破除陈旧的戏剧观念,并且也十分欣 赏那些在新的戏剧观念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然而,当自己拿起笔来的时候,旧的戏剧观念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你紧紧捆住,使你难以摆脱。比如,这次写《阵痛的时刻》,开始结构提纲的时候,一下子就相当自然地,甚至是相当自如地想出个‘只写事件不写人’的‘方案之争’来。难道是怕什么吗——不是的。完全是因为轻车熟路,被一种习惯势力所驱使。”[⑤]
这段文字,真实地表现了一代剧作家从理论上认同了新的戏剧观念,但在创作实践上对旧有的创作模式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与尴尬处境。这种矛盾现象,不但反映在梁秉坤的剧作中,也反映在沙叶新、李杰和郝国忱等大部分剧作家的剧作中。毕竟传统的戏剧观念、美学观念所形成的剧作家的心理思维定势与审美感知方式还不能随着一种新的理论的接受而彻底转向,因而,这一代的剧作家只能缓慢地蹒跚在戏剧探索的道路上,旧的戏剧观念还不时为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以致他们的创作时常呈现出徘徊状态,从而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戏剧发展的总体趋向。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中年剧作家们在历史变革时期所扮演的特殊的悲剧角色,有必要把这一代剧作家置于与青年一代剧作家的对比中加以观照与剖析。李龙云、赵耀民、杨利民、贾鸿源、马中骏、方洪友、王承刚等在新时期崭露头角的剧作家们大都生于五十年代,在“文革”中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后又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卷入农村、边疆,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文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进入高校,得以进行系统的专业训练。而其时,西方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人文思潮和文学、戏剧思潮正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他们是在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坏境和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中步入剧坛的。较之中年一代的剧作家,他们更少传统的因袭,因而,在他们开始创作之初便是以审美的视角而非政治的或伦理的视角切入生活的;他们无意于围绕着鲜明的政治主题构筑矛盾冲突,设置戏剧人物,而是努力从生活中孕育自己的艺术激情,并将之凝聚为饱含哲理意蕴的戏剧意象,构筑起丰富深邃的艺术世界;在戏剧史的总体流程中,他们不皈依于某一戏剧思潮或流派,而是努力追求并实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开拓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李龙云把创作比作“人的生命的流程”[⑥],“作品完成了,显示作家的一次存在,一个自我的完成”[⑦],因而他们所构筑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李龙云那具有浓郁的北京市民风俗的“小井”世界;赵耀民夸张怪诞的笔调勾勒出的大都市的世态人生;杨利民豪放粗犷的北国荒原中的男子汉群雕,贾鸿源、马中骏笔下那具有浓郁抒情气息的小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无不凝聚着剧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审美发现。新时期初年,中年剧作家们还在满怀激情地用陈旧的戏剧观念创作社会问题剧之时,青年剧作家们已向剧坛呈现出一批形态各异、风格不同的戏剧佳作,丰富了新时期的戏剧创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把戏剧当作政治的奴仆,恢复了戏剧的审美品格,为新时期戏剧史增添了新的因素。
青年剧作家们起步之初便站在一个高于中年剧作家的起点上,因而,他们无须经历那番撕心裂肺的艺术上的“蜕变”过程便接近了戏剧的本质。在中年一代剧作家经历着“蜕变”的心路历程之时,他们能潜心于艺术的不断追求与完善。李龙云《小井胡同》的结构安排及浓郁的北京风情描写明显受了老舍《茶馆》的影响,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把民族化的美学风格作为自己自觉的美学追求。他说:“就我的感觉,塑造典型的中国人,用中国人特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情感、精神,这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着眼点。”[⑧]“我甚至想过,创造中国气派话剧的出路,或许是话剧与戏曲在某种意义上的合流,是古典戏曲与西洋话剧的远缘杂交,这种杂交决不仅仅是表演形式上一招一式的粘贴。古老的戏曲需要当代世界文明蓬勃精力的刺激,而引进来的话剧则需要化为中国所有。”[⑨]作为一个作家,李龙云决不会仅仅把自己的思考局限于理论上。实际上,关于话剧民族化的这些思考,既是他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创作的展望。如果说,写作《小井胡同》一剧时的李龙云还处于对老舍《茶馆》一剧的模仿阶段,那么,到《荒原与人》一剧,李龙云则努力从前人的经验中完成了对自我的重塑过程,进入了艺术上的自由王国。在《荒原与人》中,李龙云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散文化的结构方式和“写意化”的美学格调,通过青春与美的毁灭从人的本质意义上对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处境作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从《小井胡同》到《荒原与人》,李龙云不断地超越着自我,“习剧十五年”[⑩]他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着自己的戏剧艺术之路。赵耀民幽默、冷峻的气质使他更多从哲学的角度把握社会人生,并以夸张的笔调,怪诞的艺术手法将他对人生的哲理思索表现出来。以荒诞的形式写出生活的本质真实,以喜剧的笔调写出悲剧的实质是他戏剧创作的主要特色。《街头小夜曲》《天才与疯子》(又称《灰色浪漫史》)、《红马》《琴声又起》等剧,无不渗透了剧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感悟。贾鸿源、马中骏在他们创作之初便开始尝试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表现手法,“《屋外有热流》是通过不合常理颇含怪诞的戏剧冲突展现于舞台的。我们试图以虚拟来反映现实,用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手法来使观众入戏,思考,通过观众与我们的共同创作来完成剧本所想表达的主题,”[(11)]在他们以后所创作的《路》《街上流行红裙子》《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与秦培春合作)、《汽球游戏》等剧作中,努力追求在整体上运用现实主义戏剧手法的同时营造象征意蕴及现实与象征、诗情与哲理的结合。杨利民、方洪友等剧作家尽管在创作之初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陈旧戏剧观念的影响,但他们没有经历中年剧作家们的“蜕变”过程便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艺术视角,由表现外在的戏剧行为和观念冲突向人物的心灵深处拓展,分别向剧坛奉献出《黑色的石头》《大雪地》《大荒野》以及《胡同里的月光》《幸运女神》等较为优秀的剧作。总之,无论是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之深度还是艺术表现之丰富,青年剧作家及其剧作都明显优于中年一代的剧作家及其剧作。应该说,是青年一代剧作家促成了新时期戏剧创作的较为繁荣的局面,使新时期戏剧在戏剧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笔者作出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要在两代剧作家之间分出优劣,更无意于对中年一代剧作家求全责备。事实上,作为历史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在戏剧史上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完成了艰难的“蜕变”历程,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与进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和青年剧作家一起,勾勒出新时期戏剧发展的总体风貌。“蜕变”后的作家,也为剧坛奉献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如李杰《古塔街》、郝国忱《榆树屯风情》《扎龙屯》,锦云《狗儿爷涅盘》等作品,足堪与青年剧作家的剧作相媲美。本文之所以把中年剧作家及其“蜕变”过程作为一个戏剧现象加以研究、剖析,旨在从剧作家与时代这一特殊的角度对政治与戏剧的关系问题作出思考。如果说,儒家“文以载道”的美学观念已形成源远流长的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戏剧史上则更为明显。从晚清的戏剧改良到文明新戏的引进,从易卜生的介绍到无产阶级戏剧,从五、六十年代的“三突出”,“演中心”到新时期初年的社会问题剧,无不把戏剧的功利目的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戏剧逐渐沦为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丧失了其审美品格,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艺术个性也逐渐消泯了。时代造就了一代剧作家的悲剧命运,他们不得不为时代与历史付出沉重的代价。往事已矣,但对一代剧作家所经历的特殊的心路历程作出理论上的思考与探讨,以呼唤审美的戏剧时代的到来,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崔德志《创作要有个新的突破》,《剧本》1982年第11期。
(23)沙叶新《关于我的五个剧本》,《文艺理论家》1988年第1期。
④李杰《我的所失,便是所得》,《新剧本》1987年第2期。
⑤梁秉坤《遗憾者的话——致友人的信》,《剧本》1984年第10期。
⑥⑦《追求、探索和奋进——话剧剧本讨论会剪影》,《剧本》1987年第1期。
⑧⑨⑩李龙云《学习·思索·追求——习剧十五年漫笔》,《小井风波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1)贾鸿源、马中骏《写〈屋外有热流〉的探索与思考》,《剧本》1980年第6期。
